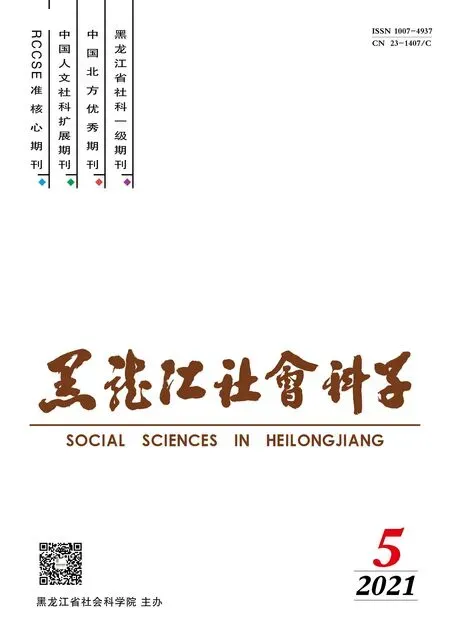儒家思想的開展
——以“忠恕”轉型為中心的思考
張 義 生
(青島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山東 青島 266071)
儒家思想發展于當代,必須思考如何與現代社會相結合,因為儒家思想除了具有某些超越性的價值和理念外,還有一部分內容是與傳統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環境相適應的,并不適應于現代社會。如以儒家“忠恕”思想為例,從本源上來說,“忠,敬也。從心,中聲”[1]217,忠的含義主要為敬;而“恕,仁也。從心,如聲”[1]218,恕的含義主要為仁。但是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歷代儒家學者對忠恕的內容和價值進行了不同的闡釋和延伸。隨著時代的推進,傳統社會秩序產生了深刻的變化,由此,儒家傳統忠恕觀面臨著時代的挑戰。我們要對儒家的忠恕思想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革故鼎新,只有這樣,才能使其適應時代的發展。
一
概括而言,儒家忠恕思想具有以下三個特點。
第一,忠恕以為仁成圣作為價值追求。孔子作為儒家的創始人,首次提出了忠恕思想,在《中庸》有“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的記載。但將忠恕思想視之為孔子核心思想的是孔子的弟子曾參,他說:“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認為孔子之道即為忠恕,實際上將孔子的仁道與忠恕等同起來,而為仁成圣就是忠恕的價值追求。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后代儒家學者對忠恕價值追求的闡釋。
第二,忠恕以盡己為忠為主要內容。雖然在孔子及其弟子曾子的思想中,忠和恕兩者的地位是等同的,但以程朱理學為代表,儒家學者提出了忠體恕用的看法,其認為忠是體,恕是用,本體是第一性的,而作用是第二性的。如“程子曰: ‘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又曰:‘維天之命,于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2]72-73朱熹亦言:“忠者,盡己之心,無少偽妄。以其必于此而本焉,故曰‘道之體’。恕者,推己及物,各得所欲,以其必由是而之焉,故曰‘道之用’。”[3]在他們看來,忠是本體,恕是作用,忠是內——盡己之心,恕是外——推己及物。而理學家們雖然在體用關系上倡導體用合一、體用不二,但是將兩者比較而言,他們更重視體,因此在忠恕范疇中,也就更重視作為體的“忠”。
第三,忠恕以推己及人為實現方式和表現。“恕”的含義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忠”的含義在程朱看來是“盡己之心”,程朱認為只有先盡己之心,才能行“推己及人”之“恕”,這實際上是將“忠”階段上的心之所得,在“恕”階段上推之于人,這種推己及人是一種積極的狀態和表現。王夫之對理學忠恕思想展開反思,他與程朱理學不同,認為“恕”是將己所不欲不推之于人,而推己及人則是一種消極的表現。他說:“吾反覆思之,其唯恕而可乎!如吾心而直行之,無迂回也;推吾心而廣通之,無阻礙也。吾之情不廢,而天下之理不爽,庶乎其以常以變,而各得其常,以順以逆,而皆成乎順,則終身行焉,其可以乎!夫恕者,推己之心以量物之心,而予之者也。己有欲矣,有不欲矣,將何所推也?質異而情亦異,一人之所嗜,不能以齊之數人;道不同而志不同,賢智之所樂,不能以強之愚不肖;故恕者不于己之所欲推之,而于己所不欲推之也。”[4]王夫之深刻反思了以恕為推己之欲及于人之欲的做法,認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求,不能因為一個人的喜好,就強加于他人,也不能因為賢明聰明的人喜歡,就強加給愚笨不道德的人,他因此得出“恕者不于己之所欲推之,而于己所不欲推之”的結論,這種觀點實際上是對程朱理學將“推己及人”看作“恕”的一種反思。當然,從這一角度來看,在程朱和王夫之那里,忠恕思想都是以推己及人為方法表現的。
二
近代以來,學者們也力圖對儒家的忠恕思想作出新的詮釋。
其一,馮友蘭認為忠恕是為仁之方。在《中國哲學史》一書中,馮友蘭說:“‘因己之欲,推以知人之欲’,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即所謂忠也。‘因己之不欲,推以知人之不欲’,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所謂恕也。實行忠恕即實行仁。”[5]他認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為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為恕,這就與宋明理學家的盡己為忠區別開來。更重要的是,馮友蘭認為“忠恕”是“為仁之方”,并不是仁本身。他說:“仁這種品質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這也是‘忠恕之道’。這還不是‘仁’,這只是‘為仁之方’,就是說,這是達到仁的品質的方法。照著這個方法所達到的品質,才是‘仁’。”[6]他認為,忠恕之道并不是仁,而只是到達仁的方法而已,兩者之間是有區別的。
其二,牟宗三認為,“仁道之真實而落實之工夫”為忠恕。他說:“蓋孔子之真生命即在‘仁’,體現仁之真實而落實之工夫在忠恕(或至少從忠恕說亦無妨)。”[7]232又說:“一貫之實即仁道,體現仁道之真實而落實之工夫為忠恕。”[7]233從這個角度看,忠恕即是仁道真實性的體現,也是仁道的落實工夫。從一以貫之的角度來看,牟宗三甚至認為“離開仁心仁道,無有足以一貫之者。以忠恕說一貫,即是以仁道說一貫”[7]232。牟宗三實際上認為忠恕即是仁心,也是仁道。仁心即是“忠以盡己”,也即仁道之真實,此為內圣;仁道即是“恕以及人”,也即落實之工夫,此為外王。仁一以貫之,忠恕一以貫之。
其三,錢穆認為忠恕人人可為。他說:“而言忠恕,則較言仁更使人易曉。因仁者至高之德,而忠恕則是學者當下之工夫,人人可以盡力也。”[8]92他還說:“孔子好學不厭,是欲立欲達也。誨人不倦,是立人達人也。此心已是仁,行此亦即是仁道,此則固是人人可行也。”[8]155又說:“子曰:吾欲仁,斯仁至,此以心言,不以行言。仁之為道,非咄嗟可冀也。只一恕字當下便可完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驟看若消極,但當下便是,推此心而仁道在其中矣。故可終身行之也。”[8]386其反復強調忠恕之道雖然就是仁道,但相較于仁道,忠恕之道則簡單易曉、學習者易行、當下便是、人人都可以做到,這就擴大了忠恕主體的范疇,使其不僅僅局限于具有崇高道德品質的君子。近現代學者相較于傳統儒家學者,對忠恕思想作出了新的闡釋,十分具有啟發意義。
三
現代社會與傳統封建社會的一個很大區別,則是在經濟制度發生根本性變化的基礎上,專制制度被民主制度所取代,宗法等級制崩潰消失,平等自由的觀念深入人心。因此,若使儒家的忠恕思想適應于現代社會,就必須對其進行創造性的轉化,使之符合現代社會制度及觀念。
首先,忠恕思想應以人與人平等為前提。一方面,雖然“忠”的含義是“盡己之心”,其對象是廣泛的,如強調對君主要“臣事君以忠”,對朋友要“忠告而善導之”,但在宗法等級制下,忠恕思想所強調的內容最終集中于對君、父、夫的忠,尤其受封建君主專制制度的影響,傳統封建社會對忠君思想的闡發尤多。如唐太宗說:“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即君主所作所為可以有誤,但臣下必須對君主盡忠。宋代的司馬光認為“臣之事君,有死無二,此人道之大倫也”,將臣子對君主的盡忠,推到了極點,臣子以生命事君則成為封建時代的人倫大道。而程朱的忠體恕用實際上過于強調“忠”,尤其是“盡己為忠”,既承接了封建社會忠君的主流思想,又在一定程度上為忠君思想進行了理論上的論證,進而鞏固加強了忠君觀念。這種以君臣等級觀念為主的忠,以人格上的不平等為前提,在君主制度消失后,已經失去了存在的依據,而當代則應發掘和提倡儒家忠恕思想中具有平等性的內容。另一方面,儒家“忠恕”思想,實際上仍然存在著一種“先知覺后知,先覺覺后覺”的道德優越感,強調的是道德高尚的士人君子對“百姓小人”進行幫助,以及兩者先天存在著等級上的差異。雖然忠恕是踐行仁的方法,但是由于“仁”是“愛有差等,施由親始”,所以即使是君子對小人的“推己及人”,也不可避免地帶有差等思想。這種差等思想顯然也是有違現代社會所提倡的機會平等和權利平等,因此需要在公共領域實現忠恕觀念從差等向平等的轉變。
其次,對忠恕的實施方式應是雙向的。傳統儒家的忠恕思想,其實施方式往往是單向的。如君臣、夫妻之“忠”,僅僅強調臣下對君主、妻子對丈夫單方面的責任和義務,對君主和丈夫的要求和限制則少之又少,這同樣與當今時代所提倡的權利平等不相適應。雖然封建社會的君臣關系消亡了,但是夫妻關系仍然存在,這就需要對夫妻關系進行創造性轉化,將其中的責任和義務由單向轉變為雙向。
在夫妻關系上,不能僅僅強調妻子的責任和義務,還要強調夫妻權利義務的對等,實現夫妻家庭地位的平等。近代以來,女性的地位不斷提高,已經在法律上保障了婦女享有與男子平等的各種權利。尤其在家庭關系中,與傳統封建社會不同的是,婦女有婚姻自主權、對夫妻共有財產的處分權、對未成年子女的平等監護權,等等,應該看到這已經從根源上保證了夫妻雙方責任義務的平等,因而不可能一方只享有權利而不盡義務。因此,傳統儒家忠恕思想在家庭夫妻關系上就必須進行創造性轉化,從強調妻子的單向責任和義務,轉為提倡夫妻之間雙向的責任和義務,這才能適應當今時代的要求。
對于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同樣也要求權利和義務的對等 。因為傳統儒家忠恕觀是以仁愛成圣為目標,提倡愛自己的親人朋友,逐漸擴大至愛所有人,這也是推己及人的方法和表現,即將個體之愛推向除我之外的所有人。但是,儒家所強調的推己及人,也往往是單向的,即僅僅注重主體自身的責任,也就是孔子所說的“我欲仁,斯仁至矣”“為人由己,而由人乎哉”,而這對于忠恕所加諸對象的責任義務卻并未涉及,這同樣是基于傳統儒家將推己及人的主體主要限定為君子士人,將其對象主要限定為小人百姓,在這種情況下,兩者在地位上是不平等的。這種觀念在人人平等的當代社會,自然也是不合時宜的。現代社會對公民基本道德規范的要求是雙向的,即互相誠實、互相守信、互相友愛、互相尊重、互相關心、互相幫助,如果僅僅是單向的要求,那么誠信和友愛的新型人際關系是無法建立起來的。因此,如果將儒家忠恕思想運用于處理現代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需要對其進行創造性的轉化,從強調個體單方面的推己及人、仁愛待人,轉型為提倡人與人之間雙向的推己及人、誠信友善。
最后,對忠恕的踐行應貫穿于日常行為活動之中——對忠恕的踐行是進行式的。對傳統儒家忠恕思想的踐行,通常是以“盡心之忠”為前提的,按照程朱理學“忠體恕用”的觀點,就是要先解決內圣修養,然后才能做外王功夫,其過于強調忠恕實踐主體的道德性。朱熹在注解《大學》“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一句時說,“有善于己,然后可以責人之善;無惡于己,然后可以正人之惡。皆推己以及人,所謂恕也”[2]9,可見傳統儒家將主體的道德完善,作為實現忠恕的前提。這種情況下,在無形之中剝奪了部分人踐行忠恕的可能性,因為現實中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成為道德至善的圣人,人們通常只能處在不斷實現道德完善的過程之中。因此,也只有如錢穆所說的忠恕是“學者當下,人人可以盡力也”,忠恕“人人可為”,才能盡可能多地使人們踐行忠恕。由此可見,對忠恕的踐行是在道德修養的過程中實現的。
如果忠恕不要求實踐主體的道德性,那如,其又何保證推己及人的合理性呢?從儒家自身的理論來看,至少存在著兩方面的約束。一是內在約束,即“良知良能”。良知知善知惡,自然能夠使人在推己及人的過程中向善避惡。二是外在約束,即禮制刑法。它會對不合理的推己及人進行懲罰,從而產生一定的制止和警示作用。傳統儒家學者往往較多地從良知角度入手來保證推己及人的合理性,對外在監督和制約的關注則相對較少。在現代社會,基本可以依靠健全的法律體系保證忠恕推己及人的合理性。一方面,現行法律所規定的刑罰,會對忠恕實踐主體產生心理威懾,預防不合理的推己及人的發生;另一方面,觸犯法律后的處罰,又具有一定的糾錯功能和示范效應,這都會使忠恕的實踐主體在道德不完善的情況下保證推己及人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