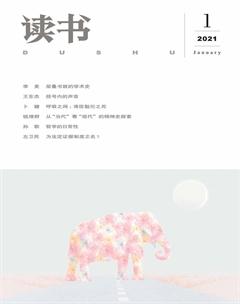閱讀埃菲爾鐵塔
畢唯樂
在羅蘭·巴特的著述中,《埃菲爾鐵塔》是獨特的:其中的大部分文字起初是安德烈·馬爾丁(Andre Martin)攝影集《埃菲爾鐵塔》(La Tour Eiffel,一九六四)的解說詞,直到一九八九年影集再版,全文才正式刊出。與生俱來的“附屬”性,注定了《埃菲爾鐵塔》在學術研究中的邊緣位置,學者們幾乎不談論它,只為它草草貼上若干標簽——從“社會神話研究”到“符號學”的過渡期作品,符號學和結構主義分析,等等。高度的文本自足、抒情的散文體裁,無一不凸顯著《埃菲爾鐵塔》的“非理論性”,但從學術寫作的“技巧”看,《埃菲爾鐵塔》恰恰是羅蘭·巴特最精妙的作品,是人們進入其思想空間的絕佳導引。
“技巧”或許是巴特作品成為“巴特體”的理由。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有本名叫《羅蘭·巴特輕松學》(Le Roland-Barthes sarispeine)的小書曾在法國風靡一時,兩位作者稱,羅蘭·巴特是“一門通用語”(un langageuniversel),讀者可以通過他們編寫的十八課(文字游戲、似是而非等)來輕松掌握這門“語言”。這番戲謔淋漓盡致地展現出“巴特體”的時髦、可辨。“巴特體”的流行源于巴特的公共寫作:一九五四至一九五六年,巴特每個月都會為《新文學》(Les Lettresnouvelles)的“本月神話”欄目撰寫短評,這些文章后來略加修訂,和長文《今日神話》一起結集出版,成了大名鼎鼎的《神話學))。人們一向認為,《神話學》是巴特最有趣、最好讀的作品,《埃菲爾鐵塔》的寫作風格與之一脈相承。
可以說,“神話學”和“符號學”是“巴特體”可辨識度的根源,也是讀者進入《埃菲爾鐵塔》的兩大關鍵。“神話”一詞在全文中共出現了十八次,而且幾乎都是偏離日常語義的巴特式“神話”,能否準確理解這些“神話”,決定了人們能否走進巴特的紙上巴黎。何謂“神話”?巴特的回答是:“神話就是一種言說方式(措辭、言語表達方式,le mytheestune parole)。”概言之,“神話”是一種有待破解的幻象,是社會生活中一種旨在淡化意識形態的文化編碼。通過制造“神話”,文化將自身呈現為合乎自然的樣貌。因此,“神話學”的任務就是“解碼”與“祛魅”,它要刺穿資產階級的日常生活細節,在譏嘲中讓司空見慣的意義現出原形,把讀者從一個個“神話”中拖拽出來。
《埃菲爾鐵塔》也是以符號學“譯解”現代建筑及城市空間的典范。巴特的“神話學”本身便深蘊符號學旨趣:神話的研究屬于符號學,神話是一種意指形式、一個次生符號學系統,其能指因含混的呈現方式而具有二重性,神話本身就是一種扭曲。巴特說,“符號學是一門形式科學,因為它研究意義,而不管意義的內容”,因此,符號學的對立面就是作為“歷史科學”的意識形態。不過,巴特的鐵塔分析所依托的,更像是一種為社會學服務的符號學,它旨在讓不同學科的目光形成充分互動。
如上種種,決定了須臾不離“想象”的《埃菲爾鐵塔》具有格外縝密的結構。整篇散文仿佛一個精巧的語法系統,連開場辭都是苦心經營的。有趣的是,現有的兩種中譯對全文首句的處理頗不相同。懷宇譯作:
莫泊桑曾經常在埃菲爾鐵塔餐廳上用午餐,然而他卻不喜歡鐵塔。
李幼蒸譯作:
莫泊桑常在埃菲爾鐵塔上用午餐,雖然他并不喜歡那里的菜肴。
這句話的原文是:“Maupassantdejeunaitsouvent au restaurant de laTour.et pourtantil ne laimait pas.”兩種譯法的主要分歧在于,被省音的代詞“l”究竟指代什么。懷宇認為那是陰性代詞“la”,指代“la Tour”(鐵塔),李幼蒸似乎受英譯影響,認為它指代“dejeuner”(午餐)。緊接著這句話的是:“他常說,這是巴黎唯一一處不是非得看見鐵塔的地方。”因而從上下文看,李譯更為妥帖——俏皮如巴特,絕不會贅言“不喜歡鐵塔”。但確切說來,這里的“l”即陽性代詞“le”,指代“le restaurant dela Tour”(鐵塔餐廳),說的是莫泊桑總愛造訪那家自己不喜歡的餐廳。于是,這篇妙趣橫生的鐵塔贊辭就在“l”的指稱游移中徐徐展開了。
在巴黎,“鐵塔午餐”是個家喻戶曉的都市傳說,據說來自莫泊桑與一名記者的塔上對話。作為《反對修建埃菲爾鐵塔》抗議書的簽署人之一,莫泊桑簡直可以代表那一代厭惡鐵塔的法國高知。因此,巴特的開場辭不僅暗示了關于鐵塔的“悖論”(要在視線上遠離,必先與之合一),還暗示了傳統與現代、藝術與科技之間的沖突。而這兩點,恰恰是巴特“譯解”鐵塔的核心。
《埃菲爾鐵塔》運思的嚴密工整,與其修辭的隨性變幻大異其趣。循“目光一物體一象征”的線索,巴特首先將鐵塔展陳為“自然現象”和“法國象征”,這是人們最熟悉的“目光”:鐵塔無處不在。旋即,巴特式“目光”使鐵塔成為具有各種“二重性”的復合體:它是含義無窮的“空能指”,是既“會看”又“被看”的完全之物,是空洞無用的紀念塔(“達到了紀念塔的某種‘零狀態”),是徹底背叛傳統審美的“藝術品”,是全無可看之物的“旅游勝地”……巴特的文化隨筆往往比理論著述更顯高明,因為前者才是敏銳洞察力的最佳歸宿。他寫道:“建筑物永遠既是夢想物又是功能的體現者,既是某種空幻之表現,又是某種被使用的工具,這種雙向運動卻具有十分深刻的意義。”(4頁)這短短的一句,卻已包含后文結構分析的全部邏輯生長點。
從天馬行空的意指運作落回喧囂熙攘的觀光人群,問題隨之而來:“我們為什么要去參觀埃菲爾鐵塔?”(6頁)巴特給出的理由是,鐵塔是夢幻的“凝聚器”——這個關鍵的隱喻可謂全文樞紐。鐵塔首先是“目光”,目光的內與外,就是對鐵塔的遠眺與回望。游客憑鐵塔向外眺望,都市空間及其人性況味立刻轉化為新的“自然景象”,而這幅鳥瞰圖景給觀者一種“結構”的心智樣式。這種“破譯”思維使巴黎的地理、歷史、社會結構成了可讀的“文本”:“每一位鐵塔的游覽者都在不知不覺中實踐著結構主義。”(9頁)“它所聚攏的正是首都的這一本質,并將其贈予向它奉獻自己‘入族禮的外來者。”(14頁)鐵塔是“閱讀”巴黎的目光,是理智力量與宗教儀式的復合。
覽勝與祭禮的交織也在向內的目光(回望鐵塔)中發生,紀念性建筑的參觀活動既是“解謎”,也是“占有”。鐵塔的獨特之處在于,它不是傳統的封閉空間,觀光者“寄身其中”又“不在其內”,而是穿行其間。在巴特看來,鐵塔為現代旅行者的想象力提供了廣闊的活動空間,它不僅呈現了外觀和現實之間的奇觀化對比,也用商業網點編織了一個親切的“小世界”。游客雖然暫時與世隔絕,但仍然是整個世界的主人,鐵塔重新統一了人類生活場所的全部功能。
在一九六四年的影集中,解說詞結束于鐵塔“目光”的凝望。作為圖冊的配文,“目光”的分析已然足夠,但只有鐵塔成為“物體”和“象征”,巴特才成為巴特。關于“物體”的分析是一個中介:“鐵塔,在被包圍的物體(如我們剛描述過的)和一般的象征(我們馬上會談到的)之間,發展了一種中間性質的功能,即歷史性物體的功能。”(19頁)作為“物”,鐵塔首先是它的材質——鋼鐵。鋼材實現了人類“千尺巨塔”的夢想,讓冶金、交通、民主的觀念征服了世界。鐵塔是“一座直立的橋”(22頁),它把巴黎所有傳統與現代的意象人性化地串聯起來。最重要的是,鐵塔預示了一種即將征服未來的全新觀念——“功能美”:
功能美并不存在于一種功能所產生的美好“結果”之中,而是存在于該功能之景象本身;此景象是在生產它之前就可感受到的。感覺一部機械或一個建筑物的功能美時,大致來說就是使時間暫停,延緩使用,以審視其制造作用(fabrication):在此我們進入一種非常具有現代性的價值體內,后者是圍繞著人類作為(faire)概念而形成的。(25頁)
“功能美”后來成了設計美學中的重要概念,它雖誕生于發達工業時代,其內核卻頗為古典,一如巴特游離于傳統與現代間的暖昧姿態。“功能美”中隱含的非功利性、合目的性,甚至能讓人窺見古典美學的痕跡。巴特認為,鐵塔的美源于某種預見力:后人仍能從“成品”中享受“造術”的審美價值,它那革命性的裝配、結構化的性質,完美地保留在成千上萬的微型復制品中。征服自然的鐵塔終將征服時間,終將使莫泊桑的抗拒消散在巴特的贊詞之中。
但鐵塔最強大的生命力在于“象征”。從鐵塔無窮無盡的隱喻中,巴特剝離出了一條指涉鏈:從法國大革命、工業繁榮,到巴黎、旅游、現代、創新,到高度、飛翔、輕盈、鏤空,再到植物、動物、人、性別,最終指向不可逾越的經驗——界限和死亡。在這個率性的“意指游戲”中,最深刻的一環是象征“有限”的“死亡”,它恰恰源于鐵塔形象的絕對和純粹。而無限延伸的想象、永恒開放的隱喻,又恰恰揭示了人類真正的自由:“因為任何歷史,不論多么令人悲嘆,都永遠不可能消除想象的自由。”(33頁)
《埃菲爾鐵塔》寫就之時,這座飽經戰火洗禮的“紀念碑”剛剛被列入法國歷史遺跡增補清單。正如亨利·盧瓦雷特所言:“羅蘭·巴特的溢美之詞遠勝工程師和建筑史學家們洋洋萬言的辯護詞,消除了在此之前一直糾纏不休的異議,埃菲爾鐵塔就此獲得于斯曼口中所謂‘高雅人士的最終認可。”《埃菲爾鐵塔》對學界的意義或許遠不及對法蘭西的意義,但純熟的寫作技藝使它事實上成為巴特的“無冕”代表作和“入門”必讀書:文選《埃菲爾鐵塔及其他神話學》(The EiffelTower,and Other Mythologies)將它與諸多“神話學研究”合編,桑塔格編輯《巴特文選》(A BarthesReader)時也將它置于首篇。
巴特這一時期的寫作帶有些許“咖啡館哲學”的特征,批評者稱它們是缺乏理論深度的文辭游戲。但不可忽視的是,自如的跨學科運思、精湛的分析“配置”,恰恰打開了所有“文本”共同面對的問題視域,贏得了學術思想上的普遍意義。巴特式解謎既是一種“文體”,也是一種姿態,它迷人且富有穿透力,歷來不乏效法者:它在揭示思辨樂趣之余,給讀者帶去了自由歡欣的精神體驗,而這正是學術寫作最獨特的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