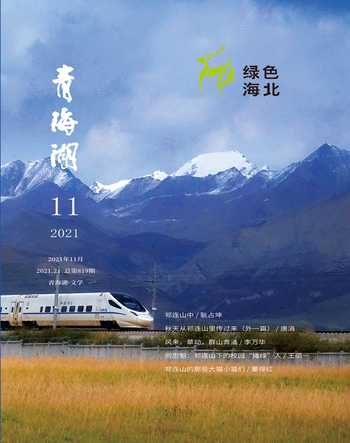秋天從祁連山里傳過來(外一篇)
在高原,秋天的抵達總是那么急不可耐。幾場秋雨過后,寬闊的草原瞬間便置換了色彩。枯黃的草色覆蓋著草原,一片片從車窗外飄然而去。遠處山巒因為升高的海拔,落下的雨滴已經(jīng)幻化成雪,與草原秋色相互映襯,倒平添了一種莊嚴(yán)之美。此次走進祁連山,都是今年的第三回了,能親近自然,終究是令人身心喜悅的事。
住宿的酒店坐落在祁連縣城入口處,與縣城隔出一段距離,便擁有了與自然相鄰的清靜。推開窗扉,聞名遐邇的牛心山咫尺之遙,背依的又是卓爾山景區(qū)。兩山深情對視的目光下,八寶河蜿蜒流淌。岸邊密集著一群群身姿優(yōu)雅的樹種,人們喜歡稱其“祁連小葉楊”。也許祁連的天時地利非常適合小葉楊生長,它的
數(shù)量可能達到了中國之最。每次來祁連,我都會癡迷這些青海的特有樹種,它們多半的樹齡都遠超過人類,很難想象,在漫長歲月的冰霜雨雪中,它們是如何延續(xù)下來自己生命的。
此次采訪的第一站是扎麻什鄉(xiāng)的西山梁,出了住地不久,皮卡車就拐進一道山溝,山路凹凸不平,坡道需要車輪用力,但對皮卡車并不是問題。祁連山國家公園每個管護站都配備有這種車,其行駛高原路途體現(xiàn)出來的優(yōu)越,讓我在西藏拍紀(jì)錄片時驚訝不已。皮卡車停在了一面山梁下,放眼望去,原本荒蕪的山坡竟然冒出幾片生機盎然的綠色。從路邊豎起的展板介紹,我才知道先前這里是某個采礦公司的采礦點。眾所周知,要想從地球獲取礦產(chǎn)資源,一定會對大地或者山體開膛破肚,這些大地的傷口,也許在氣候溫潤、雨水充沛的南方很容易愈合,但對高寒缺氧、生態(tài)環(huán)境極其脆弱的青藏高原,植被恢復(fù)卻十分困難。蘊藏著豐富礦產(chǎn)資源的青藏高原,生態(tài)價值更為珍貴。我們沒有看到這個多金屬礦的開采區(qū),幾年中開采了多少礦石,我們目睹的是為保護高原生態(tài)重新復(fù)綠,祁連縣的林草職工和生態(tài)管護員為此付出的艱辛勞動。山梁坡陡,汽車難以抵達,他們就肩扛背馱運送需要復(fù)綠的設(shè)備物品,可以想象這些復(fù)綠工程投入的昂貴代價。在西山梁,我頭回聽到了“圖斑”這個專業(yè)名詞,那是指裸露在地表失去植被的斑塊,復(fù)綠也叫圖斑治理,通過遙感技術(shù)就能監(jiān)測到治理的情況。但這些大地皮膚曾經(jīng)的傷痕,需要慢慢醫(yī)治,慢慢地休養(yǎng)生息,西山梁復(fù)綠的初見成效,如今已成為祁連縣治理圖斑的樣板。
站在西山梁上極目四野,遠山層層疊疊,云霧繚繞,秋天的草木為天地間充盈了一抹暖意。這樣的時刻,愈加領(lǐng)悟到了“綠水青山”的深層內(nèi)蘊。
走進祁連山,心里總期待能發(fā)現(xiàn)驚喜不斷的植物,盡管我的辨識能力極低。這幾年,也許是編刊物所需,也許是更想把自己的心靈放歸自然,那些在高原惡劣環(huán)境下綻放生命的植物,不斷深深地打動我。還是在夏天的祁連山,一面不起眼的山坡上,我們竟然發(fā)現(xiàn)了三種綠絨蒿,是我最鐘情的,也是青藏高原的植物名片。那花瓣呈黃色,渾身長滿細軟絨毛的叫全緣葉綠絨蒿,我曾跟隨一名攝影師在海拔3000多米的山上看到過,整個山坡怒放大朵的嬌黃,煞是壯觀。盛開藍紫色花朵,莖稈上伸出許多堅硬的長刺,是多刺綠絨蒿,這些令人望而生畏的尖刺,是它保護自己的防身武器。還有一種我第一次在戶外見到,叫五脈綠絨蒿,淡紫色的花苞垂向大地,讓人體味到一種謙卑之美。綠絨蒿品種繁多,姿色各異,主要集中在青藏高原上,許多一生只會綻放一次,展示了出人意料的美麗,十分珍貴,被人稱作是“離天最近的花朵”。山坡的更高處,還有紅景天,我與它的初次相遇,是在海拔較高的山體石縫中,由多株小紅花簇擁在一起,奪目的紅色在粗糲的石縫中艷麗無比,它家喻戶曉的名氣來自于其抗缺氧的功效。
八寶管護站我在春天來過,采訪的馬宏站長如今已是縣林場副場長,時隔數(shù)月,萬畝造林的松苗又長高了。舉目眺望,牛心山下綠茵茵的一片林海,待萬畝成林,和這些松苗一起長大的孩子將會擁有更美好的生存環(huán)境。我想,如果人類社會發(fā)展的每一步前行,都秉承為子孫后代造福的理念,那我們眼下面臨的環(huán)境災(zāi)難會大大減少。
八寶管護站有多名女性管護員,基本都是國家精準(zhǔn)扶貧政策的獲益者,由于各種原因家庭生活拮據(jù),再加上文化程度低,先前在外打工也都是干的賣力活,建筑工地上和男人一樣搬磚運土,賺點汗水錢。她們告訴我,現(xiàn)在家門口當(dāng)了管護員,每天都可以回家,穩(wěn)當(dāng)?shù)氖杖胱屗齻冃睦锖芴崳蚣毸阊a貼過日子也就夠了,雖然護林責(zé)任重大,但遠沒有外出打工那般辛苦。
國家這個政策實話好!幾名女管護員幾乎是異口同聲對我說。
野牛溝管護站距離縣城較遠,有百余公里,光聽名字,便有躍躍欲去的沖動,我們前往那里,主要是了解黑土灘的治理效果。陽光明麗,沿途美景動人心扉,野牛鄉(xiāng)寬闊的草原,被白雪覆蓋的群山擁攬懷中,營造出一種荒野的寂寥意境。汽車在雨水沖刷過的沙石路面上顛簸前行,細細觀察,這里的草原已經(jīng)退化,植被稀疏不說,還裸露出一塊塊的不毛之地。失去牧草的草原,別說領(lǐng)略“風(fēng)吹草低見牛羊”的詩意,那還能稱之為草原嗎?這些曾經(jīng)牧草豐茂的草場,最后退化為黑土灘,原因當(dāng)然有多種,但主要還是人類過度消耗自然資源造成的。有專家解釋:造成草地退化的罪魁禍?zhǔn)拙褪呛谕翞绻莸赝嘶雍⒈ǖ绕渌鷳B(tài)系統(tǒng)也將發(fā)生連鎖退化。
我們在一處被網(wǎng)圍欄圍住的草場停了下來,經(jīng)過幾年的人工種草,幾樣適合當(dāng)?shù)赝寥罋夂虻牟莘N,如垂穗披堿草、青海中華羊茅、青海草地和冷地早熟禾等,已經(jīng)旺盛生長,復(fù)原了草原最初的景象。祁連縣為此投入了大筆資金,也費盡心思和氣力,最終效果在日復(fù)一日的科研與勞作中顯現(xiàn)出來。草原生態(tài)在逐漸恢復(fù),收獲的草籽可以創(chuàng)收,牧草也給牛羊們過冬提供了足夠的口糧。收益讓村民們從最初的疑惑到欣喜,最后主動參加巡護隊來保護這片來之不易的草場。如果按這種方式慢慢擴展,若干年后,那些退化的草原是不是可以重現(xiàn)“風(fēng)吹草低見牛羊”的詩情畫意,變得生機勃勃、綿延不絕?當(dāng)然,這是我的想象,更是我的心愿。
回返途中,扎麻什鄉(xiāng)郭米村秋天的田野風(fēng)光徹底征服了我們,大家紛紛跳下車,奔向大地的懷抱。收割過的麥捆整齊地碼在田地,勾勒出九月的鄉(xiāng)野情韻。相鄰的燕麥田,幾個村民正在收割,將空氣中塞滿新鮮的青草氣息。蒼綠的云杉蓋滿山坡,遠山的雪色在陽光下閃爍,幾頭清閑的耕牛低頭養(yǎng)神,白云在山頂自由地流動。有位叫張曉風(fēng)的作家在書里這樣說道:“樹在。山在。大地在。歲月在。我在。你還要怎樣更好的世界?”我背依麥捆,愜意地閉上眼睛,秋風(fēng)清和,柔軟地敷在臉上,突然想起一個叫周華誠的作家朋友,那樣的才華橫溢,卻果斷從杭州日報副刊辭職,回歸到家鄉(xiāng)的稻田里,創(chuàng)意“父親的水稻田”十分成功,讓很多遠離土地的友人親歷了從一粒米到一碗米的勞作滋味,感悟到稻田的自然內(nèi)涵,影響力越來越大。而他自己,大量精美的文字,有如成長的稻米源源不斷,汩汩涌出。他重新躬身于土地的姿態(tài),也啟示了我。是啊,對于一個寫作者來說,大地最知道誰來過,大地是滋養(yǎng)我們文字的良田沃土。
青陽溝管護站距離縣城很近,出了縣城,車子便進入盤山小路,賞心悅目的景致別有一番風(fēng)味。從管護站的窗戶望去,窗框內(nèi)的秋光猶如一幅天然的油畫。讓人忍不住怦然心動,艷羨起每日行走在美景中的管護員來。青陽溝管護員女性多,“娘子軍”早已名聲在外,她們干起工作來一點都不輸男性。比起前輩,如今管護站的條件可謂是今非昔比,高科技的運用大大減輕了管護員的勞動量,特別是紅外相機的架設(shè),可以便捷地觀察到野生動物的行蹤,拉近了人類與野生動物的距離。這幾年我們看到的珍稀野生動物影像,如雪豹、豺等,都是紅外相機的功勞。管護員們告訴我,現(xiàn)在他們看到的和監(jiān)測到的野生動物真是越來越多了。
在青陽溝,我看到了許多遍布在山巒上的祁連圓柏,身形高大,枝葉茂盛,也是青海的特有樹種。它能在這氣候寒旱的地方頑強生長,且四季常青,是青藏高原難能可貴的“常青樹”。人們喜愛它還有一個原因,圓柏的樹枝曬干后點燃,會散發(fā)出一種獨特的香氣。我不知道當(dāng)?shù)夭刈迦遂猩r,選用的是不是圓柏的枝葉。一條小河的岸邊,生長有一種身形矮胖的樹,青陽溝的管護員叫它“西番柳”,至于此名的來由,他們也解釋不清。觀其葉片,形狀細長,的確酷似柳葉。平時他們得空會采下一些,曬干后代茶泡水飲用,說是有健胃養(yǎng)肝降脂的功效。查閱了下資料,才知道它的學(xué)名稱“窄葉鮮卑花”,別名柳茶,屬薔薇科。主要生長在青藏高原,是藏族民間的常用藥物。看多了這方土地上的植物,我發(fā)現(xiàn)含有毒性的除外,多半都可入藥,有藥用價值。這也是上天饋贈了它們頑強生命力的同時,也賦予了它們幫助人類除疾治病的使命。
大拉洞管護站坐落在一條寬闊的河床邊上,河水干涸,裸露出許多灰白色的石頭,不知玩石者會不會跑到這里尋找奇石。秋意浸染了山林,恬靜悠遠,讓人心曠神怡。管護站后面是有名的拉洞峽,不過我孤陋寡聞,還是第一次知道。正在修路,鋪滿碎石的道路無法讓不具備越野性能的車子挺進,于是我們下車徒步。拉洞峽真是奇特呀,山體高聳嶙峋,處處奇松異石,讓抵達這里的人們腦洞大開,充滿想象,難怪在此流傳有各種民間故事。
說是峽谷長度有十余公里,大拉洞管護員還說,這里常有大型野生動物出沒,如狍鹿、白唇鹿、雪豹、盤羊、巖羊等,這幾年棕熊也多了起來,說得我心頭一顫,忍不住問道:棕熊白天會不會出來呀?峽谷深處,景致愈加迷離,那些松樹至少都擁有上百年樹齡,盤根錯節(jié)的根部擺出各種令人聯(lián)想的形狀,許多松樹匪夷所思地生長在巨石之上,它們見證了比一個人生命更久長的峽谷變遷。繼續(xù)前行,陡峭的崖壁上,出現(xiàn)了墨黑色的巖石,雖然無法分辨,但感覺這峽谷蘊藏有豐富的礦產(chǎn)資源。有趣的是,陪同我們走進峽谷的一名管護員,找到了一塊化石,上面排列許多類似蜂巢的小圓點,能清楚地看到里面存在海洋生物,拍了照片發(fā)給專家咨詢,才知道這是泥盆紀(jì)珊瑚化石,距今有2億多年,可見曾經(jīng)是海洋的高原歷經(jīng)了多么復(fù)雜的地殼運動。聽說拉洞峽里這樣的化石有很多,有些大得人都搬不動,但遺憾我從來沒有見過。
人說“最美不過是清秋”,但祁連山在不同的季節(jié),有各自的妙處,不同的溝谷,也有各自的秘境。不管你在何時進入,或停留多久,總會有別樣的感覺相伴你。每次走進祁連山,我都會想起美國自然文學(xué)作家亨利·貝斯頓在他的名作《遙遠的房屋》中的那句話:“撫摸大地,熱愛大地,敬重大地,敬仰她的平原、山谷、丘陵和海洋。”
青海湖北岸的風(fēng)景
在青海天高地闊的大地上,青海湖猶如一枚晶瑩潤澤的藍寶石,吸引著人們想象,并且沉迷。此刻,我正站在大湖北岸,沐浴著它圣潔的清輝,目光深情。早晨6點,攝制組已經(jīng)來到了剛察縣境內(nèi)的仙女灣。今天,這里將要舉行隆重的祭海盛典。擁有動聽名字的仙女灣,是青海湖著名的濕地,每年都會有數(shù)以千計的白天鵝集聚于此,我曾在冬季一個飄雪的日子來到這里,透過高倍望遠鏡欣賞過大天鵝優(yōu)雅高貴的身姿,那的確令人心醉神迷、難以忘懷。
朝陽躍動,三牲拉則廣場漸漸明亮。在整個仙女灣景區(qū),高高矗立的馬、牛、羊三牲拉則非常醒目,據(jù)說這是五世達賴?yán)锇⑼_桑嘉措受封歸返西藏途經(jīng)青海湖時所建。我看見金色曙光從37米高的牦牛角尖開始,迅速覆蓋了整個廣場。在青海湖祭海儀式里,我們可以抓拍到許多充滿濃郁宗教色彩的畫面。擺滿各種貢品的長條桌;吹法號和誦經(jīng)的僧侶;煨桑朝拜的信眾;空中如雪片飄動的風(fēng)馬……然后,我們穿過長達999米的木質(zhì)棧道,來到延伸至湖水里的祭海臺。盛夏7月,從湖面上飄來的風(fēng),依然透入骨髓,寒冷如冬。當(dāng)龐大的信眾隊伍涌向祭海臺,將手中的寶瓶奮力拋向湖中時,那場面著實壯觀。
無數(shù)只承載心愿的寶瓶漂向大湖深處,湖水的波紋間閃動著神的力量。這讓我又想起了那個始終若隱若現(xiàn)在圣湖的六世達賴?yán)飩}央嘉措,他的神秘消失在此留下了令人迷幻的傳說,更讓無數(shù)癡迷于倉央嘉措詩歌的人們駐足湖岸時心生遐想。
祭海盛典結(jié)束后,我們又趕往沙柳河鎮(zhèn)的潘寶村。剛察縣畜牧獸醫(yī)工作站站長宋永武介紹這里的牛糞花,引起了我們的興趣。一路上,我都在想象草原上俯拾即是的牛糞如何能變成賞心悅目的藝術(shù)作品。在草原,我們的目光早已熟識了牛糞的價值,特別是在那個叫蘭則的牧民拍攝的紀(jì)錄片《牛糞》中,牛糞與草原牧民生活的密不可分更是被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但據(jù)我了解,在所有牛糞的用途里,唯獨缺少了牛糞花。
制作牛糞花的是一名藏族女牧民,也許是知道了我們要前來拍攝,特地換上了艷麗的民族服裝。在她的住房前,我們看到了幾排精心壘砌、拼出各種圖案的牛糞墻,墻頭上用牛糞做出的小鳥等動物栩栩如生。我們的拍攝從她攪拌稀軟的牛糞開始,先摻入些馬糞,以增加硬度,然后將其揉成軟硬合適的面團狀,再一點點地拼貼在牛糞墻上,很快一個活靈活現(xiàn)的牦牛頭就浮出墻面,最后沿邊鑲嵌一些精挑細選過的小石子,使其看上去更具立體感。如果不是親眼目睹,這樣的場景我很難想象。對于生活在都市的我們,又怎會從這樣的視角去感受一個普通牧民對于草原生活的熱愛與情趣,它太陌生,遙不可及。
在哈爾蓋鎮(zhèn)的塘渠村,一位老人正在牦牛角上精雕細刻,一些魚鱗狀的紋路在左右滑動的刀尖下逐漸成型、清晰,然后用毛刷仔細清除碎屑,再拿油砂紙打磨出光澤,一條青海湖湟魚做成了。牦牛角天然的弧度與色澤,恰如其分地與湟魚融為一體,渾然天成,惟妙惟肖。在他的工作間里,還擺放著用牦牛骨制作的各種工藝品,轉(zhuǎn)經(jīng)筒、掛飾、手鏈、煙嘴等,個個精致獨特。老人粗糙而靈動的手勾起我對手工時代的懷想,那是一個創(chuàng)造手的奇跡,一個人與自然息息相通,一個綻放著民間智慧、文化、情趣、風(fēng)俗,一個可以用詩句贊美勞動的時代。然而,追求效率與速度的工業(yè)機器,正在把這些蘊含著人的靈性的民間手工藝品淡出我們的視野。那么,失去了指尖溫度與人類靈性的工藝品,還能喚起我們對于先祖文化的記憶嗎?
舍布齊巖畫我先前了解的并不是很多,因為畫面以牦牛形象為主,所以攝制組決定前往。正值中午,日光強烈。巖畫鑿刻在公路旁一座山頂邊緣的懸崖上,機位架在那里,仿佛凌空,我看著都有些眩暈。舍布齊巖畫據(jù)說年代久遠,可以追溯到唐初時期,穿越了那么悠長的時空隧道,那些鐫刻在堅硬巖石上的牦牛、鹿、羊及人騎馬狩獵的圖案依然依稀可辨,讓人忍不住面對流轉(zhuǎn)的時光心生多種喟嘆。尤其是畫面中的那個牦牛,形體高大,正在被騎馬的獵人追逐獵殺,可見在千余年前,這里就留有野牦牛生息的痕跡。遺憾的是,我們的拍攝總也沒有充裕的時間捕捉每個畫面的最佳光線。此刻,午后灼目的陽光反射到巖畫上,大大影響了拍攝效果。盡管我們這部紀(jì)錄片基本都在室外拍攝,大多利用的是自然光,很少需要照明和布光,但對于影視藝術(shù),光線卻是它的靈魂,是攝影師的畫筆。寫到這里,我想起一部我印象極深的電影——美國導(dǎo)演特倫斯·馬利克的《天堂之日》,其吸引我的并不是它的故事,而是令人震撼的唯美畫面。影片的主要畫面幾乎全是外景,為了使畫面達到攝影師心目中的極致效果,這個叫阿爾曼德羅的家伙選擇了被攝影界稱為“魔術(shù)時刻”(即日出前與日落后的半小時)進行拍攝,令畫面呈現(xiàn)出動人心魂的油畫與剪影效果。《天堂之日》在收獲了全球多項最佳攝影大獎的同時,也為影視攝影人提供了一個出色的學(xué)習(xí)范本。另一部影片《時間的風(fēng)景》,那光與影所制造出的魔幻藝術(shù),令我們窒息。
中國著名的攝影師趙非在談到影視作品的光影藝術(shù)時,曾這樣說道:攝影這活兒包含了很多方面,把控機器只是很小的一方面,對我來說,重要的工作主要是光和鏡頭之間的設(shè)計。紀(jì)錄片攝影師可以扛著手持?jǐn)z影機,但電影攝影師重要的就是在于光線。和畫面一樣,這是用色彩表現(xiàn)空間,光線的結(jié)構(gòu)、透視,只是手里的作畫工具。誰能把光線玩兒好了,誰就牛了。
結(jié)束青海湖北岸的拍攝,攝制組將要奔赴巴顏喀拉山,而我因事必須在這里與他們分手了。青海的山川江河里,眾山之祖的巴顏喀拉山無疑是個標(biāo)志。山頂終年不化的皚皚積雪和飄飄的飛雪都是我們需要的畫面。一個月前,我剛剛赴玉樹采訪災(zāi)后重建項目,翻越巴顏喀拉山時,突遇大雪,在鵝毛大雪中游移的黑色牦牛,恍若畫家毛偉筆下精彩的牦牛水墨畫。然而,當(dāng)攝制組馳騁千里,抵達巴顏喀拉山時,陽光熱烈,雪花卻不知所終。很多時候,美好的瞬間總是與我們擦肩而過。這不僅是拍攝途中,也是人生注定的一種遺憾。
在剛察開往西寧的長途汽車上,我望著窗外一閃而過的山脈和草原,孤獨感油然而生。接下來的日子,攝制組將要前往更遼遠,也更荒蕪的草原腹地,去尋找追蹤野牦牛的身影,這樣一個驚心動魄的旅程,我卻漸行漸遠,不能同享甘苦。除了祈禱、想象,我還能說什么呢?此時,耳邊響起一首歌,那是雅克·貝漢《遷徙的鳥》中的,“明天我將會飛翔,為了回到你身邊”。
作者簡介:唐涓,女,山東文登人。編審。中國作家協(xié)會會員。曾被國家公派留學(xué)于羅馬尼亞布加勒斯特大學(xué)新聞學(xué)院。魯迅文學(xué)院第二屆高研班學(xué)員。現(xiàn)任《三江源生態(tài)》雜志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