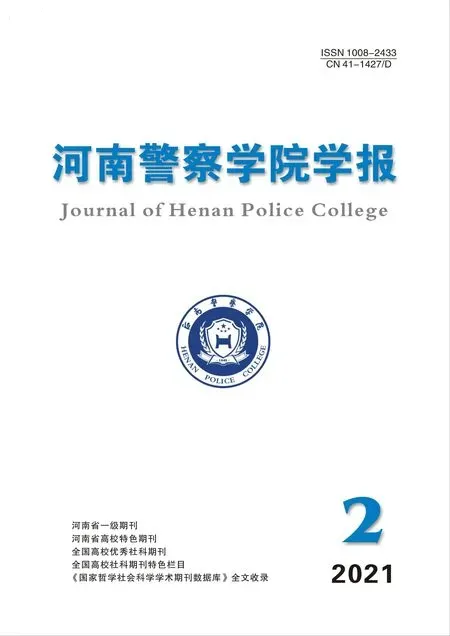論被害人自陷風險的類型區分
王芳凱
(北京大學 法學院,北京 100871)
一、導論
被害人自陷風險是指被害人在認識到風險的情形下,仍然將自己置于風險之中,但被害人并不希望實害結果的出現。從自我負責原則來看,每個人都只需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而不需要對其他人的行為負責,故而,當被害人自陷風險時,被害人自陷風險的行為可能會對行為人的不法產生影響。德國刑法通說將被害人自陷風險的問題區分成兩種類型:第一種類型是參與他人自我負責的自我危殆化,如行為人向被害人提供毒品,被害人自行注射后發生死亡結果;第二種類型是得同意的他者危殆化,如被害人在暴雨天氣要求船夫幫忙渡河,盡管船夫向其指出了渡河行為的危險性,但最終仍決定遵照被害人的請求,被害人最終因為翻船而不幸身亡。德國實務接受了上述的類型區分,并根據不同的類型進行區分處理,即,對于自我危殆化的情形,原則上采取被害人自我負責的立場,并通過共犯從屬性原理和舉重明輕的類推解釋來形式地推導出“參與他人自我負責的自我危殆化是一個不可罰的行為”;至于他者危殆化的情形,則通過被害人承諾來處理。
反觀我國,實務上其實并不缺乏被害人自陷風險的案例。例如,在“田某某過失致人死亡案”中,被告人田某某與其妻康某某因為違法生育第三胎而被本縣板栗樹鄉計劃生育工作人員帶至縣計劃生育技術指導站實施結扎手術。被告人田某某為使其妻逃避結扎手術,而對計生工作人員謊稱其妻要到指導站住院部三樓廁所洗澡。在廁所里,被告人田某某先用手掰開木窗戶,然后用事先準備好的尼龍繩系在其妻胸前,企圖用繩子將其妻從廁所窗戶吊下去逃跑,但由于繩子在中途斷裂,致使康某某從三樓摔下后當場死亡。法院認為,被告人田某某為幫助其妻康某某逃避結扎手術,用繩子將康某某捆住從高樓吊下,應當預見到自己的行為會造成嚴重后果而沒有預見,致其妻死亡,被告人田某某犯過失致人死亡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緩刑三年。從中也可以看到,我國實務并沒有將被害人自陷風險當作排除行為人不法的事由。對此,有學者基于被害人自我負責的原理認為本案被告人應當是無罪的(1)參見江溯:《日本刑法上的被害人危險接受理論及其借鑒》,載《甘肅政法學院學報》,2012年總第125期,第85-89頁。。
在實務不認為被害人自陷風險可以排除行為人不法的情形下,自然不會嚴格地界定被害人自陷風險的范圍,當然也不會去區分被害人自我危殆化以及他者危殆化的案例類型,但我國的學說并不乏支持或反對類型區分的主張。支持區分的學者有張明楷和車浩教授,但兩人的見解仍存在著較大差異。其中,張明楷教授把“對實害結果發生的支配”作為標準將被害人自陷風險的案例區分為“參與他人的自我危殆化”與“得同意的他者危殆化”,前者不可罰,后者原則上可罰(2)參見張明楷:《刑法學中危險接受的法理》,載《法學研究》,2012年第5期,第171頁。。車浩教授則根據風險的支配/控制而將被害人自陷風險的案件區分為“自控風險型案件”和“他控風險型案件”,且認為后者絕對不能通過被害人同意來阻卻違法(3)參見車浩:《過失犯中的被害人同意與被害人自陷風險》,載《政治與法律》,2014年第5期,第27-28頁。。也有學者基于規范的視角反對被害人自陷風險的類型區分,如江溯教授。
從上述分歧來看,不難得知被害人自陷風險的類型區分是被害人自陷風險問題中的重要一環,其影響甚至決定了被害人自陷風險問題在刑法體系中的位置。究竟被害人自陷風險是否有區分的必要性,如果有必要的話,又該如何區分,值得作進一步的探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由于被害人自陷風險的類型區分最初來自德國刑法上的實務見解和學說探討,故而,筆者嘗試以德國實務和學說的相關討論為基本素材去探討被害人自陷風險的類型區分問題。
二、自我危殆化和他者危殆化的實務面貌
在“海洛因注射器案”以前,德國實務盡管也會面臨著被害人自陷風險的問題,但其并未發展出相對完整的被害人自陷風險規則,而是訴諸注意義務違反性或被害人承諾。直到“海洛因注射器案”出現后,德國聯邦最高法院才明確指明參與他人自我負責的自我危殆化的行為是不可罰的。雖然學者羅克辛很早就已經主張“得同意的他者危殆化”是一種獨立的類型,但德國聯邦最高法院直到“加速測試案”出現才正式確立“他者危殆化”這一類型。
(一)“海洛因注射器案”:引入自我危殆化
1.基本案情及裁判理由
“海洛因注射器案”的基本案情是:行為人和被害人想要一起注射海洛因,被害人負責攜帶海洛因,行為人負責購買一次性注射器,因為被害人無法從其他地方弄到注射器。被害人將“煮熟的(海洛因)物質”注入兩支注射器后,將其中一支交給了行為人,自己則用另一支注射器自行注射海洛因。在完成注射不久,被害人死亡(4)Vgl. BGHSt 32, 262.。
德國聯邦最高法院認為,行為人參與他人自我危殆化的行為不可罰的原因在于“故意地參與他人自殺或自損的行為是不可罰的”這一見解。基于這一前提,德國聯邦最高法院首先基于評價的觀點認為,過失促使、引發或鼓勵他人自殺或自損同樣是不可罰的行為,否則“處罰將會違反《德國刑法典》第15條和第18條所表達出來的罪責形式的階級關系”。接著,德國聯邦最高法院認為,這一原則也可以轉用于自我危殆化:被害人有意且親自實施的(自我負責的)自我危殆化行為,同樣不在身體傷害罪或殺人罪的構成要件之中。進而,德國聯邦最高法院將這兩種主張加以結合,并形成了本案的重要結論:本案涉及的是促使、引發或鼓勵他人參與某個不符合構成要件的事件歷程,風險接受者通過危險的行為接受了危險現實化的風險,故而,其他的參與者是不可罰的。不過,判決書中既未說明為何行為人的行為僅構成被害人自我危殆化之參與,也未指出確定被害人自我危殆化的一般性標準。
2.評析
羅克辛認為,“海洛因注射器案”的積極意義是,它告別了以往關于過失犯的學說和實務見解。對于客觀構成要件的實現而言,除了因果關系之外,(根據規范性標準所進行的)歸屬也是必不可少的,特別是法所不容許風險的實現以及規范的保護目的(5)Vgl. Roxin, NStZ 1984, 410 (411).。但也有論者強調,德國聯邦最高法院僅僅表明行為人參與他人自我負責的自我危殆化并未“該當構成要件,故而是不可罰的”。因此,無法以此判決認為德國實務在逐漸接受客觀歸責理論(6)Vgl. Von Atens, Objektive Zurechnung und Tatherrschaft, 2019, S. 47.。不過,撇開客觀歸責理論的爭議,本文認為,“海洛因注射器案”存在著諸多不足之處:
第一,德國聯邦最高法院并未提出自我危殆化的一般性標準。在“海洛因注射器案”中,德國聯邦最高法院僅認定被害人的行為構成自我負責的自我危殆化,但判決書并未說明歸類的一般性標準(7)Vgl. Von Atens, Objektive Zurechnung und Tatherrschaft, 2019, S. 46.。
第二,被害人自損與自我危殆化之間具有兩個重大的差異,無法“舉重以明輕”。按照德國聯邦最高法院的見解,“參與他人的自殺或自損”相較于“參與他人的自我危殆化”是一種更為嚴重的情形,既然前者不構成犯罪,那么,后者自然也無法作為犯罪來處理。這一見解乍看起來是有道理的,因為相較于被害人自損或自殺的情形,結果出現的風險在被害人自我危殆化的情形下是更低的。不過,舉重以明輕的適用前提是,輕者與重者之間只有在某一個變量上存在著差異,其他的因素必須完全相同。但是,除了結果實現的風險之外,被害人自損(自殺)和自我危殆化之間還存在著一個不可忽視的重大差異:在被害人自殺的情形中,被害人是希望結果出現的;而在被害人自我危殆化的情形中,被害人是反對結果的出現。在兩者存在異質差異的情形下,就無法進行舉重明輕的推論(8)Vgl. Zaczyk, Strafrechtliche Unrecht und die Selbstverantwortung des Verletzten, 1993, S. 33 ff.; Matthes-Wegfraβ, Der Konflikt zwischen Eigenverantwortung und Mitverantwortung im Strafrecht, 2013, S 52.。
第三,過失犯和故意犯的正犯范圍不同,共犯論證無法適用于過失犯。德國聯邦最高法院認為,參與他人故意的自殺行為之所以不可罰,主要是因為自殺行為不是構成要件該當行為,在主行為不存在的情形下,自然無法根據共犯規定去處罰故意的參與行為。不過,這一說法只是法條應用的結果,其并未說明參與行為不可罰的實質理由。事實上,更大的問題還在于,德國聯邦最高法院認為“故意行為所造成的不法重于過失行為所造成的不法”,并通過舉重以明輕的方式從“故意參與他人自殺不可罰”推導到“過失參與他人自殺不可罰”,而這一做法明顯忽視了過失犯罪的獨立前提。
從概念上來看,過失和故意是一種異質、互斥的關系,如果一個人接受他人的死亡是自己的行為所造成的結果,那么,他就不能同時希望結果不會不發生,他的行為也只能是故意或過失中的一種。因此,從概念上來看,不能認為故意和過失存在著輕重的階層關系。毋寧說,故意和過失的階層關系必須基于規范的視角。德國實務認為,故意的法益侵害行為相較于過失的法益侵害行為具有更高的不法和罪責,在過失犯的情形中僅存在“可避免的避免義務之違反”,而在故意犯的情形中則存在“有認識的避免義務之違反”。正是在這一規范意義下,我們才可以說故意是重者,而過失則是輕者。不過,即便如此,我們仍然無法從“故意參與他人自殺不可罰”推導出“過失參與他人自殺不可罰”。因為從規范的角度來看,“故意參與他人自殺”是一種“故意的參與犯”,而“過失參與他人自殺”則是一種“過失的正犯”,這并不符合舉重明輕的推論前提——僅存在一種變量。具體而言,德國刑法在故意犯上采取限制正犯的概念,只有實施構成要件該當的行為才構成正犯,教唆犯或幫助犯則是作為一種刑罰的擴張事由。如果在刑法總則中不存在教唆犯或幫助犯的處罰規定,就不能處罰故意教唆或幫助的行為。與之相反,德國刑法在過失犯上則采取所謂的單一正犯的概念,即過失犯并不區分正犯、共犯,只要違反注意義務,惹起了法益侵害的結果,就構成過失犯。
(二)“加速測試案”:引入得同意的他者危殆化
1.基本案情及裁判理由
“加速測試案”的基本案情是:A、B、C和D同意在一條雙向四車道的聯邦公路上進行汽車比賽。A開著他的高爾夫,其副駕駛為B;C則開著保時捷,其副駕駛為D。B、D兩人在比賽中發出發車信號和互相拍攝賽車的過程。在比賽中,兩輛車的速度都超過了200公里/小時,盡管限速為120公里/小時。雖然前方右側車道出現另一輛正常駕駛的汽車,但他們仍然毫無顧慮地繼續比賽。在超車時,三輛汽車在兩車道上并排的時間并不長。在這個過程中,高爾夫車的左輪胎卡到了中間隔離帶的綠化帶上。為了將車重新開回車道,A猛打方向盤,但由于汽車打滑而撞向了中央防撞欄,并發生了翻車。A、B兩人未系安全帶,被甩出了車外,這導致了A的重傷和B的死亡。C、D兩人則沒有受傷。一審法院判決A和C的行為構成了故意的危害道路交通安全罪,D構成相應的教唆犯。經上訴,德國聯邦最高法院認為,A和C的行為構成過失致人死亡罪。在此,德國聯邦最高法院拒絕根據自我負責原則來排除死亡結果的歸責,并認為B沒有對生命危險作出有效的承諾(9)BGHSt 53, 55.。
該判決同時涉及被害人自我危殆化與他者危殆化的區分以及被害人承諾等問題,簡述如下。
第一,危險支配作為自我危殆化和他者危殆化的區分標準。德國聯邦最高法院認為,不可罰的“參與他人自我負責的自我危殆化/自我損害”和“原則上該當構成要件的他者損害”之間的區分線是正犯和共犯的區分標準。如果對危險或損害行為的支配不僅僅在被害人身上,就不能根據從屬性而認為由于主行為不存在,行為人的行為不受處罰。并且,德國聯邦最高法院在本案中完全根據客觀的標準來判斷危險支配:“在審查誰具有危險支配這一問題上,直接導致結果發生的事件歷程具有重要意義。”在本案中,駕駛員具有對(直接導致結果發生的)事件歷程的危險支配,因為同乘者負責發出比賽開始的信號以及攝影,而駕駛員則負責操控車輛和回避危險,兩相比較之下,前者處于從屬的地位(10)Vgl. Lotz, Die Einverstandliche, Beidseitig Bewusst Fahrlassige Fremdschadigung, 2017, S. 131.。
第二,本案屬于他者危殆化的情形,應通過承諾來處理。這里主要涉及《德國刑法典》第216條和第228條故意情形下的承諾限制,前者是受囑托殺人罪的規定,后者則要求同意傷害的行為不得違反善良風俗。由于生命具有不可衡量性,過往的實務認為過失致人死亡范圍中的承諾原則上是不重要的,但現在的實務見解則主張只有在承諾涉及具體的死亡危險時,被害人的承諾才是不重要的。德國聯邦最高法院進一步將這一見解擴展到過失致人死亡中的“純粹的風險承諾”情形中。因此,本案的重點問題就轉變成是否存在具體的生命危險。對此,德國聯邦最高法院并未回答“加速測試本身是否帶來了具體的生命危險”這一問題,而是指明“具體的生命危險存在于三車并行超車之時”,被害人無論在比賽開始之前還是在具體的情形中均不會承諾被告人的超車做法(11)Vgl. Lotz, Die Einverstandliche, Beidseitig Bewusst Fahrlassige Fremdschadigung, 2017, S. 132.。
2.評析
德國聯邦最高法院直接將危險支配當作自我危殆化和他者危殆化的區分標準,本文認為,這一做法存在著以下問題。
第一,在故意犯的情形下,將危險支配標準作為自我危殆化和他者危殆化的區分標準,忽視了自我危殆化與自我損害之間的區別。按照德國聯邦最高法院的見解,危險支配標準可以追溯到自我損害和他者損害的區分,即行為支配標準。德國實務之所以用行為支配標準來區分被害人自我損害以及他者損害,主要是因為《德國刑法典》第216條規定了受囑托殺人罪,而教唆、幫助自殺的行為在德國原則上是不可罰的。并且,在得同意的他者損害情形中,行為人的意志是服從被害人的意志(因為《德國刑法典》第216條的受囑托殺人罪以被害人的真摯囑托為前提),其行為是基于被害人的利益,這也就決定了無法根據主觀的標準而只能根據客觀的標準來對兩者加以區分(12)Vgl. Jetzer, Einverst?ndliche Fremdgef?hrdung im Strafrecht, 2015, S. 71 f.。不過,自我危殆化和自我損害之間在結構上存在著重大區別:在自我危殆化的情形中,被害人雖然自愿讓自己陷入風險之中,但他和行為人并不想要實害結果的出現;相反,在自我損害的情形中,被害人不僅接受風險,也接受風險的現實化。這也就意味著,在故意犯的情形下,不能將被害人自我損害和他者損害的區分標準(即客觀的支配標準)轉用于被害人自我危殆化和他者危殆化的情形,因為在被害人自陷風險的情形下,行為人的意志未必會服從被害人的意志(13)Vgl. Stefanopoulou, Verantwortlichkeit und Schuldzumessung in Mitwirkungsf?llen, 2017, S. 30.。
第二,在過失犯的情形下,危險支配標準無法與過失犯的單一正犯性格兼容。從定義來看,過失犯無法“支配”行為進程,否則他們就會構成故意犯。并且,過失犯采用的是“單一正犯”概念,其并未區分正犯、共犯。任何人只要違反注意義務導致構成要件實現,即便有其他人參與其中,皆會成立過失犯。如果行為人違反了注意義務,且因此而產生的風險也在結果中實現,那么,行為人就不能以其他人同樣未遵守注意義務為理由來免除自己的責任。換言之,過失犯遵循的原則并非是行為支配,而是注意義務違反。因此,人們不能將故意犯情形中的正犯和共犯區分標準直接運用到過失犯上(14)Vgl. Jetzer, Einverst?ndliche Fremdgef?hrdung im Strafrecht, 2015, S. 86 f.。
第三,危險支配標準無法處理所有的故意情形,特別是被害人和行為人的共同作用方式具有“類似共同正犯”性質的情形(15)Vgl. Stefanopoulou, Verantwortlichkeit und Schuldzumessung in Mitwirkungsf?llen, 2017, S. 31.。例如,艾滋病患者將自己的感染情形告訴其伴侶,并和他發生了無保護措施的性行為。根據危險支配標準,此種情形究竟屬于自我危殆化還是他者危殆化的情形,學說和實務之間存在著爭議。羅克辛認為,應根據危險的源頭來判斷危險支配者,該行為就如同“行為人對被害人注射海洛因”,因此,這屬于他者危殆化的情形。如果當事人雙方均知道感染風險且對該性行為共同承擔責任,行為人的行為才是不可罰的。反之,如果行為人未告知被害人自己感染病毒的事實而與之進行無安全措施的性行為,則是可罰的(16)Vgl. Roxin/Greco, Strafrecht AT I, 2020, S. 518.。但德國實務反對這種見解,對于行為支配的判斷而言,起到決定性作用的并不是自然意義上的危險源(即病毒攜帶者),因為危殆化并非單純源自于某人是艾滋病病毒攜帶者這一情狀,而是實際發生的、無安全措施的性行為。也就是說,對行為支配而言具有意義的要素是危險的行為而非當事人的狀態。故而,德國實務認為,被感染的一方同樣具有行為支配,該情形屬于被害人自我危殆化的情形(17)BayObLG JZ 1989, 1073 (1074).。本文認為,正確的做法是將行為支配的對象定位為行為而非當事人的狀態,事實上,也只有危險行為才會受到刑法的評判。但即便如此,人們也無法根據行為支配去區分自我危殆化和他者危殆化,因為得同意的性行為必須是一種交互的行為。在行為人具有故意的情形下,行為人的行為并非是為某個危險歷程提供助力或使之成為可能,而是和被害人共同支配了一個不可分割的危險進程。在這種情形下,危險支配說對被害人自陷風險的類型確定是無能為力的。
第四,危險支配標準的內容并不明確,其既可能因為內容過于精確而淪為僵硬的標準,也可能因為內容過于模糊而產生恣意的結論。危險支配的實質內容為何,實務和學說存在著分歧。例如,羅克辛認為,這指的是“直接導致死亡結果發生的最后一個行為”,如果這一行為掌控在行為人手中,則屬于他者損害的情形,如被害人要求行為人為其注射氰化鉀。反之,如果此一行為掌控在被害人手中,則屬于被害人自我損害的情形,如被害人決定排除所有的救援可能性。此處起決定性作用的要素是,在行為人作出行為貢獻后,被害人還能夠支配自己的生命或死亡。德國聯邦最高法院則將危險支配理解成“對(導致死亡結果發生的)事件歷程的支配”。一方面,將危險支配解釋成對“直接導致結果發生的事件歷程”的支配,其內容過于僵化,容易導致恣意的結果。舉例而言,甲和乙輪流玩射蘋果比賽,一個負責把蘋果放在頭上,另一個負責射擊。事實上,參與的任何一個人都有可能成為受害者,也都有可能成為加害者。如果按照“直接導致結果發生的事件歷程”這一說法,會認為這是他者危殆化的情形,必須處罰幸存者(18)Vgl. Stefanopoulou, Verantwortlichkeit und Schuldzumessung in Mitwirkungsf?llen, 2017, S. 32.。另一方面,運用危險支配標準所導出的結論往往會取決于人們對危險情形的描述程度。以“梅梅爾河案”為例,如果人們看到的畫面僅僅是“船夫開船,小船傾覆”,則會篤定地認為這是他者危殆化的情形,因為乘客無法對船夫的開船行為產生任何的影響;但是,如果人們更詳細地去檢視事件的歷程,即“在巨浪打入小船后,被害人不遵守船夫的指示,從自己的座位上跳起來,并因此導致小船傾覆”,人們又會認為這是自我危殆化的情形(19)Vgl. Jetzer, Einverst?ndliche Fremdgef?hrdung im Strafrecht, 2015, S. 90.。
三、被害人自陷風險的區分必要性和可行性
通過被害人自陷風險的實務面貌,我們可以確定,危險支配并不適合作為被害人自陷風險的類型區分標準。在此基礎上,筆者進一步檢視被害人自陷風險的區分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區分的必要性
羅克辛在1973年的一篇祝壽論文中提到,自我危殆化和他者危殆化的重大差異在于:在自我危殆化的情形中,被害人想要在多大程度上將自己置于危險之中是掌握在自己手上的;相反,在他者危殆化的情形中,被害人則是將自己置于某個不可預見的發展過程中,其無法掌控性地介入這一事件歷程中,當被害人不想要繼續自陷風險時,他并不能直接中斷這個流程。相較于他人的技巧,被害人能夠更好地評估自己應對風險的能力(20)Vgl. Roxin, FS-Gallas, 1973, S. 250.。另外,自我危殆化和他者危殆化在結構上的差異還體現在避免能力上,他者危殆化情形中被害人的避免能力原則上較弱。因此,從風險角度來看,自我危殆化和他者危殆化在風險支配上有著顯著的差異。
不過,學說上也有論者反對羅克辛所提出的危險支配標準:第一,就被害人對危險進程的可預見性來看,他者危殆化情形中的可預見性未必會弱于自我危殆化情形下的可預見性。事實上,無論是自我危殆化的情形,還是他者危殆化的情形,被害人均必須認識到風險及其決定的射程范圍,否則就不存在自我負責性或同意,這是行為人出罪的決定性前提(21)Vgl. Jetzer, Einverst?ndliche Fremdgef?hrdung im Strafrecht, 2015, S. 70 f.。第二,不容忽視的一點還有,即便在他者危殆化的情形中,被害人在任何時候都可以撤回自己先前的同意(22)Vgl. Murmann, FS-Puppe, 2011, S. 786.。第三,無論是自我危殆化還是他者危殆化的情形中,行為人都是不希望結果發生的,為何只在自我危殆化的情形中考慮行為人的此種內心態度,而認為行為人并未支配危險歷程?又為何在他者危殆化的情形中認為行為人的內心態度不具有法律上的重要性?這些問題有待危險支配論者的進一步澄清(23)Vgl. Jetzer, Einverst?ndliche Fremdgef?hrdung im Strafrecht, 2015, S. 70.。
另外,我國學者車浩教授則從自由的完整性來主張被害人自陷風險的區分必要性。車浩教授將被害人自陷風險的案件區分為“自控風險型案件”和“他控風險型案件”。前者是指被害人明知自己實施某種行為存在風險卻仍然實施的案件,被害人自身是風險的控制和支配者,而其他人則僅扮演著參與的角色;后者則指明知他人實施的某種行為存在著風險卻仍然參與的案件,其他人是風險的控制和支配者,而被害人則是參與者。因為自我決定中還包括了一種在風險關鍵時刻轉身和反悔的自由。只有如此,才能稱得上是一個完整、充分的自由過程。而在他控風險型案件中,被害人在關鍵時刻的反悔和退卻的自由還需要通過他人的另一個決定才可能實現,因此,這是一個不完整的自由。由于被害人自身已經承受了損害,同時結合一般預防的考量,車浩教授認為,應該將責任分配給風險掌控者(24)車浩:《過失犯中的被害人同意與被害人自陷風險》,載《政治與法律》2014年第5期,第32頁。。
但是,筆者認為,車浩教授的主張一方面無法完全涵蓋被害人自陷風險的情形,特別是人們基于事前的視角無法區分誰是行為人、誰是被害人的情形。在此,風險實現后落在何人身上,完全取決于偶然。例如,甲和乙輪流玩轉輪手槍輪盤賭,手槍中僅放入一枚子彈,甲轉動手槍后朝乙開槍,乙安全無恙后換乙對甲開槍,兩人輪流進行了多輪的游戲,直至有一個人受傷。在這種情形中,行為人和被害人的角色從事后的角度來看,完全是隨機分配的。但如果人們要求幸運者對此負責,某種程度上似乎使刑事責任的確定取決于偶然。因為當事人對整個危險歷程作出了同等程度的貢獻,也承擔了相同的風險,并同等程度地預見到了危險。此外,當行為人和被害人同時具有風險支配/控制時,人們無法根據這一標準作出正確的歸類,典型的例子就是“汽車沖浪案”。行為人負責開車,被害人則躺在車頂上抓住車窗邊緣,在一次轉彎過程中,由于離心力過大,被害人被甩出來并因此遭受傷害。此一情形中,行為人的危險支配體現在開車轉彎的行為,被害人的危險支配則表現在未能抓緊車窗邊緣。
另一方面,車浩教授的“關鍵時刻轉身和反悔的自由”某種程度上等同于自殺/他殺的區分標準(即導致死亡結果出現的最后一個行為)。只有當被害人自己逾越了所有的障礙而實施了直接導致其死亡的行為時,我們才能說被害人對自己的生命作出了一個自主的決定,需由其自行負責。這一論述在德國法下有其實定法背景,德國法不處罰幫助自殺罪但處罰受囑托殺人罪。但從我國的實定法來看,立法者并沒有做類似的安排,實務往往也將幫助自殺的行為當作殺人行為來論處。并且,從自由完整性的角度來看,車浩教授認為,在他控風險型案件中,由于被害人在關鍵時刻的反悔和退卻的自由還需要通過他人的另一個決定才可能實現,因此,這是一個不完整的自由。但事實上,在自控風險型案件中,即便被害人掌控著風險,但如果他想要在關鍵時刻退卻,事實上也可能必須依賴很多的外在條件。例如,甲為乙提供毒品,初次嘗試毒品的乙在大量注射之后感到后悔,決定在即將昏迷之前請人聯系醫院治療。但乙能否聯系到醫院,從而從危險中全身而退,是取決于很多外在條件的,例如他身邊剛好有電話、有人愿意幫他撥打電話,以及醫院有空余的床位。為何當被害人依賴于行為人(的決定)時,被害人的自由就是一個不完整的自由,而當被害人依賴于外在條件時,他的自由就是一個完整的自由?這明顯是存在矛盾的。
(二)區分的可行性:其他區分標準
從學說上講,其他的區分標準主要有對危險情形的(完整)認識、法所不容許的風險創設、被害人的信賴以及危險情境中的利益歸屬,具體內容如下所示:
1.對危險情形的(完整)認識說
奧托(Otto)認為,如果根據時間序列上直接導致侵害發生的最后一個行為來劃分自我危殆化和他者危殆化,會導致可罰性取決于偶然,因為這樣的做法忽略了危險歷程的不法內涵(25)與之相反,按照Otto的觀點,對于自我負責的自我損害和得同意的他者損害必須按照直接導致損害(身體傷害或死亡)發生的行為來區分。因為該行為具有法益支配性格,Vgl. Otto, FS-Tr?ndle, 1989, S. 175.。由于當事人均認為結果不會發生,因此,誰負責去實施那個直接導致結果發生的最后一個行為,就是一件非常隨機的事情。就此而論,何人實施最后一個行為無法表征支配法益的性格(26)Vgl. Otto, FS-Tr?ndle, 1989, S. 170.。因此,奧托選擇與外部的行為歷程相脫鉤,而直接訴諸嚴格規范化的責任范圍劃分:過失犯的正犯是指,對法益侵害直接負有責任的人,換言之,如果行為人原本能夠掌控事件歷程,從而避免結果發生,且行為人對結果發生具有可預見性,則行為人構成過失犯的正犯。對于事件歷程的掌控,是責任范圍劃分的重要標準。從這個意義而言,奧托提到,自我危殆化和得同意的他者危殆化在結果上是相同的。如果被害人已經預見到了風險,卻仍自我負責地接受風險,則可以中斷此種(通過掌控可能性建構出來的)歸責關聯。
有別于通說見解,奧托主張,如果被害人已經充分地認識到了風險及其決定的射程范圍,卻仍然將自己置于風險之中,均構成自我負責的自我危殆化。換言之,一旦滿足上述要求,即便其他行為人參與了危險的制造和發展,均能根據自主原則或自我負責原則來排除其他行為人對危險現實的責任,除非行為人相對于被害人而言具有特殊的監護義務(27)Vgl. Otto, FS-Tr?ndle, 1989, S. 172.。對于奧托而言,起決定性作用的不是行為人的參與行為與風險(現實化)之間的因果關聯,而是法益持有者認識到自己將陷入何種危險情形之中。因此,奧托將他者危殆化局限在這種情形上,即,其他的行為人相較于被害人具有優勢認知(überlegenes Sachwissen)。無論是單獨還是共同支配危險歷程,具有優勢認知(所謂的認識或錯誤支配)的人均能通過優勢認知使其犯罪貢獻成為他者危殆化的情形(28)Vgl. Otto, FS-Tr?ndle, 1989, S. 174.。就此而論,奧托已經將被害人自陷風險的類型區分及其在刑法上的處理結果直接掛鉤:參與自我危殆化總是不可罰的,而他者危殆化總是可罰的。
從上述觀點來看,奧托已經將他者危殆化限縮到非常狹窄的范圍,乃至于非常接近不區分被害人自陷風險的做法。按照奧托的見解,只有行為人相較于被害人具有優勢認知,才屬于他者危殆化,而他者危殆化總是可罰的。但從現在的學說來看,對于自我負責性的判斷而言,真正起決定作用的并非行為人相對于被害人的優勢認知,而僅僅在于被害人是否具有足夠的認知。穆爾曼也指出,盡管行為人的優勢認知對間接正犯的成立具有意義,但他和被害人的自我負責問題并不相關(29)Vgl. Murmann, Grundkurs Strafrecht, 2019, S. 192.。這些見解也已經反映在德國的實務判決中,最為明顯的例子就是BGH StV 2014,601。在該案中,被告人是一名醫生,其在所謂的替代性治療中經常會將含有鴉片制劑的止疼貼片開給具有海洛因毒癮的患者。被告人也認識到,他的病人有時會裝疼以獲得止疼貼片。他們在拿到貼片后,會將貼片煮沸,并用靜脈注射那些物質,最后有兩名病人因此不幸死亡。地方法院認為,被告人作為醫生具有認知優勢,并否定被害人自我負責的自我危殆化的成立。但是,德國聯邦最高法院認為,本案中起到決定性作用的因素是被害人對“其行為的法益關聯風險”的認識,與醫療關聯的確切知識是不必要的。對于那些長期吸毒的受害者而言,他們已經認識到了與法益相關的風險(30)Vgl. Roxin/Greco, Strafrecht AT I, 2020, S. 509 f.。
2.法所不容許的風險創設說
穆爾曼主張根據構成要件該當行為來區分自我危殆化和他者危殆化,并進行一種虛擬的檢測,即,假設行為人所采取的危殆化行為(就已經發生的實害結果而言)違反了被害人的意思,這一行為是否會被禁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話,則屬于他者危殆化的情形,原則上是可罰的;反之,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話,則屬于自我危殆化,原則上是不可罰的。他者危殆化意味著構成要件上的不法,只有通過考慮被害人具體的決定(即被害人承諾)才能阻卻違法性。相反,無論被害人的具體決定為何,參與他人自我危殆化的行為均未該當構成要件(31)Vgl. Murmann, Grundkurs Strafrecht, 2019, S. 196 ff.。
筆者認為,雖然穆爾曼是從規范意義上進行分類的,但其見解歸根到底可能同樣接近不區分被害人自陷風險的結論。具體而言,因為穆爾曼將被害人自陷風險的前提錯誤地當成被害人自陷風險的劃分標準,這一做法不僅徒勞地擴張了被害人自陷風險的范圍,某種程度上也已經將大部分被害人自陷風險的情形歸為他者危殆化的情形,絕大多數的被害人自陷風險案件最終也將會變成被害人承諾的問題。具體而言,被害人自陷風險的前提條件就是行為人已經制造了法所不容許的風險。普珀(Puppe)指出,無論是參與他人的自我危殆化,還是得同意的他者危殆化,從被害人法益的視角來看,參與人的行為均違反了注意義務(32)Vgl. Puppe, Strafrecht AT, 2019, S. 92.。反面而言,只要行為人在違背被害人意思的情形下所實施的危殆化行為不為法律所禁止,這就已經意味著行為人的行為得到了規范的容許,行為人的行為此時根本就不構成任何的不法。在這種情形下,無論是否違反被害人的意思,均不會影響到“沒有不法”的結論,這樣,當然也就沒有必要去討論被害人的自我負責是否會對行為人的不法產生影響。
3.被害人的信賴說
察齊克(Zaczyk)認為,個人行為的理性需要通過客觀性予以丈量,而這種客觀性的本源在于個人的自我決定權。故而,自我決定權并不會導致刑法的限縮,毋寧說,人們在建構刑法時必須將自我決定權納入考量,作為刑法根基的自我決定權不能被動搖。并且,作為刑法上具有重要意義的行為,它必須具有所謂的“人際關聯”(Interpersonalbezug)。在察齊克看來,不法必須是一種對他人自由的損害。自我損害行為由于不涉及他人的自由,因此,它不是刑事不法行為(33)Vgl. Zaczyk, Strafrechtliches Unrecht und die Selbstverantwortung des Verletzten, 1993, S. 25 ff.。
對于有認識的自我危殆化行為,由于被害人并不意欲結果的出現,此時無法直接形成一個“意思、行為和結果的統一體”。在此種情形下,必須去判斷行為人的行為是否構成過失不法。具體而言,如果被害人已經預見到其行為可能導致的結果,卻仍然自陷風險或不回避危險,則構成有認識的自我危殆化。但是,當行為人和被害人之間存在著行為關聯,且行為人行為和被害人行為的共同作用導致了構成要件結果的出現時,起到決定性作用的是行為人是否將被害人的法益置于偶然之中。在此,必須進行一個二階段的審查:第一個階段是確認在法所確定的形態上(in rechtlich fester Form),被害人能否信賴他人通過符合注意義務的行為去支配(導致實害發生的)事件歷程。如果被害人具有此等信賴的話,則屬于他者危殆化的情形,行為人必須對整個事件歷程負責。反之,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話,則必須進行第二階段的審查,即在法所確定的形態上,被害人能否信賴自己完全沒有自陷風險的可能性。如果被害人對此具有信賴,則行為人必須對結果負責。不過,這種情形只能是一種例外(34)Vgl. Zaczyk, Strafrechtliches Unrecht und die Selbstverantwortung des Verletzten, 1993, S. 56 ff.。如果被害人具有上述的任何一種信賴,均可認為行為人的行為存在義務違反(35)Vgl. Zaczyk, Strafrechtliches Unrecht und die Selbstverantwortung des Verletzten, 1993, S. 56 ff.。
本文認為,察齊克通過被害人的信賴去界定自我危殆化的做法并不妥當。
第一,被害人的信賴是如何被建構出來的,事實上并不明確。在其《刑事不法與被害人的自我負責》一書中,察齊克根據自己的見解對德國實務中出現的案例加以驗證。在“梅梅爾河案”中,由于船夫已經向乘客指明了在下雨天渡船的危險性和不可支配性,因此,察齊克認為,乘客不應信賴船夫能夠支配這種風險,故而,此一情形屬于自我危殆化的情形。相反,雖然乘客認識到司機因為大量喝酒而不具有駕駛能力,但乘客仍搭乘司機的汽車,此時,察齊克卻認為,乘客還是信賴司機能夠根據自己的駕駛能力調整自己的駕駛行為或(根據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規定)停止駕駛行為,故而,本案屬于他者危殆化的情形。但為何被害人可以信賴行為人能夠支配這種危險歷程,答案并不明確(36)Vgl. Jetzer, Einverst?ndliche Fremdgef?hrdung im Strafrecht, 2015, S. 80 f.。
第二,在法律上建構被害人的信賴這一做法與察齊克的基本立場相違背,甚至可能出現與現實相悖的情形。按照察齊克的說法,所謂的刑事不法是指對于“法律上構建的基本信賴”的明顯侵害。此時,個人可以信賴,自己在不實施任何作為的情形下也不會遭受他人的危害,自己不會成為他人手中的玩物。不過,這一解釋方式仍有值得商榷的地方:首先,如果被害人不具有事實上的信賴,人們可否超出事實而在法律上構建出這種信賴?按照羅克辛的說法,當職業義務者選擇從事某項危險的行業時,他在事實上就已經預見到自己在將來存在著自陷風險的可能,這也就意味著他在事實上已經放棄了不自陷風險的信賴。其次,當被害人在事實上不具有這種信賴,但我們仍然在法律上為他構建出這種信賴,某種程度上已經無異于采取了家長主義的立場,而這明顯是與察齊克的基本論述相違背。按照察齊克的說法,刑法的根基是自由,它當然也包括了“人能自行確定自己信賴什么”的自由。穆爾曼在指出察齊克方案的家長主義傾向的同時,也表示:“國家從哪里取得保護個人使其免遭自我損害的權限,以及個人基于何種原因需要這種保護,是令人難以理解的。”(37)Vgl. Murmann, Die Selbstverantwortung des Opfers im Strafrecht, 2005, S. 400.最后,如果可以脫離事實層面而直接在法律層面建構被害人的信賴,會導致很多不合常理的情形。正如諾伊曼(Neumann)舉出的例子,如果吸毒者在法律上可以信賴“毒販不能將毒品賣給自己”,從而使責任從吸毒者轉移到販毒者,那將是非常“可笑的”(38)Vgl. Neumann, GA 1996, 38 f.。
四、結論
第一,從德國實務來看,雖然德國聯邦最高法院在“海洛因注射器案”中提出了自我危殆化的概念,并在“加速測試案”中主張用危險支配說來區分自我危殆化和他者危殆化,但這一做法除了錯誤運用舉重明輕的推論外,還因為將故意犯的正犯/共犯區分標準直接運用到過失犯上而忽視了過失犯的獨特性。此外,危險支配說還存在著諸多不足的地方,如危險支配說無法妥當地處理當事人具有共同的危險支配的情形;危險支配說所導出的結論取決于對危險歷程的描述程度,容易導致恣意的結論等。因此,危險支配說無法成為自我危殆化和他者危殆化的區分標準。
第二,從區分的必要性來看,主張區分說的論者主要是從風險的角度或自由的完整性角度去論證自我危殆化和他者危殆化之間的差異,這主要體現在被害人對危險進程的可預見性和掌控性、結果回避的可能性。但事實上,這種差異并不是必然的。毋寧說,自我危殆化和他者危殆化的區分其實是一種循環論證,即當人們假設這兩者是兩種獨立的案例類型時,就需要訴諸特定的標準,但這個標準又會反過來證實“自我危殆化和他者危殆化是兩種獨立的案例類型”這一假設,故而,有必要采取一個徹底的方法論步驟,即消除所有的理論預設和假定,回歸現象本身(39)Vgl.Stefanopoulou, Verantwortungsverteilung bei Opfermitwirkung,in:Markus Abraham/Jan Christoph Bublitz/Julia Geneuss/Paul Krell/Kilian Wegner (Hrsg.), Verletzte im Strafrecht, 2020, S. 99 f.。
第三,從區分的可行性來看,目前的區分標準(危險支配以及其他的區分標準)既不明確,也不周延。如果貿然運用這些區分標準對被害人自陷風險案件進行區分,并以此來聯結不同的法律后果,人們只能被迫在以下兩種選項中作出困難抉擇:第一個選項是,自我危殆化的情形本身不該當構成要件,其行為是不可罰的,而他者危殆化的情形則因為該當犯罪構成要件,必須通過被害人承諾來阻卻違法。但是,事實上,這樣的聯結并無必然性,因為在自我危殆化的情形下,行為人的參與行為也可能具有可罰性,如行為人縱火,導致消防隊員在救火的過程中不幸遇難。第二種選項則是采取羅克辛的做法,在一定條件下將他者危殆化的情形等同于自我危殆化的情形來處理,但這也意味著區分已經不具有絕對的意義。
另外,區分說的主張還會對目前的犯罪參與體系、被害人承諾的教義學產生沖擊,但這種沖擊是否有其必要性,還有待商榷。例如,為了能夠在過失犯的范圍中使用共犯論證,危險支配說需要進一步主張過失犯的犯罪參與體系和故意犯的犯罪參與體系是一樣的,必須區分正犯和共犯。雖然學說上有論者嘗試區分過失犯的犯罪參與形式,但目前的嘗試仍未成功,其結果無法令人完全信服。在這種情形下,應當認為過失犯的正犯和“共犯”在本質上不存在差異。既然如此,在被害人自陷風險的情形中,也不宜通過危險支配的標準去創設例外。因此,應當將“參與他人的自我危殆化”和“得同意的他者危殆化”在刑法上作等同處理。
基于上述批判,本文認為,由于過失犯不區分正犯、共犯,只要行為人違反義務地導致了構成要件結果的實現,就構成過失犯。從被害人自陷風險的基本模型來看,只要行為人過失地對危險進程作出行為貢獻,他就不是不可罰的“參與他人自我負責的自我危殆化”,而是“以正犯身份參與的他者危殆化”。此時,需要進一步從自我負責原則的觀點去劃定處罰的范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