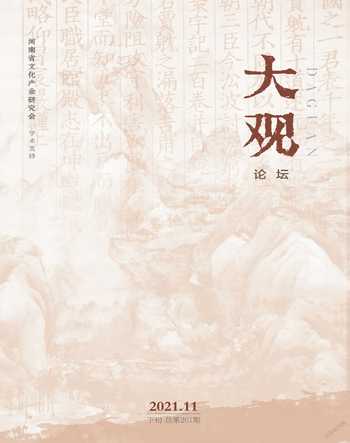當代戲劇集體創作現象辨析
摘 要:中國戲劇概念源于西方戲劇理論,在我國近代學者的研究下,戲劇概念得以明確,并與戲曲進行了區分。但嚴格意義上講,中國戲劇源自話劇。無論是國內戲劇,還是國外戲劇,現有創作內容、形式呈現出多樣化發展態勢,其中所蘊含的思想文化也各有不同,但在創作形式上,卻體現出集體創作現象。以當代戲劇發展為起始點,分析當代戲劇與集體創作之間的關系,并針對集體創作現象進行辨析,對于戲劇的長遠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現代戲劇;創作形式;集體創作
戲劇作為一種綜合藝術表現形式,包含了演員、觀眾、空間三要素,通過三者形成的觀演關系,最終呈現一出完整的戲劇演出。隨著文化藝術的發展,現代戲劇內容日益豐富,形式多樣的戲劇演出層出不窮,發展勢頭良好。戲劇創作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戲劇的發展,然而如今戲劇市場的集體創作現象非常明顯,這十分值得深入探討和研究。
一、當代戲劇的多元化發展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在國家“雙百”方針指導下,舊戲劇以及新戲劇形式都得到了完善與發展。后來,我國戲劇呈現出民族化、大眾化發展趨勢,老舍的《茶館》、郭沫若的《蔡文姬》等優秀戲劇作品進入人們的視野。在歌劇中,《紅霞》《紅珊瑚》等優秀作品呈現在人們眼前。1978年以后,戲劇發展開啟了新篇章,戲劇作品無論是在數量、質量方面,還是在深度、廣度方面,都有了巨大突破。陳白塵的《大風歌》、魏明倫的《四姑娘》以及沙葉新的《陳毅市長》等作品涌現出來,戲劇呈現出百花齊放的景象。
此外,莎士比亞、契訶夫、蕭伯納等歐洲劇作家也被我國人民熟知。這些劇作家所創作的戲劇在我國得到傳播與欣賞。我國戲劇創作者把莎士比亞戲劇移植到中國戲曲中,使二者形成優勢互補。隨著中西方文化的交融,不少現代西方戲劇也逐漸登上中國舞臺,如貝克特創作的《等待戈多》、米勒創作的《推銷員之死》、奧尼爾創作的《漫長的一天到黑夜》等。
二、當代戲劇與集體創作的關系
后現代戲劇脫胎自20世紀60年代驟起的后現代主義哲學思潮,呈現出與現代主義戲劇對抗的姿態。雖然理論界對于什么是后現代戲劇仍舊是眾說紛紜,但后現代戲劇演出早已在當代劇場中“亮相”,并呈現出熱鬧非凡的景象。法國太陽劇社的戲劇、謝克納的環境戲劇、國內孟京輝創作的戲劇作品、一些地方戲劇節如烏鎮戲劇節上出現的年輕創作者的大量戲劇作品,紛紛映入受眾視野,雖然其中部分創作者并沒有明確定位為后現代,但其藝術精神、創作指導思想等,都流露出后現代創作風格。這類作品無論在形式上還是在內容上都不盡相同,而它們的創作形式都是集體創作。后現代戲劇與集體創作,究竟是誰選擇了誰,很難清晰地劃分。可是既然存在集體創作這一現象,也就意味著存在著某些必然性。深入分析這一現象,不難發現,與后現代價值觀有著緊密聯系。后現代戲劇創作突破了以往對“雅”“俗”定義的劃分,大眾掌控話語權的通俗文化地位日益提升,這對戲劇的權威、精英領導的局面造成了很大挑戰[1]。
三、當代戲劇的集體創作現象辨析
(一)劇作者失去戲劇控制權
當代戲劇與集體創作的關系并不能通過只言片語解釋清楚,還需要在實踐中進行深入的探析。以孟京輝導演創作的戲劇作品《尋歡作樂》為例,該劇作于2014年4月在蜂巢劇場連續上演三周。孟京輝導演改變了以往了戲劇創作模式,對戲劇進行了創新,在戲劇一開場,通過三個身著黑色衣服的演員吸引觀眾的眼球。這三人穿著黑衣、黑褲,戴著黑墨鏡,激發了現場觀眾的好奇心,而后三人突然進行了一段狂野的說唱,末尾句的“快樂是什么?”突出戲劇主題。該劇作并沒有遵循以往已經形成定式的戲劇演出方式,也毫無劇情可言,演員們只是按照26個英文字母從A到Z的順序,借助關鍵詞的暗示進行表演,呈現出一個啼笑皆非的戀愛故事,包括大師授課的故事,使得劇場觀眾笑聲不斷,獲得很好的反響。但讓觀眾發出笑聲的點,并非戲劇中的人物或者情節,主要來自獨具特色的臺詞和特有的表演風格。該劇作還改變了以往大家熟悉的精巧的戲劇結構,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從《尋歡作樂》的各個段落來看,各個段落對應整個劇作的主旨,演員在導演的指導下完成了精彩的戲劇表演。《尋歡作樂》的每個段落都有一個小高潮,而后采用峰回路轉的手段,構建出一個完整的戲劇[2]。
與以往戲劇形式相比,后現代戲劇在文本處理方面,改變固有模式,更加大膽、奔放,部分處理方式甚至可以稱得上“野蠻”,分解了以往經典模式,改變了線性文本。后現代戲劇在不斷發展實踐中,改變了較為完整的傳統戲劇結構,更多地采用碎片化的情節、夢囈般的臺詞,一些情節甚至看起來不符合邏輯。不再照搬現有文本,而采用即興創作的方式,是后現代戲劇一個非常重要的特點。在后現代戲劇創作過程中,戲劇創作者失去了權威性,為戲劇導演、演員提供了良好的、廣闊的創作空間,促使集體創作蓬勃發展。
(二)導演的權威發生改變
在當代戲劇中,導演的權威也在發生改變,但改變得并不明顯。雖然整體上看,一個戲劇舞臺的呈現都出自導演,但實質上,導演的職能變化較大。從集體創作、工作坊看,無論是演員還是配合營造舞臺效果的工作人員,他們都不是導演實現理想的載體,而是更多地為自己發聲,是補充、延伸導演想法的創造者,有些甚至直接改變了導演最初的構思,進而呈現出全新的戲劇演出樣式。在很多后現代戲劇中,一些舞臺設計師、演員本身就是一個導演,而很多后現代導演卻成為劇作策劃者。法國女導演姆努什金曾說過,導演需要充分利用好權利,去挖掘超過戲劇形式的情景,在戲劇中,并沒有嚴格意義上的導演、演員、舞臺技工的區分,任何一個人都可能合作。這就意味著,在一臺戲劇表現中,導演、演員、舞臺設計者等人員都是這臺戲劇的創作者,不再是局限于導演一人的戲劇[3]。在集體創作模式下,戲劇導演的職能必然會發生轉變,就如同教育領域一般,教師需要改變“一言堂”的教學模式,而給予學生更多的自主性。戲劇創作更是如此,在集體創作模式下,導演不再是一人指揮,讓萬人執行,更多是進行領導、指引、協助的工作[4]。導演需要意識到自身戲劇創作角色轉變,在后現代戲劇人集體創作中,促使各方建立平等、尊重、信任的關系,從而使戲劇演出呈現更好的效果。
(三)藝術家與觀眾關系發生轉變
后現代戲劇改變了以往藝術家與觀眾之間不平等的關系。戲劇工作中由精英領導的局面被打破,藝術家們不能再以高高在上的姿態引導、教化觀眾。此外,以往權威化、貴族化的觀眾,也不是觀眾席上的核心,藝術家們并不需要像以往一樣,盲目地迎合這些權威、貴族而創作,不需要趨炎附勢。在后現代戲劇中,藝術家們與觀眾之間是平等的關系,這在某種意義上,可謂是與觀眾一同進行集體創作。集體創作的非常重要的特點是即興、直覺、未知,需要創作者不斷探究[5]。而觀眾參與其中,在很大程度上使得集體創作優勢發揮到極致。事實上,好的戲劇,不僅僅體現在戲劇人在舞臺上的呈現,更多的應當是融合了觀眾對演出的分析、融入,甚至促進了戲劇表演效果。這一作用有隱性,也有主觀能動性,但無論怎樣,觀眾都是后現代戲劇集體創作模式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四、結語
戲劇經過了長久發展,編劇、導演、演員成為創作核心,也有反向的,即按照觀眾好惡,向外輻射。但普遍存在的集體創作都是虛假的,不真實的。通過對當代戲劇集體創作現象進行分析探索,不難發現,后現代價值觀下,以往的劇作者戲劇控制權、精英領導不復存在,而集體創作在這種平等、全員參與的指導思想下,得到了發展并壯大,推動了戲劇發展。
參考文獻:
[1]錢玨.關于后現代戲劇與集體創作的一點思考[J].上海戲劇,2016(4):40-43.
[2]袁盛勇.集體創作與后期延安文藝戲劇作品的形成:以《逼上梁山》和《三打祝家莊》的創制為中心[J].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6(3):124-141.
[3]首作帝.中國新文學集體創作研究(1928—1976)[D].武漢:華中師范大學,2010.
[4]龔玉嬌.我國當代戲劇“集體創作”現象辨析[J].戲劇文學,2021(1):4-11.
[5]陳夢梵. 陜西省戲曲研究院戲曲現代戲劇本創作研究[D].上海:上海戲劇學院,2021.
作者簡介:
楊洋,云南藝術學院戲劇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為戲劇影視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