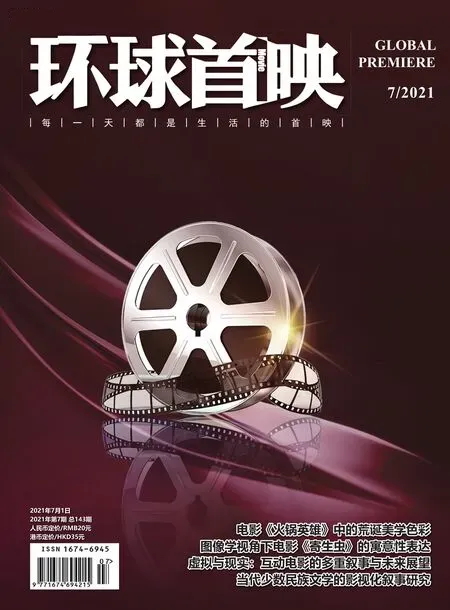作為互動儀式的網絡直播研究
禹小芳 重慶第二師范學院文學與傳媒學院
一、互動儀式鏈理論
當代美國社會學家蘭德爾·柯林斯提出的互動儀式鏈理論為研究微觀社會情境提供了理論基礎。柯林斯認為,互動儀式是人們最基本的活動,整個社會可以看作一個長的互動儀式鏈,人們從一種際遇流動到另一種際遇,不同水平的際遇形成了不同的互動儀式。在網絡直播中,主播和粉絲用戶聚集在一個虛擬的直播間,借助現代科技完成實時社交互動。在這一過程中,主播和粉絲用戶都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自我呈現和互動交往,從這個意義上來看,每一場直播都是一場社交際遇,都是一場互動儀式。可以說,無論從個體角度,還是社會層面,網絡直播都已經成為當下最重要的局部際遇空間,是社會互動儀式鏈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網絡直播互動儀式的建構
(一)虛擬的際遇空間
柯林斯指出,互動儀式是一個身體經歷的過程,只有實現身體的聚集,才能開啟互動儀式,也就是說,至少有兩個人聚集在同一場所才能啟動互動儀式。在網絡直播中,主播和粉絲用戶共同聚集在同一個直播間內,主播通過語言和肢體語言與粉絲用戶進行互動,粉絲用戶通過發送彈幕,點贊,打賞等行為與主播及其他的粉絲用戶進行互動。雖然這一過程中沒有滿足柯林斯所謂的身體聚集這一條件,但直播間這一虛擬的際遇空間也成功營造了互動儀式的具體場景。
雖然柯林斯強調了親身在場在互動儀式中的重要性,但他同時也指出,儀式成功與否的核心是互動儀式中相互關注和情感連帶的程度,成員身體的聚集只是讓互動儀式更容易成功,因為當成員處于同一物理空間,不管他們是否有意識地關注對方,都能通過身體在場相互影響,激起成員的神經系統,產生個體情感能量和團結感,相反,沒有親身到場,就難以表示對群體的參與,也難以確定一個人的群體成員身份,這會阻礙互動儀式的開展。雖然網絡直播的際遇空間是虛擬的,參與者并沒有親身在場,當下的技術也沒有達到柯林斯想象的通過神經系統收發信號,但是網絡直播平臺克服了這一障礙,平臺上,每一個主播都有一個直播間,具有一個區別身份的虛擬名字,每一個粉絲用戶也都有一個虛擬的代號,每當有粉絲成員進入直播間,直播屏幕上會有彈幕提示“某某進入直播間”,這種提示對于新進入者和直播間內的人來說,都能提供一種參與其中的感受。
(二)清晰的成員界限
網絡直播儀式設定了多重界限,并以此維系粉絲社群。
直播平臺以超低的準入門檻吸引大量網民參與到直播中。參與者只需要安裝相應的直播應用程序,并完成注冊等一系列較為簡單的儀式就能進入直播平臺,參與到時下最風靡的網絡社交狂歡中與自己喜愛的主播、自己歸屬的群體虛擬共在。第一重界限沒有明顯的排外性,甚至為了擴大用戶基數帶有明顯的討好意味。群際邊界感和對局外人的排斥從進入直播間開始。用戶一旦選擇進入某一直播間,通過觀看直播內容,發送彈幕評論,打賞主播等行為參與直播儀式中,就排除了這一直播房間外的用戶,與此同時直播間實時的人數統計時刻提醒著粉絲用戶這是一個有邊界的群體。
已經在直播間中的群體也被平臺精心地分為不同層次,這就是柯林斯所說的地位儀式。在直播這場互動儀式中,主播作為核心,是關注的焦點,是社交明星,以最高的熱情投入到互動儀式中,收獲最多的情感能量;緊緊圍繞在主播周圍的是參與度較高的粉絲觀眾,他們也沉浸在這場互動儀式中,他們不僅可以獲得主播的關注,也可以憑借大額度打賞,與主播互動等行為收獲來自直播間其他觀眾的贊許、尊敬和關注;處于群體邊緣的人是剛剛具有成員身份,剛剛來到直播間的人,他們的參與度最低,是被忽略的邊緣人,他們受到互動儀式的影響,極力想要通過某種方式提升自己的儀式地位。這種儀式地位的分層以觀看者的物質和符號資本的投入為衡量標準,這一現實生活中常用的衡量標準讓網絡直播互動儀式的不平衡以一種隱秘的方式合理化。物質資本主要以打賞的形式體現,符號資本主要是圍繞主播和直播間在以往的互動儀式中建構起來的帶有邊界性和群體性的符號體系,一般是口頭禪、行話等語言符號。這些特定符號的理解需要建立在對主播和直播間長期關注的基礎上,不屬于群體內部的人很可能無法正確解讀。物質資本和符號資本的不均衡讓群體成員地位分層,構成了群體成員的身份認同,同時也刺激了互動儀式鏈的延續,吸引用戶長期參與其中。
(三)共同的關注焦點
網絡直播互動儀式使直播間的成員注意力集中在共同的對象上,并通過彼此互動使焦點更加集中。
網絡直播的互動場景就是主播的直播間。從粉絲用戶終端屏幕看,主播的直播間主要包括兩部分,主播直播的實時影像區域和粉絲彈幕禮物區域,其中主播的實時影像區域占據最核心、最主要的位置。這樣的空間設定讓進入直播間的粉絲用戶的注意力被迫集中在主播的直播畫面中,關注畫面中主播的一舉一動,以及直播間里的背景細節等。作為一種盈利性的社交儀式,為了讓整個直播過程吸引更多粉絲,獲得更多點贊打賞,主播會人為地設計一些看似不經意的戲劇性爆點。這種人為設計往往有較好的效果,會瞬間引爆整個直播間氛圍,讓整個直播間的關注點高度集中在某一特定行為、語言或者場景中。
但是,正如柯林斯所言,當參與儀式的人不能共處同一物理空間,需要借助遠程傳播的時候,一個成功的互動儀式傳遞的內容不能只是表演者的信息,更重要的是觀眾的熱情。在網絡直播中,主播的直播儀式成功與否,關鍵還在于觀眾的熱情是否能夠有效表達出來,實現集體興奮。因此,主播精心設計的戲劇性爆點和直播平臺發明的彈幕儀式、禮物打賞儀式就在不知不覺中促成了粉絲用戶實現集體共鳴。鋪天蓋地的彈幕禮儀和眼花繚亂的打賞禮物代替了鼓掌聲、歡呼聲,每個參與者的全部注意力都被框定在直播屏幕內,身處異地的用戶們實現了高度的情感連帶。
(四)共享的情緒體驗
互動儀式的成功啟動需要儀式的參與者分享共同的情緒狀態。正如柯林斯所言,儀式開始時,成員擁有哪種情感狀態并不重要,互動儀式具有轉化情感的作用。一開始,用戶可能帶著熱情、悲傷、冷漠、焦慮等各種情緒進入直播間,隨著直播儀式的推進,關注的焦點變得協調一致,主播和觀眾不斷強化彼此共同的情緒,進而體驗到“集體興奮”。
受到商業邏輯的影響,主播的價值被關注量、點贊數、打賞額等數據決定,而這些數據與直播互動中集體興奮的強度和數量有直接的關系。成功的直播互動儀式,主播往往能夠有意識的引導群體實現多次集體興奮。集體興奮最直觀的表現是大量彈幕蜂擁而至,鋪滿整個直播畫面。對于參與直播儀式的個體來說,發送彈幕是一種極具儀式化的行為,不僅證明了參與者在場,也表達了參與者此時有高昂的情緒體驗,所以彈幕通常具有到調動情緒氛圍的強大作用,能讓少數個體的高昂情緒體驗迅速凝聚成集體情緒。
除此之外,相對于日常語言和書面語言,直播中的彈幕語言更有助于互動群體實現情緒共享。因為彈幕語言從一出現就帶有明顯的情緒特征,具有建構情緒和表達情緒的雙重功能。作為一種互聯網文化,彈幕語言一般是網民結合具體情境以拼貼、挪用等形式創造出來的表達方式,生動傳神,言簡意賅,幾個字就能闡釋豐富完整的情緒意義,讓互動的群體快速理解,并實現個體情緒向集體情緒的轉變。而且,彈幕語言天然的娛樂性、趣味性和感染力,非常容易引起其他網民的關注和模仿,進而引發互動群體的彈幕狂歡。
三、網絡直播互動儀式的價值
(一)情感能量
低情感能量的個體,不僅會有身體的倦怠和退縮,社會互動也會變得消沉、被動。積極的情感能量有極大的價值,是人們社會互動的驅動力,人們需要通過與他人的不斷互動尋求情感能量的平衡和提升,所以人們總是傾向選擇能夠獲得最大情感能量回報的互動儀式。作為社交的成本,人們在互動中花費情感能量,尋求社交回報,如若沒有得到足夠的回報,就會轉向其他互動儀式。網絡直播就是一種成本收益較大的互動儀式,參與者因為共同的愛好來到了同一個直播間,分享著共同的關注焦點,體驗著共同的情緒,達到了高度的情感連帶,獲得了積極的情感能量。在這里,現實生活中的地位、權力和身份被消解,而以每周更新的打賞榜單的形式重構,顯而易見,如若個體想要實現身份地位的提升,在付出的成本上,直播間要遠遠低于現實社會。因此,與現實社會完全不同的社交法則,以及較高的成本收益使得網絡直播儀式成了當下互動儀式鏈中非常關鍵的一環,提供給人們更多平衡情感能量的選擇,讓人們更好地應對生活。
(二)群體團結
群體團結就是作為群體成員的身份感。正如柯林斯所言,19世紀以來,團結時刻不再依靠宗教、戰爭和政治儀式提供,而是由各種精心發明的互動儀式提供。網絡直播儀式能夠給參與者帶來一種團結感,一種對群體的依戀感,對主播的忠誠感。直播中參與者的情感共鳴程度越高,成員的團結和身份感就越強。在直播儀式中,共鳴的短期情感可能是高興、放松、溫暖、悲傷,但經由互動儀式轉化后的長期情感卻是內化于心的成員身份感,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主播的每一場直播都是在創造和強化參與者的身份感。
(三)群體符號
群體的團結感典型的集中在群體符號上。群體符號由成功的互動儀式所創造,一般是參與者有意識關注的某種東西。在直播中,群體符號通常都圍繞主播展開,包括主播自身、代表性的表演、個性化的互動方式、代表性話語等。正如上文所說,在直播中主播往往會有意識地策劃情感共鳴的瞬間,這種集體共鳴會生出群體符號,這些符號一經創造就成了參與者在直播情境中新的符號資本,會在未來的直播互動中被重復使用,重新喚起成員的身份感。
(四)群體道德感
充滿團結感的參與者心中往往會有一種強烈的道德感,不僅會格外尊重群體符號捍衛其以免受輕視和背棄,而且會積極維護群體內部的正義和秩序。在直播中,通常表現為對直播間有較高的忠誠度,在各種網絡行為中維護主播,并積極推動直播儀式。
四、結語
網絡直播這種儀式化社交場景之所以成功,就在于直播平臺對平臺功能和規則的精心設計,讓主播處于互動儀式的核心地位,讓所有儀式要素都得到了充分的體現,以實時仿真的互動場景讓不同空間的用戶實現了高度的相互關注和高度的情感共鳴,從而強化了參與者成員身份感,并為每一個參與者帶來情感能量,最終實現用戶與直播平臺相對穩定的情感聯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