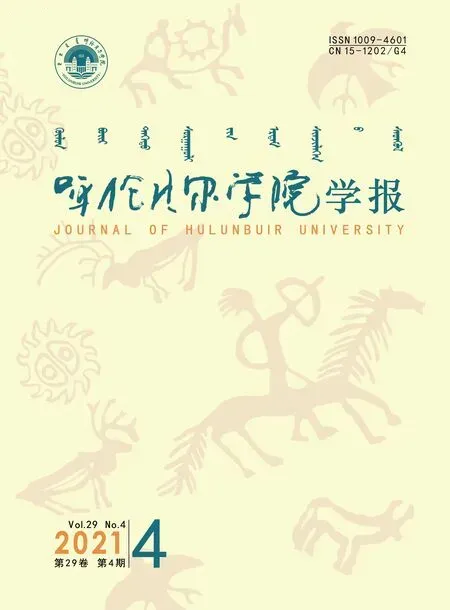“小產權房”法律問題研究
張耀軍
(煙臺大學 山東 煙臺 264005)
一﹑法律視角下“小產權房”的概念及其歷史成因
(一)“小產權房”的概念
我國現行法律規范中并沒有“小產權房”這個說法,它是法律規范制定之后形成的人們相對于大產權房而言對它的一個通俗叫法,而非正式名稱。對于“小產權房”概念的界定存在著不同的說法。有人認為,“小產權房”是集體利用農用地開發建造的,由集體為其頒發權屬證書,欠缺國家房管部門頒發的產權證明的房屋。有人認為,“小產權房”是集體未將農用地轉為國有建設用地,也未向國家繳納土地出讓金而建造的用于向本集體以外的人出售的商品房。還有人認為“小產權房” 是在農村經濟發展和城鎮化進程中,為解決集體成員的住房問題而建造的并允許向集體經濟組織以外的人出售的商品房。以上說法所介紹的“小產權房”雖用途各異,但均因其所利用的土地是集體所有的農用地而非是符合國家法律規定的國有建設用地,因而其缺乏法律支撐,自然無法取得房屋管理部門核發的房屋產權證,故其上市流轉均會受到不同程度的阻礙,相對于建造在國有建設用地上的房屋而言,在遵循房地一體主義的中國法下,土地利用上的不合法帶來了房屋產權的不合法,故而稱其為“小產權房”。綜上所述,筆者認為,“小產權房”就是指在城鄉二元體制的背景下,在非國有建設用地上建造的,不符合現行法規定的土地利用類型,而不能進入商品房交易市場的房屋。
(二)“小產權房”的歷史成因
“小產權房”之所以會廣泛存在,根源于法律對土地自由流轉的限制。2004年修訂的《土地管理法》(2019年已廢止)第63條規定:“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權不得出讓、轉讓或者出租用于非農業建設”。這表明在農村土地上需要使用土地進行建設時,必須轉換土地性質,將農業用地變為國有建設用地。這帶來了法律上的沖突和土地流轉利益上的博弈。其一,我國《憲法》并未禁止土地使用權的轉讓,但是農村集體土地的入市流轉卻受到了《土地管理法》規制,這與憲法規定產生沖突,按照法的效力位階來看,這樣的規定顯然是違憲的。我國《民法典》規定物權平等原則,落實到土地上,城市和集體土地應平等對待和保護,《憲法》和《土地管理法》在規定上的沖突導致城市的土地可以進入市場進行流轉,而集體的土地在流轉上則受到相關法律和政策的限制,這就導致“小產權房”的購房者獲得的房產證并非由國家頒發,而是由集體頒發,由此產生“小產權房”問題。加之集體土地的價格遠低于城市建設用地的價格,出售“小產權房”給集體帶來的巨大利潤,城市的購房者也愿意花更少的錢購得集體房屋,法律的沖突和對集體土地流轉的限制催生了“小產權房”市場。其二,政府參與集體土地所有者的土地利益分配是“小產權房”市場形成的經濟根源。集體土地經過政府征收方式才可以轉為國家所有的土地,再經過合法審批才可以在該土地上建造商品房從而出售。開發商用于開發建設的土地,只能由政府提供。政府是征地并向開發商提供土地的唯一合法主體。舊的《土地管理法》要求村集體或開發商若要將在集體土地上開發的房屋入市,就必須將土地性質變為國有建設用地,而開發商用于開發建設的土地,只能由政府提供。“小產權房”的出現,減少了政府環節,剔除了政府通過征收土地參與土地性質轉變的過程,土地所有者和土地征收者之間的利益沖突成為“小產權房”出現的經濟上的原因。
二、“小產權房”面臨的法律困境及其破解
“小產權房”面臨的法律困境實質是集體所占據土地使用權不能自由流轉的問題。阻礙城鄉建設用地的流通,勢必會造成效率的損失,允許集體所占據土地使用權自由上市流通,有助于打破土地流通壁壘,促進土地資源高效流動。新修訂的《土地管理法》第63條規定,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城鄉規劃確定為工業、商業等經營性用途,并經依法登記的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土地所有權人可以通過出讓、出租等方式交由單位或者個人使用。這一規定為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流轉提供了法律依據,并能有效解決之后出現的“小產權房”問題。然而,新修訂的《土地管理法》通過之前的“小產權房”如何處理,能否轉正,仍有待解決。除土地使用權流轉的問題外,“小產權房”同樣還面臨著集體土地所有權的權利主體不明確,導致集體土地所有權虛置的問題。
(一)在法律上分類處理歷史上形成的“小產權房”
現實地看,我國之所以涌現出大量的“小產權房”,完全是不合理的用地制度造成的,新修訂的《土地管理法》有效解決了這一問題。面對已有的“小產權房”,對其處理不能搞一刀切,不同類型的“小產權房”應在建造和流轉兩方面進行分析處理。對于現實中存在的違反國家土地和建設規劃,建造在基本農田和耕地上的根本性違法“小產權房”,因這類“小產權房”嚴重違反了國家對農用地的保護政策,應將其認定為違法建筑,通過行政法層面否定其合法性并予以拆除,通過行政法上的監督和限制來杜絕今后產生的此類“小產權房”。宅基地型“小產權房”是指在宅基地上建造的用于自我居住或用于出售的房屋。在宅基地上建設房屋,無論用于自身居住還是用于出賣,其建造和存在的本身并不違法。因此,在宅基地上建造房屋,只要符合建設規劃的相關規定,該建設便屬于合法建設。在流轉上,由于宅基地是無償賦予本村集體成員的一種社會保障,因此其取得和轉讓都存在特殊性。該權利雖然在期限上是無限的,但其在流轉上應受到限制。宅基地本來就是國家安排給本村集體成員用于基本住房保障的,當將其售予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以外的他人會損害本村集體成員利益,限制其流轉體現的是國家保護農民基本住宅的宗旨。因此,在宅基地上建造的房產上市流轉因會損害社會公共利益或國家利益而致合同無效。由于這種情況下買受人即使占有使用了房屋也無法進行房屋所有權轉移登記,在遇到司法糾紛時就會在司法層面否定宅基地性“小產權房”流轉的合法性。至于歷史上形成的在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建造的“小產權房”,在新修訂的《土地管理法》通過后,對于不符合規劃要求、建筑質量不合格的部分,應直接定性為違法建筑予以拆除,在拆除時應給予原購買價的補償,因為“小產權房”的形成與地方政府的懶政甚至慫恿是分不開的,政府應為此付出一定的財政代價,而不能無視購房者的信賴利益和財產權保障。對于符合規劃、建筑質量合格的部分,應作合法認定,發給集體所有土地上房屋產權證書。
(二)明確集體土地的權利主體,限制集體土地隨意流轉
我國集體土地所有權的權利主體,雖在民法中被認定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但其權利主體并不明確。在這種情況下對集體土地的處分,究竟應由哪一主體決定,應當讓哪一群體知情,應由哪一群體分配土地利益,爭議訟訴上的哪一主體適格等都是模糊的。《憲法》和相關法律中的“農民集體所有”在實踐中,往往是人人都有而事實上卻是人人都無法享有。在處分集體所有土地建造房屋時,處分權主體的模糊可能會引發了一系列問題,集體土地的流轉缺乏監督將會增加土地流轉的隨意性,進而損害經濟組織內成員的合法權益。從歷史上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人來自于早期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其具體的組織形式在現階段大部分地區都不存在。現階段,村民小組、村民委員會究竟哪一主體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人,三者經常被混為一談,難以分清。無論是作為法人實際參與民事活動的需要,還是按照民法所體現的基本理念,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人都應具備完整的運行機關。作為法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治理結構應以村民章程的形式加以明確。基層人民政府應指導和幫助村民制定一個內容全面、兼具對內和對外效力章程,并應符合村民章程的制定程序,使村民章程最大限度地體現民意。如此,為限制集體土地的隨意流轉,減少“小產權房”的出現,可行之策是盡快明確集體土地所有權的行使主體。
(三)完善土地征收制度,明確“公共利益”的概念
土地征收在具體的操作過程中應符合為“公共利益”需要的目的。然而,無論是《憲法》還是《民法典》,對“公共利益”的概念的界定都不明確。現實中政府因商業用地的需要卻打著“公共利益”的幌子進行土地征收的現象屢見不鮮。這使原本受益的集體利益落空,嚴重損害農民的利益,變相拉大了城鄉差距。村集體及成員在既得利益面臨滅失的情況下,不甘落空,這才會鋌而走險,冒著違法風險在自己的土地上建造“小產權房”。因此,要解決“小產權房”問題,在立法層面必須健全完善在征收土地方面的法規,明確“公共利益”概念,并結合司法裁判的作用加以解決。首先,要完善我國行政法規中的農地征收、征用制度,我國的城鄉二元體制使得地方政府有著征收、征用農地的權力,通過補充完善行政法規和行政訴訟法來規范政府的征地行為,防止政府濫用權力,從而規范“小產權房”的流通。村集體成員之所以熱衷于賣地是因為征地的補償過少,因此,在征地法規上應提高征地的補償標準,從而給賣地降溫,從而減少“小產權房”的產生;其次,通過憲法采用列舉的方式規定哪些是公共利益,哪些不是公共利益。在憲法關于征收土地的問題上,“公共利益”的模糊性規定,是導致實踐中政府動輒以公共利益的名頭濫用手中的權力,侵害村集體利益的根源,因此有必要對公共利益予以明確界定;最后,在司法裁判層面,法院在界定土地征收是否符合“公共利益”時,除了要遵循法律的規定,同時應著重考量土地征收是否符合用地建設規劃和土地出讓人出讓土地的意愿。
結語
“小產權房”問題關系到國計民生,由于其產生的特殊性,使它擁有特殊的法律特征。它是舊法積弊和相關群體受利益驅動等多種原因下催生的產物。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能夠入市流轉并以法律的方式加以保障,從根本上能夠解決“小產權房”問題。對于歷史上形成的“小產權房”問題,其解決思路應從建造和流轉兩方面進行處理。對于建造上不合法的“小產權房”應認定為違章建筑,使用行政的手段對其予以拆除;對于建造上合法,流轉上不合法的“小產權房”應通過對房屋流轉合同效力的否定,在司法上予以規制。為限制轉變土地性質上的隨意性,在土地出讓層面,應明確集體土地所有權的行使主體,進而加強對集體土地流轉的監督力度,減少“小產權房”的出現。在土地征收層面,立法上應明確“公共利益”的概念,限制政府為商業用途征收土地,在司法裁判上應把用地建設規劃和土地出讓人的意愿納入司法裁量的范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