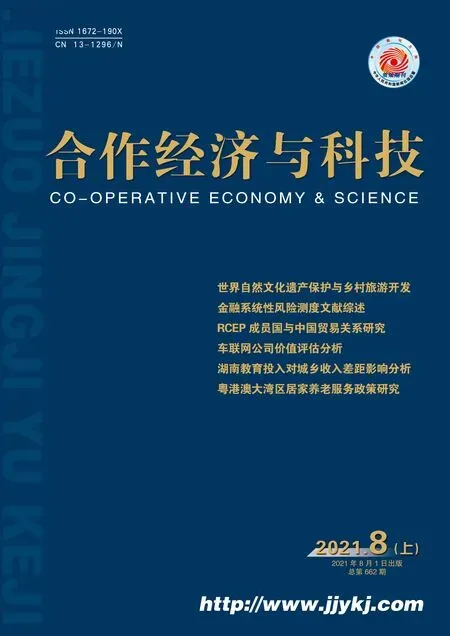非正規就業研究述評與展望
□文/劉姍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勞動經濟學院北京)
[提要]非正規就業以其靈活性等特點,在緩解就業壓力、減輕貧困等方面發揮著重要價值。本文通過回顧已有研究,對非正規就業概念內涵、測量標準以及非正規就業理論基礎進行綜述。在此基礎上,總結歸納實證研究中非正規就業的重點研究方向,并對未來研究進行展望。
一、引言
疫情過后,國家經濟下行壓力巨大,保民生、穩就業工作成為當前重中之重,國家出臺了系列政策支持勞動者通過多種形式靈活就業,在此背景下,諸如“地攤經濟”等非正規就業形式興起,同時也引起學術界對非正規就業的廣泛研究。
已有學者對非正規就業的相關研究進行了總結:首先,有學者從非正規就業概念引入中國后的本土化問題出發進行分析。例如,張華初(2002)對非正規就業概念在我國移植的情況、發展現狀與政策措施進行了總結。與此類似的,王會濤和汪戎(2011)對非正規就業的重要價值、存在的問題以及應對策略進行了綜述。其次,有學者對不同國家的非正規就業進行了總結,例如李曉曼等(2019)對我國非正規就業市場的功能定位進行了總結,并指出非正規就業市場的正規化規制會造成效率損失。姚宇(2008)對國外非正規就業的不同研究階段以及主要研究機構進行了總結,指出國際非正規就業研究一直呈現多學科、多視角交叉的特點;最后,部分學者對不同群體的非正規就業研究進行了總結分析,例如女性群體非正規就業、農民工群體非正規就業、城鎮群體非正規就業等。
縱觀現有關于非正規就業的總結類文獻,已有研究主要存在以下不足:首先,已有研究偏向于分析國外非正規就業在中國的本土化問題而對非正規就業的內涵并未做出明確的概括總結;其次,現有綜述中缺少對非正規就業理論基礎的歸納總結;最后,對非正規就業在實證研究中的應用情況與熱點研究方向缺少總結。在此背景下,本文將對非正規就業的定義、測量以及理論基礎進行歸納,并分析非正規就業在實證研究中的幾大熱點方向及未來研究展望。
二、非正規就業概念界定與測量
(一)非正規就業內涵界定。國外學者對非正規就業主要從三個方面界定:一是根據組織規模,例如有學者認為,非正規就業者所在組織的規模一般不超過6個人;二是從就業部門性質界定,非正規就業部門主要指正規就業部門之外的部門;三是從就業性質界定,例如非全日制就業、臨時雇傭等“非典型性就業”屬于非正規就業的范疇。雖然界定非正規就業概念的視角、標準不盡相同,但學者對非正規就業的認識基本具備以下共識:非正規就業者與用人單位缺乏勞動合同與相應的社會保障,雇傭關系相對脆弱。
國內學者主要從勞動關系、企業性質、政府監管等方面進行界定。一是從企業規模性質進行界定,在組織規模小于7人的小微企業中的就業往往是非正規就業;二是從勞動契約關系進行界定:勞動者雖被雇傭,但并不屬于正式職工且未簽訂勞動合同的就業被稱為非正規就業;三是從政府監管角度進行界定,認為未進入政府監管、征稅體系,處于就業邊緣的就業均為非正規就業;四是從就業的主要特征進行分析,非正規就業不具備穩定的勞動關系、不受社會保障制度保護。
從以上分析可以發現,目前國內外對于非正規就業的定義還沒有形成統一的認識,但非正規就業中雇傭關系、就業形式的“非正規性”是學者廣泛認同的。此外,盡管非正規就業在各國已成為一種普遍現象,但早期文獻中并未使用非正規就業這一概念,而是用非典型就業等詞語,諸如非全日制工作、勞務派遣、臨時就業等均屬于非典型性就業的范疇。在國內研究中,早期學術文獻常用“靈活就業”的概念,二者具有相似的內涵。
(二)非正規就業測量。學者對非正規就業的測量往往受研究所用數據庫的限制,更進一步,盡管使用同一數據庫進行實證研究,學者對非正規就業的測量也有較大出入,本文對學者利用國內幾個主要數據庫進行非正規就業測量的標準進行了總結,如表1所示。(表1)
三、非正規就業理論基礎
(一)二元經濟理論。“二元經濟理論”已成為解釋非正規就業現象的重要理論基礎,由美國經濟學家劉易斯提出。他指出,隨著一國經濟的不斷發展,國家經濟結構將出現農業經濟體系與現代工業體系的劃分,即傳統部門和現代部門。在經濟運行過程中,農業部門的產出和收入低于工業部門,有更多的剩余勞動力,而工業部門的擴大再生產造成了許多崗位空缺。因此,農業部門勞動力逐漸流向工業部門,但事實是,現代工業部門并不能完全吸納轉移的勞動力,導致沒有進入現代部門的剩余勞動力只得從事非正規就業。
也有學者在“二元經濟理論”的基礎上,進行了進一步的拓展,認為中國的社會經濟結構是三元或四元的。例如,胡鞍鋼、馬偉(2012)認為中國社會經濟轉型過程中,形成了四元的市場結構,包括農村企業就業、鄉鎮企業就業、城鎮正規及城鎮非正規就業。
(二)貧困就業理論。貧困就業理論也常被用來解釋非正規就業存在的客觀依據。非正規就業現象的出現意味著勞動力市場并未實現充分就業,技能水平與收入水平較低、無法進入現代部門的勞動者只能被迫選擇非正規就業。貧困就業理論揭示了非正規就業形成的內部動力,解釋了下崗工人以及失業人員的再就業現象。
(三)綜合理論。以上理論都只能解釋非正規就業成因的一部分。由于非正規就業的就業類型繁多,需要一個更為綜合的理論來闡釋其形成基礎。基于此,學者從勞動力的退出、進入、排斥和剝削四維度解釋了非正規就業的形成。其中,退出即為退出正規就業,非正規就業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擺脫政府管制,相對于參與正規就業,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減少生產經營成本。為此,一部分勞動者主動選擇退出正規就業市場。進入即為存在進入障礙,因為正規就業的勞動者在收入水平、社會保障等方面的待遇更加優厚,導致進入正規部門就業存在一定的進入障礙、門檻較高,一部分勞動者受學歷、能力等限制,只得從事非正規就業。排斥指正規部門勞動者對非正規就業者的排斥,正規就業者享有國家給予勞動者的各項權益,而這種權益無法實現全覆蓋,因此就會出現已享有權益保障的勞動者排斥非正規就業者的現象,使得非正規就業形式長期存在。剝奪指許多用人單位為節省開支,減少用人成本,會在一些非核心崗位雇傭非正規就業者,進而導致非正規就業的形成。
四、非正規就業熱點研究方向
(一)非正規就業的前因。對影響非正規就業的因素,學界進行了充分探討。一部分研究認為從事非正規就業是存在選擇性的,因此學者分析了哪些人更容易從事非正規就業,這種選擇受到勞動者年齡、教育程度、所在地區等因素的影響。此外,勞動者是否具備使用互聯網的能力會對非正規就業產生影響,相關研究顯示,能夠使用互聯網的人從事非正規就業的概率更低;另一部分研究分析了影響非正規就業的其他因素,政府現行的最低工資制度、社會保險制度、政府管制、全球貿易等,均會對非正規就業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
(二)非正規就業對居民收入的影響。關于非正規就業與正規就業之間的收入差距,學者通過實證研究得出了類似的結論,認為從事正規就業的勞動者收入明顯高于從事非正規就業的勞動者。正規部門對勞動者技能水平要求較高,存在進入障礙,因此從事非正規就業只能獲得相對較低的回報。相關研究表明,勞動者個人教育水平、工作經驗等影響了正規就業與非正規就業的工資差異。
(三)非正規就業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關于非正規就業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學界尚未得出一致的結論。首先,部分學者通過實證研究得出非正規就業對經濟增長具有正向影響作用,因為非正規就業崗位創造能力巨大,能夠提高就業率。例如,黃蘇萍等(2009)在東北三省的研究發現,非正規就業對經濟的貢獻占三省GDP的36%。其次,有學者實證研究的結果表明非正規就業對經濟增長有消極影響,因為非正規就業者往往不具備專業技能知識,更多從事簡單重復性工作,不利于擴大再生產。最后,也有學者通過實證研究認為非正規就業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并不能確定,例如張延吉等(2015)發現非正規就業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曲線存在一個拐點,當城鎮非正規就業群體規模超過38%并繼續擴大時,非正規就業對經濟增長起負向影響作用。
縱觀已有文獻,非正規就業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效應主要包括積極影響、消極影響以及不確定。但不能否認,非正規就業在緩解就業壓力,增加居民收入中的積極影響,特別是對弱勢群體。除了探討非正規就業對居民收入、經濟增長等的影響外,以往的研究也側重于分析非正規就業對勞動者帶來的負面影響,包括非正規就業對居民健康、主觀幸福感、社會融合、工作時間等方面的影響。
五、啟示及展望
在國家政策的鼓勵下,非正規就業形式不斷增多,也引起學界對非正規就業的廣泛討論。在已有研究基礎上,通過整理文獻,首先對非正規就業的內涵與測量進行了總結,特別是在非正規就業內涵的研究中,不是對已有定義的羅列而是進行分類歸納;其次對非正規就業運用最廣泛的理論進行了歸納總結,主要是二元經濟理論、貧困就業理論以及綜合理論;最后研究對非正規就業的主要實證研究方向進行了歸納,包括從事非正規就業的影響因素、非正規就業對居民收入的影響、非正規就業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等方面。
研究發現,目前關于非正規就業概念還未形成共識。進一步,由于概念界定的差異導致在實證研究中,不同學者對非正規就業的測量標準也有很大出入,即使使用同一數據庫,在文獻中也會得到并不完全一致的非正規就業統計數據。因此,在未來研究中,可以對非正規就業如何客觀測量這一問題進行重點研究,尋找最適合中國情景的非正規就業界定標準,為實證研究奠定基礎。另外,非正規就業在緩解就業壓力的同時,是否積極影響我國經濟增長還未能有明確的答案,未來學者可以充分考慮我國實際情景,例如隨著“地攤經濟”的興起,學者可以對“地攤經濟”這一非正規就業現象展開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