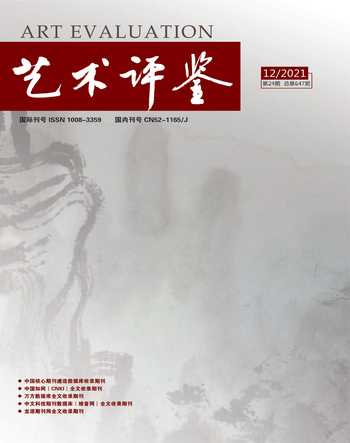中國傳統哲學思想對中國近現代鋼琴音樂創作的影響與啟示
胡奇章
摘要:中國鋼琴音樂從一開始就承載中國兩千年來一以貫之的思想文化傳統。中國音樂思維受到儒家與道家兩種思想的影響,儒家強調音樂與社會秩序的和諧,道家追求音樂中人與自然的統一。中國人思維中的實用理性與樂感文化從不否認心靈與肉體、精神與感官的統一。中國鋼琴音樂應該符合“道”,即符合自然與規律的方式創作與存在,體現了中國人音樂觀背后所體現的宇宙觀。在演奏上也應相應調整出與之相適應的模式,讓鋼琴說出最純正的中國音樂語言,體現中國人的宇宙觀,滿足樂感文化的需要,進而達成真正精神平等的中西音樂文化交流。
關鍵詞:中國鋼琴音樂? 文化滯后論? 道家哲學? 五藏相音? 創作
中圖分類號:J607?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8-3359(2021)24-0172-04
從鋼琴被引入中國的那一時起,就必然會受到中國傳統文化思想的全方位影響。這種影響的深度與廣度,隨著時間的推移,必然遠遠超出最初這種音樂文化所呈現的最早形態。眾所周知,趙元任的《和平進行曲》是中國最早以音樂文獻的方式流傳下來的鋼琴曲。事實上,在晚明和清初“西學東漸”時期,西方古鋼琴音樂文化就通過天主教傳教士傳入了宮廷。在萬歷二十八年,即1600年,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Matteo Ricci入貢古鋼琴一架獻于明神宗,西班牙傳教士、音樂家龐迪我(Diego de Pantoja)隨即奉旨教授四名內監演奏古鋼琴,為了迎合明神宗個人的藝術趣味和欣賞習慣,利瑪竇還根據天主教教義寫下《西琴曲意》共八章,供這些內監彈唱,并為明神宗在北京皇宮里表演。這是漢字韻文和鋼琴音樂的首次風云際會,也是鋼琴音樂以宮廷音樂會的形式首次登場,而這4位內監也成為中國最早的鋼琴演奏者和鍵盤手。另據清代翰林院學士高士奇所著《蓬山密記》中描述,康熙皇帝同樣在西學東漸的風氣影響下,親自學習了古鋼琴演奏,并且演奏了南宋普庵禪師所創制的佛曲,即《普庵咒》。這是一個重要的音樂史事件,《普庵咒》便成為了最早的中國鋼琴改編曲,也是一首罕見的漢傳佛教鋼琴音樂。這一早期音樂事件無疑揭示了一個重要的信息,即中國鋼琴音樂從最早的具體形態一開始就承載中國千年來一以貫之的思想文化傳統。盡管在此后中國歷史進入了所謂“三千年未有之變局”,尤其經歷了新文化運動的洗禮,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號,原本正統指導思想的儒家學說遭遇崩塌,在社會功能性上被消解,但并不意味著中國傳統哲學思想失去了對現代中國人和中國音樂文化的影響,恰恰相反,在中國人的日常生活、思維方式以及音樂創作與演奏中,儒家思想依然起到重要的影響與指導性。這不僅僅在于文化滯后理論的規律在起作用,而且還根植于中國人與西方基督教文化所不同的樂感文化和實用理性,中國人的音樂文化不僅是精神體驗上的,同時也根植于中國人的肉體與生理體驗。
一、從文化滯后理論角度思考中國鋼琴音樂的必經之路
美國社會學家F·奧格本提出的文化滯后論認為互相關聯的組成部分,各自獨立地率先變化或者滯后,因時間或者空間以及深度與廣度的運動發展產生差異,從而導致各個相關聯部分產生矛盾而減弱了其關聯性,即是文化滯后。鴉片戰爭最初鋼琴傳入中國時,英國推銷商希冀每十個中國家庭購買一架鋼琴,顯然這個愿景最終無法實現。毫無疑問撇去當時羸弱的購買力不說,中國人對音樂的認知與西方完全不在一個時空。原本在西學東漸風氣積累下來的西方文化與技術在漫長的鎖國政策下非但沒有得到任何繼承與學習,原有的知識也早已蕩然無存,鋼琴音樂的演奏與創作根本缺乏相應的文化基礎。直到世紀之交,西方近代學校制度的引進與影響下,如中西女中等西式學堂的開辦,以及西方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全方位的刺激下,中國第一代鋼琴演奏者才進入音樂歷史舞臺。在這個時期以趙元任先生所作中國最早的鋼琴作品《和平進行曲》為例案來看,在音樂語匯上更多地呈現出西方音樂的形態:大調旋律,功能化和聲,進行曲節奏,并且顯示出了海頓《驚愕交響曲》的活潑律動。如果以西方視角看待這類作品的創作技術,可能蕭友梅先生“中國音樂比西洋音樂至少落后一千年”是成立的,但是今天的音樂人類學觀點早已否定了蕭先生早期的這一論斷。一方面,《和平進行曲》是中國鋼琴音樂的胚胎,胚胎帶有西方鋼琴音樂的形態是完全合理的。而從另一方面講,中國傳統音樂中所講究的調式、氣韻、聲腔,聲的民族化特征均未在此體現,作品與這些要素的關聯顯得孱弱和有差異,即是一種文化滯后的表現,只是不能忽略的是培養中國鋼琴音樂這個胚胎的母體是中國傳統文化,奧格本認為這種非物質的傳統文化在其群體價值中的地位是非常崇高的,并且附帶了巨大的情感價值。對五聲音樂的習慣和條件反射般的認同以及傳統音樂元素在中國音樂史上的巨大影響與成功是受到中國人群體性的保護與贊賞的,因此趙元任先生在后期鋼琴曲《鋸大缸》及《賣布謠》與《教我如何不想她》等藝術歌曲鋼琴伴奏中,就一直自覺地致力于用各種方式消彌這種差異與滯后。毫無疑問,在鋼琴音樂民族化進程中,賀綠汀的《牧童短笛》具有劃時代的歷史意義。不僅僅是音樂作品已能熟練地運用對位技巧與相當的演奏技能,充分消化了歐洲音樂技術理論,而且利用中國傳統的支聲復調與旋律加花,使鋼琴音樂在表現手法上更加具有中國烙印。從演奏角度而言,旋律運動突破了西方音樂4/4拍“強,弱,次強,弱”的強弱規律,更加具有聲腔化的傾向,并且在和聲上繼承了黃自先生《長恨歌》選段《山在虛無縹緲間》,無論是人聲還是鋼琴伴奏部分,都體現出那種民族五聲化的探索。從這些音樂創作的努力上來看,這些前輩在消弭鋼琴音樂與中國傳統文化藝術上的文化滯后現象作出了積極的推動。誠然,這種消弭文化滯后現象的努力,為鋼琴音樂在中國文化的土壤上拓展了生存和發展的空間,繼而在以后對鋼琴音樂的推廣和傳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二、從中西音樂文化思維的差異上,尋求中國鋼琴音樂文化自己的音樂語言與演奏理論
中西音樂思維的差異從根本上是由于思維方式的差異而形成的。作為西方音樂理論肇始的畢達哥拉斯學說是建立在對數學的研究之上,從數學邏輯推導進行音程之間關系的研究。而在思想上亞里士多德就認為音樂的演奏與創作有道德的力量和教化的作用,而且比音樂產生的快感更加重要(儒家也有類似觀點)。縱觀西方音樂史,從格列高利素歌到近現代西方音樂,尤其是鋼琴音樂,是一個個性解放和音樂效果不斷擺脫神性以及罪感桎梏,并探索追求各類音響與聽感的過程。所以,音響橫向與縱向(尤其是縱向)之間的組合不斷地被嘗試、突破、創作以及加以理論化,最終在20世紀出現了旋律模糊,調性破碎,否定情感以體現作品的創作技術與思想深度的“折衷”音樂語匯。
中國音樂思維受到儒家與道家兩種思想的左右。傳統中國社會儒家思想是社會與個人運作與行為的秩序標準,而道家思想在與儒家思想對立和矛盾的過程中,成為中國人思想的重要補充與精神后花園。儒家強調音樂的社會性功能,在《小戴禮記》之《樂記》中,將五聲音階“宮、商、角、徵、羽”分別對應現實中的“君、臣、民、事、物”。儒家思想體系中階層與秩序的僭越與錯亂是不可以接受的,所以孔子謂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強調禮樂治國,因此儒家不可能隨機讓音階中音符不受節制地組合,從指導思想就杜絕了對位技術與和聲發展起來的可能性,因此,單線思維和強調旋律的發展使中國音樂的創作與演奏走向聲腔化,強調聲韻效果,并貫穿于整個古代與近代中國音樂史,對現今中國人的音樂趣味仍有基因式的影響。
從另一方面來看,中國人思維中的實用理性與樂感文化從不否認心靈與肉體、精神與感官的統一。而西方基督教的罪感文化中將精神和肉體對立起來,否認欲望的合理性。儒家的《樂記》指出“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辯證地將道德與欲望的矛盾統一在音樂上,高尚的人用音樂中的理性抵制音樂所引起的感官愉悅。而對于道家而言,《老子》“道法自然”的觀點承認了音樂滿足自然屬性的人的感官快感,《淮南子·本經訓》則同樣辯證地認為音樂是使身心平和,不可用于追求感官快感與縱欲,即“樂者所以致和,非所以為淫也”。
從儒家強調音樂與社會秩序的和諧或者道家追求音樂中人與自然的統一,都迥異于強調個人自證與個性的西方音樂藝術。因此在創作中,中國鋼琴音樂從其肇始以來,其創作就體現出這一特點。例如黃自《山在虛無縹緲間》鋼琴伴奏部分來自明代宮廷古曲《清平調》,直到《黃河鋼琴協奏曲》(黃河大合唱為素材,拉赫瑪尼諾夫第四鋼琴協奏曲的織體方式以西方人不可思議的“集體創作”)都并不強調肖邦式的獨特個人風格,反而與上古樂舞《云門》《咸池》一樣,創作的自證是通過自身與社會、歷史、自然的和諧圓融來達成的。同時,《黃河鋼琴協奏曲》中對水的形態描繪也充分體現了道家思想中對水的理解。《黃河頌》中的水,是《淮南子》中人們“以水為資”,是《老子》“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的描繪對象,是養育了中華五千年文明的水;而《保衛黃河》中的水,是“天下至柔馳騁天下至堅”“攻堅強者莫之能勝”的水,是在鋼琴和樂隊的共同作用下可以戰勝一切敵人的精神力量。從整個作品的風格來看,并沒有體現冼星海或者參與集體創作成員中任何一個的所謂個人手法和個人風格,反而體現出了諸如琵琶的輪指,戲曲聲腔以及民歌的民族特征,是中國鋼琴音樂語匯杰出的一次探索。
三、不僅承認音樂對人的精神情志能產生影響,而且承認音樂對人的生理狀態同樣有影響,并以此思考中國鋼琴音樂發展的走向
在《樂記·樂本篇》中,已經說明了音樂對人類情志的喜怒哀樂有能動作用,但是近現代中國鋼琴音樂的創作中似乎一直忽略了中國傳統音樂思想中的另一個側面,即音樂對人的生理狀態同樣有著巨大的能動作用!道家學說除了對人的社會屬性關注,還對人的自然屬性極為強調,即音樂與人的身心健康息息相關,即“五藏相音”。在《黃帝內經》中幾乎以列表方式的排比句,借岐伯的言論揭示了“宮、商、角、徵、羽”五音與人的各個臟器“心、肝、脾、肺、腎”各種情志、各種感官聯系在一起,并聯系在地理方位,季節,體現五音所代表五行相生相克,這充分體現了中國人音樂觀背后所體現的宇宙觀,即天人合一。而音樂應該以符合“道”,即符合自然與規律的方式創作與存在。當無視這些內在規律的情況下,人的生理機能與情志都會紊亂而導致疾病。反過來,根據這個理論,利用音樂中五音的生克,則可以調理生理機能,達到音樂養生的目的。
四、結語
結合以上幾個方面的考量,筆者認為中國鋼琴音樂應在中國人自身特有的思維模式以及音樂文化心理構建上實現與現代性相平衡的狀態,并在此基礎上下探索其未來。中國鋼琴音樂的價值并非必須將“現代性”作為其唯一的評判標準。事實上,現代性這個詞匯從來都不純粹,并非是單單科學或者文化意義上的概念,它同樣存在于政治領域,甚至在現代歷史上被美國作為文化冷戰的戰略工具而出現。為了抵抗蘇聯文化藝術領域強調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CIA出資贊助波洛克為代表的美術作品,并哄抬其價格;資助勛伯格表現主義音樂在世界公演。以無意識、反古典、反經典藝術的現代性,樹立為文化優劣的偽標準,進而體現其所謂的“政治正確”。然而,即使是深受勛伯格、韋伯恩影響的一些作曲家,諸如美國作曲家喬治·洛克伯格和波蘭作曲家潘德雷茨基等具有獨立思考能力的藝術家,在長期的創作實踐中都發現了非調性的局限性,前者甚至還宣稱無條件回歸調性,后者在《廣島受難者的哀歌》之后勇敢地重回傳統,如以1976年的《小提琴協奏曲》與1984年的《波蘭安魂曲》為代表的一系列大作品。中國傳統文化可以包容琵琶、二胡、揚琴以及嗩吶等本地樂器,也毫無疑問可以讓鋼琴說出最純正的中國音樂語言,體現中國人的宇宙觀。
參考文獻:
[1]利瑪竇.重刻畸人十篇二卷,附西琴曲意一卷.明刻天學初函本,17世紀初.
[2]威廉·費爾丁·奧格本.社會變遷——關于文化和先天的本質[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3]南京中醫學院.黃帝內經素問譯釋[M].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81.
[4]鐘子林.西方現代音樂概述[M].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