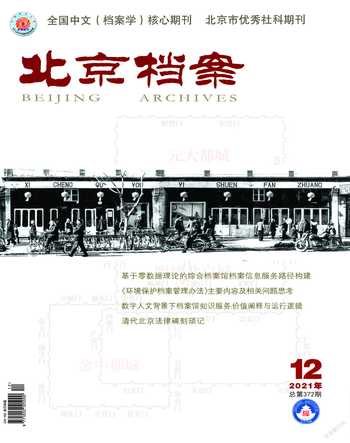清代北京法律碑刻瑣記
劉竹
碑刻是鐫刻在地面立石上的文字或圖畫,也被稱為“刻在石頭上的史書”。作為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碑刻的內容涉及特定歷史時期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方方面面。而將法律法規、訟案事例及契約憑證等刻于碑石亦成為碑刻的重要分類。法律碑刻指經過一定程序,刻載內容具有一定法律效力和約束力的碑刻[1]。這些碑刻,對于我們了解古代法律的法條、內容、實施及其效果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史料,有為數不少的法律碑刻流傳至今,值得后人細細品味。
八旗制度是清代最具特色也是最為重要的制度。旗人的土地稱為“旗地”,系國家所有,在法律上嚴禁旗人典賣、出售旗地,即禁止“旗民交產”。早在康熙年間,即已出現“典賣旗地,從盜賣官田律”的規定,雍正皇帝即位后,又重申“八旗地畝,原系旗人產業,不準典賣與民,向有定例”[2]。但隨著清朝入關日久,八旗生計問題日益突出,旗人典賣旗地的事件時有發生,屢禁不止。

郎世寧是一位外國來華傳教士,也是一位著名的畫家和建筑家。他的許多優秀作品至今仍在北京故宮博物院珍藏。這樣一位歷經康雍乾三朝的宮廷畫師,也曾因為參與“典賣旗地”活動而險些被皇帝責罰。作為清宮內廷畫師,郎世寧與清廷官員有著良好的私交。在一次游玩中,他看中了宛平城內的一片土地,想購置入手并在此傳教。于是他通過相熟的內廷官員和賣家蔡永福達成了協議,購買了此處的旗地和河淤地,雇人耕種糧谷,在河淤地割葦制席,以此換取物資和資金來補充傳教經費和個人生活所需。而在不久前即乾隆七年(1742),朝廷已再次重申嚴禁買賣旗地的禁令。此事傳進宮中,自然應當治罪,但由于郎世寧本人的誠懇態度和多方協調,最終乾隆帝恩典,以郎世寧“系西洋遠人,內地禁例原未經通飭遵行,且伊等寄寓京師,亦藉此以資生計,所有定例后價典旗地,著加恩”[3],免去郎世寧私買旗地的罪過。郎世寧本人更是對皇帝的法外恩典尤為感激,在當年同月所購買的旗地內立石刻碑,碑額上寫“欽賜”二字,內容則簡要摘錄了乾隆帝上諭的內容,以感念“皇恩”。光緒年間,在這塊碑刻旁邊興建了北天主教堂(后被焚毀),并被當地人慣稱至今,即為北天堂村(在今豐臺區內)。
在北京的城市發展過程中,燃料的種類也經歷了升級換代,在明清時期逐漸變為煤炭,其來源是京西順天府下屬的宛平縣、房山縣等地。趙翼記載京城故老之語:“燒不盡的西山煤”[4],彭玉麟也指出京城外西山、北山的煤炭“取之無盡,用之不竭”[5]。可見西山煤炭對于北京人日常生活的重要性。正因如此,開設煤窯成了一項有利可圖的產業。清政府對煤炭開采也有嚴格的規定,對于影響“龍脈”、妨礙安居的開采行為都給予禁止,對違例私挖者也有嚴厲的處置,“西山一帶私自開窯賣煤、鑿山賣石、立廠燒灰者枷號一個月”[6]。但盡管如此仍屢禁不止,對此清政府多次樹碑曉諭。如乾隆元年(1736)三月,豎立于北京門頭溝軍莊鎮香峪村的“遵旨永禁碑”記載了當地原有榆林、雙門等煤窯,由于挖掘地點附近有皇室陵墓,因此久被封禁。但此處煤產豐饒,有趨利之徒鋌而走險偷偷采挖。后來當地縣衙抓到“劉三、王四”等涉案人員,嚴懲之并封禁礦洞,為防止后續有人效仿盜采,遂立碑以曉諭村民。
又如道光年間,門頭溝的板橋村發生了因私挖煤炭影響當地村民安居和飲用水安全的案件。道光十五年(1835)北京門頭溝板橋村三官廟樹立了“軍糧廳布告碑”(今在門頭溝區板橋村三官廟),記載了西板橋村村民指控劉繼興等人“私開封禁煤窯,致裂廟宇房舍墻垣”。經過官府的調查勘定,認定劉繼興等人私挖的煤窯確實是之前封禁的舊窯,并“有礙居民房舍”,因此決定封禁煤窯、懲處相關涉案人員,并“勒石存記”。然而僅僅過了三年即道光十八年(1838),當地私挖煤窯又起波瀾:東、西板橋村村民稟告宛平縣政府,之前所封禁的東、西坯兒煤窯已經在三年前被“查明封禁在案”,但如今又有人意欲開挖,村民找到官府要求將有礙村莊安全的煤窯開采按照以往“例應封禁”。這次控告再次獲得了官府的允準,“將該窯門用石壘砌封禁,永遠不許開采”[7]。此后光緒年間還議立了開采整頓煤窯的章程[8]。可以說,從清初一直到清末,對于西山煤炭挖掘不斷,對開采的管理也始終不絕。
北京的會館是中國明清時期同鄉或同業的人在京城設立的常設機構。它因科舉而興,卻也因工商業的發展而壯大。[9]在清代社會經濟日益發展的背景下,商人愈發希望得到社會的承認,同時也為了謀求壯大本行業的利益和影響。在此背景下,以商人團體為主體興建的各類會館、公所日益壯大,對社會經濟、商業發展造成了重大影響。為了保證會館公所的良好運行,商人們紛紛將會館公所的公約、規定勒石為記。在清代的法律碑刻中,會館及公所的碑刻占有相當大的比重。這些碑刻生動而深刻地反映了清代商業社會的法律規則。這些豎立在京城各處會館及公所前的碑刻不僅打破了行會傳統的地域,更是由表及里、由淺入深,形成了系統、獨立的新型行會習慣法體系,涉及本行業、本會館(公所)的方方面面。如行業組織內互助規定,不僅能維護行業健康發展,又對社會穩定起到較大的作用。例如北京的木工行業,以精忠廟魯班殿為會館。因在京木工本人及其親眷中不少人為外地來京人員,可能因患病或事故等亡故,但因無處葬埋停放,又不能立即將靈柩帶回老家安葬。鑒于此,會館將歷年辦會剩余資金置買義地一塊,以備安葬。此舉為在京木工的親友喪葬事宜提供了便利。只要是本會人員,憑借本人身份證明“找三城首事要對條,到廟內起票,按牌開坑葬埋”,由行會出資,不需個人出錢。此事被記錄在光緒二十年(1894)所立“精忠廟魯班殿碑”(今在東城區前門外東珠市口)中。這則記載木工行業行規的碑刻在光緒三年(1877)、光緒二十八年(1902)、光緒三十四年(1908)、宣統三年(1911)四次發布行業內的議定工價并勒石銘記。
此外,會館的碑刻還記載了一些具體的會館管理規則,包括對各行業人員的行業自律行為的要求等。比如記載皮行規約的“新立皮行碑記”(今在西城區大保吉巷)中,對盜買盜賣行為堅決懲處,如有被偷盜的“生熟皮章貨物”流入市場,本行的人嚴禁購買;如果購買了,不僅要罰款,還要被追究是否與賊人同謀,即從源頭上禁絕被盜賣物資的銷贓。會館碑刻中記載的這些具體的會館管理規則,成為構成清代乃至近代的行會習慣法律體系的重要部分。
清代隨著人口的增加,資源爭奪日趨激烈,而由于沒有成文的環保法導致對資源的無序使用,也使得生態環境每況愈下。而勒石刻碑因其有效而存續時間長的特點,成為傳布生態環境保護規約的重要手段。清代的北京,也有不少生態環保碑刻,有些直到今天還發揮著功用。
在闡釋有關環保內容的法律碑刻中,保護森林的禁伐碑數量不少。如在十三陵長陵,順治帝在順治十六年(1660)因見“諸陵殿宇墻垣傾圯”,近陵的樹木多被砍伐,因此將現存樹木永禁砍伐[10];還有西山法海寺,在順治十七年(1661)也樹碑要求“滿漢閑雜人等不許放牛羊、砍樹、割草”,違背者要從嚴處置[11];清末宣統元年(1909),又在昌平發現一塊碑文內容為“篩海墳墓松柏樹株不得任意砍伐”的石碑。這三塊碑對于研究清朝有關林業法律和保護古樹的歷史都有重要意義。[12]除了禁伐碑外,北京還有保護水源的環保碑。位于門頭溝區中西部的靈水村南海火龍王廟前的八角水池邊有一通青灰色石灰巖石碑,碑面刻有“重修石記”四個大字。從碑文可知,在康熙辛未年(1691)仲夏即樹立此碑,當時的八角水池作為飲用水,被當地村民稱為“龍池”“靈水”,由于年深日久,水池破敗,于是村民集資,僅用了一個月時間就重修好水池。水池修好后,村民們特刻石碑于池前,記錄重修之事,并將保護水源的三條禁令刻于石上。從碑文記載中可知禁令內容為:水池邊禁止污穢、堆糞、洗衣三事;水池內禁止兇潑投跳,愚頑攪混,兒童汗溺三事;水池臺禁止宰殺腥,飲畜作踐,漿衣洗菜三事。違反禁令者,村內要“鳴鐘議罪,罰供祭神”,經過批評教育后“使知警畏”。凡是靈水村的村民都要遵守此碑以“流傳后輩”。這通碑又被當地人稱為“三禁碑”。可見,早在300多年前,靈水村村民不僅有敬畏自然、保護飲用水的環保意識,更將其作為村規民約的一部分,刻于碑石,要求村民遵守。由此可見,無論是官方鏤刻的禁伐碑,還是村民自發樹立的保護水源碑,都可以看出環保碑在協調人與自然關系,調和不同利益方的資源占有比例關系上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上述四類法律碑刻故事,只是清代北京眾多法律碑刻的冰山一角。此外,還有鄉規民約、宗教管理等多種內容和形式的法律碑刻。這些碑刻,有些已被珍藏在國家圖書館、國家博物館、石刻博物館等場所,有些仍然散落在北京城市鄉村的各個角落,還有些已湮沒于歷史變遷之中,它們也亟待后人去記錄、研究和保護。
注釋及參考文獻:
[1]李雪梅,沈成寶,孫斌,等.法律碑刻之分類探討[J].中國古代法律文獻研究,2016(00):431-468.
[2]張廷玉,等.清文獻通考(卷五,田賦考)[M].清文淵閣四庫全書.
[3]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乾隆朝上諭檔(第二冊)[M].北京:檔案出版社,1991:498.
[4]趙翼.檐曝雜記(卷六)[M].清嘉慶湛貽堂刻本.
[5]彭玉麟.興礦利[M]//陳忠倚.清經世文三編(卷六十八).清光緒石印本.
[6]三泰.大清律例(卷四十五) [M].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7]門頭溝區文化委員會,門頭溝區文學藝術界聯合會.門頭溝文化遺產精粹·京煤史志資料輯考[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7:91-101.
[8]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為順天府軍糧廳議擬開采整頓煤窯章程呈堂存案事,光緒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三日.檔號:06-01-002-000766-0001.
[9]李雪梅.碑刻法律史料考[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177.
[10]倪根金.明清護林碑知見錄[J].農業考古,1996(3):179.
[11]王九齡,李蔭秀.北京森林史輯要[M].北京:北京科技出版社, 1992: 79-80.
[12]施海.京郊發現三塊清朝保護樹木石碑[N].中國綠色時報.1990-05-01(01).
作者單位:沈陽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