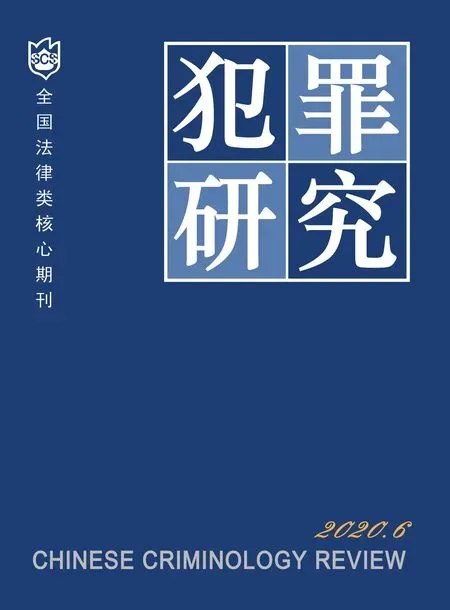中國企業家腐敗犯罪報告(2014—2018)
張遠煌 等
一、前言
本報告的是在北京師范大學中國企業家犯罪預防研究中心發布的年度報告——《中國企業家犯罪分析報告》基礎上,綜合2014—2018年五個統計年度的《中國企業家犯罪分析報告》中的相關內容,專門編制的企業家腐敗犯罪報告,也是國內有關企業家腐敗犯罪的首份五年統計分析報告。
(一)本報告的宗旨
本報告編制主要有以下目的:
1.為促進本土白領犯罪理論研究、完善白領犯罪對策提供基礎素材與問題引導
企業家腐敗犯罪,不僅是典型的白領犯罪,而且是白領犯罪的高端形態。相對于殺人、傷害、強奸、搶劫、盜竊、毒品等傳統的“街頭犯罪”,白領犯罪不僅更加隱蔽,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遠超“街頭犯罪”,〔1〕例如,1985年5月20日《美國新聞和世界報道》雜志顯示:美國白領犯罪所造成的經濟損失,遠遠大于街頭暴力犯罪,前者一年達2000億美元,后者僅為110億美元。參見陳岳:《美國的白領犯罪》,載《國外法學》1986年第2期,第47頁。而且白領犯罪往往還會產生大量不知受害的間接受害人,讓眾多的國民來共同承擔其犯罪的負擔。但長期以來,人們關注的重點卻主要集中于“街頭犯罪”。白領犯罪往往被犯罪學、刑事立法、刑事司法研究所忽視。也正是由于對白領犯罪現象及其原因缺乏深入系統的研究與透徹的理解,也就難以論及有效應對白領犯罪的科學對策,以致沿用針對“街頭犯罪”的模式來應對白領犯罪,在眾多國家成為人們習以為常的無奈選擇。
企業與企業家的社會身份、社會功能等因素決定了腐敗犯罪的生成機理與“街頭犯罪”存在顯著區別。為了科學治理企業和企業家犯罪,理應構建區別于“街頭犯罪”的防治對策。通過對企業家腐敗犯罪特征的全方位描述,并基于數據分析,揭示企業家及企業腐敗犯罪與刑法運行、營商環境、企業治理缺陷等相關因素之間的聯系,為來自包括犯罪學在內的不同領域的學者,共同探討企業家腐敗犯罪的原因與對策,促進相關立法完善,為司法改革提供實證研究素材與路徑和方向指引,正是本報告的重要目的。
2.適應我國全面反腐的現實需要,推動在反腐戰略上形成公共領域反腐敗與非公領域反腐敗協調推進的對策構想
全面反腐不僅意味著要覆蓋所有公權力部門,而且還應涵蓋私營部門。反腐敗斗爭要向縱深發展,必須重視公共部門與私營部門反腐敗之間的統籌規劃與協調發展。毋庸置疑,現階段的反腐敗,還主要局限于公共部門(黨政機關、國有企事業單位)的反腐敗。以民營企業為代表的私營部門的反腐敗,無論在理論研究還是在反腐實踐中都尚未得到應有的重視,“腐敗主要是公共部門問題”的觀念依然根深蒂固,以至于私營部門的反腐敗尚處于缺乏國家層面統一規劃與制度性推進的自發狀態。
本報告對民營企業與企業家腐敗犯罪態勢的揭示,充分說明不僅民營企業和企業家腐敗犯罪已占其全部犯罪總數的30%,增幅也明顯快于國有企業和企業家腐敗犯罪,已成為現階段我國腐敗現象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公共部門的腐敗與民營企業和企業家的腐敗之間客觀上存在著相互交織、互為因果的關系。對這一客觀事實的進一步清楚認識,有助于幫助決策機關認清非公領域的腐敗態勢,正確判斷私營部門腐敗犯罪的結構及趨勢,從而在制度安排和資源投入上將私營部門的反腐敗納入國家統一規劃中,實現全面反腐的升級發展。同時,公共部門與私營部門反腐敗斗爭的協調推進,也是營造企業家健康成長環境、構建新型政商關系不可或缺的重要抓手。
3.適應國家治理現代化需要,推動本土性刑事合規制度的建立,形成腐敗犯罪“國家——企業”合作預防的治理新格局
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必然要求犯罪治理的現代化。衡量一個國家治理犯罪現代化的水平可以有多個維度,但其中有兩個最重要的維度:一是實現從傳統的事后打擊向事前預防升級,注重犯罪風險的有效防控,實現犯罪的源頭治理;二是在政策觀念上不再將與犯罪作斗爭視為國家的專屬事務,而是事關社會可持續發展與社會成員安全感、獲得感的公共事務,從而注重吸收社會力量實現犯罪的共治、共贏與共享。
作為預防為先、合作預防這一政策觀念的制度載體,是近20年來在全球應運而生的刑事合規制度。刑事合規作為主要針對單位(尤其是企業)犯罪而非自然人犯罪的一種新型治理模式,其基本政策導向就是強調預防犯罪既是國家的任務,也是社會組織尤其是企業的社會責任,以此為出發點,通過在刑事立法中明確企業內部預防犯罪的基本要素,并將企業是否依照立法指引構建并實施旨在發現、預防內部犯罪的合規計劃,與涉罪企業和高管刑事責任的有無或輕重直接掛鉤,使注重依法合規經營、在預防自身犯罪方面勤勉努力的企業有好的待遇(出罪、減免處罰、縮短資格限制等),使忽視犯罪自我預防的涉罪企業和高管付出應有的代價,以此激發企業和企業家構建刑事風險內控機制的意愿,積極運用自身的技術、資金及人力優勢主動參與犯罪治理,從而實現國家對企業犯罪的有效治理與增強企業自身可持續發展能力的雙贏。
本報告所揭示的事實,無疑會為推動我國刑事合規制度的建立提供有力的基礎性支撐。報告表明如下兩個方面的問題:
一方面,無論是國有企業(家)還是民營企業(家)腐敗犯罪的潛伏期(從第一作案到最終案發的時間間隔)多數都在5年以上,這說明僅僅依靠國家力量從外部監督企業犯罪,無法做到及時發現和有效揭露。
另一方面,企業主要負責人在企業高管中實施腐敗犯罪的比例接近60%,表明其內生性原因在于企業內部權力制衡機制的缺失;同時,腐敗風險遍布于企業經營管理的各個環節,表明企業腐敗風險的內控機制嚴重缺失、守法文化十分淡漠。
可見,對于企業內部的致罪因素,如果不通過“國家—企業”合作預防的制度安排,激活企業方面自我預防的動力,單靠國家力量難以消除的。也正因如此,刑事合規制度成為21 世紀以來眾多國家治理企業犯罪的必然選擇。為構建我國刑事合規制度提供必要的事實支撐,正是本報告的重要初衷。
(二)本報告樣本來源與數據分析
本報告中的案例,來源于對“中國裁判文書網”在2014年12 月1 日至2018年11 月30 日五個統計年度中公開發布的所有刑事案件判決書、裁定書的檢索。
為了全面、準確描述企業家腐敗犯罪特征,本報告從犯罪行為、犯罪人、涉案企業和刑法適用四個方面,共設定了60 余項指標,并按照所設定的統計變量,對五年間檢索的所有涉及企業家腐敗犯罪的生效判決案件予以逐案解析,然后通過SPSS 統計軟件將所有案例數據進行匯總,形成“企業家腐敗犯罪案件數據庫”,作為本報告統計分析的依據。
(三)本報告術語說明
本報告的“企業家”為統計概念。“企業家”是指在企業經營中參與決策以及負責重要經營活動的高級管理人員,具體包括9 類人員:(1)董事長、總經理或法定代表人;(2)實際控制人、股東;(3)黨群負責人;(4)董事;(5)監事;(6)財務負責人;(7)技術負責人;(8)銷售(采購)負責人;(9)其他核心部門負責人。
本報告中的“企業家腐敗犯罪”,是指企業家在經營活動中實施的最終被認定為觸犯刑法的腐敗行為。對與企業經營活動無關的腐敗行為,不在本報告統計之列。
本報告統計的企業家腐敗犯罪,具體包括刑法分則中以下18 個罪名:受賄罪、單位受賄罪、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利用影響力受賄罪、行賄罪、單位行賄罪、對有影響力的人行賄罪、對單位行賄罪、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對外國公職人員、國際公共組織官員行賄罪、介紹賄賂罪、挪用公款罪、貪污罪、職務侵占罪、挪用資金罪、私分國有資產罪、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
(四)本報告的結構
本報告共分為如下五個部分:
第一,腐敗犯罪企業家的規模與身份特征;
第二,企業家腐敗犯罪的罪種與罪名結構特征;
第三,企業家腐敗犯罪刑罰適用特征;
第四,腐敗犯罪涉案企業特征;
第五,企業家腐敗犯罪高頻罪名分析。
在報告每部分的結尾,均依據所揭示特征的綜合分析,給出相應的基本結論。
作為一份專業性的統計分析報告,其主要價值在于用數據說話,發現和提出被法律規范所掩蓋的問題,至于對數據進一步的深度挖掘,尤其是基于所發現和提出的問題擬定相應的對策體系,則有待于進一步研究,尤其有待于學界和實務界同仁的共同努力。
二、腐敗犯罪企業家的規模與身份特征
(一)規模
在2014年至2018年五個統計年度中,企業家腐敗犯罪的整體情況詳見表1。

表1 涉案企業家性質
從表1 可以看出,五年間企業家腐敗犯罪的總次數為3635 次,涉案的企業家總人數為3362 人。其中,國有企業家與民營企業家腐敗犯罪的次數與涉案人數,分別占比為:33.43%、66.57%;31.41%、68.59%。
(二)性別
在3362 名腐敗犯罪企業家中,性別明確的有2753 人,具體情況詳見表2、圖1。

表2 涉案企業家性別

圖1 企業家性別分布
從圖1 可以看出,犯罪的男性企業家與女性企業家整體性別比接近9:1。其中,國企中犯罪的男女企業家比例為8.9:1.1,民企中犯罪的男女企業家比例為8.8:1.2,民企中犯罪的女性企業家比例要高于國企中的女性企業家。
(三)年齡
在3362 名犯罪企業家中,年齡明確的有2343 人。其中,最小年齡為21 歲,最大年齡為76 歲,平均年齡為45.98 歲。
在1056 名犯罪的國有企業家中,有753 的年齡明確。其中,最小年齡為25 歲,最大年齡為71 歲,平均年齡為45.99 歲。
在2306 名犯罪的民營企業家中,有1590 人的年齡明確。其中,最小年齡為21 歲,最大年齡為76 歲,平均年齡為45.98 歲。

表3 涉案企業家年齡分布

圖2 涉案企業家年齡分布

圖3 涉案國有企業家年齡分布

圖4 涉案民營企業家年齡分布
根據圖2、圖3、圖4 和表3 表明,涉罪企業家年齡的極值都分布在民營企業家中,而涉罪民營企業家的平均年齡(45.98 歲)略低于涉罪國有企業家的平均年齡(45.99 歲),但在最高發年齡段方面差異明顯:國有企業家腐敗犯罪的最高發年齡段為50—59 歲,民營企業家腐敗犯罪的最高發年齡段為40—49 歲。
(四)學歷
在3362 名腐敗犯罪企業家中,學歷明確的有2076 人。在1056 名腐敗犯罪國有企業家中,有641 人的學歷明確。在2306 名腐敗犯罪民營企業家中,有1435 人的學歷明確。

表4 涉案企業家學歷分布

圖5 涉案企業家學歷分布
從圖5、表4 對比可以看出,一方面,國企腐敗犯罪企業家大專以上學歷者占79%,民企腐敗犯罪企業家大專以上學歷者僅占45%;另一方面,初中以下學歷者,國企腐敗犯罪企業家占5%,而民企腐敗犯罪企業家占29%。
(五)職務
在3362 名腐敗犯罪企業家中,企業內部職務明確的有3362 人。其中,企業主要負責人(法定代表人、董事長、經理、廠長、礦長等正職和副職,下同)共1962 人,占58.36%;實際控制人、股東共168 人,占5.00%;黨群負責人共67 人,占1.99%;董事共12 人,占0.36%;監事共19 人,占0.57%;財務負責人、技術負責人、銷售(采購)負責人以及其他核心部門負責人共1134 人,占33.73%。
在1056 名腐敗犯罪國有企業家中,有1056 人的企業內部職務明確。其中,企業主要負責人共629 人,占59.96%;實際控制人、股東共27 人,占2.56%;黨群負責人共40 人,占3.79%;董事共5 人,占0.47%;監事共10 人,占0.95%;財務負責人、技術負責人、銷售(采購)負責人以及其他核心部門負責人共345 人,占32.67%。
在2306 名腐敗犯罪民營企業家中,有2306 人的企業內部職務明確。其中,企業主要負責人共1333 人,占57.81%;實際控制人、股東共141 人,占6.11%;黨群負責人共27人,占1.17%;董事共7 人,占0.30%;監事共9 人,占0.39%;財務負責人、技術負責人、銷售(采購)負責人以及其他核心部門負責人共789 人,占34.22%。

表5 涉案企業家職務分布
根據表5 可以看出,不論國企還是民企,在腐敗犯罪企業家的職務分布中,企業主要負責人所占比例均最高,達到半數以上。財務、技術、銷售(采購)負責人及其他核心部門負責人居于次位,比重約占三成。職務的整體分布和企業性質的關系并不十分顯著,主要區別為:國企中的涉罪黨群負責人比重較民企大,而實際控制人、股東的比重較民企小。
(六)基本結論
其一,就絕對數而言,民營企業家腐敗犯罪不論是犯罪人數還是犯罪次數都遠超國有企業家,民營企業家腐敗犯罪在全部企業家腐敗犯罪中的占比約為67%。
其二,涉腐敗犯罪人數呈逐年增加趨勢(五年間分別為406、456、622、853、948 人)。其中,國有企業家涉案人數的增長較為平緩(約為165、150、176、277、258 人),而民營企業家涉案人數持續增加(約241、306、446、575、690 人)。
其三,在性別方面,5年間整體趨勢較為平穩,變化極小,整體男女比例接近9:1。其中,民企中的女性腐敗犯罪企業家較國企中女性腐敗犯罪企業家所占的比重更大。
其四,在年齡方面,整體數據進一步說明:(1)30—59 歲是企業家腐敗犯罪的高發年齡段。國有企業家腐敗犯罪和民營企業家腐敗犯罪30—59 歲年齡段所占比分別為88.58%與88.36%。(2)涉罪企業家的年齡的極值都分布在民營企業家中,且涉罪民營企業家的平均年齡(45.98)略低于涉罪國有企業家的平均年齡(45.99)。(3)民營企業家腐敗犯罪的年齡更呈現年輕化特征,國有企業家與民營企業家20—39 歲年齡段所占比分別為15.75%與32.07%,而50—69 歲年齡段所占比分別為51.52%與32.52%。同時,涉腐敗犯罪的民營企業家最小年齡為21 歲,而國有企業家最小年齡則為25 歲。國有企業家腐敗犯罪的最高發年齡段為50—59 歲,民營企業家腐敗犯罪的最高發年齡段為40—49 歲,國有企業家腐敗犯罪的次高發年齡段為40—49 歲,民營企業家腐敗犯罪的次高發年齡段為30—39 歲和50—59 歲。
其五,在學歷方面,2014—2018年整體數據與2018年單年的數據分布基本一致。國企腐敗犯罪企業家大專以上學歷約為八成,而民企腐敗犯罪企業家以高中(中專)以下學歷為主。
其六,在涉罪企業家的職務方面,整體特征趨于穩定。表現為國有企業家和民營企業家的職務分布均以企業負責人為主,比例約為60%;財務、技術、銷售(采購)負責人以及其他核心部門負責人居于次位,比例約為30%。輕微變動體現在實際控制人、股東和黨群負責人的不同分布,主要體現在國企中的涉罪黨群負責人的比重較民企更大,而涉罪的實際控制人、股東所占比重較民企更小。
三、企業家腐敗犯罪的罪種與罪名結構特征
(一)腐敗犯罪企業家觸犯的罪種與罪名結構
在2014—2018年,企業家腐敗犯罪頻次總計3635 次,其中國有企業家腐敗犯罪頻次共計1215 次,民營企業家腐敗犯罪頻次共計2420 次。
2014—2018年企業家腐敗犯罪共涉及16 個具體罪名,其中國有企業家共涉及13 個具體罪名,民營企業家共涉及14 個具體罪名。企業家涉及的16 個具體罪名分別屬于《刑法》分則的第三章、第五章和第八章。

表6 2014—2018年企業家腐敗犯罪的罪種和罪名結構

第八章 貪污賄賂罪(2111 次,58.07%)/貪污罪(382 次,10.51%)挪用公款罪(178 次,4.90%)受賄罪(530 次,14.58%)單位受賄罪(10 次,0.28%)利用影響力受賄罪(5 次,0.14%)行賄罪(394 次,10.84%)對有影響力的人行賄罪(3 次,0.08%)對單位行賄罪(16 次,0.44%)介紹賄賂罪(7 次,0.19%)單位行賄罪(508 次,13.98%)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8 次,0.22%)私分國有資產罪(70 次,1.93%)
由表6 可以看出,我國刑法規制腐敗犯罪的特點:國有企業家的腐敗犯罪主要集中于刑法分則第八章(貪污賄賂罪),而民營企業家腐敗犯罪則集中刑法分則第三章的第三節(妨害對公司、企業的管理秩序罪)。在共同犯罪中,則出現不同身份企業家相互交叉情形。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立法上的“公共部門的腐敗才叫腐敗”的僵化觀念。

表7 2014—2018年企業家腐敗犯罪各罪名觸犯頻次和占比

?
從表7 可以看出,觸犯頻次超過70 次的腐敗罪名有9 個,依次為:職務侵占罪、受賄罪、單位行賄罪、挪用資金罪、受賄罪、貪污罪、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挪用公款罪、私分國有資產罪,并且統計發現,不論在2018年一年中還是2014年—2018年五年中,此9 個罪名的觸犯頻次排名基本保持穩定,因此可視為企業家腐敗犯罪的高發罪名。
(二)國有企業家腐敗犯罪的罪種和罪名結構
2014—2018年期間,國有企業家腐敗犯罪的頻次總計1215 次,共涉及13 個具體罪名。

表8 2014—2018年國有企業家腐敗犯罪的罪種和罪名結構
從表8 可以進一步明晰國有企業家腐敗犯罪各罪名觸犯頻次和占比,在2014—2018年五年中,受賄罪、貪污罪、挪用公款罪排在前三位且占比均達到10%以上,共占5年間國有企業家腐敗犯罪總數的79.43%,成為國有企業家腐敗犯罪的最高發罪名。

表9 2014—2018年國有企業家腐敗犯罪各罪名觸犯頻次和占比

?
表9 表明,在2014—2018年五年中,受賄罪、貪污罪、挪用公款罪排在前三位,且占比均達到10%以上,共占5年間國有企業家腐敗犯罪總數的79.43%,成為國有企業家腐敗犯罪的最高發罪名。同時,各個罪名不論在2018年一年中還是2014年—2018年五年中排名基本保持穩定。
(三)民營企業家腐敗犯罪的罪種和罪名結構分布
2014—2018年,民營企業家腐敗犯罪的頻次總計2420 次,共涉及14 個具體罪名。

表10 2014—2018年民營企業家腐敗犯罪的罪種和罪名結構分布

?

表11 2014—2018年民營企業家腐敗犯罪各罪名觸犯頻次和占比
通過表10、表11 可以發現,在2014—2018 五年中,職務侵占罪、單位行賄罪、挪用資金罪、行賄罪、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排在前五位,且犯罪頻次均在200 次以上,共占當年民營企業家腐敗犯罪總數的92.06%,成為民營企業家腐敗犯罪的高發罪名。
(四)腐敗犯罪中的單位犯罪罪名結構分布

表12 腐敗犯罪中單位犯罪各罪名觸犯頻次和占比

注:總體比例為腐敗犯罪中單位犯罪/年度腐敗犯罪總數;國企比例為國企腐敗犯罪中單位犯罪/年度國企腐敗犯罪總數;民企比例為民企腐敗犯罪中單位犯罪/年度民企腐敗犯罪總數。

表13 腐敗犯罪中單位犯罪數量在腐敗犯罪總量中的占比
從表12、表13 可以看出,2018年腐敗犯罪中的單位犯罪主要分布于單位行賄罪和私分國有資產罪。2014—2018年企業家腐敗犯罪中的單位犯罪的整體分布范圍擴大到單位行賄罪、行賄罪、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受賄罪和私分國有資產罪。同時,不論是2018年一年中還是2014—2018年五年中,民營企業實施的腐敗犯罪明顯多于國有企業實施的腐敗犯罪。或者說,單位腐敗犯罪主要發生于民營企業。
(五)基本結論
其一,就企業家腐敗犯罪占其全部犯罪的比例而言,2014—2018年的五年間,企業家犯罪總數為8965 次,企業家腐敗犯罪的總次數為3635 次,腐敗犯罪占全部犯罪的比例為40.54%。其中,國有企業家犯罪總數量為1375 次,腐敗犯罪數為1215 次,腐敗犯罪占其全部犯罪的比例為88.36%;民營企業家犯罪總數量為7590 次,腐敗犯罪的數量2420 次,腐敗犯罪占其全部犯罪的比例為31.88%。這表明,國有企業家的犯罪主要為腐敗型犯罪;而民營企業家的犯罪呈現出融資類犯罪、腐敗犯罪、欺詐類犯罪“三分天下”的情形。再考慮到民營企業家腐敗犯罪的絕對數要大于國有企業家的腐敗犯罪,這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如下的基本事實并提出了相應的客觀要求:私營部門的腐敗已經成為我國現階段腐敗現象中不可忽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反腐敗戰略上需要對公共部門的反腐敗與私營部門的反腐敗統一規劃和協調推進,才利于全面反腐不斷向縱深發展。
其二,就企業家腐敗犯罪涉及的高發罪名而言,不論在2018年還是2014—2018年的五年中,職務侵占罪、行賄罪、單位行賄罪、挪用資金罪、貪污罪、受賄罪始終排在前6位,總計占全部腐敗犯罪的比例接近80%。6 個高發罪名的排序整體較為穩定,但其中行賄罪和受賄罪的排序變化較大。
其三,就國有企業家腐敗犯罪罪名及其分布而言,呈現以下特征:(1)不論在2018年一年中還是五年中,貪污罪、受賄罪、挪用公款罪始終排在前三位,且所占比重均較大,共計占比約為77%。若加上同樣以權力為基礎的私分國有資產罪,則達到了82%,說明國有企業腐敗犯罪的防控,應當集中于這四種犯罪的治理。(2)除2018年貪污罪首次超越受賄罪頻次和占比之外,其余各個罪名不論在2018年一年中還是2014—2018年五年中排名基本相似。(3)就排在前四位罪名的觸犯頻次和占比而言,除受賄罪的頻次和占比下降,其余各罪均保持輕微增加。(4)因受賄罪頻次的下降,導致2018年腐敗犯罪總頻次低于2017年的數據,但仍高于其余各年數據。
其四,就民營企業家腐敗犯罪罪名及其分布而言,則呈現以下特征:(1)不論在2018年一年還是2014—2018年五年中,職務侵占罪、單位行賄罪、挪用資金罪、行賄罪、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始終排在前五位,占民營企業家全部腐敗犯罪的92%,這為民營企業防控腐敗犯罪劃定了明確的重點范圍。(2)2014—2018年,直接侵犯企業利益的職務侵占罪和挪用資金罪總計占比47.93%,2018年占比43.30%,歷年最高占比63%(2014年),說明企業的內控機制存在明顯缺陷。(3)2014—2018年,行賄罪和單位行賄罪基本成為民營企業家專涉罪名。統計表明,行賄類罪(行賄罪、單位行賄罪、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總計占比36.41%,而國有企業行賄類罪占比不足2%。
其五,就企業(單位)犯罪而言,呈現以下特點:(1)單位行賄罪基本為民營企業所觸犯,也屬于民營企業家的高頻罪名,并且5年間呈直線上升趨勢,2014—2018年單位行賄罪分別占腐敗犯罪總數比例為4.3%、10.2%、12.6%、20.7%、16.45%。(2)就單位犯罪的分布而言,單位犯罪主要分布于單位行賄罪和私分國有資產罪。(3)民營企業單位犯罪的比率(單位犯罪頻次/民營企業犯罪總頻次)遠大于國有企業。其中,2018年和2014—2018 五年間民營企業單位犯罪的比例為24.78%(174/702)與23.00%(556/2420),而國有企業單位犯罪的比例為12.45%(36/289)與7.32%(89/1215)。單位腐敗犯罪是企業反腐敗文化嚴重缺失、高層集體腐敗的突出表現,這在民營企業表現更為嚴重。
四、企業家腐敗犯罪的刑罰適用
(一)企業家腐敗犯罪刑罰適用總述
3362 名腐敗犯罪企業家(國有企業家1056 人,民營企業家2306 人)刑事處遇的總體情況是:301 名犯罪企業家被免予刑事處罰(國有企業家92 人,民營企業家209 人),占腐敗犯罪企業家總數的8.95%;11 名犯罪企業家被單處罰金刑(國有企業家8 人,民營企業家3 人),占0.33%;1 名犯罪企業家(民營企業家)被判處管制,占0.03%;151 名犯罪企業家被判處拘役(國有企業家23人,民營企業家128人),占腐敗犯罪企業家總數的4.49%,其中115 人適用緩刑(國有企業家21 人,民營企業家94 人);2887 名犯罪企業家被判處有期徒刑(國有企業家927 人,民營企業家1960 人),占腐敗犯罪企業家總數的85.87%,其中1265 人適用緩刑(國有企業家306 人,民營企業家959 人);9 名犯罪企業家被判處無期徒刑(國有企業家4 人,民營企業家5 人),占腐敗犯罪企業家總數的0.27%;2 名犯罪企業家被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均為國有企業家,占犯罪企業家總人數的0.06%(詳見表14 和表15)。

表14 2014—2018年腐敗犯罪企業家免予刑事處罰和主刑適用特征對比表

?

表15 2014—2018年腐敗犯罪企業家緩刑適用情況
在2287 名被判處有期徒刑的犯罪企業家中,2160 人被判處5年以下〔2〕對本報告中的“以上”包含本數,“以下”不包含本數,但緩刑部分除外。有期徒刑(國有企業家573 人、民營企業家1587 人),占犯罪企業家總數的64.25%;462 人被判處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國有企業家187 人、民營企業家275 人),占犯罪企業家總數的13.74%;223 人被判處10年以上15年以下有期徒刑(國有企業家138 人,民營企業家85人),占犯罪企業家總數的6.63%;36 人被判處15年以上20年以下有期徒刑(國有企業家24 人、民營企業家12 人),占犯罪企業家總數的1.07%;6 人被判處20年以上25年以下有期徒刑(國有企業家5 人、民營企業家1 人),占犯罪企業家總數的0.18%(詳見表16)。

表16 2014—2018年腐敗犯罪企業家有期徒刑刑期分布
892 名犯罪企業家被判處罰金刑(國有企業家491 人,民營企業家401 人),占腐敗犯罪企業家總數的26.53%,罰金數額最低為1000 元,最高為1000 萬元,其中11 人被單處罰金刑(國有企業家8 人,民營企業家3 人),占腐敗犯罪企業家總數的0.33%;230名犯罪企業家被判處沒收財產(國有企業家124 人,民營企業家106 人),占腐敗犯罪企業家總數的6.84%,其中8 人被判處沒收全部財產(國有企業家6 人,民營企業家2 人),占腐敗犯罪企業家總數的0.24%;33 名犯罪企業家被判處剝奪政治權利(國有企業家19人,民營企業家14 人),占腐敗犯罪企業家總數的0.98%,其中9 人被判處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國有企業家5 人,民營企業家4 人),占腐敗犯罪企業家總數的0.27%(詳見表17)。

表17 2014—2018年腐敗犯罪企業家附加刑適用特征
(二)國有企業家腐敗犯罪的刑罰適用
1056 名腐敗犯罪國有企業家的刑事處遇總體情況是:(1)92 名被免予刑事處罰,占腐敗犯罪國有企業家總數的8.71%;8 名被單處罰金刑,占0.76%;23 名被判處拘役,占2.18%,其中21 人被判處緩刑;927 名被判處有期徒刑,占87.78%,其中306 人適用緩刑;4 人被判處無期徒刑,占0.38%;2 人被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占0.19%。(2)在927 名被判處有期徒刑的國有企業家中,最終刑期五年以下的有573 人,占腐敗犯罪國有企業家總人數的54.26%;最終刑期為5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187 人,占17.71%;最終刑期為10年以上15年以下的有138 人,占13.07%;最終刑期為15年以上20年以下的有24 人,占2.27%;最終刑期在20年以上25年以下的有5 人,占0.47%。(3)有491 名犯罪國有企業家被判處罰金刑,占腐敗犯罪國有企業家總數的46.50%。其中罰金數額最低為5000 元,最高為1000 萬元,有8 人被單處罰金刑,占腐敗犯罪國有企業家總數的0.76%;124 名國有企業家被判處沒收財產,占11.74%,6 人被沒收全部財產,占0.57%;19 名犯罪國有企業家被判處剝奪政治權利,占1.80%,5 人被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占0.47%(詳見表18、表19)。
(三)民營企業家腐敗犯罪的刑罰適用
2306 名腐敗犯罪的民營企業家的刑事處遇總體情況是:(1)209 名犯罪民營企業家被免予刑事處罰,占腐敗犯罪民營企業家總數的9.06%;3 名犯罪民營企業家被單處罰金刑,占0.13%;1 名犯罪民營企業家被判處管制,占0.04%;128 名腐敗犯罪民營企業家被判處拘役,占5.55%,其中94 人適用緩刑;1960 名犯罪民營企業家被判處有期徒刑,占85.00%,其中被判緩刑的959 人;5 人被判處無期徒刑,占0.22%。(2)在被判處有期徒刑的1960名腐敗犯罪企業家中,最終刑期5年以下的有1587 人,占腐敗犯罪民營企業家總數的68.82%;最終刑期為5年以上10年以下共有275 人,占11.93%,最終刑期為10年以上15年以下的85 人,占3.69%;最終刑期為15年以上20年以下的12 人,占0.52%;1 人刑期為20年以上25年以下,占0.04%。(3)401 名犯罪民營企業家被判處罰金刑,占腐敗犯罪民營企業家總數的17.39%,罰金最低數額為1000 元,最高數額為630 萬元,3 人被單處罰金刑,占0.13%;106 名犯罪的民營企業家被判處沒收財產,占4.60%,2 人被判處沒收全部財產,占0.09%;14 名犯罪民營企業家被判處剝奪政治權利,占0.61%,4 人被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占0.17%(詳見表18、表19)。

表18 2014—2018年國有與民營企業家腐敗犯罪免予刑事處罰和主刑適用特征對比

表19 2014—2018年國有與民營企業家腐敗犯罪附加刑適用特征對比
(四)基本結論
其一,在刑罰適用整體特征方面,企業家腐敗犯罪以有期徒刑的適用為主,有期徒刑適用的年均占比均超過80%,最高年份的2014年達到了94%。其中,有期徒刑的適用又以5年以下為主,占比逐年上漲,年均適用率在52%—67%之間。對涉案企業家主要適用監禁刑,由此導致的對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發展造成的負面效應,在司法實踐中已經顯現,如企業因此遭受重創甚至倒閉,引發關聯企業權益受損,甚至危及一方經濟發展,需要在刑事政策層面予以反思和檢討。
其二,就腐敗犯罪國有企業家和民營企業家的刑罰適應而言,前者的刑罰較民營企業更重。表現為民營企業家免于刑事處罰、拘役、5年以下有期徒刑比重超過國有企業家,而5年以上有期徒刑尤其是10年以上的比重比例明顯低于國有企業家。對此進行分析,原因有二:一方面,囿于“重公輕私”的立法理念,刑事立法對侵犯國有企業資產的犯罪規定了比侵犯民營企業資產的犯罪更重的刑罰。另一方面,傳統觀點認為,國有企業家腐敗犯罪侵犯的法益為公權力的廉潔性,而民營企業家腐敗犯罪侵犯的法益主要為公司管理秩序與財產權,其社會危害性相對較低。這種在立法觀念與司法實踐中對不同身份企業家重視和保護程度上的區別對待,相對于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的社會貢獻,以及黨的十八大以來出臺的保護民營經濟與激發民營企業家活力的系列政策而言,顯然已不合時宜。
其三,對涉案企業家刑罰適用力度呈現輕緩化趨勢。表現在:(1)免于刑事處罰的人數和比重增加。(2)有期徒刑中5年以下的比例,不論是民營企業家,還是國有企業家,均呈現上升趨勢,而5年以上至15年以下刑期段的比例趨于下降。(3)2018年度沒有涉案企業家被判處無期徒刑或死刑。
其四,在緩刑適應方面,腐敗犯罪民營企業家的拘役緩刑率為73%,有期徒刑的緩刑適用率為49%;腐敗犯罪國有企業家的拘役緩刑適用率為91%,有期徒刑的緩刑適用率為33%。這與前述結論“其一”形成印證:對腐敗犯罪企業家目前仍以適用實刑為主。
其五,罰金刑適用方面,具有以下特點:(1)適用比例5年間呈持續增加趨勢(5%、9.4%、25.7%、35.5%、35.97%),且國企罰金最高額均高于民企罰金最高額。應當注意的是,近年來,行賄人行賄的數額在“水漲船高”。對于有能力輸送巨額利益的犯罪人而言,“蜻蜓點水”式的罰金刑只具有象征意義,難以起到遏制犯罪的效果。(2)罰金刑對國有企業家的適用比例高于民營企業,自2016年起,約為民營企業家的3 倍。
五、腐敗犯罪涉案企業特征
(一)腐敗犯罪涉案企業地域分布
在2014—2018年共3362 人的企業家腐敗犯罪中,有3343 家企業所在地可以確定,共涉及全國31 個省(直轄市、自治區或特別行政區)。各省份企業家犯罪數量從多到少依次為:廣東259,河南244,浙江225,山東220,安徽190,江蘇184,北京161,河北161,福建160,湖北155,上海132,湖南118,黑龍江113,四川108,吉林106,云南96,山西69,遼寧81,江西72,重慶71,廣西65,內蒙古65,貴州56,陜西54,天津43,新疆35,甘肅27,青海23,海南19,寧夏13,西藏4。
在2014—2018年共1056 人的國有企業家腐敗犯罪中,有1047 家企業的所在省份明確。各省份國有企業家腐敗犯罪數量從多到少依次為:河南88,山東80,安徽67,北京63,浙江57,福建53,河北50,湖北44,四川43,江蘇42,廣東39,黑龍江39,湖南38,上海37,山西36,云南36,重慶31,內蒙古24,江西23,遼寧23,貴州22,廣西21,陜西19,吉林17,天津15,新疆12,甘肅10,青海9,海南8,西藏1(見圖6)。

圖6 國有企業涉腐敗犯罪數量前十省份
在2014—2018年共2306 人的民營企業家腐敗犯罪中,有2298 家企業的所在省份明確。各省份民營企業家犯罪數量從多到少依次為:廣東220,浙江168,河南156,江蘇142,山東140,安徽123,河北111,湖北111,福建107,北京98,上海95,吉林89,湖南80,黑龍江74,四川65,云南60,遼寧58,江西49,山西49,廣西44,內蒙古41,重慶40,陜西35,貴州34,天津28,新疆23,甘肅17,青海14,寧夏13,海南11,西藏3(見圖7)。
2018年共948 人的企業家腐敗犯罪中,有945 家企業所在地可以確定,共涉及全國31個省(直轄市、自治區或特別行政區)。各省份企業家犯罪數量從多到少依次為:廣東94,湖北62,山東59,河南56,江蘇54,安徽52,四川50,河北49,湖南44,福建43,云南38,吉林35,江西32,上海32,黑龍江31,廣西29,浙江26,北京24,貴州23,重慶19,山西15,天津14,內蒙古12,陜西12,新疆12,遼寧12,海南5,青海5,甘肅4,寧夏1,西藏1。
(二)腐敗犯罪涉案企業產業類型
在2014—2018年共3362 人的企業家腐敗犯罪中,有3187 家企業的產業類型明確。各產業類型的分布情況見表20、圖8。

表20 2014—2018年涉腐敗犯罪產業類型分布表

圖8 2014—2018年涉腐敗犯罪產業類型前十分布圖
在2014—2018年共1056 人的國有企業家腐敗犯罪中,有1012 家企業的產業類型明確,各產業類型的分布情況見表21、圖9。

表21 2014—2018年國有企業涉腐敗犯罪產業類型分布表

?

圖9 2014—2018年國有企業涉腐敗犯罪產業類型前十分布圖
在2014—2018年共2306 人的民營企業家腐敗犯罪中,有2175 家企業的產業類型明確。各產業類型的分布情況見表22、圖10。

表22 2014—2018年民營企業涉腐敗犯罪產業類型分布表

?

圖10 2014—2018年民營企業涉腐敗犯罪產業類型前十分布圖
(三)涉案企業規模與罪名的對比分析
在2014—2018年共3362 人的企業家腐敗犯罪中,其中大型企業共1021 人,中小型企業共2341 人。涉案企業規模與罪名的具體分布如表23、表24。

表23 大型企業涉案罪名分布情況

?

表24 中小型企業涉案罪名分布情況
通過對比分析可見,在大型企業中,高發罪名里排名前五的為:受賄罪、貪污罪、職務侵占罪、挪用資金罪、挪用公款罪。在中小型企業中,高發罪名里排名前五的為:職務侵占罪、單位行賄罪、行賄罪、挪用資金罪、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同時大型企業共涉及14 個罪名分布,中小型企業涉及16 個罪名分布(詳見圖11)。

圖11 大中小企業高發罪名前五位對比分布圖
在2014—2018年共1056 人的國有企業家腐敗犯罪中,共有1012 人案件企業規模明確,其中大型企業涉案人員共652 人,中小型企業涉案人員共404 人。其中大型企業涉案的高頻罪名中前五位是受賄罪(291 人,占44.63%);貪污罪(172 人,占26.38%);挪用公款罪(60 人,占9.20%);私分國有資產罪(38 人,占5.83%);職務侵占罪(33 人,占5.06%)。中小型企業涉案的高頻罪名中前五位是受賄罪(143 人,占35.40%);貪污罪(128 人,占31.68%);挪用公款罪(63 人,占15.59%);私分國有資產罪(23 人,占5.69%);挪用資金罪(11 人,占2.72%)。

圖12 國有企業中大中小企業高發罪名前五位對比分布圖(%)
在2014—2018年共2306 人的民營企業家腐敗犯罪中,大型企業涉案人員共369 人,中小型企業涉案人員共1937 人。其中大型企業涉案的高頻罪名中前五位是職務侵占罪(139人,占37.67%);挪用資金罪(92 人,占24.93%);單位行賄罪(48 人,占13.01%);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31 人,占8.40%);行賄罪(23 人,占6.23%)。中小型企業涉案的高頻罪名中前五位是職務侵占罪(577 人,占29.79%);單位行賄罪(428 人,22.10%);行賄罪(323 人,占16.68%);挪用資金罪(297 人,占15.33%);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178 人,占9.19%)。

圖13 民營企業中大中小企業高發罪名前五位對比分布圖(%)
(四)基本結論
其一,企業家腐敗犯罪在地域分布上呈現出明顯的不均衡性。雖然企業家腐敗犯罪遍及31 個省級行政區,但位居前十位的廣東、河南、浙江、山東、安徽、江蘇、北京、河北、福建、湖北的發案總數,占全國31 個省份總數的59%。其中,腐敗犯罪涉案企業的地域分布,依據企業性質又有所不同。民營企業涉腐敗犯罪方面,居前十位的省份為:廣東、浙江、河南、江蘇、山東、安徽、河北、湖北、福建、北京;而國有企業涉腐敗犯罪方面,居前十位的省份為:河南、山東、安徽、北京、浙江、福建、河北、湖北、四川、江蘇。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作為我國經濟中心的上海,在企業家腐敗犯罪發案數方面,無論國企還是民企均未進入前十。影響企業和企業家腐敗發案數地域分布的因素較多。其中,一些重要的變量應當考慮:該地區的區位特點與經濟發展程度;民營企業和國有企業在該地區的比重;企業在該地區的營商環境尤其是法治環境等。
其二,在企業產業類型分布方面,所有產業均涉及腐敗犯罪,尤以制造業、建筑業、批發和零售業、房地產業、金融保險業以及能源生產和供應業涉案人數最多。其中,2014—2018年五年間,批發零售業呈現增加趨勢,超過房地產業和交通運輸、倉儲業和郵政業成為第三腐敗風險高發產業。同時,需要關注的是:(1)腐敗犯罪涉案企業的產業類型分布在很大程度上與企業的數量有關,例如,根據2018 中國統計年鑒,腐敗犯罪高發產業類型的批發零售業、制造業和建筑業和房地產業企業的數量排名,在各行業中長期位居前列。(2)產業的性質和具體結構亦會決定腐敗犯罪的分布,如2018年農、林、牧、漁業企業1926771 家,租賃和商務服務業2242096 家,但與之對應的腐敗犯罪率僅為7.08%和2.20%。(3)企業的產權性質會影響腐敗犯罪的產業類型,2014—2018年民營企業腐敗犯罪僅有57 例來自于電力、熱力等業,主要是因為掌控該自然資源類的企業均為國有獨資或國有控股企業。可以預見,隨著公有制企業接受更多的非公有制經濟成分的改革,勢必會對腐敗犯罪的產業類型發生影響。
其三,在企業規模與罪名關系方面,大型企業中高發罪名依次為:受賄罪、貪污罪、職務侵占罪、挪用資金罪、挪用公款罪、單位行賄罪和非國家工作人用受賄罪;而在中小型企業中,高發罪名依次為:職務侵占罪、單位行賄罪、行賄罪、挪用資金罪、受賄罪、貪污罪、挪用公款罪。其中,大型企業共涉及13 個罪名分布,中小型企業涉及16 個罪名分布。同時,在國有企業或者民營企業當中,不論是大型企業還是中小型企業,腐敗犯罪的高發分布情況不因企業的規模變化而變化,不論是中小型企業還是大型企業,侵占挪用及賄賂型罪名始終居腐敗犯罪罪名的高頻行列。
六、企業家腐敗犯罪高頻罪名分析
(一)企業家腐敗犯罪高頻罪名概況
2014—2018年企業家腐敗犯罪頻次共計3635 次,共涉及16 個罪名。在五個統計年度內觸犯頻次最高的前五個罪名分別是:職務侵占罪792 次,受賄罪530 次,單位行賄罪508次,挪用資金罪440 次,行賄罪394 次。

表25 2018年與2014—2018年企業家腐敗犯罪高頻罪名對比

圖14 2014—2018年企業家腐敗犯罪高頻罪名分布
由表25、圖14 可以看出,雖然五年間高頻罪名的排序有所變化,但高頻罪名的范圍整體上卻表現出相當的穩定性。其中變化較大的有:一是受賄罪持續上升至第2 位,而貪污罪淡出前五位;二是行賄罪始終位于前五位,但排序趨于下降,但單位行賄罪始終位居前三。具體到不同身份企業家方面,情形又有所不同。
2014—2018年國有企業家腐敗犯罪頻次共計1215 次,共涉及13 個罪名。五個統計年度內觸犯頻率最高的五個罪名是:受賄罪、貪污罪、挪用公款罪、私分國有資產罪和職務侵占罪。

表26 2018年與2014—2018年國有企業家腐敗犯罪高頻罪名對比

圖15 2014—2018年國有企業家腐敗犯罪情況
由表26、圖15 可以看出,國有企業家高頻罪名方面,最突出的就是受賄罪。另外一個顯著變化是高頻罪名中的挪用資金罪為職務侵占罪所代替。
2014—2018年民營企業家腐敗犯罪頻次共計2420 次,共涉及14 個罪名。在五個統計年度內觸犯頻率最高的五個罪名是:職務侵占罪、單位行賄罪、挪用資金罪、行賄罪、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詳見表27、圖16)。

表27 2018年與2014—2018年民營企業家腐敗犯罪高頻罪名對比

圖16 2014—2018年民營企業家腐敗犯罪情況
由上可以看出,在民營企業家高頻罪名變化軌跡方面,最突出的始終是職務侵占罪。同時,單位行賄罪呈現上升趨勢。這部分解釋了行賄犯罪在企業家腐敗中趨于下降的原因。此外,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作為5年間民營企業家觸犯的高頻罪名,呈現出高度的穩定性。
(二)企業家腐敗犯罪高頻罪名的刑罰適用
1.2014—2018年高頻罪名的主刑適用情況

表28 2014—2018年企業家腐敗犯罪高頻罪名主刑適用
表28 說明,在免于刑事處罰方面,單位行賄罪的比例最高,并明顯超過其他高頻罪名的比例,而職務侵占罪的免于刑事處罰的比例最低。在重刑適用方面,以受賄罪最為突出,判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比例達到了21%,高出職務侵占罪4 倍。
2.2014—2018年企業家腐敗犯罪高頻罪名附加刑適用概況

表29 2014—2018年高頻罪名的附加刑適用
表29 顯示,罰金刑適用率方面,受賄罪的占比最高,達到了53%,隨后是行賄罪和單位行賄罪;在沒收財產刑方面,也是受賄罪占比最高,隨后為職務侵占罪和行賄罪。

表30 2014—2018年高頻罪名的罰金刑幅度
表30 顯示,五個高頻罪名平均判處的最高罰金額度,相當于平均最高涉案金額的19%。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著罰金刑的威懾力較弱,犯罪人的犯罪收益較高。即使以單位行賄罪為例,判處的最高罰金也相當于最高涉案金額的20%。
(三)企業家腐敗犯罪高頻罪名的潛伏期
1.2014—2018年企業家腐敗犯罪高頻罪名潛伏期
各高頻罪名的潛伏期,即從第一次實施該罪到最終案發之間的時間間隔,如表31 所示。

表31 2014—2018年企業家腐敗犯罪高頻罪名潛伏期

圖17 2014—2018年企業家腐敗犯罪高頻罪名潛伏期
如圖17、表31 所示,整體而言,潛伏期在5年以下的比例,以職務侵占罪、挪用資金罪最高,達到了70%左右;而潛伏期在10年以上15年以下的比例,以單位行賄罪最高,其次為受賄罪和行賄罪。具體到不同身份企業家,情形又有所不同。
2.2014—2018年國有企業家腐敗犯罪高頻罪名潛伏期

表32 2014—2018年國有企業家腐敗犯罪高頻罪名潛伏期(含比例)

圖18 2014—2018年國有企業家腐敗犯罪高頻罪名潛伏期
從表32、圖18 可以看出,在涉國有企業家腐敗犯罪高頻罪名方面,實施受賄、貪污行為的潛伏期在5年以上10年以下的比例最大,達到了40%左右;而實施挪用公款、私分國有資產行為的潛伏期,以5年以下居多,占比也在40%左右。
3.2014—2018年民營企業家腐敗犯罪高頻罪名潛伏期

表33 2014—2018年民營企業家腐敗犯罪高頻罪名潛伏期(含比例)

圖19 2014—2018年民營企業家腐敗犯罪高頻罪名潛伏期
由表33、圖19 可以看出,職務侵占罪、挪用資金罪、非國家工作人員受罪的潛伏期,60%以上均為5年以下;而潛伏期最長的犯罪為單位行賄罪和行賄罪,10年以上20年以下潛伏期的比例,分別達到了18%和16%。
(四)企業家腐敗犯罪高頻罪名的發案環節
1.2014—2018年企業家腐敗犯罪高頻罪名的發案環節

表34 2014—2018年企業家腐敗犯罪高頻罪名發案環節

人事變動 0(0.00%)6(1.13%)0(0.00%)多環節 1(0.13%)9(1.70%)1(0.20%)環節不明 22(2.78%)24(4.53%)21(4.13%)總計 792(100.00%)530(100.00%)508(100.00%)0(0.00%)3(0.76%)1(0.23%)3(0.76%)8(1.82%)26(6.60%)440(100.00%)394(100.00%)
總體而言,在案發環節方面,日常經營、財務管理、產品生產、貿易、融資五個環節,為企業家腐敗犯罪的高法環節。其中,職務侵占罪、受賄罪、挪用資金罪和行賄罪,超過40%發生于日常經營活動中,而單位行賄罪的最高發環節為工程承攬,占比達到了30%,其次為日常經營和貿易環節(詳見表34)。
2.2014—2018年國有企業家腐敗犯罪高頻罪名的發案環節

表35 2014—2018年國有企業家腐敗犯罪高頻罪名發案環節
從表35 可以看出,國有企業家各高頻罪名的觸犯率,集中于日常經營和財務管理兩大環節,占全部案發環節的比例均超過了60%,而貪污罪、挪用公共款罪80%發生于這兩個環節。在受賄犯罪方面,除了日常經營環節,工程承攬環節、財務管理也是高發環節。
3.2014—2018年民營企業家腐敗犯罪高頻罪名的發案環節

表36 2014—2018年民營企業家腐敗犯罪高頻罪名發案環節
表36 說明,民營企業家各高頻罪名60%集中于日常經營和財務管理兩大環節。但具體到各高頻罪名,其高發環節又有所區別。職務侵占罪超過80%發生于日常經營、財務管理和貿易活動三大環節;單位行賄罪接近90%發生于日常經營、工程承攬和貿易環節。
(五)企業家腐敗犯罪高頻罪名的經濟發展程度特征
1.2014—2018年企業家腐敗犯罪高頻罪名的經濟發展程度特征

表37 2014—2018年企業家腐敗犯罪高頻罪名經濟發展程度特征(含比例)
表37 說明,各高頻罪名在不同經濟發展地區的比例,出現較大差異,總體上呈現出從四線城市向一線城市逐級遞減的趨勢。五個高頻罪名的發案率以四線及以下城市最高,平均超過了30%,其次為二線城市和三線城市,一線城市最低。其中,二線城市中企業家腐敗犯罪的比例,整體上多于三線城市的現象,值得進一步觀察和研究。
上述5 個高頻罪名與所在城市經濟發展程度的關系(詳見表38—表42、圖20—圖24)。

表38 2018年與2014—2018年職務侵占罪分布城市經濟發展程度對比

?

圖20 職務侵占罪所在城市經濟發展程度分布比例對比圖

表39 2018年與2014—2018年行賄罪分布城市經濟發展程度對比

?

圖21 行賄罪所在城市經濟發展程度分布比例對比圖

表40 2018年單位行賄罪與2014—2018年單位行賄罪的分布城市經濟發展程度對比

圖22 單位行賄罪所在城市經濟發展程度分布比例對比圖

表41 2018年挪用資金罪與2014—2018年挪用資金罪的分布城市經濟發展程度對比

圖23 挪用資金罪所在城市經濟發展程度分布比例對比圖

表42 2018年受賄罪與2014—2018年受賄罪的分布城市經濟發展程度對比

圖24 受賄罪所在城市經濟發展程度分布比例對比圖
(2)2014—2018年國有企業家腐敗犯罪高頻罪名的經濟發展程度特征

表43 2014—2018年國有企業家腐敗犯罪高頻罪名經濟發展程度特征(含比例)
(3)2014—2018年民營企業家腐敗犯罪高頻罪名的經濟發展程度特征

表44 2014—2018年民營企業家腐敗犯罪高頻罪名經濟發展程度特征(含比例)
(六)基本結論
其一,總體來看,企業家腐敗犯罪高頻罪名、國有企業家腐敗犯罪高頻罪名與民營企業家腐敗犯罪高頻罪名均表現出相對穩定的特征。其中,企業家腐敗犯罪高頻罪名始終是職務侵占罪、受賄罪、單位行賄罪、挪用資金罪。屬于國有企業家腐敗犯罪高頻罪名的貪污罪、受賄罪、挪用公款罪、私分國有資產罪已經進入前五;屬于民營企業家腐敗犯罪高頻罪名基本保持為職務侵占罪、單位行賄罪、挪用資金罪、行賄罪、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其中,單位行賄罪和行賄罪在2018年增長幅度較大。
其二,比較民營企業家高頻罪名與國有企業家高頻罪名的結構特征,可以發現:(1)國有企業家受賄罪頻次總數最高,約等于其余三種高頻犯罪(貪污罪、挪用公款罪、私分國有資產罪)頻次之和,說明國有企業家面臨的最大腐敗風險仍是權力交易型腐敗。(2)民營企業家高頻腐敗犯罪中的行賄類罪持續高發,尤其單位行賄罪增長趨勢明顯,揭示出“民企多行賄、國企多受賄”的對稱性現象。(3)民營企業的職務侵占罪、挪用資金罪高發與國有企業貪污罪、挪用公款罪的高發,皆說明內部管理不規范、違法犯罪內控機制缺失,是國企和民企在企業治理方面共同面臨的突出問題。而且,國有企業家貪污罪五年的總數,已經接近民營企業家觸犯的職務侵占罪的一半,再結合民營企業的總體數量遠多于國有企業(約為28:1)這一特征,說明國企內控機制有名無實情況十分嚴重。
其三,從國有企業家腐敗犯罪高頻罪名的潛伏期方面來看,整體潛伏期長,5年以下的為少數,多數集中于5—15年區間。其中,又以受賄罪和貪污罪的潛伏期最長,受賄罪潛伏期處于5年以上20年以下區間的比例總計為63%;貪污罪處于5年以上20年以下區間的比例總計為56%。同時,受賄罪、貪污罪出現20年以上的超長潛伏期的比例也占1%左右。另一方面,雖然民營企業家腐敗犯罪前五名高頻罪名的潛伏期,在5年以下的占比約60%,但單位行賄罪潛伏期處于5年以上20年以下區間的比例總計高達70%;行賄罪潛伏期處于5年以上15年以下區間的比例總計為62%。就單個罪名而言,潛伏期最長的為民營企業家高發罪名中的單位行賄罪。潛伏期普遍較長,一方面反映了腐敗犯罪較為隱秘的特點,存在發現難的共性問題;另一方面也真實地反映了在現行反腐模式下,腐敗犯罪的發現機制還比較薄弱。反腐敗斗爭要向縱深發展,亟待強化腐敗犯罪的發現機制。
其四,就企業家腐敗犯罪的案發環節而言,表現出如下特征:(1)2018年數據與五年整體數據的分布情況基本一致,一方面發案環節分布廣泛,涵蓋了企業經營的所有環節;另一方面又主要集中在日常經營和財務管理兩大環節,其次為工程承攬環節。(2)發案環節的分布與罪名的性質存在正相關系,如賄賂型犯罪多發于工程承攬過程。在五年數據中,發生于該環節的受賄罪占19.43%、單位行賄罪占29.52%、行賄罪占32.49%。(3)發案環節與涉案企業家的職務存在直接關系,因為企業運營的環節多屬于企業家的職務范圍。
其五,從高頻罪名發案企業所在城市經濟發展程度看,各罪名在一線城市分布率普遍較低,四線及以下城市的企業家腐敗犯罪發案率普遍處于高位水平,而二線城市較三線城市腐敗率偏高。可能的原因之一在于:經濟水平發達的省份因示范作用和政績考核等多方面因素綜合作用,防范和查處腐敗犯罪的力度更大,企業規范程度也相應較高;而在經濟發展水平較差的城市,企業自身管理不夠規范,政商環境相對不良,容易形成權利尋租利益輸送的鏈條,從而滋生腐敗。
其六,在高頻罪名的刑罰適用方面,各罪以5年以下有期徒刑居多。其中,單位行賄罪被判處免于刑事處罰和拘役的居多;在罰金刑適用方面,除2018年貪污罪罰金率高達88.24%外,其余罪名罰金適用率則相對偏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