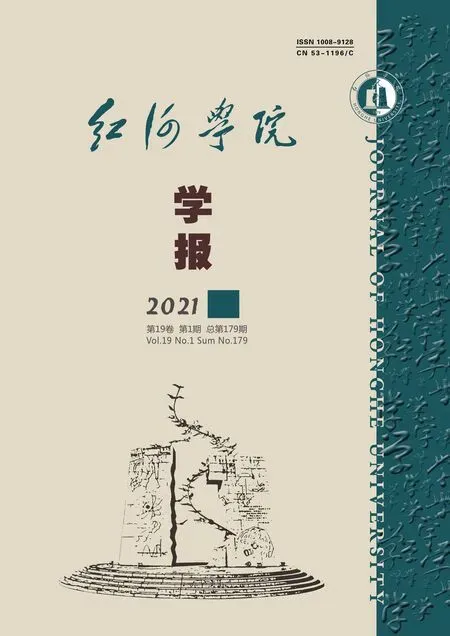麻山苗族的“歸冢”意識:《亞魯王》中的地理意象研究
李靜靜
(廣西大學文學院,南寧 530004)
《亞魯王》是一部涉及創世、戰爭、遷徙等諸多內容的苗族史詩,被譽為“苗族古代生活的百科全書”,多唱誦于麻山苗族的喪葬場所。目前,學界對《亞魯王》的研究多集中于對其宏觀文化環境及史詩文化內涵的探究,而文學地理學的理論研究方興未艾。本文從地理意象的角度出發,厘清麻山苗族的遷徙歷史,探討麻山苗族“歸冢”意識在民族精神靈魂中的存在性顯現,進而研究《亞魯王》的美學價值。
一 地理意象與麻山苗族“歸冢”意識的形成
《亞魯王》立足于麻山苗族的歷史變遷,以創世神話為創作源頭,構建了具有典型意義的麻山苗族文化意象。苗族是一個遷徙的民族,其遷徙范圍之廣,跨度之大,時間之長均為罕見。相傳苗族是蚩尤的后代,蚩尤在河北涿鹿和黃帝交戰,失敗后不得不向南遷徙。“秦漢至南北朝時期,苗族分布雖然很廣,并且接近中原,有時還有由南而北內徙的勢頭,但當時苗族的聚居區是在武陵、五溪地區及相鄰的鄂西、川東、黔東北一帶。”[1]在秦漢、唐宋之際,尤其在安史之亂后,政治動亂,戰爭頻繁,大批居于武陵、五溪地區的苗族被迫遷徙至貴州、川南、桂北和云南,形成了一個新的遷徙浪潮。“元朝統治者殘酷的民族歧視和民族壓迫政策、明王朝在黔東、貴陽、安順等地大量設置屯堡,均強迫許多苗族人遷徙,操川黔滇方言麻山次方言的苗族就是這個時期在紫云的打郎、妹場、宗地、四大寨等地居住下來的。”[2]由于麻山地區地處偏僻,直至元初元廷在與宋遺民交戰時路經麻山苗族的部分區域,這支苗族才被人們所知。
麻山苗族遷徙的過程在史詩《亞魯王》中得到了印證。“關于亞魯王的內容,是苗族先民從原武陵郡一帶遷徙到目前的川西南、滇東北、黔西北靠近金沙江一帶時產生的,其產生時間上限當在唐宋時期。”[3]史詩中記載的鹽井之戰有可能在歷史上發生過,為了爭奪鹽池而發動戰爭在苗族古歌中亦有敘述。結合史籍記載的鹽井之戰來看,麻山苗族的祖居地是位于黃河與長江之間廣袤的平原。由于戰爭因素,亞魯王率領部落,由北向南遷徙,橫渡若干江河,隨后溯江河而上,形成自東向西的遷徙路徑:
岜炯陰→哈榕冉農→哈榕冉利→哈榕吶英→哈榕吶麗→哈榕唄珀→哈榕唄壩→哈榕丫語→哈榕牂沃→哈榕卜稻→哈榕梭洛→哈榕饒濤→哈榕饒諾→哈榕咋唷→哈榕咋噪→哈榕卡比→哈榕比力→哈榕瑪嵩→哈榕瑪森→哈榕甲炯→哈榕哈占→哈榕澤萊→哈榕澤邦→哈榕嗆且→哈榕甬農→哈榕嘿旦→哈榕崩索讓→哈榕岜索久→哈榕麻陽→哈榕哈嶂→哈榕吶岜→荷布朵疆域(哈疊)。
史詩中亞魯王帶領族人自東向西遷徙,這是麻山苗族遷徙歷史的曲折反映。在祖居地中,苗族裔民以經營集市、稻作生產和魚蝦養殖等為重要的謀生手段。正是這以固定的土地為核心的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形成了苗族裔民安土重遷的民族心理。“亞魯王造田種谷環繞疆域,亞魯王圈池養魚遍布田園……亞魯王開墾七十壩平展水田,亞魯王耕種七十坡……亞魯王對七十個王后說……我要領兵去做生意,我要率將來做買賣……我要在疆域開壩場,我得到領地建集市……你們得帶兵種好糯谷,你們要領將養好魚蝦。”[4]101史詩以集市、魚蝦和糯谷等自然地理景觀構建了一個富饒宜居的祖居地,呈現了以農耕為主,以集市交換為輔的苗族經濟格局,蘊含著追求穩定和諧的價值取向。農耕民族所占據的地理空間具有穩定性,但麻山苗族由于歷史因素被迫遷徙,現實狀況與民族心理之間的沖突形成了麻山苗族強烈的“歸冢”意識。在長期的農耕生活中,糯米、麻、魚、集市等地理意象幻化為集體無意識,在時代變遷與地理遷徙中,依然根植于麻山苗族心理,成為了麻山后人“回家”的標志性符號。“蝴蝶”“馬”“魚”“糯谷”等地理意象至今仍存在于麻山苗族的喪葬儀式上。
由于戰爭因素,亞魯王被迫從富饒宜居的祖居地遷徙至偏遠貧瘠的麻山地區。“麻山位于貴州省黔西南自治州、黔南自治州和安順地區的望漠、羅甸、長順、惠水、紫云、平塘6縣結合部,面積5000多平方公里,是苗族和布依族等少數民族聚居的地方。”[5]麻山地區屬于貴州典型的喀斯特地貌,石漠化嚴重,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說。由于耕地面積有限,糧食產量低下,麻山地區長期屬于欠發達的區域,是國家重點扶貧地區。在麻山苗族的集體記憶中,先民從富饒宜居的“大平原”遷徙至貧瘠的麻山腹地。惡劣的生存環境引起了麻山苗人“東方崇拜”和“魂歸故里”的深層文化心理,由此產生濃厚的“歸冢”意識。
二 地理意象與麻山苗族“歸冢”意識的民族精神心理顯現
遷徙,在史詩文本中不僅呈現為地理空間的置換,而且鏡照出民族的集體無意識。麻山苗族人民在歷史上多次被迫遷徙,但其族群記憶感召麻山苗族人在遷徙途中建造與族源地相仿的地理空間,在喪葬儀式上吟詠祖源地,召喚亡魂回歸故土,以圓滿的心理空間彌合屢被進犯的家鄉地理空間。
麻山苗族祖居地是一個平坦開闊、集市繁榮和盛產魚米的“大平原”。河網密布,水池眾多,利于漁業發展;土質肥沃,水源充沛,便于農耕;氣候溫暖濕潤,草木茂盛,利于馴養家畜。“農業是整個古代世界的決定性的生產部門”[6],是人類賴以生存的基本條件。優越的自然地理條件能夠為人類生存提供基本食物保障及安全庇護。“東方故國”的整體地理景觀結構滿足人類長期居住的理想模式,亞魯王在遷徙途中參照祖居地的自然生態及人文生態,從水源、土地、安全等來考慮所定都的領地。亞魯王帶領苗族部落遷徙至哈榕冉農等諸多遼闊平坦的壩子,該地理位置水資源豐沛,糧草茂盛,但卻難以使族群擺脫戰爭的陰影。亞魯王只能攜妻帶兒跨上馬背繼續遷徙,走入了哈榕瑪嵩等貧瘠的山地,該地雖具備地理優勢以便躲避追殺,然而水源稀缺,不產豐盛的糧草。亞魯王只得砸破家園拿上干糧繼續上路,直至荷布朵疆域。“亞魯王說,這是一片開闊的盆地,這是一處險要的山區。一條大河穿過盆地中央,大片田壩散在河的兩岸。這里可逃避追殺,這兒能躲避戰爭。水源多多,糧草豐盛。亞魯王說這里能撫養我兒女,亞魯王講這兒能養活我族人。”[4]226荷布朵疆域周圍山勢險峻,土地開闊,具備了水源充足、生態良好、安全庇護等條件。亞魯王便將族人安置了下來,并以計謀奪取了荷布朵疆域,隨后定都哈疊。
亞魯王在艱難逃亡中定都哈疊,以祖居地為模本,重建亞魯王國,展現了苗族的“歸冢”意識。史詩《亞魯王》以集市、糯米、魚蝦等地理意象構建了一個物阜民豐的祖居地。由于戰爭的因素被迫向西遷徙,在逃亡的過程中尋找新的家園,并定都哈疊。“羊天,成群的羊過江而來,大群羊逐浪跟隨而到……稻谷種跟隨而來,糯谷種尾隨而到……青?樹跟隨而來,青?樹尾隨而到……萬物跟隨來了,萬物尾隨到了。萬物跟隨亞魯王日夜遷徙來到哈疊。”[4]159亞魯王定都后,史詩反復強調祖居地的動物、植物和糧種尾隨而至,這既是麻山苗族攜帶家畜、糧種遷徙的曲折反映,也是麻山苗族“歸冢”意識在民族精神靈魂中的存在性顯現,更是麻山苗族反抗絕望的民族精神顯現。亞魯王定都后,派兒女到“勒咚”詢問祖奶奶重建王國的經驗,并得到“耶諾”“耶婉”指點,進行了“造日月、射日月”的工作,并先后派出蚯蚓祖先、青蛙祖先、牛祖先和老鷹祖先探索疆域。亞魯王模仿先祖“開天辟地”,與兒女一同重組世界秩序,令士兵修筑長城,命將領守護王國。在亞魯王的帶領下,建立了龍集市、蛇集市、馬集市、羊集市和猴集市等十二個集市,以此進行經商貿易。“我駐扎疆域帶兵栽糯谷,我守護領地率將種小米。帶兒女駐守疆域撒下麻種,領族人守衛領地種構皮麻。”[4]258亞魯王還在新的地理空間重新種植糯谷、小米和構皮麻等植物,以構建起與先祖發詳地相似的生態環境,以延續先祖的生存方式。苗族重建亞魯王國,還原祖居地的整體地理景觀結構,在新的地域上重建和“東方故國”一樣符合人類居住的理想棲居地模式,這既是“回歸故里”的心理補償方式,也是族群身份認同的顯現。
麻山苗族的“歸冢”意識不但表現于史詩中,而且顯現于麻山苗族的喪葬場所。“在麻山苗人的世界里,世間萬物都是有生命有靈魂的,山有山魂,樹有樹魂,各種動物都有靈魂,不能隨意觸碰,否則會受到罪惡的懲罰。”[7]形滅而靈魂不滅的靈魂觀念是麻山苗族喪葬儀式的基石,也是麻山苗族祖靈信仰及送靈歸祖儀式的發端和賴以長期維系、發展的前提,其觀念信仰具體表現為“祖界觀”和“三魂觀 ”。在麻山苗族的信仰觀念中,麻山苗族信仰靈魂不滅及人死后有三個靈魂。靈魂具有不同的歸宿和存在的形態,一個住在墳墓里,一個回歸到亞魯王國與祖先相聚,一個守護在家中與子孫同吃住。在貴州省羅甸縣、長順縣、望謨縣和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縣等苗族地區,東郎在喪葬儀式上唱誦《亞魯王》,通過追述先祖的坎坷經歷和歷史足跡,幫助亡靈穿越時空回到亞魯王國。蓋“芒就”儀式、豎樁儀式、征糧儀式和砍馬儀式等均是為幫助亡靈回家而建構的文化行為。“芒就”是麻山苗人回歸故里的“通行證”,其中蝴蝶意象、魚意象、太陽意象、鳥意象和水稻意象是麻山苗族對亞魯王國的歷史記憶,體現了強烈的精神回歸生命意識。“芒就”由里外三層的三圈圖案構成,最外圍是由谷穗組成,中間層由蝶、鳥、魚和雞四種動物組成,最里層則是太陽及圍繞于其間的太陽花。苗族先祖從東方故國遷徙至貴州麻山,太陽恰是從東方升起,因而以太陽象征著祖奶奶生活的祖居地。太陽花緊繞于太陽,寓為“太陽開花”,這是苗人對亞魯王國的集體想象。魚意象、鳥意象和蝴蝶意象反復出現于史詩文本及喪葬儀式上,具有深刻的隱喻意義。“蝴蝶女祖宗從龍洞找回成千糯谷種,蝴蝶男祖宗從深坑尋來上百紅稗種”[4]51,諸多動物在麻山苗族的歷史中具有突出貢獻,故苗族后人將蝴蝶等動物尊為先祖,將其繡在“芒就”上,于喪葬儀式唱誦中訴說它們的歷史和豐功偉績。亞魯王國是一個物產豐富的魚米之鄉,盛產糯米與魚蝦。喪葬儀式上,麻山人對糯米和魚蝦的使用十分講究。孝子們以糯米供奉亡靈以及東郎的菜肴中必須有魚等文化習慣,無不寄托著麻山苗人對故土的留戀。“芒就”作為回歸故土的生命符號,蘊含著麻山苗人回歸富饒和諧家園的期許守望。
《亞魯王》以祖居地為依據重建亞魯王國,體現了恒定的民族心理。富饒宜居的祖居地承載著麻山苗族文明的精華,鏡照了民族區域的原始文化基因,蘊含著麻山苗族“歸冢”的心理意識。麻山苗族以祖居地的地理景觀構建全新但卻同質化的地理空間,即通過周圍相似的事物確立自我的身份認同和行為的合法性,以期達到與先祖溝通,以心理補償機制實現身份認同。
三 地理意象與麻山苗族“歸冢”意識的美學價值
“地理意象指具有顯著地域特色和地理因素的外觀之象進入到創作者的視野中,承載其主觀情志并在代際演變過程中融合了接受者之‘意’所復合而成的文本中的‘綜合體’;它作為文學文本的最小構成單元和元素,凝聚著創作者和接受者主體精神深處的地理基因與地域認知,并內化成文本中濃厚的地方情結,傳遞著創作者對于一個地域或超過地域的其他群體乃至全人類的精神觀照。”[8]史詩的地理意象是苗族遷移歷史與思想情志的主客觀統一體,從中可以窺探出其濃郁的“歸冢”意識。“歸冢”意識是一個民族在外界因素的影響下不斷被迫遷徙,但其集體無意識始終以族源地為靈魂旨歸,是人類渴望過安定祥和生活的圖式化顯現。
《亞魯王》以創世、遷徙與“回歸”為線索,空間上形成了一個環形的敘事結構,蘊含著“建立家園”“失去家園”和“重建家園”的敘事意涵,貫穿著麻山苗族強烈的“歸冢”意識。史詩以先祖開天辟地,創造世界為開篇,以日月星辰、山川草木、飛禽走獸等地理意象構建了一個和諧穩定的地理生存空間。亞魯王在和諧穩定的樂園上通過開墾田地、開辟市場、圈池養蝦等進一步完善家園。集市意象、魚意象、鳥意象和蝴蝶意象等構建了一個富饒宜居的祖居地。地理意象的流轉引起了地理空間的流動,蘊含著強烈的“歸冢”意識。由于外敵入侵,戰爭失敗,亞魯王在波麗莎、波麗露兩人的掩護之下,成功帶領族人遷出了含有不安定因子的居住地。亞魯王帶領族群遷徙多達30余個區域,先后走過哈榕冉農等遼闊平坦的壩子,走入哈榕瑪嵩等山地,闖入哈榕崩索讓等峽谷。地理意象的變化引起了地理背景的變換,通過詳細羅列遷徙地名,構建起麻山苗族的遷徙路徑,凸顯遷徙歷程的艱難性。史詩以重建家國大業為結局,“造日月、射日月”、探索王國疆域等情節的程式化表達,構成了史詩開篇與結尾之間的“互文性”關系,從而形成了一個環形的敘事結構。史詩文本與演唱時空亦構成環形結構,并始終貫穿著“歸冢”意識。史詩文本以亞魯王帶領苗族部落離開“東方祖居地”,自東向西遷徙為敘事內容,而麻山苗族的喪葬儀式則是為亡靈回歸“東方故國”而構建的文化行為。在“吊唁”“砍馬”和“節甘”儀式下,亡靈在東郎的引領下穿上草鞋,帶上干糧,乘坐靈馬,自西向東回歸祖居地。史詩文本展現麻山苗族離開祖居地,而喪葬場合指向回歸祖居地,二者之間相互補充,構成了環形結構。
地理意象構成了史詩文本空間,貫穿著濃郁的“歸冢”意識,體現了沉郁悲愴的敘事風格。“亞魯王攜妻兒跨上馬背,亞魯王穿著黑色的鐵鞋……亞魯王帶著撕碎了心的族群踏上了渺茫征程去前方路漫漫,亞魯王領著裂碎了肺的族群踏上了浩瀚征程去前方路長長。”[4]157-158亞魯王帶領苗族部落一同遷徙,大人、小孩、老人齊上路,攜帶糯米飯,牽牛帶馬,背上糧種,他們深深眷戀著故土,但卻被迫遷徙,產生了身心不一的撕裂感。每遷徙至一個新的地方,亞魯王命人占卜,為新區域命名,傳播民族文化種子。史詩高頻重復唱誦動植物舍命相隨,形成了語言上的回環婉轉,深切表達了麻山苗人離開故土的無奈和辛酸。遷徙途中反復唱誦的祖居地動植物意象具有深刻的隱喻內涵,其集祖居地歷史景觀物質原型與麻山苗族主觀“歸冢”情緒宣泄于一體,雜糅了客觀歷史景觀與認知主體主觀意識。史詩中反復唱誦的“羊”“雞”“狗”“豬”等動物意象,“稻谷種”“紅稗種”“麻種”等種子意象及“青?樹”“豆冠樹”“五棓子樹”等樹木意象共同塑造一個充滿鄉愁記憶的敘事環境,將東方故國的歸屬感與遷徙流亡途中的漂泊感形成鮮明對照。人的行動被迫向西,靈魂卻渴望往東,在靈與肉沖突、行為與意識相悖之下,顯現了史詩沉郁悲愴的敘事風格。喪葬儀式指向了亡靈回歸精神家園,體現了“向死而生”的樂觀心態。在麻山苗族的觀念中,死亡即是回歸故里。“在麻山喪禮上是看不到悲哀的,大家歡快,也不講究一定要穿什么顏色的衣服,大家嘻嘻哈哈有說有笑,哭只是對亡靈的一個依戀,因為他離開了我們回家了,我們想念他,這個哭是短暫的離別而不是永久的離去。”[9]喪葬儀式上為亡靈準備草鞋、鐮刀、飯籮、葫蘆等“回家”物件,寄寓著生者祈盼逝者回歸“東方祖居地”的美好期待,從而構成了悲喜交織美學特征。
綜上,麻山苗族裔民理想的家鄉在其祖居地,但因歷史上歷經多次戰爭而被迫遷徙,徙居之地的現狀和濃厚的“歸冢”意識的錯位是苗族先民生命不能承受之“重”,體現在《亞魯王》這一史詩文本中。從史詩的地理意象的空間展演可以窺見麻山苗族大體上自東向西的遷徙路徑,通過地理意象的敘事復現和印證了麻山苗族悲壯的遷徙史,表現了史詩沉郁悲愴的美學風格。“歸冢”意識終極顯現于史詩所操演的喪葬儀式上,苗族民眾在死后魂歸祖居地,雖對生命的逝去感到哀傷,但同時又對能魂歸故土這一儀式感到幸福,展現了麻山苗族裔民特有的“向死而生”的文化心理,濃郁悲愴之極又蘊含著愉悅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