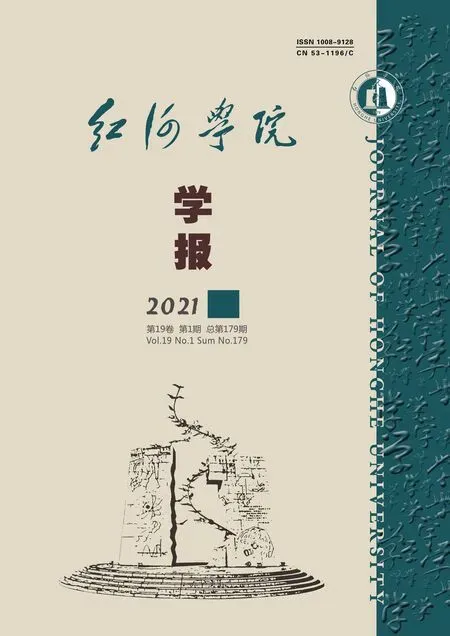郭沫若《管子集校》訓詁內容述例
田 膂,文洪睿
(1.西南交通大學人文學院,成都 611756;2.云南農業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昆明 650201)
《管子》是記錄我國春秋時期齊國哲學家、思想家、政治家管仲及其學派思想和言論的著作,因年代久遠,文獻錯漏較多,歷來被學界認為難讀。楊向奎先生指出:“先秦諸子除《墨經》外,以《管子》一書,訛誤最多,索解最難。”[1]今本《管子》由西漢劉向整理編定,定著八十六篇,今實存七十六篇,亡佚十篇。西漢之后,屢有學者對《管子》做注,然而即使到了清朝乾嘉學派古籍整理的繁盛時代,《管子》的注疏中也缺乏一部名頭響亮的著作。直到20世紀,郭沫若《管子集校》問世才改變了這一局面。《管子集校》綜合整理了前人對《管子》的研究成果,同時加入自己的考證,集歷代校勘、訓詁之大成,是學界公認最好的《管子》校注本。馬非百指其“體例嚴密,規模宏大,所見版本之多,參考歷來校勘書籍之廣,不僅是以前學者所未曾有,而且也是解放以來第一部博大精深的批判繼承祖國文化遺產的巨大著作”[2]。
然而,與《管子集校》取得的巨大成就不相符的是,學界對它的關注一直較為薄弱,研究成果甚少。在中國知網以“管子集校”為關鍵詞進行篇名檢索僅檢得論文8篇。而探討《管子集校》訓詁及校勘方面的文章則更少,僅羅業愷《從〈管子集校〉論郭沫若校勘方法》[3]、劉凱《郭沫若〈管子集校〉訓詁條例發微》[4]二文,前文列舉了《管子集校》的校勘特色和方法,后文舉例分析了郭沫若在校注《管子》時所使用的形訓、聲訓、義訓三種訓詁條例。另有幾部與郭沫若相關的專著也提到《管子集校》,但均未對其訓詁及校勘方面過多著墨,如卜慶華《郭沫若評傳》[5]、林甘泉等《郭沫若與中國史學》[6]、王錦厚《郭沫若和這幾個“文學大師”——聞一多、梁實秋、郁達夫、林語堂》[7]等。《管子集校》中的郭沫若案語多達1705條,其中的訓詁嚴謹而詳盡,鑒于學界目前對其中的訓詁內容研究嚴重不足,本文將從考證和校勘兩方面對此進行爬梳。
一 考證
《管子集校》以許維遹所纂、聞一多部分校閱的草稿為基礎,參以由郭沫若所收宋明版《管子》17種及引用校釋書目42種[8],經其多方辨別考證書中文字錯誤及真偽后,集結成書,內容豐富。郭氏在“沫若案”中的考證既考前人之說,也考釋原文。
(一)考前人之說
1.證是
證是,即考前人注說,以證其是,多為補充證據。
(1)補充古文字材料。《管子·問篇第二十四》:“毋使讒人亂(本作普)①而徳,營九軍之親。”丁士涵認為此處之“亂”當訓為“治”。郭沫若贊同丁說,并考“亂”之金文,指“‘亂’本即古‘治’字,為后人所訛誤”。
(2)補充古文獻材料。《管子·君臣上篇第三十》:“上下相希,若望參表,則邪者可知也。”何如璋注:“《淮南·天文》:‘正朝夕:先樹一表東方,操一表卻去前表十步,以參望日始出北廉。日直入,又樹一表于東方,因西方之表以參望日入北廉。則定東方兩表之中,與西方之表,則東西之正也。’即其義。”竺可楨注指何注中所引《淮南·天文訓》字句有誤:“‘日直入,又樹一表于東方’,疑是‘西方’之誤。‘定東方兩表之中’,當是‘東西兩表之中’。‘與西方之表’五字疑是衍文。”并作圖以證自己觀點。郭沫若認為竺校正確,但解釋稍顯復雜,而《周髀算經》所釋較易理解,遂補充為證:“以日始出,立表而識其晷。日入,復識其晷。晷之兩端相直者,正東西也。中折之指表者,正南北也。”
(3)補充其他版本資料。《管子·君臣上篇第三十》:“所出法則制度者明也。”丁士涵云:“‘所’字即‘則’之譌而衍者,‘則出法制度者明也’,與下文‘則循義從令者審也’對文。宋本作‘所出法則制度者明也’,恐非。”郭沫若認為丁校正確,在做進一步分析的同時,補充了古抄本及宋本材料:“丁說是也。‘出法制度者明也’與‘循義從令者審也’相對為文,故下承之以‘上明下審’。‘上’即‘出法制度者’,‘下’即‘循義從令者’,不應有‘所’字。蓋古抄本或誤‘則’為‘所’,后之錄書者兼收之,而宋楊忱本則復將‘則’字錯置‘法’字下耳。”
(4)疏解句義進行補證。《管子·君臣上篇第三十》:“量實義美,匡請所疑。”丁士涵云:“‘實’功實也。‘義’,當作‘議’,謂量其功實,議其美善也。”郭沫若贊同丁注,并通過疏解句義對丁注做了進一步補充:“丁說得之。‘量實’就內質言,‘議美’就外態言。‘量實議美,匡請所疑’以‘諸官謀士’為主辭,言諸官謀士共同審量政教設施,有所疑則求相臣匡正也。”
2.駁非
駁非,即反駁前人注說,并闡明理由,羅列證據,得出新結論。從致誤緣由看,前注之誤可分為如下十二類。
(1)誤解詞義。《管子·牧民篇第一》:“故省刑之要在禁文巧。”顏昌峣注“文巧”為“舞文巧法”,并舉《韓子·五蠹篇》“儒以文亂法”為例加以說明。郭沫若認為“顏說非是”,“文巧”義為“奇技淫巧”,與下文“無巧不禁則民乃淫”正相合。而韓子所謂“儒以文亂法”亦非顏氏所指之義,而是“指斥儒家之繁文縟禮”。可見,顏氏注的誤因為誤解“文巧”詞義,郭沫若聯系下文重釋詞義反駁顏說,理據充分。
(2)誤解文意。《管子·形勢篇第二》:“犧牲(本作牷)圭璧不足以享鬼神,主功有素,寶幣奚為?”許維遹注引“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尚書·微子篇》)”與“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牧誓篇》)”二言,指《管子》原文中的“主”應為商紂。因商紂蔑棄祭祀,其心不誠,雖設犧牲圭璧,鬼神亦不來享,故云“不足以享鬼神”。郭沫若認為許說過于牽強附會。“主”并非指商紂,而是泛指一般人。若商紂“蔑棄祭祀”,“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為何又設犧牲圭璧以享鬼神。此事不管從文辭還是事理上均說不通。許注誤因乃錯誤理解文意。
(3)不識古字。《管子·霸形篇第二十二》:“寡人不愛封侯之君焉。”豬飼彥博云:“‘君’當作‘賞’。”安井衡云:“不愛惜封之為有土之君。”戴望云:“‘君’疑‘賞’字誤。”于省吾云:“‘賞’無由誤作‘君’,安井說是也。”郭沫若指出,原文當作“尚”,假為“賞”。校書者易“尚”為“君”,是因為二字的古文形近。豬飼與戴說是,安井與于說誤。
(4)不識古音。《管子·霸言篇第二十三》:“暴國(本作王)殘之。”張佩綸云:“‘暴國殘之’句當在‘亂國并之’上,正、輕、并、民、王為韻。”郭沫若指張氏注中提及的文字押韻有誤,“正、輕與并、民、王并不韻,張喜談韻,每甚乖謬”。
(5)不識古文法。《管子·君臣上篇第三十》:“是以不言智能,而順事治,國患解,大臣勝(本作之字)任也。”陶鴻慶云:“‘大臣之任也’本作‘大臣勝任也’與‘視聽者眾也’文義相配。”郭沫若指淘注有誤:“‘大臣之任’者‘大臣是任’也,古人文法,每每之、是通用,此例至多。”
(6)誤斷句讀。《管子·小稱篇第三十二》:“操名從人,無不強也。操名去人,無不弱也。”姚永概注:“‘從人’當作‘從之’,‘去人’當作‘去之’,兩字草書頗相似而誤,以下文‘去之”為證,可見。”金廷桂注:“此承上‘有善譽我,有過毀我’而言。君有善名而從人者無不強也,有惡名而去人者無不弱也。‘操名從人’猶《孟子》言‘以善服人’也。‘操名去人’猶言‘茍不好善,士止于千里之外’也。”姚永概注因誤斷句讀而誤改原文,金廷桂注因誤斷句讀而誤讀文意。郭沫若指出:“當于‘從’字、‘去’字斷句,‘人無不強'‘人無不弱’乃指任何人,不限于天子諸侯。”
(7)誤引古文。《管子·地員篇第五十八》:“中陵十五施。”張佩綸注:“《詩·菁莪》‘在彼中陵’,毛《傳》‘中陵,陵中也’。”郭沫若指張注所引《詩》之“中陵”與原文之“中陵”有別,“《詩》因協韻故每倒言,如谷中為‘中谷’,逵中為‘中逵’,林中為‘中林’,露中為‘中露’,阿中為‘中阿’,沚中為‘中沚’,陵中為‘中陵’。”
(8)校時所參之書有誤。《管子·權修篇第三》:“賞罰不信于其所見,而求其所不見之為之化。”俞樾云:“‘化’當作‘外’,字之誤也。……《韓非子》引此正作‘賞罰不信于所見,而求所不見之外’。”郭沫若指出:“原文明白易曉,謂賞罰于所見者既無信必可言,則求所不見者為之感化,殊不可得。即賞罰不信,則不能賞罰一人而勸懲百人。”《韓非子》中之“外”字乃“化”字之訛,俞氏參訛文而校正文,適得其反。
(9)不聯系上下文。《管子·權修篇第三》:“必重盡其(本有民字)力。”孫星衍、安井衡注均指“民”字因上文而衍,戴望亦云“《治要》引此無‘民’字”。而郭沫若聯系上文“欲為天下者必重用其國,欲為其國者必重用其民”,指出此句當作“欲為其民者必重盡其民力”,若依孫氏、安井氏所言,刪去“民”字,則大謬。
(10)過度泥古。《管子·君臣上篇第三十》:“是故百姓量其力于父兄之間。”劉績云:“此言庶人。”宋翔鳳云:“《堯典》‘平章百姓’,鄭《注》‘百姓,群臣之父兄子弟’,與此義合。《楚語》‘觀射父曰民之徹官百,王公之子弟之質能言能聽,徹其官者而物賜之姓以監其官,是謂百姓’。”以上二注,郭沫若肯定劉注,同時指出宋注有誤,致誤原因為過于依賴古代文獻材料:“劉說是也。此‘百姓’即指庶人,非古之‘百姓’也。‘量其力’即‘務四支之力’。下文‘官論其德能而待之’,‘其’指百姓。官與百姓之分,即上文官與庶人之分。宋說求之古而失之。”
(11)前后矛盾。《管子·任法篇第四十五》:“不勤(本作動)力。”俞樾、戴望、王念孫均認為“動”為“勤”字之誤。而郭沫若認為“動”字不誤,指出《小問篇》中也有“動力”相聯而用的例子:“力地而動于時,則國必富矣。”同時指出俞、戴、王的校改有前后矛盾之處:“戴、俞改于此而不改于彼,王改于彼而不改于此,亦可異也。”
(二)考釋原文
《管子》雖校注者眾,但仍有不少前人遺漏未考校或考校不甚準確之字句。對于此部分內容,郭沫若做了詳盡的考釋。
1.考本字。《管子·侈靡篇第三十五》:“徒以而富之,父繫(本作擊)而伏之。”郭沫若指“父”為“斧”之初文,原文中“父”乃用其本義“斧鉞”,“父繫”義為刑戮。
2.考通假字。《管子·內業篇第四十九》:“能守一而棄萬苛。”郭沫若指“苛”通“疴”,“棄萬疴”義為袪除百病。并列舉數則二字通假的文獻用例以作支撐:“《小稱篇》‘逐堂巫而苛病起’,《小問篇》‘除君苛疾’,又《呂氏春秋·審分篇》‘惡氣苛疾無自至’。‘苛病’或‘苛疾’猶言疾病耳。”
3.考古字。《管子·侈靡篇第三十五》:“十言者不勝此一。”沫若案:“古‘甲’字作‘+’,與后人書十字,形極相近,此殆古字之幸存者。”
4.考同源詞。《管子·明法篇第四十六》:“令本(本作求)作不出謂之滅,出而道留謂之擁,下情本(本作求)不上通謂之塞。”郭沫若指出,古代以“求”為聲旁的字都有彎曲的意思,并據此系聯出一組同源詞:“‘令求不出’與‘下情求不上通’兩‘求’字均假為‘觩’。《小雅·桑扈》‘兕觥其觩’,《說文》引作‘觓’,訓角貌。《榖梁》成七年‘展斛角而知傷’,《注》‘球球然角貌’。角貌即是彎曲之意。《魯頌·泮水》‘角弓其觩’,亦言其彎也。字又作‘捄’,《周頌·良耜》‘有梂其角’。準此,可知《小雅·大東》‘有梂棘匕’,又‘有梂天畢’,亦均言其彎曲。古從求聲之字多含曲意,如玉磬謂之球,斧謂之銶,‘以財物枉法相謝’謂之賕(見《說文》)。故此‘令求不出’與‘下情求不上通’兩‘求’字均是枉曲之意。后《解》作‘令本不出’,改‘求’為‘本’,而‘下情求不上通’竟省去‘求’字,足見作《解》者已不知‘求’字之意。諸家均據后《解》以改正文,非是。”
5.考名物。《管子·侈靡篇第三十五》:“民變而不能變,是棁之傅革。有革而不能革,不可服。”郭沫若專門考辨了“皮”“革”之別及其中所含的雙關義:“‘民變而不能變’是猶皮毛已蛻而未蛻盡,則皮不為皮,革不為革,雖有革而不能為革之用。喻言變革之必須及時而盡致也。此文言變革頗有意取其雙關。古者皮與革,析言之則有別,傅毛者謂之皮,去毛者謂之革,而皮亦謂之‘變’。《易·革》之九五‘大人虎變’,又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虎變’‘豹變’謂虎皮、豹皮,皮變陰陽對轉。‘民變’與‘文變’之音相同,‘文變’即虎豹之皮也。”
6.考古器物。《管子·弟子職篇第五十九》:“右執挾匕。”沫若案:“徵之古物,匕確有兩種。取鼎實之匕小,其首銳。取飯之匕大,其首圓。飯匕謂之柶,亦謂之匙,‘是’其本字也。鼎實之匕則僅有匕名。其首銳,類刃物,故短劍謂之匕首。”
7.考天文。《管子·四時篇第四十》:“日掌陽,月掌陰,星掌和。陽為德,陰為刑,和為事。”郭沫若聯系上文中“星掌發,發為風”、“歲掌和,和為雨”二句,指出此處若為“星掌和,和為事”,則前后矛盾,“星掌和”為“歲掌和”之誤。歲即木星。
8.考職官。《管子·七臣七主篇第五十二》:“四隟(本作鄰)不計,司聲不聽。”郭沫若指“司聲”當是諫官之屬,司聲所轄之事有“陳《詩》以觀民風”(《王制》)、“瞽為《詩》,工誦箴諫”(《左傳》襄十四年)、“黃帝立明臺之議”、“堯有衢室之問”、“舜有告善之旌”、“禹立諫鼓于朝”、“湯有總街之庭以觀人誹”、“武王有靈臺之復”(以上出《管子·桓公問篇》)。
9.考農事。《管子·地員篇第五十八》:“芬然若澤若屯土。”汪繼培、孫詒讓、許維遹等人曾對原文之“土”“澤”“芬”等字均做注,然而郭沫若認為“諸說均未得其解”:“‘澤’當假爲‘蘀’,《說文》‘草木凡皮葉落陊地為蘀’。‘屯土’者殆如今之堆肥。農人積草薉腐之以為肥料者也。此既言‘若蘀’,于意尚有未盡,故申之以‘若屯土’。此正證明堆肥之法古已行之。”
二 校勘
在校勘方面,郭沫若綜合運用對校、本校、他校、理校等多種方法,對《管子》進行了全方位的校釋。
(一)校勘內容
從校勘內容看,郭沫若的校勘內容包括訛、脫、衍、倒、錯簡等方面。
1.正訛文。《管子·形勢篇第二》:“平隰之封(本作平原之隰),奚有于高。”郭沫若指“平原之隰”當作“平原之陘”。因形近而訛:“準‘濕’或作‘溼’之例,則‘隰’字亦可作‘’,與‘陘’形近,故致訛也。”
2.補脫文。郭沫若所補脫文有脫單獨一字的情況。如《管子·牧民篇第一》:“積于不涸之倉,藏于不竭之府。”吳廣霈云:“‘積’‘藏’下應各有‘糧’‘財’字,或佚脫也。”郭沫若指出,吳氏言“積”“藏”二字下有脫文不誤,然所脫之文并非吳氏所指,依據下文“務五谷則食足,養桑麻,育六畜則民福”,“積”下所脫為“食”字,“藏”下所脫為“富”字。也有脫一句話的情況。如《管子·戒篇第二十六》:“東郭有狗嘊嘊。”郭沫若根據上下文意及別篇相關內容指此處有脫文,并據此推斷該篇尚有其他脫文:“此‘東郭有狗’指易牙,下‘北郭有狗’指豎刁,‘西郭有狗’指衛公子開方。東北西均有狗,而無‘南郭有狗’。疑奪‘南郭有狗’指棠巫。《小稱篇》所載為易牙、豎刁、棠巫、公子開方四人,后此四人果為亂。下文亦缺棠巫,知此篇奪文尚不止此。”
3.刪衍文。《管子·問篇第二十四》:“十六道同身,外事謹。”郭沫若指“十六道同身”為衍文,當刪,并加以論證:“《君臣下篇》‘四肢六道身之體也’,尹《注》‘六道謂上有四竅,下有二竅也’。此即‘六道同身’之意。抄書者隨意涂鴉,摘錄此成語,校書者叉去之,乃又訛而為‘十’,竟成‘十六道同身’,并竄入正文也。本篇自‘制地君曰’以下均系抄書者卷后雜錄,故歧之中又有歧也。”
4.乙倒文。《管子·侈靡篇第三十五》:“視其不可使,因以為民等。”沫若案:“‘不可’當為‘可不’之倒,當讀為‘視其可否使,因以為民等’。”
5.順錯簡。《管子·匡乘馬篇第六十八》:“桓公曰:‘善哉!’管子曰:‘筴乘馬之數未盡也(本無‘管子曰’三字)。’”沫若案:“自‘桓公曰善哉’以下至‘高下之筴不得不然之理也’八十四字(‘管子曰’三字在內)當在本篇之末,承接‘此有虞氏之筴乘馬也’,錯簡于此。蓋下文始言‘筴乘馬之數’,此突言‘筴乘馬之數未盡也’于文失序。”
(二)校勘手段
從校勘時所使用的材料看,郭沫若的校勘手段可分為如下幾類:
1.利用古文字材料。《管子·君臣上篇第三十》:“為人上者,量功而食之以足。”郭沫若認為“足”當為“正”字之誤,因二字古文相似而訛:“古文‘正’或作‘’若‘’(見《說文》,又金文、甲骨文皆然),與足極相似,故致誤。”
2.運用古音知識。《管子·幼官篇第八》:“九舉而帝事成形。”沫若案:“原文有韻,‘形’當為‘功’。終、從、豐、充、用、功為韻。”郭沫若通過文字押韻校勘原文中的文字錯誤。
3.本書各篇章互校。《管子·心術下篇第三十七》:“意以先言,意然后刑。”郭沫若將此篇內容與《內業篇》互校,指出此句當作“意以先音,音然后刑”,音與上心字為韻。而《內業篇》中“彼心之心,音以先言,音然后形,形然后言,言然后使(二‘言’當為名),使然后治,不治必亂,亂乃死”句中的“音以先言”亦當作“意以先音”。
4.多版本綜合考量。《管子·霸言篇第二十三》:“重國輕之。”沫若案:“古本、劉本、朱本作‘輕國重之’,與宋本、趙本異。以‘輕國重之’為長,蓋‘重國輕之’,與上‘強國弱之’犯復。”郭沫若在查閱不同版本的基礎上,結合上文提出自己的觀點,令人信服。
5.引書與文意相結合。《管子·霸形篇第二十二》:“則令固始行于天下矣。”抄本《冊府元龜》七百三十六中引“固”作“因”,郭沫若結合引文及《管子》文意,認為“固”作“因”更為文從字順。
6.運用古代歷史知識。(1)運用古代政治制度。《管子·侈靡篇第三十五》:“縣人有主人此治用。”沫若案:“兩‘人’字均當為‘入’字之誤。齊于春秋時已有縣制,靈公時《叔夷鐘》銘有‘其縣三百’語。縣之所入有主持其事者,入此所以治用,然而不治,乃以積之于市。”(2)運用古代學派相關知識。《管子·心術上篇第三十六》:“物固有形,形固有名。此言不得過實,實不得延名。”王念孫云:“‘不得過實’上,當有‘名’字。”安井衡說同。沫若案:“當以王念孫、安井衡說為是,‘名不得過實,實不得延名’,即名與實必須一致,此乃戰國時正名派之基本原理。詭辯派則反是,其技倆為‘形名異充,聲實異謂’。”
7.運用地理知識。《管子·治國篇第四十八》:“常山之東,河汝之間,蚤生而晚殺,五谷之所蕃孰也。”郭沫若認為“常山”為“嵩山”之誤,一方面“常”與“嵩”字形相近,另一方面只有改為“嵩山之東”,才與“河汝之間”地域相連,原文才可能將兩地并稱。
8.根據常理。《管子·權修篇第三》:“粟與金爭貴。”郭沫若指出“粟與金爭貴”有悖常理,若粟、金同價,則人民無所食。“貴”當為“貢”字之誤,“粟與金爭貢”義為粟多金賤,人樂于獻上。同時以《君臣篇》中“財力之貢于上,必由中央之人”二句作旁證,并聯系下文“市不成肆,家用足也”,以支撐觀點。
綜上,郭沫若《管子集校》訓詁內容豐富。從考證方面看,既考前人之說,也考釋原文。考前人之說主要從證是及駁非兩方面入手,證是多為補充證據,駁非時則闡明理由,羅列證據,論述充分;考釋原文主要是對過去的《管子》校注者遺漏未考校或考校不甚準確之字句進行詳盡考釋。從校勘方面看,郭沫若綜合運用對校、本校、他校、理校等多種方法,對《管子》進行了全方位的校釋。總之,郭沫若《管子集校》考校詳實嚴謹,綜合運用文字學、音韻學、歷史學、考古學等多學科知識,結合前人研究,詳細比對《管子》各版本材料,集《管子》訓詁、校勘之大成。稱其為迄今為止最好的《管子》校注本,不為過譽。
注釋:
①括號中文字為《管子集校》中的郭沫若注釋原文,下文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