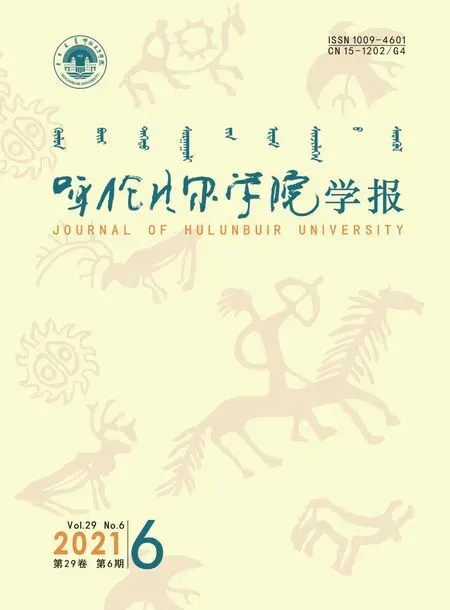精衛(wèi)故事演變探因
——以明代《列國前編十二朝》為中心
鄧 雷 楊園媛
(福建師范大學 福建 福州 350007)
“精衛(wèi)填海”是我國最廣為人知的神話故事之一,晚明被改編成情節(jié)曲折、人物形象生動的小說。余象斗在《列國前編十二朝》中,在填海情節(jié)之外創(chuàng)造出求仙守節(jié)的情節(jié),把精衛(wèi)塑造成一位貞潔烈婦。情節(jié)出現(xiàn)這樣的豐富改編,可以通過探尋余象斗的生活時代找到答案。
一、精衛(wèi)故事的早期形態(tài)
精衛(wèi)故事現(xiàn)存最早版本是在晉代郭璞整理注釋的《山海經(jīng)》中:“又北二百里曰發(fā)鳩之山,其上多柘木,有鳥焉,其狀如烏,文首、白啄、赤足,名曰精衛(wèi)。其鳴自詨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東海,溺而不返,故為精衛(wèi),常銜西山之木石以堙于東海。”[1]精衛(wèi)作為華夏始祖炎帝的女兒,經(jīng)海難化鳥后更加勇敢,她通過填海挑戰(zhàn)大海的權(quán)威,試圖戰(zhàn)勝自然,是位英雄少女。精衛(wèi)故事在最初就有較為簡單的情節(jié)。
到西晉張華的筆下,他把已經(jīng)較為簡單的“精衛(wèi)填海”更加簡化地記錄下來。他在《博物志》里寫“有鳥如烏,文首、白喙、赤足,曰精衛(wèi)。故精衛(wèi)常取西山之木石,以填東海”[2],精衛(wèi)故事沒有了海難變鳥的情節(jié),“填海”變成這種鳥的生物特性。張華另外還記錄“君山,洞庭之山是也。帝之二女居之,曰湘夫人。帝女遣精衛(wèi)至王母,取西山之玉印,印東海北山”[3]的情節(jié),精衛(wèi)除了填海,還受帝女驅(qū)使,行動的自覺性降低,英雄性變?nèi)酢?/p>
在此之后,精衛(wèi)僅在作家的詩詞中,沒有故事情節(jié)上的發(fā)展。直到晚明,余象斗在《列國前編十二朝》里把精衛(wèi)故事演繹成全新的模樣。
二、《列國前編十二朝》中的精衛(wèi)故事
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的《列國前編十二朝》在正文第一頁就有“三臺山人仰止余象斗編集”[4]字樣,這是該書作者為明代建陽書坊主余象斗的直接證據(jù)。這本書是余象斗在重刊族叔余邵魚《列國志傳》之后編著的小說,成書在萬歷二十九年(1601)至崇禎二年(1629)之間。[5]
精衛(wèi)故事出現(xiàn)在《列國前編十二朝》卷一“精衛(wèi)公主求仙化小鳥”,精衛(wèi)以其喜食黃精而得名。15歲的暮春,她在逛花園時看到春光逝去,產(chǎn)生長生不老的想法。當夜西王母降落、指引精衛(wèi)前去求仙。不料公主在東海之濱的東萊見到一個容資絕世的少年,動了凡心,贈釵并許諾求仙歸來招其為駙馬。引起目睹此情的東王公忌憚,他認為精衛(wèi)凡心不凈,愛慕男色,倘若求得長生不老,仙界的玉色仙童都會成為她的追求對象,從而擾亂仙規(guī),將是個“尤物”。所以令東海龍王興風作浪,覆溺其舟。無奈精衛(wèi)長得十分貌美,在她落水后,東海龍王又起了救護之心,精衛(wèi)感念龍王的救命之恩,但外貌丑陋的龍王怎及東萊的絕世少年,欲死不舍,欲回不能,只能憤而化鳥。
稍后的《開辟衍繹通俗志傳》基本照抄《列國前編十二朝》的情節(jié),只是將題目改為“精衛(wèi)公主訪神仙”。[6]
《列國前編十二朝》在原版填海的故事框架里,填充了很多情節(jié),讓這個簡單的神話故事變得曲折離奇。余象斗的改編主要有以下幾點:一是精衛(wèi)去東海不是游玩,而是為了求長生不老;二是精衛(wèi)公主存凡心,見到美男子主動贈釵并招為駙馬,這一行為直接導致求仙失敗;三是東海突起大風浪不是自然現(xiàn)象而是東海龍王的運作;四是精衛(wèi)化為小鳥是因為不忘美麗的東萊男子,又不愿委身丑陋的東海龍王,不愿死去也不能離開,只能化鳥。
在曲折的求仙、求婚和災難之后,余象斗最終將故事落腳在精衛(wèi)化鳥的忠貞上,甚至寫詩贊美——“趨避凋華自古然,玉顏獨肯問神仙。孤身萬里凌滄海,絲鬢雙親付碧天。曠野有盟操不棄,深濤尤許力為填。世間多少奇男子,爭向枝頭說杜鵑。”[4]余象斗認為“曠野有盟操不棄”是精衛(wèi)化鳥的直接原因,這種不放棄原始婚約體現(xiàn)她的至死不渝,值得世間男子贊頌,樹立起精衛(wèi)貞潔烈婦的形象。
將簡單的“精衛(wèi)填海”改編成如此翻天覆地的模樣,是前朝從來沒有的。通過探究余象斗生活時代的社會風貌,可以對改編緣由窺見一二。
三、改編緣由分析
(一)求仙問道的社會風氣
《山海經(jīng)》里的精衛(wèi)是一個天真卻有韌性的孩童,因在海邊游玩慘遭橫禍。余象斗將精衛(wèi)出海的理由改為“求仙訪道”。這一改編需要結(jié)合明代宗教信仰狀況來分析。
明代宗教發(fā)展異常昌盛,其中道教的影響尤為突出。明代皇帝從太祖朱元璋親近道士,到嘉靖皇帝虔誠奉道。嘉靖相信堅持齋蘸符箓就能長生不老,甚至中年以后專心煉丹,日事齋蘸,不理朝政;另外,“明代道教內(nèi)丹煉養(yǎng)術(shù)的具體化和通俗化,為它擴散到民間創(chuàng)造了有利條件”[7];同時,道教一直講究健身養(yǎng)生,休養(yǎng)生息。在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全國上下紛紛信仰道教。但明代的宗教信仰呈現(xiàn)出三教合流的局面,宗教信仰又與生活緊密結(jié)合。這樣的信仰狀況使得小說、戲曲等通俗文學里大量滲入宗教觀念,以《西游記》最為明顯和有名。這些作品描寫當時社會的宗教生活,借宗教達成浪漫主義的藝術(shù)構(gòu)思;又在作品中宣揚宿命論、因果報應等思想。余象斗也深受影響,他筆下的佛教人物在中國的創(chuàng)世神話里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列國前編十二朝》開篇講述開天辟地故事,把盤古設置成西方佛祖的弟子昆多崩娑那,只因他在佛祖商量救渡南贍部洲時合掌微笑就被派遣去開天地。昆多崩娑那開辟天地以后圓滿歸位,又被派去用心經(jīng)分離日月。除此之外,余象斗引用道教的典故,寫黃帝一心向道,曾西至崆峒山問道于廣成子,最終和元妃一起騎龍升天。同書中尚且有這些的充滿佛道色彩情節(jié),那么精衛(wèi)出海求仙也不算奇怪。
宗教都有清規(guī)戒律,信仰者都要遵守。精衛(wèi)贈釵違反道家的清規(guī)戒律,所以在余象斗筆下,精衛(wèi)出海求仙只能以失敗告終,而且為了讓讀者認識到問道心誠的重要性,心不誠的精衛(wèi)必須付出生命代價。所以作者寫出精衛(wèi)有凡心和沉船之間的因果關系,還特別在精衛(wèi)贈釵被東王公目睹后強調(diào)“莫道陰陽無報應,舉頭三尺有神明”[4]。故事到這里,作者改編的意圖似乎都在宣揚道家虔心修行、謀求長生不老。但他接下來筆鋒一轉(zhuǎn),直接贊美女子守貞。
(二)忠貞烈婦思想的加強
可能受限于余氏的創(chuàng)作水平,在他改編的精衛(wèi)故事里,除了結(jié)尾直接寫詩贊頌,前文并沒有細節(jié)表現(xiàn)婦女忠烈思想。余象斗筆下的精衛(wèi)是一位身份高貴的公主,與杜麗娘或者崔鶯鶯不同,她可以獨自游賞御花園;還可以孤身出游訪神仙,甚至沒有媒妁之言,私自贈釵求駙馬。精衛(wèi)化鳥不是她的唯一選擇,她原本有屈服的打算,直到她看到龍王的外貌,并把龍王與東萊少年的外貌進行對比。以美丑對比的心理活動作為精衛(wèi)化鳥的直接原因,讀者可能會打趣外表丑陋的龍王竟然妄想迎娶美麗的公主,或是感嘆精衛(wèi)寧愿改變物種也不放棄對美的追求,又或惋惜公主化鳥的不幸遭遇。但這樣的多重意蘊明顯不能表現(xiàn)作者改編的真實意圖,所以他在故事結(jié)尾,比較生硬地寫詩贊美精衛(wèi)的忠烈。因為在余象斗看來,即使是沒有媒妁之言的私相授受,精衛(wèi)贈釵并許諾的行為已經(jīng)是婚約,即使為了活命屈從于龍王,放棄口頭婚約也是不貞潔的表現(xiàn)。
在余象斗經(jīng)手編刻的小說里,詩歌數(shù)量普遍不多:《廉明公案》4首、《皇明諸司公案》3首、《北游記》3首、《南游記》2首,《列國前編十二朝》出現(xiàn)6首詩已經(jīng)是比較多的情況,而且詩中還專門贊頌精衛(wèi)的忠貞,可見他對婦女貞潔觀的重視。這種重視與明代提倡女子守貞直接關聯(lián)。
余象斗生活的晚明,雖然出現(xiàn)了像《金瓶梅》這種描寫婦女改嫁、直言性事的“禁書”,但國家的正統(tǒng)思想仍然是“餓死事小,失節(jié)事大”的程朱理學,對婦德、貞潔尤為看中。明代統(tǒng)治者在建國之初,不僅大力提倡理學,更有意識地倡言婦女貞潔,甚至頒布詔令,對守節(jié)婦女旌表門閭。用國家行政手段獎勵守節(jié)婦女,并為守節(jié)婦女的家族頒發(fā)榮譽。另外,國家還注重婦女教育,通過修訂《女四書》潛移默化地對女子進行思想控制。在這兩方面的作用之下,婦女節(jié)烈的悲劇空前絕后地上演。國家的指導思想讓士人將貞潔思想落實到他們能發(fā)表觀點的每一個場合,即使小說也不例外。“教化為先”成為通俗小說創(chuàng)作中的重要傳統(tǒng)[8],同時期的《有夏志傳》也將嫦娥塑造成了因不愿侍二夫吞下靈藥飛升的守節(jié)新嫦娥。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精衛(wèi)也變成貞潔烈婦。
(三)小說商品化的盈利需求
通俗小說的主要受眾是市民階級,對通俗小說需求大的市民階級包括販夫走卒之類的下層讀者、有一定經(jīng)濟能力但文化水平不太高的商人以及一些喜愛閱讀小說的士人階級,其中尤以“下層百姓的數(shù)量最多”。[9]他們的存在使得通俗小說有了龐大又穩(wěn)定的消費群。但下層讀者的文化水平相對較低,對詩文的鑒賞能力不太高,他們對通俗易懂、娛樂性強的故事非常喜歡,他們“不注重文字描寫的細膩和雅致,他們喜歡故事的曲折和熱鬧”。[10]滿足讀者需求,成為書坊主們的最大追求。
余象斗把《山海經(jīng)》里不到百字的精衛(wèi)神話改編成了近兩千字的小說,在精衛(wèi)出海、填海的主線情節(jié)之外又增添了眾多內(nèi)容:為了迎合讀者對仙界的憧憬,增添西王母指引、精衛(wèi)求仙東海和東王公的情節(jié);為了滿足讀者對男女之情的偏好,又寫了東萊贈釵、東海龍王心動以及少年與龍王美丑對比的內(nèi)容;至于小說里寫的精衛(wèi)撒嬌、炎帝夫妻思女心切等情節(jié)可能也是為了照顧讀者對帝王家庭生活的好奇。這些內(nèi)容的增加,讓小說一波三折,生動有趣,戲劇性頗強,成功達到吸引讀者閱讀和購買的目的。
(四)建陽刊本的理學之風
余象斗在《列國前編十二朝》的內(nèi)封中寫“斯集為人民不識天開地辟三皇五帝夏商諸事跡,皆附相訛傳。故不佞搜采各書,如前諸傳式,按鑒演義。自天開地辟起,至商王寵妲己止。將天道星象、草木禽獸,并天下民用之物、婚配飲食藥石等出處始制,今皆實考所,不至于附相訛傳,以便觀覽云。”[4]可見,余象斗主觀上希望這本小說能起到歷史教育作用,這種主觀意圖與以余象斗為代表的建陽書坊主始終堅守社會教化的刊刻底線直接關聯(lián)。究其原因,要從朱熹談起。
建陽地處武夷山脈的谷地,朱熹生于斯長于斯,理學從這里起源并傳至全國。建陽人以朱熹為尚,以理學為尚。福建從宋朝起就是教育大省,建陽是福建教育最發(fā)達的地區(qū)之一。元朝以后,理學成為國家正統(tǒng),四書五經(jīng)變成科舉考試的指定用書。教育的普及使理學深入建陽的普通民眾。不少建陽書坊主受過良好的教育,有較高的文化修養(yǎng),甚至可以親自編書。這些書坊主們在編著和刊刻小說時更傾向有理學價值的作品,更重視社會教化作用。因此在眾多小說類型里,建陽刊本的小說題材“主要為講史小說、神魔小說、公案小說”;[5]反而少有人情小說。因為前三種小說都有助于社會教化——講史小說通過演繹歷史宣揚忠義、君臣思想;神魔小說也多是為了闡發(fā)道德性命奧旨,勸人向善;公案小說懲惡揚善,也有助于普及司法知識。即便現(xiàn)存有種德堂本《繡榻野史》和人瑞堂本《隋煬帝艷史》,但據(jù)考證,兩種小說可能都是建陽設在金陵的分店刊刻。而余象斗親自編撰的《廉明公案》和《皇明諸司公案》是公案小說;《北游記》和《南游記》是神魔小說;《列國前編十二朝》則是講史小說,完全符合建陽刊刻的特點。
建陽書坊主們把小說的社會教化功能當做出版紅線,即使到書坊衰落的天啟、崇禎年間也“沒有介入艷情小說的刊刻以挽救自己的衰勢”[5]。上文提及嫦娥守節(jié)的《有夏志傳》也是建陽刊本的小說,所以在這種刊書傳統(tǒng)之下,余象斗寫精衛(wèi)是為宣揚婦女貞潔也就很正常了。
綜上所述,明代社會濃厚的求仙問道風氣使精衛(wèi)出東海的原因變成求訪神仙,忠貞烈婦思想是精衛(wèi)憤而化鳥的直接原因,將簡短神話改編得曲折熱鬧是為了滿足小說商品化的需求,但建陽書坊主們堅守的出版底線又把小說從男女之情的熱鬧拉回到貞潔教化之下。精衛(wèi)故事在《列國前編十二朝》中出現(xiàn)如此巨大的轉(zhuǎn)變處處體現(xiàn)出晚明社會和建陽刊本小說的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