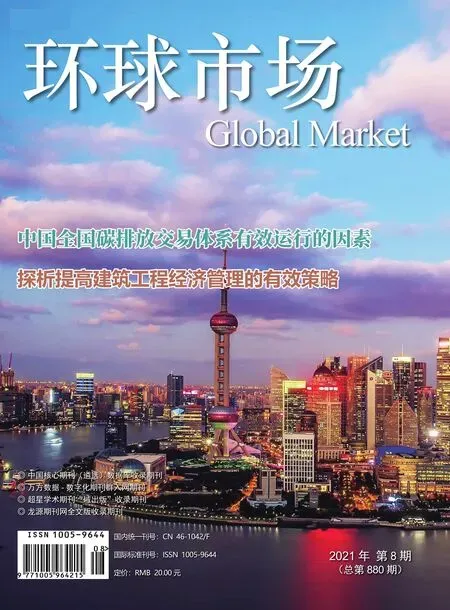產業經濟學中的塊狀發展
徐欽淋 西南科技大學城市學院
塊狀經濟(Massive economic)是指一定的區域范圍內形成的一種產業集中、專業化極強的,同時又具有明顯地方特色的區域性產業群體的經濟組織形式。“塊狀經濟”的歷史十分悠久,不是什么新生事物。在手工業時代,“塊狀經濟”就已出現,而且已是手工業發展過程中十分突出的現象。工業革命之后,“塊狀經濟”更加明顯。現代工業城市的產生就是“塊狀經濟”的集大成。
本文將詳細闡述塊狀發展、與結構張力,并根據各個國家的政策對其發展的影響進行詳細分析。為了更好理解塊狀發展的概念和適用性,首先要注意的是,它屬于一種與經濟文獻中早已建立起來并仍然主導所有教科書的理論結構的分析,也屬于“熊彼特動力學”——一種被認為是許多產業經濟學的基石的學科。這是因為產業和貿易的轉變,無論是在給定資源的最優配置上,還是在一般宏觀經濟學的主要學科上,比如商業周期、就業和物價水平,它也具有不同于新古典或傳統宏觀理論基礎的經濟增長理論,它們的平衡和不平衡與“熊彼特動力學”中所關注的重點完全不同。
轉換作為中心因素,意味著去關注什么是改變經濟市場各種事物的決定力量,重點在于關注時間和微觀實體之間的變化,這種變化是工業動態的本質,它之所以意味著不平衡,而不是干擾因素,是因為它們在轉變過程中是必不可少的。
幾乎每一次變革的一個特點都是“新”和“舊”事物之間不斷發生沖突,在這種沖突中,創業意味著技術發展和經濟變化之間的雙向交流,在廣義上起著決定性作用。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創新、傳播以及產生創造性破壞的問題,所發生的情況不僅是價格較低或質量較高的新產品和服務脫離市場,許多新事物也因此開辟了前所未有可能性,創造了新的需求。因此,必然會對其他生產商造成各種影響,因為它們可能面臨著或多或少迫切的需要,以適應新的市場情況,因為原材料價格和工資的實際或預期變化,或是因為人們被引誘花錢購買新產品或服務而不是“舊”產品或服務。
轉換過程通常在兩種極端情況之間會有臨界線。其中一種情況是有機會進入新的活動領域進而取得進展,從而促進工業和貿易的結構調整。如果是這樣的話,轉換壓力就會被標記為正。這些機會的數量和重要性以及抓住這些機會的程度,取決于創業的質量以及勞動力和資本市場的特點和運作等“體制”因素。
另一種情況也可能是由一種看似輕微但又相對劇烈的調整和為了適應的必要性所支配。在“新”和“舊”事物之間的沖突中,幾乎沒有贏家,在許許多多的分支中,輸家會占大多數,特別是如果贏家剛好是外國生產者的話。如何處理這種負的轉換壓力,即如何有效地處理隨之而來的經濟問題,同樣取決于創業素質和體制環境。
一、塊狀發展和結構張力
發展進程中某些階段的經濟成功可能需要實現一個或多個具體的互補階段。這就意味著會有發展潛力。它不包括,但有時也不排除發展抑制力,在“預備”階段,只要完成的那些工作內容是已經完成過的。反過來,一旦缺失了階段或者預期,在不久后就會釋放發展潛力。因此,“早熟”階段可能會刺激創業活動。即使被抑制的壓力所支配,這種情況也可能釋放出膨脹的力量。這便是一種“結構張力”。
這種張力可能是根深蒂固的,因為沒有人知道如何解決所涉及的問題,沒人能夠采取與技術、應用技術、生產組織、營銷、客戶服務等有關的行動。在消除結構張力方面的拖延也可能是一個更瑣碎的時間問題,因為那些認為自己知道如何進行的人所采取的許多措施是非常耗時的,也許它可能是由既得利益集團、壟斷、政府法規和法律框架等制度因素造成的。
對互補性和結構張力的關注使“塊狀發展”概念得以落實。它指的是一系列互補性,通過一系列的結構張力——即不平衡,進而可能導致平衡的情況。這可能有助于明確這一概念的至少一小部分。
在經歷了初級階段后,就會有生長潛力的產生。就像一株植物開始在地上生長,而目前在土壤下面沒有發生任何變化。一段時間后,這就導致了一種不平衡的局面,這種局面阻止了增長,但使得根系進入了一個次級發展階段,這反過來又導致增長潛力與實際增長之間產生新的平衡缺乏。這會使植物重新生長。當植物能夠脫落新的種子時,這樣的生物“發育障礙”就會以穩定的平衡結束。這一比喻可以通過以下事實來進一步擴展:這一過程的速度和質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遺傳決定的,但也取決于種子和土壤的質量以及天氣條件。如果這一進程的一個階段受到了決定性的阻礙,其他階段就注定要因此消亡。
這兩個分析概念,“結構張力”和“塊狀發展”,已被證明有助于使轉型分析具有實質性的內容,再加上兩種轉型壓力之間的區別,使得其對經濟政策具有一定的影響。
二、理論闡述
假設相當多的強大的塊狀發展被周期性的中斷,即通過暫時性的衰退,涉及貸款人和投資者之間的時間范圍縮短,通過緊縮的信貸和資本市場,再加上這種市場不那么及時地復蘇,很可能會釋放出發展潛力,因此隨后將出現相對迅速的擴張,主要是積極的轉型壓力導致的。特別是在創業活動的總體環境有利的情況下,可以預期到會有相當大的發展力量,這將會在這種擴大中加入強有力的累積因素。
另一方面,假設強有力的塊狀發展的數量很小。特別是,如果還有相當大的負面轉型壓力,商業衰退可能會是深刻而持久的,成功且快速的周期性擴張的可能性相當低。工業和貿易可能具有國際競爭力,但由于最近的貶值,在這種情況下只有一個相對薄弱的發展力量。區分靜態概念的“競爭力”和動態概念的“發展力”是至關重要的。
通過更仔細地研究它們在促進發展方面的作用,可以看出創業活動在起決定性作用的重要方面。這一作用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在理論上應嚴格區分,但在實證研究中卻遠不容易區分。
未發展完成的區塊通常用不同市場上的價格和成本“信號”來表示。這可能意味著一些地區的當前利潤很低,甚至是虧損,但只要完成這些區塊所需的步驟能夠實現,前景也是很樂觀的。少數的消費沖動也可能來自經濟生活中的參與者,在理論家所謂的“市場”之外,存在著廣泛的關系和聯系網絡‘。在這兩種情況下,嘗試去挑戰任何一種都意味著填補空白,這往往會消除結構性緊張,但也可能導致新的緊張局勢,因為技術和其他解決方案有時會超過眼前的目標。它們都是事后發展的組成部分。應該指出的是,這種“填補空白”通常意味著經濟和技術進步之間的雙向交流,有時甚至是產業進步,這絕不是利用關于現有可能性的知識,而是通過積極搜索來尋求處理信息。
不太為人所知的情況是,企業家提前去完整地設想塊狀發展,至少在他們自己的看法中,足以使他們及時采取行動。
一個區塊的至少一部分可以由一個或一組企業家完成,可能還會由另一些企業家支持或合作,因此,這些未來發展領域所涉及的動態的核心是在若干方面開展協調一致的活動。其目的是通過倡議使產品和服務能夠促進新的技術解決方案,并投資或讓他人投資于經濟的其他分支或部門。因此,這不是對實際市場信號或其他信息來源作出反應的問題,而是通過協調的創業活動來創造市場,這些活動遠遠超出了廣告、傳統銷售推廣和營銷。
即使沒有一位企業家或一群企業家的協調活動,也可能產生同樣的潛在塊狀發展,即完全基于對其他地方技術進步和其他企業或負責基礎設施的政府機構所作或計劃的投資的了解。特別是在這種情況下,商業網絡和其他聯系和關系可能會發揮重要作用。
三、政策對塊狀發展的影響
通過對瑞典和芬蘭發展情況的比較研究,能夠清楚地表明政策對經濟的一些影響。在貨幣貶值以后,它們比較容易察覺。這兩種貨幣分別在這兩個國家制造,兩種貨幣都一度被貶值。工業動態在某些重要方面時常有所不同,這一事實有助于解釋貶值的影響。
在瑞典,20 世紀30 年代有許多尚未完成的塊狀發展,與20 世紀20 年代相反,只有一個稍微負的轉型壓力。此外,負擔過重的不當投資并不多。因此,1933 年的貶值作為一種刺激手段相當有效,特別是因為它導致了高流動性和容易的信貸市場。它不僅提高了競爭力,而且還促進了工業的擴展,這總是很容易實現的,因為基本的發展力量是很強大的,也沒有產生任何相當大的通貨膨脹影響,特別是當財政政策沒有擴大,工會也不是很強大的時候。
在芬蘭,目前未完成的塊狀發展的數量少于瑞典,存在的區塊大多處于早期增長階段。這個國家仍然以農業為主。在這種情況下,貨幣被低估的結果比瑞典略少,林業是唯一重要的例外。在20 世紀40 年代,這兩個國家再次遭遇大幅貶值,芬蘭在1957 年和1967 年又多次遭遇貶值。
瑞典擺脫了戰爭,可以從未受損害的人力和物質資本中獲利,這本身使擴張的機會變得相當大。還有許多開發區塊,其中一些區塊,特別是與廣泛使用的客車有關的區塊,處于早期但相當有潛力的階段。在他們早期但具有相當大影響力的階段,與預期相反,負轉變壓力不足以抵消正轉變壓力。與預期相反,負轉變壓力不足以抵消正轉變壓力。20 世紀50 年代,紡織業的負面壓力變得嚴重,許多其他部門的正面壓力變得比以前更大,因為大多數具有廣泛影響的塊狀發展獲得了很大的力量,這在1960 年代前半期尤其如此。盡管通貨膨脹的影響比1930年更強烈,除其他原因外,由于更強大的工會和開始增加的稅收,為了增加工資,他們卻沒有預期的那么大。其中一個解釋是,包括許多塊狀發展在內的積極轉型壓力主導了工業和貿易。
大約在20 世紀60 年代中期,情況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一些早期最重要的區塊要么開始分裂,要么失去了大部分力量。此外,許多工業和貿易部門從現在起經歷了一種消極的轉型壓力。盡管克朗(瑞典和冰島的貨幣單位)不再被低估,而是被高估了,但通貨膨脹的力量變得更加突出,只有通過避免采取有目的的反周期措施,才能使其保持在相當狹窄的范圍內。
芬蘭在1960 年代開始加快工業化的步伐,盡管在十年結束時,它還沒有像瑞典那樣深刻地改變國家前途。林業的積極轉型壓力很大,現在工程行業也是如此。在這種情況下,貨幣被低估的年份無疑發揮了一定的積極作用。由于特別是林業容易受到來自國外的擴張性和通貨膨脹沖動的影響,匯率政策也導致相當迅速的國內通貨膨脹,隨后不久便出現了高估和1967 年的新的大幅度貶值。這一次,通貨膨脹的影響比以前有所減少,部分原因是現在森林和工程工業內外出現了更多、更重要的塊狀發展。從20 世紀60 年代末開始,私人汽車的普遍使用構成了一個非常強大的汽車市場。大約比瑞典晚了十年。
1970 年代末,瑞典開始出現一系列貨幣貶值。第一批在1970 年代和1981 年對工業和貿易的擴張性影響要比1930 年代和194 年的要小得多,部分原因是它們沒有造成明顯的低估。另一種解釋是,工業和貿易的基本條件與前幾十年,特別是1960 年代中期以前的基本條件根本不同。現在,在廣泛的戰線上,轉型壓力是負的,在一些最重要的工業部門中也是如此。在多數情況下,人工智能行業得到了大量補貼。在這方面,社會和政治因素具有決定性的作用。特別是由于塊狀發展很少或者過于薄弱,至少在少數和不太重要的高科技產業之外,貨幣貶值的結果是競爭力在一段時間內重新建立,但缺乏發展力量。某種貨幣貶值本身不可能造成的東西,使得本該令人滿意的前景變得相當糟糕。
1982 年,貨幣大幅貶值導致了持續約三年的市場低估。當時的工業發展場景已經開始改變。早先嚴重的負變化壓力所要求的大多數調整和結構調整都已作出,而且壓力比以前要小得多。其結果是一個具有一定發展能力的有效產業,但這個產業太小,不可能在整個商業周期內保持外貿平衡。在這種情況下,迄今低估的影響似乎更像1950 年代和1980 年代初期的影響。
在芬蘭,早期的匯率政策與以前在瑞典匯率政策一樣的時候也被宣布停止。現在允許貨幣高估持續更長時間,當時所作的修正并不會造成低估。大約一年后,這一新政策在許多方面產生了有利的后果,因為它導致了許多不當投資的迅速擠出,并迫使企業比以前更多、更廣泛地合理化。延續先前的政策極有可能導致通貨膨脹加速,從長遠來看,將對工業和貿易產生主要不利影響。這不僅是因為早先的通貨膨脹經歷導致了普遍和根深蒂固的通貨膨脹預期,而且也是因為轉型壓力在預期出現更多的負面預期的同時,變得不再占主導力量,試圖通過低估貨幣來彌補這一點很可能意味著要冒很大的風險。
雖然研究表明,由于基礎工業動態的特點,匯率政策的結果有很大差異,但事實證明,分析財政和貨幣政策的結果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這些特點。這僅僅是因為它不是一個主要策略參數的問題。顯然,用“熊彼特研究法”研究工業動態的基本特征的重要性比目前在傳統宏觀經濟學中普遍觀察到的要更大。
四、結論
從本文的主要論點出發,為實際研究得出實際結論時,會有一定的難度,這種困難在于它不是大多數經濟學家常用的方法,而且幾乎沒有足夠的能力來處理。這是因為這種研究方法必須是與經濟理論和統計、商業經濟學以及專業歷史學家使用相結合的方法。此外,也需要一定的實際業務經驗。嘗試在宏觀經濟背景下的產業經濟學中解決這些新問題,對于我們的研究工作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