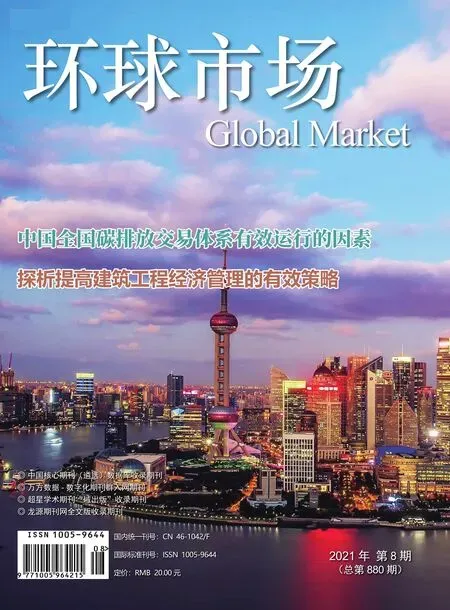金融科技創新與監管路徑探尋:基于監管科技的研究視角
黎招兵 南開大學
以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以及區塊鏈等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并與金融行業深度融合,促進金融行業從傳統金融向互聯網金融演變,并進一步催生金融科技全面成長。金融科技的創新發展,有效拓寬了金融可得性,提高了金融行業的質量與效率。[1]與此同時,金融科技對傳統金融行業以及金融監管帶來了重大挑戰與沖擊,因為金融科技作為一種創新型金融業態,具有跨界化、去中心化[2]、自伺服性及風險性等特征,從而導致其對金融行業具有“破壞式創新”,使得金融風險更加隱蔽與復雜。[3]因此,無論是從金融科技的創新發展到監管科技的監管應對,還是從金融危機的風險爆發到監管科技的監管變革,這些因素都推進了監管科技的興起。監管科技作為伴隨著金融科技發展應運而生的創新產物,其市場規模日益擴大,并在交易行為監控、客戶身份識別、金融壓力測試、合規數據報送、法律法規跟蹤以及其他場景中得以廣泛應用。監管科技也同樣面臨眾多的深度挑戰,包括金融監管環境的日益復雜、監管科技的主要技術存有短板、金融監管制度需要相關配套措施。從域外應對金融科技創新的監管路徑經驗來看,監管科技最早肇始于英國,該國首先倡導適用監管科技并大力發展“監管沙盒”,并于2016 年5 月正式由金融行為監管局(FCA)啟動了“監管沙盒(RegulatorySandbox)”機制。此后,美國在2017 年發布《金融科技框架》白皮書,明確提出要支持金融科技創新[4],注重金融科技規制以支持監管科技的發展,而澳大利亞不僅啟動“監管沙盒”機制,并設立監管科技部門,以順應金融科技的創新變革,積極推進監管科技的發展。本文擬通過對域外主要發達國家(英國、美國、澳大利亞)在金融科技創新的監管科技發展經驗予以分析,旨在探索促進我國監管科技發展的路徑[1]。
一、監管科技的理論基礎:從金融科技創新到監管變革
監管科技的理論內涵。從字面意義上看,監管科技(RegTech)是“監管”與“科技”這兩個術語的縮寫,它指在監督、管控、報告和合規等方面使用的技術,尤其是新一代信息技術。英國政府科學辦公室對監管科技的定義是:“可以應用于監管或被監管所使用的科技。”金融行為管理局(FCA)認為,監管技術是“金融技術的一個子集”,這意味著“采用新技術比目前更有效地實現監管目標”。根據國際金融協會的說法,監管技術是“一種能夠高效解決監管和合規要求的新技術”[2]。這些定義相對中立,不涉及“監管技術”的價值取向。與英國金融行為管理局不同,國外學者Douglas、Jonas 和Ross 認為監管技術不能簡單化為金融技術的一個范疇。這一定義缺乏對監管技術真正潛力的討論。國內關于“監管技術”的討論始于2017 年。孫國鋒(2017)認為,監管技術是指金融機構利用新技術更有效地解決監管合規問題,旨在降低不斷上升的合規成本(如法定報告的法律要求、反洗錢和欺詐措施、用戶風險等)。后來,他對這一概念進行了修正,認為監管技術包括“合規”和“監管”[3]。楊東(2018)將監管技術定義為“技術驅動的監管”手段,而“技術驅動型監管”是指在金融交易脫媒、分散化的現狀下,在審慎監管、行為監管等傳統金融監管維度的基礎上,增加技術維度,形成一個二維的監管體系。此外,林鵬等(2017)從本質上分析了監管技術,認為監管技術是以數據為核心和驅動力的金融監管解決方案,體現了數據邏輯的內涵。有學者認為,監管技術本質上是一種數據中介。金融技術起著金融中介的作用。它的使命仍然是服務實體經濟,為客戶創造價值。其核心功能仍然是資源配置、支付清算、風險管理和價格發現。本質上,它是用技術手段服務金融,注重了解客戶。何海鋒等(2018)認為監管科技有兩大分支:運用于監管端的監管科技(SupTech)和運用于金融機構合規端的合規科技(CompTech)。綜上所述,“監管科技”(RegTech)是“監管”與“科技”的深度融合,它是在金融與科技深度應用的時代背景下,為補充傳統金融監管的不足與低效,基于數據為核心驅動,以互聯網(Internet)、人工智能(AI)、區塊鏈(Blockchain)、云計算(CloudComputing)以及大數據(BigData)等新一代技術為依托,致力于高效合規以及有效監管的綜合解決方案[4]。
二、監管科技的場景應用與監管挑戰
(一)監管科技的發展現狀
與中國規制監管科技(RegTech)作為伴隨著金融科技(FinTech)發展而應運而生的創新產物,監管科技的市場規模日益擴大,其主要目標是“流程自動化”,即改進監管報告中的低效性,并使用技術減輕合規負擔。根據聯邦統計分析公司數據:全球在金融治理、風險和合規方面的支出約為800 億美元,預計到2020 年市場規模預計將達到1187 億美元。從2008 年到2015年,發達市場的監管規模增加了492%,特別強調對反洗錢(AML)和消費者權益保護規則的遵守。CBInsights 發布的《全球監管科技發展趨勢報告》顯示,2017 年初至9月末,全球監管科技領域融資額達8.94 億美元,涉及103 宗交易,該報告預計2017年全球的監管科技融資額將達到13 億美元,涉及148 宗交易,并廣泛分布于諸多領域:合規(59%)、反欺詐(29%)和報告(12%)。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中國對監管科技的發展持鼓勵與支持態度,并從法律規制上頒布了諸多政策文件(參見表1)。盡管中國金融市場在全球范圍內僅次于美國,但是與域外不同,我國金融監管體系大幅落后于金融科技的創新變革,我國金融機構更傾向于使用監管科技管理內部金融風險而非全面建設。自從2016 年頒布《“十三五”國家信息化規劃》以來,我國開始加強監管科技建設,并于2017 年5 月在中國人民銀行成立金融科技委員會,但相關的監管科技應用成果依然較少,監管科技建設任重而道遠[5]。
(二)監管科技在不同場景中的應用境況
當前,監管科技正處在快速發展中,并已逐步滲透到各個金融領域:通過合規性和行為分析進行風險評估;自動化的合規性監管(特定監管、按需服務、對文件和審計情況的跟蹤功能);預防欺詐,包括反洗錢(AML)、監測交易和偵測欺詐行為;員工內部監控,包括行為評估、語音和電子信息篩查;建立合規數據倉庫和案例管理系統等。從金融機構用戶、金融機構與監管機構三者角度出發,根據監管科技生態的內在邏輯以及發展現狀,我們認為監管科技主要存在于三大主體與五大場景。
三、結語
我國必須夯實監管科技的技術基礎,破解監管科技的主要技術短板,有效提升系統性金融風險的防范化解能力:一是夯實監管科技在大數據、人工智能與區塊鏈等層面的基礎技術,深入探究技術模型在金融監管層面的有效性;二是提升監管科技解決方案的可適性,基于真實實踐需要,而非某些預定的假設條件與理論模型,可廣泛適用于金融風險預警、對策建議以及監管報告自動化;三是加強金融監管機構與被監管機構的信息系統建設,從技術層面構建金融信息數據庫與信息披露系統,破解金融監管中的信息不對稱與交易成本高企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