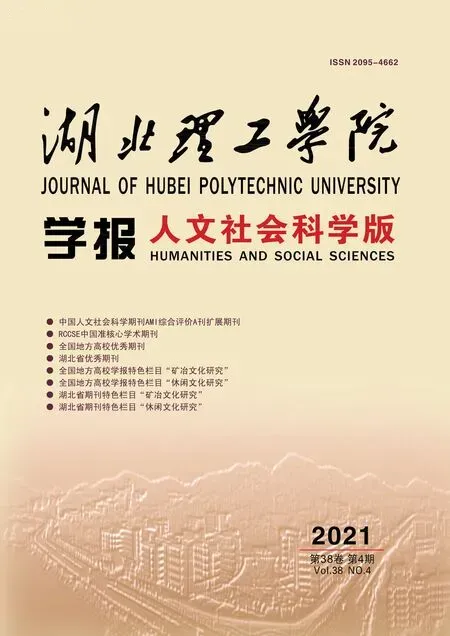蘇格拉底“奉神啟”與勞倫斯“致良知”之會通
高速平
(河北經貿大學 外國語學院,河北 石家莊 050061)
如果將人分為“理性”和“身體”兩部分,那么,在D.H.勞倫斯之前的西方人學史中,“人”基本上是以理性高貴、身體卑下的兩元對立方式出現的。勞倫斯本人直覺敏銳,善于與他人萬物做直覺交應,相信只有直覺才能體悟生命本源、與他人萬物建立一體連接,因此反對理性主義、科學主義對于身體直覺的宰制,痛批身心兩元對立思想[1]47。他認為這種傳統發端于蘇格拉底,批判蘇格拉底是“第一個覺知理性曙光”[2]91“陶醉于理性勝利”[2]196之人,甚至憤而指出,正是“蘇格拉底以來的希臘理性主義泛濫”導致古羅馬殘忍滅絕了伊特拉斯坎人這一極為推崇直覺本能、富有生命活力的可愛民族[3]377。
一、蘇格拉底對真正美德的追求
在西方,不只是勞倫斯把蘇格拉底與理性并論,在他之前、之后的一些著名思想家也是如此。亞里士多德將蘇格拉底的“歸納論證和普遍定義”視為“科學的起點”[4]398-399。不少人認為,這一論斷影響了后世對蘇格拉底哲學的基本態度[5]26。近代哲學集大成者黑格爾注重邏輯思辨,高度贊揚蘇格拉底的辯證方法和歸納推理法[6]53,甚至非理性哲學家尼采也講,西方對“概念、判斷和推理”的“尊崇”是“從蘇格拉底開始”[7]62。尼采和勞倫斯都相信人之本質在其非理性,都認為只有非理性或者說直覺本能才能把握世界本質,因此批判理性至上,對蘇格拉底有所貶損,而國內大部分學者推崇理性,多是贊揚蘇格拉底理性思辨。不少文章和著作提到,蘇格拉底有句名言——“美德即知識”,并將之釋為“美德即理性知識”。然而,并無確鑿證據說明,蘇格拉底說過此話,相反,他曾明確否認過這個命題[8]47。應該說,學界將蘇格拉底與理性并論,多是因為蘇格拉底慣用思辨式對話,然而,他與年輕人辯論,是讓他們分辨真假美德,過上有價值的生活。
蘇格拉底專門找年輕人對話,步步誘導,層層推理,不是為了啟發他們邏輯思維用以科學創造,而是辨析“節制、勇敢、正義、誠實、虔誠”等美德內涵。他認為,當時的社會權威、神話宗教所倡“美德”并非真德,年輕人卻盲目奉從,不加質疑。他與之分辨,是令之省察,認識到所從美德立不住腳,進而思考真正德行,活出人生價值。如他所言,“未經省察的人生是沒有價值的”[9]6。對于他來說,要過上有價值、有意義的人生,需要明白“真正的做人美德”。在他看來,真正美德并非俗人之發明、神廟之神定,而是進入每個人體之“神”所賦:“美德之附于人身上是神賜的……,每天討論美德,……對于人是最有益之事。”[9]112“神賜之德”,也被蘇格拉底稱作“善”。善具體包括“虔誠、正義、節制、誠實”等美德。“神啟之德”可理解為儒家所說的“天令”“良知”或“明德”。對于儒家而言,遵天令與致良知、明明德同義,人做到這些,就是遵道而行、率性而為,就能夠達到至善。
無論是對于儒家,還是蘇格拉底,實踐天賦美德乃是人之為人的最高實現;要實踐天賦美德,只能通過直覺,而非理性。用蘇格拉底的話說,“那些最幸福的人,那些到達了最佳終點的人,是那些養成了普通公民的善的人,這種善被稱作自制和誠實,通過習慣和實踐來獲得,而無需哲學和理性的幫助”[9]41。蘇格拉底這里所說的“哲學”是指思辨哲學。“無需哲學和理性的幫助”是指人若達到至誠至善境界,只有通過直覺體悟和身體踐行,而非通過思辨哲學和理性思維,因為人之理性思維具有很大局限性,“實在算不了什么”[9]101。很顯然,蘇格拉底所追求和關注的不是對自然、社會、歷史的理性認知,而是對天賦美德的體認,這種體認是以身去體的直覺之知。或許,正是因為蘇格拉底懂得,天賦美德無法用理性認知,也無法用語言表達,才述而不作,更不對之定義。
正是因為理性有限,“實在算不了什么”,人才不應以理性自居,也不應以掌握多少知識為傲。蘇格拉底言稱,他比別人智慧之處在于,他“知道自己無知”[9]82,而別人自認有知。這一宣示既是對人之理性局限性的強調,也是對當時以“擁有智慧”自居的“智者派”的批評。“智者派”是蘇格拉底那個時代以傳授辯論技巧、政治才能為業的哲學家。當時,希臘實行的是城邦民主制度。在雅典,每個具有公民資格的男子都有權利參與公共事務。要想參與公共事務,爭得一席之位,就需具有演講之術和政治智慧。在這種背景下,智者派應運而生。他們自稱具有辯術、掌握智慧,游走于希臘城邦青年之間,收費講學。而在蘇格拉底看來,人之為人,其最高價值不是體現于政治權術和政治前途,而是實踐天賦美德,聽從神啟召喚。
由此可以看到,蘇格拉底并非重理輕身。他所關切之事,既不是發展人之邏輯思維,也不是輔助年輕人提高辯術、謀取政治前程,而是引導人們重申人生價值、追求真正美德。
二、蘇格拉底的“辯論”之道
蘇格拉底為了讓年輕人認識到自己所信“美德”很有問題,經常跑到廣場與年輕人就何為美德展開辯論。其辯論方式是反詰法:先誘導對方就某個“自認美德”給出定義,再根據邏輯推理提出問題,加以質詢,讓對方陷入矛盾,引發對方反思,最后促使對方修正曾有認識。以《柏拉圖對話錄》中的名篇“游敘弗倫”為例,蘇格拉底與游敘弗倫就何謂“敬神”或“虔誠”之德展開了辯論。兩人在王宮前廊相遇。當時,蘇格拉底正頂著兩項指控——“不敬城邦所供之神”和“蠱惑青年質疑權威”待受審判,游敘弗倫則是打著“敬城邦之神”和“對城邦之神虔誠”之名前來控告父親過失殺人。事情原委是:他家一個雇工在外做工時,醉酒之下,與他家一個奴隸發生沖突,結果將其致死。游敘弗倫的父親命人將雇工綁了,投入溝中,同時差人去雅典神廟請教神巫,聽取處置。沒想到,這個雇工未能等到使者返回,連冷帶餓死去。
游敘弗倫是當時公認的宗教家和預言家,自認對神“虔誠”,哪怕是父親犯罪,也要嚴格遵照神律治罪。他前來告發父親,以示對雅典之神的敬奉。此時正戴“不虔誠”之罪的蘇格拉底,連忙抓住這個機會,向自認最懂虔誠的游敘弗倫討教“何為虔誠”。游敘弗倫得意地說,父親過失殺人,自己大義滅親就是忠誠于城邦之神、履行“虔敬”這一美德。蘇格拉底指出,這只是舉例,要求他給“虔敬”下個定義。游敘弗倫回道,“做神所喜之事就是虔敬”。對此,蘇格拉底提出三點反駁:其一,這又是舉例,并非定義;其二,希臘諸神是非、善惡標準不一,此神所喜可能是彼神所惡;其三,并非所有神一致認為,其父有罪。
游敘弗倫做了一下思考,于是給出第二個定義:做所有神喜愛之事就是虔敬,做所有神厭惡之事就是不虔敬。蘇格拉底首先指出其邏輯混亂,稱“虔誠”與“做神喜之事”并非一回事,繼而發問:“虔誠是否因其為虔誠而見喜于神,或者因見喜于神而為虔誠?”這話是問,人履行“虔誠”,是因為行事本身符合美德,做了會讓神喜悅,還是因為只要做到了讓神喜悅滿意,就等于做到了“虔誠”?接著問他:你來告發父親,是因為此事本身是內心之德所驅,還是為了讓神歡喜滿意才出此舉?需要指出的是,蘇格拉底這一問把對神話宗教的探討轉向對人倫道德的探討,具有重大轉折意義。
游敘弗倫在蘇格拉底的詰問之下,給出了另一定義:“虔敬就是對待神的那部分正義”。蘇格拉底追問何為“對神正義”,然后,從其回答中邏輯導出“對神正義就是給神供奉”,進而又根據游敘弗倫的辯白,順理成章地推出“虔敬就是給神靈好處”這一結論。蘇格拉底據此指出,如果像游敘弗倫所說,對神靈祭司祈禱,做神滿意之事,方可得到神之護佑,而不侍奉神,不做神喜之事,神就懲罰,那么,虔誠的定義就成了“神跟人交易的技術”。蘇格拉底接著追問,如果人與神在這場交易中盡占便宜,得到好處,而神靈從人這里卻一無所得,神做這種交易又有何圖?游敘弗倫于是回答,神只珍視人之崇敬、贊美和感恩,不求回報。就此,蘇格拉底推出,行“虔誠”似乎又成了做“神所視為珍貴者”。這樣一來,虔誠又與神之所喜畫上等號,回到了辯論起點。辯論至此,游敘弗倫詞盡理窮,蘇格拉底就此提出,既然你自己都不知什么是虔誠,那就沒有理由認為,控告家父過失害死一個殺人犯乃是“虔誠”之為。于是,游敘弗倫打消了告發父親的念頭,借故離去。
這種辯而無果的對話在《柏拉圖對話錄》中還有很多。每次辯論對話,蘇格拉底都試圖通過推論、質詢、辯駁、引導,讓對方最終認識到自己先前對美德的理解存在問題,促使對方重新思考何為真正的做人美德。需要指出的是,每次對話最后,蘇格拉底都未對“所論美德”給出一個“正確”定義,這是因為,在他看來,美德乃為神所賦,不能用理性知解,無法用言語說教。用他自己的話說,“品德不是可以傳授的,卻是由于神授而具有的,人們受賜而不自知”[10]206。既然美德內在于人,那么人無需求教外在神靈,只需聽從內心神啟就能分辨是非曲直。正如他在法庭向審判官所言,“我遇一件靈異的事。經常降臨的神的意旨以往每對我警告,甚至極小的事如不應做,都要阻止我做”[10]78。這種“聽神啟、知對錯”的說法,與儒家心學創始人王陽明所提出的“致良知、明是非”之論一致。
蘇格拉底所說的人人皆有而不自知的“內在之神”,也類似于康德所說的屬于“先驗理念”范疇的“實踐理性”[5]29,相當于勞倫斯所說的內居于人的“靈魂良知”。勞倫斯認為,一個人行事,有時候會聽從抽象理念、傳統教義、內心沖動。這很正常,不過,如果僅是聽從這些,而無視天賦良知的召喚,那就背離本真,毀了自己。他說,“每個人必須盡其所能地聽從自己靈魂的良知,不要聽從任何抽象理念。如果讓良知服從于一個教義、一個思想、一個傳統,甚至一個沖動,我們就毀了。……我們在某些時候固然必須依從理念、沖動和傳統行事,但是只有純潔的良知才堪為真正的指南”[11]98。“只有純潔的良知才堪為真正的指南”是說,“良知”乃是生命本源所賦,內在于身;人聽從良知,就是依循天性,活出真在;假如把機械思想、功利觀念奉為指南,則會損害天性,失去做人根本。同樣,蘇格拉底也講,人應聽從“內心神令”,不要唯“所立外神”是從。蘇格拉底不同于勞倫斯的是,他不著述立言,未曾明確說明他所遵從之“神”來自哪里,而勞倫斯卻做了具體闡釋:“良知”乃是“生命本源(the Source)”[11]54所賦,隨著卵子受精之時便進駐身體,驅動身體活動。這個寓居身體并驅動身體的生命本源,勞倫斯稱為“宇宙上帝(a Cosmic God)”[12]41“圣靈”[11]98“生命-沖動(life-urge)”[13]256等等。生命本源創造每個生命,也驅動每個生命。所驅之力,就是“天之所令”,與“良知”同義。聽從天之驅令,就是聽從內在良知,實踐天賦美德。
至此可以看出,蘇格拉底的“奉神啟”與勞倫斯的“良知論”有所會通。兩者都認為,每個人都身賦良知或天令,因此最應服從良知或天令,而非某個陳腐價值、外在神靈;兩者都探尋人生意義,都把實踐天賦美德視為人之最大成功;兩者都認識到,理性思維不能把握良知或天令,只有直覺得之。
三、蘇格拉底和勞倫斯對于理性的共同質疑
蘇格拉底鼓動年輕人質疑頭腦所受道德,帶頭拒奉眾立之邦神,將道德概念的定義權交給自己內心之神[14]16,表示只聽從內在神啟召喚。他因此引起了當權者的不滿、眾公民的不解,被定以“蠱惑眾青年、不敬城邦神”之罪。給他定罪的是當時代表雅典民主、民智的五百人大會,其中一半以上成員裁定蘇格拉底死罪。面對眾人的無理裁定,蘇格拉底進行了辯白,無效之后,坦然接受死亡。他清醒地認識到,很多人,包括這些給他定罪的公民精英,自以為掌握真理和話語權,自以為憑借理性就能把握真理,而實際上得到的只是影子,因此可憐他們。他把受限于理性認知、卻自以為有知之眾人喻為被鎖在暗黑洞穴、不能動身轉頭、看不到真實世界的可憐“囚徒”。這一思想在《柏拉圖對話錄》中有所表述。對話在蘇格拉底與克勞孔之間進行:
蘇格拉底 讓我用一個形象來說明人的本性開通或不開通的程度:——看吧! 人類生活在地洞里,這個地洞有一個口朝向光亮,日光自洞口而入;人們自幼生活在這里,他們的腿和脖子被鎖鏈拴著,不能移動,只能看見前面的東西,無法轉頭后顧。他們的后上方有一堆火,遠遠地發出光亮。在火堆與囚徒之間有一隆起的道;你(克勞孔)如果看的話,會見到在長長的路上建起的矮墻,像是一個屏幕,木偶在它前面表演,影子映在它的上面。
克勞孔 我仿佛看見了。
……
我說,對于他們而言,真理不過是影像而已。
肯定是這樣[10]2-3。
蘇格拉底“洞穴”之喻試圖說明,人之理性和視覺不能把握世界本質,只能看到局部和表面。局限于視覺和理性之人好比背對光線的囚徒,只能看到前面暗墻之上的射影,而射影只是“影像”,而非真相。接下來,蘇格拉底設想,如果一些“囚徒”得以釋放,能夠轉身,看到后面場景,或者走出洞外,看到外面世界,一開始肯定眩暈,覺得此時所見之物反不如過去在洞中所見其影像清楚。接著,蘇格拉底再設想,如果某個囚徒被強拉到高處,逐漸習慣日光,就能看到自己的水中倒影和自己的真實模樣,進而思考自己本身和周圍宇宙。當他回想起過去的洞穴以及在洞穴中的獄友,一定會慶幸自己走了出來[10]4-5。蘇格拉底的“洞穴之寓”意在說明,人之眼睛所見、頭腦所思,不僅只是影像,而且也體悟不到內心之神的召喚。
蘇格拉底對理性和視覺表示懷疑,是因為兩者把握不到真相,聆聽不到內心的“神啟”,勞倫斯懷疑兩者,則是因為兩者讓人失去了生命一體的美好狀態,聆聽不到“宇宙上帝”或“純潔良知”。勞倫斯對理性至上、壓制直覺的批判追溯到人類始祖那里。在他看來,人類始祖亞當和夏娃在吃代表“理性知識”的“蘋果”之前,是處于無思無知的直覺之態,彼此交流是通過“血液——知識”[15]348-349(直覺)。這個時候,他們與其它萬物處于“物我無分的狀態”。而他們吃了這種“智慧之果”,就有了視覺認知和理性思維。有了這些,便開始用眼睛、頭腦看待自己、他人、萬物,于是有了你我之分、無我之別的主客兩分意識。人類發展到現代,更是推崇理性至上,“過于強調……思智和意識,否定、蔑視……感官和感覺”[16]36。
理性宰制直覺,讓人失去生命一體的狀態,也讓人聽不到良知的呼喚。當人聽不到自己的良知所喚,就可能依循社會功利或抽象理念規范自身。在勞倫斯看來,這樣成長起來的人是被“標貼畫(pictures)”建構之人[17]509。這些根據“標貼畫”塑造出來的觀念之人背離了天賦之令,失去了本然自我,成了影子,也只能看到事物的影子,如勞倫斯所言,“我們所知道的都是影子,……。一切都是影子,整個世界以及我們自身皆是影子”[17]569-570。
需要強調的是,勞倫斯和蘇格拉底對視覺和理性的局限看法一致,但是對“洞穴”之“幽暗”的闡釋不同。蘇格拉底用“幽暗洞穴”比作禁錮人們視野和認知的“監獄”[9]5,而勞倫斯則把“地穴”之“幽暗”與身體血液之幽暗或者說直覺之感連在一起。他引用父輩地下采礦的經歷說明,地下“暗井”既有利于保養人的直覺本能,還能促使人與他人建立生動接觸:
地下礦坑的幽暗、深邃以及隨時出現的危險使得人們身體、本能、直覺的觸感高度發達。這種觸碰非常真切、強大,在地下煤坑達到最強程度。這些男人一到地面,見到日光,便會眨眼,不得不調節一下身體的同時,也把煤礦里那種奇妙的、幽暗的親密感,即那種赤身觸碰隨身帶到了地上。在我的童年記憶中珍藏著一種光亮,它內黑外亮,猶如煤塊閃耀著光澤。在這種幽暗卻閃亮的地方,我們活動著,擁有了我們真實的存在。我的父親很愛煤坑。他雖然不止一次地受過傷,卻從未離開,因為他愛那種人與人的身體接觸而生的親密之感[16]117。
對于勞倫斯來說,其父輩直覺發達,富有活力,是因為長期處于“地下暗處”,少有“地上理性之光的侵擾”。勞倫斯非常欣賞父輩有著敏銳之身,覺得他們擁有真實存在,具有“特別的美感”:“我小的時候,普通礦工有一種特別的美感,這種美感來自直覺和本能意識,這直覺和本能意識又是在礦下喚醒的”[16]119。勞倫斯歌頌“暗黑”,因為人越是處于暗處,越少動用理性和眼睛,身體直覺就越敏銳,直覺敏銳,才能與他人萬物生動一體。勞倫斯歌頌“暗黑”,還因為不可見、不可知的生命本源是“暗黑”的。他稱生命本源為“黑夜之波”,把對“黑夜之波”的追隨視為“歸于母體”:“我體內的日光波追逐黑夜之波,黑夜之波是日光波的源始,是萬能的創造者。從黑暗之波那里,人的種子之光就開始升騰,期望進入無限的黑暗之界——即蘊育萬物的母體”[18]377。這“蘊育萬物的母體”便是不可道、不可見的生命本源。生命本源賦予人以良知。本源和良知不能通過理性知解,只能通過直覺感知。可以說,勞倫斯重視直覺,表示聽從良知,是因為良知是本源所賦,只有聽從良知,才能做到忠實天性,體悟宇宙一體,與他人萬物建立生動聯系;蘇格拉底重視直覺,表示聽從神令,則是因為只有直覺才能領悟神示,讓人明辨是非,踐行美德。
四、結論
總之,對于勞倫斯和蘇格拉底來說,人之最大價值不是體現于世俗名利的成功、對自然的征服,而是保有敏銳直覺,順應天之所令,踐行做人之德,活出人生意義。一個人如果只信理性和視覺,無視直覺而發的自然感知,就把握不到真實,也聽不到“良知”或“神啟”叫門。遺憾的是,勞倫斯不曾看到,蘇格拉底也很推崇直覺;他也不曾認識到,蘇格拉底的“奉神啟”與自己的“致良知”非常接近。應該說,勞倫斯未加探究蘇格拉底這些思想,便批評他崇尚理性,與亞里士多德、黑格爾、尼采等前人大力強調蘇格拉底的理性論辯、忽視其倫理思想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