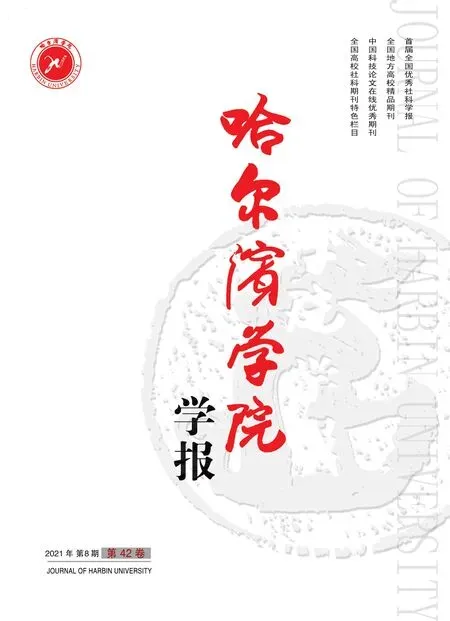淺析辛棄疾祝壽詞形成動因
呂 盛
(滁州城市職業學院,安徽 滁州 239000)
辛棄疾是南宋時期著名的豪放派詞人,他的詞作風格豪邁、沉郁頓挫,充滿了殺敵報國、收復河山的家國情懷,陳廷焯在《白雨齋詞話》中評價辛棄疾為:“詞中之龍也,氣魄極雄大,意境卻極沉郁。”辛棄疾一生創作的詞達六百多首,數量為宋代詞人之冠。他的詞風格多樣,題材廣泛,其中不乏一些祝壽詞,據多慶教授統計,約有44首,約占辛棄疾創作的詞的總量的7%,[1]這成為南宋詞壇一道亮麗的景觀,這一景觀引起了很多學者的注意,并開始進行相關研究。李晉棠、陳北祥兩位學者從思想內容上進行了評析,認為其祝壽詞思想內容主要借助祝壽之題來抒發其愛國之情和功名思想,并從辛棄疾的生平經歷和思想以及交友等方面分析了其祝壽詞思想內容形成的原因;多慶教授從祝壽詞發展的歷史著手,對辛棄疾的祝壽詞進行了分類,認為可以分為“自壽”“壽一般人”“壽親戚”“壽上司僚屬”四類,并把研究視角重點放在了“壽上司僚屬”這一類中,通過這類祝壽詞的分析來研究辛棄疾的愛國主義思想;廣西師范大學顧寶林從風格、主題兩個角度進行研究,認為辛棄疾的祝壽詞對傳統祝壽詞有所開拓,大氣磅礴,具有很高的美學風范,是其他詞家無法超越的;臺州學院閆笑非教授結合辛棄疾的生平分析其祝壽詞的思想內容,認為其祝壽詞表達了作者深深的愛國之情以及對朋友的勉勵和祝愿,同時,閆教授把研究視角也放在了辛棄疾祝壽詞的藝術風格上,認為辛棄疾的祝壽詞不落俗套,寫法富于變化,議論精辟,用典恰當等,具有很高的文學藝術價值。還有很多學者,如:李冰心、陽淑華、王倩等都對辛棄疾的祝壽詞進行了研究。通過對以上學者研究成果的梳理和分析,發現他們研究的范圍和思路基本都是圍繞辛棄疾祝壽詞的思想內容、主題、分類和藝術價值進行研究的,對辛棄疾祝壽詞形成的動因雖有涉及,但并沒有做深入、系統地探索和研究。因此,把辛棄疾創作祝壽詞這一行為放在宋代經濟文化背景下及詞體發展史中進行考察,有一定的必要。本文在以上學者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將研究視角放在辛棄疾祝壽詞形成動因上,在肯定其思想內涵和藝術價值的前提下,結合宋代經濟文化背景以及詞體發展史來考察辛棄疾祝壽詞形成的動因以及祝壽詞的特質和得失,并認為辛棄疾祝壽詞的內容和風格與他的其他抒發愛國主義激情的詞作并沒有本質上的區別,只是宋代的經濟和文化氛圍以及詞體發展推動著辛棄疾選擇祝壽詞來表現愛國主義思想。
一、辛棄疾祝壽詞形成動因分析
縱觀詞體發展歷史流程,發現在唐代和五代十國時期,祝壽活動并未入詞,詞在發展之初,題材狹窄,大多抒發男女情愛之思和離愁別恨之緒,到了北宋時期,隨著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詞的題材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更加開闊,一些文人開始把祝壽活動融入到詞體創作,祝壽詞開始興起。如果說,北宋時期,國家富強統一,市民文化逐漸興起,生日風俗開始流行各階層,祝壽詞才得以大量產生和繁榮。但到了南宋時期,國家四分五裂,外族不斷入侵,辛棄疾作為愛國人士,憂國憂民,為何還會有大量祝壽詞的產生并且形成自己獨特的藝術風格?
(一)南宋經濟的繁榮與城鎮化發展是辛棄疾祝壽詞形成的時代背景
辛棄疾“歸正”后,他的仕途主要集中在江南地區,南宋時期的江南,由于長江的地理位置,江南的城鎮遠離戰火,社會經濟發展比較繁榮,再加上南宋都城遷至杭州,原有的城鎮規模得到改造和擴大,大量的新城鎮也不斷興起。經濟的發展體現在城市化發展中,以當時的南宋文人耐得翁的《都城紀勝·序》為例:“圣朝祖宗開國就都于汴,而風俗典禮四方仰之為師。自高宗皇帝駐蹕于杭,而杭山水明秀,民物康阜,視京師其過十倍矣。雖市肆與京師相侔,然中興已百余年,列圣相承,太平日久,前后經營至矣,輻輳集矣,其與中興時又過十數倍也。……況中興行都,東南之盛,為今日四方之標準;車書混一,人物繁盛,風俗繩厚,市井駢集,豈昔日洛陽名園之比?”[2](P89)如果僅以江南地區而論,南宋時期的經濟發展水平遠超北宋時期,“民物康阜,視京師其過十倍矣”,“市肆與京師相侔……又過十數倍也”,雖有夸張之嫌,仍可作為佐證。再以南宋著名文士周密的《武林舊事·序》為例,文中記載,“乾道、淳熙間,三朝授受,兩宮奉親,古昔所無。一時聲名文物之盛,號‘小元祐’。豐亨豫大,至寶祐、景定,則幾于政(和)、宣(和)矣。”[3](P329)由文中可知,南宋乾道、淳熙年間的經濟發展已經達到北宋政和、宣和年間水平,“豐亨豫大”當是真實寫照。
對于南宋經濟發展水平,很多宋史學者也給予了非常高的評價。宋史專家漆俠先生曾做出論斷:“在兩宋統治的三百年中,我國經濟文化的發展,居于世界的最前列,是當時最為先進、最為文明的國家。”[4](P2)北京師范大學“985”特聘教授、中國宋史研究會原副會長葛金芳認為:“南宋時期我國從中古農業社會跨入了近世農商社會階段。此時商業經濟活動的規模和范圍日漸擴大,其對國民經濟、居民生活甚至政府財政的作用,已經到了一日不可或缺的程度。”[5]
南宋經濟的發展促進了城鎮的興起,尤其是兩淮江南市鎮的興起,城鎮化進程不斷加速發展,市民文化生活不斷豐富,生日作為一種重要的節日與南宋經濟的發展和城鎮化的進程密不可分。到了南宋時期,生日風俗不僅流行于市井,文人士大夫也開始普遍接受生日慶生祝壽這一風俗活動,“生日嘏詞,南宋人集中皆有”。[6](P1816)生日習俗是市民文化生活的一部分,南宋經濟社會的發展促進了文化活動的發展,為南宋人的生日風俗提供了基本的物質條件。盡管到了北宋末年,連年的戰亂,疆域的縮小,人口銳減,賦稅加重,使得經濟社會發展緩慢,但南宋人民生日慶壽的習俗已然形成,并不影響南宋人民生日風俗的流行,尤其影響不到士大夫慶生的流行。整理辛棄疾的祝壽詞發現,其祝壽詞出現在1168—1202年,集中出現在1172—1187年,這一時期,南宋經濟并沒有出現緩慢和停滯,而是呈現了繁榮發展勢頭。辛棄疾祝壽詞的形成與南宋時期的經濟發展密不可分,經濟繁榮發展決定了生日風俗發展的程度和流行范圍,生日風俗的流行往往又影響著祝壽詞的主題、思想感情、創作風格和感情基調。
(二)個人經濟狀況是辛棄疾祝壽詞以及為別人慶生的物質保障
很多學者早已關注辛棄疾的經濟問題,并有很多的研究成果,例如:吳世昌先生的《辛棄疾作傳》時提到辛棄疾經濟生活的寬裕。[7](P296-297)還有些學者為此發生了爭論,例如,20世紀八九十年代,羅忼烈、鄧廣銘先生曾經就辛棄疾的經濟狀況撰文論爭,[8]論爭的焦點主要集中在辛棄疾的收入是不是豪奢,是不是合法。但有一點毋庸置疑,那就是辛棄疾的經濟生活還是比較寬裕富足的。辛棄疾的收入主要是俸祿收入,還有放任外官時的職田、固定的公使錢,以及皇帝的賞賜等。辛棄疾經濟收入來源廣,數量比較多,盡管在歸正前的收入無可考證,但在歸正后,其做過很多次六品以上的官員,在乾道八年春出知滁州,在任兩周年,從紹熙三年春到紹熙五年又任福建提刑,攝福建帥事,遷太府卿,任福州守兼福建帥,于嘉泰三年夏起知紹興府兼浙東帥,四年春改知鎮江府,翌年六月知隆興府兼江西帥(未到任即被罷免)。
辛棄疾富裕充足的經濟生活影響到他的生活方式和創作風格,劉學和葉燁兩位學者曾考證了辛棄疾的經濟收入以及經濟生活與詞創作之間的關系,認為辛棄疾良好的經濟狀況影響到其生活方式,使其廣交游、多宴飲,從而催生了詞創作活動,導致其偏好詞體,具有尊體意識。[9]參與壽宴為別人慶生是辛棄疾交游與宴飲生活的一部分,他的很多祝壽詞描寫了壽宴時奢侈的細節以及人物的穿戴,如《虞美人·趙文鼎生日》:
翠屏羅幕遮前后。舞袖翻長壽。紫髯冠佩御爐香。看取明年歸奉、萬年觴。/今宵池上蟠桃席。咫尺長安日。寶煙飛焰萬花濃。試看中間白鶴、駕仙風。
“翠屏羅幕遮前后”是寫宴會的環境,“舞袖翻長壽”說明宴會還有歌女相伴,“寶煙飛焰萬花濃”體現壽宴熱鬧歡愉的場面。參與這樣高級別的壽宴,除了基于辛棄疾士人的身份以及與趙文鼎的關系外,也間接反映了辛棄疾有一定的經濟基礎,說明了他的經濟生活對他的祝壽詞產生了一定的影響。當然,像這樣高級別的壽宴,辛棄疾參加的不止一次,還可以通過其他祝壽詞得以體現,如《西江月·為范南伯壽》:
秀骨青松不老,新詞玉佩相磨。靈槎準擬泛銀河。剩摘天星幾個。/奠枕樓頭風月,駐春亭上笙歌。留君一醉意如何。金印明年斗大。
再如《西江月·壽祐之弟》:
畫棟新垂簾幕,華燈未放笙歌。一杯瀲滟泛金波,先向太夫人賀。/富貴吾應自有,功名不用渠多。只將綠鬢抵羲娥。金印須教斗大。
以上兩首從壽宴的美酒、笙歌、住所、壽宴場景這樣具體的物象來渲染壽宴的氣氛。這樣的壽宴都反映了辛棄疾有一定的物質基礎,他的祝壽詞也正是在這個物質基礎上形成的。概括起來,辛棄疾的經濟基礎為其交游和參加宴飲提供了物質基礎,交游和宴飲又促進了祝壽詞的產生。
(三)宋型文化背景為辛棄疾創作祝壽詞提供了實踐舞臺
如前文所述,盡管南宋戰亂不斷,疆域縮小,偏安一隅,但南宋商業經濟發達,城鎮化發展不斷加速,市民生活豐富多樣,并且財富大多集中在統治階級手中,南宋士大夫階層整日沉迷于歌舞升平之中,不圖收復失地,戰爭并沒有使他們的宴飲活動減少,反而“中興”無望,促使他們“借酒消愁”,不斷宴飲,上到皇親貴族和官僚大臣,下至市民百姓。當時的社會文化氛圍是“舉世重交游”,酬唱宴飲成了人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尤其是士大夫階層的宴飲往往伴有歌妓侍宴、賦詞酬唱等娛樂活動,這些娛樂活動鼓勵和促進了詞作的流行和傳播,推動了詞體的演變發展,尤其是生日習俗在南宋非常流行,祝壽詞也就是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中產生的。宋代重交游、喜酬唱的文化風俗氛圍深深地影響著辛棄疾詞體創作的內容選擇、風格、范圍和數量。辛棄疾歷任外放官職,均在六品以上,他是南宋士大夫的代表和縮影,置身于這樣的宴樂之風中,他的祝壽詞的出現也就顯得順其自然,參與壽宴為其祝壽詞的創作提供了契機和實踐舞臺。另外,辛棄疾作為歸正人,他的身份在南宋官場非常尷尬,他雖然為“齊之歷城人”,[10](卷四零一)但他內心深處無不充滿著收復失地、恢復中原、報國雪恥的遠大理想和抱負,他以五十騎勇闖五萬金兵大營斬殺叛徒張安國的壯舉使他“懦士為之興起,圣天子一見而三嘆息”,但南宋統治者和官僚階層對他還是不信任,他經常承受著來自朝野上下的身份歧視,為了消除這種歧視,他就需要經常參加南宋官僚階層的宴飲活動,融入他們的生活,并且在宴飲的舞臺之上表明自己的心跡以及內心的憂慮和遠大抱負,在為上司和同僚祝壽的場合把自己的心境體現在祝壽詞作之中,更多時候,他只是借助祝壽的舞臺把自己的愛國之情和收復失地的抱負以及壯志未酬的情緒表露出來,現以他的祝壽詞《水龍吟·甲辰歲壽韓南澗尚書》為例:
渡江天馬南來,幾人真是經綸手?長安父老,新亭風景,可憐依舊。夷甫諸人,神州沉陸,幾曾回首!算平戎萬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公知否?況有文章山斗,對桐陰、滿庭清晝。當年墮地,而今試看,風云奔走。綠野風煙,平泉林木,東山歌酒。待他年,整頓乾坤事了,為先生壽。[11](P148)
這首詞是辛棄疾寓居上饒時為韓元吉六十七歲生日而作,全詞也只有從詞尾“為先生壽”看出祝壽,更多的是其慷慨激昂的議論和深沉的憂國之情以及過人的見識,不落窠臼,立意迥然。他的這種見識和胸懷正是借助祝壽這樣的舞臺表現出來的,正如辛棄疾的弟子范開在《稼軒詞序》中評論到:“辛棄疾非有意于歌詞,乃是因以‘一世之豪’而不為世所用,便以詞作為‘陶寫之具’”。
辛棄疾祝壽詞的對象很多都是和他自己一樣滿懷抱負的豪杰之士,他們也是一心為國為民,希望能夠收復失地,恢復中原,為國家貢獻自己的力量,如《千秋歲·為金陵史致道留守壽》:
塞垣秋草,又報平安好。尊俎上,英雄表。金湯生氣象,珠玉霏譚笑。春近也,梅花得似人難老。/莫惜金尊倒。鳳詔看看到。留不住,江東小。從容帷幄去,整頓乾坤了。千百歲,從今盡是中書考。
此詞當作于宋孝宗乾道五年(1169年)十二月辛棄疾建康通判任上,為時任建康留守、建康知府兼沿江水軍制置使的史致道祝壽。史致道,名正志,江蘇揚州人,史致道胸有韜略,經常與辛棄疾探討富國強民、恢復中原的大計,曾上《恢復要覽》五篇,提出“無事都錢塘,有事幸建康”策略。辛棄疾對他尊敬有加。這首祝壽詞與其說是贊揚壽星的事功,倒不如可以看做辛棄疾借助慶壽宴飲這個舞臺,來寄托自己的愛國情思。
(四)詞體的屬性和功能是辛棄疾祝壽詞形成的必然
詞始于南梁,形成于唐代,是配合宴樂樂曲而填寫的,最初,題材狹窄,內容多反映情愛相思,風格多綺麗婉約,它的娛樂性和消遣性的功能得到充分發揮,“清絕之辭”“助妖嬈之態”“資羽蓋之歡”(歐陽炯《花間集序孰》),“娛賓遣興”(陳世修:《陽春集序》),“聊佐清歡”(歐陽《采桑子小引)正是詞所具有的娛樂性和功能性的體現,這個時候祝壽詞出現的比較少,在詞體發展史上,蘇軾是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一位詞人,他打破了詩詞的界限,擴大了詞的表現內容,這個時候壽詞開始多了起來。到了南宋時期,隨著詞的題材日益的擴展,寫景詠物、吊古傷懷、酬唱應和、節日宴飲均可入詞,其與現實生活日益緊密聯系,詞的交際、娛樂和抒情的功能越得到充分的發揮,隨著詞體的發展和解放,祝壽詞也開始表現更宏大的社會主題,辛棄疾也開始借用祝壽詞進行情感宣泄,開始通過祝壽詞來抒發自己壯志難酬的憤懣、對朋友們的勸勉以及對國事的擔憂。
宋代,政治上,統治者重文抑武;經濟上,城市商業經濟不斷發展;社會生活上,人民宴飲交游不斷。尤其是士大夫階層,他們的宴飲和交游活動需要詞這種當時比較流行的文學樣式表現出來,詞的交際功能得到充分發揮,社交詞在宋代得到了很大的發展,正如王水照先生所說,“詞從一開始產生就是應用文學,只不過是自然形態的應用文學而已。”[12](P433)詞作為宋代流行的一種文學體裁,在文恬武嬉、宴飲歡歌的社會文化氛圍之中,發揮著交際、娛樂和抒情的功能,這種功能在祝頌的交游活動中促進和推動了祝壽詞的出現。
辛棄疾作為南宋的士大夫,被稱為詞中之龍,交游甚廣,他的祝壽詞對象有親戚家人,但更多的是他的同僚和上司,他用詞作來與南宋的士大夫們互相酬唱和應和,充分利用和發揮著詞的交際娛樂和抒情的功能,以抗金報國的愛國之情與壯志難酬的悲憤之感融入祝壽詞,擴寬了以往祝壽詞的題材范圍,可謂是推陳出新,提升了祝壽詞的格調和文學地位。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他與南宋愛國詞人韓元吉的交往,據統計,他與韓元吉有十一首和詞,[13]還曾互寫祝壽詞,通過祝壽詞表現相惜相知之情與互相勉勵,如前文所述的《水龍吟·甲辰歲壽韓南澗尚書》就是其祝壽詞中的名篇;韓元吉也曾為辛棄疾祝壽并有《水龍吟·壽辛侍郎》:
南風五月江波,使君莫袖平戎手。燕然未勒,渡滬聲在,宸衷懷舊。臥占湖山,樓橫百尺,詩成千首。正草蒲葉老,芙蓉香嫩,高門瑞,人知否。涼夜光躔牛斗。夢初回、長庚如晝。明年看取,鋒旗南下,六騾西走。功畫凌煙,萬釘寶帶,百壺清酒。便留公剩馥,蟠桃分我,作歸來壽。(仆賤生后一日也,故有分我蟠桃之戲。)
詞的屬性和功能決定詞是辛棄疾在交游和酬唱中娛賓遣興的最好工具,當然,也成為了南宋時期士大夫們在祝壽場合中的首選。[13]
二、辛棄疾祝壽詞的特質及得失
在宋代“舉世重交游”的社會文化氛圍中,辛棄疾的祝壽詞難免會有些阿諛奉承、歌功頌德、互標風雅之作,充滿了功名思想以及歌頌長生不老、富貴安康的祝頌,這類詞作的形成既有文化風俗的原因,也有詞體功能的原因,詞本來就是一種應用文體,在生日慶壽的喜慶節日里,用詞來歌功頌德、祝福富貴安康也未為不可,畢竟辛棄疾是南宋士大夫的一員,他身上難免會打上時代的烙印,受社會文化風俗和詞體功能的局限,一些應和他人的祝壽詞篇就應世而出了,但難能可貴的是,辛棄疾能夠根據祝頌的對象創作出不同風格的祝壽篇章,在志趣相投的朋友以及上司和同僚的祝壽詞中,辛棄疾常借祝壽之機以抒壯懷,以明心志,表達自己強烈的建功立業、收復河山的壯志情懷,詞作充滿了厚重的歷史感和使命感以及不可磨滅的愛國情懷,與南宋時期其他單純的應酬唱和的庸俗祝壽詞相比,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藝術風格,對后世祝壽詞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但辛棄疾這類祝壽詞與自己其他愛國主義詞作在內容和風格上,并沒有本質上的區別,如與《水龍吟·登健康賞心亭》《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等比較,內容上和祝壽詞一樣,都是抒發愛國主義思想,只不過,這類登高抒懷詞是借登高懷古表達自我,而祝壽詞是借祝壽活動表達自我。再與其贈別詞相比較,如《滿江紅·送李正提刑之入蜀》《水調歌頭·送揚民瞻》《賀新郎·別茂嘉十二弟》等,辛棄疾贈別詞是借贈別之機來抒發自己的愛國主義思想和壯志難酬的郁郁不平之氣,這在內容上和其祝壽詞并無本質區別,還有其農村詞等,在此,不再一一列舉。總之,在南宋經濟文化發展的背景下,受詞體發展和功能的局限,辛棄疾祝壽詞雖有應酬之作,但更多的是創作出了大量與其登高、贈別詞一樣的具有濃郁愛國主義情節的祝壽詞,在南宋詞壇獨樹一幟,影響深遠。他通過祝壽詞來抒發自己的愛國主義思想以及壯志難酬的憤懣,風格上沉郁頓挫,其祝壽詞與其他愛國主義詞作在內容上和風格上無異,只是詞體的發展和宋代社會文化風氣推動著辛棄疾選擇祝壽詞來抒發自己的主體情感和志向抱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