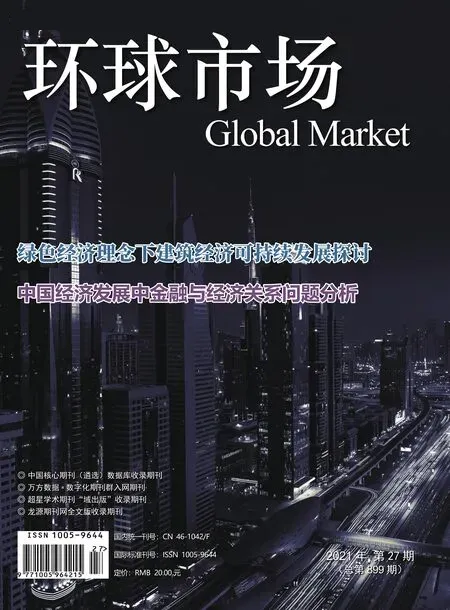中國(guó)系統(tǒng)性金融風(fēng)險(xiǎn)度量研究綜述
張翼 西南財(cái)經(jīng)大學(xué)天府學(xué)院
一般認(rèn)為,金融危機(jī)是系統(tǒng)性金融風(fēng)險(xiǎn)累積到一定階段的產(chǎn)物,是系統(tǒng)性金融風(fēng)險(xiǎn)的特殊時(shí)期。然而,在2008年金融危機(jī)后,系統(tǒng)性金融風(fēng)險(xiǎn)才真正進(jìn)入決策者的視野,研究熱度驟升,各國(guó)紛紛將對(duì)其的防范作為重要政策目標(biāo)。正如習(xí)近平總書記所說,防范系統(tǒng)性金融風(fēng)險(xiǎn)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題。
一、概念
系統(tǒng)風(fēng)險(xiǎn)systematic risk是指由于政治、經(jīng)濟(jì)及社會(huì)環(huán)境等公司外部因素的不確定性而產(chǎn)生的風(fēng)險(xiǎn),其特點(diǎn)是由綜合因素導(dǎo)致的,而這些因素對(duì)于投資者而言,是不能通過多樣化投資予以分散的。因此,系統(tǒng)風(fēng)險(xiǎn)也叫作不可分散風(fēng)險(xiǎn)。而本文的主要研究對(duì)象系統(tǒng)性金融風(fēng)險(xiǎn)systemic risk,或稱系統(tǒng)性風(fēng)險(xiǎn),雖然與系統(tǒng)風(fēng)險(xiǎn)名字相似,在過去很長(zhǎng)一段時(shí)間內(nèi)也經(jīng)常混淆,但兩者在本質(zhì)上是存在差距的。
由于系統(tǒng)性金融風(fēng)險(xiǎn)受到廣泛關(guān)注的時(shí)間并不長(zhǎng),目前來說,人們對(duì)于其定義尚未達(dá)成廣泛共識(shí)。但得到普遍認(rèn)可的是,系統(tǒng)性金融風(fēng)險(xiǎn)存在突發(fā)性、危害大、波及廣、傳播快等特點(diǎn)[1]。因此,筆者嘗試定義系統(tǒng)性金融風(fēng)險(xiǎn)為:“突發(fā)事件的沖擊導(dǎo)致金融體系嚴(yán)重受損、金融功能喪失的可能性。”[2]
二、成因
系統(tǒng)性金融風(fēng)險(xiǎn)并不是由單個(gè)原因?qū)е碌模嵌喾矫嬉蛩毓餐饔玫慕Y(jié)果。概括而言,它的出現(xiàn)不僅受到外部因素的促進(jìn)作用,也有金融機(jī)構(gòu)自身存在問題,即內(nèi)部因素的影響。
從外部來說,宏觀經(jīng)濟(jì)因素的沖擊、不恰當(dāng)?shù)暮暧^調(diào)控、監(jiān)管不足、市場(chǎng)主體的非理性行為等因素都對(duì)系統(tǒng)性金融風(fēng)險(xiǎn)起到了促進(jìn)作用。[3]
宏觀經(jīng)濟(jì)因素的沖擊:宏觀經(jīng)濟(jì)周期可簡(jiǎn)單概括為復(fù)蘇、繁榮、衰退、蕭條四個(gè)階段,當(dāng)經(jīng)濟(jì)由盛轉(zhuǎn)衰,危機(jī)也就隨之出現(xiàn)。而經(jīng)濟(jì)危機(jī)的出現(xiàn)往往伴隨著金融危機(jī)的爆發(fā),當(dāng)經(jīng)濟(jì)下行,借款人財(cái)務(wù)情況惡化,還款能力變差,信用風(fēng)險(xiǎn)增加,金融機(jī)構(gòu)壞賬增多,資產(chǎn)質(zhì)量下降;同時(shí),受到經(jīng)濟(jì)大環(huán)境影響,出借人信心不足,迫切想要收回資金,極有可能引發(fā)擠兌,最終導(dǎo)致金融體系崩潰,金融市場(chǎng)功能喪失。
不恰當(dāng)?shù)暮暧^調(diào)控:貨幣政策失誤是金融動(dòng)蕩的根源。貨幣政策的失誤引發(fā)了金融風(fēng)險(xiǎn)的產(chǎn)生和積累,結(jié)果使得小范圍的金融問題演化為劇烈的金融動(dòng)蕩。根據(jù)弗里德曼等人的觀點(diǎn),如果沒有過度的貨幣供給,金融動(dòng)蕩不太可能發(fā)生,即使發(fā)生也不至于太過嚴(yán)重。由此可以得出,政府在經(jīng)濟(jì)中應(yīng)起到宏觀調(diào)控的作用,恰當(dāng)?shù)暮暧^調(diào)控政策可以化解金融危機(jī);若宏觀調(diào)控政策不當(dāng),將有可能進(jìn)一步加劇金融風(fēng)險(xiǎn)。
監(jiān)管不足:伴隨金融市場(chǎng)的產(chǎn)生,系統(tǒng)性金融風(fēng)險(xiǎn)就持續(xù)存在,但其真正引起各國(guó)決策者的關(guān)注是在2008年金融危機(jī)之后。由此可見,此前對(duì)于系統(tǒng)性金融風(fēng)險(xiǎn)的監(jiān)管是嚴(yán)重不足的。這與當(dāng)時(shí)的歐美主要國(guó)家監(jiān)管當(dāng)局過分強(qiáng)調(diào)市場(chǎng)“看不見的手”的作用,堅(jiān)信“最好的監(jiān)管就是最少的監(jiān)管”的行為相吻合。在危機(jī)之后,雖然系統(tǒng)性金融風(fēng)險(xiǎn)進(jìn)入了決策者的視野,但是隨著金融市場(chǎng)逐漸體現(xiàn)出跨行業(yè)經(jīng)營(yíng)和跨區(qū)域經(jīng)營(yíng)的特點(diǎn),監(jiān)管改革往往滯后于金融創(chuàng)新,導(dǎo)致出現(xiàn)監(jiān)管空缺,依舊存在隱患。
市場(chǎng)主體的非理性行為:雖然經(jīng)濟(jì)學(xué)研究中一貫認(rèn)為人們是理性的,但在實(shí)際生活中,市場(chǎng)主體往往存在非理性行為。人們對(duì)于利益的追逐會(huì)使得市場(chǎng)交易理性化,但依舊存在著非經(jīng)濟(jì)因素會(huì)對(duì)決策者行為造成影響。產(chǎn)生非理性行為的主要原因是羊群效應(yīng),即從眾行為。當(dāng)市場(chǎng)處于非理性狀態(tài),商品的價(jià)格和價(jià)值不一致,系統(tǒng)性金融風(fēng)險(xiǎn)由此累積。
從內(nèi)部來說,金融市場(chǎng)作為非完全信息市場(chǎng),本身就具備著較高的脆弱性。金融脆弱性是指由于金融體系具有高負(fù)債經(jīng)營(yíng)特點(diǎn),導(dǎo)致其更容易面臨失敗的內(nèi)在屬性,即由于金融機(jī)構(gòu)負(fù)債過多,安全性降低,難以承受市場(chǎng)波動(dòng)的沖擊。出于逐利的目的,金融機(jī)構(gòu)在經(jīng)營(yíng)過程中不斷加杠桿經(jīng)營(yíng),過度使用高杠桿使得金融脆弱性不斷積累,微小的沖擊也可能會(huì)導(dǎo)致嚴(yán)重的系統(tǒng)性金融風(fēng)險(xiǎn)爆發(fā)。美國(guó)次貸危機(jī)爆發(fā)前,五大投資銀行的真實(shí)杠桿率甚至超過了88倍。在面臨沖擊時(shí),這種高杠桿運(yùn)作模式直接導(dǎo)致了危機(jī)的爆發(fā)并極大地加劇了危機(jī)的危害性。
三、測(cè)度
隨著系統(tǒng)性金融風(fēng)險(xiǎn)研究熱度上升,其測(cè)度方法層出不窮。由于篇幅原因,本文按照時(shí)間先后順序排列,介紹了幾種典型的測(cè)度方法,希望能夠?qū)ο到y(tǒng)性金融風(fēng)險(xiǎn)的測(cè)度起到一定的概括性作用。
Illing&Liu(2003)首次提出了金融壓力的概念并構(gòu)建了金融壓力指數(shù)。[4]金融壓力指數(shù)是利用一組反映金融體系風(fēng)險(xiǎn)情況的宏觀指標(biāo),或者依據(jù)一定統(tǒng)計(jì)原則加權(quán)得到的綜合指數(shù)。利用該指數(shù)來衡量金融體系風(fēng)險(xiǎn)情況時(shí),該指數(shù)越大,表示系統(tǒng)性金融風(fēng)險(xiǎn)越大;當(dāng)超過閥值時(shí),可認(rèn)為該時(shí)期風(fēng)險(xiǎn)偏大甚至已進(jìn)入金融危機(jī)時(shí)期,則這一時(shí)期值得被持續(xù)關(guān)注。利用單一指標(biāo)衡量金融危機(jī)的方式只對(duì)發(fā)生過金融危機(jī)的國(guó)家適用,而將金融壓力指數(shù)作為被解釋變量,利用其他指標(biāo)構(gòu)建模型的方式對(duì)所有國(guó)家都適用。呂江林等(2011)利用逐步回歸分析,運(yùn)用各種檢驗(yàn)選擇最佳變量,并通過實(shí)證得出變量與相關(guān)系數(shù)的選擇合理的結(jié)論,以此為基礎(chǔ)預(yù)測(cè)了我國(guó)一段時(shí)期內(nèi)的金融壓力指數(shù)CFSI。[5]這種方法易于理解,較為直觀地反映了系統(tǒng)性金融風(fēng)險(xiǎn)的大小,即使對(duì)于未曾爆發(fā)金融危機(jī)的國(guó)家也可作為判斷金融體系風(fēng)險(xiǎn)狀況的重要參考。
IMF(2009)提出“共同風(fēng)險(xiǎn)”CoVAR衡量標(biāo)準(zhǔn),即使用分位數(shù)回歸的估計(jì)方法,考察不同金融機(jī)構(gòu)CDS之間的共同依賴性。當(dāng)一家機(jī)構(gòu)的CDS息差處于其分布的第5個(gè)分位數(shù)時(shí),表明該機(jī)構(gòu)處于良性時(shí)期;當(dāng)CDS息差處于其分布的第95個(gè)分位數(shù)時(shí),表明該機(jī)構(gòu)處于困境時(shí)期。[6]Adrian&Brunnermeier(2016)在此基礎(chǔ)上提出增量條件風(fēng)險(xiǎn)價(jià)值法。[7]由于存在溢出效應(yīng),個(gè)別機(jī)構(gòu)的風(fēng)險(xiǎn)在機(jī)構(gòu)間蔓延可能會(huì)加劇系統(tǒng)性金融風(fēng)險(xiǎn),通過衡量CoVAR對(duì)VaR的變化率,即風(fēng)險(xiǎn)溢出值,來反映整個(gè)金融機(jī)構(gòu)和特定機(jī)構(gòu)之間的關(guān)系,可衡量單個(gè)金融機(jī)構(gòu)處于危機(jī)時(shí),其他金融機(jī)構(gòu)面臨的風(fēng)險(xiǎn)。這種方式強(qiáng)調(diào)的是單個(gè)金融機(jī)構(gòu)的貢獻(xiàn)程度,因此更適用于測(cè)度微觀層面的系統(tǒng)性金融風(fēng)險(xiǎn)。
Brownlees&Engle(2011)通過構(gòu)建SRISK指數(shù)來測(cè)度單個(gè)金融機(jī)構(gòu)對(duì)系統(tǒng)性金融風(fēng)險(xiǎn)的貢獻(xiàn)程度。[8]SRISK可以捕捉到許多對(duì)系統(tǒng)性金融風(fēng)險(xiǎn)存在影響的特征變量,如規(guī)模、杠桿率、風(fēng)險(xiǎn)等。當(dāng)整個(gè)金融部門存在虧損時(shí),這些變量?jī)A向于增加金融機(jī)構(gòu)的資本缺口,而資本缺口越大的機(jī)構(gòu)對(duì)系統(tǒng)性金融風(fēng)險(xiǎn)的影響越大,對(duì)金融危機(jī)的貢獻(xiàn)程度也越高。梁琪等(2013)使用我國(guó)34家金融機(jī)構(gòu)作為樣本,利用SRISK方法,分析金融機(jī)構(gòu)系統(tǒng)重要性,認(rèn)為系統(tǒng)重要性與金融機(jī)構(gòu)規(guī)模有一定聯(lián)系但并不是必要聯(lián)系,且系統(tǒng)重要性并不是恒定不變的。[9]與上一種方法相同,SRISK也是強(qiáng)調(diào)單個(gè)金融機(jī)構(gòu)的貢獻(xiàn)程度,這種方法也適合測(cè)度微觀層面的系統(tǒng)性金融風(fēng)險(xiǎn)。
馬建堂等(2016)通過計(jì)算我國(guó)總杠桿率,認(rèn)為雖然與發(fā)達(dá)國(guó)家相比,我國(guó)的總杠桿率較低,但是持續(xù)增長(zhǎng)的態(tài)勢(shì)依舊需要保持警惕;并指出分部門來看,非金融企業(yè)和政府部門的杠桿率增長(zhǎng)過快,需要給予更多關(guān)注。[10]為了避免系統(tǒng)性金融風(fēng)險(xiǎn)爆發(fā),持續(xù)關(guān)注分部門杠桿率是否觸及閥值,并根據(jù)各部門特點(diǎn)有效控制真實(shí)杠桿率是有價(jià)值的。而陳彥斌等(2019)則認(rèn)為“杠桿率/投資率”是更好的預(yù)警指標(biāo)。杠桿率上升只是一定程度上表明金融市場(chǎng)存在隱患,但并不一定會(huì)導(dǎo)致系統(tǒng)性金融風(fēng)險(xiǎn)爆發(fā)概率顯著增加;但與此同時(shí),如果“杠桿率/投資率”也上升,那么爆發(fā)概率顯著上升。[11]
總體看來,系統(tǒng)性金融風(fēng)險(xiǎn)測(cè)度的方法雖然多種多樣,但各有其特色。最好結(jié)合多種測(cè)度方法,并緊跟時(shí)代發(fā)展,結(jié)合國(guó)情不斷更新現(xiàn)有方法,來使度量結(jié)果更準(zhǔn)確,達(dá)到有效預(yù)警系統(tǒng)性金融風(fēng)險(xiǎn)的目的。
四、結(jié)論
系統(tǒng)性金融風(fēng)險(xiǎn)多方面因素持續(xù)作用的結(jié)果,是持續(xù)存在的,必須時(shí)刻保持警惕,建立動(dòng)態(tài)預(yù)警機(jī)制,時(shí)刻追蹤系統(tǒng)性金融風(fēng)險(xiǎn)。此外,即使建立健全的預(yù)警機(jī)制,由于系統(tǒng)性金融風(fēng)險(xiǎn)本身識(shí)別難度大,何時(shí)進(jìn)入特殊階段,即金融危機(jī)何時(shí)爆發(fā)難以界定,且針對(duì)系統(tǒng)性金融風(fēng)險(xiǎn)的測(cè)度方法各有千秋,因此,需要結(jié)合多種測(cè)度方法,并盡可能改進(jìn)現(xiàn)有方法,讓量化結(jié)果更加準(zhǔn)確,才能建立起更有效的預(yù)警機(jī)制,進(jìn)而預(yù)警和避免金融危機(jī)的爆發(f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