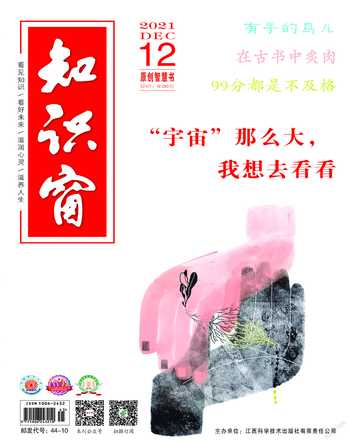好時光,盡在紙筆間
桑淼
和朋友小聚,她突然驚異地指著我桌前厚厚一沓手稿感嘆道:“你竟然寫了這么多文字,怎么不直接用電腦?”的確,在我們這個年紀(jì),幾乎所有的文字都是用鍵盤敲敲打打完成的。在手機或電腦上一通操作,簡單又快捷,整日埋首在紙筆間的日子,仿佛早已隨著學(xué)生時代一去不復(fù)返了。“我想可能是因為不習(xí)慣吧,經(jīng)年累月在紙筆間耕耘,不好改變。”我說。“可是互聯(lián)網(wǎng)越來越發(fā)達(dá),你總是要習(xí)慣的。”一時間,我竟無法反駁她。
對我而言,紙筆帶來的可觸感往往比其本身更有意義。鋪開宣紙一張,鋼筆擱置在旁,文字落在紙上,才顯得有溫度。
仍記得年少時,昏黃燈光下,母親教我一筆一畫識字的場景。從唐詩宋詞到諸子百家,每一個方塊字都被端端正正地印在田字格里。在教我寫字這件事上,母親一向是嚴(yán)厲的,要先準(zhǔn)備削好的2B鉛筆,本子必須平整干凈,若是偷懶馬虎了,必定是要擦掉重寫的。“字如其人。”母親總是這樣講。橫平豎直,一撇一捺,每一筆都透露著漢字文化本身的韻味與詩意,承載著母親對我一生建樹的期望。
有時窗外落了雪,北風(fēng)卷起荒草,寒風(fēng)呼嘯,而屋內(nèi)一盞燈火如豆,落在紙上的文字,雖寫得吃力,但心底溫暖異常。這般舊時光里的歲月靜好,怕是在鍵盤上敲幾百個回合,也難以企及。
在選用紙筆這件事上,我向來不挑剔。告別了年少時稚嫩的鉛筆字,鋼筆則顯得提頓分明,堅實有力。甚至有一段時間,我還會取來毛筆臨摹古體,想象能如名士大家般,飽蘸筆墨,筆走書海,在紙上肆意揮灑。但奈何心性急躁,再加上腕上無力,也便不了了之,那些丹青水墨,起承轉(zhuǎn)合,也就此停留在了記憶里。對待稿紙上,則更顯得粗糙,作業(yè)紙的背面、用了一半的筆記本,甚至超市購物的憑條……都能成為我創(chuàng)作的伴侶。無論高科技怎樣發(fā)展,都斷不了紙和筆幾千年的耳鬢廝磨。
讀書時,念過詩詞萬千,但我最喜歡宋時晁補之的一句:“花前燭下,微顰淺笑,要題詩、盞畔低聲。”那該是千年前吧,在雕著幽蘭芳草的閨閣軒窗前,有一女子點亮了半盞燭火,在燈影搖曳里巧笑倩兮。燈盞下定是有翻開的素箋,墨跡未干,詩行里寫滿了少女懷春的心事。
鋪紙研墨,斟酌提筆,在對待寫作這件事上,古人則顯得隆重且虔誠。文人仕族多把焚香撫琴、曲水流觴奉為樂事,幾重雅樂過后,詩文也便了然于心,落在紙上的文字,鑄就了五千年滔滔文明。另外,有些時候,瓷瓶、羅扇、花葉……也成了古人寫作的載體,很難想象在那個物質(zhì)生活無比匱乏的年代里,竟也能擁有如此豐盈的心境。不知千年前的大唐盛世,太白拿起紫毫筆時,內(nèi)心是否也會有過些許欣喜呢?
好時光,總是停留在紙筆間。宛如故事的開場白一般,抽芽于字里行間,又老成于時間的筋脈。試想一個秋日的午后,陽光慵懶地灑在桌前,你鋪開素箋,一時間文思泉涌,筆尖生蓮,鬢邊一枝秋海棠灼灼綻放、搖曳生姿……這該是怎樣的愜意和滿足呀。
曾經(jīng)讀過這樣一句話:“好時光是在千瘡百孔的生活中淬煉出的一顆舍利,散發(fā)著樸素動人的光芒。”紙筆間的起承轉(zhuǎn)合,看似清淡無味,卻是最樸素的好時光。一字一句,牽念于心。紙筆間的歲月,比哪里都更溫暖,比哪里都更悠然。
(作者系安徽理工大學(xué)山南新校區(qū)2019級數(shù)字媒體技術(shù)專業(yè)學(xué)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