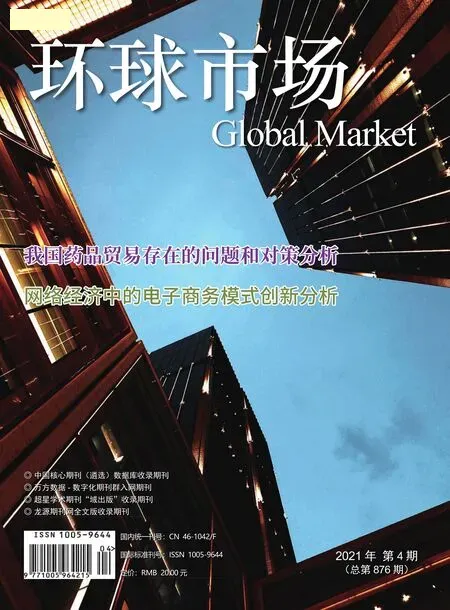淺析日本武士道精神
王文武 曹瑜虹 湖南人文科技學(xué)院
一、日本武士道的起源
日本武士道是武士階級在實際的戰(zhàn)爭中逐漸形成的體系。武士最開始是小小的私人武裝,為實現(xiàn)個人于集體、團(tuán)體的價值,盡可能的發(fā)揮自己的能力,強調(diào)“毫不留念的死,毫不顧忌的死,毫不猶豫的死”,永遠(yuǎn)敢于走在戰(zhàn)爭的最前線,為各貴族、富豪解決紛爭。在8、9世紀(jì)實行大化革新,其中有土地永世私人化條例,官僚、貴族們開始借用此條例開始擴(kuò)展勢力范圍,天皇勢力逐漸減弱,開始出現(xiàn)個人管理國家。其中藤原氏建立了第一個外戚專治,天皇也失去實權(quán)成為傀儡。
因為地方豪強勢力對莊園的大肆興建,莊園主和平民的矛盾、莊園主和國家的矛盾、莊園主和官吏們的矛盾,在各地方矛盾不斷激化。而天皇無權(quán)不能進(jìn)行調(diào)節(jié),導(dǎo)致矛盾不斷上升,最后只能由私人武裝——武士來暴力解決矛盾。官僚們不斷擴(kuò)大武士范圍,武士地位也因此不斷提高,發(fā)展成為正規(guī)的軍事力量。武士道隨著武士集體化的開始誕生,最初只是武士們對莊園主他們的忠誠。
二、日本武士道的發(fā)展
在古代的日本,從攻城略地到主人生活瑣事,武士們一律承擔(dān)。武士將保護(hù)主人的安危、維護(hù)主人利益、服從主人命令為鐵律。他們大都視責(zé)任高于己命,若沒有完成任務(wù),常以死謝罪。武士非常講究主從關(guān)系,且這種關(guān)系世代沿襲,雖然能使雙方受益,但武士得到的只是一小部分財產(chǎn),而主人卻得到的是他們的生命與忠誠。
隨著幕府制度的建立,武士階層成為政權(quán)中心,武士的忠誠直接影響到階層統(tǒng)治。因此幕府首位統(tǒng)治者源賴朝十分注重這一點,除了制度上的約束,還從思想上進(jìn)行控制。統(tǒng)治者以武士道精神的規(guī)范來對武士們進(jìn)行思想行為引導(dǎo),以此來保持武士的忠誠。推崇“君不君”臣也一定得臣,讓他們始終對自己保持高度的忠誠,武士道也這樣走向了高潮。
伴隨儒家和佛教從中國傳入日本,“死里如一”這種思想也興起于武士之中。武士們認(rèn)為人的生死其實和四季自然規(guī)律一樣會有結(jié)束和新的開始交替往復(fù),于是便愈加不尊重生命。重名輕生,僅僅是為了榮譽為了彰顯忠誠而戰(zhàn)斗。由此形成一種大無畏的風(fēng)氣,難以判斷其正誤,但身份高高在上的主人因此顯著受益。日本在歷經(jīng)系列更替后,錯過工業(yè)革命,借由列強入侵后開啟明治維新。武士制度也因此被廢除,而武士精神卻一直長存日本人的心中。
三、日本武士道精神的內(nèi)涵
武士道最注重的內(nèi)容就是“道”,道而又可細(xì)分為:義、勇、仁、禮、誠、名、忠、克等。而其內(nèi)涵便是所行所動都要嚴(yán)格按照“道”來執(zhí)行。例如:對主人的無限忠誠、對自我嚴(yán)格要求、做事誠信守諾、對任務(wù)誓死完成等等。但究其根本,日本武士道精神內(nèi)涵只有一點:即永遠(yuǎn)忠誠與自己的主人。恰恰是這種忠誠,似一條無形的鎖鏈,束縛著武士階層。
四、日本武士道精神影響的兩面性
從前述可知,日本武士不是簡簡單單的殺手、戰(zhàn)士,他們有自己奉行的諸如正直、堅毅、質(zhì)樸、儉約、膽識、禮節(jié)、大義等品德,對后世日本人影響深遠(yuǎn)。正如《菊與刀》中所說,日本武士道精神對后世的影響,存在這無畏、忠誠與殘忍、輕生兩大截然相反的品質(zhì)。
武士們效忠自己的天職,因為這樣才能獲得最高的榮譽。他們考慮下一步行動時不顧自身存亡,只以完成任務(wù)為目的。就算敵人強大眾多也絲毫無懼,也會勇往直前,不在意人們所說的無畏犧牲,因為他們認(rèn)為這是忠誠的表現(xiàn)。被俘虜?shù)奈涫坎粫蔀榕褔\,直到死去也不背叛自己的天職。這種無畏、忠誠的品質(zhì)在近現(xiàn)代日本人的“愛社榮社”的精神里得到了充分體現(xiàn)。比起個人及家庭事務(wù),日本的工勤族以公司、集團(tuán)的利益優(yōu)先,不計代價,并且注重入職后“從一而終”,及其看重就職年限長短。在日本女生看來寒冷冬天光腿穿短裙不僅是美的追求,更多的是體現(xiàn)了自己勇敢無畏的武士道精神,通過對抗寒冬,體現(xiàn)自己的頑強勇敢。日本國土狹小,資源匱乏,卻敢于與大國較量;多災(zāi)多難,但人民卻越挫越勇,一系列應(yīng)急措施由此而生,不斷適應(yīng)環(huán)境。
但武士道精神也有其殘酷的一面。《葉隱》的著述者山本常朝提到一位名為山本吉左門武士典故。其父在他很小的時候就開始對他進(jìn)行殘酷訓(xùn)練,吉左門5歲變能斬殺狗,15歲便能斬殺罪人。武士道精神雖然汲取中國的儒家精神,但沒有將“仁愛”融入其中,缺乏人性的一面,只剩下殘酷。二戰(zhàn)期間,日本軍國主義進(jìn)行的種種慘絕人寰的掠殺就是最有力的證據(jù)。對于侵略戰(zhàn)爭的罪行,至今日本還未承認(rèn),此時的武士道精神中的正直、誠實,根本不管用,武士道其實只是天皇為了統(tǒng)治的工具。對待俘虜時也是十分兇殘,戰(zhàn)爭中有不成文的規(guī)定:當(dāng)敵人放下武器,成為俘虜時不許開槍。而日本人卻不以為然,武士精神的另一面便是對不同于自己的異類進(jìn)行摧殘甚至屠殺。所謂的大義也僅僅是指聽從天皇的指揮。直到現(xiàn)在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也名副其實,在強大(美國)面前,只能為其“差遣”。步入現(xiàn)代社會,武士道的輕生取向間接影響受挫的日本人以不同形式結(jié)束生命。日本各類自殺新聞報道不斷,日本自殺率也高居世界前列。
五、結(jié)語
日本武士道精神伴隨日本武士階層而產(chǎn)生,中有許多發(fā)光點,如忠誠、無畏、克己等,但也存在殘酷、重名輕死、排異主義等弊端,我們應(yīng)當(dāng)辨證正確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