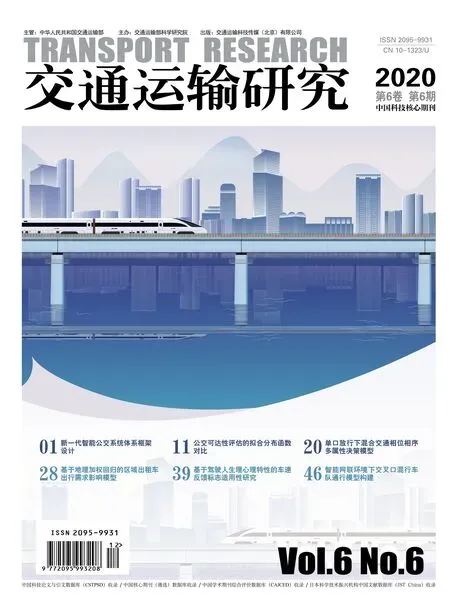互聯網租賃自行車用戶騎行大數據時空分布特征
(交通運輸部科學研究院,北京 100029)
0 引言
互聯網租賃自行車自2015 年開始在城市投放,在2016—2017 年得到迅速發展,先后有74家運營企業進入市場,全面覆蓋我國一、二線城市,逐漸延伸至三、四線城市,部分企業還將業務拓展至海外。經過激烈的競爭與市場重組,截至2019 年底,全國互聯網租賃自行車共有1 950萬輛,覆蓋全國360余個城市,注冊用戶數接近4億,日均訂單數達到4 700 萬[1]。目前,行業進入相對穩定的發展時期,基本形成美團、哈啰、滴滴三家企業三足鼎立的發展格局,經營回歸理性,精細化運營成為當前企業的發展重點。以運營企業和背后投資方聯合運作提供的這一突破傳統的城市基本服務模式需要政府、企業和居民協同合作才能可持續發展[2]。
互聯網租賃自行車可以深入城市角落,彌補其他出行方式的服務空白,其便捷的租還和支付方式、高分布密度等優勢,提高了使用者的出行體驗和出行效率,受到廣大用戶的喜愛。然而自20 世紀90 年代以來,以機動車為導向的城市發展,逐漸擠壓自行車騎行與停放空間。互聯網租賃自行車的發展影響著居民的出行行為,也推動著城市規劃和管理者對城市空間和道路資源的重新認識。同時,互聯網租賃自行車出行產生的大量的基于時間和位置的數據為描述和理解城市空間結構提供了新的途徑。因此,有必要通過對騎行大數據的時間和空間分析,揭示騎行需求規律,為城市相關規劃建設、行業管理部門和運營企業合作建立科學的投放與管理機制等提供技術支撐。
目前國內外已有部分基于互聯網租賃自行車和公共自行車使用數據進行騎行特征分析的研究成果。Long 等人[3]利用互聯網租賃自行車騎行數據分析了用戶的平均騎行距離、騎行時長和人均騎行次數等特征,并據此計算了城市的可騎行指數。冉林娜等人[4]、Li 等人[5]基于出行意愿問卷調查,分析了互聯網租賃自行車用戶屬性和影響使用的主要因素。周榮等人[6]基于城市樣本數據分析得到互聯網租賃自行車的騎行時長、周轉率等使用特征。高楹等人[7]基于北京市摩拜單車一周的訂單數據,分析了不同土地類型的車輛供需失衡的時空特征,并提出局部優化的調度模型。另外一些研究則根據網絡爬取到的零星數據來透視互聯網租賃自行車的騎行時空特征[8-11],或者根據典型地鐵站點互聯網租賃自行車使用的早晚高峰特征提出停放[12]或調度建議[13]。
由于互聯網租賃自行車起源于中國,海外市場規模較小,國外針對其使用特征的研究相對較少,目前,僅查詢到Zhao 等人[14]基于新加坡互聯網租賃自行車的GPS 數據,利用空間自回歸模型分析了可獲得的車輛數、建成環境等因素對其使用特征的影響。配置停車樁的公共自行車系統在國外發展多年,因此,國外針對公共自行車使用特征的研究較多。如,Kaltenbrunner 等人[15]、Vo?gel 等人[16]、Corcoran 等人[17]和Fricker 等人[18]分別基于巴塞羅那、維也納、布里斯班和巴黎的公共自行車使用數據,研究站點間客流分布特征。Castillo-Manzanoa 等人[19]通過分析塞爾維亞市公共自行車與私人自行車的騎行特征,發現公共自行車的平均騎行距離比私人自行車短。Compbell等人[20]通過對紐約市公共自行車客流量及其對應的公交線路客流量的分析,發現公共自行車系統有利于提升公交客流。與互聯網租賃自行車不同,公共自行車由于缺乏實時定位系統,大多數研究僅局限于固定站點的客流分析。
綜上,目前針對互聯網租賃自行車或公共自行車的騎行特征研究主要存在以下幾方面的問題:一是部分研究通過調查問卷了解用戶出行意愿、使用習慣等,從而分析得出用戶使用特征和影響因素,存在調查樣本量有限、問題可能帶有主觀傾向性、問卷質量難以保證等問題,會影響所采集信息的可靠性,容易產生選擇性偏差[21],研究結論具有局限性;二是部分研究人員通過網絡技術手段爬取零星數據來分析出行特征,由于技術方法和工作量的局限只能獲得短期用戶使用數據(一般為2~5d),利用這些短期、少量的用戶數據分析得出的騎行特征缺乏代表性,難以凝練規律。
實際上,互聯網租賃自行車騎行過程中產生了大量數據,結合原有城市物質空間數據[22],可為了解居民出行需求、提升服務水平、完善城市交通網絡、優化城市建設管理提供關鍵信息。因此,本文選取為期1 個月的互聯網租賃自行車用戶真實訂單數據,對用戶騎行時空分布特征進行深入分析;結合數字地圖與城市用地性質,通過空間分析和可視化探尋不同類型用地性質的互聯網租賃自行車騎行需求規律。
1 數據來源
1.1 騎行數據
本文擬采用的騎行數據為通過與運營企業合作獲取的某互聯網租賃自行車品牌2018 年4 月份的北京市所有用戶訂單數據,數據產生的時間為2018 年4 月1 日—4 月30 日。原始訂單數據內容包括訂單編碼、開鎖時間、開鎖位置經緯度、關鎖時間及關鎖位置經緯度等,數據表單示例見表1。這些數據為互聯網租賃自行車智能鎖中自帶的GPS和數據模塊記錄。

表1 互聯網租賃自行車騎行訂單原始數據表單示例
1.2 地圖數據
本文采用的地圖數據是北京市行政區矢量數據與北京市路網矢量數據,兩個圖層的數據坐標系均采用WGS-1984 國際標準,這與互聯網租賃自行車GPS 所采集到的位置信息的坐標系是一致的,因此不需要進行坐標系轉換。
1.3 土地使用性質數據
為了借助互聯網租賃自行車騎行大數據初步分析不同功能用地的騎行特征,本文需對研究區域的用地性質進行識別。由于缺少WGS-1984 坐標系下的地圖工具,本文采用Google Earth 軟件提供的遙感影像數據及其對應的經緯度與BD-09坐標系下在線百度地圖進行比對的方法,初步識別興趣點(Point of Interest,POI)的用地性質。
2 研究方法
2.1 數據清洗
因本文獲取的騎行數據為原始訂單數據,無法直接使用,需在數據分析前進行數據整理和清洗,以確保分析結果的有效性,主要針對以下兩方面的數據。
(1)經緯度不在本研究范圍內的數據。本研究選取北京市五環內區域,此區域坐標范圍為北緯39°50′43′′—40°2′24′′,東經116°13′6′′—116°32′00′′,凡是訂單起點或終點不在該坐標范圍內的數據均篩選剔除。
(2)異常數據。由于網絡存在不穩定性,數據在傳輸中可能產生異常值,導致部分屬性數據無法對應或數據空白,故將這部分數據篩選剔除。
2.2 數據預處理與數據模型
(1)本文獲取的原始訂單數據在經過數據清洗去雜去噪后,還需進行預處理后才能使用。首先使用Excel 將原始訂單數據進行列分隔,然后對每日數據進行篩選,將全市每日的數據保存為一個文件。根據數據分析需要,再對每日數據進行分時間段處理。
(2)為準確表達和分析預處理后的數據,構建出行數據模型(TRIP)。TRIP 數據模型可表達為:TRIP={OP,OT,DP,DT},即每個訂單代表了用戶從開鎖到關鎖的騎行過程,可表達為一次騎行的出發地點(OP)、出發時間(OT)、到達地點(DP)和到達時間(DT)的集合。舉例說明:某用戶早上8:00 從家出發,找到一輛互聯網租賃自行車,該車輛的位置定位為(東經116.3475,北緯39.9182),用戶用智能手機掃碼開鎖,開鎖時間為8:05,騎行到目的地后停車關鎖,這時車輛位置為(東經116.3812,北緯39.9342),時間為8:37,這位用戶的出行就被記錄為一次TRIP,表達為: {116.3475,39.9182,8:05,116.3812,39.9342,8:37}。
2.3 數據分析與可視化
(1)采用ArcMap 對騎行數據進行空間可視化。將北京市行政地圖和路網矢量數據導入Arc?Map,利用ArcMap 中核密度分析工具(Kernel Density)將不同時間段的TRIP數據集空間化,顯示在北京市地圖上,通過聚類分析和空間插值法,結合用地性質數據,辨識不同地塊的騎行強度,識別具有統計顯著性的空間聚集熱點。
(2)基于日內不同時間段的TRIP 數據模型,分析用戶騎行出發和結束的時間和空間規律,結合用地性質初步識別用戶的居住地和就業地。
3 互聯網租賃自行車騎行特征分析
3.1 互聯網租賃自行車時間維度上騎行規律
(1)互聯網租賃自行車一周內騎行量分布規律
對2018 年4 月互聯網租賃自行車日騎行量進行統計分析(見圖1),并將工作日、非工作日的騎行次數進行比較,為排除降雨、大風等天氣因素的影響,選擇一周晴朗且日均風力四級以下的時間進行逐日分析。總體上,工作日的互聯網租賃自行車騎行量分布較為穩定,日均可達到90萬次以上,非工作日日均50萬次以上,工作日的騎行量是非工作日的1.7 倍,可以看出互聯網租賃自行車主要用于通勤出行。

圖1 北京市2018年4月一周某品牌互聯網租賃自行車日騎行量
(2)互聯網租賃自行車逐時騎行量分布規律
對2018 年4 月工作日、非工作日的日內每半小時平均騎行量進行統計,如圖2 所示。可以看出,工作日、非工作日兩者差別明顯;工作日早晚高峰突出,早晚高峰時段分別為7:00—9:00 和17:00—19:00,與通勤時間相吻合,逐時騎行量分布曲線總體呈M 形,在中午12:00—14:00 之間也出現一個微小高峰,但是騎行量增加不明顯。非工作日早晚高峰不突出,與中間時段的騎行量較為接近。無論是工作日還是非工作日,絕大多數騎行都分布在5:30—23:00 之間,23:00—次日5:30 之間騎行量很少,這與用戶處于休息時間相對應,出行需求很少。綜上,互聯網租賃自行車在工作日和非工作日的出行需求有明顯差異,工作日早晚高峰騎行量激增,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騎行目的主要為通勤出行。

圖2 互聯網租賃自行車各時段騎行量分布
3.2 互聯網租賃自行車空間維度上騎行分布規律
本文運用ArcMap 軟件中的核密度分析工具對互聯網租賃自行車空間維度上的騎行分布規律進行分析。核密度分析工具的工作原理是計算要素在其鄰域中的密度,核密度的值隨著中心輻射距離的增大而逐漸變小[11]。首先將TRIP 數據集的起點和終點位置以點的形式呈現在底圖上,根據核函數定義,設定population 字段值為None,則輸出的柵格每個像元的密度均為疊加在像元中心的所有核表面的值之和,即輸出的值是基于實際輸入點數計算的。這樣輸出的核密度柵格圖即為互聯網租賃自行車的聚集熱點圖。基于此,通過分析工作日早晚高峰時段用戶騎行起點位置和終點位置的分布,可以探尋互聯網租賃自行車在用車高峰時段空間維度上的騎行分布特征。
北京市互聯網租賃自行車工作日早高峰時段(7:00—9:00)騎行分布如圖3 所示。可以看出,騎行終點比騎行起點更加集中,騎行熱點主要出現在金融街、國貿CBD、亮馬橋、中關村、望京等商務辦公區域,以及商務區、居住區附近的地鐵站點,例如西直門、阜成門、亮馬橋、三元橋、國貿、朝陽門、四惠等,這與居民通勤時空特征相吻合。
工作日晚高峰時段(17:00—19:00)的騎行分布如圖4 所示,與早高峰相反,騎行起點比騎行終點更加集中,且聚集分布于金融街、國貿CBD、亮馬橋、望京、中關村等商務辦公區域。
由圖3~圖4 可以看出,互聯網租賃自行車的使用在工作日早晚高峰呈現出相似的熱點區域,并且早高峰時騎行終點與晚高峰騎行起點規律相似。這說明,整體上北京市就業辦公區較為集中,而居住區較為分散,這也與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規律相一致。
3.3 典型用地功能互聯網租賃自行車騎行規律
結合北京市用地性質與上述熱力圖反映的工作日互聯網租賃自行車騎行熱點,選取典型的商務辦公區、大型居住區、公共交通站點對互聯網租賃自行車的騎行規律進行分析。
(1)商務辦公區
本文選擇金融街核心區(金融、銀行和保險業集聚的區域)和中關村核心區(IT、信息產業集聚的區域)來分析互聯網租賃自行車在商務辦公區的騎行規律,如圖5所示。

圖3 互聯網租賃自行車工作日早高峰騎行起點與終點熱力圖

圖4 互聯網租賃自行車工作日晚高峰騎行起點與終點熱力圖

圖5 工作日商務辦公區互聯網租賃自行車騎行規律
從圖5可以看出,在早高峰時段(7:30—9:30),騎行至金融街和中關村核心區的人次遠遠高于從此地出發的人次,其中金融街騎行到達人次是出發人次的17 倍,中關村騎行到達人次是出發人次的2.6 倍;與此相反,晚高峰時段(17:00—19:00),從金融街和中關村核心區出發的人次遠高于騎行至此地的人次,其中金融街騎行出發的人次是到達人次的6.2 倍,中關村騎行出發的人次是到達人次的1.8 倍。這反映了金融街與中關村核心區為辦公集聚區,居住社區較少,金融街辦公地點集聚程度更高。
值得一提的是,在早高峰時段,金融街核心區騎行峰值點在8:00,中關村核心區騎行峰值點在8:30;晚高峰時段的騎行峰值點,金融街在17:30,中關村地區在18:00,同時,中關村地區在晚上21:00 左右還有一個小的騎行高峰,這反映了中關村地區的就業機構上下班時間比金融街晚,符合中關村IT 產業員工的工作作息規律。
(2)居住區
本文選擇石景山區的遠洋山水片區和朝陽區的垡頭片區作為居住社區集中的區域來分析互聯網租賃自行車的騎行規律,如圖6所示。

圖6 工作日居住區互聯網租賃自行車騎行規律
從圖6 可以看出,遠洋山水與垡頭的騎行早高峰時段為6:30—8:30,比辦公集聚區早1h。從遠洋山水和垡頭騎行出發的人次遠高于騎行到達的人次,出發與到達人次比分別為1.4 和2.1 倍。晚高峰時段,遠洋山水騎行到達時間曲線波峰比騎行出發波峰明顯延長,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此片區的居民回家時間不集中,這與居住人群的就業性質和就業地點有關。晚高峰時段垡頭的騎行到達人次遠高于騎行出發人次,比例為3.6∶1,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該片區為住宅集聚區,提供的就業崗位較少。
(3)公共交通站點
本文選擇朝陽門地鐵站(2 號線和6 號線換乘)和西直門地鐵站(2號線、4號線、13號線換乘)來分析典型公共交通站點周邊互聯網租賃自行車騎行規律,如圖7所示。

圖7 工作日地鐵站附近互聯網租賃自行車騎行規律
從圖7 可以看出,朝陽門和西直門地鐵站總體騎行規律相似,均是早晚高峰明顯,與辦公區和居住區不同的是中間時段的騎行人次也較多。
朝陽門地鐵站的早高峰時段,騎行到達的人次總體與騎行出發人次相當,但從時間上來看,騎行到達時間比騎行出發時間分散。晚高峰出發與到達的人次也相當,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在此就業的人群與居住人群規模相當。
與朝陽門不同,早高峰時段,西直門地鐵站騎行出發人次多于騎行到達人次,而騎行到達的峰值點早于騎行出發峰值點,與之對應的是,晚高峰時段,西直門地鐵站騎行到達的人次多于騎行出發的人次。也就是說,騎行到達西直門地鐵站的人群出行目的很大程度上是去上班,而從此地鐵站騎行出發的人群是來上班的,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直門地鐵站附近的就業人群數量多于居住人群。
綜上,工作日不同用地功能的互聯網租賃自行車騎行需求規律如下。
(1)商務辦公區。互聯網租賃自行車使用具有明顯的早晚高峰特征。早高峰時段,互聯網租賃自行車的停車需求激增;晚高峰時段呈現出與早高峰相反的特征,用車需求激增。
(2)居住區。早高峰時段,互聯網租賃自行車用車需求激增;晚高峰時段,不同的居住區的騎行規律有差異,與居住人群的就業性質和就業地點有關,就業崗位較少的居住區,晚高峰時段的停車需求較大。
(3)公共交通站點。早晚高峰時段互聯網租賃自行車均呈現出用車和停車需求高峰,且與商務辦公區和居住區相比,用車與停車需求之間差異較小。附近就業人群多于居住人群的公共交通站點早高峰用車需求略高于停車需求,晚高峰停車需求略高于用車需求。
4 相關建議
在共享時代,許多傳統的城市功能分區中的空間將得到重構或升級,處于急劇變化中的城市亟需與之匹配的理論、研究范式及技術方法[23]。本文通過對用戶騎行大數據進行初步分析,得到互聯網租賃自行車的時空分布特征,研究成果可為城市相關規劃、建設和管理等方面的研究和實踐提供參考。
4.1 在城市相關規劃建設中給予互聯網租賃自行車更多的考慮
(1)鑒于互聯網租賃自行車越來越成為城市出行的重要組成部分,很大程度上騎行目的是通勤,而當前我國在進行以交通規劃為目的的城市居民出行調查時未將互聯網租賃自行車納入統計調查范圍,相應地在城市交通相關規劃中未考慮互聯網租賃自行車的使用。因此,希望從國家層面或城市層面將互聯網租賃自行車納入城市出行統計調查體系,便于研究機構對互聯網租賃自行車出行行為進行科學量化評估,并在此基礎上建立基于動態大數據分析的規劃模型和方法,在城市空間規劃、城市綜合交通規劃和相關專項規劃中強化互聯網租賃自行車與公共交通等其他交通方式的銜接。
(2)基于互聯網租賃自行車騎行大數據分析可以看出,城市中心區域的商務辦公區、公共交通站點及大型居住區是車輛使用的熱點區域。因此,城市中心區應強化完善自行車路網和停放點等設施的規劃與建設,并且在城市公共交通站點、商務區、居住區等熱點區域設置足夠的自行車停放空間,避免車輛淤積停放,促進互聯網租賃自行車與城市公共交通的高效接駁。
4.2 建立基于騎行大數據分析的投放和停放管理機制
(1)基于前文的分析,騎行大數據可反映城市空間要素信息和用戶需求信息。為改善當前部分城市存在互聯網租賃自行車無序投放的現狀,需要行業管理部門和互聯網租賃自行車運營企業合作,開展互聯網自行車出行需求的精準預測,利用騎行大數據分析技術,結合城市道路條件、停放空間資源等對整個城市或特定地區的互聯網租賃自行車進行容量測算,合理規劃投放總量和投放時序。
(2)鼓勵有條件的城市建設互聯網租賃自行車信息管理平臺,利用大數據分析進行科學精準地動態管理。要求接入所有投放車輛靜態和動態信息,及時掌握城市投放總量,通過騎行數據有效識別車輛聚集點,實時督促運營企業對超出停放限度與使用需求旺盛的點位的車輛進行及時調度。
(3)行業管理部門與運營企業合作,結合互聯網租賃自行車騎行數據分析用戶需求,在熱點區域和禁停區域等重點區位運用電子圍欄等新技術規范用戶停車行為,加強停放管理,避免造成車輛堆積、影響公共秩序。
4.3 開展互聯網自行車規范運營示范試點
根據前文騎行特征分析,互聯網租賃自行車已成為大城市居民出行的重要方式之一,特別是在通勤出行中用于與公共交通接駁。互聯網租賃自行車與公共交通協同可促進城市綠色出行分擔率的提升,同時也成為我國城市自行車復興的重要途徑。建議結合交通運輸部等多部門和單位印發的《綠色出行行動計劃(2019—2022 年)》[24],在全國選擇有條件的地區,從騎行環境建設、政策標準制訂、服務質量考核、運營管理等方面開展規范運營示范試點,探索形成有利于互聯網租賃自行車可持續發展的準入與退出機制、運行管理策略和技術方法等,形成政府、企業、公眾及社會組織共同參與的治理格局,及時總結試點示范經驗,并向全國推廣。
5 結語
本文基于互聯網租賃自行車出行大數據,通過時空分析與可視化,探尋了用戶騎行規律。通過逐日和逐時騎行次數分析得出工作日和非工作日的使用特征存在明顯差異。通過建立數據模型,運用ArcMap 軟件對互聯網租賃自行車的使用數據進行空間分析,識別騎行熱點;通過分析商務辦公區、居住區和公共交通站點3 類典型區域的互聯網租賃自行車騎行空間規律,得出不同用地功能區的用戶需求特征,可為政府管理部門和運營企業完善自行車網絡、建設自行車停放點位、提升管理的精細化和動態性提供支撐。由于互聯網租賃自行車GPS 數據量大、數據雜質和數據噪聲較大、對數據清洗和預處理方法要求較高的特點,本文所得到的結論是初步的。未來需進一步挖掘和分析互聯網租賃自行車騎行大數據,為合理規劃城市土地利用和優化職住平衡、提高城市交通系統的運行效率、提升社會治理能力等提供理論基礎與科學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