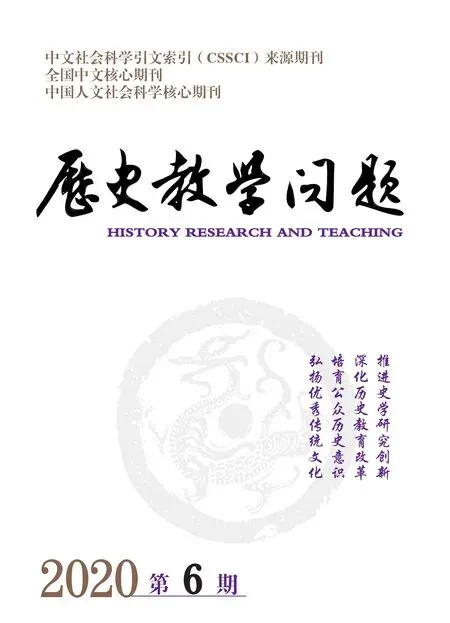試論蘭普萊希特在中美史學(xué)界的回響
王 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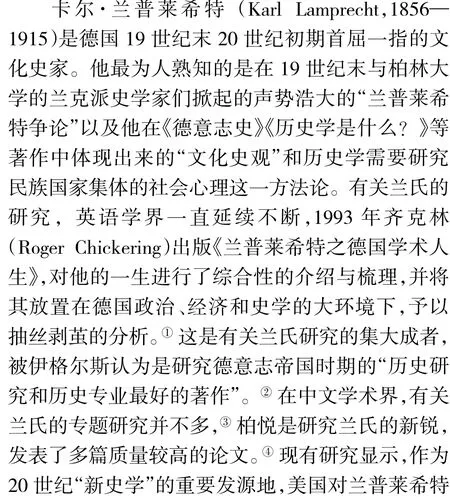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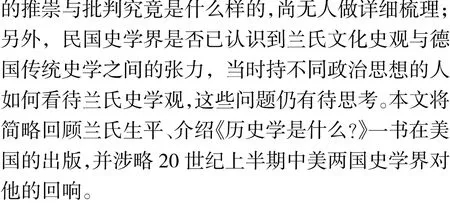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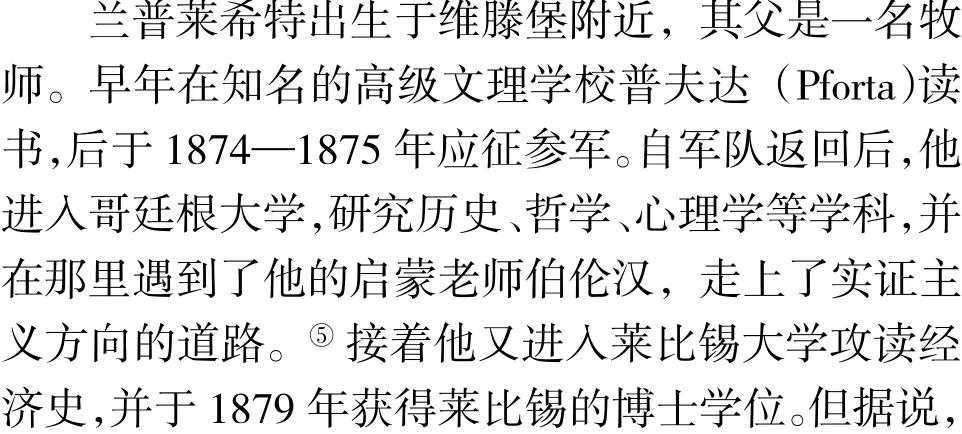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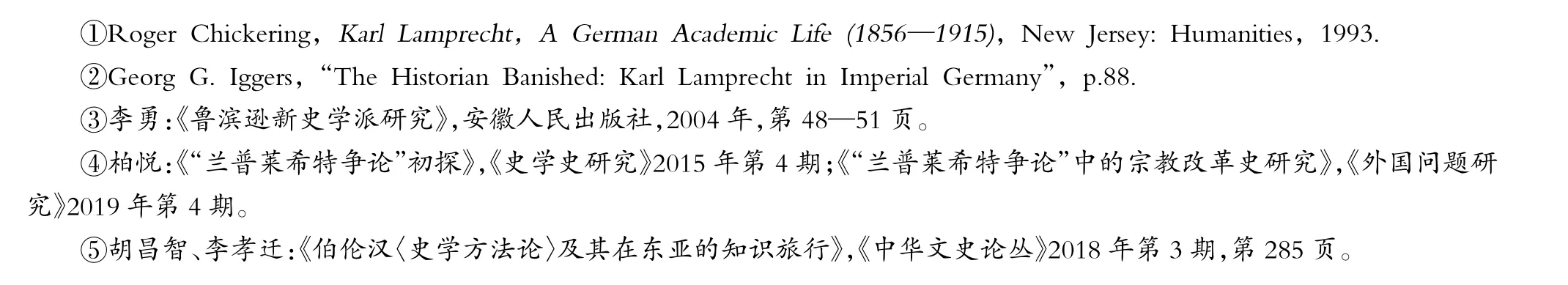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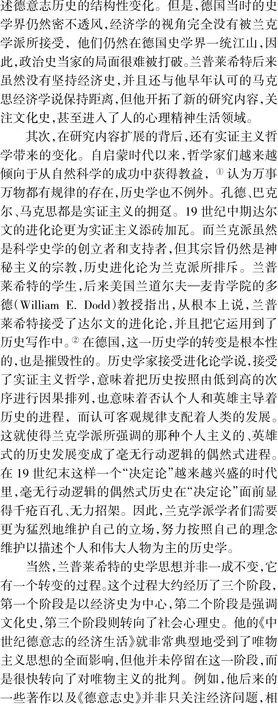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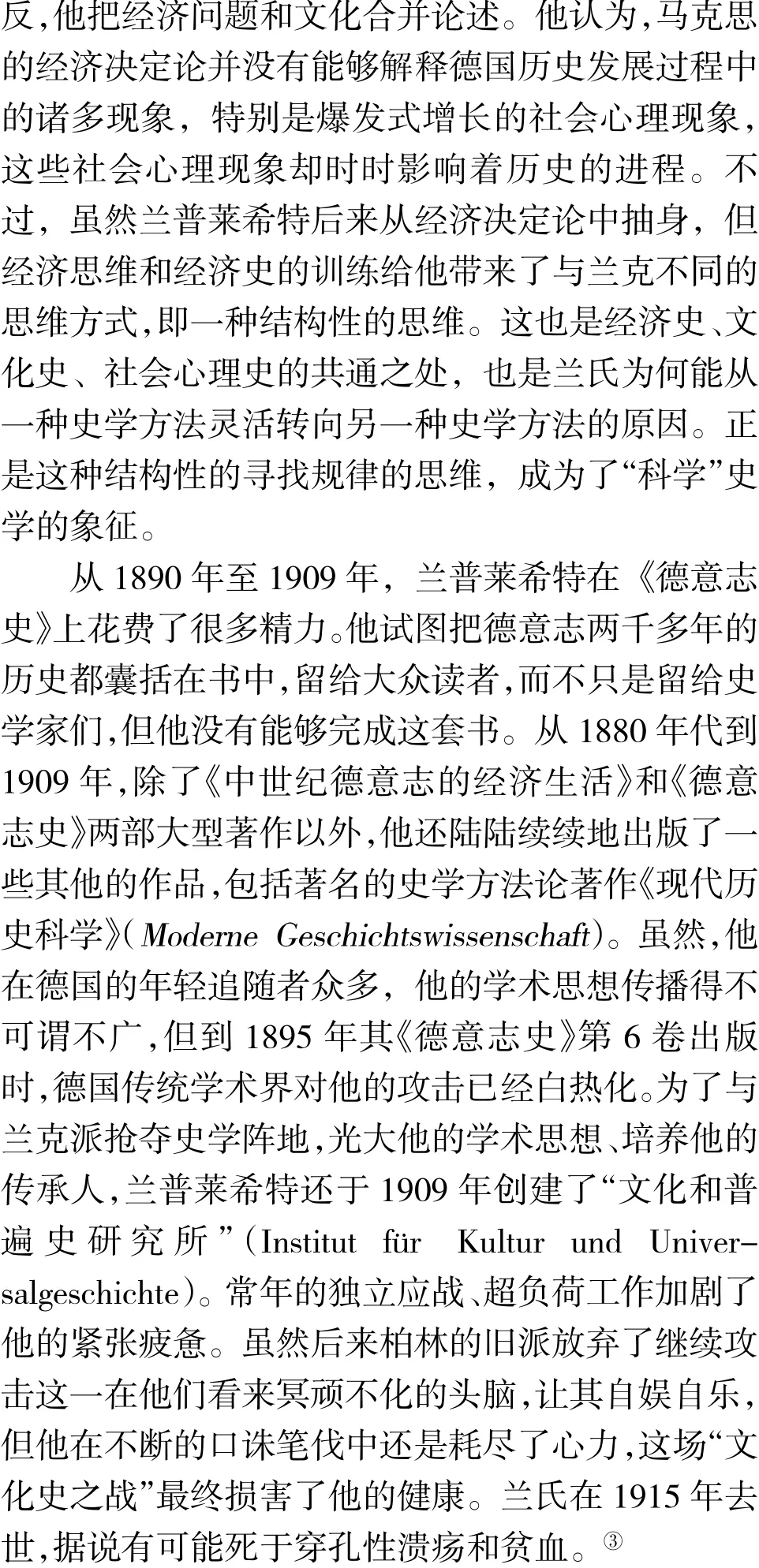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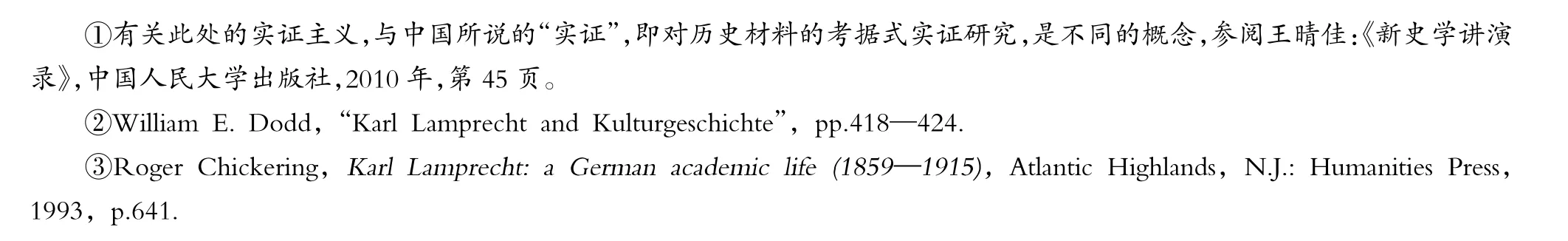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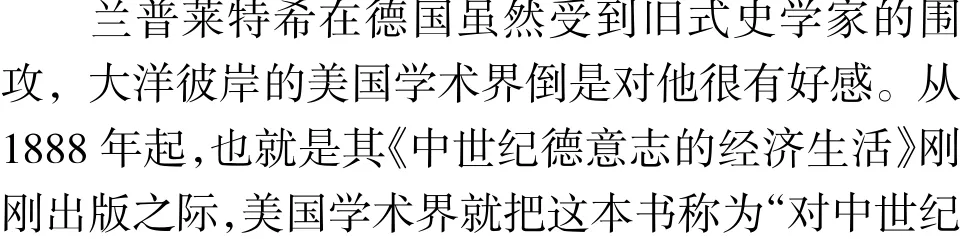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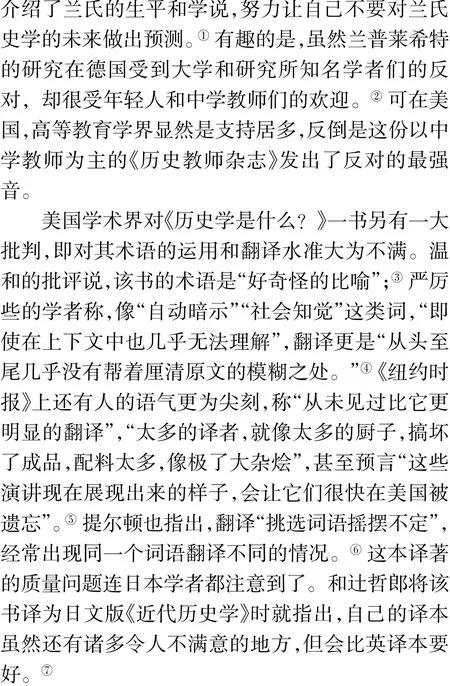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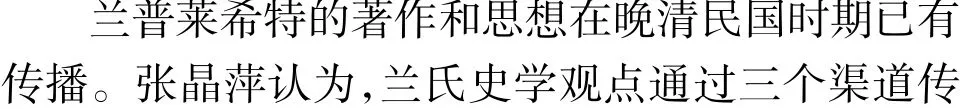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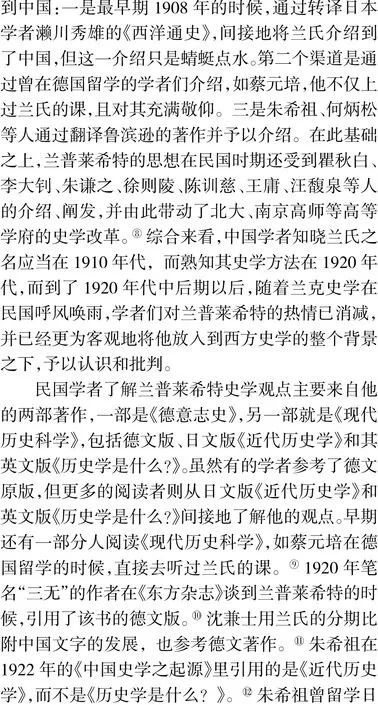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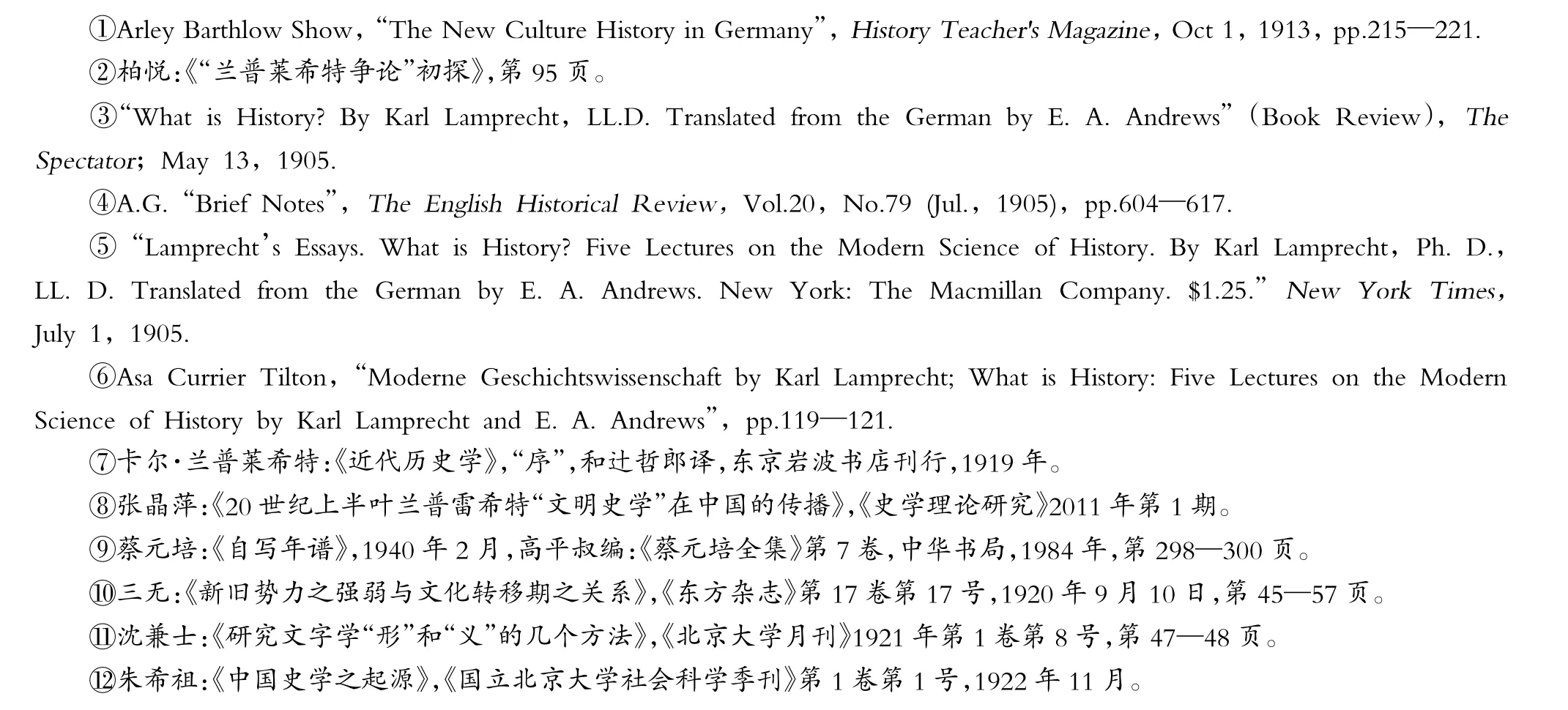
但無論是蘭普萊希特還是與他一起進(jìn)入中國的美國“新史學(xué)”流派,其學(xué)術(shù)思想在民國時期并沒有一枝獨(dú)秀,它始終與考證派共存,甚至可以說,考證派在民國時期的影響力要遠(yuǎn)遠(yuǎn)大于“新史學(xué)”流派,并形成了一時的學(xué)術(shù)風(fēng)氣,成為王晴佳筆下具有“學(xué)術(shù)美德”的典范。⑧王晴佳:《美德·角色·風(fēng)氣:清末到五四學(xué)術(shù)思想變遷的一個新視角》,《社會科學(xué)研究》2020 年第3 期。胡適是開創(chuàng)這種新的“學(xué)術(shù)美德”的人物,雖然畢業(yè)于哥倫比亞大學(xué),但他顯然并未服膺于母校的“新史學(xué)”,如果說胡適是個人興趣所致,那么蔡元培和何炳松這兩個早期就積極宣傳蘭普萊希特和魯濱遜《新史學(xué)》的人物也支持考證派,就變得令人匪夷所思了。特別是何炳松,早在1924 年就出版了《新史學(xué)》,他卻幾乎于同時對胡適的考證大加贊賞。在德國和西方史學(xué)中幾乎勢不兩立的史學(xué)流派,在民國時期居然可以得到同一撥人的支持。在民國學(xué)人的眼里,考證和新史學(xué)是不可相容的兩種史學(xué)方法嗎?他們真的理解雙方背后的爭執(zhí)嗎?蔡元培和何炳松等人是混沌的繼承者、調(diào)和者,抑或僅僅是西方史學(xué)的“拿來”者?無論是何種立場,蔡、何等人的模棱兩可在很大程度上模糊了蘭克史學(xué)與蘭普萊希特史學(xué)在西方史學(xué)上的先后順序,弱化了后者對前者的批判和試圖從前者中走出來的時代思想背景,正是這種模糊不清為“考證派”在民國現(xiàn)代史學(xué)中的興起奠定了基礎(chǔ),使得部分民國學(xué)人結(jié)合清代的考據(jù)學(xué)傳統(tǒng),按照自己的需要建立了中國的現(xiàn)代史學(xué)。
與蔡元培和何炳松等人的調(diào)和不同,朱謙之旗幟鮮明地反對“考證派”。雖然他并不同意蘭普萊希特的全部觀點(diǎn),但他支持蘭氏等人提出的現(xiàn)代“實(shí)證史學(xué)”。朱謙之是1949 年以前對其著墨最多、研究最為深入的中國學(xué)者。他的觀點(diǎn)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diǎn):
第一,蘭普萊希特的社會心理史學(xué)來自于孔德。朱謙之在《孔德的歷史哲學(xué)》中表示,他非常認(rèn)可伯倫漢(他稱之為鮑恩韓)和伯里(John B. Bury,他稱為布雷)的評價(jià),認(rèn)為蘭氏在《德意志史》中就已經(jīng)“包含了孔德的根本思想”,并不是全新的創(chuàng)造。雖然蘭氏自己特意否認(rèn)孔德對他的方法論的貢獻(xiàn),但在朱謙之看來,蘭氏毫無疑問繼承了孔德的心理學(xué)說和文化比較的方法。⑨朱謙之:《孔德的歷史哲學(xué)》,商務(wù)印書館,1941 年,第70 頁。
第二,朱謙之并不認(rèn)可蘭普萊希特劃定的文化階段說,而是更加看重從社會心理的角度去分析歷史。他認(rèn)為蘭氏的文化階段說不過是《德意志史》一書的結(jié)構(gòu)框架,是否能作為德意志史的歷史分期還有待驗(yàn)證,至于它將會成為世界各文化的普遍文化發(fā)展階段,更經(jīng)不起推敲。也就是說,朱謙之雖然很欣賞從社會心理的角度去探討歷史,但對蘭氏提出的階段論的普遍性充滿質(zhì)疑。而且,朱謙之還提出,社會心理也是歷史發(fā)展的動力,對于這一點(diǎn),蘭氏關(guān)注得不夠,因此,社會心理史研究還需要從方法論上加以改進(jìn)。⑩朱謙之:《孔德的歷史哲學(xué)》,第72 頁。有關(guān)孔德對朱謙之的影響以及朱否定文化階段論這兩點(diǎn),參閱張晶萍:《20 世紀(jì)上半葉蘭普雷希特“文明史學(xué)”在中國的傳播》。雖然朱謙之對于蘭氏的文化階段說頗多微詞,也不認(rèn)可德國文化階段的普世性,但他并未否認(rèn)每種文化都有自己的階段。朱謙之較為推崇孫中山提出的“經(jīng)濟(jì)發(fā)達(dá)階段說”,即“經(jīng)濟(jì)心理階段上的需要時代、安適時代、繁華時代”,認(rèn)為這種分期“將經(jīng)濟(jì)發(fā)達(dá)階段還原于物質(zhì)的條件,又將物質(zhì)的條件還原于心理的條件”,這是一大貢獻(xiàn)。①朱謙之:《歷史學(xué)派經(jīng)濟(jì)學(xué)》,商務(wù)印書館,1931 年,第312 頁。
第三,朱謙之贊同蘭普萊希特的世界視野。盡管他質(zhì)疑德意志文化分期的普世性,但非常贊賞蘭氏把史學(xué)的視野從民族史轉(zhuǎn)向世界史。當(dāng)他看到其把日本歷史和德國歷史相提并論的時候,朱謙之的內(nèi)心充滿了希望,認(rèn)為中國也能通過類似的方法獲得進(jìn)入世界歷史的資格。②朱謙之:《歷史哲學(xué)大綱》,明智書局,1933 年,第247 頁。不過,這種想法無論對于蘭普萊希特,還是對于朱謙之而言,都充滿了矛盾和緊張。蘭氏的世界視野明顯基于其強(qiáng)烈的民族主義和德意志精英文化立場之上,他在一戰(zhàn)前夕還執(zhí)著于世界主義的理想,但一戰(zhàn)伊始,他又急于為德國的民族主義辯護(hù);而對于朱謙之來說,他從世界性的虛無主義收縮至民族主義,在世界與民族之間不斷搖擺,也未必能意識到蘭氏思想本身具有的矛盾性。
第四,朱謙之認(rèn)為現(xiàn)代史學(xué)應(yīng)當(dāng)走蘭普萊希特“考今”和“實(shí)證主義”的道路。早年的朱謙之是一位著名的虛無主義無政府主義者,主張打破一切,“我”就是宇宙間的唯一,這種思想是他對現(xiàn)實(shí)政治憤懣、不滿的寫照,也使他從思想情感上就遠(yuǎn)離了“考據(jù)派”。朱謙之的虛無主義、無政府主義一直維持到他的愛人楊沒累生病,他才部分地服從于現(xiàn)實(shí)政治,來到黃埔學(xué)校擔(dān)任政治教官。但即使從“象牙之塔”中走出來,他注重的仍然是“現(xiàn)代的思潮和事實(shí)”,黃埔的生活使他重新感受到五四時期解決現(xiàn)實(shí)問題的蓬勃向上的精神。③朱謙之:《奮斗廿年》,收入《朱謙之文集》第1 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 年,第66—67 頁。這種以歷史探索當(dāng)下的思想,在抗戰(zhàn)以后表現(xiàn)得更為明顯。在《考今》一文里,朱謙之猛烈地批判抗戰(zhàn)以前“考據(jù)派”埋頭學(xué)術(shù)、不問世事的做法。在他看來,為一事、一物做詳盡的考古、考據(jù)對民族和國家都沒有任何益處,在國破家亡的時候,歷史學(xué)家應(yīng)當(dāng)從歷史中綜合得出歷史發(fā)展的規(guī)律,理解中國的歷史何以走到了當(dāng)下。④朱謙之:《卷首語·考今》,《現(xiàn)代史學(xué)》1942 年第5 卷第1 期。可以說,像李大釗否定歷史是“考證零零碎碎的事實(shí)為畢”一樣,⑤李守常:《史學(xué)要論》,第23 頁。朱謙之從一開始就明確了自己支持“實(shí)證主義”史學(xué)的立場,他是中國現(xiàn)代“實(shí)證主義”史學(xué)發(fā)展中的重要一環(huán)。
結(jié) 語
蘭普萊希特和他的《現(xiàn)代歷史科學(xué)》《歷史學(xué)是什么?》是考證史學(xué)向綜合性的“新史學(xué)”轉(zhuǎn)變的關(guān)鍵環(huán)節(jié)。這個環(huán)節(jié)在世界各國的反應(yīng)如此不同,德國要到二戰(zhàn)以后才正式走出蘭克考證學(xué)術(shù)的影響,美國則早在20 世紀(jì)初就在吸收批判蘭普萊希特的基礎(chǔ)上形成了自己的“新史學(xué)”。雖然20 世紀(jì)上半葉的中國學(xué)術(shù)界已經(jīng)介紹過蘭普萊希特的學(xué)術(shù)觀點(diǎn),也指出過他與蘭克學(xué)派之間的對立,但在本土的考據(jù)派和實(shí)證主義派之間,顯然沒有形成德國那樣的史學(xué)張力和沖突,更多的是妥協(xié)和調(diào)和。支持蘭普萊希特史學(xué)觀的人中,有各種不同政治傾向的學(xué)人,但總體而言,持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思想的學(xué)人更傾向于認(rèn)可其“實(shí)證主義”史學(xué),可以說,蘭氏的“社會心理”史學(xué)是“實(shí)證主義”史學(xué)在中國被接受過程中的重要一環(huán)。在抗戰(zhàn)爆發(fā)以后,類似朱謙之這樣的學(xué)人更加意識到考據(jù)不能救國,更傾向于從歷史發(fā)展中去尋找規(guī)律。歷史迫使他們回到蘭普萊希特,又越過他,從“社會心理”轉(zhuǎn)向“物質(zhì)基礎(chǔ)”,并在“世界歷史”和“民族歷史”之間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