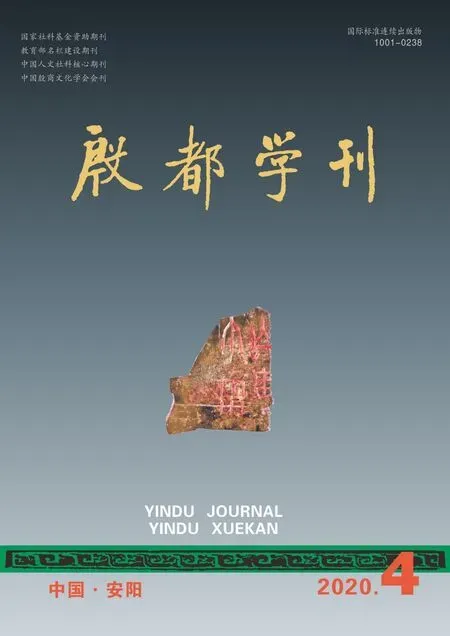焦循的通學觀念及其詩經小學研究
康國章
(安陽師范學院 文學院,河南 安陽 455000)
焦循(1763 —1820),字里堂,江蘇甘泉(今揚州黃玨)人,嘉慶六年(1801)舉人,《清史列傳》卷六十九《儒林傳下二·焦循》載其事跡云:“既壯,雅尚經術,與阮元齊名。元督學山東、浙江,俱招循往游。……經史、歷算、聲音、訓詁,無所不精。”[1]一應禮部試不第,即閉門著書。葺其老屋,稱之為“半九書塾”;復構“雕菰樓”,為讀書之所。嘉慶庚辰七月而卒,年五十八。
焦循的曾祖父、祖父、父親,世傳《易》學,他曾與著名學者王引之討論《易》學,引之以為鑿破混沌。焦循在《易》學研究方面著有《易通釋》20卷、《易圖略》8卷、《易章句》12卷,合稱《易學三書》,共40卷。《易》學之外,焦循最為看重《孟子》,著有《孟子正義》30卷,《清儒學案》卷一百二十《里堂學案》云:“里堂與阮文達同學,經學算學并有獨得,百家無所不通,《易學三書》及《孟子正義》皆專家之業。”[2]焦循精心鉆研古書注解之學,著成《周易王氏注補疏》2卷、《尚書孔氏傳補疏》2卷、《毛詩鄭氏箋補疏》5卷、《春秋左傳杜氏集解補疏》5卷、《禮記鄭氏補疏》3卷、《論語何氏集解補疏》2卷,合稱《六經補疏》。個人文集方面,焦循“手訂者,曰《雕菰樓集》二十四卷”[3];復有《里堂家訓》2卷。焦循學問浩博,據張舜徽《清代揚州學記》考述,“焦循一生著述,已刻、未刻之書,登錄了五十九種”[4]。
一、焦循的通學觀念
1.焦循通學觀念的特質
揚州學派為學宏闊,具有圓通廣大的氣象,張舜徽《清儒學記》云:“余嘗考論清代學術,以為吳學最專,徽學最精,揚州之學最通。無吳、皖之專精,則清學不能盛;無揚州之通學,則清學不能大。”[5]焦循世傳學業,長年勤學深思,刻苦鉆研,學術素養深厚。同時,他曾心懷敬意地向年輩稍長的錢大昕、程瑤田、段玉裁、王念孫等著名學者致信,虛心求教,且有幸與阮元、王引之、汪中、凌廷堪等學術名家保持交游關系。以上諸種人生際遇,加之個人因素,造就焦循一生既擁有卓越的學識,又具備宏闊的規模。阮元為焦循作傳,徑直稱其為“通儒”,其《研經室二集·通儒揚州焦君傳》云:“君善讀書,博聞強記,識力精卓,于學無所不通。著書數百卷,尤邃于經。于經無所不治,而于《周易》《孟子》專勒成書。”[6]博學通識僅是焦循學術精神的一個層面,作為“通儒”,更重要的是他在治學上不偏蔽、不局隘,張舜徽先生說:“究竟他的所以夠得上稱為‘通儒’者何在?值得我們探索。一方面,固然由于他的學問很博通,知識范圍很廣泛;而更重要的,在于他的識見卓越,通方而不偏蔽;規模宏闊,匯納而不局隘。在乾嘉學者中,不愧為杰出的第一流的人物。”[7]
2.焦循通學觀念的學術淵源
焦循的通學觀念,根源于他對孔子“一以貫之”的深入思考,其《一以貫之解》云:“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忠恕而已矣。’然則一貫者,忠恕也。忠恕者何?成己以及物也。孔子曰:‘舜其大知也矣。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孟子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于人以為善。’舜于天下之善,無不從之,是其一以貫之。”[8](P132)他在《論語通釋·釋異端》中說:“惟圣人之道至大,其言曰‘一以貫之’,又曰‘焉不學,無常師’,又曰‘無可無不可’,又曰‘無意、無必、無固、無我’,異端反是。孟子以楊子‘為我’、墨子‘兼愛’、子莫‘執中’為執一而賊道。執一即為異端,賊道即斯害之謂。楊、墨執一,故為異端。孟子猶恐其不明也,而舉一‘執中’之子莫。然則凡執一者皆能賊道,不必楊、墨也。圣人一貫,故其道大。異端執一,故其道小。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致遠恐泥’,即恐其執一害道也。惟其異,至于執一,執一由于不忠恕。……執其一端為異端,執其兩端為圣人。”[9]博學通識,一以貫之,執其兩端,方能成為圣人;偏執其一,思想狹促,勢必走向異端。異端偏執于一,而圣人忠恕,能夠趨時,能夠貫通“執中”“為我”“兼愛”為一,焦循在《攻乎異端解下》中說:“楊子惟知為我,而不知兼愛;墨子唯知兼愛,而不知為我;子莫但知執中,而不知有當為我、當兼愛之事。楊則冬夏皆葛也,墨則冬夏皆裘也,子莫則冬夏皆袷也。趨時者,裘、葛、袷皆藏之于篋,各依時而用之,即圣人一貫之道也。使楊思兼愛之說不可廢,墨思為我之說不可廢,則恕矣,則不執一矣。圣人之道,貫乎為我、兼愛、執中者也。”[8](P136)
3.焦循述圣眼界的宏闊
經學的本質在于述圣,在于貫通千家著述,從中參悟出立身經世之法,焦循在《與孫淵如觀察論考據著作書》中說:“經學者以經文為主,以百家、子史、天文、術算、陰陽、五行、六書、七音等為之輔。匯而通之,析而辨之,求其訓故,核其制度,明其道義,得圣賢立言之指,以正立身經世之法。以己之性靈,合諸古圣之性靈,并貫通于千百家。”[8](P213)經學有漢學、宋學之分,時人普遍存在著尊漢排宋傾向,這樣的做法實際上是偏離述圣目標的,焦循在《述難四》中說:“‘吾述乎爾,吾學孔子乎爾’,然則所述奈何? 則曰:‘漢學也。’嗚呼!漢之去孔子,幾何歲矣?漢之去今,又幾何歲矣? 學者,學孔子者也。學漢人之學者,以漢人能述孔子也。乃舍孔子而述漢儒!漢儒之學,果即孔子否邪……學者述孔子而持漢人之言,惟漢是求,而不求其是。于是拘于傳注,往往捍格于經文,是所述者漢儒也,非孔子也。而究之漢人之言,亦晦而不能明,則亦第持其言而未通其義也,則亦未足為述也。且夫唐宋以后之人,亦述孔子者也。持漢學者,或屏之不使犯諸目,則唐宋人之述孔子,詎無一足征者乎? 學者或知其言之足征,而取之又必深諱其姓名,以其為唐宋以后之人,一若稱其名,遂有礙乎其為漢學者也。噫,吾惑矣!”[8](P104-105)盲目尊漢排宋固不可取,簡單轉述漢人文辭而不深究其意就更為違舛了。
4.焦循解經的小學精神
欲洞察漢代人解經的真實面貌,進而窺知圣人之旨,須臾也離不開訓詁的方法。乾嘉學派的代表人物戴震在《題惠定宇先生授經圖》中說:“夫所謂理義,茍可以舍經而空憑胸臆,將人人鑿空得之,奚有于經學之云乎哉?惟空憑胸臆之卒無當于賢人圣人之理義,然后求之古經;求之古經而遺文垂絕、今古懸隔也,然后求之故訓。故訓明則古經明,古經明則賢人圣人之理義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10]焦循對于訓詁之學的追求,亦在于通達,他在《復王侍郎書》中說:“向亦為六書訓故之學,思有以貫通之,一滌俗學之拘執。用力未深,無所成就。阮閣學嘗為循述石臞先生解‘終風且暴’為‘既風且暴’,與‘終窶且貧’之文法相為融貫。說經若此,頓使數千年淤塞一旦決為通渠。后又讀尊作《釋辭》,四通九達,迥非貌古學者可比。”[11]為此,焦循特別反對那些號稱“考據”而執一害道的人,他在《里堂家訓》中說:“近之學無端而立一考據之名,群起而趨之。所據者漢儒,而漢儒中所據者又唯鄭康成、許叔重,執一害道,莫此為甚。許氏作《說文解字》,博采眾家,兼收異說;鄭氏宗《毛詩》,往往易《傳》。注《三禮》列鄭大夫、杜之春之說于前,而以玄謂按之于后;《易》辨爻辰,《書》采地說,未嘗據一說也。且許氏撰《五經異義》,鄭氏駁之語云‘君子和而不同’,兩君有之。不謂近之學者,專執兩君之言,以廢眾家,或比許鄭而同之,自擅為考據之學,余深惡之也。”[12]
二、焦循《詩》學著作考述
在《詩》學研究方面,焦循著有《毛詩草木鳥獸蟲魚釋》《陸氏草木蟲魚疏疏》《毛詩地里釋》《毛鄭異同釋》《毛詩補疏》(一名《毛詩鄭氏箋補疏》)等著作。
1.《毛詩草木鳥獸蟲魚釋》
焦循六歲習讀《毛詩》,自乾隆四十六年(1781)前后開始創稿,至嘉慶四年(1799),前后歷經19年,六易其稿,終成《毛詩草木鳥獸蟲魚釋》12卷,其《敘》云:“辛丑、壬寅間,始讀《爾雅》,又見陸佃、羅愿之書,心不滿之,思有所著述,以補兩家之不足,創稿就而復易者三。丁未,館于壽氏之寉立堂,復改訂之。至辛亥,改訂訖,為三十卷。壬子至乙卯,又改一次,未愜也。戊午春,更芟棄繁冗,合為十一卷;以考證《陸璣疏》一卷附于末,凡十二卷。蓋自辛丑至己未,共十有九年,稿易六次。以今之所訂,視諸草創之初,十不存一。”[13]
2.《陸氏草木蟲魚疏疏》
《陸氏草木蟲魚疏疏》原附于《毛詩草木鳥獸蟲魚釋》,又單獨成冊,分上、下兩卷。乾隆五十九年(1794),焦循在《陸氏草木蟲魚疏疏·卷上》記曰:“余以元恪之書既殘闕不完,而后世為是學者復不能精析,因撰《草木鳥獸蟲魚釋》。既成,又據毛晉所刻之本,參以諸書,凡兩月而后定,附之卷后。有未備,閱者正焉。乾隆甲寅仲冬月,江都焦循記。”[14]
3.《毛詩地里釋》
乾隆五十二年(1787),焦循在揚州壽家私塾授徒,有感于王應麟《詩地理考》瑣雜難通,因而考之,成《毛詩地里釋》,嘉慶八年(1803)自序云:“乾隆丁未,館于壽氏之鶴立堂,偶閱王伯厚《詩地里考》,苦其瑣雜,無所融貫,更為考之。迄今十七年,未及成書。今春家處,取舊稿刪訂其繁冗,錄為一冊。凡《正義》所已言者,不復臚列。又以杜征南撰《春秋集解》兼為土地名氏族譜,以相經緯,《隋書·經籍志》譜系次于地理,而《三輔故事》《陳留風俗傳》與陸澄、任昉之書并列,豈非有地則有人,有人則有事!《小序》《毛傳》中,有及時事者,亦考而說之,附諸卷末,共四卷。……嘉慶癸亥三月朔。”[8](P265-266)是故,該書名曰“地里釋”,實則前三卷考釋地理知識,第四卷考釋“氏族”(即“人物”)。
4.《毛鄭異同釋》
在《毛詩補疏》成書之前,焦循還撰有《毛鄭異同釋》一書,他在《毛詩補疏序》中說:“余幼習《毛詩》,嘗為《地理釋》《草木鳥獸蟲魚釋》《毛鄭異同釋》。”[15]有研究者根據收藏于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焦循手批《十三經注疏·毛詩注疏》之“題記”,考證《毛鄭異同釋》始作于嘉慶三年(1798),該題記云:“省試被落,緣此可以潛居讀書。《毛詩》久欲窮究之,因日間刪訂所撰《草木釋》及《詩地釋》兩書,晚間燈下衡寫毛、鄭、孔之義。”[16-18]解《詩》須先通訓詁,毛《傳》在訓詁上簡約精當,最得詩旨,鄭《箋》較之迂拙,不如毛《傳》,“訓詁之不明,則詩辭不可解。必通其辭,而詩人之旨可繹而思也。毛《傳》精簡,得《詩》意為多。鄭生東漢,是時士大夫重氣節,而溫柔敦厚之教疏,故其《箋》多迂拙,不如毛氏。則《傳》《箋》之異,不可不分也。”(《毛詩補疏序》)[2](P2153)對于孔穎達《毛詩正義》,焦循多有不滿,他于《里堂家訓》卷下云:“余嘗究孔穎達之《毛詩正義》,其闡發《傳》《箋》之同異,往往以同者為異,異者為同,而毛鄭之本意未能各還其趣也。”[19]
5.《毛詩補疏》
嘉慶十九年(1814),焦循刪錄《地理釋》《草木鳥獸蟲魚釋》《毛鄭異同釋》,合為《毛詩補疏》5卷,其《敘》云:“《地理釋》《草木鳥獸蟲魚釋》《毛鄭異同釋》三書,共二十余卷。嘉慶甲戌莫春,刪錄合為一書。戊寅夏,又加增損為五卷,次諸《易》《尚書補疏》之后。”[20]《毛詩補疏》又名《毛詩鄭氏箋補疏》,焦循在《群經補疏自序》中羅列有《毛詩鄭氏箋》之篇,云:“西漢經師之學,惟《毛詩傳》存,鄭箋之,二劉疏之,孔穎達本而增損為《正義》,于諸經最為詳善。然毛鄭義有異同,往往混鄭于毛,比毛于鄭。”[8](P271)
三、焦循詩經小學特質分析
解經上的通達,要訣在于以己意裁定眾說,王引之《經義述聞序》云:“大人又曰:‘說經者期于得經義而已。前人傳注不皆合于經,則擇其合者從之,其皆不合,則以己意逆經意,而參之他經,證以成訓,雖別為之說,亦無不可。必欲專守一家,無少出入,則何邵公之《墨守》見伐于康成者矣。’故大人之治經也,諸說并列則求其是,字有假借則改其讀,蓋孰于漢學之門戶,而不囿于漢學之藩籬者也。”[21]焦循解《詩》,既辨毛、鄭之別,又詳審孔《疏》之是非,兼下己意,于圓通宏闊中彰顯出專精本色。茲主要以焦循的《毛詩補疏》(以下簡稱《補疏》)加以申明。
(一)比較毛鄭異同
比較毛鄭的異同,是焦循解《詩》的核心內容。以下主要按“鄭《箋》申毛”“是毛非鄭”“《箋》義為長”三個方面,舉例而說明之。
1.鄭《箋》申毛
(1)《召南·羔羊》云:“委蛇委蛇。”毛《傳》:“委蛇,行可從跡也。”鄭《箋》:“委蛇,委屈自得之貌。”《補疏》:“循按:‘君子偕老’,《傳》云:‘委委者,行可委曲從跡也。’《箋》‘委曲’二字,正取毛彼《傳》,以解此《傳》‘從跡’二字。”
(2)《衛風·伯兮》云:“甘心首疾。”毛《傳》:“甘,厭也。”鄭《箋》:“我念思伯,心不能已。如人心嗜欲所貪口味,不能絕也。”《補疏》:“循按:厭之訓為飽為滿。‘首疾’,人所不滿也。思之至于首疾,而亦不以為苦,不以為悔,若如是思之而始滿意者,此毛義也。甘心至首疾而不悔,則思之不能已可知。雖首疾而心亦甘,則其思之如貪口味可知。鄭申毛,非易毛也。”

(4)《大雅·皇矣》云:“是伐是肆。”毛《傳》:“肆,疾也。”鄭《箋》:“肆,犯突也。《春秋傳》曰:‘使勇而無剛者肆之。’”《補疏》:“循按:《大明》‘肆伐大商’,《傳》亦以‘肆’為‘疾’,《箋》以《爾雅》‘肆、故,今也’易之。《正義》申毛,引《釋言》‘窕,肆也’,又引《左傳》‘輕者肆焉’,明肆為疾之義。此詩《箋》引《春秋傳》,即《正義》所引。然則以‘突犯’訓‘肆’,正是申毛,非易毛也。隱九年傳‘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文十二年傳‘若使輕者肆焉’,以‘肆’字代‘嘗寇速去’,正是以‘速’明‘肆’,即毛以‘疾’訓‘肆’之義。《正義》既以為異毛,又譏其引《左傳》之謬。蓋先儒互訓之妙,至隋、唐已莫能知。《周禮·環人》疏引文十一年傳注云:‘肆突,言使輕銳之兵,往驅突晉軍。’此注不知何人,蓋賈、服之遺。訓肆為突,古有此義,故鄭以為‘犯突’。”
(5)《大雅·民勞》云:“汔可小康。”毛《傳》:“汔,危也。”鄭《箋》:“汔,幾也。王幾可以小安之乎?”《補疏》:“循按:毛以‘危’訓‘汔’。危可小康,猶云殆可以小康也。‘殆’訓‘危’,亦訓‘幾’。鄭訓‘汔’為‘幾’,正發明毛義也。”
2.是毛非鄭
(1)《周南·螽斯》云:“螽斯羽,詵詵兮。”毛《傳》:“詵詵,眾多也。”鄭《箋》:“凡物有陰陽情欲者,無不妒忌,維蚣蝑不耳。”《補疏》:“循按:《箋》本《序》耳,然審《序》文,‘言若螽斯’自為句,‘不妒忌則子孫眾多’,申言子孫眾多之所以然,非謂螽斯之蟲不妒忌也。《傳》但言眾多,亦無螽斯不妒忌之說。”
(2)《召南·草蟲》云:“亦既覯止。”毛《傳》:“覯,遇。”鄭《箋》:“既覯謂已昏也。《易》曰:‘男女覯精,萬物化生。’”《補疏》:“循按:《易傳》:‘姤,遇也。’‘姤’一作‘遘’,與‘覯’通。故得訓‘覯’為‘遇’。《箋》以‘既見’為‘同牢而食’,以‘既覯’為‘覯精’,毛無此義也。”
(3)《邶風·柏舟》云:“我心匪鑒,不可以茹。”毛《傳》:“鑒,所以察形也。茹,度也。”鄭《箋》:“鑒之察形,但知方圓白黑,不能度其真偽。我心非如是鑒,我于眾人之善惡外內,心度知之。”《補疏》:“循按:茹即謂察形。鑒可茹,我心非鑒,故不可茹。如可察形,則知兄弟之不可據,而不致‘逢彼之怒’矣。《箋》迂曲,非《傳》義。”
(4)《邶風·谷風》云:“湜湜其沚。”毛《傳》:“涇、渭相入而清濁異。”鄭《箋》:“湜湜,持正貌。”《補疏》:“循按:《說文》:‘湜,水清見底。’《傳》言‘清濁異’,以‘湜湜’為‘清’也,無‘持正’義。”
(5)《大雅·綿》云:“文王蹶厥生。”毛《傳》:“蹶,動也。”鄭《箋》:“文王動其綿綿民初生之道。”《補疏》:“循按:生即性也,謂感動虞、芮之性。毛詳述爭田、讓田之事,申此義也。《箋》迂甚。”
3.《箋》義為長
(1)《召南·小星》云:“抱衾與裯。”毛《傳》:“裯,襌被也。”鄭《箋》:“裯,床帳也。”《補疏》:“循按:‘裯’,音通于‘幬’,字從‘周’。周為匝義。又‘裯’之為‘帳’,猶‘惆’之為‘悵’。《箋》易《傳》為長。”
(2)《大雅·生民》云:“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毛《傳》:“相,助也。”鄭《箋》:“謂若神助之力也。”《補疏》:“循按:毛訓‘相’為‘助’,未必如《箋》‘神助’之義。五谷生自天,必待人樹藝之乃生。后稷教民稼穡,是代天以成其能,故云‘相’耳,非謂神助后稷也。”
除上述三種情況外,焦循有時僅對毛、鄭之說各做客觀描述,而不區分其間的優劣。如,《王風·黍離》云:“行邁靡靡。”毛《傳》:“邁,行也。”鄭《箋》:“行,道也。道行,猶行道也。”焦循《毛詩補疏》:“循按:‘行’字之訓,或訓‘往’,《釋名》所謂‘兩足進曰行’也;或訓道路,《左傳》‘斬行栗’,‘行栗’即道上之栗也。《傳》訓邁為行,即是訓行為邁。既言行,又言邁,猶《古詩》言‘行行重行行’耳。《箋》以行字訓道,蓋以邁既為行,則行宜訓道,又恐人誤認,而申言‘道行,猶行道’,與毛義異也。”
(二)駁斥孔《疏》
焦循刪合自己的前期《詩》學著作,名之曰“補疏”,暗含對孔《疏》(《正義》)的強烈不滿。故而,在指摘孔《疏》失誤時,焦循有時措辭甚為激烈。例如:
(1)《周南·兔罝》云:“公侯干城。”毛《傳》:“干,捍也。”鄭《箋》:“諸侯可任以國守,捍城其民。”《補疏》:“循按:此《箋》申明《傳》義,殊無異同。《正義》言鄭‘惟干城為異’非也。”又,《詩》云:“公侯腹心。”毛《傳》:“可以制斷公侯之腹心。”鄭《箋》:“可用為策謀之臣,使之慮無。”《補疏》:“循按:‘制斷公侯之腹心’,即是策謀慮無。《箋》申《傳》,非易《傳》也。《正義》強分別之。”
(2)《召南·采蘩》云:“于以采蘩,于沼于沚。”毛《傳》:“蘩,皤蒿也。于,於。”鄭《箋》:“于以,猶言往以也。執蘩菜者以豆薦蘩葅。”《補疏》:“循按:《傳》訓‘于’為‘於’,在訓‘蘩’為‘播蒿’之下,明所訓是‘于沼于沚’二‘于’字也。然則‘于以’之‘于’何訓,故《箋》申言,‘于以,猶言往以’,訓在‘蘩’字之上。《正義》云:‘經有三于,《傳》訓為於,不辨上下。’《傳》明示‘于’在‘蘩’下,何為不辨乎?”
(3)《召南·行露》云:“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毛《傳》:“不思物變而推其類,雀之穿屋,似有角者。”鄭《箋》:“變,異也。人皆謂雀之穿屋似有角。”《補疏》:“循按:以角穿屋,常也。無角而穿屋,變也。不思物之有變,第見穿屋而推之以尋常穿屋之事,則似雀有角矣。此《傳》《箋》之義也。《正義》云:‘不思物有變,強暴之人,見屋之穿而推其類,謂雀有角。’經言‘誰謂’,無所指實之詞,故《箋》云‘人皆謂’,則非指‘強暴之人’矣。”
(4)《邶風·燕燕》云:“差池其羽。”鄭《箋》:“興戴媯將歸,顧視其衣服。”《補疏》:“循按:《左氏襄二十二年傳》云:‘譬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杜預注云:‘差池,不齊一。’《左傳》之‘差池’,即此詩之‘差池’。下章《傳》云:‘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頏。’‘飛而上曰上音,飛而下曰下音。’即差池之不齊也。蓋莊姜送歸妾,一去一留,有似燕燕之差池上下者。《箋》言‘顧視衣服’,其說已迂,至解‘下上其音’,謂‘戴媯將歸,言語感激,聲有大小’,則益迂矣。《正義》絕無分別。”
(5)《邶風·日月》云:“胡能有定。”毛《傳》:“胡,何;定,止也。”鄭《箋》:“君之行如是,何能有所定乎?”《補疏》:“循按:《正義》云:‘公于夫婦尚不得所,于眾事,亦何能有所定乎?’《傳》《箋》俱無‘眾事’義。”
(6)《邶風·谷風》云:“行道遲遲,中心有違。”毛《傳》:“遲遲,舒行貌。違,離也。”鄭《箋》:“徘徊也。行于道路之人,至將離別,尚舒行,其心徘徊然。”《補疏》:“循按:‘徘徊’申明‘違離’之義。而所以說之者,非也。‘行道遲遲’,即孔子‘遲遲吾行’之義,不欲急行也。所以然者,以‘中心有違’,不欲行也。申為‘徘徊’,是矣。乃又以‘行道’為‘行于道路之人’,則非毛義。《正義》以徘徊為異,而以‘道路之人’云云羼入毛義中,兩失之。”
(7)《衛風·伯兮》云:“焉得諼草。”毛《傳》:“諼草,令人忘憂。”鄭《箋》:“憂以生疾,恐將危身,欲忘之。”《補疏》:“循按:崔豹《古今注》引董仲舒云:‘欲忘人之憂,贈之以丹棘。’《說文》:‘藼,令人忘憂,草也。《詩》曰:焉得藼草。’重文作‘萱’。《文選》注引《詩》作‘焉得萱草’。以‘忘憂’得有‘諼’名,因‘諼’而轉為‘藼’‘萱’。謂‘萱’取義于‘諼’,可也。謂諼草非草名,不可也。《正義》云:‘諼訓為忘,非草名。故《傳》本其意,謂欲得令人善忘憂之草,不謂諼為草名。’不知《傳》言‘令人忘憂’,正指萱草言。若‘諼’僅訓為‘忘’,則忘草為不辭。至于經義,正以憂之不能忘耳。《箋》言‘恐危身,欲忘之’,殊失風人之旨,非毛義也。而《正義》直以‘恐以危身’之說屬諸毛《傳》。”
(8)《周頌·閔予小子》云:“遭家不造。”毛《傳》:“造,為。”鄭《箋》:“造,猶成也。”《補疏》:“循按:《淮南子·天文訓》‘介蟲不為’,高誘注云:‘不成為介蟲也。’是‘不為’即‘不成’。《箋》申毛義,而《正義》以為異,其解毛云‘家事無人為之’,于經義為不達矣。家不為,猶云‘魚不為’‘禾不為’‘黍不為’也。”
(三)精心考證

(2)《邶風·北風》云:“其虛其邪,既亟只且。”毛《傳》:“虛,虛也。”鄭《箋》:“邪讀如徐,言今在位之人,其故威儀虛徐寬仁者,今皆以為急刻之行矣,所以當去以此也。”《補疏》:“循按:‘虛,虛也’,《釋文》云:‘一本作虛,邪也。’此《正義》亦云:‘《傳》質,訓詁疊經文耳,非訓虛為徐。’可知《正義》本作‘虛,徐也。’《傳》以徐訓虛,《箋》讀邪為徐,‘其虛其邪’,猶云‘其徐其徐’。其徐其徐,猶云徐徐,徐徐猶舒舒,故《箋》以為‘威儀虛徐寬仁’也。《爾雅》作‘其虛其徐’。班固《幽通賦》:‘承靈訓其虛徐兮。’‘其虛徐’,即用《詩》‘其虛其徐’,而‘邪’已作‘徐’,在鄭前。毛直以‘徐’訓‘虛’,謂不特‘邪’字是‘徐’,‘虛’字亦是‘徐’。鄭氏則申明之,言‘邪讀為徐’。‘邪’同‘斜’,《說文》斜讀荼。《易》‘來徐徐’,子夏作‘荼荼’是也。馬融解‘徐徐’為‘安行貌’,即此《箋》所謂‘寬仁’也。《淮南子·原道訓》注云:‘原泉始出,虛徐流不止,以漸盈滿。’此‘虛徐’正以‘徐徐’言也。《太玄·戾》:‘初一,虛既邪,心有傾。測曰:虛邪,心傾懷不正也。’王弼解‘徐邪’為‘疑懼’,曹大家解《幽通賦》為‘狐疑’,皆本此。在威儀容止則為寬舒,在心則為遲疑。‘虛徐’之為‘狐疑’,即‘徐徐’之為‘疑懼’。‘徐徐’之為‘安行’,即‘其虛其徐’之為‘寬仁’。于此知虛邪即徐徐,而毛以‘徐’訓‘虛’,實為微妙。若以‘虛’訓‘虛’,成何達詁?《易傳》‘蒙者,蒙也’‘剝者,剝也’,上一字乃卦名,謂卦之名蒙、名剝,即取蒙剝之義,未可援以為訓詁之常例。若謂上‘虛’是丘虛,下‘虛’是空虛,以‘空虛’之‘虛’解‘丘虛’之‘虛’,顧以虛訓虛,曷以分其為丘虛為空虛?毛《傳》宜依《正義》作‘虛,徐也’。《釋文》本作‘虛,虛’,乃訛也。”焦循考證,毛《傳》‘虛,虛也’乃‘虛,徐也’之訛誤,“虛邪”為“徐徐”之義。
(3)《召南·草蟲》云:“喓喓草蟲。”毛《傳》:“草蟲,常羊也。”《補疏》:“循按:庶物之名,非以聲音,即以形狀。《淮南子·地形訓》:‘東南為常羊之維。’高誘注云:‘常羊,不進不退之貌。’《俶真訓》云:‘不若尚羊物之終始。’《漢書·禮樂志》載《郊祀歌》云:‘幡比翅回集,貳雙飛常羊。’又云:‘周流常羊思所并。’顏師古皆訓為‘逍遙’。蓋‘常羊’猶言‘相羊’,‘相羊’者,‘逍遙’之轉聲也。草蟲名常羊,猶熒火名熠燿耳。”焦循釋毛《傳》中的“常羊”為“逍遙”,完全突破了字形的局限,征引文獻之精確、恰當,更是讓人拍案叫絕,可謂得乾嘉考據學因聲求義之精髓矣!
焦循為學通達,他在經學方面取得的成就自然是最為突出的,同時他在文學創作和文學理論研究方面也頗有收獲,陳居淵先生說:“十八世紀的學術界,樸學獨盛。吳派、皖派和以揚州學者為主體的揚州學派以純漢學形式的古文經學研究,籠罩學壇,考據著述如林,人才輩出。他們不僅經學研究有相當的造詣,而且對文學理論和詩文創作也有獨到的見解。他們的學術修養、審美情趣,無不打上樸學的印記。然而豐碩的樸學成果,反將他們的藝術個性淹沒不彰,其中最具代表的莫過于焦循所提出的‘揚花抑雅’的戲劇論和‘形意相合’的時文論的文學思想。”[22](P22-23)樸學的重點和核心固然在于考據,但其精神實質卻在于探求古代文化的真相,所以說小學研究是過程探索而不是終極追求,推明故訓的最終目的還是要理解儒家之道,洞察圣人之意。在先圣那里,道學和文學完全是統一的,所以經學研究也應該充滿“性靈”,焦循在《與孫淵如觀察論考據著作書》中論曰:“循謂仲尼之門,見諸行事者,曰德行,曰言語,曰政事;見諸著述者,曰文學。自周、秦以至于漢,均謂之學,或謂之經學。匯而通之,析而辨之,求其訓故,核其制度,明其道義,得圣賢立言之指,以正立身經世之法。以己之性靈合諸古圣之性靈,并貫通于千百家。著書立言者之性靈,以精汲精,非天下之至精,孰克以與此?……蓋惟經學可言性靈,無性靈不可以言經學。”[22](P313-314)
鑒于上述,在研究焦循詩經小學的過程中,也應該能夠捕捉到有關“性靈”的說法。如,《周南·葛覃》云:“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毛《傳》:“興也。覃,延也。葛所以為絺绤,女功之事煩辱者。施,移也。中谷,谷中也。萋萋,茂盛貌。”鄭《箋》:“葛者,婦人之所有事也。此因葛之性以興焉。興者,葛延蔓于谷中,喻女在父母之家,形體浸浸日長大也。”《補疏》:“循按:《傳》訓‘施’為‘移’,故王肅推之云:‘葛生于此,延蔓于彼,猶女子當外成也。’與《箋》較之,肅義為長。《正義》合鄭于毛,云:‘下句黃鳥于飛,喻女當嫁,若此句亦喻外成,于文為重,毛意必不然。’竊謂此詩之興,正在于重。‘葛之覃兮,施于中谷’,與‘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同興女之嫁。葛移于中谷,其葉萋萋,興女嫁于夫家而茂盛也。鳥集于灌木,其鳴喈喈,興女嫁于夫家,而和聲遠聞也。盛由于和,其意似疊,而實變化。誦之氣穆而神遠。《箋》以‘中谷’為‘父母’家,以‘延蔓’為‘形體浸浸日長大’,迂矣。毛《傳》言簡而意長,耐人探索,非鄭所能及。”《周南·葛覃》一詩極具審美意趣,鄭《箋》擅長禮制考證,卻在旨趣探求方面幾無建樹,所以在解《葛覃》之類的詩篇時常招人不滿,“歐陽修所辨‘安有取喻女之長大哉’實是針對鄭《箋》‘葛延蔓于谷中,喻女在父母之家,形體浸浸日長大也。葉萋萋然,喻其容色美盛也。’”[23]焦循結合文字訓詁,發微《葛覃》一詩比興之奧妙,直指該作“其意似疊,而實變化”的結構美學內涵,并以“氣”“神”之類充滿“性靈”色彩的詞語揭示詩篇的美學價值,一掃漢代人解《詩》的迂腐之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