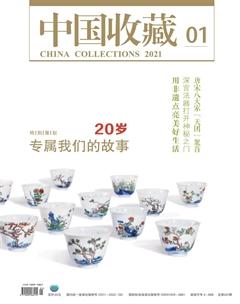文字之交 不忘初衷
謝其章

一想到《中國收藏》雜志創刊已經20年了,心情終歸是頓不平靜的。尤其是翻出了“發稿登記本”之后,往事仿佛發生在昨天,如夢如幻,清晰而模糊。經歷了20年的光陰,沒有被生活磨損了記憶而依舊生機盎然,這個事物本身即有存在的價值。《中國收藏》雜志就是如此。
20多年前,我選擇了自由寫作這個職業。“發稿登記本”是我這些年來寫作的記錄。投稿日期、題目;投給哪家報刊了、哪天發表的;樣報樣刊哪天收到的,稿費哪天收到的……很具體,像一個賬本。雖然自由職業沒人查你的賬,可是自己總要做到心中有數吧。我的所謂自由寫作,與散文小說通常習見的文體有著很大的不同,幾乎完全依托自己的藏書和藏刊,由藏品說開去,那種局限性說起來是很心酸的一種體驗。如果編輯不認可你的寫法,就意味著不會用你的稿子,何來稿費?簡直是個“生與死”的問題。
隨著收藏熱的興起,上世紀90年代以來,各種報刊或開辟收藏版面,或干脆創辦收藏類雜志,雨后春筍般興起的此類報刊,給了我廣闊的寫作園地。《中國收藏》雜志小團隊還同時編輯出版一份《中國商報·收藏拍賣導報》,對于我的寫作能力扶助最多,至今猶銘記在心。寫作總要有個練筆的地方,《中國商報·收藏拍賣導報》接納了我的習作,那是我自由寫作的初級階段。“發稿登記本”上有這些今天看來令我臉紅的文字,比如“1998.9.6《珍愛最是第一聲》”“1998.9.18《珍貴的125期〈集郵〉》”“1999.1.9《小說月報》競拍記”“1999.2.6《城市的特別節目——拍賣會》”“1999.5.1《華于春者實于秋》”等等數十篇。

2001年1月《中國收藏》雜志創刊。面對高端大氣、佳紙彩印的它,最初我不敢投稿,依舊在報紙端寫點豆腐塊文字。過了一段時間,當年的3月7日,我寫了《七十年前,一本畫報的故事》投給了雜志,“發稿登記本”上就有對這次發表文章前后的記錄,旁邊有二行小字:“陳念(當時的編輯,編者注)講有可能往后拖一下4.10”“7月也沒有,6.30”。實際情況是,拙文在當年雜志的9月刊發表了,9月7日我收到樣刊,9月5日收到稿費,這篇稿投得早、登得晚。發表在《中國收藏》雜志的第一稿應該是《燕京古玩數幾家》,4月1目投、6月1日刊出、5月27目收到樣刊、6月5日收到稿費。“發稿登記本”寫到:“陳念又來電話說她補寫了二百字又說上海的沒我寫的好,六月號發。4.12”哈哈,寫的什么我真沒印象了,得翻出舊刊來看看。
不同于報紙,雜志對圖片的要求高得多,這就難住了我。我寫作的資料是舊報刊,成本已經很吃重,當時無力再買高級相機。《中國收藏》雜志寬容待我,2003年8月刊拙文《一個人的十年競拍史》,我給了13張圖片,登記本旁有一行小字:“陳念說這回的圖片不錯5.13”。記得有兩回,我寫的是洋煙畫片和郵票,票面太小,陳念建議拿到編輯部掃描,我顛顛地去了,得虧一小時路程不算太遠。現在都可以宅家搞定、易如反掌。
近年來我想明白了一個道理——像我這種依托個人藏書藏刊的寫法,類似與“補白”或點綴版面的小品文還湊合,不大適應于所謂高端豪華的收藏雜志。傳統的收藏觀念仍然是古書畫、古器物的天下,其中“書”通常專指名人書法。像我所藏近現代期刊雜志,去今不足百年,經濟投資價值低下,容易受到輕視。多年前我曾寫民國老畫報的稿投給另一家收藏類雜志,主編輕蔑地說:“你投給別家吧,我們這不用!”還有廣東的一家雜志,一開始到北京找我約稿,接二連三地用了我七八篇稿子,圖片做得真叫一個漂亮。好景不長,刊物轉型“高大上洋”,不需要文化來點綴了,再投稿就給你個不理睬。
我說這番話的意思是,《中國收藏》雜志20年來同樣在與時俱進,但沒有像其他收藏雜志那樣赤裸裸地“嫌貧愛富”,脫去文化外衣成為富人俱樂部。沒有忘記老作者,惦記著普通的收藏愛好者,這不失為一種不忘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