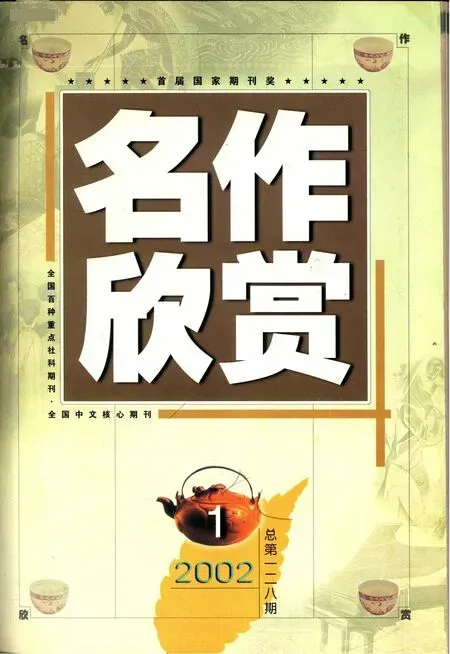《水滸》:安身立命與等待戈多
鮑鵬山
高俅上任的第一天就大發淫威,逼走了八十萬禁軍教頭王進。
那王進可是一個武藝高強的人,讀《水滸》的人都知道林沖很厲害,但是林沖只是八十萬禁軍的槍棒教頭,也就是說他只能教槍棒;而王進則是八十萬禁軍里面的十八般兵器的教頭,所以王進的武功應該在林沖之上。
宋朝本來就武備空虛,北方外敵的壓力巨大。王進這樣的教頭對國家來說實在是難得而又急需的人才,應當好好愛惜才是,但卻被國防部長逼走了。
如果王進不走,下場會更慘。
從王進個人理性上講,他出走,是最佳選擇。
從國家理性上講,王進出走,是最差結果。
作為國防部長,高俅這樣做無異于自毀國家的長城。
一
王進逃走了,去投奔延安府的老種經略相公。他說:“那里是用人的去處,足可安身立命。”這是“安身立命”一詞在《水滸》里的第一次出現,后來魯達、林沖、楊志都說過這個詞。一說一愴然,一說一悲涼。一個有正義感的人,或者只是一個不愿同流合污、不作惡而活著的人,在一個沒有正義的世界,如何安身立命,這是《水滸》的主題,也是人生的命題。
天下人都不過是以一己之才養一己之口,安一己之身,立一己之命。天高地厚,求一安身立命之處而不可得,很多人便只好鋌而走險,為盜為寇。
安身立命不僅僅是有房住,有飯吃,有衣穿,有車開,衣食住行都有了就可以安身立命了嗎?不可以。安身立命,安身立命,安身容易立命難。
安身,衣食住行有了就可以了,但是立命不同。什么叫立命呢?立命是立我們的道德之命,立我們的人性之命,立我們的靈魂之命,這很難。安身立命,必須有以下三個條件:
第一,身安。衣食住行基本無憂,如果你吃了上頓沒下頓,衣衫襤褸,上無片瓦,下無立錐之地,如何能夠安身立命呢?
第二,心安。衣食住行解決了,但是你心安于此處嗎?
第三,理得。有一個詞叫心安理得,什么叫理得呢?就是得理,就是你的生活合乎道德,合乎倫理,這樣才能活得坦坦蕩蕩,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問心無愧。
《水滸》中很多人實際上一開始就不能夠做到身安,比如說阮氏三兄弟,活得很艱苦,打魚都打不到了,所以吳用去勾引他們,讓他們參與打劫生辰綱。他們一下子就答應了,他們求什么?他們首先求的就是大塊吃肉,大碗喝酒,成套穿衣服,論秤分金銀。
但有更多的人,其實是衣食不愁的,比如史進,比如后面的晁蓋、吳用、宋江、柴進等,不僅衣食不愁,甚至活得相當滋潤,但是,他們心不在這里,用《大學》上的話說,叫“心不在焉”,所以就“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還是不能安身立命。
王進比較特殊,與后來的林沖有點像。他本來有很安逸的生活和很高的社會地位,是東京八十萬禁軍的教頭,本來很是心安理得,所以很有安身立命的感覺。但是被高俅威逼,地位不保,乃至于有性命之憂,于是他連身安也沒有了,便只好一路往西,去延安府投奔老種經略相公。
在路上,經過史家村,碰到史進,被史進的父親史太公挽留,教史進武功,半年以后,史進的十八般武藝一一都學得精熟,件件都得了奧妙,王進就要辭別,繼續上路去延安府找老種經略相公去。史進要挽留師父王進在他家里,給他養老。王進說:在這兒養老,當然是十分之好,但是只恐高太尉追捕來,連累了你,我還是一心要去延安府投奔老種經略相公處。那里鎮守邊庭,用人之際,足可以安身立命。
史進家產富足,養活王進母子不成問題。王進為什么不愿意?因為缺少安身立命的第二個條件:心安。
王進讓史進給自己養老,他心安嗎?當然不安他明說是怕高俅追來,連累了史進。其實主要原因就是:一個人,尤其是大丈夫,有一身本事的英雄,怎么能就這么樣收拾起雄心壯志,安心養老呢?一頭猛虎,愿意潛伏爪牙在動物園里面被養著嗎?
所以,在和史進的這一段話里面,他再一次提到了“安身立命”這個詞。大丈夫安身立命,這身得安在自己的地盤上,這命得立在自己的身手上,不能夠聽命于人。
二
王進走了,一去再無消息。王進的背影是《水滸》留給我們的一大空白。這個空白顯得很奇怪:施耐庵絕不會是因為疏忽才留下這個空白,要知道,細心的施耐庵,對上場的人物絕不會如此絕情,他連林沖丈人張教頭都有后續交代,甚至連董超、薛霸這樣的人渣都有下場,對開篇第一好漢、孝子忠臣,卻如此不明不白撒手不管了?施耐庵一定另有考量。
其實,這個空白處有施耐庵的無奈,也有我們的嘆息。
師父王進走了,不久父親史太公也死了,史家村的村長就是這十八九歲的史進了,他也是“里正”,“里正”者,正里也,負責村里的秩序、治安和賦稅。
而史家村附近的少華山有三個強盜:神機軍師朱武、跳澗虎陳達、白花蛇楊春。你看這三個人,又是神,又是虎,又是蛇,是不是覺得這又是一個龍虎山呢?——龍虎山,《水滸》開卷第一回“張天師祈禳瘟疫,洪太尉誤走妖魔”里面出現的山,是《水滸》里寫的第一座山,而少華山則是第二座——這兩者之間,有著玄妙的呼應。你自己去想吧。
負責村里治安的史進,按說和山上的強盜是對頭,一開始他們也確實是對頭,但是一來二去,他們反而成了兄弟,暗中來來往往,最終被官府發覺。史進為了脫身,一把火燒了莊園,與三人逃到了少華山上。
史進本來在自家莊園可以安身立命,不但自己可以安身立命,還想留住師父王進也在此安身立命。但是,此刻他安身立命的第一個條件就沒了:沒有了莊園,衣食住行都成了問題,不用說立命,身都沒法安了。
當然,還有少華山。少華山上的朱武等三人也要請他做寨主。按照朱武的說法,沒了史家村,少華山照樣可以活得很快活。但問題是:這是一個能立命的地方嗎?
不是所有的強盜山都可以安身的:二龍山,在鄧龍的手下,魯智深就不能安身;梁山,在王倫時代,林沖就不能安身。
還有,有些山固然可以安身,但未必能立命。梁山,在晁蓋的時代,就可以安身,而不能立命。為什么?因為沒有理由,不能安心。
只有到了宋江的時代,打出“忠義”的旗號,一百零八人,就可以立命了。
這就要回到我們剛才講到的安身立命的第三個條件,這個條件是“理得”,也就是說,在山上當強盜,打家劫舍,吃香的喝辣的,你覺得心安理得嗎?天下有這樣快樂的道理嗎?打家劫舍,殺人放火,搶奪別人的財產,殺死別人的生命,然后自己享受,這種快樂生活是合理的嗎?
所以史進不愿意。后來很多被迫上梁山的人,比如那些來自朝廷的降將,也不愿意。
史進說,我要找我的師父,也要到邊疆為國效力,討個出身,然后半世快樂。
史進對朱武說:“你勸我落草,你再也休提。”這話何等嚴肅,何等義正詞嚴,史進要的是一個清清白白的快活,只有清清白白,才是真正的安身立命。
只是史進不知道,在渾濁的世道,一個人,要清清白白地安身立命,卻是十分之難。一百零八人正是因為不能夠“身安”才上了梁山,上了梁山正因為不能夠“心安”才打出“忠義”的旗號,下山招安。按說這樣,“理得”了,但結局呢?最終七零八落,七死八傷。
三
當初師父王進無路可走,要投奔延安府,現在史進又無路可走,要投奔王進這個自己也無路可走的人。當初史進要留師父在莊上,為他養老,師父覺得這不是一個了,走了。現在朱武要留史進在山上,一起打家劫舍,史進還是覺得這不是個了,也還是走了。
《紅樓夢》 “好了歌”,好就是了,了就是好。不好便不了,不了便不好。
人生就是圖個安身立命,人生就是圖一個了。
什么叫“了”呢?安了身了,立了命了,就是了。身不安,命不立,就是不了。
但是,求個安身立命的了往往不可得,于是人們往往是抬起腳“走了”。王進走了,史進走了。走了,走了,就是以走為了。但是,走就能了嗎?
人生誰不愿意安歇,人生誰又不在路上呢?很多人都是以走為了,我們現在把它稱之為逃避。不是我們不敢面對,不是我們軟弱,而是如果我們不走,此刻就不得了。
高俅陷害王進,王進不得了,只好以走了之。
史進要留王進,王進覺得還是不了,還是一走了之。
現在朱武要留史進,史進也覺得這樣下去不是一個了,還是以走了之。
走,只是換一個姿勢,把此刻了了。至于接下來還有什么,先就不去想了。但是煩惱就像影子一樣,你無法拋開得了。
王進自家就是一個不得安身立命的人,漂泊江湖,不知如何是了。沒有想到,他反而成了史進的依靠,成了史進安身立命的寄托,史進以為找到王進,就可以了了。其實,即使找到王進,又能了什么?
想想這些,是不是很悲涼,又很荒誕?
讀《水滸》,讀到史進離開少華山,要找他的師父王進,不知道為什么,我就覺得鼻子發酸。一個十八九歲的小青年,師父走了,父親死了,莊園燒了,只有他沒有個了,他的世界沒了。什么叫“沒了”?沒了不是消失,而是沒完沒了——世界處處都把他了了,他卻兀自未了,慌慌張張,惶恐無地。茫茫大宋,滾滾紅塵,他在這個世界上唯一的希望就是那個走遠了的、在江湖中杳無音訊的王進師父。我們可以看出他對這個師父的感情,這種感情現在成了他唯一的依托,這種感情是這個世界最后的溫暖——這溫暖,不是世界給他的,是他自己內心殘存的。我們知道,一個人如果落入冰冷的大海,他自救生存的第一要務,是蜷縮身體,夾緊腋窩和大腿,保持自己心臟的溫度。史進此刻,他心中對師父的感情,就是他心臟最后的溫暖。
他哪里是找師父呢,他實際上是在找他失去的世界、失去的溫情。他能找得到嗎?
四
愛爾蘭現代主義劇作家貝克特,在1953 年首演了一部荒誕派戲劇《等待戈多》。
《等待戈多》的劇情是,兩個流浪漢苦等一個叫作戈多的人,但是戈多不來,等不到。其中有一句著名的臺詞:希望遲遲不來,苦死了等的人。
貝克特寫《等待戈多》,施耐庵寫尋找師父。
貝克特其實不是在等待戈多,史進其實也不是在尋找師父;貝克特在等待希望,史進在尋找方向。但戈多是等不來的,師父也是尋不到的。
史進找師父是一個寓言,是一個象征,象征著我們終身有目的而沒有方向的尋找,最終往往一無所獲。
人生最大的痛不是我們沒有目標,而是有了目標,卻不知道方向。于是我們看起來一直在尋找,其實是一直在瞎撞。最痛的是:我們知道自己不過是在瞎撞。
戈多等不來,師父找不到。
等不到的戈多才是戈多,找不到的師父才是師父。
意義不在“等”和“找”里,而在“等不到”和“找不到”里。
等待戈多,這四個字里面,實際上“戈多”不是關鍵詞,關鍵詞是什么?是“等待”。貝克特告訴我們,當我們無能為力的時候,我們只有等待,只要我們還在等待,還在期待,戈多就在,希望就在。
不是因為戈多在,我們才等。而是因為我們在等,戈多才在。
不是因為戈多會來,我們才等,而是因為我們在等,戈多才可能來。
一旦我們放棄不等了,戈多就消散在遙遠的空氣中。
這看似荒謬,其實這才是生活真正的邏輯。
同樣,施耐庵寫王進尋找師父,師父也不是關鍵,也不是意義,意義是什么?是尋找。
施耐庵在告訴我們,當我們手足無措的時候,我們只有尋找,只要我們還在尋找,還在探求,師父就在,方向就在。在《水滸》的敘事里,只要史進還在尋找,我們就覺得王進在。后來史進終于不找了,和魯智深說,要回少華山了,我們也就徹底把王進放下了——《水滸》的后文,再也沒有了王進。我們對他,也不再有惦記。
史進在當下時空一放棄,王進就在另一個時空煙消云散。
當我們對一個人絕了念想,他也就徹底消失。
所以,虛幻的希望,也勝過絕望。魯迅怎么說的?“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
魯迅還說過,人生最痛苦的是夢醒了無路可走。等待戈多,尋找師父,不過是讓自己覺得有路可走而已。
施耐庵寫史進的尋找,很讓人傷感:“史進一路上饑餐渴飲,夜住曉行,獨自行了半月之上,來到渭州。”“饑食渴飲”“夜住曉行”,何等艱苦。而且,“獨自行了半月之上”,這輕輕落下的“獨自”一詞,有不可名狀的悲涼,有無可言說的寂寞。
人生,都是孤身前行。
王進有行蹤卻無消息,戈多有消息而無蹤影。史進尋找王進,其實就是幾百年前的等待戈多;等待戈多,也就是幾百年后的尋找王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