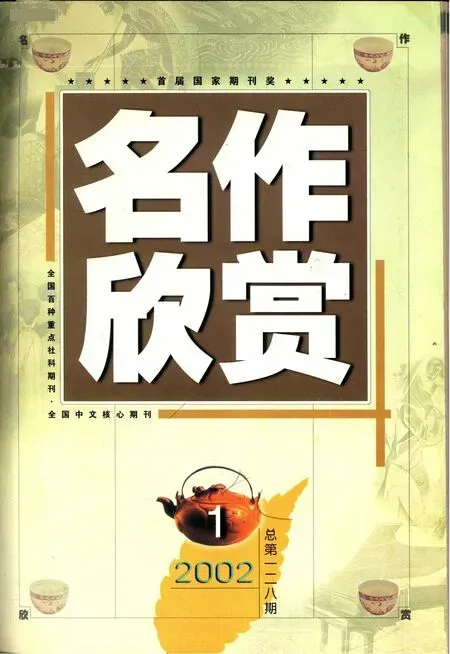千山之祖萬水之源
李元洛
關鍵詞:《詩經》 植物 動物
《詩經》是上古的祖先為子孫后代集體編寫的一部百科全書。它收集了從西周初年至春秋中葉(前11世紀至前6世紀)歷時五百多年的詩歌,分為風、雅、頌三部分,共305篇,先秦時稱其為《詩》,或取其整數名為《詩三百》。它是上古時代社會生活的全息攝影,也是上古時代先民感情的詩意寫真。此書據說經孔子審讀與刪定,但不知由何方授權,也許是他自己當仁不讓吧。關于詩的作用與詩的閱讀,他還有一段權威性的為后人所習傳的指示:“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文,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別的姑且不論,時已遠隔三千年左右,我們今日揭開《詩經》的封面走進去,一路行來,嚶嚶的鳥鳴仍然敲叩我們的耳鼓,燦燦的花光仍然照亮我們的眼睛。這篇讀書筆記,就是我的《詩經》之游,關于植物與動物的記錄,浮光掠影,有如點水的蜻蜓。
《詩經》,不僅是一部上古時代生活的百科全書,而且是中國詩歌史上第一部詩歌總集,尤為重要的是,地分南北,北方的《詩經》與南方后起的《楚辭》,是中國詩歌浩蕩長河的兩大源頭,沒有這兩大源頭的生生不已的永恒活水,就沒有長河的波翻浪涌、耀彩飛光、江聲浩蕩。如同今日的每一個華夏子孫,都一無例外地承傳了先人的血脈,《詩經》之后的古代詩人,有哪一位沒有去源頭捧飲過那清清的醴泉,有哪一位沒有受到過源泉的潤澤呢?我這篇關于《詩經》的讀書筆記,選賞的是《詩經》中的一些描寫、歌詠植物與動物之詩,同時我也會尋來龍去脈,追源探流,分神觀照后代的某些有關詩作。有如蜻蜓的點水,溯洄從之,它點的是源頭,溯游從之呢,它也會順流飛翔,匆匆點閱上游、中游乃至下游的水面和后浪。
混沌初開,乾坤始定。星光爛爛,河水泱泱。草繁木茂,鷹飛魚翔。
《詩經》產生的地域以黃河流域為中心,也就是今天長江以北五省,北括山西、陜西、河北、河南的廣大地域,南抵“漢之廣矣”與“江之永矣”,即漢水與長江的北岸。這一地域的上天下地就是先民的皇天后土,它所構成的自然環境,既是他們賴以生存的依托,也是他們原始審美的對象,同時也是他們詩歌文化的搖籃。他們最熟悉并生息其間的,除了須臾不可分離的洋洋河水,就是四季應運而生的郁郁植物了。清人顧棟高在《毛詩類釋》中就曾說,《詩經》寫到的草有37 種,木有43 種,谷類有21 種,蔬菜有38 種,花果有15 種,而現代學者以科技量化統計研究的結果,《詩經》幾乎將當時的世間萬物都收入其中,至于各類植物,即有144 篇作品共505 次提及,為今日的植物學家提供了最古老的可以皓首窮經的植物圖譜。
我不是植物學家,也非考古學家,我只是一個古典詩歌的當今發燒友,一名古老《詩經》的現代朝香客。且讓我對《詩經》中的植物世界匆匆游覽并信手拈來吧:
“荇”。在上古時代,“河”系黃河之專有名詞,“江”則專指長江,“江河”是長江與黃河的尊稱專利,其他的河流均不得僭越或取而代之。如前所述,《詩經》是中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也是中國文學長河最早的源頭,誕生于黃河之濱的《關雎》,則是源頭最初的波浪。此詩置于《詩經》之首而領袖三百篇,我以為有深意存焉。水,是生命之源泉,也是生存的希望,從古至今的人群,大都是傍水而居,上古單名為“河”而東漢時因河水黃濁而定名的“黃河”,則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黃河流域乃為中華民族文明的主要發源地,因此,《詩經》開篇首倡“在河之洲”就絕非偶然了。此外,在原始的惡劣艱苦的自然條件之下,先民們更重視生息繁衍,他們多有對與勞作結合在一起的愛情的歌唱,以雌雄有固定配偶的水鳥雎鳩的鳴聲起興之《關雎》,就正是如此。它絕非后來的經學家與道學先生所曲解的是什么美“后妃之德也”,而是一首熱烈奔放的愛情之歌,是愛情這一母題最原始的千古絕唱: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
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
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
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參差荇菜,左右芼之。
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這首中國最資深的情詩,留下了諸如“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悠哉悠哉,輾轉反側”等成語,那美麗漢語的原始股兼績優股的語言資源,讓我們世世代代將本生利,享用不盡,而詩中的淑女所“流之”“采之”“芼之”的前后出現了三次的“荇菜”呢?
“荇菜”即“荇”。荇,多年生水生草本植物,花黃而葉呈對生圓形,紫赤色,浮于水上,嫩時可食,亦可入藥、作飼料或化肥。詩中的美麗女子采集它們,應該不是屬于觀賞而是有以實用。然而,《詩經》中關于“采”者,另有《召南·采蘩》《召南·采萍》《王風·采葛》《唐風·采苓》《小雅·采薇》等篇章,何以表現愛情主題的《關雎》所采者偏偏為“荇”?答案是:荇的再生力與繁殖力很強,俗名水荷葉的它在上古是女性生殖的象征,因此,《關雎》一詩不僅表現了先民的水崇拜,也顯示了先民的生殖崇拜,隱喻情事的“荇”在《詩經》的首篇閃亮登場,其中就頗有深意存焉,而絕非偶然了。
在《詩經》之后的古典詩歌中,提及荇的作品數不在少。六朝時丘遲有“巢空鳥初飛,荇亂新魚戲”(《詩》),蕭綱有“荇間魚共樂,桃上鳥相窺”(《春日想上林詩》),唐代歐陽袞有“鹿踐莓苔滑,魚牽水荇沉”(《雨》),崔湜有“雁翻蒲葉起,魚撥荇花游”(《唐都尉山池》),這些詩都是將魚與荇合而寫之,而據聞一多等學者的考證,魚是男根的象征,蓮是女性生殖的象征,而荇葉形態近似于蓮葉,故上述詩句應與《關雎》關系曖昧,魚荇共寫而比喻情愛應是它們所表現的深層潛意識。繼承并傳揚了《關雎》這一縷心香的,還有唐詩人儲光羲的《江南曲》四首,特別是其中前兩首:“綠江深見底,高浪直翻空。慣是湖邊住,舟輕不畏風。”“逐流牽荇葉,緣岸摘蘆苗。為惜鴛鴦鳥,輕輕動畫橈。”至于明詩人楊士奇的“岸蓼疏紅水荇青,茨菰花白小如蓱。雙鬟短袖慚人見,背立船頭自采菱”(《發淮安》),如果能找到他當面問詢,我想他絕不會否認他之這一大作與《關雎》的血緣關系。
除此之外,“荇”在后代的詩歌中作為一個景物鏡頭或一種傳統文化背景,那更是不勝枚舉。杜甫《曲江對雨》中的“林花著雨胭脂濕,水荇牽風翠帶長”,就是寫景的名句;在《紅樓夢》第四十回“史太君兩宴大觀園,金鴛鴦三宣牙牌令”中,薛寶釵對此就曾予以引用評說;“芰裳荇帶處仙鄉,風定猶聞碧玉香”,魯迅的七律《蓮蓬人》贊美的是高潔傲岸的人格與風骨,生長于并喜愛清流潔水的荇,正是全詩主旨的詩意襯托,傳播的也正是遠古的那一脈芬芳。
“葭”。采采流水,蓬蓬遠春。水有多長,詩就有多遠;水有多媚,詩就有多美。《關雎》那古老而青春的愛情故事,發生在荇菜青青的河邊洲畔,而音樂家賀綠汀于20 世紀30 年代作詞譜曲流行一時的《秋水伊人》,當今臺灣鄧麗君所唱的熱門流行歌曲《在水一方》,它們的音韻、詞華和意境,也仍然和那遙遠而又遙遠的另一首民歌一線相牽:
蒹葭蒼蒼,白露為霜。
所謂伊人,在水一方。
溯洄從之,道阻且長。
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萋萋,白露未晞。
所謂伊人,在水之湄。
溯洄從之,道阻且躋。
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
所謂伊人,在水之涘。
溯洄從之,道阻且右。
溯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這首纏綿悱惻而又意境空靈的詩,在西北邊地慨當以慷的秦風中是絕無僅有的異數,在《詩經》中也是十分罕見的另類。清末民初的王國維于《人間詞話》中,將其與“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晏殊:《蝶戀花》)并論,以為它們都“最得風人情致”,而當代的大學者錢鍾書在《管錐篇》里,更遍舉中外作品以證此詩與《周南·漢廣》“二詩所賦,皆西洋浪漫主義所謂‘企慕情境也”。《蒹葭》一詩,除了前人所說的象征主義或浪漫主義情境外,我以為從審美或美的形態而言,它和《陳風·月出》篇一起,是最早表現了朦朧之美的詩,可稱朦朧詩的鼻祖,20 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涌現的熱鬧一時的所謂“朦朧詩”,雖然受到門戶乍啟西風勁吹的影響,但如果認祖尋宗,卻仍然可說是它們的兩千多年后的后裔。《蒹葭》一詩,論者已多,我這里只能言歸正傳,略說詩中的蒹葭。
“蒹”之本意為荻,其形似蘆葦,“葭”即初生的蘆葦,別稱葦、葭葦。“蒹葭”,即多年水生或濕生的蘆葦,多長于河邊澤地之低濕淺水之處。此詩中的蒹葭,寫的是秋日的蘆葦,分章疊韻,分別以大同小異的“蒼蒼”“凄凄”“采采”狀寫它的情貌,以助全詩意境的形成,以及秋日懷人與情愛追尋之主旨的表現。因此,“蒹葭”這一意象本就具有懷人念遠、悲秋傷感的原始意蘊,即中國古典語言中的“葭思”與“蒹葭之思”;而在古典詩歌的發展過程中,它除了充當時令景物的布景角色,更被賦予了漂泊無定、勢弱無依與閑情逸致等多重意蘊,使意象的內涵更為多樣與豐富。這,大約也是上古時那位無名作者所始料未及的吧?如:“蓮渚愁紅蕩碧波,吳娃齊唱采蓮歌。橫塘一別已千里,蘆葦蕭蕭風雨多。”這是晚唐詩人許渾的《夜泊永樂有懷》,風中的蕭蕭蘆葦,搖曳的正是詩人天涯漂泊的別緒離愁。
“摧折不自守,秋風吹若何?暫時花戴雪,幾處葉沉波。體弱春風早,叢長夜霧多。江湖后搖落,亦恐歲蹉跎。”這是杜甫的與《詩經》之作同名的《蒹葭》,詠蒹葭亦是寫自己,寫外物亦是抒內心,多少江湖淪落的身世之感都搖曳在那詠物的一唱三嘆之中。“釣罷歸來不系船,江村月落正堪眠。縱然一夜風吹去,只在蘆花淺水邊。”這是中唐詩人司空曙的《江村即事》,夜泊于蘆花淺水,不知東方之既白,表現的是與杜甫之作迥異其趣的閑情逸致。“搖曳巴陵洲渚分,清江傳語便風聞。山長不見秋城色,日暮蒹葭空水云。”這是王昌齡的《巴陵送李十二》,他寫與李白在岳陽初逢復又言別,全詩以景結情,蒹葭秋晚,云水蒼茫,抒發的是對友人的依依之情與眷眷之意,其語言和意境遙承的正是《蒹葭》的一脈遠香。
當代詠蘆葦的新詩似不多見,但學者楊景龍不僅以《蔣捷詞校注》《花間集注》《中國古典詩學與新詩名家》等著作傳世,也創作了近兩千首新詩而很少示人,我以為他是“五四”以來最杰出的詩人之一,在中國新詩史上應該也將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他竟然也寫有與《詩經》同題之作《蒹葭》,詩分四節:“望穿秋水無渡。/ 大河無涯/ 蒼蒼的蒹葭。/早生華發// 溯洄從之。/ 眉睫白露,頭上霜降/ 溯游從之。/ 寒衣綻開一路霜花// 到了冬天。/ 水面凝成一層堅冰/ 宛在水中央。// 終于可以抵達//所謂伊人。立冬之前已經返家。”全詩的血脈意境乃至某些語詞都源自遙遠的古典,筆下有余香,但全詩卻又是古典的新的現代變奏,新其語言,新其句式與結構,新其立意與寄托,有如《詩經》的出色的和詩,和原玉一樣具有朦朧之美而耐人尋味。
“荷”。在當代的新詩人中,詠荷多而且好的應首推臺灣名人余光中。他在而立之年所寫的懷鄉名篇《春天·遂想起》一詩中,反之復之地詠嘆“江南”,詠嘆“采蓮”,詠嘆“多蓮的湖”,而在20 世紀70 年代之初他年屆不惑時,還出版有詠荷的專題詩集《蓮的聯想》,收詠荷之詩共三十首。其中《滿月下》一詩,開篇即是“在沒有雀斑的滿月下/ 一池的蓮花睡著”,結尾則是“那就折一張闊些的荷葉/ 包一片月光回去/ 回去夾在唐詩里/ 扁扁的,像壓過的相思”,其詩思清新如出水的芙蓉,其詩語清揚如月光的芬芳。猶記1993 年夏日我應邀訪問臺灣,已然遷居高雄多年的余光中帶我去城郊,于有“臺灣西湖”之美譽的澄清湖游覽。澄清湖盛產蓮荷,臺北市區一灣蓮池曾孕育了他寫荷的靈感,澄清湖半湖的荷花當年也薰香了他的詩篇,他都一一收錄在上述《蓮的聯想》這部詩集里。不過,余光中筆下的荷花既是他妙出心裁,同時也仍然其來有自,我們可以追溯約三千年之遠的《詩經》中的有關篇章。
雖然荷花是我國的十大名花之一,然而它卻身世如謎。對化石的研究證實,在一億三千五百萬年以前,北半球即有蓮屬植物的分布,而位于浙江余姚縣的河姆鎮遺址,也曾經發現野生蓮的遺跡以及香蒲荷菱的花粉化石,至今也有七千年的歷史。遠古的歷史已渺焉難尋,然荷花搖曳在《詩經》中的倩影風姿卻宛然仍在,可以驚艷我們的眼睛: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
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山有喬松,隰有游龍,
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鄭風·山有扶蘇》)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
有美一人,傷如之何?
寤寐無為,涕泗滂沱。
彼澤之陂,有蒲與蓮。
有美一人,碩大且卷。
寤寐無為,中心。
彼澤之陂,有蒲菡萏。
有美一人,碩大且儼。
寤寐無為,輾轉伏枕。
(《陳風·澤陂》)
前一首的荷華(花)雖然是起興之詞,但與詩中這位女子心中的美好愛情有關。而《澤陂》呢?聞一多在《風詩類抄》中說“荷塘有遇,悅之無因,作詩自傷”,詩中反復詠嘆的荷花比《山有扶蘇》更進一步,既是環境的描寫、情愫的寄托,也是最早的“以樂景寫哀,以哀景寫樂,一倍增其哀樂”(王夫之:《姜齋詩話》),也即以麗景寫悲情。源遠流長,后代詩人對荷花不盡的描繪詠唱,從遺傳學的角度而言,《詩經》中的荷花提供了上古的基因與血緣。
荷花雖然有許多美麗的別名,如《楚辭》中名“芙蓉”,《說文》中曰“芙蕖”,《群芳譜》則謂“水芙蓉”,此外,還有“菡萏”“水華”“花欲笑”“白羽衣”“佛座須”等諸多芳名雅號。但是,我最喜歡的還是眾生稱她為“翠蓋佳人”。這位佳人不是深閨高閣中雍容浮華的貴婦,而是大自然中青春活潑的與勞動和愛情攜手同行的少女。“涉江采芙蓉,蘭澤多芳草”,“江南可采蓮,蓮葉何田田”,漢樂府的《涉江采芙蓉》與《江南》早就這樣歌唱了,晉代樂府的《青陽渡》也曾經如此詠嘆:“青荷蓋綠水,芙蓉發紅鮮。下有并根藕,上有并頭蓮。”蓮荷雖也開在北國,但尤其在江南盛開,詠蓮荷的詩在唐代更是嫣然怒放,李白的《淥水曲》寫道:“淥水明秋月,南湖采白蘋。荷花嬌欲語,愁殺蕩舟人。”他的友人王昌齡,和他并稱為唐代的超一流絕句高手,李白有如上的五絕,王昌齡則有《采蓮曲》七絕:“荷葉羅裙一色裁,芙蓉向臉兩邊開。亂入池中看不見,聞歌始覺有人來!”兩位高手的高作均是風華絕代,令人銷魂。時至宋代,楊萬里詠荷之作多約二百首,為歷代詩人的冠冕,而其詠荷作品之好,也完全可以與唐代詠荷的上選之作競一日之短長。他的《曉出凈慈寺送林子方》是人所熟知的了,而未被《誠齋集》收錄的遺詩《紅白蓮》也是可圈可點之作:“紅白蓮花開共塘,兩般顏色一般香。恰如漢殿三千女,半是濃妝半淡妝。”荷花香過了唐,香過了宋,香過了元明清,不知香過歷代多少詩人的詩篇。時至清代,“行人系纜月初墮,門外野風開白蓮”,王士禛的名作《再過露筋祠》為白蓮留下了俏麗高潔的身影,而納蘭性德的《一叢花·并蒂蓮》則說:“闌珊玉佩罷霓裳,相對綰紅妝。藕絲風送凌波去,又低頭、軟語商量。一種情深,十分心苦,脈脈背斜陽。 色香空盡轉生香,明月小銀塘。桃根桃葉終相守,伴殷勤、雙宿鴛鴦。菰米漂殘,沈云乍黑,同夢寄瀟湘。”納蘭公子是中國詩歌史上歌唱愛情的絕世高手,前人只有李商隱,后人只有龔自珍,可以和他一較高下,他寫象征情愛的并蒂之蓮絕非偶然,不也是《詩經》詠荷之篇的遙遠的和聲與變奏嗎?
荷不僅是象征愛情的“翠蓋佳人”,在中國人的“比德”的審美過程中,其更獲得了“花中君子”的尊號,成為志行高潔、香遠益清的君子的代名詞。“制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茍余情其信芳”,早在《離騷》之中,屈子就告白他要以荷葉為衣,荷花為裳,他不僅是服裝設計的最早的大師,更是將荷花賦予高潔堅貞人格的開山祖師。曹植是以賦詠荷的先驅,“覽百卉之英茂,無斯華之獨靈,結修根于重壤,泛清流而擢莖”,他的《芙蓉賦》開宗明義就贊揚荷花高潔的品格,其深遠影響,為時人與后人的同題賦作所不及。北宋周敦頤的《愛蓮說》就不用多說了,少為人知的是明代葉受的《君子傳》,其傳主名“君子”,又名“蓮”,復名“菡萏”,字“芙蓉”,葉受完成的是荷花作為“花中君子”的命名禮,其名不揚,其功也大,到他的筆下,荷蓮擁有的已是美女與烈男、陰柔與陽剛的兩極之美。
在古典詩歌中,將荷花作為“花中君子”來贊頌的代不乏人。唐代如高蟾的《下第后上永崇高侍郎》:“天上碧桃和露種,日邊紅杏倚云栽。芙蓉生在秋江上,不向東風怨未開。”晚唐陸龜蒙的《白蓮》:“素蘤多蒙別艷欺,此花端合在瑤池。無情有恨何人覺?月曉風清欲墮時。”宋代因周敦頤《愛蓮說》一文影響廣被,故詩人詠荷之作更多,除楊萬里是詠荷大戶之外,陸游也為數不少,他晚年寫于山陰故里的兩首《荷花》詩就別有寄托,其一是:“風露青冥水面涼,旋移野艇受清香。猶嫌翠蓋紅妝句,何況人言似六郎。”另一首則是:“南浦清秋露冷時,凋紅片片已堪悲。若教具眼高人看,風折霜枯似更奇。”蘇軾《橫湖》詩寫荷花,有“貪看翠蓋擁紅妝”之句,“六郎”則指武則天的男寵張宗昌,兄弟排行第六,身為當朝宰相的楊再思卻面諛說:“人言六郎面似蓮花,再思以為蓮花似六郎,非六郎似蓮花也。”陸游的前一首詩認為以“翠蓋紅妝”形容荷花,尚且有損于清華絕俗的風神,何況以張宗昌那種佞幸小人作比,則更是一種褻瀆。后一首詩呢?陸游說的是深秋時荷花凋落,令人不免生悲,但從獨具只眼的高人來看,雖然風刀霜劍,但荷葉荷枝仍傲然堅持,昂然挺立,那更是令人稱奇。這,正是詩人對生活中獨立不阿、堅貞不屈的君子人格的贊美。明清易代之交堅持抗清的大學者王夫之,曾作有詠荷《絕句》:“荷薏含香不出窩,藕絲未斷也無多。誰將雪色看蓮子,種向流沙萬里河?”詩中的象征與寄意,讀者如了解王夫之的生平和思想,自可于言外思而得之。王夫之晚年居于他的故里衡陽石船山下,在衡陽縣曲蘭鄉湖西村有他的故居“湘西草堂”。有一年盛夏我前去謁訪,只見草堂前幅員頗廣的荷塘中的紅白荷花,正在南風中召開它們的年度盛會,青梗綠葉將它們一一挺然舉起,似正在向前賢做隔代而又隔代的祭奠。
桃花。我多次于春夏兩季游覽過西湖,西湖盛夏的紅白兩色的荷花給我留下多彩而清高的印象,我曾賦《西湖觀荷》一詩:“滿湖翠袖舞娉婷,驕白嫣紅笑語盈。無那南風薰似酒,紅荷酣醉白荷醒。”而西湖春日岸邊的桃花呢?那熱烈而美艷也令我一見難忘,難怪當代大詩人艾青《西湖》詩的結尾要如此向它們頂禮:“清澈的水底/ 桃花如人面/ 是彩色繽紛的記憶。”艾青的詩,如果和唐代詩人崔護《題都城南莊》中的“人面桃花相映紅”算是近親,那么,它和《詩經》中的桃花之篇就是血脈相連的遠親了。
桃,果木名,起源于中國,落葉小喬木。詩文中或指桃樹的果實,或指桃花,花為紅色、粉紅色或白色,艷麗可賞。其果被稱為“天下第一果”,乃古代祭祀神仙的五果之一。在《詩經》中它多次出場亮相,《大雅·抑》中有“投我以桃,報之以李”之句,成為今日習用的成語,其“桃”乃指桃樹的果實,而《魏風·園有桃》之“園有桃,其實之殽”,同樣是指可食用之桃實。而美艷的桃花呢?它們最早是成群結隊、喜氣洋洋地開放在《周南·桃夭》里: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
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有蕡其實。
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
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召南·何彼禯矣》是一首表現周平王的孫女出嫁盛況之詩,其中有“何彼禯矣,華如桃李”之句,以艷麗的桃花和李花贊揚女主人公的美貌,但盡管“桃”與“李”雙管齊下,這首詩及詩中的如上之句,卻遠不及《周南·桃夭》一詩及“桃之夭夭,灼灼其華”的知名度與傳后性。這,既是由于前者贊頌的乃特權階層的王公貴族,后者贊美的系民間煙火的百姓平民,在內涵與境界上有前者不可比擬的普世性,也因為兩者雖同是祝婚的喜歌,同是采用重章疊句的《詩經》特具的句法與章法,但后者的語言辭藻絢爛,聲韻天成,其意象與意境之美為前者所遠遠不及。“夭夭”,本已狀春風中青青桃枝的茂盛豐美,偏旁從火的“灼灼”本意已為明亮火熱,用這種意象鮮明的疊詞來形容怒放的桃花,不僅其濃艷繁茂之狀如在目前,其生機勃勃、喜氣盈盈之意亦于言外可想矣。
西方文壇有“母題”與“原型”說,中國古代詩壇有“詩胎”與“詩祖”說,《周南·桃夭》的原型意象就是“桃之夭夭”與“灼灼其華”,母題則是愛情與婚姻,在語言和語詞范圍內流澤所及,它豐富了我們日常所用的漢語言,僅與母題和原型意象有關的,就有“桃夭”“桃腮”“桃色”“桃杏腮”“桃花面”“桃夭之化”“桃紅人面”,等等。在《詩經》之后的歷代詩歌中,桃花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如唐詩人崔護的《題都城南莊》,不過,除了愛情與婚姻的最初原色之外,在眾生的審美過程中,它還被賦予了更為豐富的美的內蘊,如春之情結、隱逸情懷以及深愁苦恨等人間情態:
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
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
(白居易:《大林寺桃花》)
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
蔞蒿滿地蘆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時。
(蘇軾:《惠崇春江晚景》)
犬吠水聲中,桃花帶露濃。
樹深時見鹿,溪午不聞鐘。
野竹分青靄,飛泉掛碧峰。
無人知所去,愁倚兩三松。
(李白:《訪戴天山道士不遇》)
隱隱飛橋隔野煙,石磯西畔問漁船。
桃花盡日隨流水,洞在清溪何處邊?
(張旭:《桃花溪》)
山桃紅花滿上頭,蜀江春水拍山流。
花紅易衰似郎意,水流無限似儂愁。
(劉禹錫:《竹枝詞》)
一樹繁英奪眼紅,開時先合占東風。
可憐地僻無人賞,拋擲深山亂木中!
(李九齡:《山舍南溪小桃花》)
從《詩經》初唱,桃花示人的本來都是正面而美好的惹人憐愛的形象,但不知從何時開始,也常常被世人抹黑,如“桃色”“桃色新聞”指不正當的男女關系,“桃花運”一以謂女子之不檢點的出格行為,一以揶揄男子得到多位女子的愛戀。即使如杜甫老先生,他也曾手栽桃李并極力贊美春日桃花之美,如他在成都草堂所作的《江畔獨步尋花七絕句》之五:“黃師塔前江水東,春光懶困倚微風。桃花一簇開無主,可愛深紅愛淺紅?”然而,寫于同一時期同一地點而且同為組詩,他的《絕句漫興九首》其五卻又說:“腸斷江春欲盡頭,杖藜徐步立芳洲。顛狂柳絮隨風舞,輕薄桃花逐水流!”真是出爾反爾,如此這般,叫無辜的桃花左右為難如何是好?
最初盛開在《詩經》中的桃花,畢竟是青春的象征、愛情的寓示、理想的寄托、韶華的回想、美感的展現。猶記我年華已老、鬢發已霜之年,由學生的學生何瓊華邀約,偕內子緹縈于早春游長沙河西之梅溪湖,初露也是初漏的春色春光贈我絕句四章,其一是:“半世流光去絕蹤,白頭長憶少年紅。春華已逝藏何處? 都在桃腮柳眼中!”這是所謂“舊體詩”,當代的新詩呢?前已引艾青《西湖》的片斷,而臺灣名詩人洛夫《邊陲人的獨白》對桃花桃實的歌詠,雖具有超現實主義的魔幻之感,精神血脈也仍遠承了《周南·桃夭》的一脈馨香:“春,在山中/ 在蒲公英的翅膀上/ 春,在羞紅著臉的/ 一次懷了一千個孩子的桃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