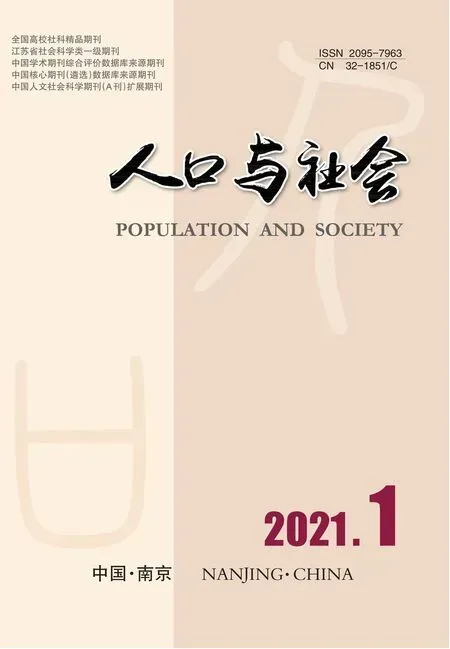中國公眾對養老責任主體的認知研究
賈 茹
(北京師范大學 政府管理學院,北京 100875)
“老有所養”是人類永恒的話題,尤其中國具有“百善孝為先”“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傳統。目前,人口老齡化已經成為中國社會的新常態。數據顯示,到21世紀中葉,中國65歲及以上老年人的數量將達到3.2億,占總人口的23.2%,老年撫養比將升至58.7%[1]。一方面,生育少子化、家庭規模小型化使得“四二一”“四二二”家庭面臨較大的養老負擔;另一方面,傳統孝道觀念式微、養老資源供給不足對國家養老能力形成挑戰。黨的十九大報告強調“要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構建養老、孝老、敬老政策體系和社會環境,推進醫養結合,加快老齡事業和產業發展”[2],將“老有所養”作為改善民生的重要組成部分。健全養老政策體系首先需要認清當前中國公眾對養老責任(1)“養老責任”是指社會規范要求特定個人或組織對于特定養老對象提供養老支持的義務和職責,并對未履行之事需要承擔相應后果。詳見:徐俊,風笑天.獨生子女家庭養老責任與風險研究[J].人口與發展,2012(5):2-10.主體的認知狀況,即解決應該“由誰來養老”的問題。本研究基于“新時代人民對社會公平正義要求的實證研究”全國調查數據,描述與詮釋當前中國公眾在養老責任主體認知方面的總體狀況、群體性差異與影響因素,試圖為解決養老問題提供理論參考。
一、誰來負責養老:子女、政府、老人還是多主體
“家庭養老”是人類社會最基本且最富生命力的養老方式,始終占據著中國養老模式的主流位置。由子女負責養老不僅受到儒家倫理的認同與宗法制度的保護,伴隨著農業社會文明綿延千載,而且受到20世紀70年代以來社會交換理論的支持。持這種觀點的學者認為子女贍養老人是父代養育子女的一種反饋模式[3],是責任倫理[4]和血親價值論[5]的體現。張波基于2010—2013年中國綜合社會調查數據認為由子女負責養老仍然是人們普遍的養老責任認知[6]。然而葛劍雄認為傳統“養兒防老”觀念正在逐漸消解[7],這種消解來源于生產方式和經濟形態的轉變,即由農業社會步入工業社會后,隨著大家庭的瓦解與核心家庭的興起,人們開始在國家層面謀求養老問題的解決。
德國新歷史學派與以庇古為代表的福利經濟學派均強調政府應該實施廣覆蓋的養老金制度,采用收入轉移支付的方式保障社會公平以促進國民經濟發展[8]。凱恩斯《就業、信息與貨幣通論》和《貝弗里奇報告》的問世標志著政府正式承擔公民的養老責任,隨后歐美諸國推行養老保險制度并催生了福利國家模式[9]。曹鑫的一項研究顯示中國養老模式從家庭養老逐漸轉向社會養老,政府在養老實踐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10]。而以張川川、陳斌開為代表的學者通過實證研究發現盡管養老保險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替代家庭養老,但社會養老無法從根本上動搖中國傳統的家庭養老模式[11]。
伴隨著全球經濟危機的爆發,政府公共財政越來越難以承受社會養老壓力,福利多元學派開始倡導政府的有限責任,認為市場、國家、家庭、社區和民間組織等都可以是社會福利的來源[12],政府、子女、老人三方養老責任分攤模式進入公眾視野。以周湘蓮為代表的學者認為在養老責任主體方面應該由政府進行經濟支持、社會組織保障老年生活、子女負責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商業組織提供養老補充[13],養老責任分攤能夠凝聚多主體的優勢并減輕單一主體的沉重負擔,中國公眾正逐步增強對多元養老責任主體的認同。
20世紀70年代中國政府開始提倡“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計劃生育政策的執行帶來了獨生子女家庭養老保障供給不足的問題。加之近年來居住方式自然分離化與人口流動常態化,獨生子女家庭對父母進行生活照料、精神慰藉和經濟支持的能力減弱,部分具有經濟基礎的父母開始規劃獨立養老。風笑天對這一社會現象表示支持,認為推行自我養老可以緩解人口老齡化帶來的壓力和化解現實養老困境[14],穆光宗、朱勁松等學者也認為自我養老不僅有助于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質量、尊嚴和地位[15],同時能夠節省社會財富以支持擴大再生產,發揮老年人的積累優勢以助力經濟發展。然而部分學者對獨立養老的鄉村可行性及其所帶來的負面效應,如疏遠親密的代際關系和稀釋孝順美德等表示擔憂。
二、理性選擇邏輯、觀念現代化與養老責任主體認知
公眾養老責任主體認知包含公眾認為某一主體“應不應該”與“能不能”承擔養老責任兩個維度,分別根植于觀念現代化程度與理性選擇邏輯。Bandura的社會學習理論認為人類行為是內部因素與環境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16],Fishbein和Ajzen的行為理論認為個體主觀認知是個體態度和社會規范共同作用的結果[17],也就是說,公眾在選擇養老責任主體時受到將養老作為社會問題還是個人問題的影響。為此本研究認為觀念現代化程度包括公眾對宏觀層面的國家責任和微觀層面的個人責任的認知,理性選擇邏輯涵蓋公眾對宏觀層面社會養老能力和微觀層面家庭養老能力的考量。
1.理性選擇邏輯與養老責任主體認知
理性選擇理論認為利益是行動者的根本動因,決定個體理性行動的因素是資源、制度及其結構[18],我們認為養老責任主體的選擇受到理性選擇邏輯的支配。從宏觀層面的社會養老能力角度出發,社會保障制度能夠增強個體經濟上的抗風險能力和獨立性,從而降低公眾對代際支持的依賴,也就是說參加醫療保險、養老保險等社會保障的公眾可能更偏好政府負責養老或三方養老責任分攤,降低對子女養老的依賴程度。公眾對社會保障制度滿意度越高意味著越認可政府供給養老資源的能力,對政府能力的認可會增強對政府養老的偏好。張波的研究成果顯示養老保障和醫療保險對人們的養老責任認知具有顯著影響,參加養老保險者較認同政府負責養老和三方養老責任分攤。丁志宏[19]的研究成果進一步支持了上述論斷。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研究假設:
假設1:社會養老能力對公眾養老責任主體認知影響顯著
假設1a:對社會保障制度滿意度越高的公眾越偏好政府負責養老或三方養老責任分攤
從微觀層面的家庭養老能力角度出發,作為理性人的個體會依據家庭養老資源選擇養老責任主體,養老資源主要包括物質條件、日常照料和精神慰藉。物質條件表現為土地、房產、金錢等經濟基礎,日常照料和精神慰藉與自身是否為獨生子女、父輩數目和子輩數目等家庭結構狀況密切相關。當家庭具備土地、房產、金錢等經濟基礎,作為子女有能力為父母養老,作為父母有能力獨立養老,反之,經濟基礎薄弱的家庭對政府養老可能會更加依賴。同理,當自身并非獨生子女、所要贍養的老人數目少,作為子女有充足的時間、精力和較輕的心理負擔對老人進行精神慰藉和日常照料,作為父母能夠心安理得地接受子女照料而不必擔心為其增添生活壓力,也就是說,家庭養老能力越強的公眾越偏好由子女負責養老或獨立養老。Chen YenJong等的研究表明社會經濟地位較高、家庭資源豐富的老人更喜歡獨立生活或者與兒女同住[20],陶濤、劉雯莉的研究成果表明與非獨生子女家庭老年人相比,獨生子女家庭老年人對子女養老的期待更低,更企盼來自政府和制度的養老支持[21]。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研究假設:
假設2:家庭養老能力對公眾養老責任主體認知影響顯著
假設2a:物質供給與日常照料能力越強的公眾越偏好子女養老或獨立養老
2.觀念現代化與養老責任主體認知
觀念越現代意味著越重視國家責任而期待由政府負責養老,觀念越傳統意味著越重視個人責任而認同“養兒防老”。觀念的現代化程度受到長期居住地、受教育程度和職業性質的影響。(1)在長期居住地方面,受聚族而居、安土重遷的小農經濟思想影響,對血緣和地緣關系的重視以及家族勢力和禮俗力量的共同作用,形成了農村公眾的狹隘功利主義[22],這意味著長期居住在鄉村的公眾比城市公眾更偏好傳統的子女養老模式。英克爾斯在對人的現代性的闡述中也突出強調了城市生活經歷有助于現代觀念的養成,即相較于農村公眾而言,城市公眾的觀念現代化程度更高,更認同政府養老。(2)在受教育程度方面,認知發展理論認為教育通過知識累積和認知發展對公眾起啟蒙作用[23],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越有能力了解社會的真實情況[24],對政府負責養老及三方養老責任分攤的接受能力越強。韋伯認為現代化進程是社會的理性化程度不斷加強的過程,教育會培育公眾的批判意識和理性精神[25],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公眾越偏好多元養老責任主體以實現養老資源的優化配置,反之受教育程度越低的公眾越認同子女養老。(3)在職業性質方面,距離公權力近的公眾往往有更多的公共參與機會和政治參與行為,而政治參與實踐對公眾觀念的現代化具有正向的推動作用[26],那么相較于體制外工作者而言,體制內工作者會偏好現代性較強的政府養老或者三方養老責任分攤;不同性質的工作在收入分配、人力資本回報等方面存在明顯差別,體制內工作者通常擁有較好的養老福利待遇,就業狀態較少受到市場波動的影響。張仁鵬等的研究發現從事穩定性就業的居民會更多選擇由政府養老或者共同負擔養老[27]。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研究假設:
假設3:觀念的現代化程度對公眾養老責任主體認知影響顯著
假設3a:相較于長期居住在城市的公眾而言,鄉村公眾更認同子女養老
假設3b:受教育程度越低的公眾越認同子女養老
假設3c:相較于在體制外工作的公眾而言,在體制內工作的公眾更認同政府負責養老或三方養老責任分攤
三、數據、變量與方法
1.數據
本研究數據來源于麻寶斌教授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新時代人民對社會公平正義要求的實證研究”,該項目組于2017年6—8月開展全國問卷調查,調查抽樣依據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采用分層多階段PPS抽樣方法。首先將全國劃分為直轄市、東部省份、中部省份、西部省份4個抽樣框,然后參照全國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分5階段從每一抽樣框中等距抽取2個初級抽樣單元(省/自治區/直轄市),2個2級抽樣單元(區/縣),2個3級抽樣單元(街道/鄉鎮),3個4級抽樣單元(居委會/村委會)、25個最終抽樣單元(家庭住戶),最后在每戶中隨機抽取1人為受訪者。項目組共抽取北京、上海、河南、湖南、山東、廣東、內蒙古、陜西8個省及直轄市,16個區縣級單位,32個街道或鄉鎮級單位,96個居委會或村級單位,獲取有效問卷2 308份,進行加權處理后獲取2 400個有效樣本,樣本對除臺灣、香港和澳門外的中國地區具有充分的代表性。本研究使用SPSS20.0進行數據分析。
2.核心變量(2)下述變量設計主要用于本研究的核心數據分析即多分類Logistic數據分析。
本研究的因變量為“養老責任主體認知狀況”,在問卷調查中選取題目“您認為有子女老人的養老主要應該由誰負責”進行測量,將4個選項操作化為:主要由政府負責=1;主要由子女負責=2;主要由老人負責=3;政府、子女、老人責任分攤=4。本研究的自變量用以量化宏觀層面的社會養老能力、微觀層面的家庭養老能力與觀念現代化程度。社會養老能力通過醫療保險滿意度和養老保障是否公平加以衡量。家庭養老能力具化為物質供給能力與日常照料能力,物質供給能力通過家庭經濟收入、土地使用權與房產所有權加以衡量;日常照料能力通過是否為獨生子女、贍養老人數和撫養子女數加以衡量。觀念的現代化程度通過長期居住地、受教育程度和工作性質進行衡量,具體變量操作情況見表1。
3.方法
由于因變量為四分類變量且無順序之分,故本文采用多分類Logistic回歸模型分析理性選擇邏輯與觀念現代化程度對當前中國公眾養老責任主體認知狀況的影響。此模型用于解釋自變量X在預測因變量Y發生概率時的作用和強度,并且因變量Y具有多種取值類型。具體而言,主要由政府負責定義為y=1;主要由子女負責定義為y=2;主要由老人負責定義為y=3;政府、子女、老人責任分攤定義為y=4,其中以“政府、子女、老人責任分攤”作為對照組,多分類Logistic模型可表述為:
P1為公眾認為“主要由政府負責”的概率,P2為公眾認為“主要由子女負責”的概率,P3為公眾認為“主要由老人負責”的概率,P4為公眾認為“政府、子女、老人責任分攤”的概率,并且P1+P2+P3+P4=1。an(n=1,2,3)為常數項;Xk為自變量,表示第k個影響公眾養老責任主體認知的因素;βnk為模型n中第k個影響因素的回歸系數。
四、研究內容
1.當前中國公眾養老責任主體認知的總體狀況
對“當前中國公眾養老責任主體認知”進行頻率分析,數據結果如圖1所示。認為有子女老人的養老主要由政府負責的人數為123人,占比5.1%;主要由子女負責的人數為1 274人,占比53.1%;主要由老人負責的人數為64人,占比2.7%;政府、子女、老人責任分攤的人數為912人,占比38.0%。也就是說,超過五成的中國公眾認為應該由子女負責養老,近三成的公眾認為應該由政府、子女和老人責任分攤,這表明當前中國“養兒防老”觀念依然深入人心,政府、子女、老人責任分攤的養老觀念擁有一定程度的社會認同基礎。
2.中國公眾養老責任主體認知的群體性差異
為了觀測中國公眾養老責任主體認知的群體性差異,本研究將受教育程度、居住地、工作性質等變量與“當前中國公眾養老責任主體認知”變量分別進行卡方檢驗和交叉列表分析(見表2),除本人是否為獨生子女差異不明顯外,其他變量的群體性差異均顯著,具體情況如下:(1)在社會養老能力方面,相較而言,對醫療保險制度滿意度越高的公眾越認同子女養老,而對醫療保險制度滿意度越低的公眾越認同由政府、子女、老人責任分攤和政府負責養老;對養老保障制度公平感知度越高的公眾越認同子女養老,對養老保障制度公平感知度越低的公眾越認同由政府、子女、老人責任分攤和政府負責養老。(2)在物質供給能力方面,低收入家庭較認同由子女負責養老和老人自己負責,中低收入家庭較認同政府負責養老,中高收入家庭較認同三方養老責任分攤;房產是父母所有的公眾更認同子女負責和三方責任分攤;無土地資源的公眾更認同三方養老責任分攤,即中高收入家庭、房產是父母所有、無土地資源的公眾偏好三方養老責任分攤。(3)在日常照料能力方面,贍養老人數少的公眾較認同政府負責和老人自己負責;養育子女數少的公眾較認同政府負責和三方養老責任分攤,即贍養老人數少、養育子女數少的公眾偏好政府負責養老。(4)在觀念現代化程度方面,受教育程度為初中及以下的公眾最認同子女負責養老,受教育程度為大學及以上的公眾最認同三方養老責任分攤;體制內公眾更認同三方養老責任分攤,體制外公眾更認同子女負責養老,體制內公眾較體制外公眾更認同由政府負責養老;居住在鄉鎮的公眾最認同子女負責養老,居住在城市市區的公眾最認同三方養老責任分攤,居住地現代化程度越高的公眾越認同政府負責養老。
3.當前中國公眾養老責任主體認知的影響因素分析
本研究從社會養老能力、家庭養老能力和觀念現代化程度三個維度對當前中國公眾養老責任主體認知的影響因素進行分析,以驗證理性選擇邏輯和觀念現代化的解釋力,所有模型均利用復雜抽樣設計的多分類Logistic回歸估計,見表3。

表3 不同因素對養老責任主體認知影響的多分類Logistic回歸結果
數據結果顯示,在社會養老能力層面,對社會保障制度滿意度越高的公眾越偏好子女養老,證明假設1a“對社會保障制度滿意度越高的公眾越偏好政府負責養老或三方養老責任分攤”不成立,這可能與社會保障制度的實際支持作用有限相關,諸如“因為即使參加了醫療保險,如果在保險報銷線之下,則仍然需要自己統籌醫療費用;而且即使到了醫療保險線,也存在著自身支付比例限制”[6],即醫療、養老等社會保障制度在現階段無法取代子女的贍養職責。
在家庭養老能力層面,房產是父母所有的受訪者選擇子女負責(與三方養老責任分攤相比)的比房產不是父母所有的受訪者高,表明房產是父母所有的公眾更認同子女養老;有土地資源的受訪者選擇子女負責(與三方養老責任分攤相比)的比沒有土地資源的受訪者高,表明有土地資源的公眾更認同子女養老;有土地資源的受訪者選擇老人負責養老(與三方養老責任分攤相比)的也比沒有土地資源的受訪者高,表明擁有土地資源的公眾更認同老人負責養老,上述數據分析結果證明了假設2a“物質供給與日常照料能力越強的公眾越偏好子女養老或獨立養老”成立。數據顯示贍養老人數越多越偏好三方養老責任分攤[28]。值得注意的是公眾并非因為物質供給能力不足而尋求政府提供養老保障,而是家庭結構核心化、居住方式自然分離化與流動常態化所造成的日常照料能力減弱,迫使公眾尋求多元主體分攤養老責任。
在觀念現代化程度方面,長期居住在鄉村的受訪者選擇子女負責養老的比居住在城市的受訪者高,證明假設3a“相較于長期居住在城市的公眾而言,鄉村公眾更認同子女養老”成立。受教育程度為初中及以下的受訪者選擇子女負責養老的比受教育程度為大學及以上的受訪者高,證明假設3b“受教育程度越低的公眾越認同子女養老”成立。值得注意的是,家庭年收入并沒有對養老責任主體認知狀況產生顯著影響,這可能因為家庭經濟收入水平與養老責任主體認知之間并非線性對應關系。從經濟角度出發,家庭收入高能夠使公眾免于因物質匱乏而求助于政府養老,但是從價值追求角度出發,家庭收入高的公眾偏好現代價值觀而可能更認同政府養老。
五、相關對策
雖然中國正處于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時期,公眾觀念受到現代甚至后現代因素的影響,然而研究結果表明超過半數的中國公眾認同主要由子女負責養老,區別于西方社會接力模式的反饋模式依然占據中國社會代際倫理的主流。筆者認為這并非是因為傳統觀念根深蒂固而阻礙社會進步,恰恰是社會演化過程中去偽存真而使傳統美德得以延續的結果,亦是中華民族能夠生生不息的根脈所在。為此,政府應把握當前中國公眾養老責任主體認知狀況,通過制度供給、道德約束、輿論宣傳等手段,發揮房產、田產在養老保障中的關鍵作用,結合養老責任主體認知的群體性差異細化養老政策,在保障老年人基本物質需求的同時關注日常照料與精神慰藉。
1.建立健全“以家庭養老為核心、多元主體責任分攤”的養老保障體系
研究結果表明子女養老觀念占據社會主流,近三成公眾認為養老責任應該由政府、子女和老人分攤,這意味著政府應該著力完善“以家庭養老為核心、多元主體責任分攤”的養老保障體系。一方面明確家庭作為養老載體的首要地位,采用道德約束、輿論宣傳、制度供給等手段強化子女的養老責任意識,促進老年群體選擇家庭養老;另一方面重視多元主體在養老保障中的協同作用,政府可以通過供給養老金、完善老年人生活設施等方式發揮物質保障功能,指導社區、村委會協同子女對老人進行日常照料與精神慰藉,鼓勵商業機構提供高質量的治療護理、臨終關懷等。
2.提高城鄉老人經濟水平,完善“以房養老、以地養老”制度
“有恒產者有恒心”同樣適用于中國公眾對養老責任主體的認知,研究結果表明房產是父母所有(相較房產不是父母所有)與有土地資源(相較沒有土地資源)的公眾更認同子女養老,土地使用權對老人獨立養老具有顯著影響力,也就是說父母擁有房產與田產不僅會減輕子女的經濟壓力使其更樂于贍養父母,而且會緩解老人的心理壓力使其更愿意回歸家庭。房產是子女養老的可靠保障,田產是獨立養老的物質基礎。這意味著公共部門應完善“以房養老、以地養老”制度,一方面政府可出臺法律法規、司法解釋或行政條款保障老年人的財產所有權,另一方面政府可協助老年人將房產、土地使用權轉化為養老資源,重點幫扶空巢、獨居老人等無法實現家庭養老的老年群體。如將農村老人的土地轉包他人,所獲收益直接用于其生活開銷,同時配套餐飲、醫療、家政等養老服務,為獨立養老提供可靠保障。
3.養老責任主體認知群體性差異顯著,養老政策精細化勢在必行
研究結果顯示,長期居住在鄉村的公眾偏好子女負責養老,受教育程度為大學及以上的公眾偏好政府、子女和老人三方養老責任分攤,這固然與農業生產生活所保留的傳統觀念以及高等教育所培育的理性精神相關,但同時反映出養老保障制度城鄉差異較大以及養老資源分配因社會地位不同而出現的嚴重分化現象。政府一方面可以采取專業化的治理方式,探索基于社會網絡的養老互助模式,著力提升鄉村養老服務供給的質效,著重緩解留守老人家庭的代際沖突與養老困境;另一方面對受教育程度較低的公眾因勢利導,轉變他們的養老觀念,同時在受教育程度較高的群體中試用養老責任分攤政策以檢驗其效果。
4.政府在提供養老保障的同時,理應兼顧生活照料與精神慰藉
研究結果表明即便中國公眾擁有能夠獨立養老的經濟收入,對現行社會保障制度滿意,依然表示出對子女養老的渴望。這意味著養老不僅需要物質的滿足,而且需要日常照料與精神慰藉。雖然日常照料與精神慰藉屬于更貼近私人領域的家庭生活問題,但是公共政策可以發揮輔助或引導作用。如在日常照料方面,采用財政補貼等手段推廣智能養老服務,對突發疾病的老人實施一鍵呼救。在精神慰藉方面,通過舉辦社區活動、建立老年大學等方式,弘揚尊老、愛老的傳統美德,實現“老有所養”“老有所為”“老有所樂”[2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