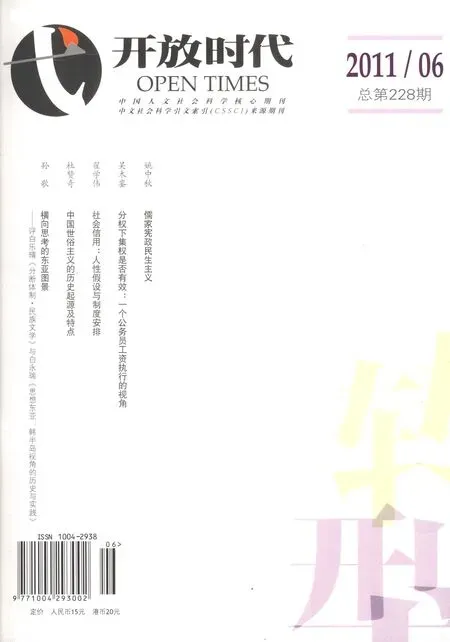脫貧攻堅實踐與中國鄉村社會重建*
——以滇西邊境彝族貧困社區功能性社會重建為例
■陳 浩
[內容提要]從社會學視角認識脫貧攻堅的意義,不能僅局限于對精準扶貧效果的考察,還應看到它對鄉村社會重建的巨大影響。在脫貧攻堅實踐中,單位掛鉤幫扶、工作隊駐村扶貧等措施,讓城市公職人員深入鄉村社區,形成了行政權力與村民個體之間新的中間力量;扶貧政策的程序規范要求和民主參與機制,促進了村落社會聯結和個體公共意識的重建。在此過程中,基于現實需求的功能性社會整合模式產生,對鄉村重建具有深遠的影響。
自2013年習近平總書記首次提出“精準扶貧”以來,中國開展了聲勢浩大的脫貧攻堅實踐,政府和社會各界付出了巨大努力,實施了大量措施,取得了非凡成效。如今脫貧攻堅已經到了最后階段,相關任務已完成絕大部分,我們可以樂觀地預測,2020年中國應能如期達到當初承諾的脫貧目標。從社會科學的視角認識脫貧攻堅,不能僅著眼于脫貧成效,因為這次規模空前的戰略舉措,不僅是一場經濟開發運動或民生改善運動,還對鄉村社會結構、個體觀念、社會關系、治理方式等產生了深遠影響。時至今日,這次脫貧攻堅在背景、時空、目標、主體、行動策略、實施效果等方面的特征都已顯現,我們有理由將其視為中國鄉村建設進程中重要的歷史事件,考察其對鄉村社會發展的意義。當然,對層次如此之高、牽涉如此之廣、耗時如此之長的全局性戰略進行歷史定位是本文力所不逮的,但在已經發生的經驗事實基礎上,從特定視角分析脫貧攻堅對社會發展影響的條件業已成熟。在鄉村社會整合的視野下,脫貧攻堅政策實踐對重建鄉村社會權威和再造鄉村社會聯結具有很強的啟示性,值得我們深入探討。
一、鄉村社會的整合危機
在中國的發展進程中,現代化的策源地和重心在都市,鄉村的地位十分不利,在產業、市場、制度、人力方面極其薄弱,成為都市現代化的附庸甚至剝奪對象,在城鄉二元結構中面臨多重發展困境和社會危機。其中社會領域受到的沖擊最為強勁,社會學者普遍認為,由于原有的內在體系和文化機制在現代化進程中解體,導致鄉村整合和治理出現危機。
對鄉村社會整合危機的學術概括有社會原子化、村落虛空化等不同視角。社會原子化并非當前中國鄉村社會特有的現象,實際上是現代性的普遍后果,在以自由市場和民族國家建立為標志的現代社會興起過程中,傳統社會的聯結方式解組,原子化危機逐漸呈現,成為“社會何以可能”的反命題,并扮演了19世紀社會學在法國誕生的助產婆,激發了古典社會學家對社會整合、社會團結的探討。①在他們看來,團結、整合是社會的應然狀態,傳統的社會聯結方式對個體造成束縛,現代社會將會出現新的整合機制,但當時這種機制尚未完全建立,因此出現社會失范。而將社會原子化解釋引入當前鄉村整合危機的學者如賀雪峰、吳毅等“華中鄉土學派”學者很大程度上受這種觀念影響。②中國當代鄉村社會(尤其在改革開放后的二三十年時間里)的確與歐洲進入現代社會初期所面臨的情境十分類似,處于不同社會體制轉換的間隙中,許多原有社會規范失效,新的秩序尚未形成,社會領域解體,原子化危機顯現。孫立平總結了原子化社會的兩個特征,一是人與人之間的聯系薄弱,二是追逐利益時以個人為單位。③以這兩個特征為標準,中國鄉村社會無疑是原子化的。鄉村社會原子化會帶來許多后果,表現在無社會聯結群眾出現、成員間有效互動缺失、公共生活匱乏、道德共識瓦解、社會秩序混亂、底線失守、④群眾是非觀念模糊、公共輿論沉默⑤等方面,這些都為鄉村治理和鄉村發展帶來巨大困難和挑戰。
鄉村虛空化的一個層面是空心村的大量出現,空心村現象不僅包括鄉村聚落空心化、住宅布局空心化、勞動力空心化、土地閑置化,還包括基礎設施空心化、公共服務空心化、產業結構空心化等方面。⑥空心村的出現帶來了農業荒廢、留守家庭、醫療養老等各方面社會問題,也讓原本就脆弱的鄉村社會難以負擔沉重的發展任務。另一個層面,鄉村的虛空化還體現為村民主體性的喪失,意識形態的虛空化和農業生產的虛空化,讓農村成了一個“沒有前途”的地方,個體在那里找不到主體體驗,盡可能地逃往城市。從鄉村流出的人口,很大程度上不是“剩余勞動力”,而是受教育程度較高的年輕人,他們也正是鄉村現代化所需要的人才。⑦
以上論述呈現的主要是改革時期中國鄉村的整合危機,這種危機不是突然出現的,而是經歷了一個社會不斷受沖擊的解體過程。在費孝通看來,傳統中國鄉村社會整合是有效的,“中國鄉土社會中本來包含著賴以維持其健全性的習慣、制度、道德、人才”,“我們中國是有一套足以使大多數人能過得去的辦法的”。⑧但是20世紀初都市工業的沖擊不僅使鄉村工業消亡,還通過高利貸等手段掠奪了農民的土地,造成鄉村市場的沒落,失去市場的都市也無以為繼,最終導致“都市破產鄉村原始化”的局面。⑨在政治層面,鄉村紳士和地方自治團體原來維持著社會的有效運行,成為國家權力和村民個體之間的聯結和緩沖力量,但現代國家權力的直接介入破壞了其作為自治單位的完整性,鄉村生活陷入混亂。⑩羅志田從科舉廢除的視角探討了這一過程,他認為中國傳統社會內部聯系緊密,科舉制的廢除導致鄉村中士與紳的疏離,“鄉紳”的來源由讀書人轉變為非讀書人,鄉紳與“知識”的疏離造成道義約束日減,其行為也可能會出現相應的轉變,致使“土豪劣紳”大量出現。“在整個世紀的系列斯文掃地活動之后,鄉村既遭受了疏離于‘知識’的痛苦,也會開始真正嘗試一種無士的自治生活。”11可見,鄉村原子化的許多表現,如社會失序、道德失守、個體直接面對國家等方面在民國時期已經出現,但基于血緣、地緣和親緣的聯結紐帶仍然存在。
新中國成立以后,逐漸進入集體化時期,呈現出強國家-弱社會的特征,一方面,國家壟斷了幾乎所有資源;另一方面,帶有獨立性的社會力量被消除。12戶籍制、人民公社制、單位制等體制既將個體整合起來,又解組了個體原有的社會紐帶。因而,對集體化時期中國鄉村社會整合的認識在此出現了一個矛盾,即集體體制既增進了社會的團結和統一,又削弱了個體之間的聯系。許多研究者將集體化時期的中國社會視為原子化的社會,其理由是,個體之間是通過一個共同權威進行聯系,而非直接聯系的。13同時,他們也不能否認鄉村社會的整合性,閻云翔將這種國家-社會-個體的關系稱為“集體式的個體化”,認為這是中國現代化事業的一部分。14這種視角的特征是將國家排除在社會之外,將國家力量的整合取代社會力量的整合視為一種非正常現象。然而,在集體化時期,不管通過什么方式,鄉村社會和村民個體之間是能夠有效整合起來的,鄉村運行的統合力量能有效發揮作用。
到了改革時代,整合鄉村社會的集體力量也瓦解了,鄉村原子化似乎表現得更為徹底,賀雪峰就從鄉村傳統社會聯系減弱和集體整合力量降低兩個方面指出鄉村的整合危機,一方面傳統宗族聯系解體,血緣和地緣關系弱化,利益聯系尚未建立且缺乏建立的基礎;另一方面,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使生產小隊共同生產的功能瓦解,村民直接與村委會聯系而缺乏與其他小組的聯系,鄉村成了“半熟人社會”。15吳重慶認為,革命的沖擊使鄉村中老人的傳統權威息微,成為社會結構主體的年輕人紛紛離鄉離土,鄉村成為輿論失靈、面子貶值、社會資本流散、以夸富求認同、周期性呈現的“無主體熟人社會”。16曹海林也認為肇始于1958年的公社化運動使傳統社會中構建村莊共同體的神圣性、倫理性和契約性的關聯鏈條瓦解,改革后集體化村莊社會共同體也隨之解體,村莊社會關聯又面臨著新的重構。17
由此,我們似乎可以得到一條改革時代中國鄉村整合危機出現的歷史線索,晚清至民國時期廢除科舉、都市工業化、保甲制度等的沖擊導致鄉村道德規范、鄉村自治團體的破壞;集體化時期國家行政力量的整合導致基于血緣、地緣和親緣的鄉村社會聯結解體;而改革時期原本整合鄉村社會的集體體制也瓦解了;一步步下來鄉村的原子化越來越徹底,幾乎真的成了馬克思所說的“一袋馬鈴薯”。然而這種看法是值得商榷的,一來鄉村社會本身并不必須是靜態、封閉、成員間聯系緊密的穩定共同體,而是動態發展的,村落對其成員來說,“大家生于斯、長于斯最后葬于斯,但是在這些生與死的節點之間卻有不斷的離開與返回”,18很多時候個體脫離村落的聯系不一定意味著永久脫嵌或負面后果;二來,在鄉村解體和原子化的過程中,我們也可以看到新的社會整合力量的出現和社會聯系重構的過程,村落社會還有另一個“組織化”的重要面向。19
當然,即使原子化的分析框架尚有許多商榷空間,我們仍然不能否認其價值,它所揭示的鄉村整合危機在很大程度上仍是鄉村面臨的巨大困境,解決這個問題需要進一步的探索。同時,有關鄉村整合危機和原子化危機的研究已經持續了相當長的時間,上述多數研究距今已有十多年甚至幾十年,在這個過程中,社會發生了深刻變化,中國已經進入一個新時代,對鄉村來說,正在經歷脫貧攻堅這樣規模空前、影響深遠的全國性開發運動。那么,在新時代,鄉村社會發生著怎樣的變遷,脫貧攻堅對鄉村社會重建發生著什么樣的影響,是否催生出了新的社會整合方式,以及對原有的鄉村社會分析框架有何作用等等問題,值得我們進行深入探討。本文將以滇西F縣Y村和T村的脫貧攻堅實踐為例,通過對幾則田野故事的分析,嘗試對以上問題作出相關回答和討論。
二、研究方法及田野點介紹
本文對脫貧攻堅實踐的探討建立在第一手田野調查資料的基礎之上,2017年5月至2019年4月,筆者被所在單位派往基層扶貧,先后在Y村和T村擔任工作隊隊員,長期吃住在村,全程參與當地在該階段的脫貧攻堅實踐。在此過程中,筆者既在完成扶貧工作任務,也在進行參與觀察;既有作為扶貧干部的主位體驗,也有作為研究者的客位觀察。這段經歷成為筆者選取當地案例探討鄉村社會的重要原因。
不僅如此,當地的具體條件也具有典型性。一方面,F 縣位于滇西邊境集中連片特困地區,是國家扶貧開發重點縣,當地的脫貧攻堅實踐是全國精準扶貧實踐的一個縮影。在精準扶貧政策實施之初,全縣共識別建檔立卡貧困村159 個,建檔立卡貧困對象19155戶、72909人,貧困發生率為16.69%。截至2017年底,全縣貧困村減少至93個,貧困對象減少至4757戶、15475人,貧困發生率降低至4.55%;2018年,所有貧困村出列,并于2019年通過貧困縣退出驗收。Y村位于F縣北部,距縣城53公里,全村轄12個村民小組,共296戶、1256人,其中建檔立卡貧困戶131戶、473人,彝族居民約占60%。T村與Y村毗鄰,共轄10個村民小組,有288戶、1191人,其中建檔立卡貧困戶37戶、127人,彝族居民約占99%。兩村地形皆為山地,森林覆蓋率達65%以上;耕地以旱地為主,河谷區原有部分水田,因水電站建設被淹沒,僅余不足250畝。Y村位于瀾滄江河谷,海拔稍低,氣溫較高,產業以糧食(玉米、麥類、豆類)和烤煙種植為主;T村海拔在2000米以上,氣溫較低,產業以糧食、核桃、茶葉種植為主;此外,外出務工收入對村民收入有較大貢獻。
另一方面,當地在發展過程中出現的社會整合危機也具有一定代表性。當地有個說法,說F 縣人是“云南的四川人”,意為F 縣人具有許多四川人的行為特征,如吃苦耐勞、行事靈活等,尤其是流動性強,外出務工人員比周邊其他地區更多,如Y村有勞動力約600人,外出務工和本地打零工的約500人;T村有勞動力約560人,外出務工、本地打零工的約450人。勞動力外流,是鄉村空心化和社會整合危機的一個重要因素。脫貧攻堅政策實施以前,當地鄉村社區是一種半放任式的狀態,農業生產不見起色,基礎設施建設滯后,公共服務薄弱,社區秩序渙散,社會動員無力,人口結構不合理,種種負面因素表現出原子化、放任化的主導地位。許多村民長期以來未接待過任何鄉鎮干部,有些甚至與政府公職人員沒有任何交集,包括跟村支書和村委會主任都極少打交道。
總體而言,滇西邊境集中連片特困地區的脫貧攻堅實踐是全國脫貧攻堅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相關實踐對當地社會整合的影響也是全國脫貧攻堅舉措諸多影響的一個重要類型,值得我們深入探討。
三、脫貧攻堅實踐對社會整合的影響
許多研究顯示,中國鄉村社會聯結的解體,無須人為破壞,隨著社會結構的變化就自然達成了;然而,鄉村社會的重新整合不是一個自然過程,需要更加積極的力量才能促成。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Y 村和T 村社會中都沒有出現這種力量,直到脫貧攻堅政策的實施,諸多實踐才對當地社會重新整合發生了很大影響。
(一)自上而下的中間力量建構
脫貧攻堅開始后,Y 村和T 村村民開始接待不同類型的扶貧干部造訪,許多人家面臨的問題可能不是缺少干部來訪,而是來得太多了。需要入戶的干部包括縣級掛片領導、鎮上的掛片領導、掛鉤幫扶單位領導、鎮上“一攬子”工作隊干部、考核人員、評估人員、督查人員、駐村扶貧工作隊隊員、“村三委”(村黨支部、村民委員會、村監督委員會)干部等,還有很多臨時抽調的公職人員如教師等等,不一而足。
故事一:擁擠的一餐。
T 村村委會很小,只有一棟兩層小樓,下層兩個房間,分別為會議室和辦公室,上層四個房間,其中一間用作村史館,另外三間原本空著,脫貧攻堅開始后成為駐村工作隊隊員的臥室。小樓下是一個約100m2的院子,院子一側有一間約15m2的平房,即村委會的廚房。廚房里只有一個火塘和一個電磁爐,平日里駐村工作隊隊員的伙食在此解決。
2018年年底,距脫貧驗收第三方評估組檢查還有6周,縣里部署了“大干50天”的迎檢工作安排,要求所有部門人員下沉一線開展扶貧工作,于是大量扶貧干部集中到達村里開展工作,工作時間有的人分散入戶,有的人在會議室整理檔案,未見異常,但到中午吃飯時,狹小的村委會廚房和院子里一下子涌入了56 名干部群眾用餐,讓人大吃一驚。這些人包括:
“村三委”干部4 人,駐村工作隊隊員4 人,掛鉤幫扶單位人員7 人,鎮“一攬子”工作隊隊員4 人,教育扶貧下沉教師7 人,健康扶貧檔案整理下沉醫務人員5 人,協助工作的村民小組組長10人、黨員5人,參與工作的村業務“大員”205人,另有進行隨機抽查的縣委督查組工作人員3人,臨時聘請來準備當日飯菜的村民2人。
脫貧攻堅政策實施以后,類似的聲勢浩大的場面時有發生,貧困村里出現了眾多外來人員,他們來自不同單位,帶著不同任務,從事不同工作。這些人反復出現,在當地社會中形成了一個新的群體,這個群體不僅在數量上具有一定規模,而且始終與當地人互動,并不可避免地產生相互影響。
故事二:從“人熟狗齜”到“狗熟人齜”。
“齜”是云南方言,表達一種憤怒、斥責的情緒和態度,與北方話的“生氣”“急眼”等詞類似,它既可作為動詞使用,亦可作為形容詞使用,責罵別人可說“齜”某人,而有人生氣則可說他/她“發齜”了。由于無法考證其對應的規范漢字是什么,我暫時使用“齜”這個音義較為相近的字。
筆者在擔任扶貧工作隊隊員時,第一次進寨子入戶就被狗“齜”了,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當時同鎮民政辦一位工作人員由村委會主任帶領,去一個以傈僳族為主體的寨子驗收危房改造項目。寨子在海拔較高的山上,離村委會有8 公里左右。車停在村口,一行人步行進寨,正是午飯過后,路上沒遇到村民,顯得很寧靜。寨中房屋依山而建,入寨道路位于中部,上下都有人家,每戶皆需向上或向下爬幾米陡坡才能進入,很少建有平整的階梯,多數時候要沿著自然踩出來的腳印坑上下。到了一棵老核桃樹旁,我們停了下來,應該是目的地到了,那戶人家在路上方,但他們沒有直接爬上去。
“阿表!”
主任仰頭朝著房屋喊了一聲,幾乎同時就有了回應,不是人聲,而是狂怒的犬吠,讓我心頭猛地一顫。一犬開口百犬齊吠,頓時狗聲大作,全寨子都喧沸起來。兩名干部沒有再喊,也沒有別的行動,只是悠閑地抽著煙,只有我警惕地環視四周,生怕有惡狗出現。過了好一陣子,隨著“吱吖”一聲,院門開了,一條黑影狂吠著沖出門外,旋即被拉住,狗是拴著的。
“睡一會呢?”主任問道。
“嗯,睡了一會。”這時我們才開始往上爬,我緊緊地跟在最后面,快到門口就停了下來。
“沒事,它不咬。”主人一邊勒住狗鏈,一邊往里招呼我。我心有余悸,幾乎貼著離狗最遠的大門右側溜了進去。
“這是云南大學的陳老師,我們村的工作隊員。”主任這樣介紹道。
“陳老師啊……坐,坐……”男主人滿臉笑容,但似乎不知對我這個陌生人說什么,便端過凳子,后又遞上香煙;女主人進屋找來杯子,從壺里倒水涮洗,泡上熱茶,拿出一盤堆著瓜子和糖果的零食,又捧出一大捧核桃。坐定后我們開始交流,我問了他的家庭成員、經濟收入、生活等方面情況,他們也問了一些我的個人情況,比如來這里多長時間了,老家是哪里的等。由于該戶沒有中學生或大學生,似乎對我的身份不太了解,也不太感興趣。驗收工作也是在閑聊中完成的,對照著文件上的標準查看建設情況,然后拍照、填表、簽字蓋手印等,整個過程大約20 來分鐘。離開時我禮貌性地夸贊他們家的核桃好吃,他們竟裝了一袋非要讓我帶回去,我堅持不收,最后村委會主任做主替我收了,當天工作完成得較晚,七八點鐘還沒回去吃晚飯,這些核桃還在路上解決了我們的肚子問題。
此后,我便開始了與這些農戶之間頻繁的交往,主要是工作需要入戶,也有一些人情上的往來,1年時間里,這個寨子我去了不下10次。每次去的目的都不同,但總是需要主人在家。逐漸熟悉后雙方交往也更加隨意,第一次見面時的客套也就不復存在,有時還會因為各種原因發生爭執,并不是每次去都會受歡迎。還有一個重要改變,就是我不再怕寨子里的狗了,一些去得多的人家,狗見著我就搖頭晃尾,不再叫了。因此,當有扶貧干部將工作隊入戶的過程總結為“從人熟狗齜到狗熟人齜”時,我發現不單形容貼切,居然還反映了一定程度的事實。
入戶是扶貧工作的常態,村干部和工作隊隊員幾乎都會跑遍全村每一戶人家。僅在每年兩次的動態調整期間,每個貧困戶至少有扶貧干部到訪3次,進行數據收集、數據核實和明白卡張貼或填寫,經常會出現扶貧干部入戶但主人卻不在家的情況,此時可能會打電話將他們叫回家。過于頻繁的入戶,一定程度上會干擾農戶的正常生活,遇到“狗熟人齜”的情況也就顯得十分正常了。
入戶工作的內容包括收入調查、材料分發、數據核實、房屋改造驗收、明白卡張貼、衛生檢查等等不一而足。每次調查除了完成特定任務外,都附帶著了解情況和宣傳政策兩項內容。所謂政策宣傳,除了向村民介紹脫貧攻堅的相關措施,還有很重要的一點是要讓農戶記住自己在這個過程中享受到多少實惠,以免脫貧驗收時他們說不清楚。同時,對于那些因未被評為貧困戶或者評上后脫貧而不滿的家庭,則需要做思想工作,讓他們了解未評上或者脫貧的依據,并在評估組來驗收時配合。這個工作是最難做的,因為很多人出于利益考慮,不承認自己家的收入已經達標,此時入戶干部不得不舉出諸多證據,而這些證據是很靈活的,雙方經常因此發生爭執,這也是到了后期入戶時出現“狗熟人齜”的另一原因。
盡管入戶過程中有各種情況發生,但不可否認的是,脫貧攻堅開展以來,各類干部和群眾的聯系密切得多了。即使這種聯系是因業務工作而發生的,但人作為社會性動物,相互交流得到的關系不會那么純粹,社會心理學的研究表明,不僅態度會影響行為,行為也會影響態度。21隨著彼此了解的深入,很大程度上也增進了感情,同時提供了更多相互協作、相互依賴的可能性。
國家與個體的聯系方式是考察鄉村社會整合的重要視角,費孝通認為中國傳統社會是依靠“雙軌政治”運行的,自上而下的皇權到縣一級就不再深入;基層事務由鄉村紳士和自治團體維持,形成自下而上的政治軌道。自上而下的政治軌道用強制的支配力下達命令,如果沒有中間力量的緩沖,就會把鄉村逼到政治死角,造成行政僵化。鄉紳和地方自治機構就是這種具有緩沖和橋梁功能的中間力量,能有效將自上而下的命令轉化為自下而上,維護基層行政的有效性。22田毅鵬認為,社會原子化危機的實質在于中間組織的缺失,個人直接面對組織化的權力,會導致精神上的無助和思想行為上的混亂,缺乏積極的、建設性的集體行動的資源和能力。中間社會的培育需要把自上而下的社會建構力量,與自下而上的社會自組織發育結合起來,形成政府、市場、社會三者良性互動的局面。23
那么,中間力量的產生是否只有自下而上這一條路徑呢?上述脫貧攻堅的實踐給出了否定的回答,在自上而下的政策實施過程中,也能形成旁逸斜出的中間力量。參與Y村和T村脫貧攻堅的扶貧隊伍中,絕大多數人對這個社區沒有任何直接的行政支配權,Y村的掛鉤幫扶單位是該市的人民銀行,駐村工作隊來自市發改委和云南大學,T村的掛鉤幫扶單位為縣委機構編制委員會辦公室,駐村工作隊來自云南大學。相關人員的編制仍在原單位,參與脫貧攻堅只是階段性任務,完成任務后就會換崗撤離,同時這些單位都有具體職能,對鄉村社區沒有直接的行政管轄權或業務指導權。我們可以說,雖然扶貧隊伍是自上而下派出的,卻是處于行政權力與村民個體之間的中間力量。一方面,扶貧干部能夠將上級的政策意圖傳遞給村民,督促村民落實相關措施;另一方面,村民在不滿意時不用完全服從扶貧干部的要求,為了有效完成工作,多數扶貧干部會將村民的意見反饋給命令下達者和政策制定者,并進行居中協調,促進政策的局部調整。因此,這些扶貧干部改變了村民直接面對組織化權力的狀況,成為剛性行政權力與社區具體實際之間的橋梁和緩沖力量。在脫貧攻堅實踐中,顯現出一條自上而下的中間力量建構路徑,對社會學研究中過于注重自下而上社會力量建構的情形構成一種反思性視角。
(二)行為實踐對文化觀念的建構
通常認為,集體行為實踐是由當地文化觀念引導的,但脫貧攻堅作為政策實踐,其行為指向來自國家意志和領導意圖,而非來自社區內部的制度規范和文化體系。因而在許多論者看來,這種外部力量驅使的實踐面臨著能否與社區內部文化邏輯進行調適的問題,而通常狀況下,統一、剛性的政策目標確實很難完全與多元復雜的具體社區文化完全吻合,沖突和矛盾時有發生,很多時候對當地文化起到破壞性的作用。脫貧攻堅過程中,這種沖突的確比較普遍,許多具體措施的執行難以到位,值得我們進行反思。然而,這并非問題的全部,另一面向的事實同樣不可忽視,即政策實踐對村落文化觀念的建構作用。
故事三:公共衛生掃除。
脫貧攻堅開展之前,T 村10 個村民小組的公共衛生幾乎無人維護,垃圾、雜物依靠歲月的洗禮自然消散。而戶內衛生也很堪憂,許多家庭人畜不分,在院壩中喂豬喂牛,滿地的飼料和糞便,夏季蒼蠅群集,氣味污濁。有領導要求貧困戶家里應做到“五個過得去”,即檢查組到達時能坐得下去、吃得下去、睡得下去、看得過去、說得過去,前四個都與衛生狀況相關。為了迎接脫貧驗收,村委會和工作隊組織了多次衛生會議,反復宣傳清潔衛生對脫貧驗收的重要性,并明確規定各小組掃除的任務和完成的截止時間。但等到臨近截止日期去檢查的時候,發現絕大多數小組并未開展任何工作,有兩個小組組織了,但是草草了事,大堆的白色垃圾還是原樣。多數人家戶內衛生也一如其舊,整個狀態就是臟、亂、差。當扶貧干部心急如焚時,村民卻不為所動,有的顧著自己的生產事業,有的冷眼旁觀,有位村民直接提出:“要掃路上的垃圾,村里面得出錢啊,隔壁村都是每人20塊一次。”這一說法得到周圍群眾的附和,但幾位村干部表示無法理解。
通過與村民的深入交流,筆者發現這種村干部難以理解的狀況,來自兩方面的觀念:環境衛生觀念和勞動報酬觀念。一方面,生產隊解體以后,組織村民參與公共事務的機制逐漸消失,在以經濟利益為中心的導向下,當地人并未真正樹立環境保護觀念。衛生觀念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加強,但人們通常只注重家庭和個人衛生,部分人在飲食和個人穿著方面的改變較大,對公共衛生的維護則沒有興趣。另一方面,當地人的個體權利意識興起,勞動力的市場價值越來越明確,只要是家庭之外的勞動,在他們看來就是應該獲得報酬的。這些觀念的結合,形成了自洽的文化邏輯,影響了他們的事實判斷和行為選擇。
通過宣傳號召來改變這種觀念,一時很難實現,村干部只好去想新的策略,發動各方力量來迫使村民行動。首先是責任落實到人,村干部和工作隊隊員每個人掛鉤一個村民小組,完不成任務就要自己負責。其次是發起一個“小手拉大手”的活動,即通過村小學的老師向學生布置任務,讓他們放假時督促家長參加清潔勞動。“家長不聽干部的,但聽孩子的;孩子不聽家長的,但聽老師的;老師不聽孩子的,但聽村干部的,相生相克啊。”一名干部打趣道。這招的確很有效,有孩子上學的人家后來都非常配合。通過一系列半強制的手段,總算將村民動員起來了。
筆者負責的村民小組在打掃衛生日,除極少數確實有事的村民外,幾乎戶戶參與,并且在勞動過程中并不抵觸或偷懶,反而熱情高漲,干勁十足,有說有笑,氣氛溫馨。這種情況出乎筆者的意料,這也顯示村民一旦行動起來,原有的觀念對他們的情緒不會有太大影響。
此后村委會又組織過幾次掃除,群眾響應積極了許多,只要定好時間,大部分人都會參與,無須再加強制。更重要的是,筆者在公路上還遇到幾次村民自發撿拾垃圾的情況,可見其維護公共衛生的意識日益增強。到當年年底,有的村民小組自發劃定了公共衛生責任范圍或排出各戶的值日表,不再有人因公共衛生掃除索要報酬;有的村民小組還開始謀劃籌集公共衛生資金。這體現了當地人衛生觀念的重要轉變:對“衛生”的理解從個人衛生擴展到環境衛生,而公共環境衛生則從“他人的事”或“與我無關的事”,變為“我們的事”。
打掃衛生本是村民日常生活中的小事,不過舉手之勞,與脫貧攻堅似乎也沒有多大聯系,直到筆者親身經歷后,才認識到它竟然牽涉如此多的問題,以致需要用文化邏輯、社會結構等宏大話語進行分析。當然,古人早就留下“一屋不掃何以掃天下”的哲言。但當村民不僅“一屋不掃”,而且向村干部要錢的事情發生時,仍然足以讓許多人無法理解。對了解社會學的研究者來說,這種要求并不荒唐,鄉村居民不關注公共事業并非新鮮事,費孝通就詳細論述過中國社會中的“私”,這與以“差序格局”為規則的傳統社會結構密切相關。24而且在一些集體經費較多的村里,確實是這么做的,凡是參加公共衛生掃除的農戶都發給一定的補貼。這些事實證明,鄉村社會公共事業的荒廢已是不容忽視的問題,“私而忘公”的文化觀念足以造成荒唐的行為發生。
從另一個視角看,這個問題的解決更值得我們重視。文化邏輯固然影響著人們的行為選擇和生活方式,但我們的經驗顯示,通過宣傳動員的方式改變村民衛生觀念的反復嘗試幾乎沒有效果。反而,以一種看似不合理、帶有強制性的策略,讓村民被動地接受,不僅促成了他們的行為實踐,而且重塑了他們的文化觀念。
由此,我們需要反思的是,在鄉村社會整合的過程中,只從文化象征、邏輯體系或社會關系入手是不夠的,而且很可能失敗。鄉村的原子化或“無公德個人”的產生,并非因為村民不受任何觀念原則限制,而是因為它本身已經成為一種文化觀念,已經成為指導人們行為的邏輯。在公共領域被金錢、權力長期占領的背景中,物質利益成為評判一切的原則,這已深入許多鄉村居民的觀念中。要改變鄉村的原子化狀態,重建社會整合,就必須改革這種觀念。但以一種觀念取代另一種觀念,以一種邏輯取代另一種邏輯,信息傳播或宣傳教育能起到的作用是很有限的。此時,實踐的重要性就體現出來了,通過行為實踐來重塑文化觀念,實現鄉村社會整合,是脫貧攻堅政策對鄉村社會重建的重要意義之一。
(三)村民公共意識的重建
改革開放后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生產隊解體,T 村經歷了與全國其他地區農村相似的發展過程。在公共生活方面,一個顯著的變化是會開得少了。20世紀八九十年代,村里每年還會開幾次會,以完成公糧收繳等不同任務;農業稅取消后,村里的會議變少了,經常一年下來一次村民會議都沒召開過,能讓村民聚集起來的只有三年一次的村委會選舉。在這個過程中,每家每戶各自為政,自己發展,“各人自掃門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對別人家的事情也關心得更少了,私下的議論當然不可避免,但絕不會公開評論。
脫貧攻堅開始后,村里的會議又多起來了,而且多了很多。貧困戶的產生需要經過多道程序,這些程序被稱為“三評四定”:“三評”指內部評議、黨員評議和村民評議,“四定”指村委會初定、村民代表議定、鄉鎮審定、縣確定。在這個過程中就會涉及許多會議,包括貧情分析會議、戶主會議、黨員會議、村民代表會議等等,每年都會舉行幾次。
故事四:貧情分析會議。
貧情分析會議是貧困戶評選的第一次會議,由各個村民小組召開,村干部或駐村扶貧工作隊隊員主持。此時小組內的所有村民都可以發表意見,提出自己認為符合建檔立卡貧困戶標準的農戶,形成最初的候選名單,如果沒有被列入這個名單的,在之后的評定中也就很難再加入。同時,貧情分析會議也是一系列會議中參與度最高、討論最開放的會議,因此對那些想獲取扶貧政策幫助的人來說,這個會議顯得格外重要。
貧情分析會議需要討論幾個名單,一是符合條件新納入建檔立卡貧困戶名單;二是符合脫貧條件退出建檔立卡貧困戶名單;三是錯評名單,即該戶不符合貧困戶條件,但被納入貧困戶的名單;四是錯退名單,即該戶不符合脫貧條件,但在上一次評定中被評為脫貧戶的名單;五是脫貧返貧名單,即該戶在上一年已經脫貧,但因各種原因返貧,需要重新納入貧困戶的名單。
貧情分析會議基本議程如下:主持人介紹完會議基本情況,然后進入戶主評議環節,讓村民依照程序逐項討論以上各個名單。發言和討論的結果及提出的問題都被記錄下來,留待核實信息后再作處理。最后,依據村民提出的相應名單進行舉手表決,并拍照留證。
多數村民對參與貧情分析會議表現出十分積極的態度,以筆者2017年在Y 村主持的一次貧情分析會議為例,當時共有3 個村民小組的成員參加,這幾個小組原本位于河谷,因水電站建設被淹沒,大部分人移民到外村,余下部分人靠后安置在本村移民點,因此3 個小組總共才37 戶,合并在一起評議。開會當日,37 戶戶主或代表無一缺席,會議討論十分激烈,絕大多數代表發言,就彼此提出的候選人的各方面條件進行評議,不時出現挑戰和質疑的聲音,耗時近3小時才結束,最終表決通過名單。
會議結束后筆者與村民進行交流,以下是當時的談話內容:
問:今天大家很積極啊!
答:討論一下也好,家家戶戶有意見就提出來,否則有意見也不知道去哪里說,不開會的話誰能管別人家的事呢?
問:村民開其他會有這么積極嗎?
答:(脫貧攻堅)以前開會聽的多,說的少,大家都不愛來,像今天這種晚上開嘛,來一半人就不錯了……扶貧了嘛,貧情分析,大家討論,各家各戶的情況都討論,有意見可以提,大家都有意見,都可以提,都來開會。
問:扶貧后開會多嗎?
答:多,經常開,但是貧情分析會爭得最厲害,意見最多,討論下也好。
貧情分析會議是脫貧攻堅實踐中村民參與公共事務的一個縮影,村民重新獲得了參與公共事務的平臺,并通過這些平臺加強了公共意識。脫貧攻堅以前,許多村民只關心自己家庭發展,現在則能夠關注社區生活。過往社區中的個體對其他家庭的事務漠不關心或是僅作為無聊時的談資,隨意說別人家的是是非非是不被認可的,若傳到對方耳朵里甚至會引起糾紛。但與脫貧攻堅相關的各種會議,讓村民不僅能夠對涉及公共生活的他人事務進行了解,還能進行評判,甚至在看法沖突時通過爭論和協商達成最后的共識。各種會議的召開,不僅為村民提供了接觸交流的機會,還提供了了解其他家庭情況以及社區整體發展狀況的平臺,使其意識到他們有權關心、評判和參與公共事務,也就重新建立了社區中的社會聯結。
故事五:扶貧動員與防疫動員。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后,中國迅速控制住了疫情,這與全國上下的統一行動和社會動員分不開。在Y 村和T 村,當地防疫動員幾乎沒有受到阻力,干部和群眾密切配合,順利度過了2月—3月最嚴峻的高峰期。當前,脫貧攻堅和疫情防控兩場戰爭仍在同時進行,二者有著密切聯系。
一方面,脫貧攻堅政策實施過程中的大量社會動員,為村民接受防疫動員奠定了心理基礎。1 月底,Y 村和T 村開始封村,禁止人員進出,毫無疑問村民的生活受到很大影響,但是絕大多數村民都積極配合疫情防控工作,政府工作人員和村干部在傳達防疫指令和防疫知識時,村民早已習慣這種宣傳動員,沒有遭遇抗拒。
另一方面,實施抗疫措施的和執行脫貧攻堅政策的幾乎是同一群體。2 月初,當其他崗位尚未復工時,Y 村和T 村的扶貧工作隊隊員剛過完春節就回到了崗位上。2 月6日,市扶貧工作聯席會議辦公室發出《致全市駐村工作隊員的一封信》,指出“面對這場突如其來的疫情,你們深入村組,參加基礎數據排查,防控知識宣傳和輿論引導,全力投入到這場沒有硝煙的疫情防控戰爭中……為保障全市人民身體健康和一方平安付出了辛勤努力”。除了上述工作外,工作隊隊員還參加守卡、封路等具體工作。2 月7 日,鎮扶貧工作微信群發出通知:“請各駐村工作隊在疫情期間無特殊情況不得擅自離崗,若有特殊情況必須嚴格遵守請銷假制度,若出現擅自離崗、離村情況,鎮駐村領導協調小組將照實上報。”可見,脫貧攻堅實踐中形成的社會力量,在危機出現時也能起到很好的社會整合作用。
此外,當地村民和商戶為防疫和扶貧工作人員捐贈了大量物資,包括酒精、方便面、礦泉水、火腿腸、大米、食用油、飲料、雨傘等,Y 村村民禹某捐贈了1 頭豬給村委會和工作隊,位于Y村的水上飯店經營者捐贈了1噸江魚給全鎮抗疫人員。
可見,脫貧攻堅和疫情防控都產生了功能性的需求,當地村民為應對這些需求,重新建立起對社區的公共意識,個人主體在功能性的需求中得以回歸。面對共同的脫貧目標或疫情危機,鄉村社會的主體意識被喚醒,社會聯結重新得以實現。
四、鄉村社會的功能性整合
在以前的研究中,中國社會整合的模式被分為先賦性整合、行政性整合和契約性整合,來自歷史傳統的以血緣和地緣關系為聯結的整合模式被稱為先賦性整合,集體化時期以組織化和行政權力為手段的整合模式被稱為行政性整合,而改革時期市場和中間組織興起,契約性整合開始占據主導地位。25對于如何重新實現鄉村社會整合的問題,有的學者注重內生文化的力量,認為根植于鄉土的文化觀念和價值體系是實現社會整合的關鍵。26還有學者認為這種文化力量表現在三個方面:村莊內部的習慣法,村莊精英的活動及其權威,民主自治的實踐。27顯然,這類觀點希望實現的是先賦性整合。另外一些學者從農村合作組織28、村民自治制度29等視角探討鄉村發展問題,無疑重在契約性整合。
脫貧攻堅實踐中,新的鄉村社會整合正在產生,但這些新的整合模式很難吻合以上三種模式。新的中間力量和社會聯結的產生,既非傳統的以血緣、地緣為基礎文化邏輯驅動,亦非基于某種契約關系,因此可以肯定,新的整合模式不屬于先賦性整合或契約性整合。值得討論的是行政性整合,扶貧隊伍和群眾之間的聯系確實肇始于行政力量,但是,群眾之間的聯結和公共意識的重建卻不是行政干預的結果。而扶貧隊伍本身不具備行政權力,不能通過強制手段整合或動員群眾。最重要的是,新的整合不是行政力量的直接政策意圖,政府執行這些措施的目標在于經濟建設和民生改善,在于脫貧攻堅。而社會整合的實現,一定程度上是脫貧攻堅政策的附帶效果。
基于此,我們可以認為有一種新的力量促成了當前的社會整合,這種整合模式可以被概括為功能性整合。不管是中間力量的形成,干部與群眾關系的密切化,還是新的觀念的出現,都是建立在脫貧攻堅基礎之上的,是出于一種功能化的需要。功能性整合只是一種新的概括,而非新的事實,傳統社會的整合力量也具有很強的功能性,宗族、地方自治團體等除了文化規范和認同的聯結外,也發揮著很大的現實作用,維護著成員的利益,并擁有大量資源,如公田就在傳統社會整合中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毛澤東1930年調查的尋烏縣,公田占比高達全部耕地的40%,其中60%為族產,20%為與信仰相關的廟產,10%為學田,還有10%為橋會、路會、糧會一類的社會公益田地。30費孝通1939年調查的祿村,團體所有田面積240 畝,占全村農田的27%,而最大的團體地主擁有土地50畝,超過任何私家田地面積。31相反,現代鄉村原子化的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社會整合力量的功能性下降,鄉村社會缺少公共服務的提供,社區聯結性必然降低。改革時期,鄉村公共服務主要由鄉鎮設置的“七站八所”提供,但在實施過程中它們主要承擔管理職能而非服務功能,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國家對鄉土社會的進一步整合。32
可見,現實需要成為新的社會整合的契機,脫貧攻堅需要人力資源,于是建立了工作隊和扶貧隊伍,產生了行政權力與村民個體之間的中間力量;需要程序,才有了各種會議機制和參與機制,產生了新的公共意識;需要決策精準,才有了頻繁的干部入戶行為,加強了社區與外部的聯系;最重要的是需要執行,村民在各種因素作用下開展行動,在實踐中形成了新的規范性力量。
五、結語
隨著中國進入新時代,鄉村社會也發生了巨大變遷,進行著許多影響深遠的實踐,脫貧攻堅、鄉村振興等政策的實施,正加劇這種變化的發生。我們印象中的鄉村問題,在這個過程中也在不斷變化,有些已經逐步得到解決,有些呈現出新的特征。這促使我們緊跟現實,考察各項鄉村政策實踐對社會發生的影響。脫貧攻堅實踐的影響已經超出經濟民生層面,導致新的社會整合過程,這是建立在現實需求基礎上的。
消除貧困是一個綜合性的目標,需要的不僅是經濟收入的提升,還有社會保障、生活質量方面的要求,而對實施成效的考核,也有群眾滿意度方面的指標。這就導致以往行政命令式的強制措施難以執行,需要各種力量參與社會整合。通過持續的行為實踐,鄉村社會整合不同程度地得以實現。在這個過程中,形成了一種與以往不同的社會整合模式,即功能性的社會整合。功能性社會整合是建立在現實需求之上的整合模式,它可能由不同的力量驅動,有不同主體參與,但最終是為了實現某個特定目標。
鄉村社會整合需求的來源并不固定,當前其動力主要是脫貧攻堅,脫貧攻堅結束后,這種需求可能會消失,其中一些業已實現的社會整合也可能會再次解體,但不可否認的是,其中許多聯系能夠繼續發揮作用,如村民的公共意識、新的環保規范等就是如此,這類整合因脫貧攻堅的契機而興起,卻不會隨脫貧攻堅結束而終止。更為重要的是,這種從實踐中探索出的社會整合模式將會影響未來的實踐,在新的社會整合需求出現時,仍可以繼續發揮作用。
今后,我們在探尋鄉村社會重建或整合的方式時,不僅應考慮當地的文化傳統或組織力量,也應更多考慮當地的社會功能性需求,以這些基于當地現實的需求為引導,社會整合或許不用刻意去追尋,而是一個自然而然的過程,這一思路對鄉村振興戰略或許有一定借鑒意義。
注釋:
①田毅鵬、呂方:《社會原子化:理論譜系及其問題表達》,載《天津社會科學》2010年第5期。
②周大鳴、廖越:《我們如何認識中國鄉村社會結構的變化:以“原子化”概念為中心的討論》,載《廣西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4期。
③孫立平:《轉型與斷裂:改革以來中國社會結構的變遷》,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255頁。
④同注①。
⑤張良:《鄉村公共空間的衰敗與重建——兼論鄉村社會整合》,載《學習與實踐》2013年第10期。
⑥劉銳、陽云云:《空心村問題再認識——農民主位的視角》,載《社會科學研究》2013年第3期。
⑦嚴海蓉:《虛空的農村和空虛的主體》,載《讀書》2005年第7期。
⑧《費孝通文集》第5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354頁。
⑨《費孝通文集》第4卷,第317—318頁。
⑩同上,第341頁。
11 羅志田:《科舉制廢除在鄉村中的社會后果》,載《中國社會科學》2006年第1期。
12 同注③,第139—141頁。
13 同上,第254—255頁。
14 [美]閻云翔:《中國社會的個體化》,陸洋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357頁。
15 賀雪峰:《新鄉土中國——轉型期鄉村社會調查筆記》,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3—5頁。
16 吳重慶:《無主體熟人社會》,載《開放時代》2002年第1 期;吳重慶:《從熟人社會到“無主體熟人社會”》,載《讀書》2011年第1期。
17 曹海林:《村落公共空間與村莊秩序基礎的生成——兼論改革前后鄉村社會秩序的演變軌跡》,載《人文雜志》2004年第6期。
18 趙旭東:《從“問題中國”到“理解中國”——作為西方他者的中國鄉村研究及其創造性轉化》,載《社會科學》2009年第2期。
19 同注②。
20 當地人對村綜治員、農管員、護林員、信息員等業務人員的戲稱。
21 [美]戴維·邁爾斯:《社會心理學》,侯玉波等譯,北京:人民郵電出版社2016年版,第126—133頁。
22 同注⑨,第336—340頁。
23 同注①。
24 同注⑧,第332—339頁。
25 同注12,第9—12頁。
26 孫慶忠:《離土中國與鄉村文化的處境》,載《江海學刊》2009年第4期。
27 同注17。
28 胡振華、陳柳欽:《中國農村合作組織的社會學分析》,載《武漢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2期。
29 藺雪春:《當代中國村民自治以來的鄉村治理模式研究述評》,載《中國農村觀察》2006年第1期。
30 《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5—112頁。
31 費孝通、張之毅:《云南三村》,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9頁。
32 徐勇:《“服務下鄉”:國家對鄉村社會的服務性滲透——兼論鄉鎮體制改革的走向》,載《東南學術》200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