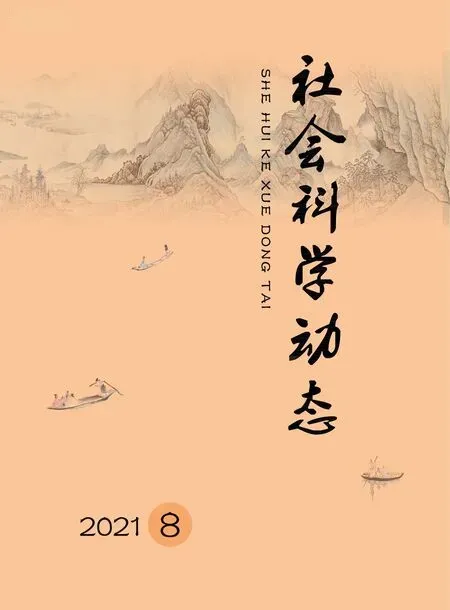中國古代情理法之當代借鑒
王君怡
一、情理法的概念
目前,不論是在學界還是現實生活中,“情理法”一詞有兩種概念詮釋:一種是將情理法看作是由“情、理、法”三個具有獨立含義的字組合而形成的并列解釋短語;另一概念解釋就是將情理法解讀為我國古代講求情理思想傳統所形成的具有情理精神的法律,將“情理法”看作一個整體,是為“情理”法。前者的概念常出現在法律相關的網絡文章及報紙的標題當中,如:《法官“情理法”并用破解執行難題》等。其內容一般為通過“動真情”、“擺道理”、“法兜底”三者并用來破解司法實踐活動當中的問題,或評價判決結果于情于理于法皆公平合理。在裁判文書當中也可以見到同樣的用法,例如法官經常措辭:“于情理法皆不符”“從情理法方面綜合考慮”等,通過“皆”“綜合考慮”這些搭配字眼可以知曉其采納的是“情、理、法”的并列解釋概念。
但與此同時,在裁判文書當中也有相當部分采納整體性概念的論述,如在裁判文書中大量出現的“符合/不符合情理法”的表述,就是將“情理法”一詞作為整體性概念來進行運用,這是因為“符合情理法”這樣的論述出現在以法律為準繩的司法用語當中;若用并列解釋概念來進行理解,就應該解釋為“合情、合理、合法”的意思,即符合“情、理、法”三個規范標準;而對于法律裁判而言,法律應該是唯一的標準,從而體現司法的獨立價值。在學術論文的探討中,更為多用的是作為整體性的情理法概念。從最早由范忠信、鄭定、詹學農三位學者撰寫的《情理法與中國人》一書開始,法學界關于情理法的學術討論基本都是圍繞作為整體概念的情理法展開的,從其他相關的學術探討題目當中也可見一斑。本文的探討亦是從“情理法”的整體性解釋概念入手,探討基于中國幾千年封建宗族制發展出融天理、國法、人情于一體的法律規范,從而更加深入理解情理法的內涵。
(一)天理的概念
獨立概念中的“天理”,包含了倫理道德、自然規律、自然法的含義。所謂“存天理,滅人欲”,最早出自《禮記》當中: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詐偽之心,有淫泆作亂之事。其意思就是說如果人之沉溺于“本我”的物欲,不能克制自己,那就一定會產生有悖常理的心理,從而做出害人的事情,那也就不能稱之為人了。這也就是人的“本我”層面,所以需要控制自己的欲望,就需要尋找“自我”,遵守天理。作為自然規律的天理,則有“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然后調理四時,太和萬物”、“禁伐當罪,必中天理”的使用。還有就是探尋萬物本原的天理,也就是作為自然法含義的天理①。西漢董仲舒認為:“王道之三綱,可求于天”,“君臣父子夫婦之義,皆取諸陰陽之道”②。天理作為絕對的精神實體,是萬物的本原,是宇宙最高實體或宇宙普遍法則,相當于自然法。所以天理其實是古代法律中的精神來源與終極理想。
(二)人情的概念
所謂“人情”,其實就是人們心中的自然情感③。首先人情的含義在《禮記·禮運》中有闡述:“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七者弗學而能。”所以人情的含義,其實就是指人的喜怒哀樂,也就是指作為人所產生的各種情緒。其次,“人情”也可以進一步發展到“人之常情”的含義,也就是指人對于相同事物所產生的普遍的情感反應,以及大多數人都會產生的情感喜惡偏向,也可以稱之為“民情”、“民意”④。再次,“人情”還有“情面”的含義,因為交往而產生的熟悉的情感,因為熟悉所以會產生感情。最后,“人情”還有物質性的禮物的含義,作為人際交往之間的禮物而存在。但是物質性的禮物,如果超出了合理的限度,不加以規制的話,就會產生“私情”,而“私情”會使人在面對兩難境地時出于物質利益的考量而作出不公正的判斷,從而作出傷害他人的事情。以上就是對于“人情”的含義的四種解讀。
(三)國法的概念
“國法”相對于“天理”、“人情”來說,其含義是更加確定的,指的就是國家制定的法規范。但是古代的法規范當中,包含了與天理和人情密不可分的情理精神。情理精神是古代法律的靈魂,霍存福先生也曾經在《中國傳統法文化的文化性狀與文化追尋》一文當中將“情理”作為中國傳統法文化的根本性格。⑤在我國古代立法當中,處處都體現中國古代人民的良心與理性。法律當中的原心定罪、存留養親、矜恤制度都是情理的要求。中國古代的法律當中也多有體現對婦女、兒童、老人的關愛精神,以及對根據血緣關系情感關系的親疏程度來進行不同的法律區分,情理處處體現在古時的法律、司法書判,乃至世代相傳的民間俗語當中。⑥
既然三者之間可以成立并列關系,那么他們的含義至少是有重合的,具有類似的性質。“人情”也就應該具有“國法”的規范意義,而非單指人際交往當中的私情,國法與私情是不可共存的。與此同時,“天理”的理本身也具有規范性的含義,三者之所以能夠并列成為一個整體性概念,其原因也是因為“情”、“理”、“法”三者都具有規范性的含義,由此構成了具有整體性意義的情理法。
二、情理法的特點
深厚的情理精神存在于古代的天道天理、禮儀刑罰、民心習俗當中。情理法既然作為人治的產物,也必然始終從普通人的心理感情出發看待法律問題。情理法在法律與人情之間本著情罪相適應,以人為本的精神和原則進行裁決,展現出了其獨有的特點。
(一)注重個案實質正義
情理法最突出的特點就是追求個案實質正義。因為追求個案正義,所以針對每個案件不同的自身情況,會產生適合其自身的特殊規則⑦,司法裁判的個別化特點在情理法的裁判中表現得淋漓盡致。司法個別化就是法官根據案件的事實來進行判斷,而非緊緊將判決依附于法律規則,其注重對案件事實的考察,具體情況具體分析,針對個案進行各方面不同的評估,最終根據不同的案件事實得出最得當的裁判結果。法官的工作價值因此也體現在對案件細節進行帶有個人主觀情感的判斷當中,而個人情感的側重,會使得裁判者在判決中運用以結果為導向的思維,因為追求實質正義背后是追求裁判結果的合理性,每一個具體案件的判決結果最能直接影響每個人的生活,也只有結果才最直接關乎百姓利益。所以我國古代的情理法為了個案的實質正義,追求最合乎情理的裁判結果,傳統的父母官在對案件進行審理時,總是會將國家法律規范之外帶有經驗色彩的“人情”與“天理”納入案件的考量,從而達到滿足民眾審判心理預期的目的,判決具有濃厚的主觀性色彩。
(二)司法裁判緣情定罪
我們在此討論的“情”更加側重于我們在上文當中所探討過的“人情”。人情當中的情,都與個人主觀經驗息息相關,是人基于對外界的客觀事實的感知而日漸形成的,它們是人類生活所產生的經驗以及包括法律在內的一切規則賴以產生的知識基礎,所以帶有人的情感經驗的“情”與“法”在本質上存在內在一致性。
正所謂“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邏輯而在于經驗。”作為人情世故經驗總結的“人情”也成為情理法裁判當中不可或缺的考量因素,對“人情”進行斟酌,實現案件的“情”、“罪”相適應,是父母官進行裁判的重要內容和任務。情罪相適應思想的背后是合理性與合法性之間的衡量,最重要的問題就是解決在法律的框架內如何作出兼具合理性的裁量。在通常的情況下,合法性與合理性兩者并不沖突,但在疑難案件當中二者還是時常發生沖突,對于司法當中的裁判者來說,作出具備合法性的裁量并非難事,但是要同時周全經驗合理性卻并非易事。情理法將情罪相適應作為其突出的特點與原則,恰恰體現了其內核是建立在裁判合理性之上的,對于作為經驗的“人情”的考量使得裁判者往往會訴諸法律外的因素,重實體,輕程序,所以更加注重對審判結果的考量,審判結果就體現在罪行的輕重懲罰當中⑧。
因此,裁判者的裁判邏輯更多是以結果主義為導向,而不甚關注對律令規則本身邏輯的遵循,其背后就是“以刑制罪”的思想,以刑制罪是古代傳統司法的基本邏輯思想。除此之外,情理法中的緣情定罪體現了裁量過程中對事實經過以及過程中人的感情的考量,更加注重對案件過程的考量⑨。反觀我們當下,我們雖然對于案件結果的推導更加注重邏輯的三段論,但是卻往往忽略案件事實的發生過程環環相扣的過程,對于案件事實更多的是根據構成要件對號入座來定罪,司法裁判更形同于自動販賣機的機械處理。
(三)司法過程具有開放性
因為情理法對于情罪相適應的追求,所以在面對個案時,裁判者一定會基于人情的考量突破法律的限制而對案件作個殊化的裁判。與此同時,基于“以刑制罪”的后果主義思維,使得裁判者在司法過程當中一定會尋求法律之外的依據為裁判的合理性尋找出路,這就導致了裁判依據的開放性。比如在古代最為常用的裁判技術比附援引當中,裁判者在遇到案件量刑更為適宜合理的“彼律”,常常會拋卻構成要件全然符合的“本律”。還有在因案生律的案件當中,實際上就是裁判者利用自己的自由裁量權突破了現有律令的限制,轉而自己改判生成新例或尋求皇帝的最高權威來突破既有前例的限制,其目的都是為了使得裁判結果更具有合理性。所以這些裁判技術的運用都體現了裁判者為了為合理性開路而將司法外的裁判依據納入司法過程當中,使得法律體系之外的“人情”得以滲透進入司法當中。當然,因為在我國古代并沒有分權的概念,省級以下的地方父母官身兼行政、立法、司法、監察多方面的職能,所以并沒有發展出獨立的司法權,當其他權力和司法權混為一體時,情理法就應運而生,就讓帶有人情性質的“情”成為法官定罪量刑的裁判依據。
司法過程的開放性還體現在審判職業人員的開放性上,我國古代一般的案件從州縣一級的衙門上訴到最高的權威皇帝,一共有六個審理級別,所以在案件的審理過程當中,隨著案件的上訴,審級越高,參與審判的人員就隨之越多。以從明朝開始的九卿會審為例,凡是特別重大的案件,二次翻供不服,根據皇帝的詔令,可由九卿會審,大理寺卿、都察院左都御史、通政使以及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尚書共同審理,最后由皇帝審核批準。經過多方的參與商討,不同部門人員的參與,因其各方參與人員的身份不同,其對案件不同情節的考慮角度以及標準也會有所不同與側重。經由多方建言,可以從很大程度上防止案件的裁判過度偏離人情的軌道,但與之相應的裁判司法專門化與職業化就會弱化。
情理法能夠在我國古代有如此豐富的實踐與理論基礎,與我國古代天-君-民的治理結構是分不開的。雖然皇帝自稱天子,代表了上天授權的權威,但實際上這種權威并沒有可以與之抗衡的制約機制。從我國古代的文明來看,其從不認為嚴格遵從事先存在的法律規范得出裁判結果的這一過程具有重大的司法價值,司法所追求的價值也是以社會普遍價值追求為基礎的,所以會竭力尋求合乎情理的解決方式。回看我國古代的司法裁判,雖然不乏依法斷案的鮮明事例,但也發現大量的情理法實踐的存在。
三、從當代法治看情理法
情理法的特點是通過我們對古人具體司法實踐而得出的,所以為了能夠更好地剖析情理法傳統,我們還應當從情理法的運用出發,進一步辨析情理法與當代法治之間的沖突與矛盾。
(一)個案正義與法律普遍性之沖突
實現個案正義與法律的普遍性兩者之間本身并不沖突,但無論是什么樣的法律都有著其本身的局限,不可能將復雜的社會問題以及具體情境規定得面面俱到。法律只能確定社會生活事務當中的普遍性規則,想要通過不斷制定、修改、完善法律而使得法律可以無所不及的涵蓋人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法律中心主義”只能是一種空想。個案永遠具有其本身的特殊性,所以同具有普遍性的法律相較而言,個案的個別性與法律的普遍性兩者之間總會有不能填補的縫隙。而情理法對于個案實質正義的追求,為了滿足個人以及大眾的主觀情感需求,勢必會試圖將個案所產生的具體規則引入司法過程的定罪以及量刑當中,使得與所適用的法律不相關的事實性的“情”被吸納而成為裁判的依據和標準,用來發揮“人情”的作用,最終影響裁判結果的得出⑩。最終,情理法當中的裁判結果會犧牲法律適用的普遍性以及當代法治所強調的罪刑法定原則。
我國古代的法律實際上是一種身份法,不管是“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還是“準五服以制罪”,都體現了面對不同身份的人法律要進行區別對待,裁量案件要根據具體情境做具體分析與不同的處理?,充分體現人情治家、治國、治天下的思想。人的情感是流動的、主觀的甚至是多變的,但法律的內在要求價值首先就應當是可以預測的、穩定的。實質正義固然也是法律的重要價值,但要實現法治,可預測性就要作為優先于實質正義的價值而存在。所以古代的情理法并不是人人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面對不同的身份,人們的情感面向是不同的。情理法當中受儒家思想文化影響使得法律失去了普遍性,失去了普遍性也就無法保證法律當中人與人之間的平等,而人人平等恰恰是我們當代法律中最重要的原則。
(二)緣情定罪與法治之沖突
情理法確實能夠使得個案的人情與處置的罪罰達到一個較為均衡的狀態,使得裁判更具合理性,更符合民心民意。古代情理法當中的緣情定罪所達到的情罪相適應的處理,與我們當代法律當中的罪責刑相適應的原則有一脈相通之處。我國刑法第五條規定了罪責刑相適應原則:“刑罰的輕重,應當與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擔的刑事責任相適應。”在古代的情理法傳統中,司法者為了追求個案裁判的情罪相適應,運用比附援引、因案生例等裁判技術對案件進行糾偏。
當代的司法者,除了受到法律當中罪責刑相適應原則的限制,同時也必須遵守法定的司法技術方法,還要受到平等原則、罪刑法定原則、法律邏輯的三段論的約束。在追求實體正義的同時,也必須遵守程序法的制約,也就是不光要關注案件的實質正義,還要遵守案件的程序正義。按照嚴格的法律程序認定個案事實與證據,不可妄自添加“人情”和與定罪構成要件無關的事實性的“情”作為考量因素。因為緣情定罪會讓裁判者陷入司法后果主義的泥沼當中,從后果出發,司法者往往就會置程序于不顧,只關注實體結果的正義;從結果出發,進而為結果尋找合法性的依據,這種逆向的司法行為模式與罪刑法定原則背道而馳。尤其是在比附援引的司法裁判技術的運用當中,比附援引看似是在以之前已經裁判生效的案件作為指引,但是實際上,其反而成為給裁判者有了援用他律的借口。司法者出于對案件最終結果的情罪均衡的考慮,并沒有援用在適用條件上本應該適用的條律,而是適用刑罰的結果與本案更加契合的其他條律。這明顯違背了罪刑法定原則,也違反了最基本三段論的法律推理邏輯,所以情理法的情罪相適應的思想與當代的法律思維有多處的沖突與背離,是不能夠相容的,到了清末比附援引制度的存廢也一度爭議不斷?。
(三)裁判的開放性之沖突
在情理法的傳統當中,司法裁判的開放性主要體現在裁判依據、裁判參與人員中。在情理法的語境下,司法權始終是讓步于行政權的。在儒家思想文化的影響下,法官斷案不僅僅是斷案,還需要考慮仁義禮智信的五常,有時候為了達到殺一儆百的震懾效果,還會蓄意加重刑罰的處罰,為了通過對犯罪行為判處重刑并用這種“以刑去刑”的手段達到有力震懾潛在犯罪的目的,但這對個案犯罪人來說是極不公平的。從當代刑罰來說,刑罰的目的不應該是通過震懾來阻止潛在的犯罪人員今后不犯罪,而是要彰顯規范指引的意義,從而引導社會一般人規范辦事,以加強對刑法的認同感,從而達到利用規范來預防犯罪的目的?。依照法律之外的經驗和標準來定罪量刑,顯然突破了法律的限制,違背了基本的罪刑法定原則和法治精神。
除了裁判依據的開放性以外,司法官員身份的多元化也反映出法律職業的多元化。九卿會審等審判人員的組成方式讓本不屬于司法審判專業的官員行使一定的審判權限,同時與西方法治的“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的法治精神不同,我國古代皇帝的最高司法權威也顯示出司法人員的開放性與非獨立性。但是司法的職業化以及專業化,對于當代法治來說至關重要,司法權力的獨立行使作為一門具有獨立價值的技藝,在社會分工如此細化專業化的當代社會更加必不可少,司法職業化以及司法專業化也一直是我們當代法治發展的必然趨勢。所以情理法吸納不同職業的官員進入司法審判當中,雖然是為了使得裁判結果集思廣益從而可以保證從多角度的合理性,但其實與當代法治的司法職業化以及專業化的趨勢不甚相符。因為司法職業化的背后是司法的獨立精神,司法具有獨立性是當代法治司法文明的標志。
(四)情理法與當代法治沖突深層原因分析
綜合以上沖突我們可以看出,情理法與當下法治之間的沖突主要體現在與罪刑法定原則、人人平等原則、司法職業化以及法治精神等等方面。情理法對不同身份的區別對待也是出于對情罪相適應精神的延伸,為了使裁判能夠達到情罪相適應的結果,所以情理法對于不同身份區別對待。如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對于身份高貴的達官貴人予以更多“情面”,所以情罪相適應的精神讓法官為了達到兩者相宜的狀態往往突破了法律的罪刑法定的限制?。從司法職業化的角度來看,由于我國古代省級以下的官員分化程度不高,地方父母官主管著司法、行政等全方位的職能,這與古代皇帝兼具最高司法權威和行政最高權威是一致的。而究其根源,是因為我國古代是皇帝作為最高統治權威的“人治”社會,所以無法孕育出“法治”的精神與概念。
作為人治產物的“情理法”將關注點主要放在了實質合理性法的追求上,馬克思韋伯曾對法律的合理性作出過區分,在法律當中,“合理性”不僅僅包括案件的實質合理性,還包括案件處理過程中的形式合理性?。西方的法治發展是向著不斷日臻完善形式合理性的趨勢發展的,而情理法則是一直在為追求案件的實質合理性尋求多方權力的幫助。韋伯認為實質合理性不僅是不能追求的而且也是永遠無法真正實現的一種價值,東方的法律在他看來就是一直在追求實質合理性的法律,所以他稱中國的法律為“卡迪司法”?,人治下的情理法無論如何都無法實現自己的終極追求。
四、情理法對于當代法治的啟發意義
不可否認的是,中國傳統的司法的確展現出了對實質和理性的追求遠遠超過了對形式合理性的關注的特征,但我國從清末沈家本修律開始,就逐漸學習了大量西方法律制度、法律思想及原則,我們擁有源遠流長的情理法的法律傳統,吸收和借鑒了西方的法律文化,并早已步入了法治的道路。
(一)注重個案實質正義對當代法治的啟發
前文當中我們提到,情理法當中的“情”具有更多人情的含義,當代的法律程序里要求裁判者對運用三段論以及合法的解釋方法對案件的進行事實上的認定,但是法律總是有著其滯后性的特點,也總會有其鞭長莫及的法律空白和漏洞,而社會事務變化萬千,立法者無法預料到所有的社會情形。因此每個案件都有其獨一無二的特殊性,有需要裁判者進行法律填補之處,法官就需要考慮立法者未曾考慮到的情況。除了案件適用的法律規范所需認定的事實之外,裁判者還需要注意到與定罪所需認定的法律事實在邏輯上相互串聯的其他事實,實際上這些事實也具有一種弱規范的效力,應當被納入案件的考量中。裁判者在法律文書的說理部分,不應當只關注法律事實的成立與否,還應該注意到這些作為事實的“情”所反映出的事實邏輯,并通過運用裁判技術、解釋方法以及特殊制度把他們納入裁判理由當中,加強裁判說理。
正如哈貝馬斯所言:“規范之運用的詮釋學過程可以理解為事態之描述與普遍規范之具體化兩者交叉的過程。最具有決定意義的是以下兩個方面的意義等值關系:一方面是作為情境之理解的組成部分的事態描述,另一方面是確定規范之描述性成分,也就是確定規范之運用條件的事態描繪。”?所以我們可以看出,法官在進行裁判的過程當中,不能僅注重與定罪所需的案件構成相對應的事實,還要關注能夠幫助我們理解這些事實的與之相連的其他事實。如在山東聊城發生的“于歡案”中,不能僅僅只關注于歡個人的殺人事實與殺人罪的事實構成要件,還應當關注于歡殺人之前一系列母親被辱的事實與情境。在一審案件當中,裁判文書當中對于“辱母”這一情節輕描淡寫:“杜志浩等多人來到蘇銀霞和蘇銀霞之子于歡所在的辦公樓一樓接待室內催要欠款,并對二人有侮辱言行。”但這一情節,其實是于歡激憤殺人的重要原因,是于歡激憤殺人的直接導火索。而二審當中,裁判文書對“辱母”情節著墨頗多,其中描寫到:“杜某2用污穢語言辱罵蘇某、于歡及其家人,將煙頭彈到蘇某胸前衣服上,將褲子脫至大腿處裸露下體,朝坐在沙發上的蘇某等人左右轉動身體……又脫下于歡的鞋讓蘇某聞,被蘇某打掉……”以上的情節描述,表明二審對“辱母”情節進行了強調,并且通過論證將這一情節與最后的量刑結果通過三段論的方式建立了邏輯關聯,通過進行更加充分的裁判說理使于歡得到了一個更公正的裁判結果。所以在判決當中,不僅要關注專業的法律說理,還要注意事實說理,而我國裁判文書當中普遍存在忽略事實說理的現象,簡單羅列證據,陳述法律事實,直接作出裁判,常常忽略了事實與證據之間的呼應。司法還需要注意其他的事實性的“情”與案件的關聯,從而作出合理的裁判。情理法中對個案特殊性的考量,提醒當代裁判者不能局限于僵化的法律三段論,要在注重事實經驗的基礎上,進行更加充分的事實性邏輯說理。
(二)緣情定罪對當代法治的啟發
情理法當中的緣情定罪達到的罪情相適應,與當今法律的罪責刑相適應原則的內在精神是相似的,區別在于當代法律并非從后果主義出發,而是通過大前提結合小前提得出最終的結論。情理法的緣情定罪具有明顯后果主義的傾向,往往是先根據情感導向罪行的輕重,決定處以什么樣的刑罰,再根據刑罰的輕重來確定罪名,從而達到懲罰與罪行相適應的結果,其定罪思路是“以刑制罪”。而當代法律當中的定罪則是先定罪,最后根據罪名和情節確定量刑的幅度,相比較之下,機械適用三段論的方法在某些疑難案件中卻暴露出裁判僵化的問題。
在上文提到的于歡一案中,一審以故意傷害罪判處于歡無期徒刑,引起社會嘩然。根據法律規定的邏輯判斷,于歡有故意傷害的事實和主觀故意,罪名沒有可以更改的余地。但是在量刑上,二審法院通過使用正當防衛(防衛過當)改判于歡有期徒刑五年。從于歡一案當中,我們可以看出,通過“以罪制刑”的思路會出現僵化的情況。但是二審法院通過重新審視案件經過,還原事實真相,考慮用社會一般人標準在于歡當時所處情境下的情感反應,認為其應當成立正當防衛,讓“正當防衛”條款不再只是一紙空文的僵尸條款,真正在司法實踐中將“人情”融入審判,從而認定于歡成立正當防衛將一審的量刑下調,改判于歡有期徒刑五年的處罰。顯然對于被告人來說,是他罪還是彼罪都不甚重要,能夠成立正當防衛從而減輕量刑才事關被告人的切身利益。雖然二審判決并非是通過從后果主義出發先確定合適的刑罰再來調整案件的定罪,但是我們可以看出在疑難案件中,通過情理的思考可以給予被告人更加合理的處罰,從而實現案件的罪情相適應性,這是值得我們繼續深思改進之處。情理法思想當中對于量刑輕重的重視是當代法律思維所應當學習的地方,其所展現出的對“人”的思想情感關懷以及罪情均衡的考量可以為疑難案件的處理提供思路。
(三)裁判的開放性對當代法治的啟發
對于裁判過程的開放性,我們也需要警惕行政力量以及社會輿論對法律裁判的干擾。雖然于歡案通過對經驗性的“人情”的運用,使二審在裁判說理部分又重新對辱母情節進行了著墨說理,但是我們也要看到,輿論在二審當中的介入,將于歡案中辱母的情節予以渲染,激發了我國社會大眾幾千年來所形成的孝念觀,為于歡成功塑造了忠孝的形象。在輿論洶涌的浪濤倒逼之下,二審才開始進行了案件的合理性建構,在輿論場域中形成的二審判決,通過法律原則的適用完成了對于歡案二審判決合理性的合法性證成。所以,我們可以看出于歡案當中,案件的合理性建構實則是在公權力之外的輿論力量的壓迫下而開啟的,這體現了我們當下司法還會受到輿論影響的現象。
此外,對于司法裁判參與人員的開放性,像我國引進人民陪審員作為司法過程的輔助人員,《刑事訴訟法》當中也引入了“具有專門知識的人”作為專家輔助人參與司法過程,我們需要進一步通過制度化的方式將其合法化,從而將其變為我們形式合理化的法治的一部分。將其他領域的專家學者納入司法活動的過程,并非是要他們干預專業的司法裁量,而是需要他們作為一種輔助性的力量,幫助法官更加客觀地斷案,以保證司法裁判的權威性。我們的情理法傳統在思想上雖然有同當代法治相沖突之處,但其中的情理精神卻體現了對人的關懷。一切的法律與制度都是將人作為目的,將人視為工具的法律是不可能的長久存續的。情理法在我國古代經歷了幾千年傳統文化的實踐得以保留下來,恰恰是因為其注重情理的本質彰顯了對人的關懷,而這一本質也不與當代法治相沖突,甚至還是我們追求形式合理性的方法之一。
五、結語
我國的情理法傳統和文化積蘊深厚,其因對人的重視而體現出的對人情的思考和對經驗性的“情”的考量對于當下依法治國的社會背景下,司法會出現裁判合理性與合法性建構相分離的狀態具有借鑒意義。當然我們也需要看到,因為我國古代的天—君—民的天人觀念,所以人們只作為國家的“子民”而存在,并沒有發育出“公民”的概念。中國古代的法律其實就是奴隸法,從來沒有限制權力的思想以及概念產生,而無法限制權力也就沒有產生保障人的基本權利的思想觀念,也就導致司法權和行政權混為一體,無法獨立出來,進而使得司法權當中摻雜了很多行政因素,裁判依據以及裁判過程都具有極大的開放性。這些都是情理法所體現出的弊端,需要當代的司法者以及裁判者予以警惕。總而言之,情理法當中有著其需要當代法律進行借鑒與思考的地方,也有與當代法治精神相背離的地方,重要的是如何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做到合法化的古為今用。
注釋:
①范忠信等:《情理法與中國人——中國傳統法律文化探微》,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17頁。②參見《春秋繁露·基義》。
③鄧勇:《試論中華法系的核心文化精神及其歷史運行》,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58頁。
④陳秀萍:《訴訟、人情與法治——現代法治視野中的訴訟人情化現象研究》,《法制與社會發展》2005年第5期。
⑤⑨霍存福:《中國傳統法文化的文化性狀與文化追尋——情理法的發生、發展及其命運》,《法制與社會發展》2001年第3期。
⑥霍存福:《漢語言的法文化透視——以成語與熟語為中心》,《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1年第6期。
⑦梁治平:《追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諧》,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283、301頁。
⑧劉軍平:《中國傳統訴訟中的“情判”現象及其分析》,《求索》2007年第7期。
⑩王亞新、梁治平主編:《明清時期的民事審判與民間契約》,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07頁。
?康建勝:《汪輝祖的司法實踐及“情理法”觀》,《蘭州學刊》2015年第7期。
?李啟成:《清末比附援引與罪刑法定主義存廢之爭——以〈刑律草案簽注〉為中心》,《中國社會科學》2013年第11期。
?周光權:《行為無價值論與積極的一般預防》,《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1期。
?范忠信:《中國法律傳統的基本精神》,山東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2頁。
?范忠信:《中西法律傳統》,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430頁。
?徐忠明:《清代中國司法類型的再思與重構——以韋伯“卡迪司法”為進路》,《政法論壇》2019年第2期。
?[德]哈貝馬斯:《在事實與規范之間:關于法律與民主法治國的商談理論》,童世駿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年版,第26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