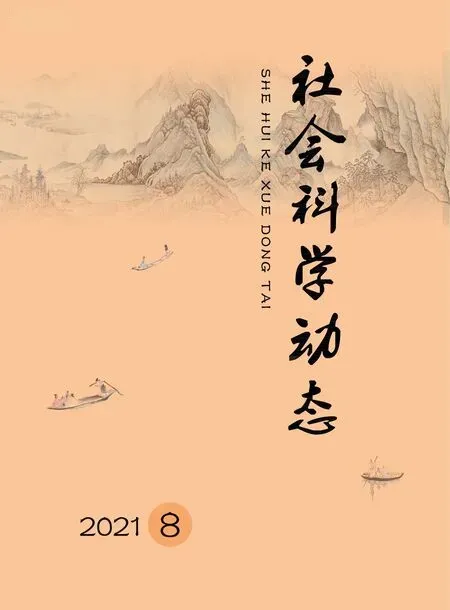武當山民間傳說的講述現狀及活態傳承策略研究
祝豐慧
矗立于鄂西北地區的武當山是我國的道教圣地和武當武術的重要發源地,優美的自然環境及深厚的文化底蘊是近年來武當山發展文化旅游的重要支柱,武當山也因此獲得“亙古無雙勝境,天下第一仙山”的美譽。歷代武當人民在接受道教文化熏陶的同時,希望探尋和解釋道教在當地的興起和發展的緣由,并賦予其更加豐富的文化內涵,因而創作并傳播了大量民間文學作品。目前,已有伍家溝民間故事、武當山宮觀道樂、武當武術、武當山廟會、武當神戲等5項由武當山人民創作的民間文化成果被列入湖北省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中。武當山的民間傳說頗為豐富,如,2006年李征康等人整理并出版的《武當民間文學》一書中就有民間傳說、故事122則,此后又有大量武當山傳說文本被研究者們整理出版。其中影響最為廣泛的是張三豐在當地修道和明成祖朱棣在此興建道教建筑群的傳說。作為民間敘事重要表現形式之一的民間傳說,根植于人們日常生活和民俗世界觀的基礎之上。在傳統農業社會,諸多民間傳說故事主要采用口耳相傳的方式實現傳承和保存,輔以文字符號對其加以記載,從根本上說,我國民間敘事大多秉持著講述人現場講述、聽眾現場聽取的敘事形式。但隨著現代科技文明的進步、城鎮化的經濟發展,傳統社會的民間敘事講述生態遭到巨大的沖擊,許多民間傳說失去了其講述土壤和社會影響力。幸運的是,武當山民間傳說迄今依然保存著旺盛的生命力,活躍在人們的日常交往和想象之中。因此,筆者在對武當山民間傳說的具體講述活動進行田野調查的基礎之上,運用文化地理學理論和表演理論等相關知識,分析武當山民間傳說在當代社會中的講述特點,并進一步探討民間敘事如何在新時代迎接現代文明的挑戰,以獲得更多傳承和發展的機會。
一、武當山民間傳說的講述現狀
武當山豐富多彩的民間傳說迄今依然保持著較高的活躍度,尚未完全與人們的日常生活相剝離。筆者在參與到武當山民間傳說講述活動中時了解到,當地民間傳說的講述者數量較多,這些講述者遍布在當地的各行各業;明顯感受到當地人對民間敘事的講述方式富有激情,部分講述者會主動積極地引導話題,激發聽眾的興趣;另外,在展開講述活動的時間、地點等方面具有武當山地區的獨特印記。武當山的民間傳說講述活動主要呈現出以下幾個方面的特征:
(一)講述者眾多,講述活動頻繁
“武當民俗文化在歷史發展的進程中不斷地吸納外來文化,與漢水文化、荊楚文化、巴蜀文化等融匯交貫,呈現個性鮮明、多姿多彩的民俗文化特點。”①在當地富有宗教特色的民俗文化滋養下,民間傳說、故事在普通民眾的生活中廣泛流布,生于斯長于斯的武當山民眾也有意識地傳承與保存其擁有和依賴的民俗文化資源,很多人自小就對此類充滿奇幻色彩的民間敘事文本耳濡目染,并爛熟于心,代代相傳。2020年6月20日,筆者以外地游客身份前往武當山進行調研,在調查過程中,曾先后與多位本地居民交談,當談及武當山當地的傳說故事時,他們表現出強烈的講述欲望。下面摘錄其中兩位講述者與筆者之間的話語序列:
第一位講述者是一位出租車司機,此處稱呼其為陳師傅,他主要根據武當山道觀建筑群的特點進行的講述。
筆者:師傅,你們這里是道教圣地,今天一見果然像仙境一般。
陳師傅:是啊,我們這里平時游客比你現在看到的多很多,今年是因為疫情,所以來旅游的游客減少了一大半。
筆者:這次疫情對各行各業的影響確實很大。師傅,你們這里有沒有什么有趣的民間故事?
陳師傅:那我們這里可多了,你看到路邊的這些道觀沒?都是大有來頭的。
筆者:請您跟我講講吧!
陳師傅:我跟你說說我們這些建筑的來歷吧!那還得從明成祖朱棣說起。當時啊,朱棣從他侄子朱允手中奪得皇權之后,心里多少還是有點愧疚,就想要通過信仰道教得到緩解。有一次他出巡到了武當山,看到這山覺得有靈氣,就想啊,不如在這里建一些道觀,好供奉黃老。朱棣當時就命令幾十萬工匠在此修筑道觀,好讓他在這里休養生息。你現在看到的,武當山上的那些道觀中比較大、比較古老的一些,大多是朱棣時期建造的……
第二位講述者是筆者所租住旅館的房東,此處稱呼其為華先生,筆者在請他推薦旅游景點時,伴有當地傳說的講述活動。
筆者:華先生好,我打算這兩天去武當山周圍逛一下,您有什么建議嗎?
華先生:你如果想去逛,武當山金頂是應該去看看的,不過疫情期間不開放。你可以去太極湖那邊轉轉。
筆者:我從網絡上看過太極湖的照片,發現那里的湖面特別靜謐。
華先生:是的,尤其是下雨天很好看,而且啊,這太極湖是很有來頭的。
筆者:您能具體說說嗎?
華先生:以前啊,據說張三豐就在太極湖畔練功。我們這里人都知道,張三豐以前做過和尚,但是做和尚的時候他覺得沒意思,所以就還俗了。后來就來到了武當山,發現這里仙霧繚繞,是修道的好地方,所以就在這里入了道教。他以前就曾在太極湖旁邊的道觀里練功,你現在去看,那邊還可以看到一個張三豐練劍的大雕像……
這些講述者在講述過程中都表現出一種強烈的自豪感,可見其講述當地民間傳說的意愿與他們自己內心的地方文化認同感有著緊密的聯系。除上述兩位講述人外,筆者還隨機與多位當地居民進行交流,這些講述活動在各種正式和非正式場合展開,發現他們大多愿意分享自己所了解的武當山民間傳說,且或多或少都能講述兩三個故事。
(二)講述方式多樣,現場互動性強
筆者在調查中發現,由于講述者眾多,不同的講述者會采用多種不同的講述方式,富有較多講述經驗的講述者也會有意識地變更自己的講述方式,以求達到最佳的講述效果。這里以所接觸到的一位講述人為例,該講述人在接受筆者請他講述一些有意思的傳說的邀請后,迅速反客為主,投入到繪聲繪色的講述活動中去。
首先,講述人會迅速判斷聽眾的身份,有針對性地進行引導。譬如,在得知我們是外地人、對武當山有趣的民間傳說了解不多時,講述人就從與當地各種建筑風物有關的傳說講起。6月21號,筆者在步行參觀火神廟時,恰巧遇到廟外有幾位老人在乘涼,于是上前詢問有關火神廟的情況。
筆者:奶奶,你們這個火神廟建了有多久了啊?
李奶奶:我們這火神廟啊,建了都有好幾百年了。
筆者:我看你們這火神廟就建在街邊,這還是挺新奇的。
李奶奶:你不知道,這街道是后來修建的,本來這一片都是道觀,后來拆離,就剩火神廟還沒有拆。
筆者:那現在來火神廟上香的人多嗎?
李奶奶:多啊,我們這火神廟非常靈驗,大家都喜歡到這里上香。
王奶奶:就是呢,我們這火神廟非常靈驗的,以前張三豐還在這里許過愿呢。我去年正月來拜過,說保佑我們一家平安,果然去年一家我們家人都很健康,這都是托了這里的神仙和太極爺的福。
李奶奶:是啊,你要參觀其實可以去我們那邊的太極湖,那里才好看。還有我們這里山上的道觀也很有看頭。
筆者:我正打算過去看看呢。
王奶奶:還有我們山上的道觀也很多。火神廟后面的山上就有好幾座。里面還有的道觀,以前是專門關那些犯了規矩的道士、道姑的。
筆者:他們也會犯法嗎?
王奶奶:當然了,以前還有一個太極爺的女徒弟,喜歡太極爺。太極爺一心修道根本不想這些事,就直接跟女徒弟說明了想法,結果女徒弟知道后沒有收心,反而不守規矩,被太極爺發現了就關在了后面的道觀里。
李奶奶:是的,我也聽說過……
整個講述的過程問答、互動非常多。面對不同的聽眾,講述者的講述方式會做出相應的改變,并且受訪的幾位講述人之間在講述方式的運用方面也存在明顯差異,有的講述人喜歡以問答的形式進行講述,有的講述人的講述則注重對表情、肢體動作的運用。
其次,當地的講述者十分重視與聽眾之間的現場互動。民間傳說的講述“是在特定語境中講述人和聽眾用口頭語言圍繞故事進行的話語交流過程”②,講述者和聽眾之間發生或多或少的語言交流,無形中構成一系列的言語序列,這和民間敘事的本質有著密切聯系。講述民間傳說等民間敘事作品不是進行嚴肅的講話,講述者雖然掌握話語主動權,但整個活動不是講述者的一言堂,而是在聽眾的問答互動中發揮其怡情功能。現場進行的活態講述行為為聽眾提供了與講述者互動的客觀條件,講述者和聽眾對互動的需求幫助民間傳說的講述活動繼續發揚民間敘事現場即時講述的傳統。參與到筆者田野調查中的諸位講述人都有意或無意地在與聽眾進行現場互動,一方面可以通過聽眾的反饋及時地了解聽眾的關注點所在,另一方面希望能夠通過交流、互動吸引聽眾的注意,從而達到較好的講述效果,實現對武當山故事的傳播。
(三)講述文本母題類同,異文豐富
武當山地區有關當地道教發展緣由及以張三豐等著名人物為主人公的民間敘事作品數量繁多,這些活躍在人們口頭上的活態傳說文本帶給聽眾一個個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和妙趣橫生的傳說故事。筆者在聽取講述時發現,這些講述人所講述的傳說文本表現出類型化的特點,參與調查的幾位講述人講述的內容大多屬于地方風物傳說和太極爺張三豐的傳說。講述人對地方風物傳說的講述,往往需要依托武當山的某一建筑或地域為“傳說核”加以講解,現存的風物遺址強化了傳說的可信度,也憑借富有傳奇意味的故事背景為文物古跡增添了吸引力。在有關地方風物傳說的講述中,講述者經常會運用到仙人謫居、帝王欽點等母題,使講述活動帶來更多趣味。講述者熱衷于講述的宗教人物傳說中,無論是講述者還是聽眾,最為感興趣的都是發生在張三豐身上的趣聞軼事,施救貧民、游戲貪官污吏、處事方式奇異等母題在講述中經常被援用。武當山地區民間傳說的具體講述上,文本母題類同化的現象比較突出,但盡管在文本的情節、母題上有同質化傾向,當地的講述人會自主追求故事的新穎性、獨特性,因此在同類母題的基礎上,又會出現許多異文。如,在講到張三豐施法讓窮人到土倉里拿金銀,其中有一位窮人沒能出來的時候,一位講述人說的是因為“這個窮人忘了張三豐要把眼睛閉上的禁令,因而敗露”;而另一位講述人則講的是“這個窮人過于貪婪以至引火燒身”。可見,在遵循傳說的基本母題的同時,講述人也會因為主動在原有文本的基礎上做出變動,結果構成大量故事的異文。
二、武當山民間傳說講述特色的成因
武當山民間傳說的講述活動在當代社會依舊十分頻繁,與其他地區民間敘事講述活動逐漸式微的局面大相徑庭,筆者以為,這種現象的出現是多種原因共同作用的結果。首先,文化地理學為分析武當山這一獨特的文化現象提供了有效視角。堅持以“人—地”關系為核心理論的文化地理學“是研究人類各種文化現象的空間分布、地域組合及文化區域系統的形成、變化和發展規律的一門科學。(它)研究諸文化要素的形成發展與地理環境的關系,以及各種文化現象的區域特征”③。其次,表演理論認為對民間敘事文本的講述活動是一種言說方式,認為“表演的文類、行為、事件和角色不會孤立地發生,而是相互作用、相互依賴的”④。在該理論指導下,研究民間傳說文本在武當山這一場域中的動態形成過程成為可能。再次,民間傳說與民間信仰之間的關系也是引導武當山人們重視對當地民間傳說的講述與傳播的重要因素。
(一)武當山獨特的地理空間位置
身處中原腹地的武當山山區,獨特的地理空間位置,塑造著當地人民對待民間敘事的態度。首先,對文化分區的分析是文化地理學的重要主題,我國民間敘事的活態傳承存在明顯的區域差異,整體表現為東部地區的講述行為較少,中西部地區為口頭講述活躍的格局。地理環境的差異及已有的文化生態格局是影響民間敘事活性因子分布的直接原因。“從根源上講,文化的差異性最終取決于人類改造和適應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的差異。”⑤民間敘事的傳承需要有較為穩固的農業生產方式、傳統文化觀念等的支撐,在經濟文化繁榮的東部地區傳統文化格局極易被新興文化所取代。而中部的武當山地區因當地的山區資源,人民保留了許多傳統的農業生活方式,與民間傳說的傳統農耕文化環境具有一致性,因此為民間傳說的講述和傳承提供了土壤。同時,該地因地理環境的閉塞,社會成員在文化思想上受到的外來文化沖擊力度經東部地區緩沖之后呈現明顯減弱的趨勢。因此,許多原始文化觀念的殘留,玄虛、神異等民間敘事中與現代文明相抵牾之處,但在武當山地區人民的心中則有其自然合理性,心理上的認同促使人們自愿參與講述和傳播民間敘事作品的活動。其次,武當山地區人均占有土地面積大,除集鎮外極少出現人口密度過大、活動空間私密逼仄的情況,許多人家仍建有開闊的場院可供人們日常生活的話家常、講故事。武當山在地理位置上遠離發達的城市,且傳統文化觀念根深蒂固,即使現代網絡技術已經普及、信息傳播迅速,但城市流行文化向該地的擴散、傳播、扎根仍會經歷較長一段時間的過渡。相對于現代化都市文化新變性強、現代娛樂手段豐富多樣等情形,武當山仍保留著傳統的鄉土氣息,為民間傳說等講述活動的開展提供了極為有利的客觀條件。
(二)武當山地區口頭表演語境的建構
武當山人民對當地民間傳說的講述或多或少存在一定的技巧,當地講述人的口述也是有規律的表演行為。鮑曼的表演理論認為,民間口頭敘事等表演在本質上是與表演中的社會結構的創造相關涉的,“它所重視的不是對一個個文本或一個個民俗事象形態的研究,而是在日常交流實踐的視角下整體地去理解社會結成與文化新生的過程”⑥。基于此,可從更為深層的角度分析武當山民間傳說的講述活動仍能有序進行的原因。首先,表演語境的建構為武當山民間傳說的表演提供了重要基礎。“‘語境’是表演理論的核心概念,注重文本在特定語境中的動態形成過程是表演視角的革命性主張之一。”⑦口頭表演所根植的背景或事件及其他結構性存在都可歸結為語境,它們制約和影響著表演的發生。武當山依靠其自然環境和宗教文化資源大力發展旅游業,慕名而來的游客們對武當山地方文化的好奇心理促使他們成為了講述活動的重要對象,而當地居民為了推動當地旅游產業的發展,很多人自覺地承擔起地方文化的講述者和表演者的重任。即,武當山文化旅游產業結構給當地帶來經濟利益的同時,也為當地的口頭表演營造了有利的表演語境,游客的鼓動為講述人的講述帶來了動力。其次,表演具有新生性的特征。“所有的表演都不是相同的,而且人們希望能夠欣賞到每一個表演的獨特個性,同時也能明了整個社區范圍內表演領域總體的模式性。”⑧講述人在講述傳說時,有意在原有文本的基礎上做出技巧性的變動,一方面是為了迎合聽眾的獵奇心理,破除復述原有文本的枯燥窘境,一方面可以顯示出講述者自身的高超技藝,獲得更多認可。所以武當山的民間傳說講述活動在遵從原有文本的前提下,做出新穎的變動,以異文的形式保留民間傳說對聽眾的吸引力。
(三)武當山民間信仰的內在規約
“民間傳說敘事方式在創作和演化中總是有一些內在和外在的東西支撐著,內在的民間信仰因素是規約傳說發展的關鍵。”⑨長期受道教文化熏陶的武當山居民,對文化的敬畏和對傳說人物的尊崇早已潛藏在人們的集體無意識中,如,在武當山地區“張三豐普遍被尊稱為‘張爺’‘太極爺’,從來沒有人敢直呼張三豐姓名的。人們怕得到‘張爺’的懲罰”⑩。這種滲透在民眾心靈深處的民間文化信仰規約和引導著人們的行為,也深刻影響著當地人對待傳說的態度。首先,對當地文化的自豪感和熾熱的信仰使人們心中保留著對于傳說故事的激情與高度重視。武當山的居民在日常生活中或多或少會聽老一輩人講述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民間傳說,來自精神文化方面的信仰抵御著現代文明帶給此類傳統民間文化的沖擊,幫助人們保持著對民間傳說的興趣,而不是以質疑、批判的眼光來審視民間傳說文本。其次,深厚的民間信仰構筑起人們彼此之間的身份認同感及其講述和表演民間傳說的方式,對于當地人而言,有關武當山道教的發源和太極爺張三豐發傳說是凝聚彼此之間關系的重要紐帶,他們也愿意把這些傳說講述給更多人,讓更多人領略到武當山文化的魅力和價值,進而推動當地文化更好的發展,并得到武當山以外人群的接受與理解。
三、武當山民間傳說的當代活態傳承與保護策略
武當山富有特色的民間傳說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其中蘊含著中華民族共同的文化精神和先民們的生活經驗、人生觀念,應該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發揮其重要價值,而不是僅僅作為研究文本被保存、凝固在文字、錄音、影像之中。從調研結果來看,盡管武當山民間傳說的講述活動相比其他地區具有一定的優勢,但是仍然存在諸多困境。如:口述傳承活動還未能夠達到內在自覺的程度,講述者局限于個人的喜好對傳說加以講述;講述方式過于保守,尚未與浩浩蕩蕩的互聯網潮流相融合,未來的傳承發展存在較大壓力;傳說內容與當代生活脫節,故事合理性逐漸缺失。本文對武當山民間傳說講述活動特點及成因的分析,正是為了更好地推動當地民間傳說口頭講述和傳承工作的進行。時代的發展為武當山民間傳說的活態傳承創造了條件,也提出了新的要求。要實現對武當山珍貴的民間傳說的活態傳承和保護,可從激發群眾保護民間敘事的自覺性、利用新媒體技術超越地理空間的阻礙、優化民間敘事中的文化觀念、為民間敘事注入時代內容等多個方面開展工作。
(一)引導群眾由自發講述轉向自覺傳承
群眾的重視和講述情況直接關系到民間傳說的傳承成果。武當山的民間傳說作品是“由民眾自創自享、自娛自樂,處于地域性封閉形態,其傳承處于自發狀態”?,現有的各種對民間傳說的講述和欣賞活動大多是武當山民眾自發的行為,是以休閑、娛樂為其主要目的。一旦傳統的民間傳說在當地社會成員心中喪失了其原有的娛樂、補償功能,就將逐漸在日常生活中消隱,這也是在現代娛樂方式沖擊下民間敘事在許多地區被人們遺忘的重要原因。因此,引導群眾轉變強化其主動自覺傳承民間傳說的心理,是實現武當山民間傳說活態傳承的有力推手。首先,可進一步研究發掘武當山民間傳說的經濟價值,以此引起人們對民間傳說的重視和主動傳承。當地居民對武當山傳說在發展武當山旅游產業的價值作用有一定程度的認知,但還未在更深層的思想觀念中影響到他們對于傳說文本的態度,目前當地人對傳說的講述往往是在游客的主動詢問下進行的。具有地域特色的民間傳說承載的當地特有的文化風貌和文化發展成果,表現出武當山個性化的特點。在全球化的今天,建立在地方文化特色基礎上的旅游等經濟開發活動無疑是能夠激發游客的消費欲望和帶來極大的經濟利益。當地社會成員只有在深刻意識到民間敘事的經濟價值后,才會更加主動積極地投身到挖掘和保護民間傳說的活動中去。其次,當地政府需要加大對當地民間傳說價值和開展保護工作重要性的工作力度。過去人們對民間傳說價值的了解主要是建立在老一輩的介紹和自身生活中獲得的點滴感受,存在著認識不深入、了解不全面的問題。這需要地方政府有效組織當地文化專題研究,豐富民間文化底蘊和文化新業態,派遣具有威望的專業人士向群眾宣傳宣講民間敘事的各種社會價值,幫助和引導群眾在深入體會武當山傳說價值的基礎上,自覺參與和拓展活態傳承武當山傳說的活動。
(二)運用新媒體技術,打破地域阻隔
網絡新媒體技術已經滲透到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網絡媒體可以超越地理環境的界限,連通不同區域的受眾和文化,其迅速、便捷、覆蓋范圍廣等優點為各種文化的發展和傳播提供了有利條件。傳承和保護武當山傳說也可根據其自身特點與網絡新媒體技術相結合,實現在新時代的傳播和發展,打破地理壁壘,把武當山的故事面向更多人講述。一方面,依托網絡新媒體,利用影視、短視頻、直播等技術推進武當山傳說的講述方式從傳統向現代化轉變。以當地動人的傳說為文本制作出精良的影視劇、網絡短視頻,從網民的接受心理出發,回應網民的景觀消費需求,把原本局限于地方的民間傳說投入到更多群眾的視野中。現代網絡新媒體不僅可以突破時空界限,實現民間傳說的跨地域傳播,還能與網民隨時隨地展開互動,即使聽眾無法到達現場也能夠感受傳說故事帶來的愉悅和樂趣。如,可以培養民間敘事的網紅講述人,以直播互動的方式給來自各地的網友講故事、談古今,通過這種虛擬的在場,在網民中傳播武當山民間傳說作品。另一方面,在通俗化、景觀化的同時,要堅守武當山傳說的文化內涵。傳說的講述在吸取短視頻等視聽結合的快捷方式時,要避免泛娛樂化趨勢。武當山傳說作為傳統文化的一部分,即使為適應現代生活環境呈現出諸多新變,其文化內核不應被遺忘。其講述方式可以發生變化,但是其追求勤勞、正義、真善美等精神內涵應該是與最廣大人民的需求相一致的,具有正面引導作用的。所以武當山傳說的現代講述不應過度娛樂化,其中優秀的價值理念不可被消解,在尋求視覺、聽覺等感官趣味的同時,要保留民間傳說的核心文化內涵。這也是以武當山傳說為文本的網絡視頻給網民帶來歡樂之后,能給群眾帶來更濃厚的精神享受,獲得社會影響力,不會被迅速遺忘,進而得到活態傳承的重要因素。
(三)優化民間敘事內容,增加時代文化內涵
文化空間的變遷是影響文化代際傳承主要因素,缺乏當代群眾認同的民間敘事內容只能是無根之木,無源之水,終將被社會淘汰,從武當山傳說的內容出發,適應現代話語體系的需要,及時變更表演手段是武當山傳說長存于大眾視野的必然要求。講述傳說文本不能一味地墨守陳規,而是要應需而變,滿足廣大人民的文化需求。傳說的內容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各個時代的人民群眾根據自身的文化需要創造出來的文化作品。所以要使武當山傳說在現代文化生活中保存活性,首先要剔除其中出現的一些如妖魔鬼怪等過于迂腐、愚昧的內容。正是這些不合時宜的內容拉大了群眾和傳說之間的距離,必須予以摒棄。同時在驅除封建愚昧內容時,不應過于片面地否定此類內容,要看到潛隱在其背后的傳統社會中人民對人與世界關系的理解和精神信仰。其次,豐富傳說文本運用的母題,在講述武當山傳說時增添能夠體現當代文化內涵的內容和現代人喜聞樂見的情節,現代人對事物的理解已經與過去的人有了很大的不同。如,在講述張三豐除惡扶貧傳說時,可以在主角機敏睿智、法力高超的基礎上,適當增加對主角以外人物的描述,豐富文本的藝術色彩,這也是今后武當山傳說的活態講述活動應該面對和解決的問題。如果說過去人們看重農業勞動能力和帶領人民反抗惡霸的反抗精神,那么現代人更為重視的智慧、創新等與現代物質文明相一致的品質。因此,要為武當山傳說在群眾生活中爭取更多立足機會,就要持有開放的觀念對待傳說,主動實現武當山傳說在內容、情節等方面的創新和變革。
注釋:
①楊蓓蓓:《武當山生態文化旅游發展研究》,《漢江師范學院學報》2019年第6期。
②祝秀麗:《民間故事講述的話語互動及其田野研究》,《民俗研究》2015年第6期。
③夏日云、張二勛:《文化地理學》北京出版社1991年版,第6頁。
④⑧理查德·鮑曼:《作為表演的口頭藝術》,楊利慧、安德明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37、41—42頁。
⑤程乾、凌素培:《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空間分布特征及影響因素分析》,《地理科學》2013年第10期。
⑥毛曉帥:《中國民俗學轉型發展與表演理論的對話關系》,《民俗研究》2018年第4期。
⑦楊利慧:《語境、過程、表演者與朝向當下的民俗學——表演理論與中國民俗學的當代轉型》,《民俗研究》2011年第1期。
⑨林繼富:《神圣的敘事——民間傳說與民間信仰互動研究》,《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6期。
⑩劉守華、李征康:《武當山民間口頭文學中的張三豐》,《漢江師范學院學報》2017年第2期。
?王衛華、霍志剛:《鄉村振興戰略視野下民間文學的傳承與傳播——基于喇叭溝門滿族鄉的分析》,《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