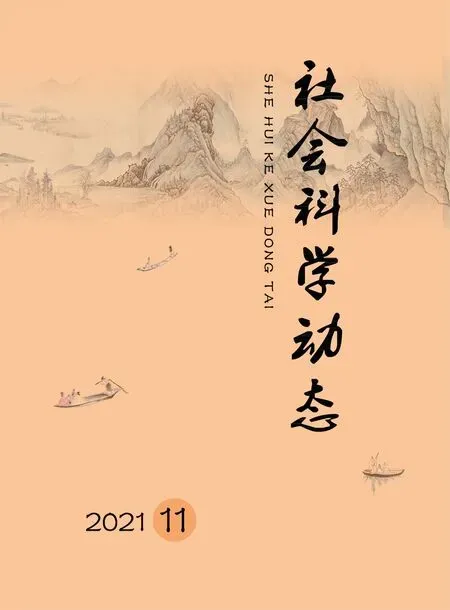由鏡到網:美學思維方式的中國革命
——論李澤厚后期美學的倫理轉向及啟示
郝二濤 侯欣園
近十年來,李澤厚美學思想研究成果豐富且形式多樣,研究深度與廣度都較之前有所加強,國外比較集中在與中國政治文化密切相關的概念“主體性”、“積淀”等方面的研究,國內比較集中在對李澤厚實踐美學思想來源、美學史書寫、關鍵詞、倫理思想等方面的研究。但國外與國內都鮮有從思維方式層面深入系統研究李澤厚后期美學思想,尤其是李澤厚后期美學思想的思維方式的成果,且從新時代建構中國特色的美學話語的語境看,這方面的研究亟待加強。
一 自然與人:從順化到逆化
李澤厚前期美學主要圍繞“自然人化”和“人的自然化”命題展開。“自然人化”命題以實踐為本體,其思維方式強調人與自然事物之間的區分與對立,主要是本質主義思維方式。“人的自然化”命題以情感為本體,其思維方式強調人與自然事物的聯系與融合,主要是非本質主義思維方式。由于后現代語境中的“倫理”一詞意味著非區分、非本質①,因此,李澤厚美學的倫理轉向主要表現為從“自然人化”命題向“人的自然化”命題的轉變。
作為一個概念/命題,“自然人化”源于馬克思的《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李澤厚較早將其應用于文學藝術作品的闡釋中,比如,通過考察中國古典抒情詩中的“人民性”,李澤厚將以抒情詩為代表的文學藝術中的“自然”之實質概括為人化的自然或自然的人化。②“自然人化”包括“外在自然的人化”與“內在自然的人化”。“外在自然的人化”主要指非人工的事物的人化,比如日月星辰、江河湖海的人化。“內在自然的人化”指人的情感(喜怒哀樂)、感知(視聽觸味嗅)、感官(眼耳口鼻身)、欲望(吃喝拉撒睡性) 的人化。
無論是外在自然的人化,還是內在自然的人化,都依靠社會的勞動生產實踐。實踐主要指生產與制造工具的活動。③這種活動來源于社會現實生活,是客觀的,有人的本質力量的參與,又是主觀的。客觀與主觀不是對立的,而是統一的,不可分割的。這種思想貫穿在李澤厚關于美學范疇的論述中。比如,美感既具有客觀功利性,又具有主觀直覺性,是二者的有機統一,忽視或否認任何一方都是錯誤的。它既沒有像康德美學那樣將美感與功利對立起來,否認美感的客觀功利性,也沒有像蔡儀美學那樣將美感視為事物自身的屬性,忽視美感的主觀性,更沒有像呂熒那樣將美感視為人的主觀審美意識,否認美感的客觀性,而是在社會實踐的基礎上將美感的精神愉悅性與社會功利性、客觀性與主觀直覺性、正確的認識與健康的道德觀念視為有機聯系的統一體,區分了美感和美,將美感視為美的反映、審美感情,既避免了美與美感界定的片面性,又避免了對美與美感區分之簡單機械性。同樣,在談到美的時候,李澤厚重點談了蔡儀、朱光潛、呂熒等美學的缺陷,認為他們的美學無法解釋自然美,進而將自然美視為社會化的結果。④這種觀點既看到了自然本身的客觀性,又看到了人在自然美形成中發揮的不可缺少的作用,還看到了自然美的社會性,既看到了自然美的靜態性,又看到了自然美的動態性。而且,在現實生活中,李澤厚也并未將美與善視為對立的觀念,而是將二者視為統一的、一致的。在談論藝術美的時候,李澤厚仍然堅持了辯證統一的立場,將藝術美視為階級性與人民性、社會性與形象性、審美性與實用性的統一。
從中可以看出,李澤厚在馬克思主義唯物主義哲學的指導下,將“實踐”作為審美基礎,雖然將美感視為美的反映,但卻并未局限于唯心主義與唯物主義對立的反映論模式,而是試圖在審美關系中闡釋美感、美和藝術美等問題,從而推動“美學大討論”思維模式由二元對立的反映論向有機統一的實踐論轉變。這種轉變不僅可以將人與自然的對立關系積淀在審美心理現象之中,也可溝通自然與人、認識與倫理、真與善、感性與理性、規律與目的、必然與偶然、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還可將藝術、審美與塑造文化心理結構、陶冶人的性情聯系起來,故而超越了心物對立的反映論模式。正如韓德民所說:“20 世紀50 年代,李澤厚首先將‘自然人化’命題引入美學研究,肯定‘實踐’對審美主體和對象的主體地位,推動美學大討論超越了心——物外在對立的反映論模式。”⑤比如,李澤厚運用心理學、符號學、精神分析學等知識,以“積淀”解釋理性表現在感性中、社會的東西表現在個體中、歷史的東西表現在心理中的過程,即(自然人化) 美感、美的發生過程。
在心理學視角下,人們在物質生產實踐活動中不僅形成了自身的社會存在形態,而且獲得了相應的倫理、意志和享受等精神存在形態。這種形態雖然以心理學為本體,但由于審美心理自身的無意識、不確定性,而實際上是無本體的心理本體。這一點與維特根斯坦的“語言本體”、海德格爾的“存在本體”、弗洛伊德的“無意識”類似。與維特根斯坦的“語言本體”、海德格爾的“存在本體”、弗洛伊德的“無意識”觀點聚焦于人之外的問題不同,李澤厚的“心理本體”對生存、死亡、性、語言等問題保持開放的姿態,探究審美與倫理、審美與情感、審美與語言、審美與藝術、審美與人等問題,試圖在關系網絡中把握美、美感。這種思維方式是偏向關系的思維方式。與羅蒂的反基礎主義、反表象主義與反本質主義的思維方式不同,李澤厚偏向關系的思維方式并未摒棄相關的本質問題,而是試圖直觀地把握美、美感。盡管這種思維方式很不徹底,但是,它對美學學者在一定程度上突破美學大討論中盛行的心物對立的反映論思維方式有一定示范意義。
李澤厚提出“人的自然化命題”的一個主要原因是,物質世界的興盛促使精神世界的來臨及人們對待馬克思主義觀念態度的變化。正如李澤厚所說:“當整個社會的衣食住行只需一周三日工作時間的世紀,精神世界支配、引導人類前景的時刻即將明顯來臨。歷史將走出唯物史觀,人類將走出馬克思主義。”⑥“人的自然化”包含三層意思。“第一層意思指,人與自然環境、自然生態的和諧關系,人與自然界友好和睦相處,相互依存,不是去征服、破壞自然,而是把自然作為自己安居樂業、休養生息的美好環境;第二層意思主要指,人與自然景物、自然景象的關系,人把自然景物、景象當作欣賞、歡娛的對象,在栽花養草、游山玩水、樂于景觀、投身于大自然的過程中,與自然合一;第三層意思,人與自然節律的關系,人的身心與自然節律的吻合呼應,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包括人體特異功能對宇宙隱秩序的揭示與會通。”⑦這三層意思一反自然人化的人類中心主義立場,轉向生態主義立場;一反人與自然二元對立的立場,強調人與自然之間的聯系與依存;一反人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立場,轉而秉持尊重自然、愛護自然的立場。它強調的是目的從屬于規律,以及個體與自然的交往。這既是為了糾正“自然人化”觀念所倡導的規律服從于目的的觀念上的偏頗,也是為了彌補理性、形式結構的泛濫對個體感性存在的壓迫之不足。前者在一定程度上調節了目的與規律之間的對立關系,后者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感性與理性之間的緊張關系。這種調節與緩解實際上是“情感本體”對“實踐本體”的補充與糾正。或者說,是對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的補充與糾正。
雖然李澤厚最早談到提出本體之“情”的類型的時候,將其分為“具有人生境界的人性情感”、“藝術創造與欣賞中的情感”和“世俗情感”三種類型⑧,但是,與梁啟超的“情感本體”中的作為感情的“情感”、錢穆的“唯道論”中與欲望相對的情感不同,李澤厚最終將“情感本體”中的“情感”定義為“情理交融的人性心理”,表征著個體與個體、個體與藝術、個體與宇宙之間的關系。與形而上學哲學中作為“事物的最后根源”的“本體”不同,在海德格爾的作為當下人的生存狀態的“煩”、“畏”的啟發下,經過修改,李澤厚“情感本體”將“本體”定義為此當下的人生“情”況。⑨
李澤厚之所以用“本體”來指代這種有名無實的“當下的人生‘情’況”,主要是為了強調人性的建設性及人生的內圣外王之道。從思想來源看,除了海德格爾的存在論思想、西方馬克思實踐哲學之外,“情本體”的思想也來源于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人情豐富經驗與習俗。⑩其特點是,既承認中國當下需要二分思維,又批判工具理性、批判二元對立思維。從所處的時代背景看,“情本體”所處的時代背景是世界范圍內形而上學本體論遭到各種各樣的解構的時期。從起點看,“情本體”的起點是“人活著”。從針對的問題看,“情本體”試圖解決的問題是如何應對人的生活的偶然性問題,試圖回應的是后現代語境中人們生活的碎片化、物化等問題。從核心范疇看,“情本體”的核心范疇是“珍惜”。“珍惜”的主體是個體,“珍惜”的對象是時間情感,以“度”為核心,而“度”的把握并沒有一個終極的標準,而是因人因事因時而異的,是充滿不確定性因素的。從宗旨看,“情本體”是為了建設人性的價值觀,或者說“為萬世開太平”。其落腳點依然是人的生活狀況,正如徐碧輝所說:“情本體理論的主旨是探討個體面對強大的不可預知、不可抗拒的必然性如何把握自己的偶然性,從而在這個世界上‘安身立命’。”?“人”始終是情本體關注的中心。
二、個性與偶然:社會歷史傳統的創造性溯源
李澤厚美學思維方式的轉變有深刻的社會、歷史根源,其根源可從以下兩層面分析。
第一個層面,孔子“仁學四結構”和康有為的“托古改制”思想中蘊含的“個人自由、個性解放”的思想因子。?李澤厚不僅從時間維度將靜態的美的本質分析與動態的美的歷史的發生過程結合起來,而且強調人在美、審美經驗等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地位,還特別重視運用美善統一的視角。正如李澤厚所說:“我所主張的‘美是客觀的,又是社會的’,其本質含義不只在指出美存在于現實生活中或我們意識之外的客觀世界里,因為這還只是一種靜觀的外在描繪或樸素的經驗信念,還不是理論的邏輯說明,為什么社會生活中會有美的客觀存在?美如何會必然地在現實生活中產生和發展?要回答這個問題,就只有遵循‘人類社會生活的本質是實踐的’這一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觀點,從實踐對現實的能動作用的探究中深刻論證美的客觀性和社會性。從主體實踐對客觀現實的能動關系中,實踐從‘真’與‘善’的相互作用和統一中,來看美的誕生。”“實踐在人化客觀自然界的同時,也就人化了主體的自然——五官感覺,使它不再只是滿足單純生理欲望的器官,而成為進行社會實踐的工具。正因為主體自然的人化與客觀自然的人化同是人類幾十萬年實踐的歷史成果,是同一事物的兩個方面,所以,客觀自然的形式美與實踐主體的知覺結構或形式的相互適合、一致、協調,就必然地引起人們的審美愉悅。”?“正是人類總體的社會歷史實踐創造了美。”?
第二個層面,太平天國、資產階級改良派、民主革命派思想中蘊含的整體性、偶然性、歷史性的思想因子。李澤厚通過研究太平天國革命,認識到,洪秀全思想的核心是對中國封建社會農民革命思想在近代歷史條件下地繼承與發展,是西方拜上帝教的宗教儀式與太平天國起義前后的革命實踐的結合,西方的理論必須與中國的實際結合。這使李澤厚看到了實踐對理論的重要意義。太平天國后期的施政綱領《資政新篇》是洪仁玕對香港社會實踐考察與思考的結果,具有指向“中華共和國——自由、平等、博愛”(馬克思) 的近代民主主義的氣息,而太平天國革命的失敗使李澤厚意識到農民階級的階級局限性。“戊戌變法”試圖將民主在政治層面付諸實踐。通過研究康有為的維新變法思想,李澤厚發現,在民族矛盾異常尖銳的情況下,晚清青年知識分子個人意識開始覺醒,試圖以西方的歷史進化論的社會發展觀來改變民族、國家危亡的局面。此外,李澤厚也意識到即使在外國侵略者肆意蹂躪的情況下,我們也是可以憑借自身的努力、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將侵略者趕出中國,贏得國家與民族的獨立的。比如,在民主主義革命中,孫中山發現并及時利用了清朝末年內憂外患、民族危機空前嚴重、革命形勢一觸即發的形勢,利用《〈同盟會〉宣言》中提出的“三民主義”,號召、組織革命,推翻了統治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專制制度,取得了舊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李澤厚由此認為,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既有“未經哲學提升的自然科學事實”的特征,又有“將自己的革命實踐作為哲學觀點的直接來源”的特征。?但孫中山對實踐之理解是狹隘的和直觀的。比如,他將人類實踐活動歸結為力學與歷史,將實踐活動的內容理解為“實驗”、“研究”、“探索”和“冒險”,雖提出過政治斗爭實踐,卻沒有認識到實踐的真正社會歷史內容和性質,沒有科學地理解政治斗爭實踐的復雜性、豐富性與偶然性。而這些特性恰好植根于中國傳統歷史文化的土壤與血脈中。
在中國傳統歷史文化中,仁學是核心。李澤厚將其結構概括為“仁學四結構”或“仁學四原則”,即“心理原則”、“血緣原則”、“人道主義”、“人格理想”。“血緣原則、人道主義、人格理想”是李澤厚審美體驗觀念中的“悅耳悅目”、“悅心悅意”、“悅志悅神”及“情本體”思想的社會歷史根源之一,因為它們是美在社會歷史文化尤其是文學藝術中的展開與呈現。比如,漂亮的時裝穿在身上使人感到舒服,齊白石畫的蝦能喚起人們對清新浪漫的春天般的生活的向往,疾風暴雨曾喚起中國工農紅軍長征途中心曠神怡的審美愉悅。這三種審美類型以及“積淀說”、“情本體”是“自然人化”與“人的自然化”命題的演繹,實質上是對“自然觀”的研究。李澤厚之所以重視“自然觀”研究,是因為,“無論是康有為、譚嗣同、章太炎、孫中山,目標都是社會,起點卻都要講自然、地球、天體。其中的原因就在于,他們都要找出或指出一個宇宙萬物包括自然和社會在內的總規律總法則,來作為自己活動的依據”。?李澤厚從認識論出發,認為自然觀必然與人有關,并且將其作為自身美學思想的一個核心構件。
從自然人化到人的自然化的轉變預示李澤厚美學思想的倫理轉向。這種轉向雖然也有彌補批評話語中倫理維度的缺失的意圖,但卻不是為了反撥解構主義與形式主義傾向,而是對解構主義的運用。它雖然關注倫理內容,卻并未走向倫理學,而是通過關注倫理問題批判人與自然對立的思維方式。
三、開放與平衡:中國美學創新的啟示
這對中國美學創新的啟示可從以下兩個方面來論述。
第一,中國美學的邊界要開放有界。以“情本體”為核心的李澤厚后期美學既借鑒了心理學的研究成果,也借鑒了倫理學的成果,還借鑒了精神分析學的研究成果。這是美學研究的跨學科方法,也是美學邊界擴展的表現。比如,“情本體”將美學的邊界向內推向宗教,向外推向政治,因為“情本體主要與宗教性道德有關,也影響到社會秩序(政治道德) 的規范建立”。?這既可能產生宗教美學與政治美學兩種美學形態,也可能會使美學走向宗教與政治,最終被宗教學、政治學抑或文化研究取代,走向終結。后一種可能是“情本體”遭到諸多美學學者質疑的一個重要原因。
針對上述質疑,李澤厚通過引入時間維度,以“情感時間”為核心,將“珍惜”作為“情本體”的基本范疇。“珍惜”的關鍵是把握好“度”。這種回應其實也是對中國美學邊界問題的回應。從中國美學學科誕生之日起,尤其是20 世紀90 年代以來,中國美學一直面臨著跨越邊界與保持邊界的問題。這個問題被概括為“本土與西方”、“傳統與現代”間的矛盾。前者為空間矛盾,后者為時間矛盾。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這兩對矛盾尤為凸顯,也是一直沒有解決的矛盾。這兩對矛盾的根本特點是二元對立。二元對立的出發點是古希臘人在理論與實踐、歷史與現實之間的分離之假設,以探求終極知識為中心和宗旨。?“情本體”的“度”從情感時間維度出發,以“人活著”這個事實為起點,以人生的真實意義和人的幸福為中心,在起點與宗旨上都與二元對立的起點與宗旨不同,挑戰了二元對立。它啟示我們,中國美學既要大膽的越界,敢于超越既有美學藩籬,但也要謹守自己原有的邊界,在圖像、身體、市場、消費等盛行的情況下,適當回歸美學,成為更具包容性的美學。這需要我們把握好越界與回歸的“度”。這恰好抓住了美學的邊界的動態性以及美學保持開放姿態所引起的不確定性,為我們重新思考美學的邊界問題提供了借鑒。
第二,中國美學理論應在國家需求、社會倫理問題、理論獨創性之間保持均衡。“情本體”作為李澤厚實踐美學的延伸與調整,從內容上看,“情本體”主要指人生的真諦,人生的真實意義,是一種文化心理結構,與認識論意義上的“本體”無關。從形式上看,“情本體”似乎是以情感為本體,但實際上是對“工具本體”的修正與發展。“情本體”摒棄了“工具本體”的“本體”特點以及“理性”認識論特點,不再執著于對終極知識的追尋,轉而探求人的生活狀況,使美學不再是象牙塔里的抽象思辨,而是對人的生活的關懷;使美學能以人與自然的整體利益為中心,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
筆者認為,李澤厚的“情本體”概念雖然有不完善的地方,但是也有極大的獨創性和示范性。后者的重要性要大于前者。“情本體”既響應了國家增強文化軟實力之號召,又踐行了國家增強文化軟實力的理念,同時還闡釋了嚴重的社會倫理問題,使美學既有現實問題的闡釋力,又具有一定的獨創性,不僅有力地證明了中國美學具有生命力,而且回應了中國美學合法性問題的。比如,在全球化與地方、中國與西方、民族與世界、傳統與現代、引進與創造等的關系中,“度”為中國美學確立自己的坐標提供了有益借鑒。“情本體”的無本體性既是中國美學超越西方認識論美學的一個表現,也是中國美學在后現代文化語境中的一個自覺選擇,無疑為中國美學思維方式的變革提供了一個典范。
注釋:
①[法]雅克·朗西埃:《審美與政治的倫理轉向》,郝二濤譯,《中國美學研究》2018 年第1 期。
② 李澤厚: 《關于中國古代抒情詩中的人民性問題——讀書札記》,《光明日報》1955 年6 月19 日、26日。
③ 李澤厚:《試論人類起源(提綱)》,《李澤厚哲學美學文選》,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第180 頁。
④李澤厚:《論美感、美和藝術(研究提綱) ——兼論朱光潛的唯心主義美學思想》, 《 哲學研究》 1956年第5 期。
⑤ 韓德民:《李澤厚與20 世紀后半期中國美學》,《安徽師范大學學報》 (人文社會科學版) 2000 年第1期。
⑥ 李澤厚:《哲學探尋錄》,參見《世紀新夢》,安徽文藝出版社1988 年版,第10—11 頁。
⑦ 李澤厚:《美學三書》,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 年版,第 454 頁。
⑧ 李澤厚:《關于主體性的第三個提綱》,金觀濤主編:《走向未來》第3 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第 118—121 頁。
⑨ 李澤厚:《歷史本體論·己卯五說》 (增訂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 年版,第91 頁。
⑩ 李澤厚:《中國現代思想史論》,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 年版,第361-362 頁。
? 徐碧輝: 《論李澤厚實踐美學的情本體理論》,《四川師范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 2015 年第5 期。
? 李澤厚:《二十世紀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派思想論綱》,《歷史研究》1979 年第6 期。
?李澤厚:《美學三題議——與朱光潛同志繼續論辯》,《哲學研究》1962 年第2 期。
? 李澤厚:《美學四講》,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9 年版,第 73 頁。
? 張磊、李澤厚:《論孫中山的哲學思想》,《科學通報》1956 年第12 期。
? 李澤厚: 《中國近代思想史論》,人民出版社1979 年版,第 365 頁。
? 李澤厚:《哲學綱要》,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年版,第64 頁。
? [美]理查德·羅蒂:《哲學與自然之鏡》,李幼蒸譯,商務印書館1987 年版,第337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