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天下”到民族國(guó)家:歷史中國(guó)的認(rèn)知與實(shí)踐》評(píng)析
吳凌杰
“中國(guó)”作為政治性概念的詞匯,它的存在似乎為大多數(shù)人所熟悉。但究其根本而言,何以“中國(guó)”?“中國(guó)”作為先驗(yàn)論的存在,似乎是不言自明的,故它的來(lái)源與演變,一直為人們所忽略。筆者近讀王柯教授《從“天下”到民族國(guó)家:歷史中國(guó)的認(rèn)知與實(shí)踐》①一書(shū),發(fā)現(xiàn)此書(shū)就“中國(guó)”一詞的演變與歷代中國(guó)的認(rèn)知等問(wèn)題展開(kāi)了詳細(xì)的論述,諸多觀點(diǎn)極為精辟,故筆者特撰本文,就此書(shū)的價(jià)值等問(wèn)題,略成管見(jiàn),以示引玉之意,諸多論述未必允當(dāng),敬請(qǐng)作者與學(xué)界同仁批評(píng)。
一
“天下”與“國(guó)家”作為傳統(tǒng)史書(shū)中的話語(yǔ),到了20 世紀(jì),隨著西方列強(qiáng)的入侵轉(zhuǎn)變?yōu)榱苏涡栽~匯,即梁?jiǎn)⒊浴爸刑煜露恢袊?guó)家”②。自西方諸國(guó)在經(jīng)濟(jì)與政治上的強(qiáng)勢(shì)擴(kuò)展以來(lái),傳統(tǒng)東亞秩序的中國(guó),遭到了以外部“民族—國(guó)家體系”(Nation-State) 為代表的學(xué)說(shuō)沖擊。如何重新審視傳統(tǒng)中國(guó)?把握中華民族長(zhǎng)期以來(lái)的發(fā)展,以及建構(gòu)起一套屬于本國(guó)自身、符合多民族國(guó)家發(fā)展與演變的理論,成為了當(dāng)前國(guó)內(nèi)史學(xué)界面臨的重要問(wèn)題,葛兆光、羅志田、李大龍、黃興濤等人對(duì)此問(wèn)題皆有專著論述③,王柯教授的著作無(wú)疑是極大地豐富了對(duì)此問(wèn)題的探討。此書(shū)于2001 年問(wèn)世,曾于2014 年在臺(tái)灣政大出版社發(fā)行,此次以簡(jiǎn)體版在大陸出售,共十章約20 余萬(wàn)字,其內(nèi)容詳論于下。
第一、二章主要探討了中國(guó)一直以來(lái)的“天下”概念。作者認(rèn)為“天下”一詞是中華文明的核心內(nèi)容,它是以“天”的存在為前提,“天子”為“天”之子,三者構(gòu)成了先秦時(shí)期的“天下思想”。再以此作為邏輯的出發(fā)點(diǎn),探討了“天下”與“四海之內(nèi)”“九州”等詞匯的關(guān)系,并認(rèn)為“九州”是先秦時(shí)期諸政權(quán)所能控制的“天下”,而“四海之內(nèi)”則是一種理想化“天下”。作者還從服制出發(fā),將“天下”分為“內(nèi)服”與“外服”,前者多為直接控制的京幾與諸侯國(guó),后者則為蠻夷民族地區(qū)。這樣在“天下”模式上,形成了“三重天下”模式,即在地理上將天下劃分為“九州”與“四海”,在方位上劃分為“中國(guó)”與“四夷”,在民族集團(tuán)上劃分為“華夏”與“蠻夷戎狄”。
基于以上的論述,作者又探討了“天下”之內(nèi)的“華夷之辯”等問(wèn)題,并舉出大量事例證明中國(guó)最初的民族思想,劃分依據(jù)非人種與地域,而是生活生產(chǎn)方式、價(jià)值觀念與文化思想。即判斷中國(guó)人的標(biāo)準(zhǔn)在文化而非血統(tǒng),在生活方式而非地域差別。這種區(qū)別的意義在于,它將“民族”作為一種可更替的屬性,賦予了少數(shù)民族自由選擇是否作為中國(guó)人的權(quán)力。即 “蠻夷戎狄”如若接受“華夏”的文明方式就變成了“華夏”,反之亦然。而“蠻夷戎狄”向“華夏”有兩種轉(zhuǎn)變方式,其一通過(guò)各種手段移居中原,接受農(nóng)業(yè)文化,其二采用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方式,主動(dòng)向“華夏”靠攏,這賦予了“中國(guó)”向外擴(kuò)展的路徑。在談及夷夏之防的問(wèn)題時(shí),作者指出“天下思想”強(qiáng)調(diào)的是德治,即“禮”的構(gòu)建,“中國(guó)”的“天子”有“德”知禮,則使得域外蠻夷歸附,如若“四夷”之人明德修禮,則可入住“中國(guó)”,禮與德成為了文明與野蠻易位的關(guān)鍵,并為異民族建立“征服王朝”提供了統(tǒng)治“中國(guó)”的合法性依據(jù)。
第三、四、五、六章則主要細(xì)論由秦至明,歷朝民族與國(guó)家的關(guān)系。秦滅六國(guó),開(kāi)始了對(duì)周邊民族的戰(zhàn)爭(zhēng),秦始皇每征服一個(gè)異民族地域,便在此地建立了臣服于自己的“屬邦”,實(shí)行間接統(tǒng)治。作者認(rèn)為“屬邦制”的意義是它開(kāi)啟了中國(guó)歷史上兩千年中央集權(quán)制時(shí)代多民族國(guó)家體制之先河。漢承秦制,漢朝將秦朝統(tǒng)治之下的南越、東越、西南夷和朝鮮等異族居住地,劃為“內(nèi)屬國(guó)”,采取了撤邊、統(tǒng)令等舉措;而認(rèn)定西域等地為“外屬國(guó)”,與它們“約為外臣”,實(shí)行間接統(tǒng)治。由此一來(lái),秦漢王朝建立“三重天下”的秩序,即將“天下”劃為了“漢人”之地、中國(guó)之內(nèi)的“內(nèi)屬國(guó)”、以及中國(guó)之外的“外臣國(guó)”。
五胡十六國(guó)時(shí)代,胡人在中原建立了一系列政權(quán)。盡管他們未能一統(tǒng)中國(guó),但他們認(rèn)為自己為中國(guó)之正統(tǒng)。此時(shí),胡人政權(quán)出于維護(hù)統(tǒng)治需要,并受中國(guó)文化中“天子修德”思想的影響,在自身的政治制度上采取了中華王朝化的方式,在文化制度上采取了儒學(xué)化的方式,在經(jīng)濟(jì)形勢(shì)上采取了農(nóng)業(yè)化和地緣化的方式,使得自身不再保留異族風(fēng)俗,極力同化于漢族。
唐遼元清四朝的統(tǒng)治者,不僅具有民族首長(zhǎng)的身份,更是中華王朝的統(tǒng)治者。由此一來(lái),基于這雙重身份,使得漢人統(tǒng)治者將其治下的地域分為多重來(lái)進(jìn)行統(tǒng)治,非漢民族統(tǒng)治者則將其治下的地域分為多元來(lái)進(jìn)行統(tǒng)治。基于此種認(rèn)知,唐朝的統(tǒng)治者對(duì)異族采取了“羈縻府州制”,此制度之意義在于,它開(kāi)啟了中華文化的中國(guó)與非漢文化的周邊民族共存的雙重構(gòu)造體制,拋棄了戰(zhàn)爭(zhēng),采納了文化作為征服異族的主要力量,讓異族吸收、認(rèn)可中國(guó)文化,繼而將其改造為中華之一部分。遼朝和元朝,因?yàn)槎邽楫愖褰⒅?quán),故在政治與文化制度上,兩朝的統(tǒng)治者在堅(jiān)持自身民族個(gè)性與吸收中國(guó)文化間不斷搖擺,從而形成了“民族與中華”二元性體制,通過(guò)將“中國(guó)” (即漢人活動(dòng)區(qū)域)與本民族的活動(dòng)區(qū)域相隔離,形成了“南北區(qū)隔”的二元體制。但隨著時(shí)間的發(fā)展,這些異族征服王朝,在政治與文化上,或有意或無(wú)意地接受了中華文化,并用中華文化改造自身,這對(duì)中國(guó)多民族統(tǒng)一國(guó)家思想和多民族統(tǒng)一國(guó)家傳統(tǒng)的形成過(guò)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元朝開(kāi)始的土司制度,在尚未滲透中華文化的西南地區(qū)確立了國(guó)家主權(quán),明清繼承了元的土司制度,將西南地區(qū)置于自己的統(tǒng)治后,開(kāi)始實(shí)行“改土歸流”,變對(duì)西南地區(qū)非漢民族的間接統(tǒng)治為直接統(tǒng)治,積極促進(jìn)邊疆地區(qū)內(nèi)地化和非漢民族漢化。
第七、八章則將視域?qū)W⒌角宕鷮?duì)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的統(tǒng)治,重點(diǎn)論述了清政府對(duì)新疆統(tǒng)治方式的建立與轉(zhuǎn)變。作者通過(guò)梳理清朝統(tǒng)治者入關(guān)前后思維的轉(zhuǎn)變,即以異族入主中原,在先天的思維上采取了不信任漢人、與蒙古等少數(shù)民族交好的政策,此時(shí)清朝的天下構(gòu)造具有雙重性,即清帝不僅是中國(guó)的皇帝,而是蒙古等少數(shù)民族的盟主,此時(shí)清人不再視異族為“夷”,“夷”逐漸與“外”相配套,用于指代沙俄等外國(guó)。
基于此,作者以新疆為探討重點(diǎn),認(rèn)為清朝前期在新疆等地實(shí)行的是“藩部制”,即延續(xù)了長(zhǎng)期以來(lái)“因其教不改其俗、齊其政不改其宜”、“以當(dāng)?shù)厣蠈咏y(tǒng)治者治理本地”的思維。同時(shí)清政府禁止?jié)h人與其交流,使得新疆等地的人民缺乏中國(guó)國(guó)家意識(shí)與中國(guó)人的意識(shí),進(jìn)而成為了近代中國(guó)民族問(wèn)題產(chǎn)生之禍源。此時(shí)的清政府,形成了一種以民族等級(jí)制度為基礎(chǔ)、按民族異同劃分地域單位的“多元型天下”的政治傳統(tǒng),進(jìn)而將其統(tǒng)治疆域建設(shè)成為了一種旨在牽制漢人的、主權(quán)定義模糊、領(lǐng)土疆界不清、國(guó)民范疇分歧的“多元型天下”。在這種“天下國(guó)家”之內(nèi),領(lǐng)土、主權(quán)和國(guó)民的范圍,三位一體,無(wú)法適應(yīng)以民族國(guó)家為基本單位的近代國(guó)際體系的現(xiàn)實(shí)需要。而后隨著清政府的沒(méi)落以及西方列強(qiáng)的入侵,日本開(kāi)始試圖搶占臺(tái)灣,而新疆的阿古柏政權(quán)也在外國(guó)支持下發(fā)動(dòng)“圣戰(zhàn)”。一時(shí)之間,海陸兩域皆面臨失去之危險(xiǎn),內(nèi)憂外患層層疊加,這使得傳統(tǒng)的“藩部制”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zhàn)。自1864 年“新疆動(dòng)亂”以后,清政府開(kāi)始思考改革“藩部制”之弊端,1876 年左宗棠收復(fù)新疆后,清政府便徹底地放棄“藩部制”,改用行省制。這一舉措具有重大意義,因?yàn)樗粌H標(biāo)志著清政府放棄了自身民族政權(quán)性質(zhì)與“多元型”天下,而且標(biāo)志著中國(guó)人還是轉(zhuǎn)變了自己的國(guó)家思想與民族集團(tuán)意識(shí)。
第九、十章則為近代章,主要探討了中華民國(guó)與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時(shí)期的民族國(guó)家觀念。隨著清政府統(tǒng)治的日益沒(méi)落,革命家開(kāi)始了民族革命活動(dòng),這時(shí)孫中山等人吸收西歐的民族國(guó)家觀念,其思想發(fā)展大體分為三個(gè)階段,其一是反滿排滿的狹義民族主義,其二是“五族共和”的思想,其三是同化中國(guó)所有各族為一個(gè)中華民族的“大中華民族思想”。作者通過(guò)比對(duì)了西方民族國(guó)家思想與孫中山所提出的民族國(guó)家思想。他認(rèn)為西方所說(shuō)的Nation既指民族又指國(guó)民,故Nation State 既是民族國(guó)家又是國(guó)民國(guó)家,且西方的民族主義是一種地域型民族主義,強(qiáng)調(diào)統(tǒng)一的法律和制度之下的團(tuán)體意識(shí)和共同文化,并以此構(gòu)建起一個(gè)同屬于某個(gè)政治同心圓的民族。但孫中山所主張的民族主義,雖號(hào)稱吸收西方民族國(guó)家思想,然實(shí)則與其相去甚遠(yuǎn),孫氏所謂民族國(guó)家思想即為民族型的民族主義,不僅只強(qiáng)調(diào)族群的血統(tǒng)、輕視共同的生活地域與文化,而且要在原有的多民族國(guó)家中以民族為要素區(qū)別各個(gè)共同體,進(jìn)而打破了清王朝現(xiàn)有的中央集權(quán)的國(guó)家秩序,故孫氏的民族主義不僅容易出現(xiàn)地域之間的割據(jù),而且也容易出現(xiàn)民族之間的分裂。
而中國(guó)共產(chǎn)黨所主張的民族國(guó)家主義,在自身的發(fā)展歷程中經(jīng)歷了三個(gè)較為重要的階段。第一階段為1922 年—1937 年,即在中共二大所產(chǎn)生的《宣言》與《決議案》中,提出的“民族自決”政策,其內(nèi)容為允許少數(shù)民族獨(dú)立地建設(shè)自己的民族國(guó)家,主張建立“聯(lián)邦制國(guó)家”,并希望少數(shù)民族與漢族共同建立中華聯(lián)邦制國(guó)家。第二階段為1937年—1945 年,即中共中央提出的“民族自決論”,否定了之前主張的“民族獨(dú)立”論。第三階段為1946 年—1949 年,即中共中央否定了“聯(lián)邦制”,逐步實(shí)施并最終確立“民族區(qū)域自治”為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的一項(xiàng)根本政治制度。此三個(gè)階段反映出中國(guó)共產(chǎn)黨在自身發(fā)展歷程中,不斷適應(yīng)時(shí)代變化,改革自身的觀念,從而維護(hù)了無(wú)產(chǎn)階級(jí)和中華民族的利益,使得中國(guó)國(guó)家站穩(wěn)了立場(chǎng),并不斷領(lǐng)導(dǎo)各民族欣欣向榮的發(fā)展。中國(guó)共產(chǎn)黨的民族思想不斷成熟與進(jìn)步,才使中國(guó)多民族統(tǒng)一國(guó)家的優(yōu)秀傳統(tǒng)在現(xiàn)今不斷得以繼承和發(fā)展。
二
王柯先生出生于1956 年,1982 年就讀于中央民族學(xué)院,獲民族學(xué)專業(yè)碩士學(xué)位,1994 年就讀于東京大學(xué)研究生院,獲博士學(xué)位。在長(zhǎng)達(dá)三十余年的時(shí)間里,專攻中國(guó)近現(xiàn)代思想史、國(guó)際關(guān)系史,出版了多部著作,可謂日本近代史學(xué)界魯?shù)铎`光。本書(shū)便是王柯教授20 余年心血之作,對(duì)此書(shū)的特點(diǎn)與學(xué)術(shù)貢獻(xiàn),筆者略歸納如下:
一是行文邏輯思維嚴(yán)密,就某一問(wèn)題采取層層深入的方式進(jìn)行探討,所得出的結(jié)論令人信服。作者在本書(shū)的研究開(kāi)頭,即明言以中國(guó)一直以來(lái)的“天”與“天下”思想為切入點(diǎn),闡述二者之間的聯(lián)系,并梳理了中國(guó)人“天下”的世界觀,進(jìn)而理解了“中國(guó)”與“四夷”的關(guān)系。在論及“華夷”的問(wèn)題時(shí),作者舉了大量事例指出文化與德治才是華夷之辯的核心,華夷在一定條件下可以相互轉(zhuǎn)換,這為異族入主中國(guó)提供了理論支撐。為了看清異族與中國(guó)之間的互動(dòng)關(guān)系,作者以朝代梳理的方式,論述了中國(guó)歷代王朝的“天下”思想觀念的影響下所采取的民族政策與文化方式,并以新疆為典型案例進(jìn)行專題分析,最終論證中國(guó)自古以來(lái)便是一個(gè)文明型的多民族共同發(fā)展的國(guó)家。
二是對(duì)近代以來(lái)西方中心論的駁斥與回應(yīng)。近年來(lái),隨著西方族群理論的傳入,加之理論視角與學(xué)術(shù)話語(yǔ)的差異性等問(wèn)題,西方史學(xué)界不斷對(duì)傳統(tǒng)中國(guó)的民族與國(guó)家提出質(zhì)疑與批判,如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 主張的“內(nèi)亞視角”以及羅友枝提出的“新清史”,不斷地沖擊著中國(guó)史學(xué)界,一些單純的學(xué)術(shù)討論不斷地被摻雜上政治與意識(shí)形態(tài)的內(nèi)容,一些西方學(xué)者借機(jī)否定中國(guó)對(duì)少數(shù)民族實(shí)施主權(quán)的合理性,認(rèn)為中國(guó)自古以來(lái)便是一個(gè)兼并與強(qiáng)權(quán)的政治角色,此書(shū)的誕生恰恰是對(duì)這些命題的有力駁斥與回應(yīng)。
作者從民族和國(guó)家的關(guān)系出發(fā),分析了少數(shù)民族與中國(guó)政權(quán)的互動(dòng),認(rèn)為“夷夏之辨”最主要的不在血緣與地域,而在文化與思想,中國(guó)之所以得以不斷壯大,是因?yàn)樯贁?shù)民族不斷地認(rèn)可并吸收中國(guó)文化,以中國(guó)文化改革自身的思想,使得中國(guó)的地域范圍不斷擴(kuò)大,從而否定了西方史學(xué)界一直以來(lái)提出的“武力兼并說(shuō)”。
在近年來(lái)的新疆問(wèn)題上,作者指出新疆作為清政府治下的一部分,長(zhǎng)期囿于“藩部制”的隔閡,使得新疆人民缺乏中國(guó)人的意識(shí)與認(rèn)同感,但這并非意味著新疆不是中國(guó)的一部分,相反之下,隨著左宗棠等人在新疆設(shè)立“行省制”,使得新疆作為中國(guó)的一部分重新納入政權(quán)治理體系之中,故新疆絕無(wú)獨(dú)立區(qū)域之說(shuō)。作者就近年來(lái)“中華民族”是一個(gè)想象共同體而非客觀事實(shí)的問(wèn)題,指出“中華民族”是近代才出現(xiàn)的概念,它的出現(xiàn)模糊了“民族”、“國(guó)民”、“國(guó)家”之間的界限,進(jìn)而形成了超乎血緣與地域之上的組織,為中華民族學(xué)說(shuō)的發(fā)展奠定了基礎(chǔ)。
在清朝是一個(gè)“內(nèi)亞性”王朝的學(xué)說(shuō)上,西方史學(xué)界意圖通過(guò)滿清入主中原表明這是一次少數(shù)民族對(duì)漢民族的征服,即證明清朝是一個(gè)內(nèi)亞性的王朝,其統(tǒng)治的內(nèi)亞地區(qū)與漢族區(qū)域相對(duì)立,極力否認(rèn)清朝統(tǒng)治者對(duì)中華文化以及漢化的認(rèn)同,并認(rèn)為清朝之所以能夠統(tǒng)治近300 年是因?yàn)樗麄儽3至藵M洲與滿族的習(xí)俗,進(jìn)而達(dá)到“去漢化”“去中國(guó)化”的目的。本書(shū)對(duì)此說(shuō)進(jìn)行了批判,作者認(rèn)為滿清對(duì)滿蒙回藏的統(tǒng)治采取了與內(nèi)地不同的方式,在前者主要以可汗、文殊菩薩等身份統(tǒng)治,而后者則主要以皇帝身份統(tǒng)治。滿清入主中原后,于康熙時(shí)期控制滿蒙、于乾隆時(shí)期控制藏疆進(jìn)而完成了對(duì)內(nèi)亞的控制。但這種控制并非實(shí)質(zhì)的,而是采取前代“以夷制夷”的方式,故而可見(jiàn)清朝在治理國(guó)家經(jīng)驗(yàn)上的一致性。自后漢族地主官僚不斷崛起,滿蒙八旗與綠營(yíng)軍戰(zhàn)斗力的衰落,使得漢族官僚興盛團(tuán)練,并掌握軍隊(duì),從而擁有了私人武裝勢(shì)力。曾國(guó)藩、李鴻章、張之洞、左宗棠等漢族官僚入主中央并擔(dān)任高官,滿蒙回藏的民族聯(lián)合體不再被重視,清帝逐步拋棄了滿蒙回藏盟主的身份,使得清初形成的“多元型天下”秩序瓦解,使得其內(nèi)亞性最終消亡。
三是善用圖表等形式對(duì)文中的論點(diǎn)展開(kāi)敘述。一篇文章、一部著作,其最終的受眾為讀者,因此想要讀者易懂作者想要表述的觀點(diǎn),就要借用到圖表進(jìn)行歸納與闡述,本書(shū)在此方面都做到了盡善盡美。通讀本書(shū),可知此書(shū)圖表十分精要,如“五服圖”、“明堂圖”、“胡人統(tǒng)御非漢族集團(tuán)官職表”等,精要地向讀者展現(xiàn)了作者的思維邏輯。
三
當(dāng)然,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亦有一得,雖然本書(shū)創(chuàng)見(jiàn)極多,但筆者細(xì)度之下仍有些許疑惑,特列于下以示引玉之意。一是在本書(shū)的引文上,似偏重于日本學(xué)者和古籍材料,而對(duì)中國(guó)學(xué)者的成果引用較少。諸如前述,中國(guó)學(xué)界在“民族與國(guó)家”問(wèn)題的研究上,涌現(xiàn)出不少出色的學(xué)者與著作,但在本書(shū)中較少出現(xiàn)。筆者猜想蓋王柯教授旅居于日本之緣故,對(duì)中國(guó)史學(xué)界較少接觸,故難以苛責(zé),但終顯遺憾。二是文章在論述時(shí),似乎有結(jié)論先行之嫌疑。如作者在論述“中國(guó)”人對(duì)“蠻、夷、戎”等詞匯沒(méi)有民族歧視時(shí),舉出了春秋時(shí)期諸國(guó)國(guó)君與大夫在為后代取名字時(shí),常加“蠻、夷、戎”等詞匯,作者就此得出“中國(guó)”人沒(méi)有歧視“蠻、夷、戎”等詞匯的結(jié)論。筆者認(rèn)為這個(gè)結(jié)論是值得商榷的,因?yàn)樵诠糯⒛酥连F(xiàn)代,中國(guó)人取名字常常有“賤名”的思想,常以“豬、狗”為名,因?yàn)槿藗冋J(rèn)為取賤名表示父母對(duì)后代的歧視,從而達(dá)到欺騙鬼神之意,故賤名制是中國(guó)傳統(tǒng)社會(huì)人們?nèi)∶牧?xí)俗,而此處以“蠻、夷、戎”為名,恰恰反映出這些詞匯的低劣與人們對(duì)它的歧視,因此作者在此處的論證似乎值得商榷。諸如此類不復(fù)贅言。三是作者的行文時(shí),出現(xiàn)一些缺憾,如在注釋上存在著一些問(wèn)題。其書(shū)第119 頁(yè)正文第二段,所引《晉書(shū)·陳元達(dá)載記》,其頁(yè)下無(wú)注釋出現(xiàn)。又如在結(jié)語(yǔ)上,本書(shū)似有重復(fù)啰嗦之嫌疑。因?yàn)樽髡咴诿恳粋€(gè)論證結(jié)束后會(huì)以小結(jié)形式出現(xiàn),而后為了強(qiáng)調(diào)單獨(dú)匯集成為每章結(jié)語(yǔ),最后在全書(shū)之后,又形成結(jié)語(yǔ)一章,如此以來(lái)就形成了三處總結(jié),而全文的總結(jié)也只是對(duì)前文的結(jié)語(yǔ)進(jìn)行匯集與歸納,非提煉與深化,故似有贅述之嫌。
總之,該著具有邏輯推斷縝密、史料考證具體等特點(diǎn),并對(duì)長(zhǎng)期以來(lái)的西方中心論給與了有力的回應(yīng),駁斥了西方史學(xué)界一些意圖借學(xué)術(shù)探討為名、行貶低打壓中國(guó)之實(shí)的學(xué)者論斷,為古代中國(guó)的演變提供了堅(jiān)實(shí)的論據(jù)。雖然全書(shū)在文本校對(duì)上有一些瑕疵,但終究瑕不掩瑜,《從“天下”到民族國(guó)家:歷史中國(guó)的認(rèn)知與實(shí)踐》 是一部值得肯定、具有創(chuàng)新且推動(dòng)民族與國(guó)家研究的重要成果。
注釋:
① 參見(jiàn)[日]王柯:《從“天下”到民族國(guó)家:歷史中國(guó)的認(rèn)知與實(shí)踐》,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 年版。
② 梁?jiǎn)⒊骸缎旅裾f(shuō)》,《飲冰室合集·專集第四》,中華書(shū)局1989 年版,第21 頁(yè)。
③葛兆光:《何為“中國(guó)”?——疆域、民族、文化與歷史》,牛津大學(xué)出版社2014 年版;羅志田:《民族主義與近代中國(guó)思想》 (修訂版),三民書(shū)局2011 年版;李大龍:《從“天下”到“中國(guó)”:多民族國(guó)家疆域理論解構(gòu)》,人民出版社2015 年版;黃興濤:《重塑中華:近代中國(guó)的中華民族觀念研究》,北京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17 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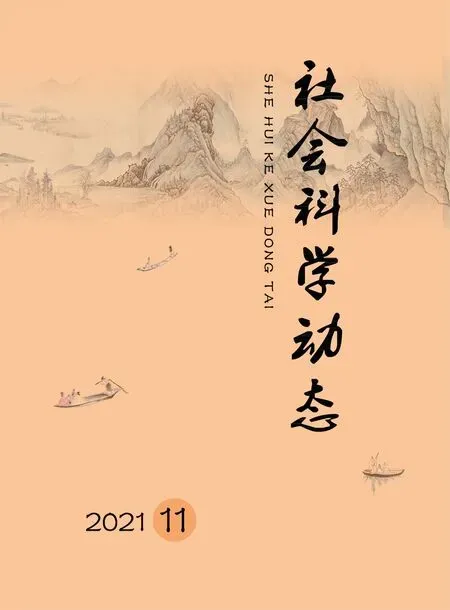 社會(huì)科學(xué)動(dòng)態(tài)2021年11期
社會(huì)科學(xué)動(dòng)態(tài)2021年11期
- 社會(huì)科學(xué)動(dòng)態(tài)的其它文章
- 行政訴訟自認(rèn)規(guī)則之理論、立法與實(shí)踐
——基于107 份裁判文書(shū)的統(tǒng)計(jì)分析 - 國(guó)家治理視域下社會(huì)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的影響因素
- 《宋代石刻功能的多元透視與文學(xué)個(gè)案分析》的學(xué)術(shù)特色與價(jià)值
- 唐宋變革視域下的文人身份認(rèn)同與群體書(shū)寫(xiě)
——評(píng)田安的《知我者:中唐時(shí)期的友誼與文學(xué)》 - 系統(tǒng)全面論述長(zhǎng)江經(jīng)濟(jì)帶演化進(jìn)程的寫(xiě)實(shí)佳作
- 文化轉(zhuǎn)型中的中外文學(xué)關(guān)系研究
——中國(guó)比較文學(xué)第十三屆年會(huì)第一分組綜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