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文人與聲韻詩學(xué)的自覺
黃金燦
一、獨(dú)得胸衿:大家與名家的多樣貢獻(xiàn)
魏晉南北朝時(shí)期的不少大家、名家,如曹植、陸機(jī)、范曄、沈約等人,都在聲韻詩學(xué)自覺的進(jìn)程中發(fā)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曹植(192—232) 對(duì)聲韻規(guī)律已經(jīng)了然于胸。釋慧皎《高僧傳·經(jīng)師論》云:“始有魏陳思王曹植深愛聲律,屬意經(jīng)音,既通般遮之瑞響,又感《魚山》 之神制;于是刪治《瑞應(yīng)本起》,以為學(xué)者之宗,傳聲則三千有馀,在契則四十有二。”②又云:“昔諸天贊唄,皆以韻入弦管,五眾既與俗違,故宜以聲曲為妙。原夫梵唄之起,亦肇自陳思。始箸《太子頌》 及《睒頌》等。因?yàn)橹坡暎录{抑揚(yáng),并法神授,今之皇皇顧惟,蓋其風(fēng)烈也。”③對(duì)此,范文瀾總結(jié)說:“曹植既首唱梵唄,作《太子頌》 《睒頌》,新聲奇制,焉有不扇動(dòng)當(dāng)世文人者乎!故謂作文始用聲律,實(shí)當(dāng)推原于陳王也。”④筆者認(rèn)為,曹植的確對(duì)聲律之學(xué)頗有會(huì)心,但他還沒有明確的理論表述,并未將其方法總結(jié)出來,上升到理論的高度。
陸機(jī)(261—303) 是首先試圖從理論上對(duì)聲律問題加以闡發(fā)的文人學(xué)者。他在《文賦》 中云:“暨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考殿最于錙銖,定去留于毫芒,茍銓衡之所裁,固應(yīng)繩其必當(dāng)。”⑤他的“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之論是從聲律上對(duì)文學(xué)創(chuàng)作提出的明確要求。徐復(fù)觀解釋道:“按此兩句就文章的韻律所言。此時(shí)四聲之說未出,但音聲有高低、長(zhǎng)短之不同,自有歌謠以來,即有自然的感覺。”⑥可見,陸機(jī)雖然尚未明確用四聲概念來解釋聲律現(xiàn)象,但他已經(jīng)從文學(xué)經(jīng)驗(yàn)出發(fā),產(chǎn)生了提出“聲調(diào)配合原則”的自覺意識(shí)。
范曄 (398—445) 《獄中與諸甥姪書》 曰:“文章轉(zhuǎn)進(jìn),但才少思難,所以每于操筆,其所成篇,殆無全稱者。常恥作文士文,患其事盡于形,情急于藻,義牽其旨,韻移其意,雖時(shí)有能者,大較多不免此累。政可類工巧圖繢,竟無得也……性別宮商、識(shí)清濁,斯自然也。觀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處,縱有會(huì)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言之皆有實(shí)證,非為空談。年少中,謝莊最有其分,手筆差易,文不拘韻故也。”⑦范曄將“宮商”“清濁”等概念用于論文,說明它們已經(jīng)不再是純粹的音樂概念。他認(rèn)為“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處”,而自己則是“從根本中來”的天生解此,“言之皆有實(shí)證,非為空談”。尤其是他的“韻移其意”“文不拘韻”的批評(píng)表述,已經(jīng)是帶有鮮明理論色彩的詩韻觀點(diǎn),這些觀點(diǎn)在后世比較常見,但在詩韻論的濫觴階段卻顯得非常重要。
沈約 (441—513) 也深諳詩文的聲韻規(guī)律。《梁書·沈約傳》載其“撰《四聲譜》,以為在昔詞人累千載而不寤,而獨(dú)得胸衿,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⑧。說明沈約已經(jīng)將一直“隱形”的漢語聲韻規(guī)律顯性化。不過他說“在昔詞人累千載而不寤,而獨(dú)得胸衿”就有點(diǎn)夸大自己的功勞,至少在他之前的范曄就已經(jīng)試圖從理論上對(duì)聲韻規(guī)律予以揭橥。當(dāng)然,沈約確實(shí)是將之外化為成果的第一人,也是與同好一起大肆宣傳、實(shí)踐的第一人。例如《南齊書·陸厥傳》 載:“永明末,盛為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瑯琊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颙善識(shí)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以平上去入為四聲,以此制韻,不可增減,世呼為‘永明體’。”⑨可見當(dāng)時(shí)已經(jīng)形成了風(fēng)氣,而沈約在其中則發(fā)揮著關(guān)鍵作用。他在《答陸厥書》中針對(duì)陸厥的質(zhì)疑仍堅(jiān)持己見:“自古辭人,豈不知宮羽之殊,商徵之別。雖知五音之異,而其中參差變動(dòng),所昧實(shí)多,故鄙意所謂‘此秘未睹’者也。以此而推,則知前世文士便未悟此處。”⑩沈約認(rèn)為,“五音之異”雖自古就有辭人了解,但這里面博大精深,還有許多茫昧不明之處,這就給了后人發(fā)揮創(chuàng)造性的機(jī)會(huì)。
蕭子良(460—494) 與曹植一樣,對(duì)制作梵唄新聲很有興趣。陳寅恪《四聲三問》指出:“南齊武帝永明七年二月二十日,竟陵王子良大集善聲沙門于京邸,造經(jīng)唄新聲。實(shí)為當(dāng)時(shí)考文審音之一大事。在此略前之時(shí),建康之審音文士及善聲沙門討論研求必已甚眾而且精。永明七年竟陵京邸之結(jié)集,不過此新學(xué)說研求成績(jī)之發(fā)表耳。此四聲說之成立所以適值南齊永明之世,而周颙、沈約之徒又適為此新學(xué)說代表人之故也。”?所謂“新學(xué)說研求成績(jī)之發(fā)表”正是從曹植等“建康之審音文士及善聲沙門討論研求”至蕭子良“大集善聲沙門于京邸,造經(jīng)唄新聲”這段時(shí)間所積累的聲律經(jīng)驗(yàn)的一次大總結(jié)。沈約等文士對(duì)聲韻之學(xué)的情有獨(dú)鐘,既是受當(dāng)時(shí)風(fēng)氣熏染,也與他們個(gè)人的詩學(xué)旨趣息息相關(guān)。“此四聲說之成立所以適值南齊永明之世,而周颙、沈約之徒又適為此新學(xué)說代表人之故也”,也就是說,在這個(gè)時(shí)候,佛教聲律論和文學(xué)聲律論已實(shí)現(xiàn)正式的合流,匯成一股聲勢(shì)浩大、影響深遠(yuǎn)的潮流。
陸厥(464—499) 由于曾致書沈約同他商榷聲律問題,沈約又致書答辯,故而一直被視為聲律論的反對(duì)者。實(shí)際上他不滿的是沈約“自靈均以來,此秘未睹”的自負(fù)與偏頗。《南齊書·陸厥傳》載,陸厥寄書與沈約云:“但歷代眾賢,似不都暗此處,而云‘此秘未睹’,近于誣乎?……意者,亦質(zhì)文時(shí)異,古今好殊,將急在情物,而緩于章句。情物,文之所急,美惡猶且相半;章句,意之所緩,故合少而謬多。義兼于斯,必非不知明矣。”?陸厥不忽視前人的功勞,合理地分析了“情物”與“章句”的主次關(guān)系,他的論說步步為營,穩(wěn)扎穩(wěn)打,或許使沈約也差點(diǎn)理屈詞窮。但沈約也堅(jiān)持認(rèn)為,“文章之音韻”同“管弦之聲曲”其實(shí)是一個(gè)道理。“五音之異”自古就有辭人了解,但仍有許多茫昧不明之處,即音韻之學(xué)前代有詩人觸及,但并不全面,更不系統(tǒng),其中許多規(guī)律性的東西需要探討。
甄琛(?—524) 與沈約的爭(zhēng)論則更側(cè)重于就聲律問題本身展開。 《魏書·甄琛傳》:“所著文章,鄙碎無大體,時(shí)有理詣,《磔四聲》……頗行于世。”?可見,史書對(duì)甄琛的文學(xué)成就評(píng)價(jià)并不太高。日人遍照金剛《文鏡秘府論》之《四聲論》則云:“魏定州刺史甄思伯,一代偉人,以為沈氏《四聲譜》,不依古典,妄自穿鑿,乃取沈君少時(shí)文詠犯聲處以詰難之。”?甄琛之所以反對(duì)四聲論,是因?yàn)樗X得:“若計(jì)四聲為紐,則天下眾聲無不入紐,萬聲萬紐,不可止為四聲也。”?可見甄琛對(duì)沈約的四聲論,似乎未得其趣。他說“天下眾聲無不入紐”還可,說“萬聲萬紐”就不對(duì)了。按照中國語音發(fā)展的實(shí)際,把語音分為平、上、去、入四聲,在很長(zhǎng)一段時(shí)間內(nèi),是符合語音發(fā)展規(guī)律的。因此,遍照金剛評(píng)價(jià)說:“甄公此論,恐未成變通矣。”?針對(duì)甄琛的指責(zé),沈約也作了答辯,他強(qiáng)調(diào)四聲并不違反“古典”,而且有助于寫出符合美學(xué)原則的好作品。沈約認(rèn)為,五聲是音樂的必備要素,四聲是詩歌的必備要素,如在詩歌創(chuàng)作中“善用四聲”,就能收到“諷詠而流靡”的藝術(shù)效果。
教室里鴉雀無聲,但我卻感覺有點(diǎn)不對(duì)勁兒,孩子們并不像我想的那般著迷與陶醉。他們中有的相互使著眼色,有的驚訝地望著我,也有的向我投來驚喜的目光。當(dāng)我把從文中領(lǐng)會(huì)到的情感用目光傳遞出來、與這些眼神交匯的時(shí)候,這些眼睛便趕緊低垂下來,一副極不好意思的樣子。原來孩子們關(guān)注的不是課文,而是我!好像他們從來沒聽過老師這么朗讀課文似的。
鐘嶸(約468—518) 也是聲律探討的重要一家,但他也是作為反對(duì)者出現(xiàn)。他在《詩品》中認(rèn)為:“昔曹、劉殆文章之圣,陸、謝為體貳之才,銳精研思,千百年中,而不聞宮商之辨,四聲之論……今既不被管弦,亦何取于聲律邪……余謂文制本須諷讀,不可蹇礙,但令清濁通流,口吻調(diào)利,斯為足矣。至平上去入,則余病未能;蜂腰、鶴膝,閭里已具。”?由此可見,鐘嶸的反對(duì)立場(chǎng)是非常明確的。但是與劉勰相比,劉勰已經(jīng)通過提出“外聽”“內(nèi)聽”等概念將音樂之聲律與文學(xué)之聲律截然分開,而鐘嶸仍然停留在音樂之聲律上,認(rèn)為樂府、古詩如果不譜曲入樂其聲律就無從談起。其實(shí)樂府、古詩即便不入樂而僅是純文學(xué)文本,那其字句章法之間也是可以有聲律的,這個(gè)聲律就是文學(xué)的聲律。但鐘嶸對(duì)這種聲律是極為反對(duì)的,他說:“王元長(zhǎng)創(chuàng)其首,謝朓、沈約揚(yáng)其波,三賢或貴公子孫,幼有文辯,于是士流景慕,務(wù)為精密,襞積細(xì)微,專相陵架,故使文多拘忌,傷其真美。”?在當(dāng)時(shí)文壇和理論界一味推崇聲律的大環(huán)境中,鐘嶸對(duì)聲律論的反對(duì)有一定的扶弊糾偏作用。但文學(xué)從“原生態(tài)”創(chuàng)作走向規(guī)律指導(dǎo)下的創(chuàng)作是歷史的必然,后來的唐詩、宋詞所取得的高度藝術(shù)成就也證明了聲律論的科學(xué)性和藝術(shù)價(jià)值。鐘嶸對(duì)這一歷史發(fā)展的必然規(guī)律不以為然,就顯得有些落伍了。
二、同聲相應(yīng)謂之韻:劉勰押韻論的獨(dú)特貢獻(xiàn)
學(xué)界在談及“聲韻”與“聲律”時(shí),很少對(duì)二者進(jìn)行比較嚴(yán)格的區(qū)分,時(shí)常是一帶而過,籠統(tǒng)混用。之所以會(huì)如此,是因?yàn)槎咴诟拍顑?nèi)涵上確實(shí)有較大的重疊面。需要聲明的是,筆者在使用這兩個(gè)概念時(shí),卻有明顯的區(qū)別傾向:用“聲律”時(shí)強(qiáng)調(diào)“律”,即強(qiáng)調(diào)文本在聲調(diào)、音律、格律等聲音層面的規(guī)范和要求;用“聲韻”時(shí)則強(qiáng)調(diào)“韻”,即強(qiáng)調(diào)文本所達(dá)到的聲音上的和諧狀態(tài)。這種和諧狀態(tài)既可以來自文本的外在音樂性,又可以來自文本的內(nèi)在音樂性,更可以來自二者的結(jié)合;押韻正是文本獲得內(nèi)在音樂性的核心結(jié)構(gòu)要素之一,也是文本內(nèi)在音樂性與外在音樂性相呼應(yīng)的媒介,故而押韻在“聲韻”范疇中具有更為特殊的地位。劉勰既高度重視“聲律”問題又對(duì)押韻問題予以了深入闡發(fā),這是遠(yuǎn)遠(yuǎn)超越了同時(shí)代其他人的獨(dú)特貢獻(xiàn),在聲韻詩學(xué)史上具有承上啟下的關(guān)鍵意義。
劉勰 (約 465—520) 在 《文心雕龍》 中專設(shè)《聲律》一篇闡發(fā)文學(xué)聲律問題。從某種程度上說,他的探討比沈約等人的表述更精密、更系統(tǒng),堪稱魏晉南北朝以來聲律探索的集大成。他在該篇開頭就指出:“夫音律所始,本于人聲者也。聲含宮商,肇自血?dú)猓韧跻蛑灾茦犯琛9手鲗懭寺暎暦菍W(xué)器者也。故言語者,文章(關(guān)鍵),神明樞機(jī),吐納律呂,唇吻而已。”?通過簡(jiǎn)明扼要的語言,論證了聲律客觀存在于作為“文章神明樞機(jī)”的言語之中;接下來對(duì)“古人教歌”之法的論述也不再是簡(jiǎn)單的借音樂概念來比附文學(xué)概念,其目的則是通過音樂歌唱離不開聲律來論證文學(xué)創(chuàng)作同樣離不開聲律。劉勰所質(zhì)疑的“今操琴不調(diào),必知改張,摘文乖張,而不識(shí)所調(diào)”的奇怪現(xiàn)象也是源于人們對(duì)音樂聲律和文學(xué)聲律所持不同態(tài)度的反思,這一反思同樣也是意在說明文學(xué)創(chuàng)作需要講求聲律。劉勰對(duì)這一奇怪現(xiàn)象產(chǎn)生的原因也有所思考:“響在彼弦,乃得克諧,聲萌我心,更失和律:其故何哉?良由內(nèi)聽難為聰也。故外聽之易,弦以手定,內(nèi)聽之難,聲與心紛,可以數(shù)求,難以辭逐。”?他認(rèn)為音樂的聲律是外在的,而文學(xué)的聲律是內(nèi)在的,外在的東西好把握,“故外聽之易,弦以手定”,而內(nèi)在的東西難把握,故“內(nèi)聽之難,聲與心紛,可以數(shù)求,難以辭逐”。接著他又強(qiáng)調(diào):“凡聲有飛沉,響有雙疊;雙聲隔字而每舛,疊韻雜句而必睽;沉則響發(fā)而斷,飛則聲飏不還:并轆轤交往,逆鱗相比;迂其際會(huì),則往蹇來連,其為疾病,亦文家之吃也。”?可見文學(xué)聲律的規(guī)律性非常強(qiáng),如果不能遵循這些規(guī)律,就會(huì)出現(xiàn)文病,造成詩文的蹇吃窒礙。
劉勰《文心雕龍·聲律篇》對(duì)押韻問題的探討,充分表明了他在這一問題上所達(dá)到的理論高度。在《聲律篇》 中,劉勰認(rèn)為文章窒礙的原因在于:“夫吃文為患,生于好詭,逐新趣異,故喉唇糾紛。”?其解決的辦法是:“將欲解結(jié),務(wù)在剛斷。左礙而尋右,末滯而討前,則聲轉(zhuǎn)于吻,玲玲如振玉,辭靡于耳,累累如貫珠矣。”?范文瀾注引《文鏡秘府論》 四曰:“若文系于韻,則量其韻之多少,若事不周圓,功必疏闕。與其終將致患,不若易之于初。”?范文瀾認(rèn)為“此說頗可推暢彥和之意”,說明劉勰的解決辦法也適用于韻的安排。接下來劉勰更是詳細(xì)地介紹了具體操作辦法,其中就明確對(duì)押韻提出了要求:“是以聲畫妍蚩,寄在吟詠,吟詠?zhàn)涛叮饔谧志洹#ㄗ志洌?氣力,窮于和韻。異音相從謂之和,同聲相應(yīng)謂之韻。韻氣一定,故馀聲易遣;和體抑揚(yáng),故遺響難契。屬筆易巧,選和至難;綴文難精,而作韻甚易。雖纖意曲變,非可縷言,然振其大綱,不出茲論。”?范注曰:“和與韻為二事,下文分言之。范曄《獄中與諸甥姪書》曰:‘常恥作文士文,患其事盡于形,情急于藻,義牽其旨,韻移其意,雖時(shí)有能者,大較多不免此累。’又曰:‘手筆差易,于文不拘韻故也。’”?按注引范曄“韻移其意”“文不拘韻”諸論,與劉勰之論并列,正可起到互相闡發(fā)的作用。一則能說明劉勰之論乃淵源有自,一則可以說明押韻問題早在范曄時(shí)就有精辟闡發(fā)。范注又曰:“異音相從謂之和,指句內(nèi)雙聲疊韻及平仄之和調(diào);同聲相應(yīng)謂之韻,指句末所用之韻。韻氣一定,故馀聲易遣,謂擇韻既定,則馀韻從之;如用東韻,凡與同韻之字皆得選用。和體抑揚(yáng),故遺響難契,謂一句之中,音須調(diào)順,上下四句間,亦求合適。此調(diào)聲之術(shù),所以不可忽略也。”?此注對(duì)劉勰押韻之論的闡發(fā)非常準(zhǔn)確,也進(jìn)一步說明押韻之法是“調(diào)聲之術(shù)”中不可或缺的一個(gè)部分。
劉勰接著又總結(jié)說:“若夫?qū)m商大和,譬諸吹籥;翻回取均,頗似調(diào)瑟。瑟資移柱,故有時(shí)而乖貳;籥含定管,故無往而不壹。陳思潘岳,吹籥之調(diào)也;陸機(jī)左思,瑟柱之和也。概舉而推,可以類見。”?范注曰:“此謂陳思、潘岳吐言雅正,故無往而不和。士衡語雜楚聲,須翻回以求正韻,故有時(shí)而乖貳也。左思齊人,后乃移家京師,或思文用韻,有雜齊人語者,故彥和云然。”?劉勰的這段話有些抽象,范文瀾結(jié)合所論諸家的用韻訓(xùn)釋之,其義乃粲然大明。劉勰接著又就用韻問題補(bǔ)充道:“又詩人綜韻,率多清切;楚辭辭楚,故訛韻實(shí)繁。及張華論韻,謂士衡多楚,文賦亦稱知楚不易,可謂銜靈均之聲馀,失黃鐘之正響也。凡切韻之動(dòng),勢(shì)若轉(zhuǎn)圜;訛音之作,甚于枘方;免乎枘方,則無大過矣。”?范注引陸云寫給陸機(jī)的論韻諸書信,指出:“觀此諸語,知當(dāng)時(shí)無標(biāo)準(zhǔn)韻書,故得正韻頗不易也。”?又注云:“《札記》曰‘此言文中用韻,取其諧調(diào),若雜以方音,反成詰詘。今人作文雜以古韻者,亦不可不知此。’自陸法言撰《切韻》,方言雖歧,而詩文用韻,無不正矣。”?這些都相當(dāng)準(zhǔn)確地捕捉到了劉勰的本意,并透露了系統(tǒng)的聲韻知識(shí)之于詩歌創(chuàng)作的價(jià)值。
此外,《文心雕龍》除在《聲律》篇中系統(tǒng)討論押韻,在其他篇章中對(duì)押韻也多有提及。 《明詩》篇云:“孝武愛文,柏梁列韻;嚴(yán)馬之徒,屬辭無方。”?又云:“至于三六雜言,則出自篇什;離合之發(fā),則明于圖讖;回文所興,則道原為始;聯(lián)句共韻,則柏梁馀制。”?《銓賦》篇曰:“至如鄭莊之賦《大隧》,士蔿之賦《狐裘》,結(jié)言短韻,詞自己作,雖合賦體,明而未融。”?《頌贊》篇曰:“及景純注《雅》,動(dòng)植必贊,義兼美惡,亦猶頌之變耳。然本其為義,事生獎(jiǎng)嘆,所以古來篇體,促而不廣。必結(jié)言于四字之句,盤桓乎數(shù)韻之辭,約舉以盡情,昭灼以送文,此其體也。”?《哀吊》篇曰:“揚(yáng)雄吊屈,思積功寡,意深文略,故辭韻沉膇……夫吊雖古義,而華辭未造,華過韻緩,則化而為賦。”?《封禪》篇曰:“至于邯鄲受命,攀響前聲,風(fēng)末力寡,輯韻成頌,雖文理順序,而不能奮飛。”?《章句》篇云:“若乃改韻從調(diào),所以節(jié)文辭氣:賈誼枚乘,兩韻輒易;劉歆桓譚,百句不遷;亦各有其志也。昔魏武論賦,嫌于積韻,而善于資代。陸云亦稱四言轉(zhuǎn)句,以四句為佳。觀彼制韻,志同枚賈;然兩韻輒易,則聲韻微躁;百句不遷,則唇吻告勞;妙才激揚(yáng),雖觸思利貞,曷若折之中和,庶保無咎。”?《總術(shù)》篇曰:“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為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夫文以足言,理兼詩書,別目?jī)擅越!?《才略》篇曰:“曹攄清靡于長(zhǎng)篇,季鷹辨切于短韻,各其善也。”?以上諸論皆是劉勰對(duì)押韻問題的思考,尤其是《章句》 篇中所論之換韻理論、制韻方法,其精深程度絲毫不亞于《聲律》篇。因此說劉勰《文心雕龍》一書在廣泛吸收前代及同時(shí)人的聲律論成果基礎(chǔ)上,既豐富了聲律論又深化了押韻論,從而集該歷史階段的聲韻詩學(xué)之大成,殆不為過。
三、余論
還有一點(diǎn)值得補(bǔ)充,即王斌其人對(duì)聲律學(xué)的發(fā)展應(yīng)當(dāng)也有貢獻(xiàn)。但文獻(xiàn)既已不足征,近年來學(xué)界對(duì)王斌的研究又出現(xiàn)較大的爭(zhēng)議,故筆者不敢有固必之論。杜曉勤在《六朝聲律與唐詩體格》一書中專辟“‘王斌首創(chuàng)四聲說’辨誤”一章對(duì)相關(guān)問題進(jìn)行了探討,最終結(jié)論認(rèn)為:“齊梁時(shí)期至少有三個(gè)王斌:一為曾任吳郡太守之瑯琊王斌(一作瑯邪王份),一為曾任吳興郡太守之瑯邪王彬,一為‘反緇向道’之洛陽(或略陽) 王斌,三人生年均晚于沈約,其中前二人未見有論四聲之作,沙門王斌雖撰有聲病著作,然生年可能比劉勰、鐘嶸還晚,更遑論周颙、沈約了……歸根結(jié)底,對(duì)于‘四聲之目’的首創(chuàng)者,筆者還是相信《文境秘府論》中所引隋劉善經(jīng)《四聲指歸》:‘宋末以來,始有四聲之目。沈氏乃著其譜、論,云起自周颙。’當(dāng)如沈約夫子自道,周颙才是四聲之目的首創(chuàng)者。至于沈約,功在首倡詩文創(chuàng)作中四聲調(diào)諧之法,而非創(chuàng)立四聲之目。”?所論具有條理,值得參考。
隨著聲律探討與押韻批評(píng)的深化,聲韻詩學(xué)理論與實(shí)踐也愈加清晰地顯示出其深度與廣度。吳光興曾指出:“詩歌以語言為載體,語言含聲音一端,本是客觀的因素,但是,在齊梁時(shí)代之前,古人對(duì)于詩歌之聲音自覺的意識(shí),大致只停留在對(duì)于句式整齊、韻腳節(jié)奏方面。對(duì)于漢語漢字平、上、去、入四聲的認(rèn)識(shí),是齊梁人的新發(fā)現(xiàn);而將之推廣至詩歌文章,更是文學(xué)史上的一大創(chuàng)新。”?可以想見,隨著聲律規(guī)則被越來越廣泛地運(yùn)用到詩歌創(chuàng)作中,押韻技巧的變化也勢(shì)必呼喚新的經(jīng)驗(yàn)總結(jié)與理論歸納,而聲韻詩學(xué)由魏晉時(shí)期的開始自覺走向南北朝時(shí)期的初步集成,正是這一潮流向前涌進(jìn)的必然結(jié)果。在這一潮流中,魏晉南北朝文人群體身處其中,既引導(dǎo)之又推動(dòng)之,最終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xiàn)。
注釋:
①②③④??????????????????????? [梁]劉勰撰、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58 年版,第554、554、554、555、552、552、552-553、553、553、559、553、559、559、553、561、553-554、561、561、66、68、134、158-159、241、394、571、655、701 頁。
⑤⑥ 徐復(fù)觀:《陸機(jī)〈文賦〉疏釋》,《中國文學(xué)精神》,上海書店2004 年版,第227、227 頁。
⑦ [梁]沈約:《宋書》,中華書局1974 年版,第1830 頁。
⑧ [唐] 姚思廉: 《梁書》,中華書局1973 年版,第243 頁。
⑨⑩? [梁]蕭子顯:《南齊書》,中華書局1972年版,第898、900、898 頁。
? 陳寅恪:《金明館叢稿初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第 329 頁。
? [北齊]魏收:《魏書》 (點(diǎn)校本二十四史修訂本),中華書局2018 年版,第1649 頁。
??? [日]遍照金剛撰、盧盛江校考:《文鏡秘府論匯校匯考》,中華書局2006 年版,第285、285、285頁。
?? [梁]鐘嶸撰、曹旭集注:《詩品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版,第438—452、452 頁。
? 杜曉勤:《六朝聲律與唐詩體格》,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7 年版,第103 頁。
? 吳光興:《八世紀(jì)詩風(fēng):探索唐詩史上“沈宋的世紀(jì)” (705—805)》,社會(huì)科學(xué)文獻(xiàn)出版社2013 年版,第582 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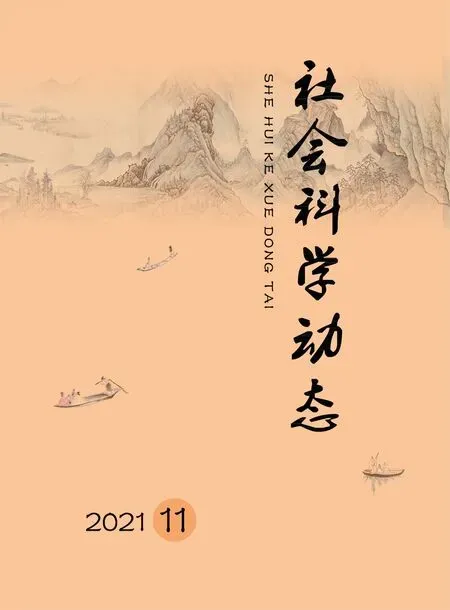 社會(huì)科學(xué)動(dòng)態(tài)2021年11期
社會(huì)科學(xué)動(dòng)態(tài)2021年11期
- 社會(huì)科學(xué)動(dòng)態(tài)的其它文章
- 行政訴訟自認(rèn)規(guī)則之理論、立法與實(shí)踐
——基于107 份裁判文書的統(tǒng)計(jì)分析 - 國家治理視域下社會(huì)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的影響因素
- 《宋代石刻功能的多元透視與文學(xué)個(gè)案分析》的學(xué)術(shù)特色與價(jià)值
- 唐宋變革視域下的文人身份認(rèn)同與群體書寫
——評(píng)田安的《知我者:中唐時(shí)期的友誼與文學(xué)》 - 《從“天下”到民族國家:歷史中國的認(rèn)知與實(shí)踐》評(píng)析
- 系統(tǒng)全面論述長(zhǎng)江經(jīng)濟(jì)帶演化進(jìn)程的寫實(shí)佳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