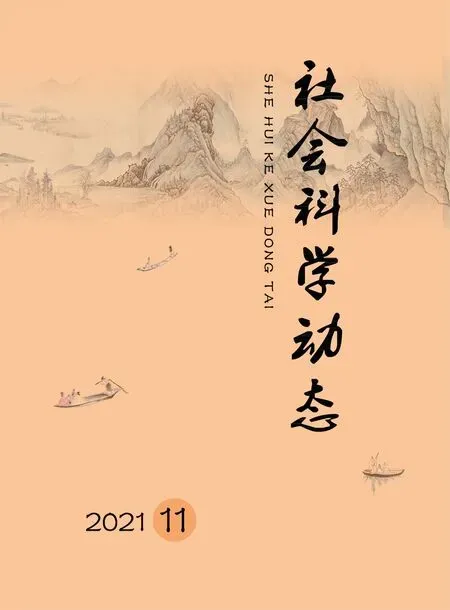人工智能的哲學研究:文獻檢視與理論前瞻
魯 靜
自從20 世紀50 年代以來,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就成了人們日常生活中的一個新事物。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人工智能逐漸嵌入到人們生產、生活當中并開創了一種新的文明形式——信息文明。在信息高速公路上,我們必須擺正人工智能的位置,惟此才能匯聚社會發展的合力。基于此,學界對人工智能這一新“景觀”展開了哲學反思,為我們處理好人與人工智能的關系提供了可資借鑒的方案。
一、人工智能的哲學研究概述
自改革開放以來,國內學界便開始了有關人工智能的譯介與研究。1978 年, 《國外社會科學》《哲學譯叢》 (后更名為《世界哲學》) 和《哲學研究》先后刊發了有關“機器思維”和“人工智能”的文章,開了國內學界關于人工智能哲學研究的先河。隨著信息技術的進步,信息、網絡、人工智能在人們生活中出現的頻次逐漸增多,覆蓋面也逐漸增大,影響程度也逐漸加深。由此,學界對于人工智能的關注和研究也逐漸增加,人工智能也成了一個新的學術生長點和學術熱點。
在四十多年的時間里,學者們對于人工智能的哲學反思可以從以下六個方面加以總結:就發文數量來看,學者們圍繞人工智能的哲學研究呈現逐年上升的態勢;就研究主題來說,學者們圍繞“人工智能技術”“人工智能時代”“大數據”“物聯網”“云計算”“機器人”“人工智能應用”“人工智能時代”和“深度學習”等主題展開了詳實的探討和分析;就理論陣地來看,《自然辯證法研究》《自然辯證法通訊》 《科學技術哲學研究》 《哲學研究》 《馬克思主義與現實》 《世界哲學》 《哲學動態》 和《上海交通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 《上海師范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新疆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大連理工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西北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等期刊持續支持著人工智能的哲學研究,它們積極為學者提供了發聲的平臺;就研究機構來看,中國社會科學院、華東師范大學、中國人民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師范大學、浙江大學、北京大學、復旦大學和上海大學匯聚了人工智能哲學研究的主要力量;就研究隊伍來說,國內人工智能的哲學研究形成了一個“老—中—青”銜接有序的研究陣型,既有學術前輩的指導,又有實力派學者的參與,還有青年一代的積極努力;就研究范式來說,國內人工智能的哲學研究雖然側重理論研究——集中主要力量闡述人工智能的本質、規律、特點等理論問題,但也從未忽視過應用研究,形成了理論研究和實踐應用相結合的研究范式。
二、人工智能的哲學研究:四大基本問題
圍繞人工智能的哲學思考,學界刊發了一系列涉獵廣泛、研究精深和視野開闊的研究成果。這些研究成果主要圍繞著人工智能的本體論、認識論、倫理學等方面展開。
(一) 本體之維:何謂人工智能的理論回應
雖然按照傳統的本體論的界定與思路,“技術不可能成為本體”,但技術哲學要成為“真正的哲學”,就必須要“搞出一個技術本體論或技術存在論來”。①探討人工智能的本體之維,實則是要從理論上回應何謂人工智能的問題,也即要對人工智能的內涵界定、本質屬性和特點進行全面反思和科學展示。
對于人工智能的界定問題,雖然學界尚存爭議,但基本上都承認如下事實:一是人工智能是與計算機科學技術相伴相生的;二是人工智能的主要工作是模仿(模擬) 人的智能。由此,人工智能就是一項技術——“人工智能技術”。②作為計算機科學的一個分支,“計算”可謂是人工智能的本質。不同于常規的“算術運算”,人工智能的“計算”更為復雜,它“通常用計算機的指令序列來描述,在工程實現上表現為可被計算機硬件CPU 執行的程序”。③由此反觀人工智能,“人工”是一個前置性概念,人工是基于“技術規律”和“人工智能科學原理”而存在的。作為一種“人工技術物”的人工智能,它是一個技術性和人工性的復合體。其中,“技術性”所體現的是“改變事物的方法和路徑”,“人工性”則是這種具體方法“實現的結果”。④截至目前,人工智能的應用還屬于弱人工智能(Weak AI),它們采用了與人腦完全不同的運作機制,以實現對人腦的部分模仿。這樣的人工智能只是看起來像智能,它們具有較強的“人工操作性、功能限制性”等特點。究其性質而言,它們依舊是一種“人類的工具”⑤而已。更進一步地講,人工智能是通過對“人的智能”的“高仿”而形成的一種“數據編程”,它以網絡空間的數據和信息為“原材料”,以計算為“運行方式”,以“仿真模擬”為特征,以智能系統為“立足根基”的存在物。人工智能作為這樣一種特殊的存在,它是“一種以‘數據為本’和‘系統為王’的‘擬人化的操作程式’和‘技術人工物’”。⑥
通過對人工智能發展歷程的反思與總結,有學者劃分了人工智能的發展階段,即“邏輯推理”(1956 年至 20 世紀90 年代)、“概率推理” (20 世紀90 年代至2000 年) 和“因果推理”(2000 年至今) 三大階段。⑦與之對應,有學者進一步解釋了人工智能的發展歷程,即“形式化階段”——機器在形式上展開對人類思維的模擬、“經驗化階段”——機器開啟了對人類經驗的模仿、“理性化階段”——機器對人類理性的仿真。⑧也有學者從當前人們對于人工智能發展狀況的態度而理性分析了從“專用人工智能”到“通用人工智能”的可能性、問題與前景。⑨這些研究為我們了解人工智能的未來趨向提供了指引,人工智能有從弱(弱人工智能) 變強(強人工智能),并逐漸邁向“超級人工智能”的可能性和現實性。
(二) 認識問題:人工智能與人的關聯性
早在1978 年,就有學者提出人工智能所涉及的不僅是一個單純的“科學問題”,還是一個復雜的“哲學問題”。其原因在于,人工智能在認識論中處于特殊地位,“它把主體的認識能力轉化為認識客體,然后對之進行認識和模擬”。⑩人工智能的認識論問題,最為關切的是它與人的關系 (人機關系) 問題,由此延伸出機器意識等相關問題。
人工智能是一種技術人工物,它是人類技術的結晶。在此視角之下,人工智能與人的主客體關系是十分明確的。然而,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人工智能的能力得到了極大提高,智能機器對于人腦的認識活動與情感活動的模仿達到了“相當精細化的程度”。?在此境況之下,人機關系也就成為了一個必須加以探討的重大哲學問題。有學者認為在大數據時代里,人和技術呈現為一種全新的“體現關系”——“融為一體”的人機關系。具體來說,“在人的目的性的引導之下,人機結合越來越緊密而精致,至大數據時代甚至達到人機合一的狀態”。?正是人工智能具備了類似于人的認知功能,人工智能與認識主體的“屬人性”的問題就被廣泛討論并開始顛覆了認識論的傳統。雖然目前的人工智能還不具備認識主體的能力,但人機之間的認識論分工問題卻是擺在我們面前并亟待回應的話題。人機之間的認識論分工不同于傳統意義上的分工,它需要以“價值可能性”統攝“技術可能性”,以“人是目的”為價值視域,繼而對人工智能機器的發展方向與限度有一個全面認知。人則在這種分工中占據主體地位,人、機器和信息技術則各就其位。?有學者通過對機器介入科學認識過程的研討而回應了機器認識論何以可能的問題,即建構一種以機器“經驗”為基礎的認識論。以“機器為主體的非人類中心認識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人機對立,正視機器在認識論中的價值。?也有學者闡釋了人工智能與關系存在論的關聯。作為一種關系存在論的人工智能,其基本意涵就在于突出信息的人工智能。由此,人工智能的“物能性質”就淡化了,其“關系性質”得以強化。?
隨著機器人的不斷進化,“有意識的機器人”一時成為討論的熱點。學界集中探討了人工智能能否具有意識,或者有意識的人工智能何以可能的問題。鑒于學界關于人工智能和自我意識關系的論爭,有學者指出爭論的核心并不在于“人工智能是否具有自我意識”,而是“如何區分人工智能與自我意識的問題”。?也有學者從意識現象學的角度梳理了“意識”與“自身覺知”的關系,并認為通過對這一關系的探究能為建構一種“自身覺知的人工智能”提供理論準備。?總體而言,對機器意識能否產生的問題有持保守意見的,也有持樂觀意見的。前者認為人工智能在人類情感、意志層面的模擬是很難實現“根本的突破”?,后者則認為機器具有“意向性的心理能力”在理論上是可行的。?也有學者富有前瞻性地表達了擔憂,人工智能的“危險之處”就在于“自我意識”,人工智能一旦擁有自我反思能力、擬人化的情感、欲望和價值觀,就會使人陷入險境。?
(三) 倫理向度:人工智能關涉的倫理問題
面對人工智能的倫理沖擊與社會風險,學者們分別闡述了人工智能的倫理角色、倫理挑戰、倫理(道德) 評價和倫理建構等問題。就倫理角色來說,人工智能作為一種特殊的存在——在人機交互中通過自動認知、決策和行為執行相關任務,繼而彰顯出某種“主體性”并成為一種介于“人類主體”與“一般事物”之間的實體。人工智能也就具有了一種特殊的“擬主體性”。由此,具有擬主體性的人工智能也將承擔一種“不同于其他技術人工物的特有的擬倫理角色”。?借助莫爾按照價值與倫理影響力對機器人的分類,可以將人工智能的這種“擬倫理角色”劃分為“倫理影響者”“倫理行動者”“倫理能動者(施動者)”和“倫理完滿者”四類。?就倫理挑戰來看,人工智能對于人類社會的沖擊不僅主要表現為對“什么是人”和人的本質的深層挑戰、對傳統的倫理關系和道德規范的挑戰、數字鴻溝和社會排斥等造成的社會難題、超級人工智能誕生之后對人的操控和反噬等?,還會引發一系列的道德決策風險、環境倫理、醫療倫理、家庭倫理和教育倫理等問題。?就倫理(道德) 評價而言,人工智能的道德判定需要對“AI 本身的道德評價問題”和“AI 研發與應用后果的善惡評價問題”進行區分?,這期間就不僅涉及到人工智能的倫理及其評價問題,還關系到人工智能這一技術背后的“人的問題”。就倫理建構來說,這是學界探討人工智能的倫理問題的落腳點,也是研討的重點內容。有學者在分析兩大人工智能的倫理原則——“人本主義原則”(強調自由、安全、公正等) 和“技術主義原則”(強調可信、可靠、可治理、可持續等)的基礎上,結合現實提出了AI 倫理原則是一個極大的“綜合性難題”,我們必須借助“透明性”和“關聯性”這兩大原則方能架構有支撐的、穩定的人工智能倫理。?有學者不僅確認了“人機系統的責任分配原則”——以人為本和共生共存、人類作為責任主體承擔全部后果和分級分類制訂擔責,還闡述了“人機系統的責任承擔方案”,即對于人工智能的輸入、輸出均可控制的人機系統,事故責任主要“依賴傳統的技術補救和法律追責”;對于輸入不可控、輸出可控制的人機系統,事故責任應“依賴政府和企業的安全監控”;對于輸入可控、輸出不可控制的人機系統,事故責任可通過“技術的價值敏感設計和風險轉移機制來規避風險”;對人工智能的輸入、輸出均不可控制的人機系統,則要依靠“國家之間締結盟約來共同應對全球威脅”。?當然,不同的學者結合自身的學科背景和學術興趣分別展開了對人工智能的算法倫理?、政治倫理?和智能駕駛倫理?等問題的分析與討論。
(四) 社會效應:人工智能與社會歷史變革
對于人工智能的社會效應問題,學者們進行了辯證分析——既分析了人工智能的積極效應,又剖析了它的消極影響。就人工智能的積極效應來說,方便、快捷是人工智能給人帶來的直觀感受,與之伴隨的是人們交流的暢通、迅捷和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人工智能既有助于物質財富的創造,也有益于精神世界的豐富。有鑒于此,有學者分析了人工智能的三大積極效應:“社會的智能化程度”已成為社會發展水平的重要標志,它為人的自由發展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生產方式趨向人性化”可以幫助人們理性地作出最優選擇和進行正確的評判;“增加人的自由時間”有助于人的全面發展。?有學者從歷史觀的維度闡述了人工智能(包括智能制造)、生產的無人化將有助于勞動解放、社會解放。同時,人工智能并不會直接或必然導致對人的奴役,亦不會引發大量的失業問題。?當然,任何事物都有其反面,人工智能也有消極影響。人工智能會拉大“數字鴻溝”,造成新的不平等和拉大貧富差距。也就是說,人工智能的“商用”(資本主義應用) 不僅會造成“贏家通吃的新型超級壟斷”,還會將“它的用戶甚至民族國家牢牢地‘鎖定’在某種‘技術軌道’上”。?不僅如此,人工智能的錯用還會造成人們異化的處境,人工智能受到資本邏輯的宰制而會異化為一種特殊的權力,從而催生技術理性的泛濫。在人工智能的應用中,人們之間的交往也異化了,不僅人的“自我認知”會發生裂變——“生理我”和“心理我”之間的兩歧,還會導致人逐漸脫離掉其社會本質屬性。?有學者將這種異化更加具體地敘述為人工智能致使人們“深陷被智能造物支配與控制的危機中”,人的主體性在智能機器的侵占中不斷被削弱,主體間的關系日漸“疏離化、數字化和物化”,機器不斷侵蝕著人的尊嚴、自由和價值。?
對于人工智能的歷史趨向,樂觀者有之,悲觀者有之,中立者也有之。當然,學界總體上還是對人工智能持有樂觀態度的。有學者從兩個層面論述了人工智能是可以助力我們到達“自由王國”的,即從物質財富的創造和積累層面認為人工智能“大有可為”,從精神境界的鍛造和提升層面認為人工智能“潛力無限”。?也有學者認為不能將人工智能視作一種“技術的應用”,21 世紀馬克思主義的任務就是要打破資本主義對人工智能技術的壟斷與占有,使其為社會主義提供“可靠的基礎”。?也有論者從人類與技術“反身互動”的角度出發,繪制了三種不同的“后人類社會圖景”——“工業4.0 社會、賽博格社會和技術奇點社會”。?總之,我們應在唯物史觀視域之下來審視人工智能,要積極探尋將人工智能從“技術—金融壟斷資本主義”中解放出來,并竭力建構由無產階級主導的“數字社會主義”繼而擺脫技術異化。
三、人工智能的哲學研究:存在問題與展望
誠如前文所言,學界圍繞人工智能問題的哲學思考與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呈現出了發文量激增、研究主題廣泛、理論陣地強大、研究機構眾多、研究隊伍齊整和研究范式科學的大好局面。當然,當前的研究也暴露出一些問題,主要表現為:
一是研究成果宏觀有余而微觀不足。縱觀現有的研究成果,學者們集中探討了人工智能的本體論、方法論、價值論和認識論等哲學問題,這些成果有助于帶領我們走近、走進人工智能的哲學世界。可以說,對于人工智能的宏觀哲學思考是研究過程中必要的“初級階段”。對于人工智能中的一些微觀問題,如人工智能的認知建模、機器思維、自然語言理解和莫拉維克悖論等的精細化討論和思考是人工智能研究進入“高級階段”的重要內容。如何將人工智能的哲學研究帶入微觀化、精細化的范式中,這也是今后的重要任務。
二是研究視域開闊但學科融合不夠。大體來說,學界關于人工智能的哲學研究除了涉及科學技術哲學這一學科外,馬克思主義哲學、外國哲學、中國哲學、倫理學、邏輯學和美學等學科的學者也都展開了積極探討。具體而論,學者們多從現象學、心靈哲學、政治哲學、技術哲學、馬克思主義哲學和倫理學等層面入手為人工智能的哲學問題尋找理論依據和化解問題的策略。如此,學界關于人工智能的哲學研究形成了較為完備的研究體系。但是人工智能作為一個復雜事物,需要多學科之間的交叉、融合研究。
三是研究成果豐碩但原創成果不多。就已有研究成果來看,文獻數量頗多,對于相關問題的展示與討論也較為深入。但在眾多的研究成果中,不僅呈現出理論研究與現實應用脫鉤的現象,還存在原創性成果不足的尷尬情形。我們雖然占領了人工智能研究的諸多領地,但是并未登上研究的高峰。目前的前沿成果多是譯介國外的新進展,國內原創性的成果較為缺乏。
當然,對于人工智能的哲學研究,我們也應該堅持以下基本原則:一方面是以人為中心的原則,即在人工智能的研究與應用中應該始終尊重人、為了人。另一方面則是要以增進人類福祉為重要任務,即人工智能的研究和應用應該造福人,而不是造成人的異化。
注釋:
① 吳國盛:《技術哲學講演錄》,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 年版,第165 頁。
② 宋振杰:《政治哲學視角下的人工智能本質與功能思考》,《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20 年第12 期。
③ 陳鐘:《從人工智能本質看未來的發展》,《探索與爭鳴》2017 年第10 期。
④ 王治東:《人工智能研究路徑的四重哲學維度》,《南京社會科學》2019 年第9 期。
⑤ 沈文瑋:《論當代人工智能的技術特點及其對勞動者的影響》,《當代經濟研究》2018 年第4 期。
⑥? 付文軍:《人工智能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內蒙古社會科學(漢文版)》2019 年第6 期。
⑦ 梅劍華:《理解與理論:人工智能基礎問題的悲觀與樂觀》,《自然辯證法通訊》2018 年第4 期。
⑧程廣云:《從人機關系到跨人際主體間關系——人工智能的定義和策略》,《自然辯證法通訊》2019 年第1 期。
⑨ 徐英瑾:《人工智能技術的未來通途芻議》,《新疆師范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9 年第1 期。
⑩ 陳步:《人工智能問題的哲學探討》, 《哲學研究》 1978 年第 11 期。
?? 尚智叢、閆奎銘:《“人與機器”的哲學認識及面向大數據技術的思考》,《自然辯證法研究》2016 年第2 期。
? 肖峰:《人工智能與認識主體新問題》,《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20 年第4 期。
? 董春雨、薛永紅: 《機器認識論何以可能?》,《自然辯證法研究》2019 年第8 期。
? 王天恩:《人工智能和關系存在論》, 《江漢論壇》 2020 年第 9 期。
? 江怡: 《對人工智能與自我意識區別的概念分析》,《自然辯證法通訊》2019 年第10 期。
? 倪梁康:《意識作為哲學的問題和科學的課題》,《自然辯證法通訊》2019 年第10 期。
? 李國山:《人工智能與人類智能:兩套概念,兩種語言游戲》,《上海師范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 年第 4 期。
? 周昌樂:《機器意識能走多遠:未來的人工智能哲學》,《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16 年第13 期。
? 趙汀陽: 《人工智能的自我意識何以可能?》,《自然辯證法通訊》2019 年第1 期。
?? 段偉文:《人工智能時代的價值審度與倫理調適》,《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7 年第6 期。
?? 孫偉平:《關于人工智能的價值反思》,《哲學研究》2017 年第10 期。
? 王軍: 《人工智能的倫理問題:挑戰與應對》,《倫理學研究》2018 年第4 期。
? 王銀春:《人工智能的道德判斷及其倫理建議》,《南京師范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 2018 年第4 期。
? 楊慶峰: 《從人工智能難題反思AI 倫理原則》,《哲學分析》2020 年第2 期。
? 宋春艷、李倫: 《人工智能的自主性與責任承擔》,《自然辯證法通訊》2019 年第11 期。
? 孫保學:《人工智能算法倫理及其風險》,《哲學動態》2019 年第10 期。
? 張愛軍、秦小琪:《人工智能與政治倫理》,《自然辯證法研究》2018 年第4 期。
? 孫偉平: 《人工智能導致的倫理沖突與倫理規制》,《教學與研究》2018 年第8 期。
? 林劍:《論人工智能的發展對人的勞動解放與社會解放的意義》,《人文雜志》2019 年第11 期。
? 安維復:《人工智能的社會后果及其思想治理》,《思想理論教育》2017 年第11 期。
? 程宏燕、郭夏青:《人工智能所致的交往異化探究》,《自然辯證法研究》2020 年第9 期。
? 閆坤如、曹彥娜:《人工智能時代主體性異化及其消解路徑》, 《華南理工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2020 年第 4 期。
? 藍江: 《人工智能與未來社會主義的可能性》,《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19 年第6 期。
? 李恒威、王昊晟: 《后人類社會圖景與人工智能》,《華東師范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 2020 年第 5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