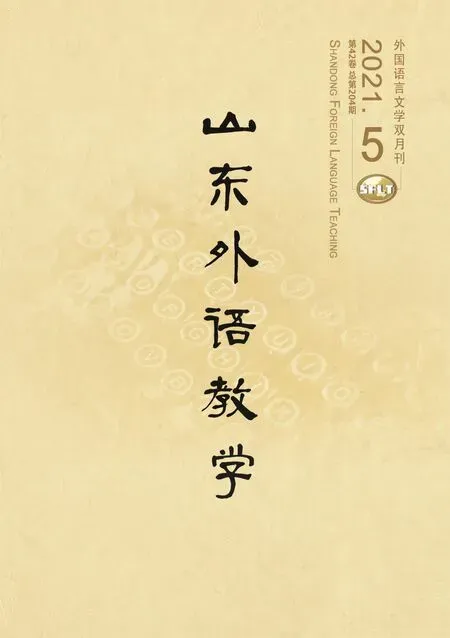《人間詞話》“境界”理論的英譯對比研究
——以涂經詒譯本與李又安譯本為例
榮立宇 王洪濤
(1. 天津師范大學 外國語學院, 天津 300387;2. 北京外國語大學 英語學院, 北京 100089)
1.0 引言
王國維的《人間詞話》(以下簡稱為《詞話》)堪稱中國文論史上的經典之作,問世以來,一直備受學界推崇,時至今日仍然閃爍著奪目的光輝,為人津津樂道。傅雷視之為中國有史以來“最好的文學批評”,葉嘉瑩稱之為銜接古今、匯通中外的“一座重要橋梁”(王國維,2009:封底)。黃維樑對《詞話》評價更是達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王觀堂的《詞話》魅力最大,傾倒者眾,仿佛成了今日的詩學權威;傳統的經典之作如《詩品》和《滄浪詩話》都紛告失勢”(黃維樑,2013:81)。截至目前,《詞話》在英語世界已經有兩種全譯本問世:其一為中國臺灣學者涂經詒所譯的PoeticRemarkInTheHumanWorld:JenChienTz’uHua(1970),內中收錄詞話64則;其二是美國學人李又安(Adele Rickett)所譯的WangKuo-wei’sJen-chienTz’u-hua:AStudyinChineseCriticism(1977),前后包含評語141則。
《詞話》問世以來,王國維的文論思想,尤其是其“境界”理論,一直都是文藝學界探討研究的熱點。朱光潛、馮友蘭、饒宗頤、顧隨、周振甫、周錫山、周煦良、徐復觀等都有所論述辨析(王國維,2013)。葉嘉瑩(1982)對“境界”“造境”“寫境”“有我之境”“無我之境”等概念做了詳盡的考察與辨析,在理解和辨別相關概念方面帶給我們許多新的靈感與啟發。與《詞話》很早就成為文藝學界研究對象的情況相較,翻譯學界對于其英譯情況的研究起步較晚,研究成果又以國內學者的著作為眾,其中包括對于《詞話》英譯本的評析(彭玉平,2012;榮立宇、劉斌斌,2013)、關于《詞話》英譯本中副文本部分的研究(榮立宇,2015;焦玉潔,2015)、關于《詞話》英譯歷史的簡要梳理(王曉農,2015a)、對于《詞話》中征引-評論關系的再現研究(王曉農,2015b)等。考察現有關于《詞話》翻譯研究的文獻,不難看出這些研究雖然已在翻譯學界引發了一定的關注,也為更加深入的研究奠定了初步的基礎,但是目前尚停留在譯評、綜述、比較的初級階段,基本上只是關注文本敘述層面的翻譯問題,尚未對《詞話》所蘊含文論思想的英譯予以關注和考察,故此本文將立足于《詞話》現有的比較完備的兩個英譯本,對比分析兩位譯者涂經詒和李又安對于其中“境界”說理論與相關核心術語的英譯,以期學界對于中國文論思想譯介過程中存在的重要問題引起足夠的重視。
2.0 “境界”說的基本義涵及其兩種英譯
“境界”說是《詞話》基本理論的概括。“境界”也隨之成為該理論的核心概念、核心術語。應該說,王國維對于此概念的提出頗為自得。此種得意不難從《詞話》第9則中的相關論述見出。“然滄浪所謂興趣,阮亭所謂神韻,猶不過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為探其本也”(王國維,2009:5)。很明顯,在王國維看來,其所提出的“境界”一說當為“興趣”說、“神韻”說之超越。
“境界”說問世以來,學界有關的探討可謂是聚訟不已,眾說紛紜。關于“境界”說的討論歸納起來,約略有幾種說法,其中影響較大的有二:一是將“境界”等同于“意境”,持此論者頗眾,以顧隨、黃維樑、李建中為代表,“‘境界’又或謂之‘意境’”(顧隨,2010:139)。“本文即把此二詞視為同義詞”(黃維樑,2013:86)。“‘境界’與‘意境’并無質的區別”(李建中,2002:334)。二是主張“境界”系指“作品中的世界”,代表人物為李長之、劉若愚。前者直接將“境界”解讀為“作品中的世界”(葉嘉瑩,2009:95),后者則徑直將“境界”翻譯為英語詞匯“world”(黃維樑,2013:82)。
對于將“境界”等同于“意境”的觀點,葉嘉瑩詳細考察了王國維在歷史上使用這兩個術語的具體情況,明確指出“‘境界’一詞之含義必有不盡同于‘意境’二字之處。”而對于將“境界”與“作品中的世界”相等同的看法,葉氏的觀點可謂是一語擊中要害。她指出“‘世界’一詞只能用來描述某一狀態或某一情境的存在,并不含有衡定及批評的意味,可是靜安先生所用的‘境界’二字則帶有衡定及批評的色彩。”“我們可以說‘詞以境界為最上’,卻難以說‘詞以作品中的世界為最上’”。“‘境界’一詞的含義,也必有不盡同于‘作品中的世界’之處”(葉嘉瑩,2009:94-95)。
事實上,葉氏的工作不僅在破除前人誤說,同時還包括在此基礎上創立新論。在她看來,“境界”在不同語境中使用時具有不同的義涵,這可以分為兩種情況:按照一般習慣用法來使用的情況(見第16,26,51則);作為批評基準之特殊術語來使用的情況。同時也指出,在后一種情況中“境界”一詞又常常因受到一般習慣用法的影響而獲致多重的含義(同上:101-102)。葉氏的此種區分可以說是發前人所未發,將“境界”理論的辨析進一步精細化,這無疑更加接近王國維詩論核心的真相。
以上是關于“境界”說理論的考察辨析,下面我們開始對“境界”說英譯問題的探討。考察《詞話》兩個英譯本,我們可以發現,正如涂經詒在《詞話》英譯本中所指出的,他對于“境界”(“境”)概念的認識來自劉若愚。在劉氏看來,“境界”與“境”沒有分別,指的是詩歌中“情”與“境”的融合,于是徑直以“world”一詞譯之。涂氏則蕭規曹隨,在自己的譯文中秉持了這種認識,并且一以貫之,通篇無二。正如涂氏在自己譯文中所指出的那樣,“劉若愚教授指出‘境界’即詩歌中情與景的融合。我遵從劉教授的做法將‘境界’譯作‘world’。……為了避免混淆起見,‘world’用作‘境界’或‘境’的譯文時,將之做斜體標示。”(王國維,1970:1;筆者譯)
涂氏的譯法折射出他對于“境界”概念的認知和理解——詩歌中情與景的交融而構成的世界。這種認識和理解固然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和價值,但一如葉嘉瑩(2009:95)所指出的,“world”“只能用來描述某一狀態或某一情境的存在,并不含有衡定及批評的意味。”
與之相較,李又安對于“境界”說有著十分不同的理解。她的研究著重于“境界”與“境”兩個概念的區分。她指出在別人那里“境界”與“境”固然有混用的情況,但是王國維對于這兩個術語的使用卻顯然不同。她給出的理由有二:其一,兩者之間具有明顯的形式區分,即“境界”之前常被置一“有”字(見第1,43,76,79,81,93,120則)(Rickett,1977:26-27)。只是這種說辭說服力十分有限,因為有很多地方“境界”之前并無“有”字(見第1,6,7,8,9,26,34,51,76,77則)。其二,兩者之間深意不同,“境”僅是一個靜態的感情或景物狀態,所以不可以說有“境”;而“境界”則指向作品、詩人、某一界域含有并且因之變得偉大的一種激蕩的、動態的人格狀態,因此可以說有“境界”。后者并非只是一個尋常的狀態,而是一個自有其邊界的卓然獨立的狀態。此種狀態已經非是“境”之一字可以充分刻畫者,而為了描述每種不同的卓然獨立之狀態,需要在“境”字之后加一個“界”字。(同上)
李又安對于“境界”中“界”字的強調在某種程度上與顧隨的主張頗為暗合。后者認為“境界者,邊境、界限也,過則非是”(顧隨,2010:239)。無疑,這一觀點頗具說服力。或許我們還可以更加咬文嚼字一些,倘若從“界”字著眼,似乎也可以說“境”是無“界”之“境界”,而“境界”則為有“界”之“境”。事實上,這種認識可以得到《詞話》文本內部的有力支撐。“境界有大小,而不以是而分優劣”(王國維,2009:4)。顯然,無“界”的“境”不能區分大小,有“界”的“境界”方有大小可言。
可以看出,在李又安眼中,“境界”與“境”之間有著本質的區分,在翻譯過程中需要進行截然不同的處理。 于是在其《詞話》英譯本中“境界”通篇采用音譯“ching-chieh”,而每當“境”字單獨出現時則始終譯作“state”或“poetic state”。如《詞話》第6則,“境非獨謂景物也,喜怒哀樂亦人心中之一境界”(王國維,2009:3)。李又安譯作“The [poetic] state is not limited to scenery and objects alone. Pleasure and anger, sorrow and joy are also a sort ofching-chiehin men’s hearts. ”(Rickett,1977:42),而涂經詒則譯作“Theworlddoes not refer to scenes and objects only; joy, anger, sadness, and happiness also form aworldin the human heart.”(王國維,1970:4)。
實事求是地說,李又安對于“境界”與“境”的區分與翻譯的確具有一定的道理和價值,只是這種區分在某些評詞語境中顯得過于生硬,未免不通情達理,何況王國維在使用這兩個概念的時候也確有混用的情況。如第6則,“境非獨謂景物也,喜怒哀樂亦人心中之一境界”(王國維,2009:3);第26則,“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之境界:……此第一境也。……此第二境也。……此第三境也”(王國維,2009:16)。
順便一提的是,涂、李兩家也都持有“境界”有異于“意境”的看法,這體現在各自的譯文中。具體來說,涂經詒將“境界”譯作“world”(王國維,1970:1)而將“意境”譯作“profound meanings”(同上:29);李又安則將兩個語詞分別譯作“ching-chieh”(Rickett,1977:40),“meaning and poetic state(yi-ching 意境)”(同上:58)便是明證。
3.0 “境界”理論相關核心術語的英譯對比分析
“境界”說是王國維詩學理論的綱領,此概念自然是《詞話》中不斷出現的高頻語匯(見第二小節所列條目)。事實上,除“境界”而外,王國維還在《詞話》具體的詩詞批評實踐中使用了一些“境界”的衍生概念和相關概念,這些概念堪稱“境界”說的核心術語,既成為理解和認識《詞話》的金鑰匙,也構成《詞話》翻譯的重點和難點。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造境”與“寫境”、“有我之境”與“無我之境”、“隔”與“不隔”等幾組概念。這里我們試圖對這些核心術語進行辨析并對涂經詒和李又安各自英譯的合理性與存在的問題進行對比與考察。
3.1 “造境”與“寫境”
張金梅等(2016:352)認為,“造境”與“寫境”是王國維提出的第一組境界范疇,涉及作者身份、創作方式與創作流派三層內涵。李建中(2002:334)進一步指出“造境”與“寫境”是王國維受到“西方文論的‘現實主義’、‘浪漫主義’理論的影響”所進行的劃分,屬于“境界”的進一步分類。
關于“造境”與“寫境”,學界存在許多探討,很多不同的聲音。吳宏一將此一對術語與“有我之境”與“無我之境”關聯起來;蕭遙天則將它們與“主觀”“客觀”混為一談。葉嘉瑩對上述認識持否定性意見,她指出“造境”與“寫境”乃是“就作者寫作時所采用的材料而言的。”本身與“有我”“無我”“主觀”“客觀”之間“并無必然之關系”(葉嘉瑩,2009:114-115)。
在《詞話》英譯本中,涂經詒將前后兩處出現的“造境”與“寫境”依次譯作“create worlds, describe worlds”“the worlds created, the worlds described”(王國維,1970:1)。前一組譯法將源文中概念的偏正結構理解并且翻譯為動賓結構,后一組譯法則明顯是由前一組譯法轉換生成而來,據此似乎可以說,涂經詒并未按照《詞話》重要術語來解讀這一組概念。
與之相較,李又安則采用了“直譯+音譯”的翻譯模式,譯為“creative state (tsao-ching)”, “descriptive state (hsieh-ching)”(Rickett,1977:40)。直譯中保留了源生術語的偏正結構,可以看出李氏是將之作為一種批評術語來解讀和翻譯的。需要指出的是,李氏翻譯“造”與“寫”所使用的“creative”與“descriptive”兩個詞與涂氏所使用的“created”“described”為同根詞,則說明了兩位譯者對于源文使用字眼理解的暗合之處。
然而,使用英文字眼的暗合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另一個不容忽視的方面在于“造境”“寫境”與“境界”彼此之間的關系問題。李建中(2002)、葉嘉瑩(2009)、張金梅等(2016)將“寫境”與“境界”作為“境界”說的二級概念進行探討,以此彰顯出“境界”說中概念的層級關系,當屬近乎王國維“境界”說之本意的觀點。由是觀之,涂氏譯文并非按照這種層級關系進行翻譯的結果,而李氏譯文則再現出一種上下的層級關系,更加貼合王氏理論的真諦。
另外,鑒于《詞話》第2則的表述——“有造境,有寫境,此理想與寫實二派之所由分”(王國維,2009:1)。這里有必要順便提及另外一組語匯“理想”與“寫實”的翻譯問題。葉嘉瑩(2009:116)對于王氏所使用的“理想”與“寫實”兩個語匯進行了深入的辨析,指出這“實在不過只是假借西方學說理論中的這兩個詞語來作為他自己立說的代用品而已。”涂經詒將此組術語譯作“idealism”“realism”(王國維,1970:1),李又安(1977:40)譯作“idealists”“realists”,雖然語匯有異,但是詞源相同,譯法可謂異曲同工。
3.2 “有我之境”與“無我之境”
“有我之境”與“無我之境”自問世起便備受關注。在探討“有我之境”“無我之境”兩個概念時,王國維援引了一些詩詞。如第三則,“有有我之境,有無我之境。‘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千秋去’,‘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里斜陽暮’,有我之境也。‘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鳥悠悠下’,無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觀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無我之境,以物觀物,故不知何者為我,何者為物。古人為詞,寫有我之境者為多,然未始不能寫無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樹立耳”(王國維,2009:2)。
張金梅等(2016:352-353)認為,“有我之境”與“無我之境”之說“融入了王國維獨特的思考,頗具理論價值。”按照她的解讀,“有我之境”在于讓物“人化”,而“無我之境”則為人之“物化”。
朱光潛(2008)從“移情作用”的美學理論出發,指出王國維的“有我之境”與“無我之境”實為移情作用之下的“無我之境”和“有我之境”,同時進一步提出可以“同物之境”與“超物之境”的概念來加以替換。蕭遙天在《語文小論》中以“主觀”與“客觀”來解釋“有我”與“無我”(葉嘉瑩,2009:106)。
葉嘉瑩(2009:105-107)指出《詞話》中“有我”與“無我”既不同于朱光潛所說的“同物”與“超物”,也異樣于蕭遙天所言的“主觀”與“客觀”。葉氏在追根溯源與考察分辨之際①,進一步指出所謂“有我”當指存有“我”之意志,與外物之間存在“某種對立之利害關系”,所謂“無我”當指泯滅了“我”之意志,與外物之間不存在“利害關系相對立。”
考察涂、李兩家的譯文,涂氏將“有我之境”與“無我之境”譯作“a world with a self”“a world without a self”(王國維,1970:2);李氏則將之譯為“personal state(yu-wo chih-ching)”“impersonal state (wu-wo chih-ching)”(Rickett,1977:40)。根據《朗文當代高級英語辭典》的解說,“self”意為“the whole being of a person, taking into account their nature, character, abilities etc.”(1998:1372)。“personal”意為“concerning, belonging to, or for the use of a particular person; private;”(同上:1116)很明顯,涂氏對于“有我”“無我”的處理強調的是“一己”(self)之有無;而李氏對于“有我”“無我”的理解突出的是“個人”(person)之關礙。
應該說涂經詒、李又安兩種譯法與源文術語在語言文字層面均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可謂約略似之;然而在源文術語所指的義界方面卻都未能體現出這一組概念區分的要害之所在——即是否存在個人與外物之間對立的利害關系。
在概念英譯的問題辨析之外,對于與“有我”與“無我”相關的批評實踐之英譯來說,這里還有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王國維為說明“有我”與“無我”之區分而援引的詩詞片段其翻譯能否契合上文中對于“有我之境”與“無我之境”的說明?如“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秋千去”句,李譯“With tear-filled eyesIask the flowers but they do not speak. /Red petals swirl past the swing away.”(Rickett,1977:40)。涂譯“The flowers do not respond tomytearful query, and the scattered petals fly over the swing. ”(王國維,1970:2)
再如“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里斜陽暮”句,李譯“How canIbear it, shut within this lonely inn against the spring cold? /Slanting through the cuckoos’s cries the sun’s rays at dusk.”(Rickett,1977:41)。涂譯“Unbearably, all aloneIlive in the inn locked in spring chill; the sun is setting amid the chirping of the cuckoo.”(王國維,1970:2)。
眾所周知,漢語詩歌一大特征是主語的缺省。“中國詩歌的最高境界是自我消失在自然之中以及‘物’‘我’兩者之間的區別蕩然無存”(轉引自邵毅平,2008:263)。可是原本主語缺席的漢語詩詞譯成英語在很多時候需要根據具體情況補充相應的主語。事實上,如前面所臚列的例子,《詞話》的兩個英譯本在此處也都是如此做的(見例中標示黑斜體的部分)。談及“有我之境”,如此處理不存在太多問題,可是到了翻譯“無我之境”涉及的詩詞時,恐怕就成了一個大問題。如“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句,李譯“Ipluck chrysanthemums by the eastern fence, /Far distant appear the southern mountains.”(Rickett,1977:41)。涂譯“Ipluck chrysanthemums under the east hedge; easily the south mountain comes in sight.”(王國維,1970:2)。
再如“寒波澹澹起,白鳥悠悠下”句,李譯“The cold waves rise smoothly, quietly/White birds glide softly down.”(Rickett,1977:41),而涂譯“Lightly, lightly arise the chilly waves; slowly, slowly descends the white bird.”(王國維,1970:2)
兩個譯本對于后面一句的翻譯固然無妨,而對于前面一句的翻譯則都存在“無我”之境中有“我(I)”的問題;這樣的“無我之境”還能譯作“a world without self”或“impersonal state”嗎?
而對于后面一句的翻譯,兩個譯本又都不存在類似的問題。后者與其說是譯者有意作為的結果,毋寧說是無意而為的巧合:皆因源詩中存在非“我”的主語“寒波”與“白鳥”。而前者的問題也可以解釋為源詩主語雖不在場,但通過挖掘找到的最理想結果舍“我”其誰。再一層,葉嘉瑩(2009)固然指出“無我”一詞的選用實為方便立論起見,“無我之境”也只是名為“無我”,但觀賞外物的主人又豈能離得開“我”?如是觀之,“a world without self”“impersonal state”之譯文又能否體現此種細微差異呢?
另外,鑒于《詞話》第4則的表述——“無我之境,人惟于靜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動之靜時得之。故一優美,一宏壯也”(王國維,2009:3)。這里還要順便提及另外一組語匯“優美”與“宏壯”的翻譯問題。黃維樑(2013:114)認為“優美”與“宏壯”顯然來自西方美學上的“graceful”“sublime”,可是王國維純從欲念和厲害關系方面來解讀這兩個詞,這種理解可以說是迥異于西方一般傳統的解讀。本著王氏獨特的解讀,“淚眼”“可堪”兩句稱得上“sublime”,而本著西方的概念來看,這兩句實在與“sublime”無關。翻譯“優美”“宏壯”,涂經詒使用了“beautiful”“sublime”兩個詞(王國維,1970:3),李又安譯文兩處用詞相同,只是補充上了音譯,譯作“beautiful(yu-mei)”“sublime(hung-chuang)”(Rickett,1977:41)。不僅如此,李又安還就自己的用詞做了進一步的說明,指出“從西方傳統長大的,很難看到‘淚眼’和‘可堪’等情景,有何sublime”(黃維樑,2013:115)。
3.3 “隔”與“不隔”
“隔”與“不隔”是《詞話》中另外一組十分重要的概念范疇。它們與“境界”說密切相關,在王國維的理論體系中,“不隔”是有“境界”的必然要求。但至于其所指究竟為何,則一如前面的其他幾組重要概念術語,王國維并沒有給出界定,而只是一如既往地進行舉例說明。如第39則,“‘二十四橋仍在,波心蕩、冷月無聲’,‘數峰清苦,商略黃昏雨’,‘高樹晚蟬,說西風消息’,雖格韻高絕,然如霧里看花,終隔一層。”(王國維,2009:25);第40則,“‘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等二句,妙處唯在不隔。”(同上:26)
后人對于此組概念也有著諸多的探討。朱光潛認為此種論說堪稱王氏之原創,道破前人所未言說(張金梅等,2016:353)。只是對于王國維用“語語如在目前”與“如霧里看花”解釋“隔”與“不隔”的說辭持有否定意見,認為其有欠妥當(彭玉平,2009)。
涂經詒將“隔”與“不隔”譯作“veiled”“not veiled”(王國維,1970:26),這種解說性的文字似乎說明涂氏并未將此組概念作為《詞話》中的重要評詞術語來理解和翻譯。李又安(1977:56)關于“隔”與“不隔”的譯法頗為多樣,第39則“雖格韻高絕,然如霧里看花,終隔一層”中譯作“by a veil(ko 隔)”,“梅溪、夢窗諸家寫景之病,皆中一隔字”處譯作“ko 隔”。第40則“問:隔與不隔之別”處譯作“seen through a veil”“unobstructed by a veil”;第41則“寫情如此,方為不隔……寫景如此,方為不隔”處譯作“lack any obstructing veil”(李又安,1977:57-58),從中我們可以看到李氏對于此一組概念核心術語地位的警醒以及在不同行文之中的靈活變通。
此外需要充分考慮的問題還有此處援引詩詞片段的翻譯與“隔”與“不隔”的核心概念相契合的問題。應該說,用來說明“隔”的詩詞其翻譯結果應該是“隔”的。同樣道理,用來說明“不隔”的詩詞其翻譯的結果也應該是“不隔”的。然而鑒于漢英詩歌在語言、文化等方面存在著巨大的差異,不同譯者在才華、譯筆方面又顯現出天壤之別,“隔”的源文有可能譯成“不隔”的譯文,而“不隔”的源文也有可能會因為這樣那樣的因素而變成“隔”的譯文。
前者如“二十四橋仍在,波心蕩,冷月無聲”句,王國維以之為“隔”的模本。事實上,關于此句“隔”與“不隔”的問題存在許多不同的聲音。如傅庚生(2018:205)指出姜夔詞中暗用了杜牧詩作《遣懷》《寄揚州韓綽判官》,“借原詩之豪華氣象,為今日蕭條局面之反襯”,到了“幾乎奪小杜之詩作此詞之附庸”的地步。此為一目了然的“用事”,王氏評此句為“隔”的本意當在于此。而黃維樑對此則提出了迥異的意見,他認為“冷月無聲”四字,“觸、視、聽三覺交感,尤為出色。”“即使讀者不知道二十四橋所指為何,仍可以體會到這幾句所營造出來的意境。”當為“不隔”的典范(黃維樑,2013:130)。其實,傅、黃兩氏的主張未必不可調和。傅庚生之觀點源自通篇考慮,黃維樑之看法出自單句分析,各有各的道理。
考察涂、李兩家譯文:“The twenty-four bridges are still there, and the waves are agitating; silent is the chilly moon-night.”(王國維,1970:25),“The twenty-four bridges are still there/Deep in the rippling waves, the soundless moon is cold.”(Rickett,1977:55),可以看出,兩家譯文均將“二十四橋”處理為“the twenty-four bridges”。由于詩學傳統方面重要信息指向的阻隔,這種譯法自然不能再現作者擬通過今夕盛衰對比、映襯蒼涼悲愴情感的創作效果,“隔”的問題依舊明顯。“波心蕩,冷月無聲”處,涂氏分而譯之,前后兩個小句作簡單并列句處理,略顯平庸。李氏則將前后拉通,將波心、冷月的位置關系明確化,特別是由“冷月無聲”到“無聲月冷”(the soundless moon is cold.)的創造性改造更是讓人眼前一亮,加深了譯詩中所描繪場景的真切之感,可謂“語語都在目前”,當屬“不隔”的譯文。
后者如“池塘生春草”句,此句出自謝靈運《登池上樓》中“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句。王國維目之為“不隔”的典范,無非是因為其“不用典故,容易懂,寫出蓬勃春意”(周振甫語,見王國維,2013:178)。考察此句的兩個英譯版本——“In the pond grow the spring grass.”(王國維,1970:26);“Spring grasses come to life beside the pond.”(Rickett,1977:56)不難發現,“池塘”與“春草”在源詩中雖有所特指(謝靈運所登臨處之處),但是在中國詩歌的閱讀語境中已經去掉了特指的意味,慢慢滋生出泛指的義涵。但就兩個英譯本看,其中的定冠詞成為語言層面的必然要求,如是“the”的添加便打破了源文泛指的可能性,衍生出“如觀一幅佳山水,而即曰此某山某河,可乎?”(王國維,2009:35)的問題,也便有了一重“隔”的問題。
此外,還需要指出,源文中的“春草”貌似是單純寫景,其實不然,此意象在中國文化里經常與“思念”之情相關聯,這一傳統可以追溯到《楚辭·招隱士》,其中有“王孫游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句(葉嘉瑩,2018:111)。謝靈運源詩中緊隨其后的一聯“祁祁傷豳歌,萋萋感楚吟”可以與此構成相互的支撐與印證。西方讀者由于不熟悉如是的文化傳統,兩種英譯文對于“春草”這一核心意象的翻譯很難引發超過純粹寫景層面的文化內涵,也并不能夠引發英譯文讀者與源文讀者相仿的興發感動,這樣便造就了另外一重“隔”的問題。
如是觀之,涂譯、李譯兩種均不能視之為成功的譯文。當然,他們的不成功是漢英兩種語言在語言、文化、詩學幾個層面“不可通約性”使然,我們是沒有任何理由去苛責譯者的。
4.0 結語
由上文的具體分析,我們不難發現,涂經詒、李又安對于“境界”理論及其相關術語的翻譯體現了兩位譯者對于《詞話》的個人研究與獨特理解。具體來說,在涂氏看來,“境界”同于“境”,是《詞話》中的唯一核心概念,似乎并不存在或者沒有必要凸顯其中二級概念的存在,在翻譯“境界”概念的時候借用了劉若愚的譯法,通篇以“world”譯之,在翻譯“造境”與“寫境”、“有我之境”與“無我之境”、“隔”與“不隔”等二級概念時則使用了類似于解釋、說明式的譯文。而在李氏眼中,“境界”與“境”并不能做等量齊觀,二者有別,譯文需做必要的區分,于是便有了“ching-chieh”與“state”或“poetic state”兩種譯法的分野;不僅如此,李譯還特別強調了“造境”與“寫境”、“有我之境”與“無我之境”、“隔”與“不隔”等術語的二級概念地位。從理解認知層面來看,較之涂譯,李譯對于“境界”理論中的重要概念有著更加深刻的認識與更為細化的把握,這對于西方讀者深刻理解“境界”說理論更加具有建設性的意義。從翻譯策略層面來看,涂譯更像是一種歸化做法,而李譯則更近于異化處理。按照潘文國(2017)有關中華文化翻譯傳播中“格義”與“正名”兩種途徑的區分②,涂譯應當屬于“格義”處理,而李譯則更加具有“正名”性質。“格義”譯法雖然在中西文化交通的歷史上、現實中普遍存在,并且發揮過也正發揮著十分積極的作用,但這種做法總是難以避免地造成原始概念的扭曲,導致部分真相的遮蔽。與之相較,“正名”譯法則更加有利于避免上述問題發生,進而還原出本初概念的原貌,揭示出其中蘊含的真諦。如是觀之,在中國文論的國際傳播方面,涂譯在英語世界可以起到認知鋪墊的作用,李譯在西方學界則可以更多地發揮概念還原的功能。“目前,我國大力實行文化‘走出去’戰略”(胡作友,張丁慧,2019:107),在如此宏大背景之下,李譯的“正名”譯法較之涂譯的“格義”處理更加貼合時代的主題。
注釋:
① 葉嘉瑩認為,王國維所謂的“有我”與“無我”兩種境界其分野乃是根據康德、叔本華之美學理論中由美感之判斷上所形成的兩種根本區分。見葉嘉瑩,“《人間詞話》之基本理論——境界說”,見王國維,《人間詞話》,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109頁。
② 潘文國研究中華文化翻譯傳播,做了“格義”與“正名”的區分,前者指“為了便于人們的理解,采用本土文化中的類似概念去比附”,后者則是“在系統論思想的觀照下,重新審視中華文化的譯傳歷史,對重要的文化術語及其譯名進行重新審查和厘定。”見潘文國,“從‘格義’到‘正名’——翻譯傳播中國文化的重要一環”,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5期,141-147+1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