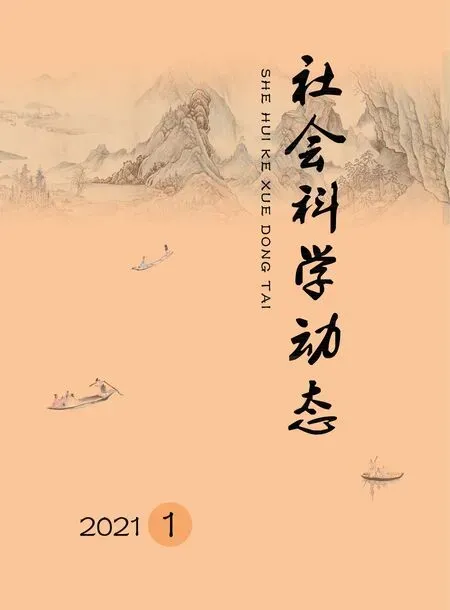構建馬克思主義發展經濟學范式的內在邏輯
孫浩進 趙 茜
新時代的發展階段,需要構建基于新形勢、新變化、新特征的符合中國國情的“致用”的經濟學理論范式。構建馬克思主義發展經濟學范式的理論邏輯已經成為新時代中國經濟發展的現實理論訴求。200 余年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不斷得以豐富與發展,是極具生命力的理論,并且一脈相承、與時俱進①。發展經濟學旨在研究發展中國家由不發達到發達狀態轉型的原理②,近50年來在全球逐漸興起,并已成為世界各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所重視和應用的重要經濟學理論。根據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發展經濟學的內在規律、普遍性與特殊性的關系,在二者相似的內容、相同的指向、相通的邏輯中探討馬克思主義發展經濟學范式的內在邏輯,可以更好地踐行并服務于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和發展。
一、構建馬克思主義發展經濟學范式的內在邏輯的必要性
新時代的中國經濟發展,需要新的符合自身發展的經濟學理論體系作為理論指導工具。構建符合中國自身國情的馬克思主義發展經濟學范式的內在邏輯,是增強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現實解釋力的需要,是推動發展經濟學追溯問題本質的需要,也是指導中國經濟發展實踐的需要,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 一) 增強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現實解釋力的需要
毋庸置疑,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探究本質的理論經濟學,具有根本意義上的科學價值。馬克思主義作為我國意識形態的引領和指導,其政治經濟學相關理論對于我國的經濟建設同樣具有重要指導意義③。但在進入新時代,對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若是陷入教條主義、實用主義的誤區,則會直接導致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話語權的降低,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指出“實際工作中,在有的領域中馬克思主義被邊緣化、空泛化、標簽化,在一些學科中‘失語’、教材中‘失蹤’、論壇上‘失聲’。這種狀況必須引起我們高度重視”。因此,當前增強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現實解釋力,重視其話語體系建設,從而適配我國經濟發展的新形勢、新問題、新需要是迫在眉睫的問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更具有普遍性與一般性,具有科學的理論抽象性、概括性,而發展經濟學則偏向于經濟結構的特殊性,具有切合實際的現實性,二者依據理論邏輯進行有機結合,從更具解釋力的范疇上探究經濟發展的動力、經濟發展的韌性,能夠在現實層面增強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現實解釋力。這意味著,構建新時代的馬克思主義發展經濟學不僅是提高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對現實解釋力的理論本身的需要,也是走好中國經濟道路、確立理論自信的迫切需要。
( 二) 推動發展經濟學追溯問題本質的需要
盡管發展經濟學以發展中國家如何實現經濟發展為主要研究內容,但大部分理論往往以發達國家的歷史經驗、現象表征為參考依據,而忽視了發展中國家本身內在的固有特性,缺乏從問題本質層面的深入剖析,這就不可避免地阻礙了發展經濟學追溯其本質機理。從歷史的視閾審視,發展中國家數量眾多、稟賦各異、模式多元,其發展本身面臨極其復雜的問題④,且世界經濟局勢尚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更需要能夠深入分析經濟問題本質的經濟學理論來進行闡釋和研究。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最具抽象意義、能夠透過紛繁復雜的經濟現象探究問題本質的理論,也是與時俱進、因勢而新的理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早已在我國經濟改革與發展中凸顯出強大的理論魅力與智慧;而發展經濟學在現實維度上對于發展中國家的研究獨具自身的學科特色和范式優勢⑤,正需要在理論維度上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實現有機結合,補齊理論短板,在追溯問題本質的層面豐富學科內涵、深化研究范式,結合我國的經濟發展實際,就能夠對當今發展中國家提供更具實質意義上的實踐指導。
( 三) 指導中國經濟發展實踐的需要
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尤其是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以來,社會主要矛盾發生深刻變化,經濟發展正面臨著產業結構優化、技術轉移升級的重大問題。新時代需要不同于以往的理論創新,對于經濟理論具有新的需求,在深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范式研究和借鑒發展經濟學范式經驗的基礎上,思考構建怎樣的馬克思主義發展經濟學范式,指導中國經濟發展的新實踐,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黨的十九大報告在闡述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時候特別強調,必須堅定不移地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發展理念,這一理念正是構建馬克思主義發展經濟學范式的具體邏輯。改革開放40 多年來,中國經濟發展更多的是靠“摸著石頭過河”渡過難關,但如今我國處于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新的歷史條件下,在新時代的實踐中,就需要更加符合時代特征的經濟理論來予以指導,以馬克思主義發展經濟學來闡釋、剖析、研究中國經濟發展道路,能夠在理論指導實踐的范疇上凸顯當代價值,更加堅定道路自信。
二、發展目的的內在邏輯:人的主體性
( 一) “以人為本” 的同一指向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自誕生的那一天起,就堅定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場,即為無產階級革命和共產主義運動提供強大的思想理論支撐,是具有“人”的階級性的經濟學。有關“人的發展”這一思想進入到人類的視野,要追溯到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經典著作《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馬克思開始關注“現實的人”源于對異化勞動理論的探究,關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人們遭受到的剝削和不公平待遇的普遍狀態,理性地分析了人的本質問題,并提出了“人的本質并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實際上,它是一切關系的總和”,將關注點轉移到了現實的人的生存狀態與發展上來⑥。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關于“以人為本”的相關思想,其內涵在于發展的目的是改善底層工人待遇,提高被剝削的無產階級的地位,從而實現人的全面發展。而從發展經濟學的視閾審視,20世紀80年代以來,發展經濟學取得的理論進展中最能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具有同一指向的就是對于“人”的重視。發展經濟學在突出人的主體性方面,認為發展的目的是實現發展中國家以及落后國家和地區弱勢群體的發展。曾因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問題進行透徹研究而榮獲197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著名發展經濟學家Theodore W.Schultz,在“以人為本”這一思想中也有相似的研究。他提出了“人力資本論”,認為人力資本是影響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經濟發展的質量并非絕對依賴于自然資源和金錢是否豐厚,而是主要取決于人力資源的質量。198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發展經濟學家Amartya Sen 的理論建樹就是在不同的層次上滿足人的基本需求和發展人的能力。2019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發展經濟學家Abhijit Banerjee、Esther Duflo、Michael Kreme,他們的理論核心就是如何減少人的貧困,這充分表明發展經濟學對于“人”的問題研究取得重要進展,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具有“以人為本”的同一指向。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發展經濟學的有機結合看似是場“不期而遇”,實則絕非偶然,而是“目的相通、指向相同”的必然。
( 二) “以人為本” 的內容銜接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這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根本立場。”⑦由此可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人的主體性上,具有“以人為本”立場的堅定性,研究的本質則在于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消滅階級剝削,促進人的全面自由發展,這貫穿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始終。作為馬克思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于實現共產主義、實現作為人的自由,提出了具體的以“人”為出發點的經濟理論,比如剩余價值理論強調勞動的付出沒有得到同樣的回報、勞動者創造的剩余價值被沒有付出勞動的“資本”所剝削等,在理論內涵中充分體現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視域下的人文關懷。而在發展經濟學中,“人力資本理論”作為重要的發展要素,同樣對經濟的發展起著不可估量的作用。發展經濟學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產生的背景雖然不同,但確實在發展中國家這一研究主題產生后,不約而同地對發展相對落后的國家向發達國家轉型的出路進行探究,旨在對發展中國家的優劣勢以及其面臨的核心問題進行深入剖析,并提出相應的對策建議。其核心觀點就在于在突出人的主體性的前提下,判定發展遠不是單純地依靠經濟數量的增長那般簡單,因為經濟的增長并不會自動導致人的全面發展。由此可見,從以人為本的發展目的來講的,二者的內容和歸旨基本相似。
三、發展動力的內在邏輯:資本作用的推動
( 一) “資本形成” 的同一指向
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發展經濟學視域中,發展的直接動力都是資本,凸顯了資本作用的推動。在經濟學領域,有關經濟發展直接動力的詳細說明,可以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找到相應的答案,即把剩余價值再轉化為資本,實現資本的擴大再生產,同時,經濟發展必須依靠剩余價值產生追加的資本,故而資本也被認為是經濟發展的直接動力源。而在發展經濟學中,R.Nurkse 認為在經濟落后的國家,發展問題的核心就是資本形成,認為經濟發展緩慢的根源在于資本匱乏和投資嚴重不足,并將資本形成視為經濟發展的直接動力。R.Nurkse認為一個國家的資本形成越充足,該國家距離貧困惡性循環就越遠。換言之,資本形成的問題是廣大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發展中面臨的關鍵所在,足見資本形成對于發展中國家的重要意義。雖然該理論存在局限性,但是在關于“資本形成”這一指向上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相同。綜合上述理論觀點來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發展經濟學在關于經濟發展動力的研究上,都闡釋了“資本形成”對于經濟發展的重要促進作用。構建馬克思主義發展經濟學范式的內在邏輯,不僅是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創新與發展,更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成果因時而進的展現,因此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實踐更具指導價值。
( 二) “資本形成” 的內容銜接
盡管當今自成一體的經濟學派眾多,在理論上為經濟發展道路的多樣性提供了更多的選擇空間與可能,但對于目前經濟發展問題研究的多樣化選擇,并不意味著能夠做到“有的放矢”。因而,針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發展經濟學在內容如何銜接的研究在新的歷史階段仍具有極大的理論價值和較大的學術發展空間。尤其是在發展動力的探究上,關于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不能僅僅是零敲碎打,而是要有連貫性、邏輯性地追溯其與發展經濟學相通的內在機理。無論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還是現代發展經濟學,都凸顯了資本作用的推動,認為資本積累形成對經濟發展具有重要作用,甚至批判了資本的剝削,且都指出“資本形成”已不是決定經濟發展的唯一條件。但在明確發展的直接動力——“資本”的基礎上,深入分析投資及其作用,不僅是一項有現實價值的課題,更是當今時代仍需要解決好的難題。鑒于發展中國家的市場容量小,并不能通過資本融資的方式解決資本不足的問題,便需要深刻地檢討過去資本形成中的制約因素,比如是否將投資用于回報率低、效率低的部門?如何處理投資互補性的弊端?從世界經濟發展來看,仍有許多貧困型的發展中國家,仍面臨著過低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落后的教育和醫療衛生資源約束,對于這些國家或地區而言,資本仍是稀缺性生產要素。這就需要進行反思,貧困型的發展中國家和地區與發達地區相比存在著巨大的信息鴻溝和發展落差,要打破這種增長的不對稱性,就需要大量的投資,以免陷入貧困的惡性循環。從我國的經濟發展來看,改革開放后的40年來取得了飛躍性的發展,即使是我國經濟發展相對落后的地區,其人均GDP 也要高于部分相對落后的發展中國家,這是因為“資本形成”的效率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四、發展路徑的內在邏輯:創新的內生化
( 一) “創新驅動” 的同一指向
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發展經濟學中,經濟發展的內生路徑依然相互貫通——“創新驅動”。在馬克思的理論研究長河中,技術創新這一部分耗費了他極大的精力。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并沒有對“創新”一詞進行明確的闡釋,但是在其經典著作中仍能發現與技術創新相似的表達,這一點在馬克思關于機械發明的論述中尤為凸顯。例如,馬克思對發明蒸汽機的看法,認為技術的發明與創新對于推動經濟發展具有重大的意義和作用。此外,馬克思的技術創新概念可以從勞動生產率提高、價值規律和資本有機構成理論中發現。而在發展經濟學中,經過198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Robert Merton Solow 及201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Paul M.Romer 等經濟學家的努力,技術創新經歷了一個外生化到內生化的過程,他們認為經濟長期的增長主要依賴于科技的進步而非金錢的投入,并且提出技術創新是衡量社會進步的重要指標,也是發展的內生路徑和動力。發展經濟學關于技術—經濟的變革研究,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技術變革思想有著相通的邏輯,且二者都認為技術創新屬于生產力范疇,是推動經濟增長與發展的主要動力,在針對此部分內容的研究中都包含“創新驅動”的同一指向。
( 二) “創新驅動” 的內容銜接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發展經濟學都對“創新驅動”的本質有著清醒而科學的認知,為當代經濟內生增長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機理,并且可以將此內生路徑的探尋與應用落實到我國的經濟發展實踐當中。在現代經濟中,技術創新越來越成為衡量一個國家國際競爭力的重要指標,越是發達國家,越是重視技術創新。換言之,技術創新不僅是兩個經濟學理論范式的內生路徑,更是引領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內生動力,可以為一國的經濟發展提供新的動力與新經濟增長點。技術創新已經成為當代經濟發展的重要內生動力,對技術創新予以重視的發展中國家才有向發達國家轉型的可能⑧。
在當代,關于技術創新的定義是寬泛的,而從外部和整體來看,可延伸到以企業為主體的產學研技術創新體系。在發展經濟學中,許多經濟學家認為經濟的增長不是代表經濟發展的唯一指標,技術創新的推動力才是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從我國的國情來說,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在堅持以創新驅動作為現代化建設核心的“十四五”高質量發展階段,唯有通過拓展發展新空間、培育新的增長點,通過刺激需求、釋放消費活力、降低成本、發展新業態等應對疫情不利影響,才能把經濟下行壓力降到最低。要謀求創新驅動的新突破,在基礎性的創新制度上尋求突破,更快速度推進創新要素資源的聚集。在科技要素資源的配置上,尤其是在人才要素、資本要素、技術要素、數據信息要素配置上要用好增量,盤活存量,把要素配置的文章做好,更應該重視長期通過新基建建設催生新產業、新業態。
基于上述分析,從現代化的視閾審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發展經濟學中關于“技術創新”的闡釋,形成了關于“創新驅動”的內容銜接,這也構成了馬克思主義發展經濟學范式的內生路徑,對其內在邏輯的研究必然成為經濟發展問題研究的重要環節。
五、發展規律的內在邏輯:互動演化
( 一) “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作用” 的同一指向
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馬克思誕辰200 周年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時指出,“學習馬克思,就要學習和實踐馬克思主義關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思想……我們要勇于全面深化改革,自覺通過調整生產關系激發社會生產力發展活力,自覺通過完善上層建筑適應經濟基礎發展要求,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更加符合規律地向前發展”。由此可見,在當今馬克思政治主義經濟學對于發展規律的指向也非常清晰。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發展經濟學強調,發展的根本規律都是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的互動演化規律。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相互適應的規律,始終也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探討的最本質的問題。盡管在歷史的進程中涌現了諸多現代經濟學派對此加以解讀或者試圖重新定義,但馬克思對其深刻認識和本質性概括至今仍具有首創性和巨大貢獻。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分析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表明,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狀況的規律,這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根本的普遍的規律。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規律始終占據著不可撼動的地位,其對于社會歷史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發展經濟學理論中關于發展的根本規律的敘述則更加具體,是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補充與銜接。在發展經濟學那里,制度變遷可以提高經濟效率,即制度變遷作為一種生產關系演化,能夠促進生產力發展,即經濟效率的提高⑨。制度變遷與經濟效率是互動演化的⑩,其在本質上遵循了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規律。由此可見,二者關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作用”的概述具有相同的趨向性,雖然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發展經濟學闡述的具體概念界定和形式有所不同,但在理論維度上具有互動演化的同一指向。
( 二) “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作用” 的內容銜接
發展規律的同一指向,決定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發展經濟學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互動演化”方面具有相同的銜接邏輯,可以在此基礎上構建馬克思主義發展經濟學在發展規律上的內在邏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而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又具有反作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關系在任何社會結構中都是最基本的存在。馬克思認為,誰擁有科學的管理體系與技術創新,誰就能掌握生產力發展的核心,因為生產力是經濟發展中最具動力和積極的因素。生產力是具有橫向性的,其主要要素構成中不僅包括勞動資料、勞動對象和勞動者,還包含著科學技術。而在發展經濟學中,將經濟發展的過程視為專業化和分工不斷深化的過程,而由此所帶來的交易費用也會與日俱增。如果沒有一種新的能有效降低交易費用的制度產生,就會阻礙專業化和分工的進一步發展,從而導致經濟停滯甚至衰退。而通過建立能夠減少交易費用的制度,就能促使專業化和分工過程的深入,并帶來長足的發展動力?。基于這一角度,我們可以說歷史上經濟發展的過程,就是不斷推動這種能夠降低交易成本的制度不斷完善、變化的過程。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視閾下,制度被視為生產關系范疇,因此發展經濟學中的觀點指向,仍沒有脫離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相互適應的理論范疇,二者具有密切的內容銜接。在發展經濟學的發展根本規律中,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邏輯依舊存在,如制度的功能是指其在經濟上的效能,其最終目的是使生產關系更好地與生產力相適應,并形成良性的互動演化。
任何理論的發展都離不開與實踐維度的密切聯系,馬克思主義發展經濟學也是如此。因此,認識馬克思主義發展經濟學范式在當今歷史階段的現實引領與指導具有重要意義。從我國的國情來看,中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仍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發展仍是核心的問題,而發展經濟學就是致力于解決發展中國國家落后的經濟狀況所產生的。新中國成立70年來,特別是改革開放40 余載的波瀾壯闊歷程,為中國的經濟從高速度增長轉變為高質量發展奠定了堅實的發展基礎。但改革開放初期,我們更多的是“摸著石頭過河”,因此不能單純地把這段經濟發展歷程用一般的經濟學視角進行分析。這就意味著,中國的經濟發展與實踐是離不開發展經濟學的理論與創新的,發展經濟學揭示了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普遍規律,但需要與實踐完美融合才能發揮出其理論的力量;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能夠解釋經濟發展的最一般、最本質的規律,只有二者互為補充、相輔相成,才能為新的歷史階段下經濟的發展提供更多的潛力與可能性。馬克思主義發展經濟學范式的現實引領與指導,具體來說,就是要引領與指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實踐,讓我們在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的基礎上,逐漸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目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新時代下的經濟學領域最新理論成果之一——馬克思主義發展經濟學范式,亟需發揮其對我國新常態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踐的指導作用,加強其對現實的引領與指導。具體來說,就是要加強頂層設計,總結歸納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規律,更好地進行宏觀調控,比如要善于利用財政、貨幣政策等調節手段,更好地調節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以五大發展理念為引領,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保證我國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
綜上所述,構建馬克思主義發展經濟學范式的內在邏輯既符合時代需要,又具有歷史淵源和理論傳承。馬克思主義發展經濟學范式的理論屬性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維度,同時也具有政治經濟學或經濟學的歷史性、社會性、階級性和國別性,究其根源是其研究對象的特殊性。政治經濟學或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社會的人或事物,這就使其具有社會科學或社會意識形態的性質。此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獨特性,也決定了馬克思主義發展經濟學范式理論體系的構建和發展具有獨創性,是不同于西方經濟學范式和傳統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范式的一種新的政治經濟學范式?。從經濟思想史的維度審視,許多經濟學理論流派未能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本質出發,致使其后續發展出現了異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科學地闡述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基本原理,批判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弊端及其理論,原則性地闡述科學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及其理論,是人類經濟思想史上的偉大革命,對于構建馬克思主義發展經濟學的理論范式具有重要價值?。由此可見,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本質特征與發展經濟學的普遍規律相結合服務于中國經濟發展實踐,不僅是時代的需要,更是理論發展的內生需求,不斷在理論結合與創新中彰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時代智慧。在明確內在邏輯的基礎上,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為理論引領和理論核心?,以發展經濟學為理論支撐和理論工具,這是新時代馬克思主義發展經濟學范式構建的方式與路徑。
注釋:
①張維達:《政治經濟學》,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05頁。
②張培剛、張建華:《發展經濟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22頁。
③衛興華、林崗:《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原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39頁。
④姚洋:《發展經濟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203頁。
⑤馬春文、張東輝:《發展經濟學》,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76頁。
⑥《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2頁。
⑦中共中央宣傳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學習綱要》,學習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03頁。
⑧紀玉山:《現代技術創新經濟學》,長春出版社2001年版,第82頁。
⑨盧現祥:《西方新制度經濟學》,中國發展出版社2003年版,第17頁。
⑩陳勁、王煥祥:《演化經濟學》,清華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95頁。
?盛洪:《現代制度經濟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72頁。
?王立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報告》,濟南出版社2016年版,第142頁。
?邱海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屬性》,《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2017年第5期。
?吳宇暉、張嘉昕:《外國經濟思想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191頁。
?張宇:《不斷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人民日報》2016年8 月29 日。
?王朝科:《關于新時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解讀》,《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17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