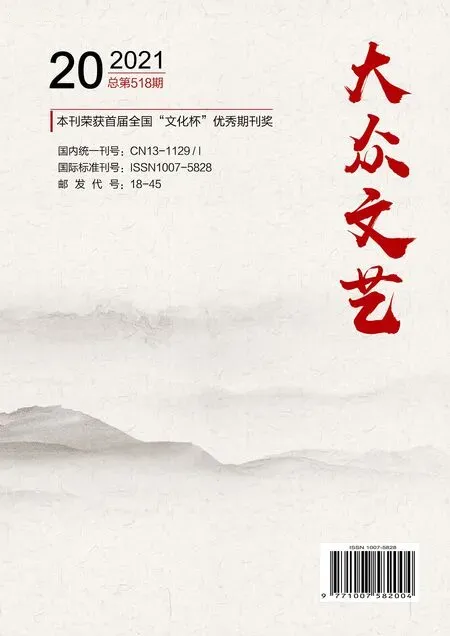嚴(yán)復(fù)和泰特勒翻譯之異同
(云南大學(xué)外國(guó)語(yǔ)學(xué)院,云南昆明 650500)
一、中西方翻譯史簡(jiǎn)述
(一)中國(guó)翻譯簡(jiǎn)史
中國(guó)翻譯史上出現(xiàn)了五次翻譯高潮,即從東漢到唐宋時(shí)期的佛經(jīng)翻譯,明末清初時(shí)期的科技翻譯,晚清民初的西學(xué)翻譯,“五四”以后的社會(huì)科學(xué)和文學(xué)翻譯,以及新中國(guó)成立以后的翻譯。
就佛經(jīng)翻譯來(lái)說(shuō),中國(guó)用文字記載的翻譯正始于它,玄奘、鳩摩羅什和真諦被譽(yù)為中國(guó)三大佛經(jīng)翻譯家。
我國(guó)明代學(xué)者徐光啟,對(duì)數(shù)學(xué)、天文皆有狩獵,對(duì)明代科學(xué)發(fā)展做出突出貢獻(xiàn)。徐光啟翻譯作品有《幾何原本》《泰西水法》等,促進(jìn)東西方文化交流。這是第一次將歐洲的數(shù)學(xué)理論介紹給中國(guó),標(biāo)志著譯著的方向性轉(zhuǎn)變。
自十九世紀(jì)四十年代,晚清政府被打開(kāi)國(guó)家大門(mén),西方在文化與武力上對(duì)晚清進(jìn)行壓迫。此時(shí)西學(xué)翻譯,基本以學(xué)習(xí)西方先進(jìn)政治文化為主。
自二十世紀(jì)開(kāi)端,國(guó)民思想逐漸開(kāi)化,在五四運(yùn)動(dòng)與新文化運(yùn)動(dòng)加持下,白話文逐漸取代文言文。在俄國(guó)十月革命取得成功的影響下,本階段翻譯作品主要以蘇聯(lián)作品為主,馬列主義開(kāi)始在中國(guó)傳播。
1949年新中國(guó)成立,穩(wěn)定的政治條件給予文化藝術(shù)生存土壤。本階段翻譯思想呈現(xiàn)百家爭(zhēng)鳴全面發(fā)展,出現(xiàn)意境論、化境論等翻譯要點(diǎn)。
(二)西方翻譯簡(jiǎn)史
縱觀西方翻譯史,在歷史長(zhǎng)河中上下跨越兩千四百余年,共計(jì)存在六次有重大影響的翻譯盛況。
第一次出現(xiàn)在公元前4世紀(jì)到公元4世紀(jì),古希臘文學(xué)戲劇介紹到了羅馬。
第二次是公元5到十一世紀(jì)出現(xiàn)在羅馬帝國(guó)后期-中世紀(jì)初期的翻譯,它具有宗教性質(zhì),其中以《圣經(jīng)》翻譯為主要表現(xiàn)形式。
在中世紀(jì)時(shí)期十一世紀(jì)到十二世紀(jì)左右,出現(xiàn)第三次翻譯盛況。在本階段,許多阿拉伯文學(xué)作品傳入歐洲大陸,譯為拉丁文作品。
歐洲文藝復(fù)興時(shí)期出現(xiàn)第四次翻譯高潮,本階段具體時(shí)間約為十四世紀(jì)到十六世紀(jì),促進(jìn)歐洲各國(guó)文化交流。
第五次是十七世紀(jì)下半葉至十九世紀(jì)世界文學(xué)名著的翻譯。
第六次從20世紀(jì)至今,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來(lái),翻譯事業(yè)繁榮興盛。
二、中西翻譯標(biāo)準(zhǔn)簡(jiǎn)介
翻譯是一種文化交流活動(dòng)。有了翻譯活動(dòng),翻譯標(biāo)準(zhǔn)自然隨之出現(xiàn)。在中西翻譯發(fā)展史上,有很多翻譯家都曾就翻譯標(biāo)準(zhǔn)提出了自己的見(jiàn)解。例如,我國(guó)的道安曾提出“五失本”和“三不易”;玄奘曾提出“五不翻”;嚴(yán)復(fù)曾提出“信、達(dá)、雅”;傅雷曾提出“神似”;錢(qián)鐘書(shū)曾提出“化境”等等。在西方翻譯思想中,英國(guó)學(xué)者泰特勒于十八世紀(jì)九十年代出版《論翻譯的原理》一書(shū),在其中首次提出翻譯三原則。二十世紀(jì)著名語(yǔ)言學(xué)家彼得·紐馬克在翻譯上注重實(shí)際意義,因此提出“語(yǔ)義翻譯”和“交際翻譯”。美國(guó)翻譯學(xué)者尤金·奈達(dá)于二十世紀(jì)提出翻譯核心應(yīng)為功能對(duì)等。
我國(guó)翻譯學(xué)者嚴(yán)復(fù)生活年代在戰(zhàn)火紛飛的近代中國(guó),特殊的時(shí)代特征使他的翻譯理論具有時(shí)代特色。我國(guó)唐朝就存在佛經(jīng)翻譯,嚴(yán)復(fù)取其精華,學(xué)習(xí)傳統(tǒng)文化中優(yōu)秀思想,對(duì)現(xiàn)有翻譯理論進(jìn)行總結(jié)與概括,針對(duì)中國(guó)特色提出“信、達(dá)、雅”翻譯原則和標(biāo)準(zhǔn)。
泰特勒在《論翻譯的原則》書(shū)中認(rèn)定,翻譯作品成功與否取決于譯文能否使得原作的優(yōu)點(diǎn)得以完全呈現(xiàn),以及使譯文的讀者像原作讀者一樣地對(duì)這種優(yōu)點(diǎn)有著相同的感受(譚載喜,2016:129)[1]。基于此,泰特勒提出翻譯三原則,即保障譯文與原作傳達(dá)思想一致,譯文應(yīng)保持與原作風(fēng)格一致,保持文章翻譯后語(yǔ)句通順。
三、二者比較
(一)相同點(diǎn)
1.在語(yǔ)言表達(dá)方面,嚴(yán)復(fù)主張“達(dá)”,也就是譯筆的通俗曉暢,這和泰特勒提出的三大原則中的第三條,在本質(zhì)上屬于同一目的。
2.嚴(yán)復(fù)的“雅”,和泰特勒的三大原則中的第二條,強(qiáng)調(diào)的都是翻譯的風(fēng)格問(wèn)題。
3.在思想內(nèi)容方面,嚴(yán)復(fù)在翻譯作品過(guò)程中強(qiáng)調(diào)“信”,意為對(duì)譯者行為進(jìn)行規(guī)范,同時(shí)做到對(duì)原文內(nèi)容做到不改變其思想與描述形式,做到譯文內(nèi)容與格式與原文一致,準(zhǔn)確將原文思想內(nèi)容進(jìn)行傳達(dá)。
首先,“達(dá)”,是為了“信”。可以說(shuō),“達(dá)”的最終目的,便是“信”(王秉欽,2017:56)[2]。
其次,“信”與“達(dá)”是統(tǒng)一的(王秉欽,2017:56)[2]。嚴(yán)復(fù)在《群己權(quán)界論》譯凡例中說(shuō):“原書(shū)文理頗深,意繁句重,若依文作譯,必至難索解人,故不得不略為顛倒,以此中文譯西書(shū)定法也”。可見(jiàn),嚴(yán)復(fù)的“達(dá)”,始終是以意義為本的(王秉欽,2017:57)[2]。
最后,“雅”是為了“達(dá)”(王秉欽,2017:57)[2]。“雅”在嚴(yán)復(fù)理念中意為語(yǔ)言優(yōu)美,辭藻清雅,保障文章可讀性與藝術(shù)價(jià)值。但文字優(yōu)美是對(duì)譯文內(nèi)容準(zhǔn)確傳達(dá)的錦上添花,“達(dá)”是目的,“雅”是手段(王秉欽,2017:58)[2]。
其實(shí)這也就是泰特勒的第一條原則。泰特勒表示,在對(duì)文學(xué)作品進(jìn)行翻譯時(shí)需要把握原文所傳達(dá)思想,對(duì)其思想進(jìn)行準(zhǔn)確傳達(dá),翻譯中需要注重語(yǔ)言修飾與筆觸,但準(zhǔn)確傳達(dá)文章思想是翻譯要點(diǎn),筆調(diào)發(fā)揮輔助作用,其存在是為了更好將文章思想進(jìn)行表述。當(dāng)三原則不能兼顧時(shí),可以先犧牲語(yǔ)言表達(dá)形式,其次是風(fēng)格,但必須保留原作的思想內(nèi)容。
(二)不同點(diǎn)
1.嚴(yán)復(fù)翻譯理論中對(duì)“雅”的要求與泰特勒翻譯原則中的第二條有所相同,但這兩位學(xué)者在對(duì)翻譯中語(yǔ)言風(fēng)格的理解并不一致。嚴(yán)復(fù)的“雅”強(qiáng)調(diào)的是用漢以前的字法、句法,以“達(dá)易”,求顯(王秉欽,2017:57)[2];而泰特勒所指的風(fēng)格,是基于他認(rèn)為,譯者必須準(zhǔn)確地判斷出原作風(fēng)格屬于哪一類(lèi),然后譯者必須有能力在譯文中同樣明顯地表達(dá)出來(lái)(譚載喜,2016:130)[1]。
2.嚴(yán)復(fù)身處陷于內(nèi)憂外患的舊中國(guó),以譯介西方先進(jìn)思想、改造中國(guó)為己任。嚴(yán)復(fù)在翻譯書(shū)籍上側(cè)重于對(duì)西方國(guó)家政治理論進(jìn)行描述,意為激發(fā)國(guó)民反抗意識(shí)。這些書(shū)成了日益腐朽的封建統(tǒng)治下的“頑固派”和中國(guó)知識(shí)分子了解西方世界的重要窗口。所以“信、達(dá)、雅”翻譯原則的提出,是源于嚴(yán)復(fù)的具體翻譯實(shí)踐。然而泰特勒較之嚴(yán)復(fù),處于較為安逸的象牙塔之中,其三原則的提出是出于理論研究的目的(劉傳瑋,2016)[3]。
3.在學(xué)術(shù)傳統(tǒng)的價(jià)值取向上,中西方存在一定差異。中國(guó)自古以來(lái)重視學(xué)以致用,西方重視尋求真理(王晨婕,2008)[4]。中國(guó)傳統(tǒng)思維重實(shí)踐經(jīng)驗(yàn),輕理論分析。嚴(yán)復(fù)的“信、達(dá)、雅”翻譯原則起初只是用來(lái)描述他在翻譯的實(shí)踐過(guò)程中,所遇到的困難。相對(duì)對(duì)翻譯理論進(jìn)行概括,嚴(yán)復(fù)較為重視翻譯本身(楊繼良,2010)[5]。這就導(dǎo)致了嚴(yán)復(fù)沒(méi)有對(duì)“信、達(dá)、雅”做出明確界定。然而西方的學(xué)術(shù)研究看重邏輯和理論,強(qiáng)調(diào)科學(xué)性和條理性。因此,泰特勒承襲了歐洲大陸的理性傳統(tǒng),提出的翻譯三原則條理清晰,結(jié)構(gòu)嚴(yán)謹(jǐn),在三項(xiàng)總的原則下又分若干細(xì)則。
4.我國(guó)傳統(tǒng)譯論體現(xiàn)著中國(guó)人的悟性思維,然而西方傳統(tǒng)譯論體現(xiàn)著理性思維(趙巍、石春讓?zhuān)?005)[6]。當(dāng)我們從思維方式的角度來(lái)思考嚴(yán)復(fù)未對(duì)“信、達(dá)、雅”做出清晰界定和詳細(xì)論證這一事實(shí)時(shí),我們會(huì)發(fā)現(xiàn)這和中國(guó)人的思維偏悟性有關(guān)。它使得人們?cè)诒硎錾细:秃睿瑥?qiáng)調(diào)人對(duì)事物的領(lǐng)悟,俗話說(shuō)“只可意會(huì),不可言傳”。原文存在于譯者和讀者的個(gè)人意識(shí)當(dāng)中,很少見(jiàn)諸字面(趙巍、石春讓?zhuān)?005)[6]。受西方傳統(tǒng)哲學(xué)思想控制,泰特勒在進(jìn)行翻譯時(shí)對(duì)原文思想進(jìn)行明確表述,將其清晰地在字面上描述。
5.中國(guó)人的思維方式較之西方,具有保守、崇尚權(quán)威的特點(diǎn),不敢質(zhì)疑,缺乏否定和超越的精神。這一點(diǎn),可以在“信、達(dá)、雅”翻譯原則長(zhǎng)期受到的崇拜中得以體現(xiàn)。一方面,“信、達(dá)、雅”翻譯原則本身確有價(jià)值,言簡(jiǎn)意賅。但另一方面,人們也或多或少地認(rèn)為,“信、達(dá)、雅”的翻譯原則象征著完美和權(quán)威,是無(wú)法真正超越的(嬪國(guó),2011)[7]。而西方文化強(qiáng)調(diào)科學(xué)、理性和個(gè)體意識(shí),使西方人不固守前人已有的思維模式。泰特勒在十八世紀(jì)發(fā)表的《論翻譯的原則》,系統(tǒng)地論述了翻譯的原理和規(guī)則,這在某種意義上給西方翻譯研究帶來(lái)了新的突破。泰特勒翻譯原則雖然意義重大,但并不是唯一原則,在西方后續(xù)的翻譯學(xué)說(shuō)中仍然不斷涌現(xiàn)著新形式的翻譯理論。
四、結(jié)論
通過(guò)對(duì)比分析,可以看出嚴(yán)復(fù)和泰特勒兩位翻譯家在翻譯原則的語(yǔ)言表達(dá)、風(fēng)格,內(nèi)容側(cè)重點(diǎn)方面,大致具有共同點(diǎn)。然而,同時(shí)也看出兩位翻譯家在翻譯原則的具體闡釋和翻譯原則提出的目的方面,具有明顯的不同;以及中西方在學(xué)術(shù)傳統(tǒng)的價(jià)值取向和思維方式上的不同,也可以在兩位翻譯家的翻譯原則上得以體現(xiàn)。中西翻譯理論既有相通之處,又各有其特點(diǎn),這有助于正確認(rèn)識(shí)中西方傳統(tǒng)翻譯理論的優(yōu)勢(shì)和局限性,推動(dòng)翻譯理論及實(shí)踐的發(fā)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