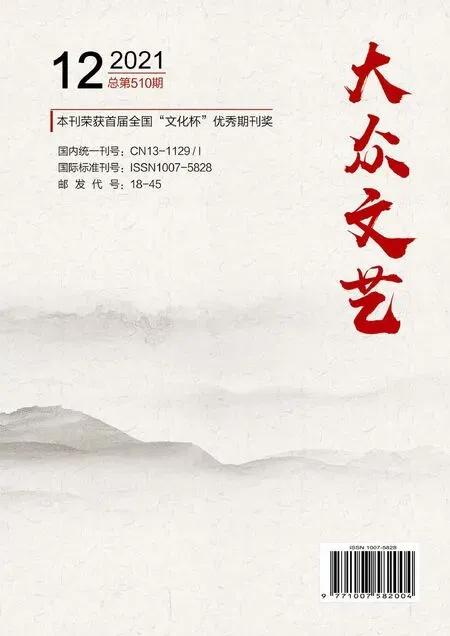《吶喊》《彷徨》中雪的意象
(武漢大學(xué)文學(xué)院,湖北武漢 430072)
讀《吶喊》《彷徨》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在這兩部頗具整體感和自足性的集子里,魯迅運(yùn)用乃至創(chuàng)造了大量“魯迅式”意象,這些反復(fù)出現(xiàn)并帶有強(qiáng)烈個(gè)人氣質(zhì)的意象在作品中形成獨(dú)立的敘事空間。
一、魯迅氣氛:雪的情感內(nèi)核
象內(nèi)含意,意為象心,作為一種復(fù)雜的多面體,意象含混著自然、社會(huì)、歷史、心理等多層面的意義,《吶喊》《彷徨》中的“雪”融合了“魯迅氣氛”,折射著作者的個(gè)體生命體驗(yàn)。
(一)雪與悲情氣質(zhì)
“雪”以其冰冷的物理屬性彌散著濃郁的悲情氣質(zhì),魯迅小說(shuō)發(fā)揮這一特質(zhì),借意象傳遞作者的憂郁心境。《吶喊》集內(nèi),“雪”唯一的出場(chǎng)是在《故鄉(xiāng)》里,閏土向“我”講述捕鳥(niǎo)的方法,因捕鳥(niǎo)只能借助下雪天氣,“我于是又很盼望下雪。”初讀此處,“雪”承載著童趣與友誼,似與悲情氣質(zhì)無(wú)關(guān),實(shí)則雪景存儲(chǔ)著“我”與少年閏土的歡樂(lè)記憶,多年后當(dāng)成年閏土面色灰黃、恭敬地叫著“老爺”時(shí),記憶與現(xiàn)實(shí)在隆冬交疊,加重了現(xiàn)時(shí)的悲哀,“我”對(duì)故鄉(xiāng)的許多眷戀被驅(qū)散。正是魯迅在《自序》里說(shuō)的“所謂回憶者,雖說(shuō)可以使人歡欣,有時(shí)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絲縷還牽著已逝的寂寞的時(shí)光,又有什么意味呢。”《彷徨》里的雪則無(wú)一例外與嚴(yán)冬的肅殺構(gòu)成一體。在《祝福》中,人物內(nèi)心活動(dòng)通過(guò)環(huán)境描寫(xiě)得以外化和加強(qiáng),下雪的天氣與主人公煩悶的心緒構(gòu)成映射關(guān)系,反復(fù)出場(chǎng)后更形成“雪花意象流”,暗示著主人公的情感動(dòng)向。伴著冬夜大雪,“我”回味祥林嫂飽受夫權(quán)、族權(quán)、神權(quán)摧殘的生平,巨大的失落感鋪展開(kāi)來(lái),最終在“團(tuán)團(tuán)飛舞的雪花”中,“我”仿佛看見(jiàn)受盡牲醴的圣眾預(yù)備給人們以無(wú)限的幸福……熱鬧的雪景是魯鎮(zhèn)悲劇的反諷,雪花飄落是“我”與魯鎮(zhèn)的訣別。《故鄉(xiāng)》與《祝福》里的雪花承載著魯迅深刻的悲憫情緒,既是對(duì)底層農(nóng)民苦難命運(yùn)的悲憫,也是對(duì)進(jìn)步知識(shí)分子與故鄉(xiāng)、故人隔膜的悲憫。
《吶喊》集內(nèi)僅出場(chǎng)1次的“雪”在《彷徨》集中反復(fù)“飄飛”,這一明顯變化更潛在隱喻了文本之外魯迅主體情感的失落。1923年7月,魯迅兄弟失和被趕出家門(mén),同時(shí)肺病復(fù)發(fā),從身體到精神皆跌入谷底,而嘆“一者不再與新認(rèn)識(shí)的人往還,二者不再與陌生人認(rèn)識(shí)……不如銷(xiāo)聲匿跡之為愈耳”。次年春節(jié),魯迅連作《祝福》《 在酒樓上》《幸福的家庭》三篇作品,顯出抒情性的沉溺。
(二)雪與孤獨(dú)心境
作為中華古典詩(shī)文中的典型意象,“雪”以其古典的軀殼包裹著先驗(yàn)的與經(jīng)驗(yàn)的文化內(nèi)涵,成為政治無(wú)意識(shí)的表征,以清冷孤寂的姿態(tài)跨越歷史時(shí)空,映襯著面對(duì)黑暗開(kāi)戰(zhàn)、于絕望中反抗的先驅(qū)者形象,映照著先驅(qū)者內(nèi)心的孤獨(dú)。
《在酒樓上》精心織構(gòu)了故人重逢的情節(jié)模式,漂泊者“我”在故鄉(xiāng)遇到曾經(jīng)的革命同道人呂緯甫,懇談間卻發(fā)覺(jué)少時(shí)眼里常閃著射人的光的他如今像蜂蠅般“給什么來(lái)一嚇,即刻飛去了”,消盡了先前的銳氣,仿佛一個(gè)認(rèn)罪伏法的犯人。作為革命先驅(qū),“我”與呂緯甫無(wú)疑都包含著魯迅的自傳成分,二人各執(zhí)“漂泊者”與“固守者”的一端展開(kāi)的關(guān)于人生狀態(tài)的對(duì)話可看作是魯迅內(nèi)心兩種聲音的“自我辯駁”。這場(chǎng)辯駁是在大雪里做結(jié)的:“我獨(dú)自向著自己的旅館走,寒風(fēng)和雪片撲在臉上,……和屋宇和街道都織在密雪的純白而不定的羅網(wǎng)里。”寒風(fēng)、雪片和黃昏隱喻著嚴(yán)酷的社會(huì)環(huán)境,也暗示了一場(chǎng)駁詰后“我”絕望悲涼的心境,但就是這看不到出口的絕望倒讓“我”覺(jué)得爽快,決絕前驅(qū)——雪中禹禹獨(dú)行著孤獨(dú)的戰(zhàn)士。
《孤獨(dú)者》的情節(jié)模式與《在酒樓上》相似,雪的出場(chǎng)是在我收到魏連殳來(lái)信的夜晚.這讓人聯(lián)想起艾略特筆下的荒原景象,一望無(wú)際的雪堆如同困陷在山陽(yáng)縣城的“我”精神荒原的對(duì)應(yīng)物。在這樣的雪夜,“我”想起了被孤立到走投無(wú)路的革命者魏連殳,隨即收到了他的來(lái)信:“我這里下大雪了……我已經(jīng)躬行我先前所憎惡,所反對(duì)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張的一切了”。大雪穿透了時(shí)空的阻隔,將寫(xiě)信的魏連殳與讀信的 “我”并置在同一個(gè)場(chǎng)景里展開(kāi)了靈魂的對(duì)話,“我”最終失去了同行者,魏連殳放棄了從前的堅(jiān)持,也為先前的自己所拋棄了。遙相呼應(yīng)的大雪勾連起先驅(qū)者的寂寞。
二、有意味的形式:雪的結(jié)構(gòu)創(chuàng)造
在敘事作品中,意象作為“故事的眼睛”點(diǎn)綴在各敘事單元,在重復(fù)出場(chǎng)中連綴情節(jié)片段,調(diào)節(jié)敘事作品的節(jié)奏,發(fā)揮著結(jié)構(gòu)全篇的作用。《吶喊》《彷徨》中作為意象的雪出現(xiàn)了18次,在重復(fù)中實(shí)現(xiàn)著意義的遞進(jìn)和增添,推動(dòng)小說(shuō)層次感和節(jié)奏感的形成,并參與敘事模式的建構(gòu)。
(一)雪的線索作用
《祝福》中雪的意象。全文雖按插敘進(jìn)行,但梳理時(shí)間線索來(lái)看,第一次下雪是在祥林嫂重回魯鎮(zhèn)時(shí),改嫁卻夫死子夭的她被視為不潔不祥之人,在祭祀中被架空,“微雪點(diǎn)點(diǎn)的下來(lái)了”,這是悲情的預(yù)兆,在這點(diǎn)點(diǎn)微雪之前,祥林嫂已經(jīng)歷了一番夫死改嫁、出逃被抓、新家庭毀滅的悲劇,當(dāng)雪花再度落下,柳媽和東家的避諱從精神處向她施壓,神明將她的靈魂叛入地獄,肉身還要受兩任丈夫的分割。微雪下落是祥林嫂走向末路的鋪墊,預(yù)示了其承受神權(quán)壓迫、走向精神危機(jī)的命運(yùn)走向。第二次下雪是在“我”遇見(jiàn)形容枯槁的祥林嫂后感到不安的下午,大雪紛飛,“將魯鎮(zhèn)亂成一團(tuán)遭”,雪勢(shì)加大暗示著事態(tài)進(jìn)一步惡化。最后,“我”聽(tīng)到了祥林嫂死去的噩耗,雪落在“積得厚厚的雪褥上面”,雪花落地細(xì)微的聲響仿佛就是這位舊農(nóng)村婦女落地成塵的一點(diǎn)波瀾。祥林嫂數(shù)次命運(yùn)的轉(zhuǎn)折都伴隨著雪意象的出場(chǎng),并且,當(dāng)雪勢(shì)越來(lái)越大,祥林嫂的生存狀況就越來(lái)越糟糕。如果說(shuō)祥林嫂逐漸隕落的命運(yùn)是《祝福》里的明線,那么雪便成為故事發(fā)展的暗線,風(fēng)景與人物之間是存在對(duì)應(yīng)關(guān)系的。
同樣的線索作用也表現(xiàn)在《在酒樓上》里,在這場(chǎng)感傷的重逢中,雪景伴隨始終:“我”踏進(jìn)酒樓,微雪已飛舞起來(lái);呂緯甫的到來(lái)讓樓上熱鬧起來(lái),“雪也越加紛紛地下”,伴著廢園的雪花,他向“我”講述近況;二人別后,“我”獨(dú)自朝旅館的方向走去,走進(jìn)了密雪織就的羅網(wǎng)。雪景閃爍在敘事的節(jié)點(diǎn),不僅烘托抒情氣氛,也連綴情節(jié)片段,控制著敘事節(jié)奏。
(二)雪與情節(jié)模式建構(gòu)
作為線索作用的外延,反復(fù)出場(chǎng)的意象通常與小說(shuō)特殊的情節(jié)模式相關(guān)聯(lián)。在魯迅筆下,雪意象就參與著其小說(shuō)經(jīng)典情節(jié)模式“封套結(jié)構(gòu)”的建構(gòu)。封套結(jié)構(gòu)又稱(chēng)圓形結(jié)構(gòu),是指“把重復(fù)的因素放在一個(gè)故事或一個(gè)情節(jié)的開(kāi)頭和末尾,使這個(gè)重復(fù)因素起著戲劇開(kāi)場(chǎng)和結(jié)束時(shí)的幕布作用。”[1]這是重復(fù)手法的一種特殊應(yīng)用,在此種結(jié)構(gòu)中,人物的行為與思想路徑構(gòu)成一個(gè)圓圈的循環(huán)。封套結(jié)構(gòu)不僅具有結(jié)構(gòu)創(chuàng)新的意味,更構(gòu)成豐富的意義指涉。
在《祝福》中,故事的敘述在微雪中拉開(kāi)序幕,交代了祥林嫂人生悲劇發(fā)生的背景,烘托了“我”歸鄉(xiāng)的沉悶心緒,而在結(jié)尾,團(tuán)團(tuán)飛舞的雪花為祥林嫂的人生畫(huà)上句點(diǎn),也終結(jié)了“我”的歸鄉(xiāng)旅程,首尾呼應(yīng)間,從離去、歸來(lái)到再離去,“我”對(duì)故鄉(xiāng)人事的懷戀心態(tài)也變換為“哀其不幸,怒其不爭(zhēng)”的批判情緒,死而不僵的舊文化殘影被封套在一冬的雪景里,加重了“我”與回不去的故鄉(xiāng)、融不進(jìn)的舊人之間的隔膜感。《在酒樓上》中,故人的重逢同樣是伴著深冬大雪開(kāi)始的,在結(jié)尾的密雪和寒風(fēng)中兩人又各奔殊途,構(gòu)成一個(gè)圓圈的循環(huán),暗示著呂緯甫與周遭環(huán)境對(duì)抗而終究敵不過(guò)強(qiáng)大舊勢(shì)力、回到原點(diǎn)的革命軌跡,也映襯著“我”掙扎于希望與絕望的輪回、對(duì)抗虛無(wú)的決絕姿態(tài),深化了先驅(qū)者的寂寞形象。
三、詩(shī)化小說(shuō):雪與文體創(chuàng)造
詩(shī)化小說(shuō)是詩(shī)歌藝術(shù)形式向小說(shuō)滲透所形成的一種文體,在詩(shī)化小說(shuō)中,“作者需要利用詩(shī)歌的特色手段來(lái)替換或轉(zhuǎn)化散文性敘事的形式技巧”[2][4]。
(一)雪與敘事的象征化
“意象的運(yùn)用,是加強(qiáng)敘事作品詩(shī)化程度的一種重要手段。”[3]受安特萊夫的影響,魯迅的小說(shuō)借助意象和隱喻,調(diào)和著象征主義與寫(xiě)實(shí)主義,染上濃郁的詩(shī)化氣質(zhì)。
《在酒樓上》里關(guān)于“廢園茶花”的描寫(xiě)是這方面的典型。小說(shuō)對(duì)廢園的描寫(xiě)共有三次,以第一次“我”在酒樓上獨(dú)自賞雪最有代表性——幾株老梅斗雪開(kāi)著繁花,不以深冬為意,山茶樹(shù)在雪中花開(kāi)如火,“憤怒而且傲慢,如蔑視游人的甘心于遠(yuǎn)行”。這段廢園景象化用了 “紅梅傲雪” 的古典意境,又融入了啟蒙與斗爭(zhēng)的時(shí)代主題。紅梅和茶花是啟蒙先驅(qū)的化身,它們?cè)谏疃笱├锖杖痪`放、明艷如火,隱喻革命戰(zhàn)士面對(duì)黑暗社會(huì)毫不屈服,甘于遠(yuǎn)行的游人則暗示著先驅(qū)者的孤獨(dú)——啟蒙對(duì)象對(duì)于被啟蒙的態(tài)度是冷漠且排拒的。在小說(shuō)中,大雪、老梅、茶花、游人統(tǒng)一于廢園的意象系統(tǒng),營(yíng)造出紅梅傲霜斗雪的審美意境,成為聯(lián)結(jié)主體與客體的秘密通道。
(二)雪與行文的音樂(lè)化
“節(jié)奏作為詩(shī)歌的最原始的結(jié)構(gòu)因素,是小說(shuō)音樂(lè)化的先決條件”。節(jié)奏的本質(zhì)是重復(fù),密集性的重復(fù)總能賦予小說(shuō)集中的主題動(dòng)機(jī)、強(qiáng)烈的抒情效果、多樣的節(jié)奏形式,“通過(guò)意象的重復(fù),詩(shī)更接近音樂(lè)。”
在《祝福》中,雪作為一條暗線,映襯著祥林嫂的命運(yùn)軌跡,隨著雪勢(shì)漸盛,主人公的命運(yùn)漸衰。小說(shuō)如同一曲主調(diào)音樂(lè),雪意象在其中充當(dāng)和聲,處于襯托地位,或增強(qiáng)主調(diào)的氣勢(shì),或削弱主調(diào)的回響,使樂(lè)章更富節(jié)奏感。《在酒樓上》《孤獨(dú)者》表面上采用與《故鄉(xiāng)》《祝福》相似的“故人重逢”情節(jié),實(shí)則相去甚遠(yuǎn)。《故鄉(xiāng)》和《祝福》中的“我”獨(dú)處于主體位置,相對(duì)于閏土、鄉(xiāng)民和祥林嫂,“我”在知識(shí)和思想上占有絕對(duì)優(yōu)勢(shì),重逢故事是一場(chǎng)啟蒙者對(duì)于被啟蒙者的獨(dú)白。而《在酒樓上》與《孤獨(dú)者》里的“故人”不過(guò)是自我的分身與異化,兩個(gè)主體在平等的地位中進(jìn)行對(duì)話。如果把前者看作獨(dú)白型的主調(diào)音樂(lè),后者則更像是對(duì)話體的復(fù)調(diào)音樂(lè),雪意象則聯(lián)結(jié)起不同主體的感覺(jué),使二者相互對(duì)應(yīng)、產(chǎn)生對(duì)話,由此,小說(shuō)的復(fù)調(diào)形式得到更充分的體現(xiàn)。在《在酒樓上》的開(kāi)頭有一段“我”對(duì)故鄉(xiāng)的“雪”的評(píng)價(jià)——“我這時(shí)又忽然想到這里積雪的滋潤(rùn),著物不去,晶瑩有光,不比朔雪的粉一般干”,爾后呂緯甫也有一句相似的話——“積雪里會(huì)有花,雪地下會(huì)不凍”,這于返鄉(xiāng)遷葬事件中宕開(kāi)的一筆,或可看作是對(duì)“我”的看法的回響與反射,雪花成為雙聲部敘述的聯(lián)結(jié)者。在《孤獨(dú)者》中有類(lèi)似的安排:“我”看著窗外大雪紛飛便想起了魏連殳,結(jié)果當(dāng)晚就收到了他的來(lái)信,信的開(kāi)頭正是“我這里下大雪了。你那里怎樣”,這種自然環(huán)境的呼應(yīng)收到了蒙太奇的效果,將受到時(shí)空阻隔的兩個(gè)主體牽連在一起,使得附于信件的精神交流順利進(jìn)行,一如兩支旋律的匯合。如是,雪花的重復(fù)促進(jìn)了魯迅小說(shuō)音樂(lè)性的發(fā)揮,加強(qiáng)其詩(shī)化特質(zhì)。
論及《吶喊》《彷徨》的意象系統(tǒng),研究者多關(guān)注作為社會(huì)文化符號(hào)被創(chuàng)造并在中國(guó)文學(xué)現(xiàn)代化進(jìn)程中經(jīng)典化的意象,而甚少觀照自然景觀意象,但細(xì)致體察魯迅小說(shuō)中的這些“風(fēng)景”,我們發(fā)現(xiàn),它們都或隱或現(xiàn)參與著作品內(nèi)容與藝術(shù)的建構(gòu),這是有待繼續(xù)發(fā)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