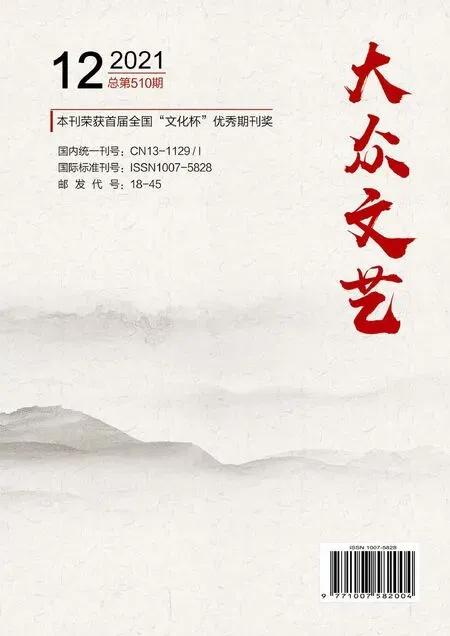淺析《日瓦戈醫生》中的人道主義思想
(遼寧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遼寧大連 116029)
鮑里斯·列昂尼多維奇·帕斯捷爾納克是20世紀俄羅斯著名作家、詩人,憑借小說《日瓦戈醫生》榮獲1958年諾貝爾文學獎,以表彰他“對現代抒情詩歌以及俄羅斯小說偉大傳統做出的杰出貢獻。”[1]小說《日瓦戈醫生》在廣闊的歷史背景下展示了知識分子多舛的命運,整部作品雖充滿了悲愴的氣氛,卻飽含濃厚的人道主義思想。
人道主義思想源于古希臘羅馬,C.弗蘭克曾說:“古希臘羅馬世界就是‘人道主義’的真正故鄉,是最早認識并以高尚形式逐漸闡明人的尊嚴、人形象之美和意義的地方。”[2]但是隨著社會的發展,人道主義逐漸扭曲,神權淹沒了人權,人的價值受到貶低。文藝復興時期的人道主義正是在與宗教哲學的斗爭中發展起來的,它提倡以人為中心,反對教會獨斷,強調個性自由。18世紀法國啟蒙運動時期的人道主義則從理性出發,倡導“自然法”“自由、平等、博愛”等觀點。19到20世紀,人道主義思想在俄羅斯蓬勃發展,俄羅斯思想家們對傳統的人道主義思想進行了深刻地反省與思考,并與本土宗教哲學相結合,將“人”視為社會生活領域的最高價值,提出了“新精神哲學”的人道主義,為人道主義思想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在小說《日瓦戈醫生》中,主人公日瓦戈和拉拉正是這種人道主義思想的代表,可以說人道主義是潛在的一條線索,貫穿于整部作品之中,本文將分別闡述日瓦戈和拉拉身上的人道主義思想。
一、日瓦戈身上的人道主義思想
鮑里斯·帕斯捷爾納克出生于一個猶太家庭,他雖然不是基督教徒,卻深受基督教思想的影響。作家晚年在與來訪者的談話中說道:“基督從歷史的遠處走向我們……全部新的歷史從基督福音開始……”[3]可以說基督教義中的仁慈博愛、道德完善、人道主義等觀念對作家生活觀、歷史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以至于作者筆下的人物或多或少都帶有人道主義的思想。在小說《日瓦戈醫生》中,日瓦戈年少喪母,一直與舅舅生活在一起,舅舅是一個還俗的神甫,認為人一定要有信仰,才能有所成就。在《福音書》中,信仰的基本要素之一就是:“愛你的鄰人,這是生命活力的最高表現。這種愛一旦充滿了人的心靈以后,必定會洋溢著泛愛眾人的情感。”[4]在這種潛移默化的影響下,日瓦戈逐漸成長為一個善良、具有博愛之心的人,他心懷憐憫,心系社會,雖然喜歡歷史與藝術,但是為了造福人類,他毫不猶豫地選擇了醫學專業,從而治病救人,為社會做出貢獻。正是這種人道主義精神使日瓦戈對周圍事物始終懷有善意,他愛護家庭,一直為了家庭生計而四處奔波,試圖用自己的努力使妻兒過上安穩的生活;他待人真誠,哪怕在困難時期也同朋友、鄰人分享自己的食物與住處。而人道主義又是一種不分階級的、廣泛的、無私的愛,既能給予親人、朋友、陌生人,也能給予不同階級立場的某些人,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猶太人備受排斥,可在陌生的猶太老人遭受戲弄時,日瓦戈依然挺身出,及時出言制止,解救了老人。在戰場上,日瓦戈的人道主義思想更是體現得淋漓盡致,他難以理解殺戮的意義,排斥新式武器所造成的恐怖景象,但是卻無力改變這種現狀,只能盡力做好救死扶傷的工作。在游擊隊期間,日瓦戈的內心充滿矛盾,他討厭喋喋不休的游擊隊長,可是當游擊隊長的性命受到威脅時,他卻試圖救他;而謀劃者面臨槍決時,他又感到于心不忍;對于敵方陣營的一些白軍他也同樣懷有善意,當他發現白軍的許多知識分子單純的出于對祖國的熱愛才奔赴疆場時,同情之心油然而生,暗中救下被他誤傷的白軍青年,自己則設法從隊伍中離開,從此遠離戰爭與殺戮。
日瓦戈一生追求自由,渴望人格獨立,他在面對任何新鮮事物時,都不隨波逐流,而是聽從自己的內心,保持人格的獨立。日瓦戈發現舊社會存在著種種壓迫與奴役,他渴望一種新的變革能徹底改變這一切。十月革命的勝利令他欣喜若狂,認為這是“一次絕妙的外科手術!一下子就出色地把發臭的舊膿包全切除了!”[5]可是他期待的自由并沒有到來,人們的思想依舊陳腐,且被條條框框所禁錮。為了維護內心的自由,日瓦戈對革命一直保持著冷靜的態度,他沒有加入任何社會團體,而是選擇回歸田園,過自食其力的生活。盡管日瓦戈對于社會現狀有所不滿,但是人道主義思想卻使他難以用暴力進行反抗,只能靠保持內心的自由與思想的獨立與周圍的現實相抗衡。他熱愛自然,常常引用詩句來表達對自然的贊嘆:“多美的夏季,多美的夏季!這真是像魔術般神奇。我問你,他那個樣子,是怎么從藍天中變出的?”[6]日瓦戈熱愛生活,善于觀察,面對妻子冬妮亞的細微變化,他敏銳地察覺出她已經孕育了新的生命,并在隨筆中記下了自己對生命的理解與感悟,“任何懷孕都是純潔的,而圣母無原罪的教條表明了一切母道的觀念。”[7]在日常勞動之余,日瓦戈時常同家人一起朗誦經典作品,探討藝術的內涵和創作的真諦,他認為藝術是“一種適用于作品的力量,一種在創作中發現的真理”[8],生活和工作只是自己個人的事,創作不應一味地使用“未來的黎明”“人類的火炬手”[9]這類夸大的辭藻,而應當從身邊的小事入手,將日常生活中的所思所想轉化為文字,從而引起讀者的共鳴。在瓦雷金諾的那段日子里,日瓦戈秉燭夜書,潛心創作,靈感迸發,創作“拉拉”之歌。盡管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日瓦戈難以在現實生活中獲得真正的自由,可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他對自然的熱愛、對生命的探索、對藝術的思考又何嘗不是一種靈魂的自由呢。
二、拉拉身上的人道主義思想
拉拉是一個極具魅力的女人,她同日瓦戈一樣,一生都在追求個性獨立與精神自由。她曾身負枷鎖,但卻不向命運屈服,而是竭力改變自己的命運。少女時代的拉拉在科馬羅夫斯基的引誘下走向墮落,這使她陷入焦慮與迷茫,但是她并沒有就此沉淪,而是一直依靠不懈的努力,爭取獨立自由的生活。盡管拉拉身陷泥潭,她依然保持著善良的本心,常常用薪水暗中接濟男友帕沙,以減輕他的負擔。可是科馬羅夫斯基卻試圖利用她的弟弟讓拉拉重回自己身邊,忍無可忍的拉拉在圣誕舞會上朝科馬羅夫斯基開槍,雖然沒有射中,但是這一槍卻給了她擺脫控制,追求自由的勇氣。拉拉最終決定嫁給聰明勤奮的帕沙,在新婚之夜,拉拉向他坦白了自己的曾經,可是這段不堪回首的過去卻成了他們婚姻的障礙,帕沙漸漸懷疑“她愛的不是他,而是對他的一種神圣使命,是體現在他身上她的一種功勛。”[10]于是他自愿參軍離開了妻子女兒。帕沙的離開使拉拉備受打擊,但是她并沒有向命運低頭,她努力學習醫學知識,成為一名護士,去前線尋找丈夫。在那里,拉拉與日瓦戈相遇了。日瓦戈理解她的苦難、欣賞她的性格,而拉拉也被日瓦戈的思想與才華所吸引,他們惺惺相惜,都厭惡戰爭,反對暴力,追尋思想自由、人格獨立,不喜歡“當代人那種機械性的興奮、大喊大叫的激昂,還有那種致命的平庸”[11],正是這種心靈上的高度契合使二人慢慢地走到了一起。拉拉激發了日瓦戈的創作激情,日瓦戈也使她逐漸擺脫了過去的陰影,暫時過上了夢想中獨立自由的生活,可以說他們的愛情是“不可撼動、與最完美的精神相聯系的愛情”[12]。拉拉并不完美,她年輕時的虛榮與輕浮使她落入科馬羅夫斯基的魔爪,讓她的生活倍受磨難,可是她勤勞善良、堅強勇敢,從不向命運低頭,在社會動蕩的年代依然追求思想自由和人格獨立,正如埃德蒙·威爾遜所說,拉拉是俄羅斯文化女神的象征。[13]
綜上所述,《日瓦戈醫生》是一部史詩性的作品,它的問世被稱為是“人類文學史和道德史上的重要事件”。[14]作者歷時十年,在廣闊的時空背景下再現了20世紀俄羅斯罕見的社會變革,描繪了知識分子在歷史浪潮中坎坷的悲慘命運,刻畫了他們的信仰、追求與迷茫。主人公日瓦戈和拉拉是作者理想化的人道主義代表,他們真誠善良,雖然置身于社會動蕩的年代,可是不管經歷多少波折,他們都敢于與時代抗爭,固守自己的道德準則,維持精神的自由與人格的獨立。《日瓦戈醫生》是一部帶有自傳色彩的作品,日瓦戈的悲劇既是個人的悲劇也是時代的悲劇,它的形成既有社會因素也有思想因素,帕斯捷爾納克對此進行了深刻的探索與反思,他控訴暴力,呼吁人道主義的自由、平等、博愛。可以說,作者對歷史的反思和人道主義的探索值得我們思考、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