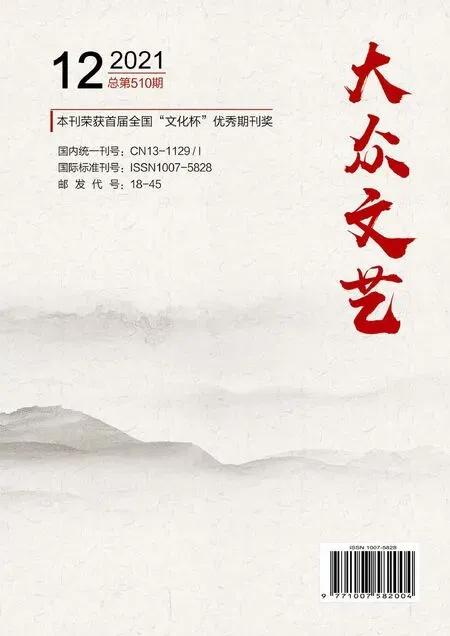中國(guó)戲曲與西方戲劇理論在置景攝影中的運(yùn)用
——夢(mèng)境對(duì)創(chuàng)作的啟發(fā)
(中國(guó)傳媒大學(xué)南廣學(xué)院 攝影學(xué)院,江蘇南京 211172)
戲曲藝術(shù)家時(shí)常用“置景”手法組織舞臺(tái)空間。例如:將舞臺(tái)當(dāng)中的道具、戲劇、服裝和聲樂(lè),結(jié)合聲光場(chǎng)景轉(zhuǎn)換和劇情表現(xiàn)組織自己的舞臺(tái)作品。在突出主題的同時(shí),畫面中出現(xiàn)的元素也能夠有效被使用。主觀意識(shí)對(duì)多重觀念進(jìn)行蒙太奇式的再加工,呈現(xiàn)出作品自身的藝術(shù)真實(shí)美。
一、中國(guó)戲曲的“虛擬性”在置景攝影中的體現(xiàn)
作為流傳歷史悠久的中國(guó)戲曲,其舞臺(tái)人物形貌裝束與景物造型與西方戲劇大量設(shè)置道具裝置在舞臺(tái)上不同。中國(guó)戲曲的置景造型通常比較簡(jiǎn)化。人物臺(tái)詞上追求極致,形式表現(xiàn)上以“一桌二椅”為代表的戲劇演出環(huán)境,或在空無(wú)一物的舞臺(tái)中依靠人物造型穿戴的程式,引導(dǎo)欣賞者進(jìn)入戲劇情境中。京劇《打漁殺家》里原梁山英雄蕭恩和女兒出場(chǎng),父女手中握有船槳。對(duì)于觀眾,這就暗示著他們已經(jīng)站在大船上了。在一些置景攝影中,被攝主體手拿著一塊手表就代表著生命的流逝、陰暗沉郁的背景就能暗示人物所處環(huán)境的壓抑氣氛。戲曲舞臺(tái)上“馬鞭船槳”“云片水旗”“文房四寶”等,用最簡(jiǎn)潔的呈現(xiàn)手段再現(xiàn)劇本,重現(xiàn)千軍萬(wàn)馬奔流而過(guò)的宏大場(chǎng)景。在京劇《一夜須白》中,演員在臺(tái)上快速來(lái)回走動(dòng)幾次,代表了戲劇空間中幾百里空間上移動(dòng)。在西方戲劇中,場(chǎng)景的構(gòu)建需要花費(fèi)大量資金以增強(qiáng)舞臺(tái)效果,依托物質(zhì)疊加呈現(xiàn)的方式對(duì)于表現(xiàn)中國(guó)戲曲實(shí)不相符,這種組合場(chǎng)景的方式常常被運(yùn)用到“置景式”攝影創(chuàng)作流程中。西方戲劇的外向張揚(yáng)、中國(guó)戲曲的含蓄內(nèi)斂,因虛擬性呈現(xiàn)方式不同而相互區(qū)別。通過(guò)戲曲的“虛擬性”維持作品臺(tái)下欣賞者與舞臺(tái)之間的審美情緒,過(guò)程中依賴戲劇“劇場(chǎng)性”“假定性”的審美心理,將有限地表演空間由劣勢(shì)轉(zhuǎn)化為優(yōu)勢(shì)。
二、“劇場(chǎng)性”“假定性”還原置景攝影創(chuàng)作初心
劇場(chǎng)性——維持觀者審美情緒,使舞臺(tái)演出與觀眾之間形成一種密切地觀演關(guān)系。各種道具、服裝、出場(chǎng)音樂(lè)配合,舞臺(tái)和觀眾間形成一種觀演空間。使觀眾和演員間達(dá)成“接受假定性呈現(xiàn)”的高度默契,在有限地活動(dòng)空間里將整個(gè)宇宙囊括其中,充分發(fā)揮“置景式”手法能夠在有限空間中的優(yōu)勢(shì)。假定性——營(yíng)造置景情境的真實(shí)感,非現(xiàn)實(shí)的戲劇情節(jié)借助假定性的契約,使置景舞臺(tái)中的元素能以觀眾可接受的方式呈現(xiàn)。通過(guò)情節(jié)與戲劇沖突的引導(dǎo),完成觀眾與創(chuàng)作者審美欣賞的戲劇心理體驗(yàn),置景攝影可以借助“假定性”戲劇理念打破創(chuàng)作者與欣賞者間的觀念壁壘。同時(shí),借助“貧困戲劇”理念在置景創(chuàng)作中劃清作品與觀眾間觀念壁壘的底限,即:以“置景”方法創(chuàng)作出的作品歸屬于可被進(jìn)行藝術(shù)欣賞的范疇。界定清晰戲劇上的最低審美界限,才能在后期創(chuàng)作方面守住不離本原、張弛有度的初心。戲劇《騎馬下海的人》中寡婦毛麗亞在明知男人出海即赴死的宿命,強(qiáng)忍內(nèi)心悲痛送小兒子出海踏上沒(méi)有歸程的旅途。舞臺(tái)上的演員拿著的是簡(jiǎn)陋的道具、紙片做的馬兒,這些道具物件不會(huì)影響到觀賞者將情緒投入進(jìn)劇情的發(fā)展中。欣賞前充分了解過(guò)作者的創(chuàng)作時(shí)代,能更好地在演出過(guò)程中與舞臺(tái)上的演員形成固定的觀演默契。
三、置景主觀意識(shí)在戲劇中的使用
同戲劇中或多或少在傳達(dá)的寓意上類似,攝影創(chuàng)作在平面介質(zhì)上呈現(xiàn)出的是持久的、永恒的、創(chuàng)造性的意志表現(xiàn)。通過(guò)激發(fā)創(chuàng)作者對(duì)生命本真的原始尋求,主觀意志的得以真實(shí)體現(xiàn)。將置景創(chuàng)作意識(shí)加以藝術(shù)工作者自身,挖掘其對(duì)肢體、器官、判斷力及情緒的調(diào)動(dòng),更好地把握住感性思維中置景意識(shí)以及審美規(guī)律。
置景方法的產(chǎn)生也是創(chuàng)作者對(duì)個(gè)人審美要求的再現(xiàn)。為了使肉體有限的精神得到持久的滿足,必須將其通過(guò)各種媒介轉(zhuǎn)嫁于某一符號(hào)上。對(duì)于審美的要求不斷在實(shí)現(xiàn)滿足的過(guò)程中提出更高的要求,當(dāng)超越客觀現(xiàn)實(shí)上限再現(xiàn)力時(shí)。例如,在置景攝影創(chuàng)作中加入一種不能被直接再現(xiàn)的觀念時(shí),就要認(rèn)識(shí)到意識(shí)思維在把握神秘且琢磨不定情況時(shí)的優(yōu)勢(shì)。用意識(shí)驅(qū)動(dòng)創(chuàng)作者調(diào)配現(xiàn)實(shí)中賦予意義的建筑、情境、人物間的表情、角色間矛盾沖突,共同置于同一時(shí)間、同一情境中。綜合以上呈現(xiàn)出創(chuàng)作者在道具、物件等表象,以便于從更深層次抒發(fā)生命意志方面的理性情緒。置景意識(shí)也從側(cè)面體現(xiàn)出藝術(shù)工作者對(duì)自我意識(shí)的掌控能力。與客觀世界物語(yǔ)對(duì)話,對(duì)主觀意識(shí)掌控能力越牢固就越能從復(fù)雜瑣碎的物件中提煉出本質(zhì)規(guī)律,把握住生活的本質(zhì)就更能提升創(chuàng)作者自身對(duì)現(xiàn)實(shí)之于自身深層意識(shí)的再現(xiàn)能力。
四、日有所思、夜有所夢(mèng)——在夢(mèng)境構(gòu)建置景攝影情境
在人的做夢(mèng)過(guò)程中,大腦的特殊機(jī)能會(huì)將清醒狀態(tài)下被壓抑的意識(shí)與觀念進(jìn)行重組,白天被偏移的情緒重新在頭腦里重新再現(xiàn)。做夢(mèng)過(guò)程中大腦自主降低了主觀上的偏見,放下被外在負(fù)擔(dān)壓力所束縛的思緒。以一種更為宏觀的視角審視個(gè)人內(nèi)心世界的多樣性,清醒時(shí)被理智束縛的思維慣性可以在夢(mèng)的重構(gòu)中得以修正。更快速地進(jìn)入審美情境。在日常生活中,有太多的事情對(duì)創(chuàng)作者的心理產(chǎn)生煩惱或者困擾,以至影響正常生活狀態(tài)。每當(dāng)這時(shí)就預(yù)示著大腦已經(jīng)進(jìn)入疲憊狀態(tài),需要一段充分地休息使白天被社會(huì)壓力禁錮的思想得以解放在夢(mèng)境當(dāng)中。同時(shí),大腦也會(huì)充分利用這段時(shí)間進(jìn)行修整以備第二天清醒時(shí)繼續(xù)使用,這也就是說(shuō)做夢(mèng)或者說(shuō)睡覺的這個(gè)過(guò)程是能夠?qū)﹂L(zhǎng)期的藝術(shù)創(chuàng)作提供一個(gè)長(zhǎng)期可靠的動(dòng)力支撐。在進(jìn)行一幅作品創(chuàng)作前,經(jīng)常碰到一個(gè)很好的思路指導(dǎo)創(chuàng)作者進(jìn)行初步構(gòu)圖、并規(guī)劃的創(chuàng)作路徑,但創(chuàng)作者經(jīng)常會(huì)收到社會(huì)的壓力阻礙創(chuàng)作者無(wú)法沉下心來(lái)投入單純的創(chuàng)作情境中。同時(shí),這些心情會(huì)改變創(chuàng)作者對(duì)預(yù)期色調(diào)與明暗的運(yùn)用、影響調(diào)整照片中道具的擺放、一組照片之間的戲劇性置景的連接,還有情境中出現(xiàn)的人物角色之間統(tǒng)一。
在夢(mèng)境中深度睡眠(快速眼動(dòng)時(shí)期),也是大腦對(duì)于創(chuàng)造力完全開放的最佳窗口時(shí)期,但這個(gè)時(shí)期并不能被清醒狀態(tài)的理性所干擾,做夢(mèng)時(shí)無(wú)法被其他人的思想接入。做夢(mèng)的片段如同轉(zhuǎn)瞬即逝的蒙太奇畫面,夢(mèng)境中美妙的幻境在夢(mèng)醒后快速褪去鮮亮的色彩。而有一種可以控制夢(mèng)的方法可以將做夢(mèng)的過(guò)程延續(xù),那就是日常人們所說(shuō)的“清醒夢(mèng)”。清醒狀態(tài)和夢(mèng)的狀態(tài)相互交織,就能夠獲得自由控制夢(mèng)的能力,此時(shí)的狀態(tài)就是我想要達(dá)到置景手法中創(chuàng)作審美情境與戲劇性結(jié)合的圖式。戲劇性與夢(mèng)境的結(jié)合,進(jìn)一步激發(fā)大腦創(chuàng)造力夢(mèng)境。將過(guò)去未來(lái)你所遇見的人或發(fā)生的事、看見過(guò)的電影、難以覺察的細(xì)節(jié),在一晚上片刻地夢(mèng)中同時(shí)進(jìn)行分解與重構(gòu)。夢(mèng)中發(fā)生的情境往往都是受潛意識(shí)的驅(qū)動(dòng)下前進(jìn),這就像夢(mèng)就像做過(guò)玩游戲一樣。白天的生活往往是三點(diǎn)一線的,在指的時(shí)間規(guī)定的地點(diǎn)干指定的事。但是夢(mèng)中,人沒(méi)有辦法預(yù)見會(huì)夢(mèng)見什么。從天而降的任務(wù)在夢(mèng)中亟待完成,這種緊迫的任務(wù)會(huì)激發(fā)個(gè)人的創(chuàng)造力,發(fā)揮主觀能動(dòng)性去攻克它。完成的那一刻,就是對(duì)于之前積壓情緒的釋放,就像電腦關(guān)機(jī)前清空內(nèi)存一樣。只有把白天復(fù)雜的解決不了的進(jìn)行清空,用積極的心態(tài)去面對(duì)現(xiàn)實(shí)的生活,才能將大量空閑的心境預(yù)留給白天創(chuàng)作過(guò)程。
熬夜影響創(chuàng)造力發(fā)揮。通常情況下,缺乏睡眠的人往往長(zhǎng)時(shí)間工作下來(lái)會(huì)積壓大量抑郁的心情,陷入煩躁不安的情緒中,這都是未能發(fā)揮大腦來(lái)進(jìn)行有效代償?shù)谋憩F(xiàn)。經(jīng)常因業(yè)務(wù)犧牲夜間睡眠熬夜的人,長(zhǎng)此以往在工作當(dāng)中會(huì)缺失部分創(chuàng)造力,這些都是人腦疲于應(yīng)對(duì)長(zhǎng)時(shí)間工作而做出的負(fù)面反應(yīng),被動(dòng)的應(yīng)對(duì)方式從負(fù)面反證了夢(mèng)對(duì)人的積極作用。夢(mèng)中最容易觸發(fā)的事情往往與本我相對(duì)應(yīng)。意識(shí)源自頭腦的原始機(jī)能,基于人本身的原始欲望。對(duì)于人性的沖動(dòng),還有被日常生活所壓抑住的、由無(wú)數(shù)個(gè)不由主觀意識(shí)所支配的狀態(tài),這種由夢(mèng)中流淌的連續(xù)性片段構(gòu)成“意識(shí)流”。這種連續(xù)性的意識(shí)狀態(tài)若能用到“置景”創(chuàng)作攝影中。即:在創(chuàng)作前閉眼小憩幾分鐘,將生活當(dāng)中的片段重新在休息時(shí)進(jìn)行拼接和構(gòu)成,那么之后表現(xiàn)的內(nèi)容也會(huì)呈現(xiàn)出一種類似于夢(mèng)境的狀態(tài),并引導(dǎo)觀賞者進(jìn)入一種意識(shí)流動(dòng)的狀態(tài),這便是用“意識(shí)流”對(duì)流動(dòng)意識(shí)做出的闡釋,進(jìn)而可以用到攝影藝術(shù)的創(chuàng)作中,結(jié)合置景后期手法集中表達(dá)作品中突顯的主題思想。“三重人格理論”使創(chuàng)作接近藝術(shù)真實(shí),在前期的準(zhǔn)備當(dāng)中將“本我”觀念融入創(chuàng)作的主旨中,用“自我”去約束創(chuàng)作過(guò)程當(dāng)中所要主觀控制光線的明暗層次以及畫面構(gòu)圖的整理,用“超我”觸及創(chuàng)作上限。結(jié)合該理論創(chuàng)作出的攝影作品雖脫離了真實(shí)性,但更接近藝術(shù)的真實(shí)。找到了可替代性對(duì)象的同時(shí),更能替代性滿足創(chuàng)作者或欣賞者對(duì)于某一抽象觀念的真實(shí)再現(xiàn)。
五、結(jié)語(yǔ)
直覺引導(dǎo)下的審美情緒易將夢(mèng)境中人與社會(huì)的矛盾、人與物之間的沖突脫離現(xiàn)實(shí)。此時(shí),需從人性的本性去出發(fā),即:從原始生命的沖動(dòng)將自己設(shè)身處地融入作品當(dāng)中去感受,由內(nèi)向外去體驗(yàn),將戲曲“虛擬性”的再現(xiàn)與西方戲劇“劇場(chǎng)性”“假定性”的觀演審美情緒融入置景攝影創(chuàng)作中,追尋戲劇理論與夢(mèng)境結(jié)合的藝術(shù)真實(shí)美。用純粹的直覺就可以完全把握對(duì)象作品的本質(zhì),不需要通過(guò)理性的規(guī)律去結(jié)構(gòu)分析,用夢(mèng)境對(duì)攝影創(chuàng)作的啟發(fā)尋找當(dāng)代攝影置景的新路徑。同時(shí),借助夢(mèng)境對(duì)現(xiàn)實(shí)創(chuàng)作中的道具、物象進(jìn)一步解構(gòu)和重組的表達(dá)方法。既能夠使置景攝影作品引發(fā)一種“延綿柔長(zhǎng)”的情緒,又能夠在形式上產(chǎn)生綿延恒久的厚重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