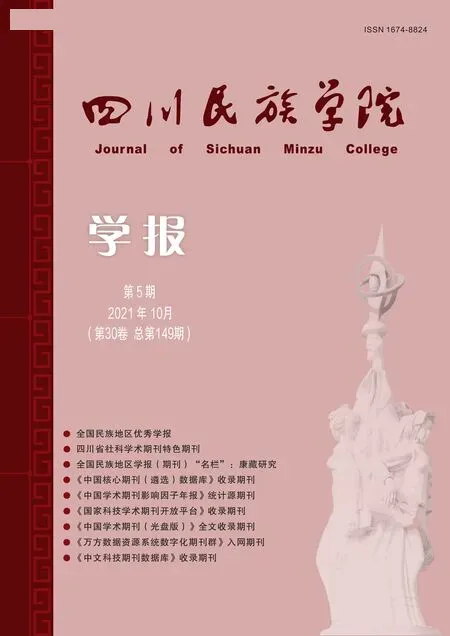戲曲音樂向交響化方向轉變的創作思維分析
汪伊珺
(安徽藝術學院,安徽 合肥 230000)
戲曲音樂作為我國民族民間藝術寶庫中最重要的內容之一,在中國乃至世界都占有極高地位。它是在人民大眾勞動中產生和發展起來的,具有極強的生命律動和群體形象。將其和現代交響樂手法結合起來,既是戲曲音樂的創新發展,更是音樂文化進步的重要體現。對于如何在交響音樂中弘揚民族精神,鐫刻中國印記,當代中國作曲家在過去數十年的創作實踐中已經交付了大量極具特色的答卷,但如何在借鑒交響音樂語言的基礎上,從更深層面展現和揭示中國戲曲音樂的風格韻致就成為了當前亟待解決的重要問題。
一、戲曲音樂和交響樂的聯系性
交響是一種綜合性概念,從內部來看,它是在西方多聲部復調作曲理論下形成的一種音響形態,詮釋的是具有西方調性與調式的音樂;從外部來看,它是多類西洋樂器依照相應的數量、形制和音色差異融合在一起的配器組合。將其適當融入戲曲音樂,是戲曲在“古為今用”的方針下進行取長補短。
而中國戲曲音樂和“純”音樂有所不同,它必須和其他藝術手段結合起來推動故事情節發展,烘托舞臺氛圍,塑造人物形象,完成音樂戲劇化的相關任務[1],因此具有一定戲劇性、敘事性和抒情性,特別是戲劇性在一些傳統劇目當中占有極高地位。從這一點來看,它與西方交響樂之間是存在共性的。西方交響樂源于歌劇序曲,從戲劇中衍生而來,因此中國戲曲音樂和西方交響樂間就出現了某種關聯性,給兩者的結合找到了切入點。比如秦腔中的滾白語言最典型的特征就是把唱和白結合在一起,半念半唱、半訴半哭,沒有較為規整的節奏,口語味比較濃厚,極具生活感。因此這種不規整的節奏和西洋歌劇中詠嘆調的表演形式具有相似性,更能夠展現人物的理性失控,非常適合通過交響樂進行處理。
二、戲曲音樂交響化的發展原因
一方面,傳統戲曲音樂不免受到當代技術及審美變革的影響。長期發展以來由于戲曲傳承以師承方式為主,即便是外界音樂環境產生重大變革,戲曲音樂對其吸收也是極為審慎和有限的。在各項技術文化飛速發展的今天,即便戲曲音樂始終在盡全力保持傳統,但在周圍所有藝術形式都飛速轉變的情況下,戲曲音樂其定力開始有所動搖。
另一方面,傳統戲曲音樂地位受到挑戰。在各項藝術文化呈爆發式增長的當下,戲曲的傳統地位受到了巨大影響,有些戲種甚至面臨滅絕。為迎合大眾審美,促使傳統戲曲音樂重新煥發生機,必須著手對其進行全面改革,在傳統和交響化之間尋找平衡點。比如,交響川劇《思凡》在實際創作時就始終堅持還原傳統唱念做打,即便是在國外巡演時也都始終通過原汁原味的唱腔進行表演,不但彰顯了文化自信,還促進了川劇傳承[2]。
三、戲曲音樂交響化的創作實踐歷程
(一)萌芽時期
回眸戲曲藝術發展歷程,中國戲曲和西方交響樂結合的第一部作品為小提琴協奏曲《梁山伯與祝英臺》,該作品使戲曲音樂交響化步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取得了里程碑式的成就。
縱觀整個現代化萌芽期,其主要保留了“三大件”,但也適時加入了一些比較新的民族樂器,改善了傳統戲曲配樂過于薄弱的缺陷。比如《詹天佑》中在借鑒勞動者辛勞的時候就將民歌中勞動號子的體例應用了進去,創作了幾首合唱曲目作為背景音樂,實現了民歌曲調和戲曲元素的融合。《白云紅旗》中直接以蒙古族音調二聲部合唱為引子,使民族樂器和其相互映襯,給戲曲演員登場做好了充足鋪墊。雖然戲曲革新浪潮已經在整個圈子中涌動,但大部分欣賞者其審美依然沒有產生變化,整體創新構思還需一個最佳的時機。
(二)發展時期
進入20世紀60年代,受到文藝發展環境的影響,戲曲音樂的發展主流就是借鑒西洋歌劇的基本手法,其中的音樂元素、結構模式都體現在了當時的舞臺上[3],其中最典型的樣板戲模式就呈現出了中西結合的音樂編配形式。比如《沙家浜》中就直接把戲曲音樂和交響與結合在一起,將合唱和極為宏大的舞蹈場面加入進去,在樂隊配置方面不但包含了全套的文武場戲曲班底,還加入了西洋雙管編制樂隊,給后續戲曲音樂交響化發展留下了寶貴的經驗與財富。通過交響樂形式伴奏戲曲音樂最典型的當屬六七十年代的各種京劇現代戲,例如,《紅燈記》《智取威虎山》《杜鵑山》等。這些作品運用現代多聲部創作手法,極為注重結構的完整性和聲部的均衡性,主要通過單管編制的西洋管弦樂和傳統樂器進行伴奏,使中國戲曲音樂漸漸迎來了交響化創作的高潮時期,尤其是在20世紀末期受到了廣泛歡迎和肯定,大多數學者都認為這是近百年來中西方藝術文化發展融合中獲得最大成果之一。其中誕生了《駱駝祥子》《映山紅》《蝶戀花》等作品,音樂編配程式化色彩漸漸轉淡,文武場配樂的曲牌也產生了更多新的設計與構思,大提琴一時成為了伴奏標配。在一些新劇目當中還漸漸和交響樂當中的管樂組、弦樂組,甚至電聲樂器進行搭配組合,雖然也有失敗,但整體交響化發展已經是大勢所趨。
(三)平穩時期
進入本世紀,戲曲音樂交響化取得多項突破。整個創作領域呈現出了多元競爭的發展態勢。如2003年,交響京劇《大唐貴妃》正式拉開了戲曲藝術和交響樂全面融合的序幕;2004年,川劇《鳳儀亭》則通過和交響樂隊合作,直接進入美國劇院演出;2005年,京劇《梅蘭芳》成為了第一步交響劇詩;2006年,戲曲電視劇《楊門女將》結合交響樂首次在CCTV戲曲頻道播放;2009年為紀念鄭和下西洋600周年,《鄭和下西洋》以京劇為主體,在展現京劇魅力的同時,融入了交響樂和歌舞劇等藝術形式,取得了良好的創作效果[4]。
現階段,戲曲音樂的展現方式為“耦合共時”。例如漢劇在發展過程中基本都是使用“三大件”伴奏,后來漸漸加入京二胡,甚至增加國民族管弦樂,選用了木管、低音等西洋樂器,作曲手法眾多,有優勢也有不足。比如有些非常注重音樂色彩的變化,但只通過勾譜標示樂器的進入和退出;有些注重民族調式和聲的配置,但并未成為整個漢劇發展的共識。同應用多種形式進行伴奏的漢劇相比,楚劇等專業劇團則直接拋棄了原生態伴奏,使傳統伴奏形式成為了歷史遺存。因此,戲曲音樂要想取得發展,就應在吸收借鑒新質和異質的音樂優勢中,選擇出適合本劇種且能夠展現特色的元素,將其作為戲曲交響化轉變的主要方向。
四、戲曲音樂交響化創作思維
(一)戲曲音樂交響化創作內涵
1.學習借鑒交響樂
交響樂織體編配習慣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戲曲劇本的結構設計。一直以來戲曲劇情受限于唱詞的拖沓及伴奏的舒緩,導致其中人物形象塑造和戲劇沖突力道過弱,阻礙了整個戲曲藝術的發展,但在加入交響樂后則能夠促使其中輕重緩急的轉變更加迅速,劇情整體張弛有度,更使歌劇中的一些表現手法及場景轉換模式被引入其中。“交響”從其一般意義上來說,是對西洋交響樂隊編制的簡稱,但從根本層面來講,則充分展現了音響配比的科學性、復調和聲的平衡性與和諧性,整體音樂色彩極具國際化,同時其中還由音樂配置而引起了戲劇題材、表演手法、聲腔唱法、舞臺形態等方面的全面變化[5]。所以戲曲音樂交響化最終產生的完全是一種連鎖性反應,并非只是簡單地給其中加入相應的伴奏體系。在實際進行交響化創作時,應對戲曲音樂傳統伴奏樂器作出改變,把具有西方色彩的調性及調式吸收和借鑒進來,從而解決現代劇情寫實與伴奏老套之間存在的矛盾,促使音樂編配和劇本創作更加融合。
2.跨越意識層面
從戲曲藝術的發展歷程來看,在原先的傳承過程中一直都極為注重門派之分,雖然這使得大量寶貴的藝術積累實現了完整傳承,但在一定程度上卻制約了戲曲藝術的創新發展。然而目前的戲曲藝術以某個人或某個門派作為軸心的發展形態已經基本消失,西學東漸中,西方交響樂和歌劇的發展經驗被更多地借鑒過來,打破了語言障礙,使更多西方人也能夠聽懂戲曲,了解其中的門道,實現意識層面的跨越。
(二)戲曲音樂交響化創作度量把握
戲曲是一種聽覺藝術,更是一種視覺和審美藝術。最近幾年,在現代舞臺極具科技感的包裝手段下,從感官上提升了戲曲的層次性,但這種通過技術營造出的所謂創新感并未從本質上促進戲曲藝術改革。對其創新發展而言,應該是進一步轉變,這種轉變是質變性的,即在不破壞戲曲文化精神的基礎上,給戲曲音樂加入交響樂,開辟出一條新的發展道路,彌補傳統戲曲音樂結構上的缺陷。但戲曲音樂交響化的實現并非簡單進行樂器移植,而是要將西方音樂律制及表現手法全面滲透進去,但這種滲透絕不能破壞中國戲曲本身的民族文化意蘊和獨特風貌,所以其中對于創作度量的把握就成為了戲曲音樂交響化轉變的核心問題[6]。
以川劇為例,在原先的對外宣傳當中,基本都是分解式推廣,比如把滾燈、變臉等絕活作為招牌展現在各種舞臺上,雖然其獨特的表演手法及精湛的技藝能夠得到觀眾的普遍肯定,但長期下去勢必會導致這些技藝和川劇本身產生相互脫離的現象,使得觀眾誤以為這些技藝就是川劇的核心及全部,進而影響到川劇未來的進一步發展。所以戲曲和交響樂的結合則不能直接將一些精彩片段或者能讓西方人看懂的部分展現在舞臺上,而是要把戲曲的所有內容完整地應用進去。
與此同時,有些學者主張摒棄“四擊頭”“老三件”這類傳統戲曲伴奏樂器,完全實現伴奏西化。他們認為傳統伴奏樂器沒有低音聲部,在渲染氣氛方面存在一定不足,且和西方樂器之間難以搭配,不具有現代感。對此必須充分認識到,一方面,倘若戲曲聲腔本身不夠新潮,演繹手段過于傳統,即便是完全使用西方樂器也不能解決當前戲曲藝術發展的困境;另一方面,如果將戲曲本色全面削弱,其造成的文化影響將遠遠超過戲曲革新之功[7]。所以在實際推動交響化發展時就必須明確實現交響化的主要目的是取長補短,例如戲曲樂隊樂器搭配存在問題,但在引入交響樂后發現其和京胡這類傳統樂器在音色及表達形式上有明顯的碰撞問題,這時候則不能直接拋棄京胡,而是要對其及時進行優化改造,應用京二胡等,有效解決和交響樂間的配合問題。
(三)戲曲音樂交響化創作思路
戲曲音樂表現手法和交響樂形式的融合,在優化戲曲藝術方面是一次探索和創新,其創作初衷主要是為了實現取長補短,通過豐富的交響樂形式追求戲曲音樂的神似,最終在西方主流音樂配器的方式下對戲曲音樂進行包裝。比如京劇《徐九經升官記》中,只需要通過三弦獨奏以帶滑音的形式就能夠準確展現出主人公的憂思和歡樂。在喜慶歡快的農村題材中可以使用笛子和嗩吶作為主奏,在塑造解放軍等偉大形象時則必須使用銅管樂器。
傳統戲曲唱腔及伴奏曲牌都是單聲作曲,即使用樂音單一線條的橫向運動去表達內涵。從單一線條的縱向來看,也始終都是單個的音,且通過多人多件樂器的齊唱與齊奏營造音樂意境[8]。雖然縱向上已經包含了同音不同八度的復合,但依然是通過單聲思維創作的音樂。多聲思維是對單聲思維的深化和補充,可以把單聲音樂當中蘊含的不能同步展現的內涵同步展現出來。比如荊州花鼓戲《家庭公案》中李云霞的唱段其伴奏及幫腔都是使用的多聲作曲法,進而在展現主人公悲憤心境的同時,還渲染出了電閃雷鳴的舞臺效果。當前大眾思想逐漸復雜、豐富、深刻,萬事萬物也都變化多端,因此這些客觀存在只有通過多聲思維的創作技法才能將其完美展現出來,使音樂藝術的表現功能得到進一步拓展。當代專業音樂創作領域中,單聲思維音樂基本消失,非單聲伴奏的民間歌曲與通俗音樂也都基本是通過多聲思維創作的。在沒有大樂隊的時候,幾件樂器也能夠實現多聲創作。如漢劇《翁婿鬧公堂》第二場中焚香祈禱的場景就直接以洞簫緩慢吹奏其文堂曲牌小桃紅的主旋律,再用中阮輔奏,填充進一段與小桃紅相似的旋律。這種通過深度剖析劇情,選擇適合樂器的創作方式,往往能夠實現以少勝多。
以秦腔為例,傳統樂隊由文場和武場兩部分組成,前者給唱腔伴奏、間奏和演奏背景音樂,后者則配合演員的拉架子、耍身子、武打、念白等程式化表演。對此在實現交響化的過程中可以重點將生、旦、丑等行當中的秦腔音樂元素作為核心,用交響樂的形式展現出來。比如對于生行來說,可以直接把秦腔中生角的典型唱腔進行重新編寫,在秦腔唱段旋律之下,使用弓弦樂器及木管樂器展現勞動的歡喜之情,或使用銅管樂器展現行兵布陣的戰爭場面,營造出悲壯吶喊的效果[9]。由此使得生角本身濃郁的書生氣和風流瀟灑的一面也被展現出來。在丑行中,則可以直接將其中的代表性唱腔拆解揉碎之后再巧妙連接在一起。如使用木管樂器展現丑角的幽默、風趣、憨態,使其念白展現出灑脫詼諧、清脆犀利的效果,同時在音樂慢板的作用下營造出丑劇的性格特點。在旦行中,由于其經常都是通過唯美清秀的姿態及體貌展現內心世界,所以這就可以將秦腔本身的唱腔作為基本旋律,使用深沉的慢板展現其凄楚哀怨、纏纏綿綿的意蘊,或展現出良好的儀態。這種直接將交響樂應用到戲曲音樂中的方式,不但克服了原先戲曲樂隊單調與乏力的表現形式,還給戲曲音樂的傳播奠定了基礎,充分展現旋律美,給其舞臺表演起到了極大推動作用,更給古老戲曲的發展開辟出了一條新的途徑。
五、結語
當今世界呈現出了多元化的格局,世界渴望了解中國,對中國文化本身以及其中所蘊含的民族特色藝術都有著強烈的好奇心;中國文化也應順應趨勢,融入世界文化大范疇中,而戲曲音樂交響化的創作探索正是順應這一發展趨勢的主要表現。從20世紀中期開始,中國戲曲音樂就開始探索交響化的創作路徑,經過半個多世紀的發展其交響化已然成熟,促使中國戲曲藝術漸漸走出國門,在繼承創新之下成為世界藝術舞臺上的一朵奇葩。實際創作時,應重點分析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戲曲和歌劇間的異質同構性,進而使它之精髓能夠被戲曲音樂交響化所應用,最終呈現出更加完善且獨具特色的戲曲文化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