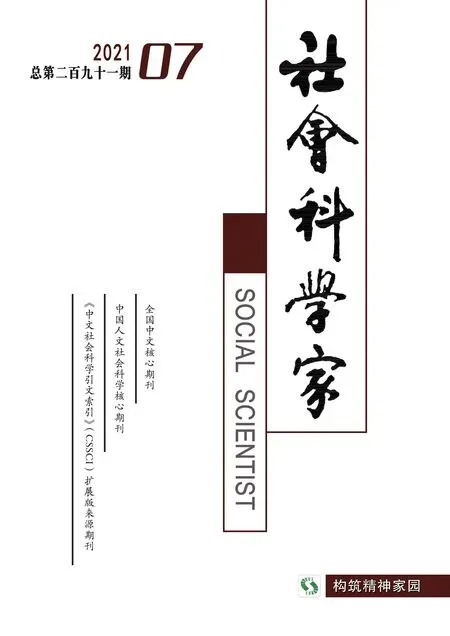ICSID仲裁管轄權爭議中證明責任適用的局限與克服
馬明飛,蔡斯揚
(大連海事大學 法學院,遼寧 大連 116026)
一、問題的提出
隨著近年來國際投資仲裁①本文討論的國際投資仲裁,范圍僅限于外國投資者與投資東道國基于投資爭端而提起的條約仲裁,不包括一國與他國因投資爭端所引發的國家間仲裁。的案件數量呈指數增長,投資者與東道國在案件管轄權問題上的激烈交鋒已成為該領域的關注焦點之一。國際仲裁界就曾統計在全部國際投資仲裁案件中,由于管轄權原因而全部駁回與部分駁回申請人仲裁申請的案件比例高達60%[1]。而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在《2018年投資者—東道國爭端解決案件報告》中也指出,截至2018年年底全球約有600起已審結投資仲裁案件,在東道國勝訴的案件中,約一半因管轄權異議而駁回投資者的仲裁請求[2]。可見,管轄權問題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仲裁案件的后續進程與最終結果。在作為當前最重要的投資爭端解決機制——“解決投資爭議國際中心(ICSID)”仲裁中,絕大多數的投資東道國都會對投資者的仲裁申請提出管轄權異議②國際投資仲裁的管轄權基礎是東道國與投資者母國締結投資條約中的仲裁合意。實踐中該投資條約被解釋為東道國將投資爭議提交仲裁的持續要約,投資者甫一啟動仲裁程序即被視作對該要約的承諾。所以,投資者可以隨時作為仲裁申請人啟動仲裁程序,東道國在國際投資仲裁中只能作為被申請人進行應訴。。ICSID仲裁庭于實踐中通過審查仲裁請求是否滿足《關于解決國家與他國國民之間投資爭議公約》(以下簡稱“ICSID公約”)和涉案具體投資協定中規定的相關要件,來確定能否對個案行使管轄權,這一過程也必然要求仲裁雙方對涉及管轄權爭議要件事實進行舉證與說明。由于ICSID公約及其仲裁規則均未明文規定具體的證明責任規則,仲裁庭因而在管轄權要件事實的證明責任分配上擁有較為廣泛的自由裁量權③ICSID公約第43條第(1)款僅規定:“除雙方另有協議,仲裁庭可在程序的任何階段認為有必要時,要求雙方提出文件或其他證據”。而ICSID仲裁規則第34條只是原則性地規定,“仲裁庭對于所提供的證據,應就其是否接受及其證明價值作出判斷”。。
證明責任制度本身的產生源自裁判者對待證事實的認識手段不足與認識能力局限[3],其包涵若無法說服裁判者而將導致承受不利后果之意。故此,仲裁庭在投資者與東道國之間裁量分配證明責任,將對管轄權爭議的最終結果有著深刻的影響。雖然“誰主張、誰舉證”這一世界范圍內所公認的證明責任分配法則在ICSID仲裁實踐中被廣泛適用,但是一方面由于ICSID公約和具體涉案國際條約就管轄權要件規定的多重性與復雜性,另一方面緣于不同背景的仲裁員往往會選擇性援引以往仲裁裁決中的證明責任分配方法,證明責任因此在不同案情中的適用中可能出現相應的嬗變與異化,最終導致管轄權裁決出現實質不公的不良效果。由此,本文從證明責任的概念分野出發,通過考察部分典型案例以發現證明責任適用于管轄權爭議中存在的若干局限性問題,在剖析其背后原因的基礎上,對如何更為合理地適用證明責任提出建議。
二、ICSID仲裁管轄權證明責任分配的一般原則
ICSID仲裁無論在公約還是在仲裁規則上均未對證明責任的概念進行明確規定,此概念于仲裁中的運用,實際上是對國內法的轉借。對證明責任內涵的準確認識,有助于深刻理解ICSID仲裁中證明責任分配的功能。
(一)ICSID仲裁中證明責任的雙重內涵
國內法上,證明責任是有自身邏輯內涵的一個整體概念。英美法系的證明責任(burden of proof)包括說服責任(burden of persuasion,或稱“法定證明責任”legal burden of proof)和提出證據責任(burden of producing evidence,或稱“舉證證明責任”evidential burden of proof)。前者指整個訴訟過程中,當事人提出證據以說服裁判者相信其主張的事實為真的責任;后者指在訴訟各個階段,當事人就爭議事實提出證據,并在質與量兩方面達到最低要求,否則其訴請將被駁回[4]。大陸法系的證明責任理論體系則區分客觀證明責任與主觀證明責任,前者是指在庭審的最后階段若要件事實依然真偽不明,由主張該事實的當事人承擔不利的裁判后果;后者是指當事人為了獲得對其有利的裁判、避免敗訴,通過提供證據的方式對爭議事實進行證明的一種必要負擔[5]。
相較而言,英美法系通過分析被告針對原告的答辯來確定說服責任的承擔者,大陸法系則是由實體法條款來規定客觀證明責任的承擔者,在適用效果上“說服責任”大體相當于“客觀證明責任”,二者都強調不能說服法官而產生的敗訴風險,是結果意義上的證明責任,在案件審理中均始終不發生轉移[6]。“提出證據責任”的主觀證明責任則是程序法上的責任。均是行為意義上的證明責任,也都在具體案件進程中發生轉移。
以上對兩種證明責任內涵的區分,在國際仲裁理論界被較為一致地認可。學者們指出,證明責任作為一項課予事實主張者的基本負擔,其中的法定證明責任或說服責任在國際仲裁整個過程中從未發生轉移;而舉證證明責任作為程序事項,可以在主張者與抗辯者之間來回轉移[7]。更有學者論及,用證明責任(burden of proof)術語來代替舉證負擔(burden of evidence)是不準確的,證明責任由事實主張者承擔,直到案件所涉整個主張得到證明[8]。實踐中,直到Apotex v.the United States案仲裁庭明確作出“法定證明責任(legal burden of proof)不轉移,舉證證明責任(evidential burden of proof)隨著證據出示的情況而在當事人之間發生轉移”的論證后[9],ICSID仲裁開始有意對兩種證明責任內涵進行區分,這也體現在Mercer v.Canada案、Koch Minerals v.Venezuela案和Gavazzi v.Romania案等一系列仲裁實踐中[10]。由此,ICSID仲裁中的證明責任概念融合了兩大法系的制度內涵,將說服裁判者的義務和提供證據的義務區分開來。
(二)ICSID仲裁中證明責任分配的一般原則
“提出主張者承擔證明責任”(onus probandi incumbit actori)這一起源于羅馬法的原則,已被兩大法系的國內訴訟作為一項普遍接受的證明責任分配原則而持續恪守,也為國際仲裁中經常適用的《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仲裁規則》(UNCITRAL Rules)所明文規定①UNCITRAL《仲裁規則》第27條第1款規定:“每一方當事人應對其仲裁請求或答辯所依據的事實負舉證責任”。。
雖然ICSID公約與仲裁規則均未明文確認此項規則,但是仲裁實踐中該原則得到廣泛遵循。在AAPL v.Sri Lanka案中,仲裁庭開創性地總結出關于證明責任的兩條首要原則:第一,法律的一般原則將證明責任課予權利主張者;第二,不能僅從程序立場出發而機械地讓原告承擔證明責任,而應從具體爭議來檢視誰是真正的權利主張者[11]。嗣后,大多數ICSID仲裁庭對上述分析予以呼應[12],其中以Rompetrol v.Romania案與Bernhard v.Zimbabwe案仲裁庭對該原則的闡釋最為典型。前案指出,如果被申請人提出自己的新主張以反駁或破壞申請人的事實請求,則該新主張的證明責任由被申請人承擔[13];后案論道,若主張與抗辯涉及相同的事實問題,每一方都承擔證實自身觀點的提出證據責任,管轄權異議提出時并不存在證明責任轉移的概念[14]。而且,部分仲裁庭在承認“提出主張者承擔證明責任”的基礎上還進一步澄清,證明責任的分配原則不會因為獲取與提交證據中存在困難而發生改變[15],也不能因為另一方更容易獲得證據而改變[16]。故此,證明責任一般由提出事實主張的申請人或提出新事實抗辯的被申請人自始承擔①否認是指對于一方當事人主張的事實,另一方當事人向法院或仲裁機構表示是不真實的;而抗辯則是一方當事人通過主張與對方當事人不同的事實或法律關系來排除對方的主張。參見李浩:《民事訴訟法適用中的證明責任》,載《中國法學》2018年第1期。,此時的證明責任應理解為的法定證明責任或說服責任。
由于實踐中的仲裁庭對其須滿足何種條件舉證證明責任方得以轉移的論述不多。國際仲裁理論界對此進行了彌補:國際仲裁中,當事人提出的證據至少需要達到表面上的確定性,才能將證據負擔轉移給對方[17]。一方當事人提出表面證據(prima facie evidence)②表面證據(prima facie evidence),是指除非提出相反證據,否則據此證據已能確立某項事實或支撐某項判決。表面成立的案件(prima facie case)是表面證據在證明案件成立時的一種證明標準(也即說服責任的標準),其在說服責任中則表現為:如果對方當事人不提供相反證據,對方當事人就將承擔敗訴的風險。表面證據的作用可以是轉移提出證據責任,也可以作為一種減輕當事人證明責任的推定。參見徐康:《英國表面證據規則初探》,載《司法改革評論》2013年3月第1輯(總第16輯)。后,實際上免除自身的提出證據責任,在對方當事人反駁該已經成立的表面證據之前,不再承擔該待證事實進一步的舉證負擔③Amerasinghe教授還進一步列舉了四種申請人提交表面證據的后續可能結果:1.相對人沒有回應,法庭最終認定申請人提交的證據滿足了適用的證明標準,并支持其主張;2.相對人沒有回應,但法庭認定申請人提交的證據無法滿足適用的證明標準,不認可其主張;3.相對人以提出證據或進行解釋的方式提出抗辯,但仲裁庭最終發現該抗辯無法動搖申請人證據對證明標準的滿足,因此支持申請人主張;4.相對人以提出證據或進行解釋的方式提出抗辯,仲裁庭最終發現申請人證據無法滿足適用的證明標準,因此不認可申請人的主張。See Chittharanjan F Amerasinghe,Evidence in International Litigation,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2005,pp.251.。質言之,盡管表面證據不一定能滿足某一案件的最終說服責任標準,但其包含的最低程度之說服責任意義卻可輔助仲裁庭對舉證性證明責任的履行情況進行檢驗并決定是否轉移。
綜上,ICSID仲裁中的兩種證明責任內涵所引致的證明分配結果應當有所不同。在仲裁程序啟動之初,對某一案情事實的法定證明責任與舉證證明責任均歸于同一當事人(提出主張的申請人或提出新事實抗辯的被申請人)。當該當事人提出事實證據并形成了表面證據時,舉證證明責任由此轉移給對方,且在對方對該表面證據反駁之前,他都不會承擔進一步地法定證明責任④參見前注29,Mojtaba Kazazi書,第273頁。。對方當事人為阻止對其自身的不利裁判,提出證據反駁該表面證據,舉證證明責任再次回到原方當事人而迫使他提出更多針對該待證事實的證據。上述過程中,法定證明責任始終居于一方當事人,舉證證明責任的來回轉移,引導著雙方對特定事實論證的說服力不斷發生變化,從而有助于仲裁庭認識證據的全貌和判斷一方當事人是否完成了法定證明責任。
(三)ICSID仲裁中需要證明的多重管轄權要件事實
國際投資仲裁是一種運用國際商事仲裁方法來處理外國私人投資者與投資東道國之間的投資糾紛的方式。相較而言,國際商事仲裁的管轄權爭議較為少見,其大多數與平等商事主體間訂立的仲裁條款之約束范圍有關。而國際投資仲裁因涉及的仲裁條款包含在國際公法性質的條約之中,東道國往往針對條約若干具體條款提出管轄權異議,其管轄權上的爭議則相對廣泛得多[18]。為保持仲裁效率并兼顧公正,ICSID仲裁常會對仲裁程序進行管轄權審理階段與實體問題審理階段的“二元劃分(Bifurcation)”⑤這種程序劃分的案件管理方式為ICSID公約第41條第2項所明確規定:“仲裁庭有權決定是否將管轄權異議作為先決問題處理,或與該爭端的實體問題一并處理”。即使其他仲裁機構也不同程度的支持此種程序處理方法。例如,被其他仲裁機構廣泛適用的《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仲裁規則》(UNCITRAL規則)(2010)第23條第1款也規定:仲裁庭“對管轄權作為初步問題還是一并與實體問題作出裁決”有自由裁量權;國際商會仲裁院(ICC)《仲裁規則》第2條指出,裁決分為“臨時、部分以及最終的裁決”,并于該規則附錄4補充道:“如果諸如二元切分的案件管理技術能更為高效地處理案件,仲裁庭可以使用”。,以便通過對管轄權爭議要件進行審查而駁回沒有適格管轄權的仲裁申請,由此避免對后續實體問題再行徒勞審理⑥在ICSID仲裁語境下,實體問題(Merits)是指投資者基于東道國違反涉案國際投資條約中投資保護條款而享有的條約請求權。為支撐針對東道國違反種種具體條約義務的訴請,投資者需列舉若干基礎事實,這就可能與關涉管轄權要件的事實發生重疊。實踐中,仲裁庭一般就管轄權與實體問題中事實的重疊程度,決定是否進行程序的二元切分。由于討論的主題及篇幅所限,對實體問題與管轄權問題的重疊程度如何具體判別,本文暫不做詳細論述。。這也就塑造了ICSID仲裁管轄權爭議審理階段的相對獨立性。
國際投資仲裁可在ICSID公約體系內進行,也可于該公約體系外的非ICSID機構進行⑦非ICSID仲裁,包括根據《ICSID附加便利規則》進行的投資仲裁、適用《UNCITRAL仲裁規則》進行的專設臨時仲裁、在以斯德哥爾摩商會仲裁院(SCC)與國際商會仲裁院(ICC)為主要代表的國際商事仲裁機構進行的投資仲裁等。。而在ICSID體系下對仲裁案件行使管轄權,除了要符合涉案條約對上述投資保護范圍的限定之外,還須滿足該公約第25條規定的其他管轄權要件。詳言之,該規定的要件包括雙方書面同意將爭端提交給中心解決(同意管轄要件)、涉案爭端系直接因“投資”而產生的法律爭端(屬物管轄要件)、仲裁雙方必須是締約國與另一締約國國民(屬人管轄要件)⑧ICSID公約第25條:1.中心的管轄適用于締約國(或締約國向中心指定的該國的任何組成部分或機構)和另一締約國國民之間直接因投資而產生并經雙方書面同意提交給中心的任何法律爭端。當雙方表示同意后,任何一方不得單方面撤銷其同意。2.“另一締約國國民”是指:(1)在雙方同意將爭端交付調解或仲裁之日以及根據第28條第2款或第36條第3款登記請求之日,具有作為爭端一方的國家以外的某一締約國國籍的任何自然人,但不包括在上述任一日期也具有作為爭端一方的締約國國籍的任何人;(2)在爭端雙方同意將爭端交付調解或仲裁之日,具有作為爭端一方的國家以外的某一締約國國籍的任何法人,以及在上述日期具有作為爭端一方締約國國籍的任何法人,而該法人因受外國控制,雙方同意為了本公約的目的,應看作是另一締約國國民。3.某一締約國的組成部分或機構表示的同意,須經該締約國批準,除非該締約國通知中心不需要予以批準。4.任何締約國可以在批準、接受或核準本公約時,或在此后任何時候,把它將考慮或不考慮提交給中心管轄的一類或幾類爭端通知中心。秘書長應立即將此項通知轉送給締約國。此項通知不構成第一款所要求的同意。。正如SGS v.Paraguay案仲裁庭所指明的,仲裁庭在管轄權階段應根據涉案BIT和ICSID公約的相關規定,對仲裁合意、國籍、受保護的投資、投資位于的領土、條約保護的時間范圍等直接決定管轄權的事實進行確定[19]。National Gas v.Egypt案仲裁庭也指出,盡管被申請人可能提出若干具體的管轄權異議,對各項管轄權要件事實的證明責任應由申請人承擔[20]。由此,基于ICSID仲裁總是由投資者作為申請人發起,根據“提出主張者承擔證明責任”一般分配原則,其將承擔案件管轄權成立的法定證明責任。又基于ICSID公約所設置的上述多重管轄權要件,作為仲裁主動發起者的投資者在一般情況下還需要承擔每一要件事實的法定證明責任,以說服仲裁庭認定該事實主張的成立。
三、證明責任適用于ICSID管轄權爭議的局限性
ICSID仲裁本質上是運用商事仲裁的方法解決雙邊投資糾紛,同樣對包括證明責任分配在內的諸多具體證據規則未作出硬性要求①在國際商事仲裁領域,得到最廣泛運用的《UNCITRAL仲裁規則》和《國際律師協會國際仲裁取證規則》均未對證明責任分配及滿足標注作出詳細規定,意在尊重當事人意思自治和賦予仲裁庭自由裁量權。前者僅由第27(4)條規定,仲裁庭應就所出示證據的可采性、關聯性、實質性和重要性作出決定;后者僅由第3.1條規定,在仲裁庭確定的期限內,每一方當事人均應向仲裁庭和對方當事人提交該當事擁有的、其作為依據的全部書證。。實踐中的仲裁機構也表示,其不應在解決爭議時被要求強制適用任何特定的證明責任或標準[21]。故此,ICSID仲裁庭在管轄權爭議中對證明責任的適用范圍與程度確定,也就隨其自由裁量權的行使和個案案情而發生些許嬗變,適用效果上的局限性問題也就此產生。
(一)確定管轄權要件事實的真正“主張者”并非易事
仲裁界學者們曾對在國際仲裁中運用“提出主張者承擔證明責任”的一般分配原理提出了擔憂。Amerasinghe教授就提出適用上的問題,在國際法程序中有效區分事實主張者與抗辯者可能存在困難;在國際爭端中同時提交訴請是被允許的;仲裁庭審理案件所依據的相關基礎文本材料對證明責任分配保持緘默;爭議雙方有義務與國際仲裁庭合作,以此構建出案件的真相[22]。而ICSID仲裁管轄權審理實踐中,于特定案件中確定“主張者”的確存在困難與爭議。
以投資者適格國籍為例,按照證明責任一般分配原則,投資者應當承擔該要件事實的法定證明責任(即說服責任)。但是在面臨投資者具有雙重國籍的案件時,問題就變得較為棘手②依ICSID公約第25條第2款第1項的規定,對于爭端中作為投資者的一方當事人,必須同時滿足兩項國籍要求:必須具備另一締約國的國籍(又稱“積極要求”),且其不得同時具備投資東道國的國籍(也稱“消極要求”)。。在Ambiente v.Argentina案中,依涉案意大利與阿根廷BIT的相關條款規定,投資者的適格國籍要件包括具有意大利國籍(積極事實)、不具有阿根廷國籍(消極事實)和未在阿根廷居住兩年以上(消極事實)等三個要素③該仲裁涉案BIT規定,具有阿根廷國籍的投資者不受該BIT保護以外,開始進行投資之前已在阿根廷居住滿兩年以上者,也不受在該 BIT 的保護。See Ambiente Ufficio S.p.A et al.v.Argentine Republic,ICSID Case No.ARB/08/9,Decision on Jurisdiction and Admissibility(8 Feburary 2013),para.312.。該案仲裁庭的多數仲裁員將具有意大利國籍的法定證明責任課予投資者,同時把證明該投資者不具有阿根廷國籍且未在該國居住兩年以上的法定證明責任分配給東道國阿根廷。而該案少數仲裁員在其反對意見中則指出,應由投資者承擔適格國籍的積極要件與消極要件的總體法定證明責任,否則將有違國際法上對證明責任分配的一般公認原則[23]。此案若按多數意見處理,東道國對該國籍消極要素只存在反駁的舉證證明責任,課予其該要素的法定證明責任則導致一個要件事實中出現了兩個說服責任,顯然有悖于證明責任分配原理;而少數仲裁員意見處理,則存在申請人(事實主張者)承擔對不存在的消極事實進行證明這一顯然有違常理的做法。該案仲裁庭對證明責任的分配也由此在理論界被不斷探討與爭論。
(二)投資者被賦予過重法定證明責任所導致的不平等
盡管實踐中ICSID仲裁因只能由投資者發起而看似在程序上對其有利,但作為被申請人的東道國在管轄權的證明責任規則上卻擁有較大優勢。因為投資者對國籍、適格投資、仲裁合意與可歸責性等管轄權事實需提供證據予以證明,而東道國往往就這些事實提出多項管轄權異議,且東道國所獨享的警察權力也使其可能坐擁投資者永遠無法獲取的信息。是故,附加投資者以過于苛刻的證明責任,會使仲裁雙方的程序地位嚴重失衡。
Caratube v.Kazakhstan案是畸高的法定證明責任導致投資者敗訴的典型實例。該案緣于CIOC公司因哈薩克斯坦政府征收其石油與天然氣開采特許權項目而申請ICSID仲裁,其中管轄權確立的焦點在于美國公民Hourani是否有效控制了位于東道國的合資企業CIOC④依ICSID公約第25條第2款第2項的規定,法人的國籍問題存在著“國籍標準”與“控制標準”兩種適合標準,即外國法人可以是東道國以外的某一締約國國籍的任何法人(國籍標準);而受外國控制的且具有東道國國籍的法人,經雙方特別約定,也可以視為另一締約國國民(控制標準)。只有能夠證明CIOC公司(全稱“CARATUBE INTERNATIONAL OIL COMPANY LLP”)被美國公民Hourani實際控制,才能符合涉外BIT與ICSID公約對屬人管轄要件事實的規定。。雖然仲裁庭依間接證據認可了Hourani持有涉案企業92%的股權,但認為這并不能夠充分說明對涉案企業的實際控制[24]。在哈國政府提出了可能存在他人實際控制企業的意見后,仲裁庭命令申請人證明投資資金的來源、對投資項目的實際貢獻和參加股東會與董事會頻率等事項,以此說服仲裁庭其對企業的實際控制①See Ibid,paras.425-427.。問題在于,自CIOC公司的業務被征收時起,其辦事處已遭到哈國警方多次搜查,在相關重要文件被沒收且部分工作人員已被拘留與審訊的情況下②See Ibid,paras.2,15,171,194.,這種過高的說服責任使申請人難以訴諸充分舉證而最終敗訴,而且縱觀該案審理過程,擺脫舉證義務、卻掌握相關記錄證據的哈國政府,也未有效地證明CIOC是由Hourani以外的其他人所實際控制的事實。
無獨有偶,Libananco v.Turkey案仲裁庭亦適用絕對的說服責任導致投資者最終敗訴③該案是一家名為Libananco的塞浦路斯控股公司針對土耳其政府提出索賠,理由是土耳其軍隊和警察部隊于2003年6月12日,查封扣押了Libananco控股的位于土耳其境內的兩家垂直一體化電力公用事業公司(CEAS公司和Kepez公司)并撤銷了其特許經營權,從而違反了《能源憲章條約》(ECT)。See Libananco Holdings Co.Limited v.Republic of Turkey,ICSID Case No.ARB/06/8,Award(2 September 2011).。該案管轄權爭議的焦點是,Libananco公司是否在土方軍警查封CEAS公司和Kepez公司的日期之前擁有此兩公司的控制權,以此證明其為適格的外國投資者。Libananco公司在該案中出示了包括無記名股份交易記錄在內的表明其控制權的關鍵要素事實,并指出在涉案關鍵日期或其不可能再進行股權交易,因為土方已經沒收了存放股份的相關設施④See Ibid,paras.145-146,155.。然而,土耳其方面堅持不懈地主張投資者的股權是由其欺詐行為所得,并依靠投資者的證人證言與書證之間的不一致之處⑤這種不一致之處源于案件中投資者公司人員作為證人,對其飛往塞浦路斯準備股權交易事宜的時間與航班描述。該證人稱當日只有一家從約旦至塞浦路斯的直航航班,而仲裁庭掌握的證據表明,這架航班在當天于黎巴嫩做過一次中途停留。See Ibid,paras.414-415.,成功地讓仲裁庭對投資者合法持有股權產生了懷疑。仲裁庭認為,申請人對于已發生事件描述存在一定的矛盾與抵觸,而證明所有權存在的負擔必須被“確定性地解除”,故而最終駁回了投資者的管轄權申請⑥See Ibid,para.536.。然而,該案中東道國所主張的投資者對兩公司的股權系欺詐所得,卻自始至終沒有得到有效證明⑦土耳其出示其動用技偵手段后得到的涉案股權先前受益人Uzan家族的電子郵件與傳真,以表明Libananco與該家族的股權交易是在查封扣押行為之后進行的。然而這些書面證據的真實性也遭到了作為Libananco公司的證人的Hakan Uzan的強烈質疑。See Ibid,para.441.。
從上述兩案分析可知,在投資爭議提交ICSID后,東道國實際上有大量機會通過主張投資者存在欺詐行為或證據缺乏真實性等事由,在可能掌握對其有利證據的同時,促使仲裁庭將投資者對某一要件事實的說服責任提高至“明確和令人信服的標準”。在面對投資者主張與東道國反駁的要件事實存在兩種不同解釋時,仲裁庭很可能超越現有雙方提交證據的記錄,以說服責任來替代對證據進行全面調查和相應的權衡比較,最終作出對投資者較為不利的判斷。
(三)以說服責任的適用替代對同意仲裁條款的合理解釋
近十幾年來,越來越多的投資者認為涉案雙邊投資條約中的最惠國待遇條款(以下簡稱“MFN條款”)⑧最惠國待遇是指根據條約,締約國一方有義務使締約國另一方國民享受該國給予第三國國民的同等權利。無論何時締約國給予第三國更優惠的條件,則締約他方有權享有這種新的更優惠的條件。參見余勁松主編:《國際投資法》,法律出版社2014年12月第4版,第246頁。可適用于爭端解決等程序事項,從而援引東道國與第三方國家雙邊條約中對爭議解決更為放寬的條件的條文,作為其主張東道國對本爭議提交仲裁的同意基礎。然而,不同雙邊投資條約中對MFN條款在措辭、范圍等方面都不甚統一,仲裁庭對MFN條款能否給予東道國對提交仲裁的同意的解釋莫衷一是。以Maffezini v.Spain案⑨該案中,依1991年阿根廷與西班牙BIT,阿根廷投資者須先向西班牙國內法院尋求救濟,并且在18個月后也未獲裁決的情況下方可提起ICSID仲裁。而該投資者依照智利與西班牙BIT中“僅需6個月磋商期后即可提起ICSID仲裁”而援引MFN條款,繞開18個月的等待期而直接就投資爭議向ICSID提交仲裁。See Emilio Agustín Maffezini v.The Kingdom of Spain,ICSID Case No.ARB/97/7,Decision of the Tribunal on Objections to Jurisdiction(25 January 2000).和Siemens v.Argentina案⑩該案中,德國投資者援引阿根廷與智利BIT中不要求優先采用當地救濟的條件,從而避開德國與阿根廷BIT中規定的“爭端發生18個月內先向阿根廷法院尋求救濟”條款,徑直向ICSID提交仲裁。See Siemens A.G.v.The Argentine Republic,ICSID Case No.ARB/02/8,Decision on Jurisdiction(3 August 2004).為代表,仲裁庭強調爭端解決條款是在涉案BIT項下賦予投資者的權利中重要組成部分,與他們所受待遇緊密聯系,因而符合“同類原則”,進而認定MFN條款代表了東道國對仲裁的同意①在解釋最惠國待遇條款時,兩項解釋工具經常被使用,一是《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31條確定的“善意解釋規則”;二是“同類原則(ejusdem generis principle)”,即只有在第三方條約與基礎條約規定的事項屬于同一類別,并且該事項本身須與最惠國待遇相關時,方可援用最惠國待遇條款。參見趙駿:《論雙邊投資條約中最惠國待遇條款擴張適用于程序性事項》,載《浙江社會科學》2010年第7期。;而以Plama v.Bulgaria案為典型,明確否認投資者基于MFN條款的管轄權請求。該案仲裁庭指出,MFN條款適用于爭端解決程序僅是一種例外,若要通過MFN條款引入第三方條約中的爭端解決機制,該條款也必須是明確而不模糊的,能夠使締約方毫不懷疑地認為同意仲裁的意思包含在其中②該案中塞浦路斯投資者認為保加利亞與芬蘭BIT中對提交ICSID仲裁的關于征收的爭議并未限定范圍,而優惠于塞浦路斯與保加利亞BIT“僅限于征收補償額的爭端提交ICSID仲裁”,故援引MFN條款申請ICSID仲裁。See Plama Consortium Limited v.Republic of Bulgaria,ICSID Case No.ARB/03/24,Decision on Jurisdiction(8 February 2005),paras.198,199,223.。
上述兩種針鋒相對的觀點被后續不同的仲裁庭援引,尤其在Impregilo v.Argentina案中激烈碰撞。該案仲裁庭的多數仲裁員援引Maffezini案中的論證觀點和分析方法,認為投資者可以依據MFN條款直接對阿根廷提起仲裁③該案意大利投資者援引第三方投資條約中的MFN條款,繞開了意大利與阿根廷BIT中“投資爭議須提交阿根廷國內法院,并在未獲判決18個月后方可提交仲裁”的規定,直接向ICSID提起投資仲裁。 See Impregilo S.p.A.v.Argentine Republic,ICSID Case No.ARB/07/17,Award(27 June 2011).。而仲裁員Stern則援引Plama案觀點并在其反對意見中則指出,在沒有明確且清晰的仲裁合意表示的情況下,必須對該MFN條款進行解釋,然而任何對MFN條款的“解釋”都必須得出該條款無法應用于BIT中關于同意的規定的結論[25]。縱觀上述幾個案件的分析論證,可以察覺出仲裁庭就兩種不同觀點均試圖發展出一種支配同意條款證明的法定證明責任規則,即“除非另有明確的消極規定,MFN條款一般可以適用于爭端解決的程序性事項”(肯定規則)或“除非另有明確的積極適用規定,MFN條款一般不可適用于爭端解決程序性事項”(否定規則)。依證明責任分配的一般原則,投資者應承擔說服仲裁庭MFN條款適用與否的責任。通過課予投資者以這種要么較輕要么很重的說服責任,仲裁往往回避了對爭議雙方提交的有關MFN條款背景材料的審查與解釋。
可見,通過經典判例中的觀點而試圖發展出正式證明規則的做法,并未起到平衡投資者與東道國在ICSID仲裁管轄權利益上的效果。若適用肯定規則,那么投資者能夠輕易地滿足說服責任,為投資者通過MFN條款擴張管轄權范圍大開方便之門。若依據否定規則,投資者顯然被課予了極為沉重的說服責任和絕對明確的證明標準,直接后果則是阻塞了投資者唯一公平地解決投資糾紛的有效途徑。仲裁庭以相對武斷的說服責任規則偏好來替代對當事方證據材料的平衡檢驗與合理解釋,容易造成案件結果的實質不公。
四、ICSID管轄權爭議中證明責任適用的完善進路
管轄權證明責任適用中業已出現的事實主張者確定困難甚至錯誤、過重的法定證明責任招致的爭議雙方間實質不平等、說服責任取代本應對同意仲裁條款作出的合理解釋等問題,是ICSID仲裁證據制度自身特點所引致的必然副產品。一方面,ICSID制度不論從公約起草還是仲裁規則制定,都體現了發達程度與法律傳統上不同的國家間妥協與融合的特點,不同背景的仲裁員在證明責任運用的方法與范圍上難免有所出入。另一方面,被賦予較大自由裁量權的仲裁庭,面對具體個案時也常選擇性地引用先前裁決,而這些先例中蘊含的證明責任分配方法,卻可能因案情、仲裁員背景與證據出示情況等方面的不同而存在差異。
對于上述證明責任適用的局限性問題,ICSID裁決撤銷機制所能提供的矯正效果卻極為有限。盡管ICSID公約第52條規定了對可能的錯誤裁決可啟動撤銷程序予以救濟④ICSID公約第52條第1款規定:“任何一方可以根據下列一個或幾個理由,向秘書長提出書面申請,要求撤銷裁決:a.仲裁庭的組成不適當;b.仲裁庭顯然超越其權力;c.仲裁庭的成員有受賄行為;d.有嚴重的背離基本程序規則的情況;e.裁決未陳述其所依據的理由。”,然而該條款中“嚴重背離基本程序規則”“仲裁庭明顯超越其權限”等撤銷事由只是蘊含了要求仲裁庭在作出裁決過程中不能過于偏離國際訴訟與仲裁在證明規則上普遍采用的做法,受到裁決不利的一方很難通過主張證明責任分配上的偏頗,使特別委員會認定該裁決達到了“嚴重”或“明顯”的錯誤程度。實際上,ICSID裁決撤銷機制的預設功能是關注程序性問題,最終的裁決結果是否具有實質上的抽象正確性不在其評價范圍之內[26]。實踐中的特別委員會就曾指出,其不認為仲裁庭應被要求在解決爭議過程中強制適用任何特定的證明責任或證明標準[27]。前文Caratube案,該案特別委員會亦維持了原仲裁庭在證明責任上的認定[28]。Impregilo案故此,在現有ICSID仲裁框架內對上述管轄權爭議中證明責任的適用局限加以克服,只宜從仲裁庭裁決方法上尋求突破。
ICSID仲裁管轄權是一種有限的管轄權,它必須在確保提供給投資者以唯一獲得起訴國家的救濟機會和貫徹國家有限同意參與仲裁的真實意圖之間作出權衡。基于以上特質,ICSID仲裁管轄權裁決方法上,參考同樣適用國際法解決糾紛、也僅具備有限管轄權的國際法院與國際仲裁庭對證明責任的適用,不失為一條克服現有證明責任分配局限性的有效的進路。
(一)突出舉證證明責任的作用,淡化法定證明責任的適用
強加給投資者嚴格的說服責任所導致的地位不平等問題,根本上還是由于仲裁庭回避或無法進行清楚的事實發現,而最后不得不援引證明責任規則。此種困境可以通過運用“善意推定規則”這一國際公法上的裁判方法加以破解。依善意推定規劃,一國的所有行為都應被認作更有可能是正常的、與國際法相一致的,與此相反的主張須由其提出人加以證明[29]。善意推定規則的法律淵源是國際條約①1969年《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26條就提及該善意推定,即“每一生效條約對當事方均有約束力,必須善意履行”。該公約第27條還補充道:“條約締約國不得援引其國內法的規定作為其不履行條約的理由”。、國際習慣以及國際法院的判例,其在國際法院與法庭若干案件中獲得承認與適用[30]。而ICSID仲裁庭作為國際法上的爭端解決機構,根據該公約第41條第2款的規定,其有權力適用可能的國際法規則。善意推定規劃運用于ICSID仲裁中,是預設投資者在投資有關的交易中的行為是誠實與合理的,一旦東道國提出了與此推定相左的反駁主張,則其需要提出證據加以證明[31]。由此,善意推定規則可以推動仲裁各方就案情進行積極的攻防互動。
在ICSID仲裁管轄權的證明中適用善意推定規則,在不違反證明責任分配一般原則的同時,又可避免課予投資者畸高的說服責任所產生的實質不公,因為推定制度本身不轉移說服責任而是轉移舉證證明責任。兩大法系經典主流觀點均認為,推定不能轉移含有說服責任內涵的法定證明責任。推定之所以能夠轉移舉證證明責任,是由于在當事人提出證據對基礎事實加以證明后,仲裁庭運用善意推定規則得出了對投資者有利的推定要件事實,投資者暫時無須進一步對要件事實予以舉證,而東道國為反駁此善意推定事實,必須對其提供有一定說服力的證據。可以說,善意推定制度對阻卻東道國提出無充分證據且對仲裁員心正形成不利影響的反駁意見,有著相當重要的作用。
具體到ICSID管轄權適格投資要件上,前文Caratube案仲裁庭更為合理的證明責任運用方法是對投資者Hourani擁有CIOC公司92%股權的事實進行善意推定,得出該投資者擁有公司控制權的推定事實,使得投資者的法定證明責任暫時得以解除,舉證證明責任交由作為被申請人的東道國承擔,以促使其向仲裁庭出示更為全面的證據。該案東道國對其提出所謂掌握公司實際控制權另有其人的反駁,須提供具有一定證明力的證據加以支持。仲裁庭在權衡推定事實與反駁事實兩者間證據說服力后,得出的傾向性結論才能被視為經過了審慎事實檢驗,也更具有實體結果的正當性。同理,Libannaco案的東道國,亦應承擔其對投資者提出無記名股權系欺詐所得和股權取得系發生在該國軍警強制措施之后的這兩項反駁意見的舉證證明責任。仲裁庭應憑借善意推定規則,使東道國出示更多的證據,以此緩解投資者在適格投資要件上承擔過重的證明責任的狀況,維持爭議雙方在舉證方面的實質平等。
而對于由事實主張者確認困難,而引起的要件事實上的法定證明責任爭議的問題,同樣可以適用善意推定規則予以克服。具言之,在法定證明責任分配遇有爭議時,仲裁庭應盡可能地向仲裁雙方強調其應承受的舉證證明責任,運用推定事實以解除事實主張者的舉證證明責任,促使對方當事人將各自掌握的全部證據向仲裁庭展示,從而進行動態上的證據分量權衡,以查清管轄權的某一要件事實[32]。這種動態強化雙方舉證證明責任的“中間立場”,在特定情況下有助于紓解證明責任分配的兩難境況。
(二)完善仲裁合意條款的解釋方法,而非創設證明責任規則
前文Impregilo案和Brandes案仲裁庭對MFN條款能否擴展至提交仲裁合意的裁決出發點,是試圖制定一種國際投資法上的證明責任規則,而不是對條款本身是否包含合意表示的解釋。這也使管轄權裁決建立在了法律含義不清的基礎上。仲裁庭機械地調用法理學中的法定證明責任概念,而不是以對涉案投資條約或國內投資法的解釋為根據,意味著仲裁庭未能有效行使ICSID公約第42條賦予其的裁決職能,以法律含義模糊為由作出了不甚清楚的裁決②ICSID公約第42條第2款規定:“仲裁庭不得借口法律無明文規定或含義不清而作出真偽不明的認定”。。
解決這一問題需要進行分析范式的轉變:仲裁庭不尋求創設證明責任規則,而是將重點置于理解決定管轄權成立與否的國際法上。國際法院在判例中所采用的方法,為此提供了答案。常設國際法院(PCIJ)③常設國際法院(Permanent Court of International Justice),是根據1921年《常設國際法院規約》成立的解決國際爭端的常設司法機構,位于海牙,1922年開始運作。常設國際法院審理由于條約的解釋、有關國際法的問題、違反國際義務等事項產生的爭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停止活動,戰后為國際法院〔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所取代。在審理Factory at Chorzów一案時,運用一種蓋然性標準來對待有關法律的證明問題:“為建立管轄權,法庭必須考慮一系列因素,包括仲裁條約的歷史發展、這些條約的術語學問題、字面上的語法和邏輯意思、可歸因于締約雙方對管轄權同意的功能意圖”①See Ibid,p.64.。有學者對該案解讀道,Factory at Chorzów案所采用的方法的關鍵要素是在管轄權問題上承認事關同意管轄的法律之不確定性。對于這種不確定性的克服,是通過對比與解釋雙方當事人關于管轄權的主張和反對主張,最終宣布兩者中更可能的一方(而不是“正確的”一方)為管轄權交鋒中的勝利者[33]。
以此方法回溯考察ICSID仲裁合意問題,實際上在任何特定案件中,對涉及管轄權問題的法律解釋都可以支持與主張截然相反結果的論點。如果單獨來看,這兩種觀點均非明顯錯誤的或不可信的。相反,每一種觀點都會更多地利用對同意仲裁的解讀,以贏得這場投資者步入唯一法律救濟渠道和東道國讓渡極為有限的主權間的競爭。又由于不同案件中的涉案投資條約在措辭、上下文背景與立法政策等方面均有所不同,仲裁庭對爭議雙方就ICSID仲裁合意條款提供解釋的對比結果就無法具備一致性。這也就說明了在MFN條款是否及于同意仲裁問題上,創設固定課予一方當事人的說服責任規則、過于追求裁決結果一致性的做法緣何失敗。Inceysa v.Salvador案仲裁庭也論及“為了避免進行片面或主觀的分析,對管轄權的任何分析必須一絲不茍地進行,不能從有利于或不利于中心管轄權的推定開始。任何推定都會破壞分析,不適當地限制或擴大當事方的最初同意”[34]。
在ICSID仲裁中運用Factory at Chorzów案對同意仲裁條款的蓋然性解釋方法,首先要將重點置于爭議雙方對條款文本各自解釋立場的對比上。根據《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31條,“條約應根據條約文本通常所具有的含義,結合條約的目標和宗旨被善意地予以解釋”。在管轄權爭議的雙方當事人依賴語義和語法而對同意仲裁條款進行解釋后,仲裁庭可以根據整個涉案協定的上下文來分析同意仲裁相關部分的雙方各自解釋,以發現一方的解釋與條約的其他規定之間可能產生矛盾,從而權衡出說服力較強的一種解釋[35]。其次,有學者也指出,ICSID仲裁庭可以參閱過去的仲裁裁決的相關爭議點來測試本案雙方提出的論證,通過類比過去的案例的方式來區分或確認現在本案的權衡解釋觀點[36]。通常情況下,任何一方當事人都不能提出完全優于另一方當事人的解釋。這種綜合的解釋模式使管轄權分析中的蓋然性標準變得具體而豐滿,也使最終裁決更具有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