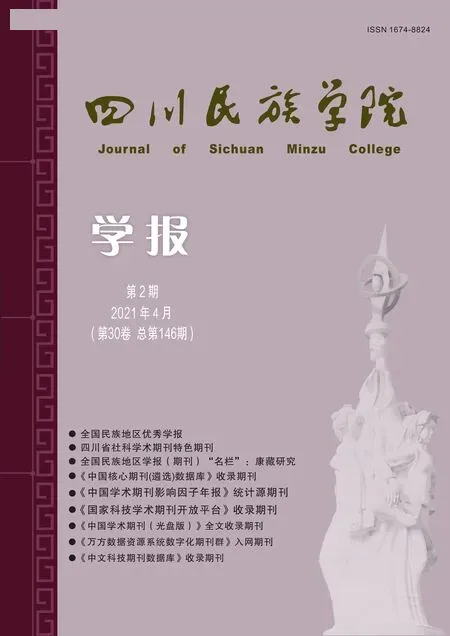論壯族家訓的成因、特點及功能
——以壯族家訓歌《傳家寶》《傳家教》《傳家訓》為例
韋亮節
(廣西民族大學,廣西 南寧 530006)
中國家訓文化歷史悠久,著名的家訓有如諸葛亮的《誡子書》、陶淵明的《與子儼等疏》、王守仁的《示憲兒》等。近現代轉型后的家訓形式主要有專著、家書和家訓詩三類,較知名的有趙炳麟的專著《庭訓錄》、傅雷的家書、陳毅的詩《示女兒》等。關于家訓的系統研究,朱明勛以朝代為綱,從先秦的發軔期、漢魏六朝的發展期、隋唐的成熟期、宋元明清的鼎盛期到近現代的轉型期論述了家訓的發展歷程及其背后的文化內涵[1]。關于家訓在特定時空的研究,有如王衛平、王莉認為“明清蘇州家訓數量繁多、形式多樣、內容豐富,其中多數家訓依譜而生,形成家譜與家訓共同昌盛的景象。”[2]至于家訓的功能意義,徐秀麗將其分為修身、治家、睦友、處世、教學、婚姻、擇業和仕宦8大類[3]。以單篇家訓為研究對象的論文較多,如《顏氏家訓》有352篇,《了凡四訓》有34篇,《錢氏家訓》則有11篇(1)數據基于筆者2020年7月10日就中國知網相關的關鍵詞統計。。此外,研究傳統家訓的文化淵源或某個具體德育功能的論文不計其數。
相較之下,少數民族家訓相關研究較少。單就壯族而言,韋笑宇僅就忻城莫氏土司家譜及相關內容展開論述[4],黃雁玲則著重討論壯族傳統家庭倫理的形成、內容、特質、演變及現狀等[5],但這些研究都未視壯族家訓為核心的研究對象。基于研究現狀,本文以廣西忻城縣壯族家訓歌《傳家寶》《傳家教》《傳家訓》為例,并結合該縣的民族、歷史、政治、教育、文化等因素,從成因、特點及功能三方面入手,描摹壯族家訓的基本輪廓,以豐富中華民族家訓文化研究的領域,豐富新時代家風建設的民族內涵。
一、壯族家訓的成因
(一)自身發展的需要
1.家庭建設的需要
壯語中ranz可表示房子,可表示家庭,甚至可引申為丈夫(戶主),(2)忻城縣壯族婦女稱自己的家、自己的房和自己的丈夫均為ranz gou。可見壯族人將不動產、人和家庭緊密聯系在一起,突顯其對家庭的重視。包括家訓在內的諸多壯族典籍在精神上都起到建設家庭的作用,但與漢族家訓不同,壯族往往將家訓編成山歌(壯語叫fwen)來傳唱,來進行家庭熏陶。值得注意的是,這三部家訓歌都名為“傳家”,顯然是家庭中的長者用來引導和訓誡晚輩的。教育晚輩與壯族文化中的“貴少”[6]傳統相契合,除了稱呼上以子名父、以孫名祖之外,將子女教育成才、光耀門楣才是真正的“為之計長”。另外,家訓也符合壯族尊老的家庭建設需要,因為家訓多為具備一定話語權的家長所撰寫,所以提倡尊老是必然的,如《傳家寶》則圍繞壯族的孝文化來展開。同時,壯族家訓還反映男女分工、夫妻平等、兄弟和睦等內容,詳見《傳家教》《傳家訓》。總之,家訓基本滿足了壯族家庭建設在精神上的基本需要。
2.家族政治的需要
弗雷德里克·詹姆遜說“沒有什么事物是非社會和非歷史的,事實上,一切事物‘在最終的分析中’說到底都是政治的”[7],的確,壯族家訓自然也是社會與歷史的產物,并指向其時的家族政治。《傳家寶》第283、284句曰“民國第二年,認可我才說”[8]783,可知這三部忻城家訓文獻定形于1913年,正值土司漸漸退出歷史舞臺、舊桂系主政廣西的時代[9]。其時的壯族家庭并非孤立的存在,而是處在家族體系之中,如林耀華《金翼》、陳忠實《白鹿原》所描寫的家族。長老權力的建立與鞏固在思想上需要家訓來維持,因為某種程度上家訓反映的思想就是長老意志。在家族內部,家訓有引導性的一面,它指引家族成員(尤其是后生晚輩)邁向族內長老所預設的方向,從而達成家族一榮俱榮的功效;家訓又有強制性的一面,它起到了家法的實質作用,約束著家族成員的行為,堅守家族行為的底線。在家族外部,家訓具有家族凝聚力的作用,由它規訓所建立和鞏固起來的勢力使得家族在與其他家族,甚至是國家權力進行對話時,能一定程度上維護自身利益。
3.民族進取的需要
壯族是一個開放的、包容的、極具進取精神的民族,“自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以來,壯族及其先民的文化就不是封閉性的。壯族先民曾經將本族文化傳送到華南以外的地方,中原文化、吳越文化、湘楚文化、巴蜀文化、滇黔文化都以不同的方式,從不同的側面,在不同的程度上,對壯族文化的發展起到各自的作用。”[10]在“多元一體”的民族格局下,對融入中華民族大家庭集體的渴望使得壯族在弘揚自我文化精華的同時,也會不斷地吸引“他者”文化的精華,故而“見賢思齊”的進取思想使得壯族人在民族交流中不斷自我建構,如仿漢字“六書”造字法來創制記錄壯語的方塊壯字,又如將諸多漢族故事改編成壯族山歌來傳唱。至于家訓,更是壯族人“見賢”于漢族家訓文化后的民族化生成與發展。
(二)受外部環境的影響
1.受傳統儒家思想教育的影響。何成軒認為,秦漢以后,儒學逐漸進入壯族地區,并在壯族社會中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11]。單說產生《傳家寶》等三部壯族家訓文獻的廣西忻城縣,它于明洪武三年(1370年)始辦縣學,宣德元年(1436年)停辦。弘治九年(1496年)降為土縣后“例不建縣學”,直到康熙年間,莫氏土官在衙署右側設義學[12],爾后私塾漸多。到了民國初年,忻城縣境內的“新學”興辦情況為:民國2年,思練國民小學、三寨國民小學開辦;民國3年,大塘國民小學開辦;民國6年,加仁國民小學開辦[13]12。此外,鄉村依然盛行私塾教育,學習傳統儒家典籍。忻城壯族三浪村的情況是“清代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新文化潮流興起,廢科舉制,改革學制。民國9年(1920),私塾蒙館改為國民基礎小學。”[14]可見從被廢除到改為國民基礎小學,又經歷了15年的傳統私塾教育。而稍晚興學的忻城壯族勃旺莊則“1932年(民國21年)至1936年(民國25年),由韋金輝任校董,先后在韋金輝和韋作新家辦私塾……他們學習《三字經》《孟子》和《幼學瓊林》。”[15]從明朝到民國,傳統儒家思想教育都自然而然地影響著壯族人民的思想,包括儒家“庭訓”的相關思想,故而壯族家訓文化應運而生。
2.受土司崇尚漢文化的影響。包括忻城莫氏在內的廣西土官大都有偽造漢裔的情結和行為,“這種觀念,先從土官和土官家族開始,后來逐漸波及普通的平民百姓,進而發展成為清中葉,大多數壯族人都存在的一種普遍情結。”[16]上行下效,如忻城縣思練鎮新練村六個屯(3)此六屯為板兒屯、板塘屯、板朝屯、板么屯、岜直屯、六悶屯。的韋氏壯族村民之堂號多寫“京兆堂”。廣西土官此舉除了統治的需要之外,還體現他們對漢文化的推崇,如忻城縣莫氏土司官族中流傳于世的有文20篇、詩98首、聯12副[17]。其中,莫氏用漢字寫就的、有家訓意味的文章有土官始祖莫保的《力田箴》、第四任土官莫魯的《官箴》、第七位土司莫鎮威的《訓蔭官》、莫崇詔的《遺訓》……崇尚漢文化的忻城土官在民國十七年(1928年)才正式退出歷史舞臺。而在近500年的土官威權之下,普通壯族人民在各方面自然而然地接受漢文化,尤其是漢文化中“耕讀傳家”的思想——這源于壯族是一個崇尚稻作“那”文化的民族,其文化基源就是“耕”,加上受土司影響而熱衷于科舉取仕的“讀”,所以很自然地將“耕”與“讀”結合起來,反映在壯族家訓之中。
二、壯族家訓的特點
(一)風格的“歌”化
歷史上保存下來的家訓多出自名人之手,傳于名門望族之后。這些名人及背后的名門望族在傳統漢族社會中可歸類為“大夫”和“士”階層,“在封建社會制度中,大夫和士是統治階級的一層,雖則在統治階級中說是很低的一層,但究竟還是統治者,是握有政權的。”[18]可以說,作為家庭或家族文獻的漢族家訓一定程度上是國家意志的延伸,是“大傳統”和“小傳統”的有機統一體。
如果說這些保存下來的家訓是文官家訓,突顯其“文”的話,那么壯族家訓則是歌者家訓,突出其“歌”化的一面。首先,就編撰者而言,壯族家訓多平民兼民間歌者。蒙元耀先生在收集、翻譯研究《傳家寶》《傳家教》《傳家訓》三壯族家訓文獻時僅能追溯到文獻的擁有者是梁佳祿先生(忻城縣城關鎮高塘村拉料屯人,2012年時56歲,農民兼民間歌手),但已無從得知編撰者為何人。原抄本上也沒有任何原作者的相關信息,但可以肯定的是,編撰者是一位民國時期精通壯族山歌的民間歌者。其次,此三部壯族家訓歸為壯族山歌,屬于韻文的一種,故突顯其押腳韻和押腰腳韻的特征,如《傳家寶》第41-42句的拼音壯文寫道:“lwg deng seak ngoenz bingh,boh meh cienh mbouj dingz.(兒生一日病,父母轉不停。)”[8]734其中bingh和dingz屬于尾—尾押ing韻,又如《傳家教》第11-12句的拼音壯文寫道:“meh laux buz gwnz caz,gamz daek ma ciengx meh.(老鴉伏叢上,仔銜蟲養母。)”[8]792其中caz與ma屬于尾-腰押a韻。第三,這三部壯族家訓均屬于壯族山歌中的“勒腳歌”,體現了循環反復吟唱的特點,即歌本內(從開篇算起)每8句為一腳,每腳內部各句的吟唱順序為1—2—3—4—/—5—6—1—2—/—7—8—3—4。可見,第1、2、3、4句都要重復吟唱一遍,腳內每4句為一個意義單元(用“/”劃分)(4)關于勒腳歌,蒙光朝在《論壯族勒腳歌》(載于《民族藝術》1989年第3期)一文中描述道:“勒腳歌,以三首短歌為一組,三首互相勒腳。即第一首開頭兩句,拿來做第二首的第三第四句;第一首的第三第四句,拿來做第三首的第三第四句。”李娜在《論廣西民歌中的重復手法》(載于《民族藝術》1994年第3期)一文則說:“在壯族、毛南族民歌中有種具有高難度詩律技巧的體裁,稱為勒腳歌。歌詞每首八句,分為甲乙丙丁四聯,其中兩聯重得秋一次而得十二句。唱時分三按勒腳原則選唱為甲乙、丙甲、丁乙。”此二者之所言,與筆者所述異曲同工。。
(二)內容的世俗化
歷史上影響較大的家訓往往體現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思想,如諸葛亮的《誡子書》主要規訓后人“靜以修身,儉以養德”,又如司馬光在《家范》中推崇“禮”。相比之下,壯族家訓的內容并沒有宏大、高遠的規訓,而是更世俗化,更貼近普通壯族人的日常。
關于孝道,壯族《傳家教》細致入微地呈現各個生活的片段:反對“任有薯有芋,自個吞入嘴”(5)本文所引注皆自蒙元耀先生之譯文,其中某些譯句有所改動。,而主張“咱有魚有肉,念父母在心”[8]798,認為“背公婆私吃,這種人不孝”[8]818,而“端水洗臉腳,也算還情意”[8]813。
此外,壯族家訓《傳家訓》更是假設在各種可能發生的、世俗化的生活場景之中加以規訓——
訓出門在外者:“外出去求人,不要出差錯。帶錢財過路,莫露賊人見。若外出久住,應該要寄信。父母親盼望,免妻兒查問。”[8]855-856
訓賭博者:“財錢人亂用,有幾個出名。有時輸時贏,不是真本分。贏有人問錢,輸不見誰送。窮到脫衣賭,這回臉尷尬。”[8]856-857
訓做生意人:“做生意的人,千萬要良心。稱貨要公平,銀錢要明白。和氣客才來,要公平交易。早晚心要記,千萬要弄清。”[8]861-863
訓人莫做賊:“半夜做賊者,得吃咱別饞。不然人查知,咱不知咋說。先游街示眾,后送入衙門。挨打又挨抓,過后方知悔。”[8]871-872
訓人莫作奸:“別去嫖女人,花錢又丟命。我勸你們聽,別拿命玩笑。若不挨宰殺,挨打也受傷。撞見人主子,砍你就丟命。”[8]876-877
(三)文獻的共享性
歷史上較有影響的家訓多名為“×氏家訓”,如顏之推的《顏氏家訓》、錢镠的《錢氏家訓》、朱熹的《朱子家訓》等,這些家訓冠之以姓氏,既突顯家訓的獨特性,又強調了家訓適用對象的特定性。相比之下,壯族家訓起于家庭或家族內部的規訓,但又不斷突破某一家庭的藩籬。可以說,《傳家寶》《傳家教》《傳家訓》既是忻城歌手梁佳祿先生家族所獨有的,但又是面向所有家庭的。
《傳家寶》開篇寫道:“拿筆寫歌書,傳揚傳家寶。任老人少年,要報父母恩。教子孫后代,到鄉下傳唱。此時思不周,過后悔不及。”[8]725-727這里“到鄉下傳唱”句點明了“傳家”不僅僅是傳于家庭內部,而是推己及人,傳到別家,讓更多能看得懂方塊壯字的壯族人傳習其中的內容與思想。該家訓文獻結尾又寫道:“最后囑歌書,任你們誰用。到何時有空,送它去傳揚。因才華有限,把歌傳圩上。君子有才華,讀到就動心。”[8]787-789“把歌傳圩上”句已說明壯族傳揚歌更有跨族際的共享性,因為“圩上”的受眾則不限于壯族內部,還有同趕一圩的漢、瑤、仫佬、苗、回、侗等其他14個兄弟民族。壯族家訓的共享性使得它被諸多歌者、學者歸為倫理道德傳揚歌之列,彰顯其社會功能。饒是如此,壯族家訓最初是作為家庭教育文本而存在的,之后以沖破家庭、族際之限界而被傳揚,反映了壯族民間在家庭思想教育方面的無私性。
三、壯族家訓的功能
(一)勸孝
壯族現階段崇尚的孝文化是本土孝思想與儒家孝文化有機結合的產物。《傳家寶》中“任年老年少,要報父母恩”一句點出了該家訓的目的是行孝。與漢族家訓相比,該家訓不直接以訓誡的口吻來達成家庭教化的作用,而是寓教于樂。從第9句到第200句鋪敘了父母與子女生命的交集,包括如下的子單元:1.母懷胎身心不適,2.兒出世受珍愛,3.兒哭母撫,4.兒睡干處母睡濕,5.兒病求醫,6.寄名求平安,7.為兒買衣食,8.囑兒防水火,9.送兒讀書,10.替兒娶妻,11.兒媳回門丟父母,12.鬧分家,13.兒媳不理父母,14.兒媳虧待老人,15.病倒無人照顧,16.死后棺前裝哭,17.死后做道場,18.論不應薄生厚死。第201句到第256句以侯神三子的不孝與孝、孟宗跪求冬筍、董永賣身葬父、五娘賣發養老人的故事加以補充,爾后引出“棄老型故事”的“換位觸動型”亞型,再次點明勸誡目的:“若不愛父母,老日也臨身。棄天地不要,咱將來也老。咱瞧父不值,兒照例施行。老了倒無用,話就戳心頭。”[8]778-779
《傳家教》則以羔羊跪乳來質問與父親分家而獨食魚肉者,以烏鴉反哺來勸人報父母恩情。之后用大量篇幅來對比生與死,勸晚輩應重視父母在世時的行孝,體現了壯族的厚生思想。該家訓文本較明確提出“一要養母親,二也要還恩”的要求。之后以“當初母生育”“兒病又要醫”等來要求以同理心來照顧年華老去的父母。
(二)勸耕讀
儒學南漸以來,迅速在壯族地區成為文化教育的重要內容。洪武十七年(1384年),忻城教諭駱基上奏曰:“洪武廿二年(1389)十月廿八日,明太祖朱璋準忻城教諭駱基奏,免忻城縣學歲貢生員。口諭:‘邊夷設學,姑以導其向善耳,免其貢。’”[13]7可以說,官方對儒學的推動對其在忻城的傳播影響很大,同時也影響了壯族人的經世思想。而在儒家思想中,“耕讀傳家是鄉土中國生活觀念的底色”[19]。故《傳家訓》云:“讀書與做工,都是傳家寶。任青年老人,勤奮就有吃。”[8]836“任青年老人”句與“讀書與做工”相對應,說明“讀書”事業是終身的,而這種終身事業又與科舉制度掛勾,契合了古諺“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同時“做工”則專指做農活——壯族的農耕歷史或可追溯到早期人類水稻培育和種植的時期。所以說,壯族家訓中耕讀傳家的思想是壯族本土文化與儒家文化相結合的文化產物。
(三)勸惜時
從《論語·子罕篇》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到辛棄疾的“可憐白發生”,從《增廣賢文》中的“一寸光陰一寸金,寸金難買寸光陰”“黑發不知勤學早,轉眼便是白頭翁”到《曾國藩家訓》中的“黎時即起,醒后不沾戀”,漢族古代文學和勸諭名言中的“惜時”是一個經久不衰的主題。壯族《傳家訓》則寫道:“一日盼清晨,一年就盼春。人們來天下,想吃就要勤。活莫留后日,怕將來天變。活計別留著,怕明天有事。”[8]837-839其中前兩句與南朝蕭繹《纂要》“一年之計在于春,一日之計在于晨”句異曲同工;后四句則與明人錢鶴灘《明日歌》“明日復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萬事成蹉跎”相當,同樣體現了壯族人對光陰的珍惜。
《傳家訓》又道:“人怕熱怕涼,來世上冤枉。不怕你會算,好漢來也窮。春秋他生氣,冬夏他又嫌。月亮跟太陽,日夜走不停。”[8]839-840“熱”“涼”對應 “春秋”和“冬夏”的四季意象,與漢語“寒來暑往”表示時光流逝相近。而漢語中,“月亮”和“太陽”的意象也常與時光飛逝有關,有如“烏飛兔走”“兔走烏飛”“日月如梭”等;壯族人則常以月亮、太陽的光亮來表示光陰的飛逝,如忻城壯語中用“mbwn laep youh rongh(天黑了又亮)”表達時光易逝。作為稻作文化(“那”文化)發達的民族,壯族家訓中的惜時自然也少不了對農時的勸誡,有如“春時要耕種,秋到才得收”句等。
(四)勸為人處事
“家庭是社會的細胞,注重家庭道德教育,穩定家庭結構及人倫關系,對于治國安邦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因此,古人極重‘齊家’,父慈子孝、夫妻愛敬、兄友弟恭、平和禮讓在古代家訓文獻中隨處可見。”[20]壯族家訓也體現相似主題,在提倡孝文化之余,《傳家訓》云:“兄弟要同心,人家會禮讓。父母要孝順,做萬事皆成。朋友別怠慢,親戚別斷情。貧富皆看望,別給人看賤。”[8]863-864這句訓言指出在為人處事時如何處理與兄弟、父母、朋友、親戚的關系。“禮”“孝順”“別怠慢”和不分“貧富”說明壯族自身文化的底色已與儒家文化融為一體。《傳家訓》又云:“下人要待好,人方有心幫。別說話刻薄,人家知活計。任上村下村,說話別去損。講話要公平,上下人皆知。”[8]864-866此訓言由親友拓寬到對待家中的傭人及周圍村中的四鄰,是一種“遠親不如近鄰”的人際觀。壯族的士人與地主階級有著眾多的交集,所以處理主仆關系既是家庭和諧的重要內容,也是保持經濟生產的有力保障。
對于經濟上的糾紛問題,則訓曰:“銀錢與地租,千祈要分明。欠多弄不清,怕官家過問。咱們來天下,得吃別吹噓。見幾人能干,家當還四散。”[8]866-867這里進一步明確在財物的處理上要遵紀守法。同時面對財富,不可吹噓,堅守“財不外露”的處事思想,避免“家當還四散”的悲劇。
(五)勸安分
子夏(《論語·顏淵》)說:“生死有命,富貴在天。”此觀點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壯族家訓中的財富觀,有如《傳家訓》的“發大財是命,發小財靠力”和“命帶富貴者,干啥都發財。窮人命就衰,拼死也是窮。窮人命不富,四處人皆說”。[8]853-855“在孔孟為代表的儒家思想中,‘命’包含兩個層次:一表示‘天命’,代表至上神 ——‘天’的意志,是道德的最后根據;二表示通常所謂命運,是對人的客觀限制,反映了人的有限性。”[21]“發大財是命,發小財靠力”后一句是“任窮家富戶,別胡亂來搞”。可以說,儒家的命運觀讓人認清某種限制性,或是“天命”的或是客觀現實的,從而引出真正要規訓的內容:無論貧富,都不能以不義的手段獲取財富。同樣,“窮人命不富,四處人皆說”后一句為“若有一件衣,也不挑花色”。不挑衣服的花色品種和“別胡亂來搞”一樣,要人遵守“本分”,而“本分”又與儒家思想中的等級觀念有關。這種等級觀念也即費孝通先生所謂的“差序格局”。這種等級觀念的進一步外推,即整個傳統社會的等級制度。故,壯族家訓中的貧富觀也是傳統儒家文化的發展。
四、結語
2015年春節團拜會的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不論時代發生多大變化,不論生活格局發生多大變化,我們都要重視家庭建設,注重家教、注重家風,使千千萬萬個家庭成為國家發展、民族進步、社會和諧的重要基點。”[22]講話強調了家庭、家風建設在新時代的重要性,同時也強調了時代變遷中家風建設的傳承性。這就使得家風建設的研究不僅限于歷代名家的傳統家訓,家風建設應該是全民性的。新時代語境下反觀壯族家訓文化,可獲取諸多啟示。傳承和發揚壯族家訓文化有利于在新時代建設壯族家庭。弘揚壯族家訓文化有利于針對性地建構具有時代精神與民族特色的壯族家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