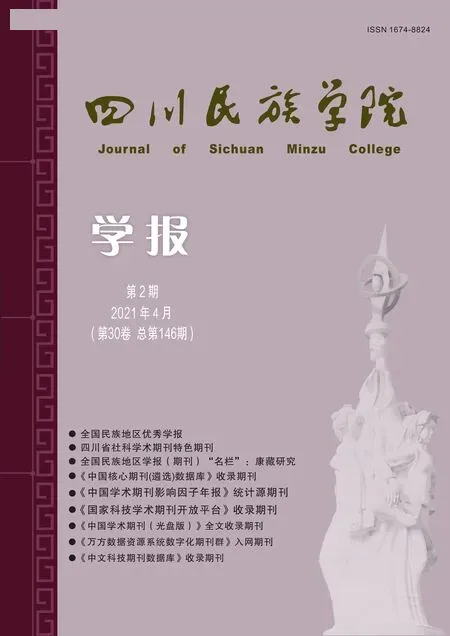旅游發展背景下的西北民族社區空間生產分析
——以甘南州郎木寺鎮為例
梁旺兵 吳宇鋒
(西北師范大學,蘭州 730070)
我國西北與西南地區是少數民族主要的聚居地,這些少數民族聚居地作為地緣相近、血緣相親、價值觀趨同和人口同質性強的傳統性共同體,促進了民族社區的產生[1]。隨著中國經濟的進步、社會結構的調整和思想觀念的變化,民族社區逐漸演化成為兼具精神屬性和空間屬性、以文化為核心的“地域綜合體”[2]。西北民族社區的自然、人文旅游資源富集,是自然環境、社會性、記憶和想象交織的空間,甘南藏族自治州的扎尕那、拉卜楞鎮和郎木寺鎮等民族社區因其獨特的空間景觀、民族風情和宗教文化,成為游客首選的文化旅游目的地。但旅游發展使得西北民族社區原有的空間被開發、設計、使用和重構,間接影響著旅游者的滿意度與旅游體驗[3]。總的來說,西北民族社區旅游發展背景的空間要素從邊緣走向核心[4],凸顯著社區居民對于空間生產實踐的價值判斷和態度取向[5],也契合社會學、地理學研究“空間轉向”和“社會轉向”的發展趨勢[6][7]。在此背景下,本文以具有典型性的甘南州郎木寺鎮為例,基于列斐伏爾空間的“三位一體”辯證法,著重回答物質空間、精神空間和社會空間的變遷,對空間生產主體——社區居民的態度、行為的影響問題,從而在微觀層面加深對旅游影響的認知和理解,為旅游領域空間生產的研究提供有益探討。
一、研究設計
(一)理論導入
空間生產的邏輯起點始于空間中要素、功能和活動的發展變化對空間本身的建構,從而要求我們以相對的、動態的眼光理解空間的內涵[8]。20世紀下半葉,法國社會學家列斐伏爾從“社會—歷史—空間”的視角提出空間的“三位一體”辯證法,明確了空間生產的概念和分析框架(見表1)[9]。列斐伏爾的空間生產理論超越了“二元論”和“兩極論”,將“(社會)空間是(社會)生產”作為核心,把空間置于日常生活的起點,指明了空間與生產的耦合關系[10]。

表1 空間的“三位一體”辯證法的基本內容
在國外,Halfacree在對西方鄉村空間、話語權和定義研究的基礎上,依據列斐伏爾的空間“三位一體”辯證法構建了一個“鄉村空間三元辯證框架”[13][14]。Frisvoll將Halfacree的研究框架拓展為非物質維度、物質維度和個人維度,分析了旅游發展下權力在鄉村空間生產中的作用[15]。國內學者宗曉蓮首次以列斐伏爾的空間生產理論為工具,研究了麗江古城空間商品化的過程和對社會文化的影響[16]。郭文對周莊古鎮的居民旅游空間體驗[17]、旅游場域中的多維空間生產[18]和居民的社會空間感知[19]進行了深入研究,指出了社區型文化遺產地的旅游空間生產與形態轉向[20]。孫九霞則將空間生產置于旅游發展的背景下進行分析[4],對民族旅游社區的交往空間的變遷及特征[21]、社會空間生產的過程、表征及影響[22]和空間想象與旅游體驗之間的相互作用進行了探討[6]。近年來,資本、權力給空間生產帶來的異化,使得“空間正義”這一概念逐漸成為旅游研究的熱點,李創新對旅游空間正義邏輯、語境和理念進行了思考[23],胡大平對旅游空間正義的性質、重心和價值作了分析[24]。總的來看,在旅游領域空間生產的研究呈現出兩個趨勢,一是從宏觀層面逐步深入微觀層面,體現在研究對象從城市到鄉村古鎮再到民族社區的演變過程;二是關注旅游發展下空間重構過程中對主體的空間壓迫與剝奪,體現在學界對空間生產的弱勢群體政治與倫理話語的高度關注。
(二)研究案例地
郎木寺鎮因寺興鎮,由甘南藏族自治州碌曲縣和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若爾蓋縣共同管轄,位于白龍江北部的“賽赤寺”和白龍江南部的“格爾底寺”均屬藏傳佛教格魯派寺廟,是安多藏區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漢藏“茶馬互市”沿線的重要交易場所。本文所指的郎木寺是位于白龍江北部的“賽赤寺”。
郎木寺鎮的旅游發展可大致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20世紀70年代至90年代,主要是國內外背包客從若爾蓋北上來到郎木寺鎮觀光游覽,以寺院為載體締結的宗教空間掌握著空間生產的話語權,旅游發展對社區居民生活方式的影響較小。第二階段是20世紀90年代至2017年九寨溝7.0級地震前,在該階段,郎木寺鎮的交通和基礎設施建設不斷完善,旅游業態日益豐富,小吃店、賓館、手工藝品店和馬隊公司不斷涌現,牧業、寺屬產業的傳統地位受到削弱,依托消費主義形成的商業空間迅速發展[25],游客接待人數和社區居民旅游收入不斷增加。第三階段是2017年九寨溝7.0級地震后至今,這一階段郎木寺鎮旅游發展的腳步放緩,一是郎木寺鎮作為甘南川西自駕游線路上的重要一環,與九寨溝的自然資源具有一定的互補性,九寨溝地震使得游客赴九寨溝旅游的意愿減弱,間接影響了郎木寺鎮的游客接待人數;二是由政府牽頭進行的主街片區改造工程使得原有的空間成了標準化的“產品”,現代化、同質化的景觀難以充分響應郎木寺的民族文化和宗教文化[26],影響了社區居民的感知和游客的滿意度。
(三)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質性研究方法,于2019年3月17日—24日和7月15日—23日前往甘南州碌曲縣郎木寺鎮進行觀察和深度訪談,深度訪談的對象為社區居民,即除寺院喇嘛以外,郎木寺鎮的戶籍居民和在郎木寺鎮停留一年以上的非戶籍居民。為克服語言障礙、民族與宗教文化的差異,研究團隊選擇非概率抽樣法中的滾雪球抽樣,先找出目標群體中個別成員(L-1),對其開展初步的調查,然后根據其提供的有關其他成員的信息,逐步拓展調查范圍,直到得到滿意的全部樣本單位為止[27]。訪談對象的基本信息見表2。

表2 訪談對象的基本信息
以上訪談對象在性別構成方面較為合理,年齡構成上最小為8歲,最大為53歲,民族以藏族為主,兼有回、漢和白族,文化程度方面,高中及以下學歷占大多數(含不詳),職業分布以參與旅游經營為主,兼有包車司機、放牧等工作方式,戶籍居民與非戶籍居民的比例均衡,具有較好的代表性。
(四)資料分析
首先對甘南州碌曲縣郎木寺鎮觀察筆記和深度訪談轉錄文本進行開放式編碼,標注資料中表征概念類屬的各個意義單元,命名有顯著意義的子類屬;其次進行軸心式編碼,構建各個意義單元乃至子類屬之間的有機關聯,挖掘有描述、解釋或詮釋功能的次類屬;最后進行選擇式編碼,在已確定的次類屬中,探尋一個有統領性的主類屬,將其置于理論模型的主導地位。

表3 編碼分析確定的各級類屬
(五)分析框架
本文在列斐伏爾空間的“三位一體”辯證法基礎上,嘗試構建旅游發展背景下西北民族社區空間生產的分析框架(圖1)。

圖1 旅游發展下西北民族社區的空間生產的分析框架
其具體內涵呈現如下:空間的實踐是指被感知維度的物質空間,在空間利用的博弈中,其生產的結果則以物質空間中各種產品及其本身表現出來,助推了物質空間的資本化;空間的表征是指被構想維度的精神空間,體現在話語建構式的空間活動和精神性空間再現下,景觀嬗變與社區居民的地方依戀、旅游者的空間想象之間的沖突,引發了社區居民的失地感;表征的空間是指日常生活維度的社會空間,體現在與旅游交往相聯系的社會關系、行為規訓的重新建構過程中,凸顯了社會空間的世俗化。
二、旅游發展下西北民族社區的空間生產
(一)空間的實踐
空間的實踐作為社區居民進行生產和擴大再生產的互動場所,在郎木寺鎮旅游發展的第二、第三階段,郎木寺鎮資源所暗含的資本屬性是吸引各方對生產性和消費性物質空間投資的主要原因,郎木寺臨近四川九寨溝的區位資本、主街的土地資本、賽赤寺與格爾底寺及其物化的民族宗教資本以及歷史文化資本,已經成為凸顯郎木寺鎮相比其他物質空間更具有消費吸引力、投資回報率的因素。
我一開始在拉薩大橋開店,經營了十年,那個時候生意比較好,但13、14年以后房租就高了,不賺錢。所以我就來郎木寺鎮了,這兒的房租我還能承受,開店第一年時生意特別好。
——L-2文玩店老板
以前我們最起碼的水、電、下水道都很吃力,現在游客多了,政府給修得比以前好多了……郎木寺不僅僅是個寺院,還有自然景色和神話傳說。
——L-6學生兼職導游
開這個店一是受我妹妹的拉攏,二是覺得郎木寺旅游發展前景比較好,主要是離四川九寨溝近,覺得比拉卜楞鎮未來強。
——L-18手工藝品老板娘
隨著郎木寺鎮游客人數的不斷增加,政府認識到了空間消費的巨大潛力,資本投資的積極性也愈發高漲,2018年在碌曲縣政府為主導的48個項目中,有27個直接服務于郎木寺鎮的城鎮建設,郎木寺鎮交通、接待、水電等基礎設施的改造升級,不僅優化了旅游發展的“硬環境”,也間接地將社區居民吸引到了旅游發展的進程中。
郎木寺鎮作為依托寺院發展而來的村落,以藏傳佛教為核心的寺院空間是僧尼和藏族民眾的信仰和精神依托,依照格魯派“曼陀羅”理想圖式設計的寺院建筑、轉經道,使郎木寺的空間形式極具宗教象征意義[28],其給予了郎木寺僧尼和藏族信眾強烈認同感和歸屬感,是郎木寺鎮神圣性的空間占有。在郎木寺宗教感召力的影響下,僧尼和藏族民眾必然向這一朝圣地云集,原始的農牧業和信眾供奉只能滿足其基本的生存需要,在寺院周圍諸如經營紡織印染、手工藝品、服裝日用品等傳統商業店鋪作為對寺院內斂型經濟的補充,形成了郎木寺鎮世俗性的空間占有。郎木寺續部、醫學和雕版學院相繼完成重建,對游客的吸引力進一步增強,外向型的旅游經濟加強了郎木寺鎮內部社會與外部世界的聯系[29],游客現代化的衣著服飾、多元化的思想觀念和高層次的消費需求對社區居民的物質生活方式造成了一定的沖擊。
我兒子出去和朋友玩就會去網吧,聚會、過生日就會去飯館茶館,沒有旅游的話就沒有這些飯館茶館。我的大女兒今年22歲了,她小時候就沒有這些個花樣,我兒子花錢就比我大女兒花得多。
——L-1賓館老板娘
我們做的是新派藏餐,比如你們吃的這些糌粑,感覺不會有那些油膩的酥油味,我們都是經過改良迎合游客的口味,本地人有時也會來吃……以前的話我們每年賺的錢就是買賣牛羊,不會去投資,也不會去讓孩子們上學,不過是買珊瑚、買蜜蠟、買金子戴在身上。但現在幾乎都是怎么想辦法再去賺錢,把房子修繕一下,去買輛小汽車。
——L-11酒吧老板
我們不是平時不穿藏袍,我們這兒有火鍋什么的,上菜什么的真的很不方便,再加上我們廚房離得比較遠,藏袍你看著穿起來很漂亮,但是邁大步什么的特別不方便……我的朋友們現在藏袍也穿得少,一般都是漢服,除非我們過節日。
——L-16旺季餐館兼職服務員
隨著旅游開發進程的加快,被游客和社區居民所裹挾的空間消費需求同郎木寺鎮原始的神圣性、世俗性空間占有呈現出不相匹配的狀態。在國家“以寺養寺”政策的支持下,寺院除了修建商業停車場、收取寺院門票費和擴大游覽區域之外,還通過買賣土地資本,開設了達倉郎木寺院賓館、集貿綜合市場和藏醫院,直接參與商業經營活動,以謀求更大的旅游收益。在寺院外圍區域,社區居民消費觀念和偏好的變化打破了原有的以生活必需品為主的消費結構,賓館民宿、餐飲小吃、咖啡廳酒吧和現代紀念品店不斷涌入。在空間利用的博弈中,利潤較高的旅游服務類店鋪往往掌握更大的話語權,傳統商業店鋪逐漸分散與萎縮。當資本直接投資于神圣性、世俗性的空間占有,以滿足空間消費需求時,物質空間就成為資本增值的直接途徑和手段,即空間的資本化[30],這凸顯了資本對物質空間的主導和塑造作用。
空間的資本化將大規模的“物流”“信息流”“資金流”和“旅游流”帶給郎木寺鎮的物質空間[31],不可避免的使得空間生產出現異化現象:身著僧服的年輕喇嘛聚集在寺院門前主動向游客詢問是否需要價值“一張紅票票”的導游服務;訪談對象白龍江源頭小向導(L-15)佩戴著印有支付二維碼的胸牌,不太熟練地講解著各個景點的歷史傳說;包車司機(L-17)坦言會根據客人的情況報出不同的價格,也有固定的酒店賓館為其提供客源。此外,淡旺季差距明顯的商鋪、種類繁多的賓館民宿和鮮有居民問津的手工藝品店也顯現出物質空間的“去生活化”趨勢。
社區居民作為相對弱勢的空間生產主體,面對空間的資本化大背景中規訓力較強的物質空間,往往妥協于異化現象和“去生活化”趨勢,在充滿異化又滿載希望的日常生活中生存,一部分社區居民被納入旅游服務業中來,成為空間占有的利益相關群體,另一部分社區居民則不得不適應旅游發展下新的物質生活方式,成為空間消費的追隨者。
(二)空間的表征
空間的表征作為被構想的精神空間,體現了意識、權力通過話語建構式的空間再現和精神性的空間活動對西北民族社區富有宗教、民族色彩景觀符號的建構、再現和開發。在郎木寺鎮旅游發展的第一階段,改革開放后政府實行的“草畜雙承包責任制”改變了牧區的生產方式,使得逐水草而居的牧民有了固定的生活場所,以土石筑墻、木板裝修,住宿與畜棚分上下兩層聯為一體的踏板房應運而生。對于社區居民特別是藏族牧民而言,一方面改善了其生產生活的空間,另一方面則增強了對郎木寺鎮的情感聯結、認知聯結和意欲聯結;對于游客而言,極具民族特色的人居建筑、富有宗教特色的寺院建筑在政府商業宣傳、旅游中介策劃營銷下,成了個體對郎木寺鎮社區旅游的知識、印象、意向及精神性思考的來源[32],但社區居民的地方依戀、游客的空間想象與空間體驗之間往往無法保持一致[6]。
哎,從拉薩剛到這時我覺得還挺好。現在的話感覺就不怎么樣,有100個人來的話,一半以上都說很失望,覺得跟宣傳比有天地相差,就兩個寺嘛。
——L-2文玩店老板
說老實話,旅游人數從我20歲到現在一年不如一年,味道變了,很多東西都沒了,老工匠做的那個磨青稞的雕花藏式老磨坊,木頭做的藏式回式的踏板房,有一些保存下來的,但說拆就拆,一點都不心疼,民族特色搞沒了,都是大眾化的,誰來看。
——L-4西餐廳老板娘兒子兼特產店老板
理論上純粹空間的表征形式是觀念性的,它從精神空間中獲得觀念,并將這些觀念投射到現實世界去[33],體現了意識、權力所掌握的知識、暗含的秩序的表象化。在郎木寺鎮旅游發展的第三階段,政府進行了多次片區改造,除了完善水、電、暖等基礎設施以外,還包括翻新主街的路面、粉刷主街兩側店鋪的墻面和整治街道亂擺亂放占道經營等內容,但社區居民對此頗有微詞。
我們是旅游飯館,有個保護了三十多年的木質招牌(寫有郎木寺鎮的路線、旅游景點和菜品),但在二樓走廊擱著不讓掛……一樓餐廳為了看著整齊劃一,只能把旗子取掉(天花板和墻上掛了許多驢友團的特色旗子),現在游客來了就問我為什么和宣傳上的不一樣了,我只能又掛回去。
——L-3西餐廳老板娘
現在街道上不讓擺攤,雖然表面看著干凈整潔,但這樣游客就慢慢地少了,收入就沒有了,現在關門的人太多了。得有氣氛,不能弄什么東西只為了表面好看,你看現在是旅游旺季,街道上又在挖路、粉刷和搭腳手架,游客也感覺到沒意思。
——L-9超市老板
無地方特色的低水平重復建設、大眾化的景觀符號,重塑著郎木寺鎮的建筑風貌和格局,消解著社區空間的差異性與多樣性,進而潛移默化地影響著民族、宗教文化。對于游客而言,媒體關于郎木寺鎮景觀特色的宣傳、背包客針對郎木寺鎮風土人情的描繪和記錄社區居民的言談舉止的文字記錄和攝影圖片,都是其建構空間想象的重要來源,但現實的社區空間與游客的空間想象之間存在較大的差異,進而削弱了他們的空間體驗和消費意愿;對于社區居民,特別是被納入旅游服務業的群體而言,往往通過集體敘事的方式回應游客的空間想象,但嬗變的景觀符號既無法支撐其對于郎木寺鎮社區文化的一致性表述,也不利于其通過生產行為將游客空間想象的內容通過物質化的形式表現出來[34],不僅引發了游客對于民族社區“真實性”的質疑,也影響了社區居民與地方價值觀、精神追求相聯系的地方感。
空間的表征作為在社會(或生產方式)中占統治地位的空間,對于政府、旅游開發商和本地鄉紳所進行的規劃控制,在旅游收益尚可的情況下,社區居民還能容忍“地方感”缺失帶來的負面影響,但2017年九寨溝7.0級地震和片區改造工程使得郎木寺鎮的游客數量驟減,七月份正值甘南的旅游旺季,但游客服務中心冷冷清清,主街兩旁關門的店鋪比比皆是,呈現出一片肅然的景象。
感覺近生意兩年沒有前幾年好了,街邊房子沒裝修之前挺好,最主要以前建筑物有古老的,但一翻修就全變樣子了,再加上九寨溝地震,來的人就更少了……以今年的情況看來基本就是不行了,有時候開單有時候不開單,我以后可能不會來給家里幫忙了。
——L-8手工藝品店小老板
就郎木寺而言,可能游客慢慢越來越少,我們也考慮這兩年撤出去,因為從這里特別興旺到現在,房租每年漲,游客每年減……說難聽了,我們從家里跑到鎮上做這家店,誰都沒有那么偉大,不是說傳播我們的文化啊,我還沒有達到那個境界,就是以營利為目的,如果在這里效益一天不如一天,人一年比一年少的話,我可能會第一時間選擇離開這。
——L-11酒吧老板
誠然,由意識、權力主導的建構、再現和開發將空間的表征引入現代化的進程中,但旅游者對于西北民族社區“真實性”的空間想象和居民基于景觀符號的地方依戀往往與其相悖,原本被社區居民的集體意識所構想的精神空間,成為與之迥異的“政府主導型”發展戰略下旅游產業化的載體,一定程度上擠占了社區居民的旅游收益、加大了社區居民間的文化差異,使社區居民的“失地感”較為明顯,甚至出現逃離郎木寺鎮的情況。
(三)表征的空間
不同歷史階段下社區的生產方式與其特定的生產關系所形成“親歷性”表征的空間,既是物質的,也是精神的,更是實踐的,體現著社會性與空間性辯證統一[11]。而社會關系作為一種具體的空間存在,一方面支撐著日常生活維度的社會空間,另一方面為社區居民的社會生活方式打上烙印。社區居民在旅游者的空間消費中或主動或被動地與其發生互動,形成帶有社會屬性和空間屬性的旅游交往,進而建構起復雜交織的社會關系,其中生物性生產關系——即民族、宗教和家庭成員之間等自然演變的關系占據著社會空間的主流,而物質性生產關系——即旅游發展下主客在物質資料的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環節所產生的關系則暗藏于日常生活之下[35]。
1747年,碌曲縣雙岔籍噶丹寺法臺堅參桑蓋應河南蒙旗親王丹津旺舒的請求,返里弘法創建郎木寺并任該寺法臺,遷來60余戶牧民居于此地作為香火戶,后又有大批藏族信眾來此聚居。當時,社區居民特別是藏族信眾同僧侶之間交往成為社會互動的主要形式,居民主動拜佛、轉經、供奉和接受寺院教育。那時開展牛羊、毛皮貿易的回族居民和經營傳統商業店鋪的漢族居民人數寥寥,其與僧侶、藏族信眾和游客之間除貿易外并無過多互動,處在社會空間邊緣化的位置。之后的旅游開發顯著地增加了郎木寺鎮的游客數量,也擴大了旅游服務業經營主體的范圍,大部分社區居民通過正規或非正規就業直接或間接參與旅游交往,為物質性生產關系提供了建構符合自己地位、身份特征的契機,社區居民之間、社區居民與游客之間以業緣為基礎的物質性生產關系成為社會空間的重要支撐。
現在生意都靠來過之后的回頭客(店內很多快遞單,很多打包好的牛肉干),他們覺得好就會把微信加上,多個朋友多單生意嘛,比以前靠天吃飯強多了。
——L-7牦牛肉特產店老板
我爸最初來這邊是給寺院加工那些銀器,后來游客慢慢多了就進了一些別的貨來賣……我們白族人在這邊有好幾家,都是云南一個地方的,平時也會一起吃個飯交流下,畢竟生意不好做,互相幫襯。
——L-8手工藝品店小老板
旅游發展下社會空間中社會關系的變遷表征著郎木寺鎮日常生活狀態的漸進過程,也帶來了社會生活方式的新實踐。舊時郎木寺藏傳佛教頗為煩瑣的行為規訓,如供養、包辦婚姻、送次子入寺為僧和天葬等,反映了生物性生產關系在社會生活行為方面的另類投射,更暗含了藏族民眾與寺院這一神圣空間的情感聯結。在滿足旅游者空間消費需求所進行的社會互動過程中,參與旅游交往的社區居民受到了全新社會觀念與價值觀的熏陶,凌駕于物質性生產關系的消費欲望與生活追求逐漸向社會空間滲透,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固有的行為規訓[36]。
我在縣城里上的高中,大學自己選了一個專業(法學),藏族學的人比較少,我以后可能不打算在這了……還有一些佛殿里面是放酥油燈的,但游客來的話很不放心,擔心安全問題,就改成了電燈,我覺得對儀式有一定的影響。
——L-6學生兼職導游
現在對寺院的供養壓力小了很多,一方面現在寺院自己都有旅游收入,不太完全需要依靠我們,另一方面許多喇嘛會被人請出去做法事,不用我們太操心。
——L-11酒吧老板
我們這邊結婚還是挺看重一些民族成分的,以父母介紹的居多,但現在也有相親和自由戀愛認識的……我老婆是她來甘南玩,我們就認識了,談到現在有六年了,平時她在蘭州,我在這邊。
——L-12青年旅社老板
與旅游發展相適應的行為規訓撕裂了籠罩在物質、精神之上的“神圣帷幕”,佛事活動讓位于世俗化社會空間的市場經濟邏輯,在宗教的世界觀指導下的婚喪嫁娶也在逐漸被世俗的觀念重新建構,社區居民開始重新審視他們用于理解和解釋世界的宗教信仰,思考著行為規訓的公共性與社會職能,辯證地看待改變和形塑社會空間發展的旅游業[37]。
我們自己的信仰還在堅持,寺院是要定時去的,不相信也說不上,相信也說不上,自己的生活自己決定,還是比較理性……游客也要自我約束,一些寺院的阿哥,不懂漢語,有的游客不尊重規定,就買票這個事兒跟阿哥吵,后來給他退了票才高興,讓我們感覺很寒心。
——L-6兼職學生導游
有一些特殊或者大型法事的時候,會有人在門口守著不會讓游客進去,像曬佛等對外公開活動的不會禁止游客進入,但必須遵守秩序……郎木寺后山有個天葬臺,一般我們用七天的時間來進行超度,然后再舉辦天葬儀式,在那種傷心的情況下,很多游客都會圍過來,讓我們很反感。
——L-11酒吧老板
天葬臺那個沒什么大不了的,也是讓你去看下人的一個輪回,有些游客有誤解,以為做天葬就是要上天堂,其實我們任何人從出生、成長到去世,一直在向大自然、花草樹木索取,所謂天葬就是在你死之后做人生最后一次供奉……許多人對我們民族有一些認識上的偏見,外面的一些新鮮事物,慢慢也會讓有些文化程度不高藏族同胞犯一些錯誤,不光是要求游客怎么樣怎么樣,我們也要做好自己。
——L-12青年旅社老板
旅游發展下彌漫著的社會關系和行為規訓的世俗化社會空間日漸消解著郎木寺鎮空間生產的神秘性、不可知性,似乎社區中藏族信眾的宗教信仰正在被現代性所“祛魅”,但宏觀層面上藏傳佛教影響力的下降并不能說明個體宗教信仰的缺失,藏傳佛教的儀式、活動中社區居民與游客比例的失衡與個體虔信的強度也沒有必然的聯系[38]。對于社區居民而言,“戒律存則佛法存,戒律滅則佛法終”,宗教信仰仍然有被堅守的合理性和現實性基礎,旅游只是改變了宗教精神表現形式,使其與世俗化的社會空間緊密地融合了在一起,而恪守藏傳佛教的倫理準則和道德規范、追求真善美才是堅守宗教信仰的主體與核心。
三、結論與討論
(一)結論
郎木寺鎮作為西北民族社區旅游發展的前沿,空間生產的實踐在政府、社區居民和游客等主體的相互作用下日漸復雜,在列斐伏爾“三位一體”辯證法的指導下我們可知:(1)在空間的實踐層面,被游客和社區居民所裹挾的空間消費,推動了神圣性與世俗性空間占有的變遷,引發了空間的“資本化”,處在弱勢的社區居民只能妥協于物質空間的異化現象和“去生活化”趨勢。(2)在空間的表征層面,權力對郎木寺鎮的建構、再現和開發將其引入現代化的進程中,一方面同旅游者對于西北民族社區“真實性”的空間想象相悖,另一方面使社區居民的“失地感”較為明顯,甚至出現逃離郎木寺鎮的情況。(3)在表征的空間層面,旅游交往使得以業緣為基礎的物質性生產關系成為世俗化社會空間的重要支撐,潛移默化地影響著與潛意識的神秘性、有限的可知性相聯系的行為規訓,但社區居民仍堅守著暗含合理性和現實性基礎的宗教信仰。
(二)討論
首先,旅游只不過是人們對于現代性生存條件“好惡交織”的反應和體現之一[39],在依托列斐伏爾的空間“三位一體”辯證法研究西北民族社區的空間生產時,需要思考如何剝離其他因素對于物質空間、精神空間和社會空間的影響,專注于旅游研究的視閾進行考察。
其次,空間生產的研究必須有一個明確的立場和清晰的正義判斷[9],西北民族社區空間生產的實踐中所產生異化現象,促使我們加深了對空間正義的思考:如何減少空間生產的實踐中權力、資本帶來的負面影響,如何在文化旅游發展的浪潮下實現社會主義性質的空間生產以及如何保證旅游發展中社區居民空間權益的公平和公正。
最后,盡管列斐伏爾的空間“三位一體”辯證法為研究空間乃至旅游空間提供了新的理論視角,但在后續的研究中要避免空間概念和空間生產邏輯的泛化,并非所有影響空間的要素和活動都能改變空間本身,即“生產”,要把握諸如占有、消費、想象、社會關系等重要因素和深層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