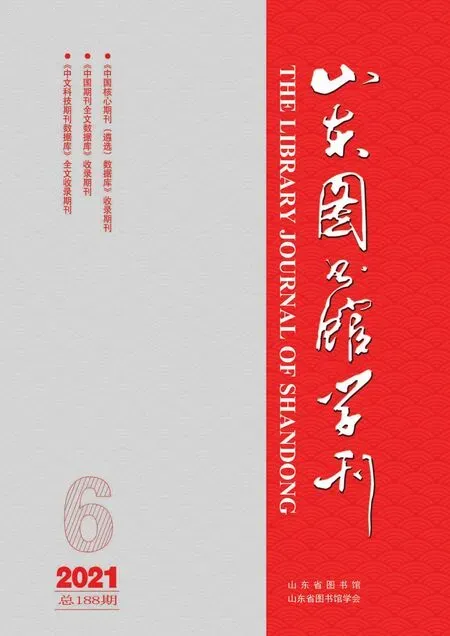云南少數民族古籍修復的探索與實踐
——以彝文古籍修復為例
楊敏仙
(云南省圖書館,云南昆明 650031)
彝族是一個有著悠久歷史、豐富傳統文化的民族,擁有“自成體系的文字符號系統,彝文記載了浩繁的傳世古籍,在彝文流傳使用的地區都有彝文古籍留存。”[1]彝文古籍是中華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保護好彝文古籍,就是保護和維系中華文化的根脈,是促進各民族共同繁榮和進步的重要舉措,是落實黨的十七大關于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要求的重要內容。保護好民族古籍,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中具有獨特價值和意義。
1 云南彝文古籍基本概況
據統計,云南省少數民族古籍達10余萬冊(件),其中彝文古籍達2萬余件。國家圖書館珍藏的古彝文典籍共有 592 冊(件),其中 500余冊是馬學良、萬斯年先生在抗日戰爭時期到云南武定縣慕連鄉那安和卿土司家,以及武定祿勸一帶彝區收集的。[2]如今,云南仍藏有大量的彝文古籍,這些彝文古籍主要分布在云南的昆明、楚雄、玉溪、曲靖、麗江等地區。2008年,云南省古籍保護中心牽頭向國務院申報《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國務院公布的截止第六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云南有81部少數民族古籍入選,而彝文古籍占有較高的比重達76.5%,共62部,其中包括云南省少數民族古籍整理辦公室收藏的《百樂書》清抄本;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民族事務委員會收藏的《尼蘇》一卷,(明)嘉靖十六年(1583)抄本(國家珍貴古籍名錄號02348);云南省楚雄自治州博物館收藏的《勸善經》存一卷,(明)刻本(國家珍貴古籍名錄號06745);云南省社會科學院楚雄分院、云南省楚雄彝族文化研究院收藏的《彝族六祖源流》一卷,(清)同治二年(1863)抄本(國家珍貴古籍名錄號09727);云南民族大學圖書館昂自明私人收藏的《阿詩瑪》一卷,(清末)寫本(國家珍貴古籍名錄號06777)等。[3]在這些入選《國家珍貴古籍名錄》的彝文古籍中,部分破損極其嚴重,在云南省圖書館的支持下已得到修復。
目前,云南的彝文古籍大部分收藏在高校圖書館、公共圖書館、檔案館、博物館和民族古籍整理辦公室等單位,仍有相當一部分收藏在民間私人手中,而民間收藏彝文古籍則以畢摩①畢摩是彝族傳統宗教中的祭司。在彝語中,“畢”為舉行宗教活動時祝贊誦經之意,“摩”意為長老或老師。畢摩在彝族社會中扮演著講述歷史,傳播知識,規范行為的文化教育角色,被視為“智者”和“知識最豐富的人”,是彝族歷史文化的記錄者、保存者和傳播者。收藏為主。近年來,隨著國家對民族文化的保護和傳承高度重視,部分彝文古籍收藏單位存藏條件得以改善。與此同時,民間收藏彝文古籍的保存方式則是簡陋的,多數畢摩習慣用帆布或麻布袋子儲存彝文古籍,極少數畢摩有專門儲存彝文古籍的書柜。[4]還有的彝文古籍放置在山洞、火塘上方房梁、墻洞、神龕及屋檐等處進行保存。在這樣簡陋的條件下,彝文古籍所處的環境是非常惡劣的,破損情況也是比較嚴重的。2012年以來,云南省古籍保護中心組織搶救修復《百樂書》《猜考書》《記腦更早》《歷算書》《查姆》《吾查》《賣花女》《看人死兇吉日》《反詛咒經》《祭祖獻牲經》等彝文古籍14000余葉,本文根據筆者近年來參與修復彝文古籍的實踐進行總結和論述。
2 彝文古籍修復
2.1 彝文古籍裝幀形制
彝族擁有載體多樣、卷帙浩繁、內容豐富的彝文古籍。彝文古籍的載體形制主要有紙書、皮書、布書、骨書、巖書、瓦書、木牘、木刻、金石銘刻等,但紙質文獻是目前所見最多的一種。本文所講的彝文古籍,主要指的是紙本彝文古籍。彝文古籍中材質最多的是構皮紙,紙張厚薄不勻,有的粗且糙,有的薄如蟬翼。當然也有竹紙、草紙和其它紙類,但構皮紙是最常見的材質。
彝文古籍大多為抄本,也有刻本及少數印刷版本。抄本大多由畢摩世代傳抄流傳,用毛筆或竹筆書寫。一般用一似帶尾云朵符或一個正三角形頂端再加一橫表示某段完結。有的彝文抄本插入單色或多色的插圖作為裝飾,具有濃郁的民族色彩,既是書籍,又是藝術品。
彝文古籍的開本五花八門,有整張紙、4開、8開、16開、32開、64開等不同規格。[5]篇幅則相差懸殊,有的僅三至五葉,有的多達上百葉。裝幀形制大多為線裝或線訂卷裝、毛裝等。為了使書籍便于攜帶、收存、不易磨損,在線裝的基礎上加一層比書葉稍寬的麻布、火草布、棉布、牛皮、綿羊皮等,并在上面訂上帶子,將書卷好進行捆扎,這就是我們常說的線訂卷裝,是彝文古籍最常見的一種裝幀形式。裝訂的書眼隨意性大,少則三個眼,多則十幾個眼,但多數以單數眼為主。彝文古籍的封面材質有麻布、棉布、火草布、皮紙,也用到綢緞、羊皮、牛皮或鹿皮的。
2.2 彝文古籍破損情況
由于彝文古籍數量多,分散性強,很多難以得到及時整理,加上保存條件差,現存彝文古籍的損毀已經非常嚴重,有些文獻壘積在收藏室內數十年之久,甚至腐爛不可辨認,亟待修復整理。而大量散存民間的彝文古籍因年代久遠,保存條件惡劣,發霉、受潮、粘連、結磚和破碎現象非常普遍,這些珍貴的民族遺產如不及時搶救保護,隨時都有損毀和喪失的危險。從筆者的彝文古籍修復實踐來看,彝文古籍的破損主要有以下幾種情況。
2.2.1 水漬、油漬
由于彝文古籍使用人群的特殊性,大部份彝文古籍是畢摩使用,畢摩在做法事時大多圍繞在火爐或飯桌旁,這也是大多數彝文古籍葉面留下了水漬、油漬的原因。
2.2.2 絮化與霉變
彝文古籍材質皮紙居多,絮化是彝文古籍最為常見的一種破損情形。許多彝文古籍在使用或儲藏取拿過程中,由于書芯過度磨損或其他原因,導致書葉紙張纖維蓬松并拉長變形,呈棉絮狀態。絮化的書葉紙張纖維因變形而上下左右粘連,組織稀松,難以分層,并且韌性缺失,紙張強度降低。彝文古籍的霉變主要與存藏的方式有關,私人收藏的彝文古籍很少有專門的書房書柜,而大多使用布袋、麻袋、皮、紙、布等裝置或包裹,藏之房梁、神龕、屋檐、墻洞,甚至是山洞之中,當遇雨時,古籍被漬或受潮,沒能及時進行晾曬或采取有效的方法除去水分,長期濕潤,滋長細菌,導致古籍紙張霉變、書葉粘連。
2.2.3 煙熏與脆化
彝文古籍特別是民間私人收藏煙熏火炙的情況較為嚴重,因為彝文古籍多由畢摩傳抄、應用保管,為表敬惜和防潮,平時一般供放于火塘上方樓梁上或神龕中,長年煙熏火烤而顯得煙漬陳舊。彝文古籍經過煙熏,紙質發脆,煙塵顆粒物還會附著滲入書葉中,形成難以清除的污斑。一些彝文古籍不幸被燒,這些被燒古籍大多用水澆滅,因沒有及時晾曬處理,也容易霉變粘結成書磚。經長時間的煙熏火炙,導致彝文古籍文獻紙質漸漸發黃,甚至是變黑,嚴重者部分古籍邊沿的字跡也會隨之模糊不清。
2.2.4 破壞性修復
古籍的破壞性修復是修復人員認知能力和修復技術的局限所致,主要指古籍修復人員在修復的過程中違背古籍修復的標準和原則,誤用修復技術和材料、過度修復古籍等原因,導致古籍再次受損。譬如:2019年8月,云南省古籍保護中心工作人員對云南雙柏縣文化館收藏的一批彝文古籍文獻的保護情況進行調研,經調研發現雙柏縣文化館收藏的一批彝文古籍存在破壞性修復的情況,這批彝文古籍在修復過程中大量采用化學膠水作為粘合劑進行托裱,造成了不可逆轉的損害。類似的破壞性修復在私人收藏的彝文古籍中仍然存在。
2.3 彝文古籍修復方法
如上所述,現存的彝文古籍數量雖多,但藏存分散,且普遍存在不同程度的破損,亟需搶救修復。云南省古籍保護中心自2012年以來,以多種方式開展少數民族古籍修復。云南省古籍保護中心先后在云南云南省圖書館、曲靖市圖書館、楚雄州圖書館、石屏縣圖書館、瀾滄縣圖書館等彝文古籍收藏地區舉辦彝文古籍修復技術培訓班,招集云南省內古籍收藏單位的古籍工作人員參加培訓,通過以“以干代訓”的方式培養少數民族古籍修復人才,同時也搶救修復了一批彝文古籍。
2.3.1 修復原則
在修復原則上,彝文古籍修復應遵循漢文古籍修復的普遍性原則,也就是現在行業內通行的“整舊如舊”“最小干預”“安全可逆”“可辨識”等原則。同時還必須以文化部頒發的《古籍修復技術規范與質量要求》(WH/T23-2006)中的標準進行修復。
2.3.2 修復紙張選取
據彝族的學者介紹,云南彝文的寫經用紙一部分來自祿勸、祿豐的彝族地區,在文獻《滇海虞衡志》《鎮南州志略》中已有記載,這些地區生產的主要是竹紙。我們今天所見彝文古籍的紙質大部分為構皮紙,有學者認為這種構皮紙是來自云南其它民族地區。根據文獻資料記載云南大理鶴慶縣、臨滄耿馬、保山騰沖、曲靖羅平等地都生產過構皮紙。而最具影響力的是大理白族自治州鶴慶縣的白族手工造紙,在云南各民族手工造紙中,鶴慶“白棉紙”①由于構皮紙較白,其特征明顯,所以稱“白棉紙”。的造藝水平最高,有“安徽宣紙甲天下,鶴慶棉紙譽西南”的美稱。科技史專家袁翰青先生曾例舉了6種中國有名的手工紙,其中就有云南鶴慶的白棉紙。由于大理鶴慶的白族手工造紙技術贏得了聲譽,云南各民族也廣泛使用鶴慶白棉紙。筆者自2010年以來,曾多次考察云南鶴慶松桂鎮龍珠村、六合鄉靈地村的手工造紙,發現鶴慶一帶生產的構皮紙張與所見的彝文古籍紙張有一定的差異,但也有部分構皮紙可用于修復彝文古籍。另外,貴州丹寨的構皮紙,特別是“迎春”系列的構皮紙與部分彝文古籍紙張質地較為匹配,可選擇這一系列的構皮紙經國畫原料染色后作為彝文古籍的修復用紙。
2.3.3 技法要點
筆者根據所見彝文古籍紙質特征和破損情形,借鑒漢文古籍修復技法開展彝文古籍修復。以下介紹幾種常見的彝文古籍修復技法。
去污。去污最常用的方法就是清洗,對于紙質較好的書葉清洗之前利用鑷子、挑針挑除污垢,在必要時利用手術刀或馬蹄刀刮除緊實的污垢。清洗書葉之前要檢查字跡是否會洇染,若存在洇染,需進行固色加工后方能除污。固色最常見的方法就是用宣紙包裹書葉后,放入塑料袋密封,放蒸鍋里高溫蒸半小時左右,墨色穩定后再用溫水刷洗。對于污漬較為嚴重但紙質較好的書葉,可在水中適當加入少量小蘇打進行刷洗。對于書葉破損嚴重而無法進行刷洗的,需借助一張化纖紙,在化纖紙上將書葉展平,然后噴大量溫水,再用毛巾按壓吸水。吸水的同時也吸走了一些污漬,同時一些污漬也會吸附在化纖紙上。
拆揭。絮化、霉變的古籍一般都是粘連或結成書磚,在修復前必須進行揭葉。修復起來也是難度大,風險大,一不小心就會造成不可逆轉的損毀。所以揭葉時對修復工具、輔助材料、實施方法的選擇是極為重要的。揭書葉時,需根據紙質和粘連的程度選擇適合的方法進行揭葉。揭葉的方法主要有干揭、濕揭、蒸揭、粘接等。對于粘連不太嚴重的書葉采用干揭;對于粘連嚴重的書葉,干揭不易揭開,可采用毛筆局部潤濕,使粘連處遇水脫膠分離。對于粘連非常嚴重的書磚,可根據其耐水性,先用水浸泡或不浸泡而直接選用宣紙包裹書葉后放入塑料袋密封,放蒸鍋里高溫熏蒸,趁熱隨蒸隨揭。
裱補。對于脆化、絮化、霉變、火燒的破損書葉,需根據實際情況對書葉進行局部裱補或整葉裱補。在裱補過程中,可以先裱后補,也可以先補后裱,要視具體情況而定。需要注意的是,裱補的書葉切忌上墻,要讓書葉自然晾至八成干后,再噴水輕壓。
裝訂。彝文古籍大多為線裝或線訂卷裝,“線訂卷裝”是彝文古籍特有的裝幀,其裝訂方法是:把彝文古籍上護葉后加訂紙捻,用一張厚皮紙作為書的封面,用一張比書葉稍大的棉布作為封底,根據原書大小打眼訂線。裝訂前,作為封底的棉布四周要由外向內轉邊封一圈,并在書口一端的棉布中點封上一根帶子,帶子上封一別子。線訂好后,布面朝外由書脊卷起,用帶子繞捆再用別子別住即可。裝訂后封底在外,以底代面。線訂卷裝也可以使用一整塊棉布作為封底和封面,訂線后按同樣的方法加帶、上別簽卷起。
2.4 云南彝文古籍修復成果
自“中華古籍保護計劃”實施以來,在國家古籍保護中心的支持下,云南省古籍保護中心針對云南民族文字古籍資源豐富但缺乏專業保護、亟待搶救修復的實際情況,充分發揮古籍修復人才資源優勢,在全省范圍實施“少數民族古籍搶救修復文化志愿者在行動”服務項目,通過多種方式開展少數民族古籍的修復,先后舉辦了5期彝文古籍修復技術培訓班,搶救性修復《百樂書》《記腦更早》《猜考書》《歷算書》《查姆》等多種彝文古籍14000余葉,并建立了一批彝文古籍修復檔案。云南省圖書館以多種方式開展少數民族古籍修復,得到了國家古籍保護中心和業界的一致認可。在2015年中國古籍保護協會成立大會上,國家圖書館領導充分肯定了云南省古籍保護中心的古籍修復工作,肯定“云南省古籍保護中心結合培訓開展藏文、彝文等少數民族古籍修復工作,不斷探索修復形式,取得了重要突破”。2012至2016年,云南省古籍保護中心修復的彝文古籍先后入選國家圖書館舉辦的“第四批國家珍貴古籍特展——中華古籍保護成果展”和文化部、國家文物局、國家圖書館聯合舉辦的“民族記憶精神家園——國家珍貴古籍特展”。2020年,由國家古籍保護中心舉辦的“全國古籍修復技藝競賽”,云南省圖書館甄選《查姆》《歷算書》《驅禍》三部彝文古籍修復作品參賽,在全國21個省43家參賽單位中,是唯一以少數民族古籍修復作品參賽并獲獎的單位。
3 彝文古籍修復的啟示
筆者認為,要進一步提高彝文古籍乃至其它少數民族古籍修復的科學性,應從以下幾個方面著力:
3.1 加強對民間收藏者的古籍修復技術培訓
近年來,國家古籍保護中心在全國舉辦了十余期少數民族古籍修復技術培訓班,每期招生范圍僅限于公共圖書館或少量藏有少數民族古籍的收藏單位。目前仍有相當數量的少數民族古籍散落于民間,唯有提高民間古籍收藏愛好者對古籍保護的意識,讓他們參與少數民族古籍保護修復的培訓,通過培訓讓這些民間古籍收藏者了解一定的古籍保護修復技法,能對自己收藏的古籍有意識地進行保護與修復,避免破壞性修復。
3.2 加強對手工紙作坊工作人員的古籍修復技術培訓
少數民族古籍修復用紙有其特殊性,以筆者近年來對云南少數民族手工紙的尋訪來看,真正適于修復少數民族古籍的手工紙少之又少,無論從造紙的工藝,還是造紙設備的使用上,都與古籍修復的要求相差甚遠。就拿抄紙的簾子來說,有的作坊采用鐵絲網來做紙簾是不科學的。用鐵絲網做為紙簾抄紙,勢必造成紙張氧化而發脆,這樣的紙張是不適宜作為修復用紙的。古籍保護與修復培訓班的大門可以向這些手工造紙作坊的人敞開,讓他們通過參加培訓了解少數民族古籍修復用紙的要求,從而生產出更合適的修復用紙。
3.3 聘請彝文及其它少數民族古籍研究專家參與古籍修復
由于少數民族古籍文字的獨特性,能識讀少數民族文字的人并不多。據筆者多年來參加少數民族古籍修復的經驗來看,修復人員需簡單識別一些少數民族文字及符號,了解其文化背景,從而了解古籍的破損成因,再選擇恰當的修復方法進行修復。在這種情況下,彝文研究專家參與修復,對彝文古籍修復實踐將會起到導向、參考和借鑒的作用。
3.4 加強彝文及其它少數民族古籍修復的技藝和理論研究
由于少數民族古籍載體、裝幀等方面的特殊性,加強少數民族古籍修復技藝研究十分必要。云南省古籍保護中心在2014年修復“納格拉洞藏經”時,成功研制“人工紙漿補書法”,并在后來的藏文古籍修復中運用和推廣。筆者認為“人工紙漿補書法”同樣適于修復其它紙質較厚的少數民族古籍。要開展少數民族古籍修復技藝的問題分析,并探究古籍修復的理論依據。只有對古籍修復實踐進行理論總結,才能將古籍修復從技藝傳承推向問題分析,走入追尋科學性、合理性與長久性的研究階段,從而提高古籍修復和保護技術的水平。[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