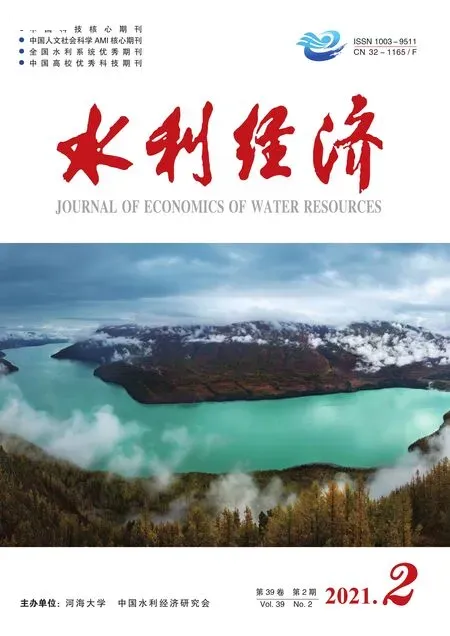城市中小河流河長制的建設實踐與思考
胡興球,過昕彤
(河海大學商學院,江蘇 南京 211100)
河湖是水資源的載體,中小河流是其中重要的組成部分,承擔著所在地區極其重要的資源功能、生態功能和經濟功能。城市管轄范圍內中小河流的保護直接關系著該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同時也是該地區人民對美好生活環境迫切期盼的體現[1]。
我國中小河流數量眾多,流經地域廣泛、治理難度較大。中小河流一般流域面積為200~3 000 km2[2],承擔著水運、供水、防洪、排澇、發電和生態調節等重要功能。從管理范圍來講,城市中小河流和鄉村中小河流的保護與治理目標相差較大,甚至地級市與縣級市的城市中小河流的保護與治理目標方法都不相同。我國長期以來重視大型河流抗洪防汛,對中小河流治理由地方自行實施。近年來,我國全面開展了針對城市中小河流的治理工程,獲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整體治理工作仍然比較滯后、建設成效不夠顯著。
1 城市中小河流河長制建設的重要性與緊迫性
城市中小河流治理,需要工程項目支撐,建設經費較大,主要由地方政府承擔。不同地方對治水的重視程度、迫切性不一樣,經濟發展水平差異較大,有的地方政府沒有足夠財力用于河流治理[3]。同時還普遍存在著“多龍治水”、重建輕管、管理責任落實較差等情況。
1.1 城市綠色發展和人民幸福生活的迫切需要
水是生命之源、文明之基。從發展的角度看,人類的發展依賴于水的滋養,無論是從畜牧業的發展到農業的豐收,還是從蒸汽機的發明到現代工業的振興,都離開水的支撐。中小河流是城市生態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不僅僅只作為資源和環境的載體而存在,對城市的形成和經濟的發展起到了關鍵的決定性作用[4]。
人們對生態宜居的要求不斷越高,由此對身邊水環境的關注度也越來越高,山清水秀的生活環境已經成為追求美好生活的重要內容。而曾經由于發展的需要,造成開發與保護失衡的局面亟須解決。在當前社會發展條件下,人們對于身邊河流干凈與否的感受度,往往要比對于經濟發展或者GDP增速的感受度來得更加直接、更加迫切。
1.2 解決復雜水污染問題的需要
在相當長一段時期,我國的城市化發展和社會經濟效益增長是以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的。城市土地開發利用率高,經濟發展伴隨著工業、農業污染越來越嚴重,排污量的增大和不加處理直接惡化了城市河流,加之多年積淤、水土流失,城市中小河流面臨萎縮、生物環境瀕臨崩潰等問題。可以說,在河長制建設引領下,大力推進城市中小河流的綜合治理已經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5]。
1.3 彌補治水體制短板的需要
治水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除了水具有自身的復雜性之外,涉水的利益主體較多,在國家機構方面會涉及水利、農業、環保、住建、國土、交通等多部門共治,這給水治理帶來了極大的難度[6]。除了多部門參與共治之外,由于城市河流歸屬不同行政區域,不同行政區域內各方利益主體對治水的思路和看法又存有差異,不同利益關系的驅動使得城市河流治理很難形成統一的治理意見和治理方法。
過去治水重視技術層面,忽視制度安排。九龍治水,遇到關鍵問題相互推諉。在明確河長后,將考核具體到河長個人,解決了以往制度上存在的困境,為實現城市中小河流的有效治理提供了一種可操作機制[7]。
2 城市中小河流治理實踐
2.1 歐洲萊茵河流域的協同治理經驗
萊茵河流經西歐的很多城市,是孕育西歐文明的重要源泉,至今仍影響著沿岸各城市的經濟社會文化。然而20世紀中葉之后,隨著城市化和工業化快速發展,環境保護沒有及時跟進,萊茵河出現了嚴重的水體污染、沿岸生態退化的問題,嚴重影響城市景觀和生態系統。隨后,沿岸各城市開始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開始對萊茵河進行協同治理,經過幾十年的努力,流域內生態環境終于得到了大幅改善[8-9]。
萊茵河的治理經驗是成立協同治理機構,建立流域管理體制。萊茵河沿岸各城市深受水體污染影響,雖然經濟發展水平不同,治理符合其共同利益,故成立了萊茵河國際保護委員會(ICPR)。經過ICPR的領導、組織、管理與協調,堅持可持續發展、預防為主、源頭治理等基本原則,采取不轉移污染、污染者付費、發展和應用新技術等措施,萊茵河流域治理獲得較好成效。ICPR主要職責為:開展萊茵河系統調查研究,提出目標計劃、進行科學決策;推進成員國和城市落實計劃,提供年度報告;評估成員國和城市的行動績效等;向公眾公布萊茵河狀況和治理成效[10]。此外,萊茵河治理不僅是國家和城市政府職能,流域內各種企業、社會組織和民眾也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2.2 江蘇省無錫市河長制的實踐
2007年,太湖藍藻大暴發,造成水污染與供水危機[11]。為持續改善水質,完成河道水環境綜合治理,當地政府被迫探尋治水新方法,無錫市政府緊急出臺《水質控制目標及考核辦法(試行)》文件,將河流水質監測結果納入市(縣)、區黨負責人政績考核內容,市黨政主要負責人分別擔任64條河流的“河長”,強制黨政一把手進行污水治理,而這個文件后來被認為是“河長制”起源。無錫市推行河長制的基本做法是,首先由黨委、政府作出“決定”,即《中共無錫市委、無錫市人民政府關于全面建立“河(湖、庫、蕩、氿)長制”全面加強河(湖、庫、蕩、氿)綜合整治和管理的決定》(錫委發〔2008〕55號),所有河(湖、庫、蕩、氿)都逐一確定“河長”;然后是建立機構,明確河長全面負責。加強社會監督,各地區均在主要河道岸邊建立了“河長”公示牌,標明了河長職責、目標、措施、進度以及河長的聯系電話,并制定辦法,組織考核[12]。
該制度推出后成效顯著,成功控制并改善了太湖水環境質量。2012年,江蘇省將河長制從以水質管理為主擴展到以河道綜合管理為主,將河長制在全省范圍內推廣,此后全國各地均對此模式進行仿效,成為水環境治理的一種新的治理模式。學術界雖對河長制有不同的看法和意見,但江蘇省的實踐證明,河長制是一個有效機制,是符合當前我國水污染治理現狀的有效之舉[7]。
2.3 浙江省紹興市的政企合作經驗
浙江省紹興市是較早推行企業河長的地區之一,并取得了良好的治理效果。2018年,紹興市柯橋區為破解工業區治水難點,全面推廣工業園區“企業河長制”,420名企業總經理擔任“河長”,簽訂責任書。“企業河長”積極響應,帶頭落實企業治水、護水責任。目前,全區各類企業已累計投入資金2億多元,用于工業污水處理、污水管網改造、生活污水治理等技改治理項目[13]。
柯橋區明確了“企業河長”的工作規則,實施巡查處置、激勵優先和落后淘汰等機制,建立定期聯絡、問題及時反饋處置制度,推動“企業河長制”落在實處。專門出臺政策文件,對工作成效顯著“企業河長”,在企業技改、資源分配、政策獎勵等方面給予優先安排,對未完成節能減排任務,履職不到位的“企業河長”予以淘汰。“企業河長”組織員工定期巡查河道,及時發現解決問題,截至2018年共發現、解決各類問題1 790多個,提出治水建議127條,劣Ⅴ類小微水體全部剿滅,水質基本上穩定在Ⅳ類以上[10]。企業河長制的推行充分發揮社會力量,加強了企業的參與力度。
2.4 構建智慧河長信息技術平臺
過去,河長治水信息化建設滯后,主要存在問題為:沒有統一的信息化系統平臺;無法實時了解各級河長工作落實情況;無法及時處理并上報各類問題;無法系統體現河道檔案和治河策略;無法實時查看重點河段區域的視頻監控、水污染源等。為了解決上述難題,2016年紹興市推出了河長制信息管理系統——“河長通”,包含用于手機端的“河長通”APP和電腦PC端的“紹興河長通管理平臺”。該平臺可以通過手機拍攝取證,并上報至上級。
河長制信息管理系統,將問題匯總到治水辦后再分配解決,極大地提高了辦事效率。信息系統采用分級管理模式,厘清了四級河長的責任分工,加快推進上一級河長及時解決下級河長反映的問題,同時監督下級河長履職是否到位。截至2016年,紹興市、縣(區)、鎮、村四級5 300余名河長全部用上了河長制信息管理系統,實現了市域范圍電子化巡河全覆蓋[14]。通過構建“河長通”等智慧河長信息技術平臺,可及時掌握重點河段的視頻監控、斷面水質狀況,了解各級河長工作落實情況,實現了信息公開和社會監督,有利于城市中小河流的信息化管理。
3 城市中小河流河長制建設的對策與建議
目前,河長制在城市中小河流治理中取得了良好成績,但在當前階段主要是依靠上級干部的權威和層級之間的單向指揮命令為主的模式,更多地傾向于人治而非法制。為更好地推進河長制建設,需進一步深化與完善相關制度,使河長制能夠成為可持續的長效機制。
3.1 充分發揮社會力量,加強公眾參與
歐洲萊茵河、浙江紹興的成功經驗表明,社會力量參與能夠有效推動城市中小河流治理。在城市中小河流的治理中,地方黨委、政府應將河長制作為平臺,從讓普通群眾用上清潔干凈的水,享有河暢、水清的生產生活環境,轉變為讓民眾參與到河長制建設中。建立河長制公眾參與機制,充分發揮群眾力量,聘請民間河長,設立群眾監督、舉報等制度,加強宣傳教育,引導公眾參與河湖治理,實現全民治水的格局[15]。進一步研究污水處理費征收模式及其標準,建立征收標準與截污率同向聯動的動態調整機制,甚至建立階梯水價體制[16]。通過市場運作,采用PPP或BOT等模式,引入社會資本,引導更多的社會力量參與治水,參與到河湖治理中來。
3.2 完善法律法規體系,構建長效機制
水環境的管理應該是法治管理。從短期來看,可以通過推進河長制,依靠河長們的個人行政命令和權力,取得治理的成效。從長期來看,要維持河長制治理成果的長效化,要明確作為河長的黨政主要負責的人的相關權力、法律地位和責任[17]。市級有地方立法權,可因地制宜頒布地方法規,在法律法規中明確政府及各部門的具體責任,并細化不同級別河長需要履行的工作任務,完善績效考核和環境問責方面的法規制度,為規范河湖管理提供依據[15]。加強治河執法監管,以政府部門為主導,整合相關部門共同參與,依法制止和打擊企業偷排、侵占河道等行為;依法劃定河湖管理范圍,依法清理飲用水水源保護區內違法建筑和排污口;依法建立解決左右岸、上下游的水環境治理成本生態資金橫向、縱向補償機制[17]。
此外,應加強流域/區域協同治理。河流本身是流動的,只有兼顧好上下游、左右岸的關系,各司其職,才能將河流水環境系統治理成功。歐洲萊茵河的協同治理組織機構——萊茵河國際保護委員會(ICPR)在河流治理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通過系列的法律法規和管理辦法,實現了流域/區域協同治理。
3.3 健全考核機制,增強激勵作用
在具體工作中,應該注重兩個方面的責任:一是壓實縣鄉主要領導的責任,經常和地方主要領導溝通治河之策,反饋工作中發現的一些問題,可以邀請一起巡河、會辦;二是壓實各縣級河段長、支流河長的責任。定期召開例會,通報問題,研究對策,不定期召開支流推進會,對履行責任不力的及時進行約談問責。完善河長制的監督考核機制。將河長制實施情況納入地方政府年度目標考核。河長制工作考核與水資源管理、水污染防治考核結合,考核結果作為地方黨政領導干部綜合政績評價的重要依據[18]。
2018年無錫市制定了市縣級河長履行河道整治職責考核辦法,對全市165名市(縣)、區級河長細化考核。對河長職責細化明確,如河長每季度要現場巡河、召開協調會解決難點問題,否則扣5分;環境整治河道,斷面水質達標得30分,水質下降得0分;黑臭水體河段,整治后初見成效得15分,達到長治久清得30分。河長年終考核結果作為干部年度綜合考核及任用的重要依據,有效促進河長履職盡責。
3.4 提高先進科技支撐,加強保障措施
隨著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等信息技術的蓬勃發展,創新發展河長制的精細化管理平臺體系和運營機制成為提升河長制管理水平和成效的重要舉措。紹興市上線運行的“河長通”系統有利推動了城市河長制建設的實施,是利用先進科技推動河長制建設的重要體現。通過信息技術與河湖長制深度融合,完善采集監控體系,建立信息資源平臺,從城市水體的維護、管理、監測與對河長的監督、考核等方面多管齊下,確保實時更新、信息公開、監管透明、責任到人,提升城市的河長制數字化管理水平[19]。
3.5 控制過剩高耗水產能,持續推進產業綠色發展
全面推行河長制是生態文明建設、綠色發展的內在要求,也是產業結構調整、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助推器。只有淘汰過剩高耗水產能,切實轉變發展方式,大力發展高科技產業,才能從根源破解河流治理問題[20-21]。曾是歐洲工業引擎的德國的魯爾工業區,為保護萊茵河,當地的埃森煤礦不得不轉型,于2001年成為世界文化遺產。而魯爾區商業和服務業也日益繁榮[22]。在新的時期,應該以推進河長制為契機,制修訂行業用水定額標準,對過剩、落后、高耗水產能企業實行累進征收水資源費。關停取締“散亂污”企業,加快淘汰落后產能,加快推進制造業信息化提升、綠色化改造,以河流管理保護倒逼產業轉型升級,為城市留足生態空間、環境空間,推動高質量發展。
4 結 語
城市中小河流的治理對于人民幸福生活、生態文明建設以及社會經濟發展意義重大,河長制則為城市中小河流的有效治理提供了一種行之有效的操作機制。目前城市中小河流河長制仍處于建設與實踐階段,雖然已初步取得成效,但仍需進一步的深化與完善。歐洲萊茵河流域的協同治理、無錫河長制的實踐、紹興的政企合作以及信息化系統平臺建設等國內外成功案例為河長制的深化與完善提供了參考依據。需要通過充分發揮社會力量,鼓勵公眾參與;完善法律法規體系,為規范化管理提供依據;建立健全考核機制,促進河長履職盡責;借助現代科技,提高數字化管理水平;以及控制過剩高耗水產能,促進城市中小河流河長制成為一種可持續的長效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