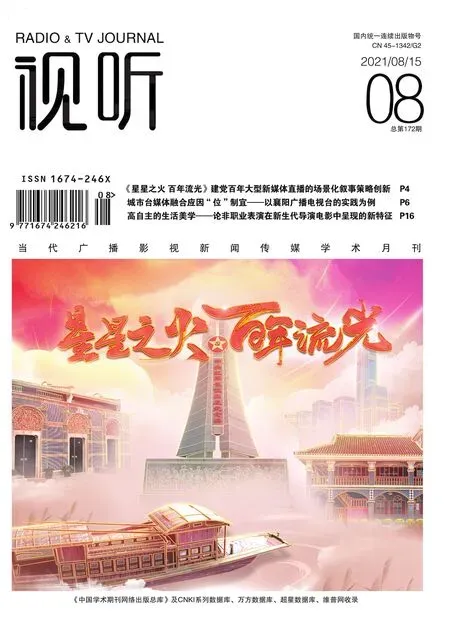倫理視角下《我的姐姐》的價值構建
張 政
《我的姐姐》是由殷若昕執導,根據真實事件改編而成的電影。影片講述了21歲的姐姐與6歲的弟弟因一次車禍失去雙親。在承受著失去親人的痛苦時,姐姐還面臨著追求自己的人生還是撫養弟弟的艱難選擇。2021年《我的姐姐》上映后,引起了巨大的反響。影片結尾,姐姐將弟弟帶出領養家庭,這一結局是引起討論的重要因素。一部分受眾認為選擇撫養弟弟的結局是導演和社會強加給姐姐的結局,在歷經種種謾罵和指責、缺失了種種情感后,姐姐應當為自己而活。而另一部分受眾則認為,姐姐擔負起撫養弟弟的責任,才是這部電影該有的結局。提到“姐姐”,受眾往往會增加許多附加項,無論出于道德還是親情,姐姐都有責任和義務將弟弟撫養成人。影片中,導演賦予了姐姐更多的社會關懷與道德層面的關注,從而去彌補姐姐從小到大缺失的親情與關愛。
“倫理道德幾乎是人人都會遇到的問題,因此,由它們構成的故事更容易引起大眾的關注和認可。”姐姐最終選擇撫養弟弟這一結局,是對倫理道德價值的正向體現。影片中,姐姐在歷經身份的迷失、道德的失衡以及代際傳承思想的影響后,對自己責任心的重構、良心的重拾和所缺失情感的重生,在倫理學視域下構建出影片的價值內蘊。
一、身份迷失后的責任重構
從古至今,一直有著長兄如父、長姐如母的說法。在倫理學中,同輩人要做到團結和睦。社會主義社會里,家庭成員之間的關系也都是平等的,同輩人如兄弟、姐妹等之間的關系也是平等的,同輩人之間既有血緣關系,又是互幫互助的朋友關系,應當親密和睦、平等共處。影片的前半段姐姐在面對自己六歲弟弟時態度冷漠、界限分明,沒有任何感情可言。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弟弟是父母執意要生的,且姐姐很少與弟弟相處,兩人年齡相差較大,甚至都沒有見過幾面。但父母雙亡后,姐姐成為弟弟唯一的依靠。這時姐姐的內心是迷茫的,也帶有怨氣,因為她認為“姐姐”這一身份并不是她自己的選擇,而是父母忽視她的感受后強加于她的。當父母去世后,她更是被身邊的親戚要求擔負起姐姐的責任,將弟弟撫養成人。姐姐對自己的身份無法進行準確的定位,同時對自己的未來感到迷茫,姐姐是否應放棄自己的夢想與人生,承擔起父母的職責撫養六歲的弟弟長大?在這一過程中,姐姐一次次的夢境都隱喻著她內心的茫然和糾結。從倫理道德的視角來看,影片探討的問題是:姐姐應當如此,還是本該如此?
在道德的層面上,姐姐應當擔負起撫養弟弟長大的責任;在倫理的層面上,姐姐本該將弟弟撫養成人。在姐姐看來,弟弟對她來說只是一個累贅,她與舅舅、姑媽等親戚做了一次又一次斗爭,最終決定將弟弟送養到其他家庭,自己要完成去北京讀研的夢想。但當她試著將弟弟送給舅舅撫養,幾天后看到弟弟像一個街頭小混混在路邊罵人時,姐姐的情緒首先是憤怒,其次是心疼,這一細節體現出她對弟弟的感情是逐漸在加深的。影片中,姑媽站在自己的角度,給姐姐講述自己是如何為弟弟付出的,姑媽的付出看似毫無怨言、心甘情愿,但她卻通過套娃這一物件細節告訴姐姐套娃也有很多種組合方法。套娃隱喻著姑媽的人生是被一件件事套牢的,她并不希望安然也像“套娃”一樣按部就班地過完這一生。當受眾參與到“姐姐”的選擇過程中,也就逐漸理解了姐姐的傷痛之處,姐姐對自我身份認定的過程也是她揭開自己傷疤的過程。姐姐從開始的迷茫,對弟弟的抵觸、敷衍、不耐煩,逐漸變得溫柔、關心、有耐心,每一次姐姐對弟弟情感態度的變化,都是姐姐身份找尋過程中的自我肯定,也是對弟弟的責任心重構的過程,最終姐姐擔負起撫養弟弟長大的職責,肯定了自己“姐姐”的身份。
二、道德失衡后的良心重拾
道德是社會意識形態之一,是依靠社會輿論、人們的內心信念和傳統習慣調節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自身之間的倫理關系的行為原則、規范的總和。而倫理行為則是在一定倫理意識支配下表現出來的,由主體自覺選擇而發生的,有利或者有害于他人和社會集體的行為。也就是說,倫理行為是具有善惡意義的。倫理行為包括道德的行為即善行和不道德的行為即惡行。影片中人物的道德行為有時是失衡的,在善行與惡行之間搖擺不定,界限模糊。影片中的道德失衡不僅體現在姐姐對弟弟的棄養上,還體現在社會多方的道德缺失上。這些失衡的道德行為如同一根根稻草般積壓在姐姐身上,當壓死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將安然的精神世界壓倒后,安然開始變得敏感、多疑、冷漠、自尊心極強,也造成了她親情的缺失和空白。
導演傳達給受眾的情感不是濃烈直接的,而是細膩克制的。影片開頭安然父母發生意外,安然站在車禍現場面無表情地目睹著眼前一切的發生,配合警察的調查與備案,整個過程都十分冷靜理性。在倫理道德的角度,安然身為親生女兒,父母給予她生命并將其撫養成人,她應當孝順,父母遇難后應當是悲痛的、感傷的,而不是這樣冷血的。姐姐的內心一直在責怪父母為了生弟弟不擇手段,甚至不惜傷害自己的內心,給自己的精神世界帶來巨大的創傷。影片中,姐姐不止一次在夢中感到窒息從而驚恐地醒來,一次次的夢境也隱喻著她對父母這種做法的耿耿于懷,堅定了她將弟弟送走的決心。
影片中無從得知車禍中的另一個司機否是因酒駕才造成了這次車禍,但是通過老師與他的對話以及他在面對姐姐與舅舅時的心虛,并積極地為弟弟尋找條件比較好的養父母的行為使受眾猜測或許這并不是一次單純的意外。一方面,他有一個女兒需要撫養長大,他不得不逃避“酒駕”這一罪名;另一方面,他積極幫助姐姐與弟弟從而彌補自己內心的愧疚感。他也是這部影片中除了姐姐以外另一個陷入道德困境中的人,而良心的發現促使他產生道德行為去幫助姐姐和弟弟。
姑媽也是陷在道德困境中的角色之一,她既希望姐姐能夠撫養弟弟長大,又不忍心這個正值美好青春的小姑娘就這樣交付自己的一生,所以在姐姐請求她簽署同意書時縱使萬般不舍也簽上了名字。而當她得知安然已經給弟弟找到了領養家庭后,卻打電話過去告訴領養家庭弟弟有暴力傾向,故意破壞姐姐的送養計劃,使姐姐無法順利將弟弟送走。在這一糾結的行為中,姑媽成了一個失衡的道德行為主體,而在姐姐說出自己從小在姑媽家被哥哥當沙包、被姑父偷看洗澡時,這一主體的變化是從震驚到自責再到憤怒的,倫理道德瓦解了姑媽最后一絲希望,最終她還是默認了安然將弟弟送走的決定,并鼓勵安然勇敢追求自己的人生。
在將弟弟送走與接回的過程中,也是姐姐身為道德行為的主體心態逐漸變化的過程,寺廟里姐姐為父母和弟弟點燃的平安燈也是對自己內心的慰藉。姐姐逐漸從困境中找到答案,血濃于水,最終還是重拾良心,將弟弟從送養家庭接回。
三、代際歸因后的情感重生
在古往今來的社會環境中,女性在政治、思想、倫理等各個領域都處于與男性不平等的地位,即便在家庭中,女性也處于與男性不平等的地位。這種性別歧視并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由社會環境和人的主觀思想建構起來的。自傳統社會以來,“父權”思想就一直是社會秩序的代表。盡管今天在家庭里父親的權威發生動搖,但整個社會的秩序體系仍然維持著已有的父權制“父法”狀態。影片中,姐姐對待身邊人和事的敵意都來自于她認為自己遭受了不平等的待遇。在醫院中,一個家庭已經有兩個女兒,妻子還要不惜生命危險再去生兒子,看在眼里的姐姐精神受到了巨大的沖擊。從這一細節中可以看出,代際傳承是中國人倫中根深蒂固的思想,只有男性才是一個家族的根,才能為一個家族延續香火。
父母的葬禮結束后,家中的親戚討論弟弟應該由誰撫養的問題,自然而然地討論起房子繼承的問題。在他們看來,房子應當歸兒子所有,姐姐終歸要成為“外人”,父母發生意外前,也就房子改戶名的原因給安然打了無數次的電話。而姐姐遲遲不肯松口,姐姐認為應該男女平等,自己所要守住的并不是房子和財產,而是自己身為一名女性在這個家庭以及整個社會環境中的尊嚴與地位。也正因如此,姐姐與弟弟不僅在性別上,也在倫理關系中形成了對立。從倫理學的視角來看,姐姐的成長過程中親情對于她的滋養是不夠的,唯有夢境中母親的溫柔能夠擊破安然堅硬的外殼,但母親的愛亦是在“父權”籠罩下小心翼翼的愛。為了生二胎,父母將姐姐說成是瘸子,姐姐無心“露餡”后,父親氣急敗壞甚至對姐姐大打出手。在姐姐高考報志愿時,父母偷偷篡改她的高考志愿,只因可以讓她早點工作掙錢,彷佛這一切都是作為一名女性應當承受和經歷的,只有弟弟的到來才給這個家庭帶來新生的希望。根深蒂固的代際傳承思想給姐姐的成長造成了極大的打擊,甚至給她帶來了心理陰影。所以,筆者看來,父母對姐姐和弟弟不平衡的愛是形成姐弟之間情感芥蒂的根本。代際歸因對于姐姐來說就像是一根無法拔出的刺,時刻刺痛她敏感的內心。這也是姐姐在去父母的墳墓前探望后,遇到舅舅并對他說“有時我更覺得你才是爸爸”的原因。在舅舅面前,姐姐才不用小心翼翼、故作堅強,能夠敞開心扉做真正的自己。但這一切都歸因于外界,弟弟對姐姐的依賴以及弟弟的懂事成為打開姐姐心門的鑰匙,姐姐對弟弟的感情也愈發深厚與濃烈。造成姐姐將弟弟拒之門外的所有歸因,都被姐姐與弟弟之間的親情消解,最終姐姐對弟弟的情感也重新滋長,姐姐的情感世界與人生得到了升華。
四、結語
《我的姐姐》這部影片由小見大、由點到面地詮釋了人性的善,通過倫理學的視角對女性、家庭、社會、道德進行了解讀。人與人之間倫理關系不同,道德行為也就不同。影片中導演通過姐姐對弟弟情感的變化歷程,將違背倫理道德的行為進行消解,建構起正能量的社會價值。在倫理道德的視域下,影片從自我的迷失到責任感的重構、從道德的失衡到良心的回歸、從代際傳承的思想到打破傳統觀念的過程,也是主人公自我成長與靈魂救贖的過程。伴隨著人物內心世界的變化,受眾的情感也跟隨姐姐的視點發生改變。人性的本真是樸實善良的,影片表現的內容更能體現出社會求真、向善、愛美的正向能量,也使影片更具傳播價值與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