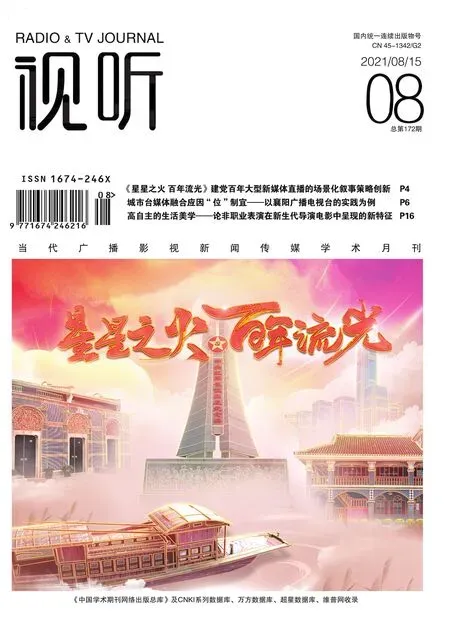從“奶茶社交”梗看青年“梗”文化的風格與儀式
張靜雅
一、“奶茶社交”梗的模因裂變與傳播
(一)何為“奶茶社交”
在中國,比較受歡迎的奶茶主要有兩種:一種是草原奶茶,另一種是南方奶茶。而“奶茶社交”則是指以奶茶為基礎形成的社會人際往來方式,它基于人們對奶茶喜愛的共情力,與其他社會群體進行互動。在此過程中,人們對于社交的需求已經遠遠超出了奶茶本身。不算昂貴的奶茶,就在你來我往之間,逐漸提升了人與人的感情,長此以往,奶茶便在不知不覺中成為當代青年最為經典的社交貨幣之一。
(二)“奶茶社交”梗的模因生成
模因是指像基因一樣依賴宿主、復制傳播的“文化基因”。道金斯認為模因是在文化傳承過程中的一種復刻因子,是文化模仿的最小單位,但它不只限于符號,還是其他元素的組合①。“奶茶社交”現象的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源于一次次“奶茶”梗引爆社交網絡的不斷積累。回顧“奶茶梗”的流行發現,每一次爆出的“奶茶梗”都在青年群體中引發了互動狂歡。諸如2020年9月“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梗的突然流行,源于有人在微信上給朋友發了一句“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對方立即回了一個52元的紅包,意思是用它去買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喝。在她發布聊天截圖后,全網紛紛效仿。截至2020年12月31日,“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梗在抖音平臺播放次數已達33.4億次。以“奶茶”為關鍵詞,由百度指數的數據可知,在9月22日至9月25日之間,奶茶梗在全網的熱度突然攀升,最高搜索指數接近150萬,遠超平均值120萬。
(三)“奶茶社交”的模因擴散
何自然教授提出“任何被廣泛復制和傳播的現象都可以稱為模因現象,語言在人類交往的過程中會被不斷復制和傳播,因此也有語言學的模因”②。語言模因之所以能夠得到穩定發展,并逐步得到社會的重視與關注,正是由于來自不同區域、不同時期的傳播者對語言的不斷模仿、復制以及傳播。“奶茶社交”梗內容豐富,既包含以表情包為基底的圖像轉載,也包括了許多視頻片段的集合。同樣以“秋天的第一杯奶茶”為例,在此“梗”爆出的初期,大多數人迷因式的傳播只是出于對此梗的不解與好奇,但隨著“梗”的不斷發酵,受眾參與度不斷提高,全民性色彩也就越來越強烈。此外,“奶茶梗”的衍生性和原生性也完全符合基因復制的標準要求③。隨著“秋天的第一杯奶茶”的傳播規模越來越廣,受眾創作度也越來越高,接而衍生出“秋天的第一個包”“秋天的第一頓火鍋”等以“秋天的第一個×”為基底的梗。這種保有本源模因基本內涵的“梗”,在融入網民的集體智慧后,再次擴散到社交網絡中。
二、青年“梗”文化的流通表征
(一)“梗”文化的含義與起源
“梗”之意源于“哏”,“哏”往往以相聲形式出現,傳統對口相聲有逗哏和捧哏兩個角色,“哏”在此之意便是笑料、包袱。將“哏”誤寫為“梗”,最早可以追溯到臺灣的娛樂節目中。“哏(gen)”與“梗(geng)”讀音近似,在主持人和嘉賓的多次使用下,節目的字幕就將兩字混用,才使“梗”字有了“好笑”之意,傳入內地后“梗”逐漸成為流行詞。
“梗”文化并非國人首創。日本學者東浩紀在《動物化的后現代》中追溯了日本御宅族的起源和性格④,從中可以看到“梗文化”的異域前身。與發源于歐洲、傳遍世界的放射狀傳播結構不同,“梗文化”繼承了去中心化的特點,所在亞文化的區位也讓其具有“圈地自萌”的行為特征,形成“梗文化”中各個圈層的代際,構建以“玩梗”為標志的身份認同⑤。在互聯網語境下,青年群體通過不斷的造“梗”、玩“梗”,創造了奇異的“梗”文化。
(二)生產:符號文本的邏輯異變
造“梗”是“梗”文化傳播的前提,而“梗”文化的創造依靠的是將邏輯推向極致所帶來的荒謬,并借助這種荒謬來完成一個個笑料⑥。回顧近兩年刷爆社交平臺的“梗”,發現爆“梗”的雛形主要是通過“變音”和“變字”兩種邏輯形式來形成的⑦。“變音”是指巧用漢語“同音語素多”的特點,通過替換同音字或近音字的方式將方言或者外語進行文字轉化,從而產出妙趣橫生的“梗”。如大可不必——duck不必:2019年12月11日,李佳琦直播出售鹵鴨,并要求店主再加5萬份,結果店家加成了50萬份,觀眾們不小心就搶了10多萬只。此舉讓李佳琦驚呼:“老板,你多打了一個0!全中國的鴨子要被你們家殺光了吧?”隨后網友們紛紛說道:“duck不必,鴨鴨惶恐。”而李佳琦本人也發布了一條鴨子的表情包,讓網友們玩起了的諧音梗。至此,類似的諧音梗系列層出不窮:不可思議——book思議、四大皆空——star皆空等。“變字”是指以某一詞組為原型,進行字符的變化。如“翔”一字,原意是詳細或盤旋地飛而不振翅,但在網絡用語中,“翔”意為“屎”。其緣由充滿荒謬:一位叫“軍神李翔”的網友,曾在貼吧里舌戰群儒三天三夜,最后丟下一句:“我就是一坨屎”,于是“翔”就成了“屎”的代名詞。貼吧里的網友罵架時,常常調侃:“干了這碗熱翔吧!”
(三)流通:網絡迷因的多重演繹
玩“梗”是“梗”文化的基本生產方式,幾乎每一次“爆梗”都要靠受眾的二次創作。處于web2.0時代,模仿、戲謔、病毒式傳播的媒介生態成為這個時代的特征。社交平臺在加速傳播進程的同時,也激發了受眾自主創作的主動性。而網絡迷因則是用戶“有意為之”的產物,是一類具有共同特征的信息體。有了技術加持,網絡迷因往往會在一定群體內掀起傳播密度,激發人們在視覺、語言、音樂或行為上的聯想,從而輕松快速地模仿,并將二次創作的成果傳遞給他人。在迷因式的模仿參與中,玩“梗”不再是趣緣群落里的可憐獨白,而成了一場全民參與的互動狂歡。從“芋泥啵啵奶茶,不要芋泥,不要奶茶,只要啵啵”到“芋泥瑪奇朵,不要芋,不要奇朵,要泥瑪”,從“打工人”到“尾款人”再到“干飯人”,幾乎每一個“梗”的流行,都會引發聯動效應。
(四)消費:情感共在的身份認同
美國社會學家里斯曼說:“今天最需求的,既不是機器,也不是財富,更不是作品;而是一種個性。”現代消費社會不僅是一個商品和物的世界,它已經成為一個符號的世界、消費的王國,商品的使用價值不再是考慮的重點,而是其指代意義⑧。受眾在消費的過程中,除了消費產品本身的使用價值,更在乎其情感上的期待與認同。在“梗”文化的流通過程中,參與網絡狂歡的受眾消費的實質便是情感。雖然當代青年亞文化是獨立于主流文化的分支,但不可否認的是,無數亞文化圈層之間,往往存在一定的話語壁壘,不同圈子之間雖有交流的可能,但彼此未必能真的適應與理解。各自圈層里的“梗”,其實正是“圈地自萌”的結果。因此,如何判定自己與對方是否在同一個文化圈子里,“梗”就成了鮮明的身份識別標志。比如,“網易”游戲圈子里的“豬肝醬”,就是一個辨別使用者是否是“自己人”的典型“梗”。沒玩過網易游戲的人可能對此不知所云,自然也無法進入圈子進行暢快交流。該“梗”是網易游戲愛好者的自嘲昵稱,如果你玩過網易的游戲,就可以自稱豬肝醬。因為網易的別稱是豬場,而“肝”用在打游戲上表示拼命努力為了游戲的某一個目的而奮斗,“醬”則是一個萌萌噠的尾稱而已。由于受眾對“豬肝醬”這一身份的肯定,在使用該“梗”期間,基于同一身份的認知,拉近了不同個體之間的情感距離,集結而成共情的社交群體。
三、“玩梗”切勿“喪志”
馬爾庫塞在《單向度的人》中認為,發達工業社會會帶來充足的物質資本,保證舒適自由的生活質量,但同時也會帶來一種新型不自由,即人們丟失批判性、質疑力,變成單向度的人,沿著社會洪流不假思索地單向度走著⑨。追溯“梗”文化的流行,不得不承認,“梗”是依托網絡空間傳播與發展出來的。在日新月異的網絡環境中,新奇的網絡流行語層出不窮,海量的輿情事件不斷發酵。隨著新流行語的出現,“梗”文化的風格也會隨著網絡環境的變化而變化。青年群體創造、發展并傳承“梗”文化,但同時也會迷失在文化的洪流中。
(一)玩弄經典、招致濫俗
盡管“梗”趣味十足,有些甚至可以流傳千古,成為經典,但“梗”也有云泥之別。從早年的“杜甫很忙”到“我給你買點橘子”,從調侃杰出人物到玩弄經典文學作品,剝離原意義是必要一步,但也讓“梗”失去了支持,變得空洞而不明所以⑩。不管是真實的歷史人物,還是經典的文學作品,如此玩梗會扭曲他們的真實面貌,也會給人們留下錯誤的印象。爛“梗”從小眾群體擴散到大眾視野,在這個過程中,它們不斷掀起“狂歡”的同時,也逐漸變得爛俗,不僅失去了原本的獨特性,還造成了受眾的審美匱乏,甚至被人反感。
(二)不斷迭代、形成區隔
顯然,“梗”是社交的調味品、催化劑,能博得眾人哄堂大笑,但其天然帶有某種亞文化屬性。在拋“梗”、接“梗”的互動之下,總會徒留另一些人不知所措,造成個體間的區隔。當此之時,玩梗便不再具有大眾性,而有較強的排他性。此外,隨著“梗”文化更新的速度不斷提高,不刷抖音、不玩雙微、不玩“梗”的人,就會在他人拋梗時一頭霧水,會受到網友陰陽怪氣的諷刺:“都2021了,你家還沒聯網呢”。許多人不愿被隔離在群體之外,不想成為被時代拋棄的人,在流行的表象之下,是人際關系帶來的社交壓力與恐懼。
(三)對抗主流、扭曲價值觀
雖然“梗”文化的存在為社交注入了新的活力,但也對受眾的文化價值觀念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尤其是處于多元化社會當中的青年群體,其價值觀仍然處于不斷發展的階段,在接受多重文化與思想的沖擊下,更容易被誤導,從而形成錯誤的價值觀念。比如一些違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梗”:“寧愿在寶馬車里哭,也不愿在自行車上笑”“三年血賺,死刑不虧”等,這類充分體現拜金主義的流行“梗”,難免潛移默化地扭曲著青年群體的價值觀。此外,還有具有典型低俗化特征的網絡流行語,不僅在社交網絡中傾倒負面垃圾,還侵蝕著傳統道德文化,其內含的消極色彩充斥著對主流社會的不滿與抗議。這種博弈是對主流話語體系凝聚力與向心力的消解與重構。
(四)過度玩梗、傳遞語言暴力
于大多數傳者而言,玩梗不過是為了拉近距離、調節氛圍,但許多“梗”于受者而言卻是無形之中的語言暴力。如2020年7月,杭州一名女子因家庭矛盾,在熟睡中被丈夫傷害,且被扔到化糞池中分尸而衍生出的“化糞池警告”梗就在網絡社交過程中傳遞出了新的意義。它可以是安全與親密的武器,也可以是丈夫別有用心的威脅。以生命為梗,表面上是有趣的社交談資,實質上卻成了帶有戲謔的嘲弄。伴隨著每一次“警告”的傳播,于受者而言,其受到的傷害也在日積月累中不斷疊加。
四、結語
不可否認,“梗”的流行在于其可以提供笑點、制造話題,以及推動溝通交流。“玩梗”能快速識別“同道中人”,并且能很快地接近對方,“玩梗”未必能夠換到知己,卻成了朋友圈社交的入場券;“玩梗”能夠在特殊的場合緩解尷尬,活躍氣氛,但卻根治不了人們內心的孤獨。說到底,“梗”不過是新時代的社交談資,青年群體在為亞文化注入活力的同時,應堅守自我、不盲目跟風、不迷失、不麻木,既要敞開懷抱,接受更多的新詞匯、新表達,也要有所判斷、有所選擇。
注釋:
①Heylighen F.&Chielens K.(2009).Cultural evolution and memetics.Meyers,Encyclopedia of complexity and system science.New York,63.
②黎雅琴.模因論視閾下流行語中的隱喻現象探析[D].青島:中國石油大學(華東),2016.
③田淼琪,俞貴.社交媒體時代網絡流行梗的傳播學思考——從“六學”梗談起[J].巢湖學院學報,2020(01):97-103.
④[日]東浩紀.動物化的后現代——御宅族如何影響日本社會[M].褚炫初 譯.臺北:大鴻藝術股份有限公司,2012:92.
⑤陳潤庭.為了歡愉的徽章——論“梗文化”中的身份意識[J].創作評譚,2021(02):24-27.
⑥析子.李雪琴:對抗“梗”文化泛濫的另一種可能性[J].光彩,2020(11):67.
⑦楊昆.網絡流行語的社會語用學研究[J].學術探索,2017(10):84-89.
⑧孔明安.從物的消費到符號消費——鮑德里亞的消費文化理論研究[J].哲學研究,2002(11):68-74+80.
⑨劉明昊.“梗文化”到底是什么文化[J].創作評譚,2021(02):30-33.
⑩王霜奉.我的“梗”,你能“get”嗎?[J].上海信息化,2020(09):49-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