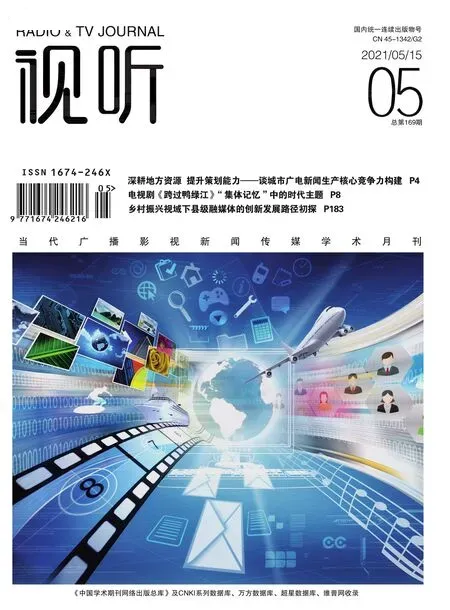官方媒體時政新聞親近性轉向研究——以央視新聞B站短視頻新聞實踐為例
□ 何東穎 劉 祎
在輿論引導工作要求下,為了在新媒體環境下維系宣傳體系,官方媒體傳播范式開始背離傳統宣傳主義,建構了一種吸納專業主義、煽情主義等不同范式元素的雜糅化形態①。隨著網絡技術的變革,傳統媒體改革逐漸深化,作為內容承載體的新興短視頻平臺成為傳統媒體變革的又一關鍵切入點。官方媒體作為輿論引導的主導力量同樣加入了新聞短視頻戰場,尋求與社交媒體平臺的深度融合。以人民日報、央視新聞為代表的主流媒體陸續進駐抖音和嗶哩嗶哩等視頻平臺,補全了官方媒體社交媒體矩陣中的視頻板塊。視頻媒介形式本身具有更強的包容性與接近性,相較于之前的文本,體現出親近性的不同面向。
親近性新聞(intimate journalism)的概念起源于上世紀90年代的新聞實踐,它強調對普通人日常心理與生活的記錄,倡導對平民化報道的實踐經驗總結。作為新聞實踐的親近性新聞是對“新新聞主義”的進一步發展,主要表現為題材選取的平民化與記者介入的理性化②。作為新聞價值的親近性則是接近性在心理上的深化與延伸,報道的關注點從新聞本身轉向關注新聞中信息與人的關系,以及受眾在情感、認知、信仰等方面的心理認同③。從具體文本分析來看,親近性指的是文本的表達方式與文化解讀者的符號表達方式、思維方式、解讀心理、時空相一致④。
一、官方媒體時政新聞的親近性轉向
(一)敘事情感化:從告知到講述
與傳統電視新聞相比,短視頻新聞憑借平臺特質打破了組織生產限制和政治符號限制,實現了從告知向講述的轉向。由于短視頻新聞是官方媒體的革新嘗試,媒介內部的生產限制得以打破,其作為主體電視節目附屬補充的角色同樣免除了官方媒體的政治符號屬性。
以《主播說聯播》欄目為例,主持人以口述、點評、呼告等方式進行報道或點評,呈現出情感化和傾向性特點。例如在母親節當天推出的視頻中,新聞聯播主持人海霞紅著眼圈講述了李靜芝母子通過央視認親大會成功團聚的故事,其中包括大量的情緒表達、個體感受與價值評價,如“我也是一個母親,李靜芝這些年的錐心之痛,對我來說恐怕連想都不敢想”。與傳統新聞客觀性報道規范所要求的“新聞與評論分離”不同,短視頻新聞允許甚至促成個人情感與價值的介入。
從敘事框架來看,短視頻新聞采用“宏大敘事下的個體情感”架構,將小人物的情感和利益與宏大的國家利益和布局聯系在一起。例如在5月20日推送的“有愛的日子不僅是你儂我儂,更是家國平安”中,敘事邏輯將個體婚戀圓滿引向疫情下的家國團結。從敘事文本來看,短視頻新聞吸納非正式語匯與網絡熱詞,實現語言上的親近性。例如報道北京新發地疫情的視頻名稱為“熱干面挺過來了,炸醬面也會好起來的”,在報道長征五號運載火箭首飛成功時將其描述為“胖五”“刷了個大火箭”“V5”。
(二)媒體人格化:從媒體品牌到個人品牌
廣電媒體在視頻制作方面具有天然優勢,但其源媒體特征仍然突出,新聞短視頻中主持人的存在感也仍然較強⑤。《新聞聯播》長期以來作為政治性儀式存在,主播作為節目的發聲者也被附著了濃厚的符號色彩。央視主播在外形(視覺符號)和聲音(聽覺符號)的塑造上力求純正完美,但隨著傳統媒體改革和短視頻新聞實踐深化,作為“門面”的央視主播開始走下神壇,從精英化、去情緒化、去個性化的靜態形象轉變為網紅化的、可接近的、人性化的動態形象,從“聲音傳遞者”變成了“聲音發出者”⑥。
《主播說聯播》欄目從立意上就凸顯了主播的個人價值判斷,將受眾感知的“發聲者”從宏觀的國家體制縮小到具體講話者,從最直觀的標題設置上突出主播的發聲者姿態,如“康輝為美國某些議員補課”。在短視頻中,央視主播從語言符號到非語言符號都突破了程式化限制。在語言符號上,口語化敘事、情緒化表達和網絡詞匯得到大量使用;在非語言符號上,主播擁有豐富的肢體語言,如點贊、攤手、搖頭等動作,隨著具體新聞內容的變化,主播的聲調與情感也會相應改變。通過這種形式,受眾在觀看過程中仿佛置身對話環境,主播所傳達的國家意識形態則被看作講話者的個人化觀點。
在接近性上,央視主播的曝光也不再囿于新聞節目。2019年11月推出的“康輝Vlog”集中體現了央視對個人品牌的打造,在評論中有網友戲稱“第一次看到康輝腰部以下”并獲得了四萬多的點贊,排在第一位,這充分說明了此前央視主播印象塑造的刻板化與模式化。在破除符號化形象之外,央視新聞還借用了飯圈話語,將康輝與朱廣權、撒貝寧等人氣主持人稱為“央視Boys”,塑造社交媒體上的“網紅”主播。通過這種形式,媒體被賦予了人格化的特點,擬人化的傳播促進了傳受關系的平等,央視主播、外交部發言人等個體元素共同構成了媒體的性格特質。這是央視新聞親近性轉向的重要一步,也是媒體品牌向個人品牌轉變的過程。
(三)后臺透明化:從中心到邊緣
電子媒介融合了不同的媒介場景,為了解釋場景融合后交往行為的折衷風格,在“前臺”“后臺”的概念基礎上,梅羅維茨將場景混合之后在新場景中產生的新行為稱為“側臺/中區行為”⑦。
從2019年底“康輝Vlog”推出以來,央視新聞已經將Vlog作為常規化的短視頻新聞報道形式,在后續的兩會報道、疫情報道里都廣泛采用。目前央視新聞的Vlog主要分為兩類:一種是新聞工作人員記錄自己的日常工作,表現了生產后臺的透明化;另一種是記者探訪采訪對象的日常生活,體現了內容后臺的透明化。對新聞內容后臺的揭露強化了新聞的真實性和可信度,對中心議題的側重是由重要性和顯著性決定的,但相比于宏觀的新聞價值,具有接近性的邊緣議題往往更加接近生活,增強了新聞的真實性和可信度。
(四)平臺接近性:從媒體中心到受眾中心
短視頻形態本身具有很強的平臺依附性,B站作為網絡青年亞文化社群,從符號意義上來講與主流文化相對。官方媒體入駐B站,不僅完成了對青年亞文化的收編,也實現了官方媒體的形象重塑。由于短視頻的平臺依附性,B站的平臺屬性、社區文化構建了央視新聞短視頻新聞創作的底層邏輯。B站的社交媒體平臺定位及其獨特的彈幕文化確定了平臺視頻的社交屬性,這就決定了央視新聞短視頻更多是以平等的對話姿態呈現,并且具有一定的互動性。從社區文化來看,B站具有顯著的青年亞文化屬性,央視新聞也進行了迎合,例如嘻哈文化視頻“朱廣權新rap央視新聞來B站了”。
B站的文化與規則是用戶和受眾在長期的亞文化實踐中形成的,央視新聞對B站的依附實際上是對受眾習慣與喜好的接近與迎合。此外,主流媒體對亞文化社群的收編行為本身就是親近性轉向中的關鍵一環。從引導公眾接收主流話語、接受官方媒體,到主動迎合網絡話語、接觸網絡文化和社區,央視新聞通過平臺的接近實現了由媒介中心到受眾中心的轉向。
二、官方媒體時政新聞親近性轉向的效果
如果從國家意識形態領導的要求來看,官方媒體時政新聞的親近性轉向無疑是成功的。首先,入駐視頻和亞文化平臺的行為本身就代表著親近性轉向,有助于擴大受眾范圍;其次,短視頻與文字相比是一種無門檻的閱讀方式,將時政新聞以可視化、流行化的形式推送則降低了閱讀和理解門檻,激發了公眾對嚴肅時政新聞的興趣;最后,雖然這種親近性本質上是葛蘭西文化霸權的一種體現,是官方話語向民間話語做出的某種程度的妥協,但是央視新聞在B站400多萬的粉絲數量證明其傳播效果的成功。不過這種親近性轉向也可能會造成一些問題。
(一)嚴肅議題娛樂化與碎片化
短視頻的時長限制、移動觀看的媒介特質決定了傳播形式的輕松化和娛樂化。央視新聞是中央廣播電視總臺的主要新聞播送窗口,時政新聞是其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央視新聞的適應性調整易造成嚴肅議題的娛樂化與碎片化。這種片段式、碎片化的時政新聞無法幫助公眾深入了解事情全貌,最后只能淺嘗輒止、浮于表面。
(二)親近性無法完全替代公信力
公信力是媒體通過長期新聞傳播實踐與受眾和社會建立起的信任關系,媒體的公信力應當來自于其生產的新聞產品。在親近性路線下,受眾不再關心新聞的內容,而是關注媒體以何種形式進行呈現。媒體對受眾閱聽心理的迎合無法從根本上獲得公眾信任與媒體公信力,只能獲取暫時的、情緒化的反向接近。此外,央視新聞的短視頻中出現了大量帶有強烈傾向性、觀點性的內容,這反而會對公信力造成削弱。
(三)迎合網絡民族主義思潮加劇意識形態極化
近年來,文化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極化呈現加劇趨勢,在網絡民族主義的社會思潮和官方宣傳的“大國崛起”敘事下,網絡空間面臨進一步撕裂的風險。“大國崛起”敘事是當下意識形態宣傳的主導框架,它迎合了民族主義者的想象與偏好。央視新聞短視頻中存在大量以“大國崛起”為母題框架的內容,雖然這是由國家整體宣傳話語和其官方主流媒體定位決定的,但短視頻因為時間限制只能呈現部分事實,大部分新聞背景都被省略,只保留了事件沖突或高潮。“聽說你們愛看‘外交天團’?趙立堅40秒高能限定”等視頻就充分體現了這一點,視頻只剪輯了外交部發言人的強硬回擊合集,但沒有針對具體事件,也沒有交代發言背景。這類短視頻共同形成了官方話語的“爽”文化,迎合了網絡民族主義思潮,助長了網絡空間“后真相”風氣。
注釋:
①龍強,李艷紅.從宣傳到霸權:社交媒體時代“新黨媒”的傳播模式[J].國際新聞界,2017(02):52-65.
②吳飛,盧艷.“親近性新聞”:公民化轉型中的新聞理論與實踐[J].新聞記者,2007(11):52-55.
③易艷剛.“后真相時代”新聞價值的標準之變——以“羅爾事件”為例[J].青年記者,2017(04):17-19.
④楊保軍.創制親近性文本:跨文化有效傳播的重要基礎[J].國際新聞界,2001(06):59-63.
⑤殷樂,高慧敏.傳統媒體新聞短視頻發展現狀與傳播態勢[J].當代傳播,2018(06):45-50.
⑥周勇,黃雅蘭.《新聞聯播》:從信息媒介到政治儀式的回歸[J].國際新聞界,2015(11):105-124.
⑦劉娜,梁瀟.媒介環境學視閾下Vlog的行為呈現與社會互動新思考[J].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19(11):47-54.